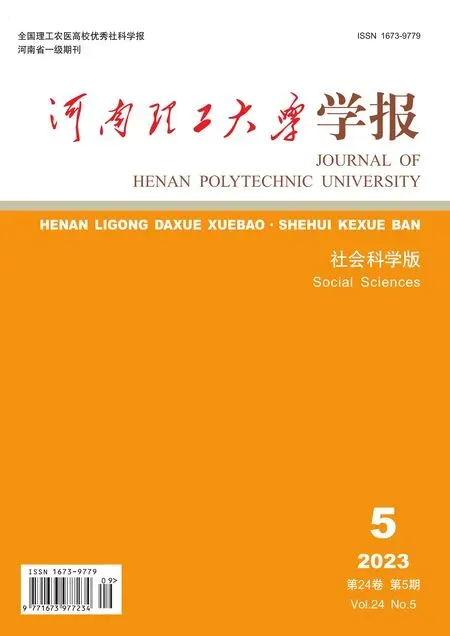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接榫:教育管理思想的本土挖掘与发展
肖建国,李雨豪
(1.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2.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一直以来,受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影响,中国教育管理研究一直在西方教育管理范式内发展。如何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是专家与学者必须直面和思考的问题。正如褚宏启教授所指出的一样,“我们要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我国教育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体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能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的理论。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是西方框架与话语的殖民地,我们需要好好梳理我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知识。同时,我们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管理现实。教育管理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与润泽,理论需要实践的滋养与检验,二者之间需要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在持续健康的互动过程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和进步[1]。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卓有成效的、积极的、具有现实价值和启示作用的教育管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向深度发展、向内涵式跨越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教育管理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采取何种管理理念和价值取向,这与教育管理者所具备的理论认知和文化涵养是一致的。本文基于孔子“礼”的思想,阐发孔子“以礼约人,以仁化心”的传统教育管理思想,从中一窥中国传统教育管理思想的精道之处,为教育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生成提供经验启示。
一、传统教育管理思想注重以人为本
传统教育管理思想注重以人为本,这主要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教育管理思想中。传统教育管理的形式依托“礼”,通过“礼”的约束与规范在教育管理中贯彻以仁爱为核心的育人观念。在此基础上,传统教育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将“礼”与“仁”相互融合,以礼育仁、以仁行理,将受教育者作为“礼”与“仁”相互作用下成全的对象。
(一)“礼”为形式,仁爱为本
教育管理实践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过程。在教育管理的师生范畴下,教师或学生都是以人这一独立个体形式存在,只是在具体的角色上有不同的分工,因此,师生之间的交往互动必须遵循角色名分所规定的伦理准则,各司其职。将“礼”放在教育管理的师生层面首先就是确定师生间的伦理名分,何以为师与何以为学生,只有确定了彼此的角色名分才能更好地按照制度、规范做事,就是要求在师生间形成一种师之为师、生之为生且“以礼及仁”的师生伦理制度,这样才能使得师生之间形成和谐的秩序,也才能各行其是,也各得其所。这也符合韦恩·塞西尔的观点:学生与教师带着他们个人的需要、目标和信念、确立自己的个人发展取向,理性地理解自己的角色[2],“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则须要明确自己该有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地履行所应遵守的规范,这恰好契合孔子“以约失之者鲜矣”的观点,在教育管理中如果以符合“礼”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就很少会出现错误,师生间也就和谐了。因此,教师应该履行其管理育人的职责,恪尽职守;学生同样应该遵规守纪,敬重师长,当师生间都遵守和遵循了名分所赋予的职责后,师生间的教育管理自然就处于应有的符合规范的秩序上。
“礼”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时代巨变与社会失序,孔子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展,越发向人文性和道德性趋势转向。孔子的“礼”主要是体现在其作为制度的内涵意义上,落脚于对人道德层面的约制与教化,用符合“礼”的规范与制度来约束人的不合规范、超出本位的行为,达到一种趋近于“仁”的状态,最终使社会有序和谐。孔子保留了春秋早期的文化思想,在“礼”的框架中定义“仁”[3]。孔子的“礼”是具有道德精神与价值取向的“礼”,目的是在“仁”的基础上重建以“礼”为用的秩序与伦理,指个人需要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望以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这也正是孔子所主张的用“礼”作为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孔子更是把“礼”视为每个社会成员均应该遵守礼仪规范,君要以“礼”待臣、臣要以“礼”侍君、百姓要以“礼”待人,才能使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和谐状态中。“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中所表达的观点就是约束的“礼”必须要具备“仁”的基础才可以,否则“礼”就会成为简单约束人的规范而不是服务和谐社会的道德范式。从“仁”的角度审视就是不合乎“礼”的,不能够被接受,也不可以做,否则就无法达到“仁”的标准。在师生范畴下的教育管理实践,无论是教师或是学生都应该从人这一本质属性出发,才符合“仁”的伦理准则。因为,教师面对的是准备接受教育的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教师的角色定位是育人者,即便是管理也是把育人作为最终目标,超越教师的角色范畴,如果将自己视为简单的管理者而抛弃教师这一本位角色,那么所谓的教育管理就会是施暴、诘责甚至是侮辱,并不具备育人的意义。从教育管理师生视角审视“礼”,“礼”是以一种规范制度形式存在,功能是起到约束与引领的制约作用。“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是人与人交往间该遵循的伦理原则。因此,孔子用“礼”的制度规范来教育管理学生,使学生能够知礼、明礼、用礼,就是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遵守自己该遵循的规范。
孔子将“礼”上升到道德精神层面,目的是通过“礼”这一“约人”形式来达到“仁”这一“化心”目标,注重的是对受约制的人的道德引领与人格培养。孔子以“礼”约人的终极目标是在社会化情境下得以实现,最终达到整个社会能明礼、尊礼、用礼,保持安定和谐的道德精神和伦理秩序。“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与人相亲,孔子认为人最本真的存在就是“仁”[4];而且“仁”发端于“以其中心与人交”,就是对人的亲近感,从亲近感出发,发展为“爱”,而爱亲、爱人就是“仁”[4]。“‘育人’所 追求的首先是将学生当作‘人’来看待,并将其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合格成员。”[5]“子曰:‘仁者,人也’”,以“仁”为本要求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教师应本着人之为人的人本主义理念,充分认同与照顾学生的心理感受,关注学生所具备的道德提升与人格发展诉求,既要“礼”的约束,又要“仁”的化育。因此,“礼”的前提是教师要怀德,管理的出发点是学生“仁”,这也可以解释孔子以“礼”约人目的是使学生明了善与恶,好与坏,这是在“礼”约之后,学生内在生成的最终结果。在用“礼”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引导学生的同时,必须将“爱人”“亲民”的“仁”的品德内化为学生修养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在培养学生知礼、懂礼、约之以礼的行为规范的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礼”与“仁”共同作用培养“成人”
孔子的“礼”具有道德性倾向,突出其具备的道德精神,“礼”与“仁”是相协而存,彼此融通。孔子运用“礼”来管理与规范学生的行为,帮助学生消减道德品性中的不足与缺欠。“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从孔子的思想可以看出,恭、慎、勇、直都是值得肯定的德性,也是现在学生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但是,如果没有“礼”的规范约制,就会劳而无功、胆小怕事、滋生祸乱、尖刻伤人的不良后果,这也同样是现代学生道德培养中,所必须要警惕和尽量使学生避免的负面效应。说明学生即便具备先天优良品质,但是如果脱离了“礼”的规范也会最终走向对立面,只有借助“礼”约身这一外在条件的施加,最后才能实现“仁”化心这一内在效果。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两者的成全是相辅相成、一里一表,相互成就,“仁”的实现是无法离开“礼”的规范与制约;同样,礼的约束必须具备道德层面上“仁”的价值取向,孔子的“礼”是以“礼”约人,但是必须在“仁”的范畴下才可以。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不仅仅是用“礼”的规章制度限制,而应该使学生在懂得“礼”,在仁爱的基础上展开的,使学生在被约制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内心道德精神的浸润。马斯洛认为人具备一种需求不断提升的动机层次模式,在这一层次结构中共分五个层次,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开始,逐渐提升需求层次,第二层次的需求是安全需求的;继而是归属,爱和社会需要;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最后是自我实现[2]。孔子以“礼”为用,约人化心的教育管理思想,更集中地表达了从第四层次开始的“尊重需要”,特别是学生在被教师管理约束的过程中,内在心理需求趋向一定表现为对被尊重的期待与渴望。教师在面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中,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的“管理”,用一种严肃而具有威慑性的制度、手段、形式使学生产生恐惧,害怕再次出现问题后的惩罚。但是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的目的,最后仍然要落实到育人这一根本取向上,育“成人”,使之人之为人,这不仅是外在行为的合乎规范制度,更在于内在品德的陶冶与生成。这要判断教师是出于何种伦理原则去设定教育管理的动机及与之适应的手段形式,如果教师仅是以常规的制约来平息出现的不遵守规章和扰乱秩序的情况,那就只能是一种机械性的惩罚,而没有实际的道德引导意义,甚至这一管理行为产生的结果就是师生关系的恶化与对立,即便有效,也只起到约束的外部作用,而没有产生对内在品质道德提升的一种积极作用。从“礼”与“仁”的关系来看,简单形式的体罚、侮辱都不具有“仁”的道德精神与内涵,仅仅体现的是机械性的管理。教育管理中,如果作为约束的规范制度和行为自身没有一种道德情感的承载,没有道德价值的取向,就失去了教育管理的意义,只能得到一种有违期待的结果,那就是“民免而无耻”,而在教育管理没有触及到的地方,违反制度的情形会更加严重。
因此,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中,用“礼”这一规范制度来达到约束学生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礼”的规范与约束必须具备“仁”这一道德内涵,也就是说,“仁”必须统摄“礼”,“礼”的运用也必须在“仁”的框架范围内得以实现,否则就会是不“仁”。
孔子以“礼”约人,以“仁”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出发点是人之为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但是着落在道德精神、人格品质上,在于培养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维护社会的制度规范和伦理秩序。这一过程中化育的完美人格并不仅仅是持有和赞同善与美的道德精神,更是有完美人格的人知道善与美是什么,懂得欣赏善与美,并将善念付诸于实践[6]。孔子将学生视为“成人”过程中的一个生命个体,以“礼”约制学生,目的是使学生明礼、知礼,成就的是最终能够修己安人的理想目标。孔子以“礼”为用,以“仁”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也是一个塑造“成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在成长需求得到不断满足后的一种积极的上升趋势,以“礼”做约制,以“仁”来做保障,一表一里,互为协同,成就的是人不断向“成人”的迈进。孔子的教育管理中的“礼”与“仁”的关系,是管之“礼”基于“仁”之本这一伦理原则发生的,对于师生间的教育管理来说,教师用管理的方式使学生明“礼”目的是育其成人,因此,这一连续的教育管理过程中,“礼”与“仁”相互成全,互为补充,不可或缺,用“礼”约制引领学生和以“仁”化学生内心是一个共存共融过程,是同时或是瞬时发生的状态,是由外及内,浸润陶冶地塑造“成人”的过程。
二、传统教育管理实践中的三重维度
传统教育管理实践立足于社会秩序稳定之上,促进社会和谐统一,这就要求教育管理的对象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正面积极状态将所学以一种合规律性的行为方式彰显,而教育管理又要通过一种富有人文色彩的形式反观教育对象促成其与社会的同步。因而传统教育管理实践表现为三种维度,要求依“礼”使学生立于社会,突出道德使学生内外兼修并培养审美情趣提升管理境界。
(一)依“礼”使学生立于社会
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实践,首先是“礼”对学生的约束与引导作用,“不学礼,无以立。”唯有学“礼”,方能自“立”,在此,立于“礼”成于社会,指出以“礼”约人的教育管理目标不仅具备现实性也具备未来性,约在此时,立于彼时。孔子认为通过“礼”的规范才可以培养出社会所用的人才,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各司其职的和谐状态。颜回所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中,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在教育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用符合“礼”的规范、礼仪来约制引导学生,使学生在获得“文”的同时更要知“礼”明节。这是孔子育人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教育与管理是合二为一的,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孔子对人的认知使其明白教育就是一个使学生“成人”的过程。一个人只有成为一个仁、智、勇、礼、乐、艺得以满全的“完人”,才能在社会中肩负安人、济世的时代使命。培养“成人”落实到教育上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人格全面的“完人”,而回到人格培养中,学生如果没有“礼”的约束与引导,将必然出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样“无以立”的结果说明,教育管理中,仍然要突出对学生以“礼”进行教育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孔子的“礼”不仅是内在的伦理认知同时也是外在行为的道德准则,在具体的做法上,孔子认为应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礼”的约束可以使学生认识并掌握“礼”。在用“礼”的尺度与分寸上,孔子所提倡的是制造和谐的人际氛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以“礼”约人的教育管理实践过程中,这种以“和”为实践准则的教育管理充分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本思想,突出“和为贵”的“礼”是“仁”的外在形式,是教育管理的道德准则,是规范学生行为的伦理标准,当然,以“仁”为本的“礼”最终将成为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在教育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如何做到“约人化心”,以“礼”为用是孔子最依赖的方法。
(二)突出道德使学生内外兼修
孔子始终强调修己,因此,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行为是手段,实现化育人心才是最终目的。孔子代表的儒家把“礼”更加道德化,突出其道德精神,当然也致力于保持礼以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包含着要把“礼”变成德的倾向[3]。孔子尚“德”,提出“道之以德”,就是在对人的教育管理中必须具备德的价值内涵,不能脱离道德精神而仅仅停留在规范制约这一简单的手段上。孔子认同“齐之以礼”,即以“礼”为规范行为的外在控制,但注重内在道德提升才是核心,所推崇的教育管理是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制约,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齐之以礼”与“道之以德”的教育管理实践形式互为表里,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用道德来引导、感化,再用“礼”来规范,学生就会心归“德”、行近“礼”;反之,教师用严苛的规章制度约束,不加区分地惩戒,训罚学生,学生表面屈服,但内心抵触逆反,反而会引起师生间的矛盾与冲突。学生对教师公然抵触反抗,在师道尊严、道德人伦至尚的先古时代不太可能出现,但现代社会,随着人性的解放,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社会环境的熏染下,就难免会给师生关系带来各种问题与冲突。
“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言传身教、行为规范的榜样作用。”[7]“道之以德”的首要条件是教师要怀德,才能做到以“德”服人,这就要求作为管理者的教师必须通过自身的道德自省和伦理自律来起到示范的作用,以一种具有引领性的道德行为使学生将尊礼、明礼的价值认知与行动准则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这是注重内在约制与管控的教育管理方法,集中体现了孔子以“礼”为用,以“仁”为本,育人化心的教育管理思想。“齐之以礼”在教育管理中就是用符合“礼”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学生的内心思想、言谈举止,做到合“礼”。“齐之以礼”是管理与自主管理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教师约束学生,形成依“礼”行动的道德自觉。“德”“礼”同时发挥作用影响学生的认知,与受认知支配的行为并建构起符合“德”“礼”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可以说,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育管理思想就是主张管理学生必须注重内外同时作用,以“礼”约之同时还要用“德”润之才可能达到教育管理的理想目标。
(三)培养审美情趣提升管理境界
孔子认为仅仅是“立于礼”不足以实现“成人”之教育理想,因为人的人格满全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人的情感意识、审美情趣上同样要得到陶冶与熏陶。因此,必须要进行“成于乐”的人格陶冶与审美情趣的提升,才能塑造“修己安人”的合格人才。孔子的教育管理思想中“乐”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不但要以“礼”约人,还要用“乐”来成就学生的情感意识和审美能力。“乐”可以使学生的思想道德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主张的“乐”并不单纯指音乐弹唱之能力,更是透过音乐后的乐理,对学生进行审美情趣培养,在培养学生艺术美感的同时,达成一种无形的约束,一种内心修为,促使学生的性情,心性都归于恬静,以一种更加理性、平和且有审美感的态度看待规范与制度,更高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于乐”其实培养的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控力。
孔子“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道出了“礼”“乐”的教育管理层次问题,将“乐”的功能上升到实现人格满全的高度。儒家的教育管理思想始终是将核心放在如何实现人的“修己济世”之根上,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合乎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礼”必须发挥作用,但是,思想的净化与陶冶,必须有“乐”来成就,即一个成人不能缺少审美情趣,否则无法欣赏美,也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礼”层面实现的是对学生行为规范,接人处事之伦理道德;而“乐”则实现的是对精神境界的进一步提升,是一种情绪与审美力的管理,礼乐融通之际,教育管理也实现了一种层次的跃升,将外在约人的实践上升到内在的精神境界层面。
总之,孔子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实践,从外入内,由内生发,不仅是以“礼”约人,还要使人具备伦理美德与高尚情操,注重的是化育“成人”的过程。因此,教育管理中“礼”用都是在“仁”这一伦理准则统领之下,时刻不能脱离“仁”而单独存在。用“礼”来管理学生,是方法手段,孔子要学生经过“礼”教后实现“仁”的理想状态,通过“礼”的践行达到社会和谐。
三、对现代的启示
孔子把人类视为一个大生命,认为人类的大生命就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个大生命的本质就是“仁”,因此,一个仁者要从人类的高度感受一切,理解一切,对待一切,这样人类才能存在与发展[4]。而且人肩负超越“小我”的社会使命,要通过内在的修为生发成积极践行使命的“大我”,突出的是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孔子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思想本质是以“仁”为本,“仁”“礼”相协,修己弘毅,化育“成人”,最终实现安人济世的理想。因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最重的特色不在知识,而在力行[8],这说明孔子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哲学。梁启超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修身这一层面,不具有时代性限制。新时代中国教育实践可以从中汲取精粹,用以凝练新时代中国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具有启发性、建设性意义的思想。
(一)教育管理的本真追求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师生关系
师生范畴下的教育管理应是教育与管理融合共生的整体,不可拆分后简单视作教育与管理的交叉。如果用简单意义上的“礼”,也就是制度、规章约人,那就是一种扭曲禁锢为主的“礼教”,禁锢意义明显,预设的管理结果或许可以达到,但是教育管理效能值必然是负向趋势。因为,单纯约制的管理思维或是模式能够具有短期的效果,但不具有又好、又科学的可持续性特质。教育管理中没有教育内涵和意义的管理是不能被称为教育管理的。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如果没有一种道德情感的承载,没有道德价值的取向,就失去了教育管理的意义,只能得到一种不被期待的结果,即“民免而无耻”,而在管理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学生违反规范制度的情形会更加严重。
在教育管理中,教育惩戒是一种必要的补偿,但是必须是以教化这一价值选择为根本,以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以“爱之深”为内涵,才产生“责之切”的外延,否则仅仅是惩戒,而脱离教育管理的伦理准则和学生所能承受的程度限度之外的惩戒,就失去了孔子所主张的“约身化心”以“礼”为用、以“仁”为本的教育管理核心思想,制造的也许是顺从,但更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反抗与对立,这也是在教育管理中,师生间关系僵化紧张的原因之一。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使教师具备运用权力的权威,但是教师运用权力的前提是“使权力的运用变成‘正确的与适合的’的时候,权威就产生了”[2]。当前,师生间关系失序的问题,特别是暴力的冲突,大部分就是教师仅运用简单化的惩戒,而没有考虑学生的身心接受限度。因此,教育管理中的惩戒必须具备“仁爱”这一价值内涵,否则就仅仅是一种惩罚而已,起不到教育管理的作用,没有制度规范的约束,教育管理无法实现,但是离开对学生的仁爱的教育管理也是形式化,空洞的。惩戒是一种约制和教育引导,目的是避免再次出现可能的违反常规的情况,这是与体罚、变相体罚有本质区别的,惩戒的目的是教育,在约身的同时注重的是化心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学生感受到痛苦而屈服的体罚。孔子的“礼”用“仁”本思想,并不排斥惩戒,但是会绝对反对体罚的简单粗暴式的体罚式教育管理,因此,教育管理可以在“仁爱”基础上惩戒。
孔子思想中人的德性结构核心是“仁”,教育管理指向人,人是教育管理的切入点也是落脚点,实现教育管理这一过程中“仁”生成的根本准则就是“礼”具备“仁”的道德意义与承载,凝练后就是“礼”用“仁”本,“礼”应载“仁”。教师能够成为以“礼”约人的教育管理者必须也同时成为一个示范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教师个人都无法到的规范和要求,就不可以成为管理学生的制度,教师明“礼”之用,也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这是教师成为管理者的前提条件,否则约制学生的规范就会是一种“反噬”力量,不仅不会有期待的作用,还会向相反方向发展。在教育管理中,“礼”约的同时,用“仁”来统领,还具有另一层意义,就是避免出现教师的情绪化管理冲动。因为,在教学、工作、竞争、生活的压力下,面对学生出现的状况,教师的情绪化管理就可能无法避免,而师生间关系紧张、伦理失序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教育管理中,教师的行为往往忽略自身所扮演的教师角色,忽视了教育管理制度规范的公平与正义,仅仅以管理者自居,结果必然是反向的。从这一点来辨析,教师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仁”的品质才能做到以“礼”约人。简单的体罚、约束都是没有“仁”的简单粗暴的机械形式,仅仅体现的是工具性管理思维,没有实际的道德引导的意义,甚至这一方式产生的结果就是师生关系的恶化与对立,只起到了约束的外部作用,而没有对内在的品质道德养成的一种积极的作用。
孔子“礼”的教育管理思想核心是“仁”为根本,“礼”用可以载“仁”,现代的教育管理应该是一种体现人性关怀,具有仁爱特质的制约与规范,体现出对学生的成长、成人的关注与关爱,仅仅是僵化的,没有人情味的规范制度,只讲管理,只讲绝对权威,师生间的关系将会无法调和,自然出现当下师生关系紧张的问题。约之以“礼”的前提是要有爱人之“仁”,制度规范是一个可以承载着仁爱的制度,不论是规章制度的设计还是执行都要将学生这一具有人这一属性的个体的“成人”放在第一位,才会发挥“礼”作为制度规范应有的作用。真正的教育管理不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制住学生的身体与行动,而应该是在内心层面起到了多大的化育引领与道德提升作用。反之,再严苛或是简单有效的管理,仅仅是产生畏惧,并不能使学生内心真正的诚服,所以,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要突出以“仁”本的价值取向,这应是教育管理中最为本真的追求。
(二)教育管理应落脚于学生道德精神引领
孔子的“礼”,已经超越了春秋早期的礼治范畴,将其上升到道德层次,遵守制度,规范,其实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使社会回到一种秩序井然的和谐状态,各安其事,使社会可以按照伦理原则运行。从这一角度审视孔子的“礼”其实是一种美德,是具备道德精神和崇高追求的伦理准则,这也同时是“礼”的一个功能,即是作为个人修身的创造性智慧的具体化手段[9]。孔子的“礼”落脚于社会关系层面,已经上升到社会文明的层次,必须要直面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大的社会图谱问题。因此,“礼”这一看似个人身体力行的行为伦理准则,实则应成为社会道德的调节器和稳定器。教育管理中的以“礼”约人关键要做到爱人,要爱护自己的学生,爱护自己面对的人,以推己及人的观念践行教育管理实践活动。师生间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互动过程中,能否实现各得其所,需要“礼”这一伦理准则作为师生关系的稳定器。以“礼”为用的教育管理,彼此都按各自名分所赋予的职责行事,都做到各自该做的符合伦理之本的行为,那师生间关系就会和谐有序;否则,矛盾与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不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矛盾,都是破坏师生间关系稳定的导火索。
不论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衡量,还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判断,人必然会成为社会人,而社会生活的成败,取决于人格是否完备,人格不完备必然导致的是社会生存能力不足。“礼”的目的是治人情,修人义[10],“礼”把文明人与野蛮人区分开来[11],若“不学礼”就会使很多学生出现虽接受了较高层次教育,但在社会上,在生活中“无以立”的尴尬局面。如何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完备的人,是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教育管理不在学业知识层面上育人,但是在道德意识、精神境界层面起到净化、提升、引领的作用。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应摒弃“一俊遮百丑”的固化思维,从紧盯学生学业水平这一方面,回到育人成才的“成人”教育上,育人化心的教育管理实践取向上,不仅要培养学生具备生存的能力,更应注重内在品质德行的塑造。
人性假设以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相对于其他管理,教育管理模式虽以人为主体,从属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但是其不仅作用于人身还直接影响人心[12]。教育管理中的人性管理,管理外在行为,但效果都是由内而生,教育管理的实质应该是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化育人的思想意识、态度、认知。现代的教育管理实践必须是在教育基础上的管理,如果没有教育这一前置性价值引领与约束,教育管理是不具备合理性的,如果不存在教育价值与意义,管理的行动预设就是错误的,那么,管理的结果就必定是无效的,甚至是可能起到反向效果。“礼”作为教育管理的制度规范,不仅为了约束学生而存在,而是为了化育学生,价值在于能够起到“仁”的道德精神作用。然而,现行教育管理实践中,约束管制这一单一功能仍然突出,以道德精神作为引领的实践取向上仍然欠缺。
(三)新时代教育发展必须挖掘传统智慧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文化发展层面的代价就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疏离倾向外显化,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与传统文化的剥离在加剧,渐行渐远趋势愈加明显。漠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向西方的价值认知靠拢,将效率、价值作为直接目标;效益至上、利益为本的思潮,在大力发展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是却在不断的冲击我们的道德底线。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愈发“现代化”的同时,曾经引以为傲、孕育中华智慧的一片文化沃土被闲置,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落荒地”,即便是偶有打理,也不被深耕,立意虽高但却曲高和寡。同时,由于没有西方价值认知、宗教文化、人文根基,必然导致当前道德下行的现状,在被西方先进文明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认知混沌与思想迷茫成为挥之不去的文化窘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文化再次崛起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我们更该“精耕细作”这片文化沃土,才能真正发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精髓,在“损”“益”之间实现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涅槃重生。孔子“以礼为用,以仁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仁”的道德精神统摄下,通过“礼”的规范与引领,使学生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兼济天下的“君子”使命,“君子”“尊礼怀仁”,才能实现由“内圣”到“外王”的过程性发展。孔子教育管理着眼于人,以人为中心,管理前提是人之为人的人本主义,管理方式是“约人”,管理本质是“化心”,管理目标是“修己安人”。孔子“礼”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礼”的约束与规范,最终实现人之为人的“仁”的德性境界,将其放在现代中国教育管理中仍然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管理理念。因此,孔子“以礼为用,以仁为本”的教育管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深入挖掘孔子的教育管理思想可以为教育管理本土化生成提供有益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教育应该实现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要具备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这不仅可以彰显民族自信,更能够成为一种可以具备感召力、引领力的时代性全球化文化潮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社会科学有一种对传统无视的价值与行动趋向,很多社会科学家接受进步主义观点,于是产生了厌恶传统把传统视为落后甚至是反动。正因为如此,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受现代社会科学者待见。当前,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善待。但是,李泽厚教授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已经无孔不入地深入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已经是中国人自觉与不自觉地处理事务所遵循的原则。不论我们承认与否,这种行为伦理准则已经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只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并没有意识到而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将民族内涵放在重要位置,必须运用中国自己的传统智慧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