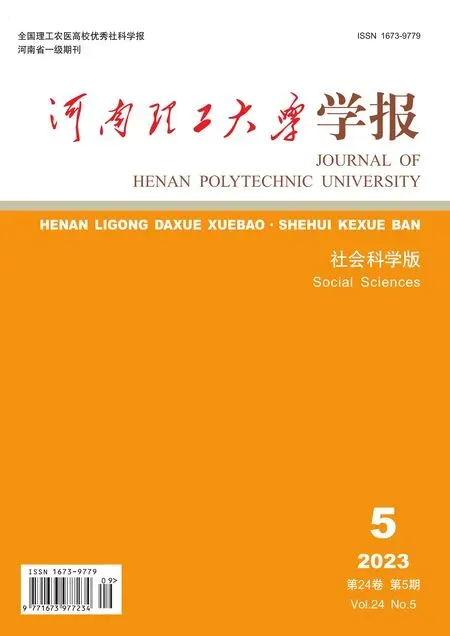《楚游日记》所见明末湘南盗匪研究
牛 浪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曾有人赞誉“是南方社会最直接、最真实、最生动的记载,可说是一部游史,一部当之无愧的信史”[1]。细读《徐霞客游记》中的《楚游日记》(以下简称《游记》),发现《游记》保存了诸多湘南盗匪的史料,涉及盗匪来源构成、时空活动等内容。目前只有王雅红[2]、蒋乾[3]、马核[4]指出湘南存在匪患,但未分析匪患原因及影响。唐立宗[5]、贺喜[6]在研究明清湘南矿区与地方社会时,亦提及湘南盗匪,但未对湘南盗匪进行研究,本文以《楚游日记》中的盗匪为例,欲从侧面反映明末湘南地区的社会现状。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十一日,徐霞客自江西永新县进入楚地,同年闰四月初七日离开,在楚历时115天。楚游期间,徐霞客于茶陵州登上云阳山,又钻入被村民视为神异的麻叶洞;于衡山县抵南岳庙,北游水帘洞,游览衡山各景;于衡州府游览石鼓山、回雁峰,二月十一日乘船自湘江前往广西。然而,至衡阳新塘站遇盗,行囊被烧,所带旅资分文不存,随行的静闻、顾仆多处受伤,衣不蔽体,迫不得已返回衡州府求助。徐霞客在衡州府困顿20天后,借得20两银子,于三月初三日开始环湘南游历。祁阳、永州、道州一带,带病探寻元结、柳宗元等先贤的踪迹;宁远县,登九嶷山,搜寻有关舜的遗迹,并到三分石考察潇水源头;郴州,游览白鹿洞、乳仙宫,详细记载了苏仙传说的碑文。四月十四日,返回衡州府。楚游期间,徐氏足迹走遍湘江上游,途经两府、三州、十五县,将所见所闻撰为57 000余字的《楚游日记》。
上述两府为衡州府、永州府;三州为茶陵州、道州、郴州;十五县为攸县、衡山县、衡阳县、常宁县、祁阳县、零陵县、江华县、宁远县、蓝山县、临武县、宜章县、兴宁县、永兴县、耒阳县、东安县。徐霞客在楚主要游历湘南地区,所以本文研究的地理空间即以上述区域为主。
一、盗匪来源与构成
据统计,《游记》有20处记载盗匪事迹,且对盗匪有不同称谓,如“群盗”“大盗”“盗”“流贼”“流寇”,实际表达相同的意思。为便于研究,本文将该类表述均以“盗匪”称之,泛指抢劫、叛乱、破坏社会治安的人[7]1435。盗匪主要由以下几类人员组成:
(一)沙 贼
1.沙贼源起
何谓“沙贼”?“沙贼”即矿夫,明清湘南地区的方志将“矿夫”记为“坑丁”“坑徒”“砂贼”或“沙贼”。为便于统一,本文均以沙贼称之。湘南地区多为山区丘陵,稻作经济远不及湘中、湘北地区,但本区域藏有丰富的铁、锡、煤等矿产资源,故其矿冶业却为湖南之最,尤以郴州、桂阳、宜章、永兴等州县为中心,吸纳了大量的投资者和手工业工人。徐霞客观察到湘南兴宁县矿产的运输、转卖情况:“程乡水西入郴江,其处煤炭大舟鳞次,以水浅尚不能发。上午,得小煤船,遂附之行……岭上多翻砂转石,是为出锡之所。山下有市,煎铁成块,以发客焉。”[8]334
“在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里,从事一线挖煤、开矿者大抵皆为破产农民或无业游民,以致在临武、蓝山、嘉禾、桂阳和衡阳一带形成了‘矿夫’这一特殊群体。矿夫依附于矿业的无产者,靠出卖劳力为生,四处流亡,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这种生存状态使得他们养成强烈的反叛精神、冒险精神和暴徒意识。”[9]117只要有人带头闹事,矿夫便一呼百应,群起造反。“邻省乃衡之临蓝嘉桂,永之新田等处,其人专以坑冶为生,动集数千,名曰砂夫。或有衅可乘,平仓劫村,攻城掠邑,遂为砂贼。”[10]218由于明朝对“坑治”屡禁屡弛,湘南频现盗矿事件。由明至清,郴州一带“坑治招祸,砂夫酿乱,历历可数者也”[10]129。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郴、桂贼龚福全、刘福兴等劫略安仁县,破其城,掳知县韩宗冕”[11]102。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蓝山贼等陷蓝山城及桂阳州城,焚掠而去。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桂阳州临、蓝矿贼来州开矿,驱去复来,几至燎原,守备童仲葵统兵杀退”[10]209。喻国人曾撰《郴州矿厂十害论》,痛批矿厂滋生之弊[10]589。
崇祯八年(1635年),临武矿工首领刘新宇、郭子奴倡乱,联合蓝山县李荆楚为首的造反瑶民,同时结连莽山九峰峒瑶,聚党万余,攻郴州城。后来起义队伍逐渐壮大,攻势愈发凶猛:
九年,沙贼自郴来攻州城,宜章知县杨守厚、守备吴大鼎蹑贼后赴援,围乃解。守厚等前率宜章民兵及临武四十八庙(临武村各立社号为庙,以分境)乡兵守宜章、郴州,屡破贼,贼趣桂阳,复移军赴救,贼遂遁去[12]54。
崇祯十年丁丑正月,临、蓝矿寇攻常宁县,屠居民数千,焚毁民屋殆尽。攻桂阳州城,几陷。联舟数十,由衡州下湘潭,往来凡三郡。城戒严,兵巡副使李嵩督兵御之,结筏于耒江口塔下,为堵截计。贼首刘新宇、郭子奴等蜂拥来犯,持巨斧破筏,官军大溃,莫有当其锋者。指挥闵师孔伤于炮,溺水死。事闻,诏巡抚偏沅副都御史陈睿谟调兵进剿[11]102。沙贼由湘南蓝山、临武等县逐渐向北发展,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开始攻打衡州、长沙等地。
2.徐霞客所遇沙贼
如上所述,沙贼势头正猛之时,徐霞客刚好进入楚地,《游记》中记载盗匪的活动特征表明徐霞客所遇盗匪就是沙贼。
首先,沙贼活动范围与徐霞客的行程不谋而合。时间上,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临、蓝沙贼攻常宁、桂阳,徐霞客正在茶陵州、攸县,正月底才进入衡州府。沙贼几陷常宁后,沿湘江经衡州府,下湘潭县。二月十一日,徐霞客沿湘江前往广西,适逢沙贼走水路攻衡州府、湘潭县。空间上,徐霞客一行被劫于新塘站上流之对涯,而新塘站正处于常宁县至衡州府的湘江岸边。其时,沙贼攻常宁县后,主力队伍已经前往长沙府,据《长沙府志》记载:“崇祯十年三月初一日,临、蓝矿贼至湘乡劫掠。四月初五日复来,拥罗千余人攻陷县城。”[13]1003留下来的小股沙贼活跃于永州、衡州、郴州等地,徐霞客在湘江所遇便是小股沙贼,故《游记》称之为“群盗”。《游记》多处记载可以佐证:“而前晚下午,忽七门早闭,盖因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也……是日南门获盗七人,招党及百,刘为余投揭捕厅……是夜二鼓,闻城上遥呐声,明晨知盗穴西城,几被逾入,得巡者喊救集众,始散去。”[8]280数日之内,盗匪同时出现在祁阳县、东安县、衡州府城,可见有多股沙贼活动。此后,徐霞客环湘南游历,未与沙贼主力部队相遇,一路所见多为小股势力沙贼。据徐霞客所描述的盗匪人数来看,最多为二三百人。
其次,从作案手法来看,更像是沙贼行径。小股沙贼势力薄弱,一般夜行昼伏,未敢鸱张。所以徐霞客一行在湘江夜晚遇盗,又在衡州夜间听闻有“大盗”临城。沙贼为矿夫组成,“专以挖坑淘沙为事,呼朋引类,百千成群”[14]736,掘墙挖坑正是其擅长之术。二月二十四日晚二更时分,徐霞客听到呐喊声,第二天得知是盗匪挖掘城墙,幸得巡逻者发现,呼喊众人救助,盗匪才逃离。挖掘城墙的技术非普通民众掌握,应为熟悉挖坑之术的矿夫所为。
最后,从劫掠对象来看,更契合沙贼“仇官”“仇富”的理念。新塘遇盗时,盗匪劫掠的是客船,而非所有船只。明代客船多为有身份或有钱之人乘坐,徐霞客乘坐的客船分前、中、后三个舱位,船上有徐霞客一行人、桂王府官员、从事贩木的徽商①
①明代宫廷建筑运用大量木材,以贩木为业的徽州商人在全国木业采伐中取得优势,成为势力最雄厚、地位最突出的地域木商。[8]276。客船被劫,其他船只已经逃散,两艘谷船仍在原地,并未被盗匪劫掠。可见,盗匪的劫掠目标非常明确。换一种角度考虑,谷船船身小,只能容纳两三人。乘坐谷船之人多为平民百姓,沙贼觉得不足为掠。徐霞客被劫后,衣不蔽体,乘坐谷船的戴明凡分衣予之,戴明凡未遭抢劫。四月二十三日,徐霞客在祁阳县大鱼塘再次遇见客船被劫。
前文提及盗匪曾出现在衡州府南门、西城,专挑府城作案,公然对抗官府权威。沙贼头目之一的郭子奴,号称“铲平王”[15],说明沙贼要求铲除现实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不平均现象,而官府之人与富商贵族(乘坐客船的有钱人)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劫掠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游记》中有两次盗匪不扰民的记载:“抵逆旅,始知上午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林中,经宿而去,想必有所阚而不敢动也。”[8]328盗匪南下广东,告知路人不要恐慌,言外之意,普通民众并不是他们的劫掠目标。第二条史料指出沙贼在丛林里待了一晚,并未入村劫掠。由上所述,这伙不扰民的盗匪与沙贼理念较为契合,应是由沙贼组成。
(二)瑶民与土寇
湘南的临武、蓝山、宜章等县,地处山区,界连两广,为瑶人聚居之地。“今之郴、桂,虽系中土,而山川险阻,延袤广漠,毒露瘴烟,蛇巢虺穴,猺猫杂处,性习异常,以斗杀为生,以劫略为利,……然猺情彝态,尚为跳梁,虽所卫联属,营堡错制,亦不过羁縻抚绥之耳。”[10]587明朝对瑶区以“羁縻扶绥”手段为主,缺乏社会控制与管理,导致瑶区经常发生叛乱事件。正德十二年(1517年),常宁洞瑶王廷谏、李昌光等联合临武、蓝山县的矿夫,攻临武县城。嘉靖年间,蓝山县赵朝胜因土地纠纷带领瑶民作乱。先前就有瑶民加入矿夫起义队伍之中,崇祯年间亦不例外,“崇祯九年乙亥,临武、蓝山饥,坑徒起衅平仓,嘉、桂、常、新,在效尤,势同鼎沸……言临蓝夥贼不独为郴、宜患,燎原势成,必为湖南大忧。后果结西莽、九峰诸猺獞,啸聚万计,始犯郴、桂,继犯祁、常,甚而犯衡、长,犯湘、攸,并袁、昌、韶,咸被其毒”[16]602。瑶民与矿夫联合,扩大了沙贼的劫掠范围。当沙贼北上不利,部分沙贼经瑶区中转,进入两广地区。徐霞客在桂林期间,听闻沙贼进入广西的传言,“时方日落,市人纷言流贼薄永城,省城戒严,城门已闭……自闻衡、永有警,即议省城止开四门,而余俱闭塞”[8]446。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沙贼分为五路,其中一支进入广西,攻打全州府。
《桂阳直隶州志》记载:“六年、七年,桂阳诸州县土寇蠹起,新宇故勇悍狡黠,为矿夫所畏服,因乱而起,势甚盛。”[12]54可知,除矿夫外,土寇亦为当时作乱行盗团伙之一。
(三)僧人、木客等其他人员
徐霞客路过高粱原,听向导与当地人讲述盗匪事迹:“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岭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8]314该条史料记载了这伙盗匪的人数、具体职业,表明盗匪是由多种身份转化而来,成员具有广泛性。盗匪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应是小股沙贼。其中,蓄发者具体身份尚不明确,但古人蓄发为加冠,即到成年时(二十岁)行冠礼,“才蓄发者”为刚成年之人。
明确身份的有僧人、木客。僧人本不参与世俗之事,遑论做出劫掠等违背佛门规定的行为。徐霞客在宜章县多次见到寺庙被盗匪侵扰,“昔为贮藏之所,近为贼劫,寺僧散去,经移高云,独一二僧闭户守焉……寺向有五十僧,为流寇所扰,止存六七僧”[8]327。僧人受盗匪侵扰,多数弃庙而逃。面对湘南动荡的社会现状,为了生存,不少僧人被迫选择加入盗匪。湘南地区山高林密,“此中山木甚大,有独木最贵,而楠木次之。又有寿木,叶扁如侧柏,亦柏之类也。巨者围四、五人,高数十丈”[8]311。丰富的林木资源,吸引木客前来经商,但朝廷竹木草柴,无所不征,苛税繁多。由于地方官府的欺压及朝廷对木材贩运的征收,木客铤而走险转变为盗匪。其实,僧人、木客只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必有许多其他身份的人因社会动乱而走上劫掠之路。
总而言之,明末湘南地区的盗匪主要是以临、蓝矿夫为主体,而矿夫攻打地方政府过程中,瑶民也趁机泄愤,加入矿夫之中,下山闹事。还有零星的占山为王者,趁火打劫,以及部分为生计所迫的其他人员,组成了横行湘南的盗匪团伙。徐霞客遇到鱼龙混杂、奸良难辨之人,不清楚盗匪的身份或性质,只能以自己所见与本地人所言记为“盗”“贼”“流寇”“流贼”等。需要说明的是,起初史料中“沙贼”一词仅表示砂夫,即矿徒。后来随着起义人数的扩大,各种成分的人加入沙贼队伍。“沙贼”的主体指代范围发生变化,具有抢劫窃杀的行为,都被视为沙贼行径。
二、盗匪频发的原因
湘南盗匪形成的原因,徐霞客在《游记》中已经有所提及。本节通过分析《游记》内容,结合地方志记载,将原因梳理为以下几点:
(一)山川险阻,易于藏匿
楚地水系发达,湘江作为楚地最大的河流,支流众多且多发源于湘南山区,总体呈南北流向,水运较为通畅,徐霞客游历楚地多以水路为主。沙贼攻衡州、长沙等地都是沿水路而下,发达的水系利于盗匪跨地区作案。虽然楚地水系发达,但部分河段流经山区,产生诸多港汊,河流蜿蜒曲折,船速行驶缓慢,易被盗匪劫掠。如“自永州至双牌,陆五十里,水倍之……新城之西,江忽折而南流,十五六里而始西转,故水路迂曲再倍于陆云”[8]335。此外,河湾众多,盗匪易于藏匿以实施劫掠,如遇不测,这样的地理环境又利于脱身。徐霞客在新塘站遇盗,新塘刚好处于湘江流向的曲折处。
湘南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山脉,地理条件错综复杂。程秀民曾描述郴州:“诚以郴之为郡,虽系腹里地方,而界连两广,接壤边隅,崇林大谷,多人迹之所不经,高山峻岭,为猺彝之所杂处,夫固湖南之大边也。”[10]586湘南的蓝山、临武、宜章等县山脉较多,连接各山脉的大小通渠自然成了交通要塞,极易被盗匪利用。牛头江为盗匪频繁活动的地点之一,“江水东自紫金原来,江两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艰。时以流贼出没,必假道于此,土人伐巨枝横截崖道,上下俱从树枝,或伏而穿其胯,或骑而逾其脊”[8]310。牛头江地处两山之间,江岸仅有一条“崖路”向外通行,当地居民砍伐树枝,阻止盗匪通行。山间林木茂密,盗匪利用山区作为活动据点,一则便于劫掠,二则作为藏身之所。《游记》所记盗匪渊薮之地,如高粱原、紫金原、禾仓堡,都处于山区之中。
(二)地方矛盾,错综复杂
首先,藩王豪奢与兼并土地,加重民众负担。宋元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至明清时期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湖广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因此成为藩王的主要封地之一。楚地宗藩分布较多,朝廷对其恩宠有加。藩王利用自己在地方的权力,不断兼并民田、无主田地,并指认“荒田”等请求皇帝赐封。衡州府作为桂王的封地,十分豪华,“府在城之中,圆亘城半,朱垣碧瓦,新丽殊甚。前坊标曰‘夹辅亲潢’,正门曰‘端礼’。前峙二狮,其色纯白,云来自耒河内百里。其地初无此石,建府时忽开得二石笋,俱高丈五,莹白如一,遂以为狮云”[8]268。桂府拥有较多私产,《游记》载:“余先循庵东入桂花园,乃桂府新构庆桂堂地,为赏桂之所……又五里为东阳渡,其北岸为琉璃厂,乃桂府烧造之窑也。”[8]272《游记》记载了桂府对民众的压榨,“而夹岸鱼厢鳞次,盖上至白坊,下过衡山,其厢以数千计,皆承流取子,以鱼苗货四方者。每厢摧银一两,为桂藩供用焉”[8]338。此外,桂府还有桃花源、绿竹庵等用于游玩与焚修的场所。而修建这些配套设施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疑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不断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农民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无地耕种的农民及被压迫的小生产者不得已离开原地,向山区进发,转变为流民。
其次,灾害频发逼迫灾民铤而走险。崇祯年间,自然灾害频发,明朝虽然设置预备仓,至明后期已名存实亡,失去赈济功能。《衡州府志》载:“仓无颗粒之粟,虚张敛散之数,官以点视为名,假为渔猎之计,茫无寸益于民。则保齐时,其仓尚存,今则并遗址而废矣。往岁荒歉,有司坐视民饥,束手无救。”[17]卷4,8官府救济不力,导致多数民众变为灾民。崇祯九年(1636年),临武县发生灾荒,饥民公开抢夺粮仓,后成为沙贼领袖的周龙宇趁机发动起义,笼络人心,灾民加入沙贼队伍,走上劫掠之路。
最后,流民涌入加剧土客矛盾。明末繁重的赋役制度,部分民众为了逃避赋税,成为逃户。人烟稀少、交通欠发达的湘南山区,成为流民、逃户逃亡的地方。尤其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明神宗废除对矿场的禁令,开始在全国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大批外人前来湘南采矿。郴州喻国人讲道,“且本地居民从无辨炉火识砂色者,率皆临、蓝、嘉、桂、常、新各处奸徒,及四方亡命”[10]589,本地人不识矿产之色,该说似有夸张之嫌,但从中也可得知,外地采矿人占据多数。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矿区,势必会影响当地的生产生活,久而久之,土客矛盾加剧。万历时期,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因矿监、税使引发的官斗民变也愈发激烈。
(三)政区设置,存在纰漏
《游记》所记盗匪渊薮多位于政区交界地区,如冷水坳,“此岭乃蓝山、宁远分界,在三分石之东,水亦随之”[8]311。高粱原,“为宁远南界,蓝山西界”[8]313。凤集铺,“其铺正在岭侧脊,是为临武、宜章东西界”[8]32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宁远、蓝山、临武、宜章四县在政区设置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临武县,东至郴州宜章县界三十五里,南至广东连州界六十里,西至蓝山县界八十五里,北至本州界八十五里,自县治北至本府三百二十里[17]卷1,6。
蓝山县,东至临武县界四十里,南至广东连州界五十里,西至道州宁远县界三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县东北至本府二百里[17]卷1,7。
宜章县,东西百六十里,南北六十二里,东至桂阳县界八十里,南至广东连州界百五十里,西至衡州府桂阳州临武县界五十里,北至州,又州东南二百里为桂阳县[18]卷6,2。
宁远,东抵蓝山县界四十里,西通本州界二十八里,南接本县九疑山界六十里,北控本县上流山界一百三十里,东西广二百六十里,南北袤一百九十里,自(县)治西至本府二百二十里[19]602。
可以发现,上述四县紧邻其他府县政区。其中,临武、蓝山、宜章三县紧邻广东省连州府,处于本县、邻本府县、邻省府县三个政区之间。政区交界之地,各级互相推诿,易产生管理空缺,使“盗贼取径道向广东”一事发生。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有出现,《滇游日记》载:“盖是岭东为越州,西为石堡,乃曲靖卫屯军之界,互相推诿,盗遂得而称之耳。”[8]883各县距府治较远,均在二百里以外,远离地方行政中心,难收王化之成效,出现了“山谷之民,至今有老死不见官府者”[20]16。且此类地区多为汉夷杂处之地,盗匪劫掠更为频繁,地方官员难以缉捕。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虽云错壤,然疆界山谷,实多歧路,官威不至之处,则弄兵一隅,致使社会治安较差,盗匪横生。
(四)基层治安,疏于整治
首先,国家法制与宗族自治走向衰败。明朝对强盗匪徒的惩罚十分严厉。如“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若逃避山泽,不服传唤者,以谋反未行论。其拒敌官兵者,以谋叛已行论”[21]317。虽是严刑峻法,但州县官吏惩办不力,致使盗匪更加猖獗。与此同时,明初太祖提倡的乡约、保甲制度,随着明后期政治的腐败而逐渐瓦解,其广教化、重风俗的基层治理功能逐渐消失。
其次,巡检司遭到裁撤。明初为强化地方治理,凡天下要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来往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需要常加提督或遇所司呈禀”[21]86。巡检司多沿交通要道、关口分布,缉捕盗贼是其重要的职能之一。然而,自弘治年间以来,巡检司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22]476。巡检司的裁革,使基层治安的防线更加衰落。徐霞客在宜章县多次遇见盗匪,而这伙盗匪白天经过白沙巡检司,毫不担心被捕。湘南盗匪横行足以揭示明末巡检司在基层治安职能的下降。
最后,城池武备废弛,修筑困难。“夫天下皆城也,然城之制,其善者寡也”[23]3,湘南州县城池缺乏修缮,武备废弛。徐霞客在衡州府看见西城被盗匪入侵,“盖衡城甚卑,而西尤敝甚,其东城则河街市房俱就城架柱,可攀而入,不待穴也”[8]280。西门城墙低矮狭窄,东门城墙毋需挖穴,直接利用街上的房屋,架着柱子便可入城。东西城墙多年缺乏修缮,防御体系极差,足见地方官吏疏于整治。另外,湘南地区的县级城池多在明中后期修建,修建原因是为抵御盗匪侵扰。如:
衡山县,旧无城,成化八年知县刘熙重修。正德十二年,桂东盗起,知县邹冈筑城;耒阳县,旧有土城,周围一千三百八十步,元末兵燹颓圮。正德六年,郴桂流贼突至,民遭屠俘者甚众。正德十一年,知县王睿区处上闻,始筑土城;临武县,旧无城,天顺四年,因獞寇,县丞张祯筑土城;蓝山县,旧无城,天顺八年,因獞寇,知县萧祓筑土城[17]1。
面对湘南层出不穷的盗匪问题,而地方官员却借口修城为难、畏缩退避,致使城工难以兴举。郴州永兴县,历来无城,“弘治年间,苗寇窃发,桂阳、兴宁俱被攻,势且逼永兴,当道始有筑城之议。然工钜役繁,屡课屡寝”[16]416。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修筑永兴城。然而,“未数月,程侯以述职去,继者举措颇乖,工匠逃者大半”[16]416,修筑工程不了了之。直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永兴城才算建成。崇祯十年(1637年),临、蓝沙贼攻衡州城后,次年桂王建议增筑府城,十四年开始大兴,至十六年西门城墙仍在修缮之中,此时衡州府已被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攻占。从地方政府修缮城池的史实来看,明末湘南基层治安能力的下降,可见一斑。
三、匪患的影响
首先,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引发社会恐慌。沙贼起义后,“渐聚多人,公行无忌,焚掠村镇,续至县治”[14]779。加之一些亡命之徒加入,昼则横肆抢夺,夜则公行剽劫,行凶手段变得极为残忍。如崇祯十年正月,“临蓝矿贼攻衡州常宁县,屠居民数千,焚毁民屋殆尽”[11]102。盗匪四处活动,劫掠钱财,杀害客商,徐霞客在大鱼塘见客船被劫,“哭声甚哀,舟中杀一人,伤一人垂死”[8]343;又在冷水滩听闻“为流贼杀掠之惨,闻之骨悚”[8]287。更为严重的是,“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冷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8]313。捕官,是府(州)县从事缉捕盗贼,捉拿犯人的官职,盗匪敢于杀害官府之人,公然与官府为敌。由于盗匪杀掳焚劫,无所不至,湘南遍布盗匪传言,所以有人人能言盗匪之事。而百姓谣传盗匪之事,有时会扩大甚至会夸张盗匪的事迹。新塘遇盗时,船客艾行可身亡,而当时谣传盗匪将其“支解为四”,事实上艾行可是受伤后溺水而亡。民众之所以夸大盗匪事迹,从根源上讲是盗匪频繁掠夺带给民众的恐惧所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提盗色变,而残忍的行凶传闻导致人心惶惶,无疑加剧了湘南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官府派军镇压沙贼,双方发生激烈交战,“水战于白沙洲,血染江波;陆歼于黄巢岭,尸横满地”[14]785,战争不仅带来的是胜负结果,还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湘南社会处于恐慌状态。为了寻求内心安慰,转而信奉秘密宗教,又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其次,影响民众生活,社会风气发生转变。盗匪频繁攻掠州县城池,导致人们出行受阻。州县城池一般为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人在此贩卖货物,为了防御盗匪,城门紧闭,民众的生产、贸易、出行受到影响。如“而前晚下午,忽七门早闭,盖因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也。余恐闭于城外,遂复入城,订明日同静闻往游焉”[8]277;徐霞客在宜章县听闻有盗匪前来,“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有自北而南者……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犹缩缩不前也”[8]326。为了避免遇见盗匪,行人都不敢前往北边。湘南山区部分路段需要结伴而行,“水下至凤集铺止三里,而岭荒多盗,必得送者乃可行”[8]323。盗匪频现使湘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以郴州兴宁、永兴二县为例,永兴旧志(正德)载“士耽文学,家习诗书,俗称愿朴”[10]125,永兴志(康熙)载“山深地僻,不知礼法,赋性刁悍,竞尚徂诈,讦讼成风,所称愿朴而劲不可问矣”[10]125,兴宁旧志“宁壤沃,……食无纷华,敦朴崇素。近因四方射利者,沓至杂处,转相唆诱,邑始多事,寖失其初”[10]125。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湘南地方风气发生了变化,而这正是湘南匪患最为严重的时期。盗匪带来的焚烧掳掠,导致社会风气从“淳朴”向“刁悍奸诈”转变。
再次,危害区域广,扰乱地方行政。盗匪不仅活跃于湘南一隅,周边省份无不遭受其荼毒。崇祯十年三月,临、蓝矿贼至湘乡劫掠,四月初五日复来,拥罗千余人攻陷县城,焚杀五日而去。五月,聚众数千人,大肆劫掠安化、宁乡等地。十一月,前往长沙府,“所历诸邑,焚掠一空”,又前往浏阳、醴陵,一路直达江西袁州府。十一年三月,砂贼头领刘新宇带领2 000人攻广东韶州府,转而又攻桂阳州,失败后转永州,经水路进入广西全州府。盗匪四处活动,每至一地,会对该地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地方政府需要花费大量财力、劳力用于修建城池,防御盗匪侵扰,而民众需要承担修城的劳役与费用,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逃亡。加之灾荒频发,地方政府无暇赈济灾民。灾民、流民问题难以解决,会随之引发更多的问题。灾民、流民易与盗匪融合,烧杀抢掠,迫使更多的流民产生,流民与盗匪相混,更巨大的盗匪集团出现。尤其在湘南地区,州府治所距离各县较远,盗匪频繁出现,导致地方行政效率变得更低。崇祯十二年(1639年),本次沙贼起义基本平定后,为镇抚矿夫,防备瑶民,明朝析桂阳州与临武县地,添置嘉禾县,以禾仓堡为治所。又分永州宁远县南北二乡十五都,以原来屯兵防瑶的新田营为治所,增设新田县。此举显然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地方管控,防止沙贼事件再次发生。然而,在明末政治腐败与全国农民起义局势下,本次调整政区的措施并未恢复湘南地区的社会秩序。
然后,盗匪因矿业而起,倡乱过程中,又会影响矿业开发。湘南山区交通不便,盗匪依山为营,挖断哨壁,破坏地方交通,阻止明军进入,不仅使得当时政府征收锡铅等矿料变成困难,同时也断绝与西南铜料矿区采办、交通的联系,致使明末财政与矿争更加难理[5]。沙贼主要由矿夫组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如万历初期,沙贼不出五日来到粤北英德锡坑。官员形容“今次矿徒,来去疾如风雨”[24]65。沙贼四处活动之时,矿徒纷纷加入,矿场劳动力流失,矿业渐趋衰败。随着沙贼队伍壮大与战乱局势的扩展,湘南矿区的秩序被完全破坏。清朝建立,恢复湘南矿区秩序,只允许土著开采矿产,禁止外来人口开采并且将其驱逐,给外地人贴上了“异棍”的标签[6]。之所以会以“土著”与“异棍”区分,应是清统治者吸取了明末湘南盗匪作乱的教训,防止外来人口聚集,从而引发社会动乱的现象再次发生。
最后,转移明军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自成、张献忠面对的军事压力。沙贼起义时,张献忠在湖北一带活动,明朝本想将偏沅巡抚陈睿谟调往荆州守卫惠王朱常润的蕃地,但统治者担心“万一逆与流犯互结,其毒将有不可言者”[14]789。加之桂王朱常瀛上奏请求四省围剿,明朝遂令陈睿谟专力镇压沙贼。明朝将注意力集中在湘南盗匪身上,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仍有喘息发展的空间。而且,未被官兵围剿的漏网之鱼,后来纷纷加入张献忠的队伍之中,如崇祯十六年,“因流寇乱,砂贼复起,发牌张示,约六月至刘家塘开挖”[10]211,壮大了起义军的阵营。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明末湘南盗匪主要是以临武、蓝山县矿夫演变而来的沙贼为主,沙贼起义过程中联合湘南、粤北瑶民,同时吸纳了不少流民、土寇,这一群体成为制造湘南社会动乱的主要元凶。湘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由来已久的地方矛盾、矿夫生活的极度困苦与政府疏于治理基层等历史成因,使湘南成为盗匪猖獗的沃土。纵观明朝楚地起义事件,其策源地多在湘南地区。《游记》有关沙贼的记载,为后人保留了明末湘南矿工起义、瑶民反叛真实可靠的实证。仅以此例,就体现了《徐霞客游记》珍贵的、百科全书式的史料价值。
湘南盗匪横行,揭示了明末基层治安治理能力下降,社会组织功能涣散,地方官吏不作为等多种问题。追本溯源,皆归因于明末政治的腐败。此时,明王朝的统治已风雨飘摇,多种形式的社会问题显现,盗匪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游记》中已经记载社会失序,人心涣散的现象。“是时衡郡有倡为神农之言者,谓神农、黄帝当出世,小民翕然信之,初犹以法轮寺为窟,后遂家传而户奉之。以是日下界,察民善恶,民皆市纸焚献,一时腾哄,市为之空。”[8]281社会谣传新帝出世之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实为山雨欲来之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