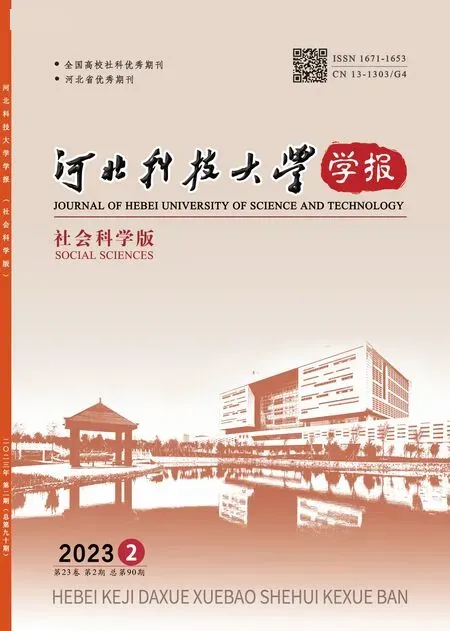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历史地位再思考
张飞龙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木巴厘俱乐部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在非洲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尚未有对“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相关研究,而西方和非洲学界曾对伊巴丹、奥索伯和埃努古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分别进行了个案研究,甚至把它们当作非官方机构,研究其在非洲文化转型时期的作用。这些研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史料,但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发展脉络,从而忽略了它们。因此,对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历史地位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历史回顾
尼日利亚于1960年10月宣布独立,具有浓郁非洲中心主义倾向的新黑人性文化成为了新政府的选择。“新黑人性”发轫于“黑人性”,在20世纪50年代,黑人性所倡导的“平等”“和平”的主张逐渐被国大党等一些激进政党抛弃,开始走向排斥一切白人文化传统的道路。自此,“黑人性”开始向“新黑人性”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受过欧洲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961年,穆法利利(Ezekiel Mphalele)、阿契贝(Chinua Achebe)、沃雷(Wole Soyinka)、克里斯托佛·奥吉博(Christopher Okigbo)、克拉克(J.P. Clark)、法贡瓦(D.O.Fagunwa)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经过多次会议讨论[1](P178),成立了尼日利亚第一家俱乐部。俱乐部虽然成立,但还没有合适的名字。1962年,阿契贝参加了伊博地区奥威利镇(Owerri)一年一度的“木巴厘节”后受到启发,建议把俱乐部命名为“木巴厘俱乐部”,并得到了其他创始人的赞同,俱乐部正式命名为“木巴厘艺术家和作家俱乐部”(The Mbari Artists' and Writers' Club),穆法利利被选为第一任主席[2](P43)。之后,弗朗西斯·阿迪莫拉(Francis Ademola)、达玛斯·尼沃科(Demas Nwoko)、玛贝尔·西贡(Mabel Segun)、乌切·奥科科(Uche Okeke)相继加入。
该俱乐部的主要使命可从名字略窥一斑。科尔(Herbert M. Cole)详细考察了“木巴厘”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认为这个词有三重含义,一是源于伊博语“igba mbar”(意为“舞蹈”),含义是伊博的神[3](P34-41);二是祭祀伊博神的舞蹈和艺术品,其中蕴含着自尊[4](P42-51);三是神的皇冠,是伊博人的生活[5](P8-17)。从这三重含义上看,俱乐部的基本精神是立足本土艺术,追求自立自强。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尼菲斯(Boniface I. Obichere)认为,科尔只是片面理解了“木巴厘”的意义,它的真正含义是“道德的完善和对生活准则的秉持”以及“艺术的创新”[6](P87)。阿契贝也曾经提到“木巴厘节(Mbari Festival)上善恶之间常常对立”[7](P49)。正因为善恶之间的对立,所以伊博人才在雨季举行木巴厘节庆祝活动,在木巴厘屋前跳起舞蹈,祈求神灵除去恶的一面,赐予人们“和平、健康和繁荣”[8](P681)。可能正是由于“木巴厘”所蕴含的含义与这些创始人的理想一致,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发现尼日利亚政坛不但腐败,而且全面压制具有艺术自觉的创新型艺术家,因此他们才选择以“木巴厘”来命名。
1962年,受伊巴丹“木巴厘艺术家和作家俱乐部”的启发,杜罗·拉迪波(Duro Ladipo)决定在奥索伯(Osogbo)再创建一个俱乐部。他同木巴厘俱乐部的创始人沃雷、克拉克、尤利和法贡瓦商量,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特别是他的老师兼好友尤利·碧尔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杜罗把自己的夜总会“Popular Bar”装修一新,又从文化自由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得到一笔资助,将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画廊和露天剧场,木巴厘-木巴友俱乐部(Mbari-Mbayo Club)即宣告成立。俱乐部随即展开了一些活动,比如尤利前妻苏珊妮的绘画作品展。受前两个俱乐部的鼓舞,伊巴丹木巴厘俱乐部的成员之一穆法利利在约翰·恩尼克伟(John Enekwe)的领导下,1963年在埃努古(Enugu)又建立了另一个木巴厘俱乐部[8](P686)。三家俱乐部独立经营,又密切合作、资源共享。自此,木巴厘俱乐部分别在尼日利亚3个城市扎根,并成为西非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
1963年,穆法利利前往肯尼亚庆祝国庆日。他接受了好友亨特(John Hunt)的建议,在首都内罗毕成立了切姆切米创作中心(Chemchemi Creative Centre)。在斯瓦希里语中“切姆切米”是“泉水”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穆法利利及其好友的意图是建立“与尼日利亚木巴厘俱乐部相同的艺术机构,旨在向肯尼亚和乌干达更多的读者引介具有创意的艺术,而不仅仅限于坎帕拉、达累萨拉姆和内罗毕的大学”[2](P43)。在切姆切米创作中心的影响下,东非也开始了反新黑人性的艺术实践,并培养了大批的艺术家。倪谷吉·瓦·第戎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作家之一,其文学成就斐然,于1973年获得莲花国际文学奖(Lotus Prize for Literature)。其实,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影响远不止切姆切米创作中心,乌干达的《转型》杂志也成为了反新黑人性文学的主要阵地。沃雷第一次流亡到乌干达之后,即担任了《转型》杂志的主编,继续秉承木巴厘俱乐部的文化主张,在非洲文坛发挥了重要影响。
虽然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和切姆切米创作中心存在都不足十年,但它们培养出了大批的艺术人才,其中沃雷和戈迪默(Nadine Gordimore)分别于1986年和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莱辛、库切和古尔纳也相继获得世界大奖,为非洲文学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隐文学奖以及各类艺术国际大奖的人数之多,一度引发了世界学术圈的关注。
二、木巴厘俱乐部的文化活动和价值追求
随着俱乐部的发展,阿契贝、穆法利利和图图奥拉等人逐渐退居幕后。“总体上,尼日利亚三巨头——克拉克、奥吉博和沃雷维持着它们的发展”[8](P680)。1962—1965年,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共同致力于推进文学艺术创新和创作。针对当时盛行的新黑人性文学和文化诗学,大胆革新,在艺术实践上呈现出了较为强劲的反潮流倾向,并开始探索非洲文学走向世界的创新之路。
(一)提倡新文学,培训新人才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正处在独立运动的关键时期,去殖民化呼声高涨,以国大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推行独裁,文化上实行管制,推行具有典型非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新黑人性”文化策略。这种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去殖民化道路存在着弊端:在文学艺术领域,国大党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对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艺术家,从舆论上进行清算,在传播媒介上进行压制,结果尼日利亚被黑人性文学和新黑人性文学一统文坛。由于国大党排斥欧洲文学和艺术,故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很难有所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伊巴丹木巴厘艺术家和作家俱乐部创建了艺术工作坊,并组织了系列艺术活动,主要包括戏剧培训、传统非洲艺术讲习班。沃雷亲自主持戏剧培训班的工作,他招募了一些有经验的戏剧演员做技术指导,其中包括奥顺剧场(此前是沃雷经营的)的5位元老:图恩济·奥耶拉娜(Tunji Oyelana)、威尔·奥贡耶米(Wale Ogunyemi)、约米·奥比雷耶(Yomi Obileye)、塞贡索·佛沃特(Segun Sofowote)和费米·法脱巴(Femi Fatoba)[9](P15)。随着这些表演经验丰富的大师加盟,艺术工作坊的创意越来越多。后来,沃雷又在奥顺剧场的基础上,组建了“茜茜·克拉拉大师戏剧工作坊”,以纪念曾为假面剧团(1960 Mask)做出特殊贡献的茜茜·克拉拉。另外,培训师还包括屈科·迈克(Chuck Mike)、佛拉博·阿加伊(Folabo Ajayi)和达玛斯·尼沃科(Demas Nwoko)等知名人士。
在沃雷等艺术家的领导下,艺术工作坊的培训品质不断提升。演员们常常为了恰当地表现某一主题,为了一段舞蹈或者主题音乐而进行充分的研讨,不论采取的素材源自西方或者本地,都要认真地改编[9](P16)。此时艺术工作坊试图将欧洲艺术理念本土化,这与新黑人性思潮一概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恰恰相反。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沃雷在内的许多人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培训师,也是学员。最为典型的是屈科,他在工作坊学习期间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后来还负责韵律和舞蹈的培训工作。拉迪波不仅参与工作坊的领导工作,还在工作坊坚持戏剧创作方面的学习,他导演了自创的戏剧,并在俱乐部上演,受到新兴艺术家们的充分肯定。
当时欧洲具有先锋意识的艺术家,诸如奥地利的艺术家安敦尼·奥罗丽莎(Adunni Olorisha),在艺术工作坊讲授艺术创作[10](P147)。经过学习和训练,艺术坊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焕发了创作的激情,他们利用本土题材,采用西方的写作技法,创作出了许多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戏剧有克拉克的《山羊之歌》、奥吉博的《天门和极限》、沃雷的《沼泽地居民》等,诗歌包括巴卡尔的约鲁巴语诗歌《奥吉利》、南非作家阿列克斯(Alex la Guma)的《夜间漫步》等等,这些作品大抵都是歌颂黑人的生活,但不再把黑人看作不同于其他种族的人,而是与白人一样,具有同样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因此,伊巴丹木巴厘俱乐部在索因卡的领导下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西非的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即反新黑人性的文化中心。
(二)发起奥索伯艺术运动
伊巴丹木巴厘艺术家和作家俱乐部建立后不久,杜罗·拉迪波就与索因卡等人商量筹建奥索伯木巴厘俱乐部。至于拉迪波要另立门户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奥索伯既是奥顺州的首府、拉迪波的故乡、约鲁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西非本土文化的重要中心,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涵养新艺术的理想之地。其二,伊巴丹木巴厘艺术家和作家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之间龃龉不断,奥吉博和克拉克独断专行,该俱乐部还闹出受外国经济支持的丑闻[1](P221)。拉迪波在尤利的支持下,在奥索伯成立木巴厘-木巴友俱乐部。1962年5月17日,拉迪波在这里上演了《奥巴·摩罗》(ObaMoro)。1963年8月,拉迪波组织了该俱乐部的第一次暑期艺术工作坊,由几内亚艺术家丹尼斯·威廉斯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提高学员综合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当时颇具国际影响的温格担任了培训班的指导教师和班主任,在她的指导下学员们掌握了艺术形式分析、艺术鉴赏和表现方法,提高了艺术表现力。此外,尤利还邀请了荷兰著名画家露·范·罗森(Ru Van Rossen)为学员讲授绘画知识,传授绘画技巧[11](P86)。
与前者相比,奥索伯木巴厘-木巴友俱乐部在推广具有“本真性”①的非洲艺术方面卓有成就。他们从奥顺当地的民间传说、神话、节日和日常生活中取材,用音乐、舞蹈、雕刻和绘画等方式展现这些主题。俱乐部培养了大批艺术家,包括1962年威廉斯培训的雅各布·阿佛拉比(Jacob Afolabi),1963年培训班的鲁夫·奥贡德乐(Rufus Ogundele)。1964年培训班的成绩最为丰硕,著名的艺术家吐温斯·赛文-赛文(Twins Seven-Seven)、穆拉伊纳·奥耶拉米(Muraina Oyelami)、阿德比西·法本米(Adebisi Fabunmi)、基莫·布拉伊莫(Jimoh Buraimoh)和提佳妮·玛雅基里(Tijiani Mayakiri)均在此俱乐部培训[12](P156-157)。据穆拉伊纳·奥耶拉米回忆,该俱乐部吸引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加入,包括官员、商贩、学生、酋长(奥耶拉米自己就是一位酋长),奥索伯木巴厘俱乐部已成为了当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正是由于浓厚的艺术氛围,奥索伯木巴厘-木巴友俱乐部文化后来也被称为“奥索伯艺术运动”[11](P86)。
(三)推动非洲现代文学的发展
20世纪中期之前,英国出版社垄断着西非出版市场。为了推行文化垄断,英国还特别成立了西非英语考试委员会,在教材方面进行推介,文学艺术方面的出版物则寥寥无几。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伊巴丹大学尤利教授与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学者和作家创办了非洲第一本文学类专业杂志《黑肤的俄尔浦斯》,主要发表非洲作家用英语创作的诗歌、小说、评论。伊巴丹木巴厘作家和艺术家俱乐部成立之后,尤利把杂志贡献出来,将之作为该俱乐部的喉舌,宣扬“新文学和新主张”,这是不同于新黑人性诗学而追求多元文化价值的诗学。特别是1960—1964年期间,沃雷和穆法利利担任编辑,进一步改变了杂志的风格,把大众艺术也纳入了出版视野,出版了具有浓郁非洲本土风格的艺术作品。在这四年当中,该杂志发表了一线作家、艺术家的诸多作品,这些作家主要包括桑格尔(Léopold Senghor)、卡马拉·雷耶(Camara Laye)、塞萨尔(Aimé Césaire)、拉古玛(Alex La Guma)、沃雷、克拉克、丹尼斯(Dennis Brutus)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黑肤的俄尔浦斯》的读者群不仅包括成人,也包括儿童,它甚至成为了儿童的必读书目,这无疑为提高他们的英语文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初中毕业之后还不知桑格尔或艾米尔为何人的尴尬局面”[13](P276)。由于《黑肤的俄尔浦斯》产生的巨大影响,它被誉为“整个西非艺术觉醒的有力催化剂”[14](P189)。
在推动非洲现代文学发展方面,切姆切米创作中心也发挥了巨大作用。1964年,中心成立了非洲戏剧公司,几个月以后便排练了3个独幕剧,并用斯瓦西里语演出了南非作家的戏剧《浪子》。在培养作家方面,该中心先后邀请约瑟夫·卡里基(Joseph Kariuki)、约翰·夏曼(John Sharman)、埃德加·赖特(Edgar Wright)讨论非洲作家关于传统的立场、非洲口头文学与英语文学的互翻、非洲文学的发展趋势等问题。穆法利利曾说,在培养文学艺术的新人才方面,“我们主要靠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和知识分子来指导我们,在任何国家他们都是善于表达和敏感的人群。特别在非洲环境中,他们在没有文化机构的支撑下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整个时代,人类创建文化机构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延续文化,正如我们在欧洲人那里看到的,后来便出现了以在域外阐释和传播为主的文化机构。非洲,若以促进人们衣着打扮和有意识地消费为目的的文化则毫无意义,这里毕竟还没有形成有闲阶级。所以这些文化机构必须把自己视为成人教育中心……只有这样,非洲性才会形成。”[15](P117)由此推论,位于东非的切姆切米创作中心一直以寻找真正的非洲性,即欧洲文化的本土化与非洲本土文化的结合,这无疑与新黑人性的文化主张不同,而与反新黑人性的潮流契合。它培养的人才成为了后来非洲现代文学艺术的抗鼎人物。
为了进一步扩大非洲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木巴厘俱乐部的领导者筹建了木巴厘出版社(Mbari Publication House),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之前在俱乐部上演的作品《山羊之歌》《天门和极限》《沼泽地居民》《奥吉利》和《夜间漫步》等均得以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引起了欧美英语文学界的关注,后来版权卖到英国、欧洲大陆,进而传播到美洲,为非洲现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三、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历史地位
西方学者在研究木巴厘俱乐部时,只是进行了个案研究,不能把握全局。如果把上述5个机构统一考察,会发现它们的历史地位体现在参与去殖民化文化进程、发挥现代性启蒙作用和产生社会影响3个层面。
(一)参与去殖民化的文化进程
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切姆切米创作中心、《转型》杂志的主要领导人、发起时间、文化主张等层面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因此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考察。从木巴厘俱乐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属于非洲去殖民化的文化进程的一部分。其中,非洲最先产生了黑人性和新黑人性两种文化认知方式。前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寻找黑人的文化根基,在殖民文化的氛围中树立黑人文化的自信,以对抗殖民文化的侵略;而后者本质上是在独立前后兴起的民粹主义文化策略,是通过拒绝接受欧洲文化而实现文化独立。在新黑人性文化策略的推行过程中,一群具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组建了木巴厘俱乐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来对抗新黑人性文化策略,试图用本土化的欧洲文化代替具有原始奴隶文化色彩的非洲中心主义文化。从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木巴厘俱乐部文化与前两者是同一的。唯一的不同是,它采用的策略具有包容性、反奴隶制、反专制的特点,比如阿契贝的《瓦解》、沃雷的《解释者》和《国王的侍从》等,具有浓郁的非洲文学现代性启蒙的色彩。
(二)发挥现代性启蒙作用
早在尼日利亚独立之前,确切地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黑人性文学运动逐渐摆脱了杜波伊斯、塞泽尔和桑戈尔对白人文化的温和反思,发展出了带有浓郁“本土主义”色彩的对抗性诗学。作为民族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潮流,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其影响才日渐式微;由于主要思想发轫于黑人性文化运动,因此常被认为是黑人性文学运动的延续,故沃雷称之为“新黑人性运动”(neo-negritude movement)”[15](P66)。在新黑人性运动中,代表人物钦维祖等以木巴厘作家沃雷、克拉克、奥吉波等为靶向,提出了新黑人性文化的基本美学原则:作家不应使用古朴的、拗口的、没有节奏感的语言……不能使用模糊不清的词汇;作家亦不应使用外国的意象;现代诗歌应该遵循非洲的口语传统,而不应将生僻字纳入文学语言的范畴。文学题材方面应该尽量避免采用基督教的文学题材;创作技法上应该尽量避免模仿欧洲现代派的创作技法。文学批评方面,非洲的文学不适合非洲以外批评家的胃口,也不是为其创作的,故其批评不得要领,也不适合非洲文学[16](29-37)。
由此看出,新黑人性文化的主张是向世界宣布非洲文学的标准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标。其标准可以理解为非洲文学,即“非洲人的文学”,这是非洲文学领域新版的“门罗宣言”,是非洲独立之后在去殖民化道路上做出的文化选择,不幸的是它却沦为了非洲民粹主义。正如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后来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毕敖顿·耶一佛(Biodun Jeyifo)教授所说:“以‘是不是非洲人’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经常而且必然会折射出……文化保守主义和非洲性。”[17](P38)所以,在检视“新黑人性”这个术语时,倪伊·阿佛拉比(Niyi Afolabi)认为“新黑人性”的基本内涵是“反奴隶、反殖民、非-美共有、非洲现代、非洲中心主义、非洲流散和非洲先锋主义”[18](P177)。在去殖民化的历史前提下,新黑人性运动虽然兼具反奴隶制、反殖民统治的历史重任,但在艺术实践上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原则,所以它的文化道路就显得过于幼稚,结果给非洲文学艺术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可见,阿佛拉比把它定义为“非洲中心主义”并非没有道理。
木巴厘文化诗学与黑人性/新黑人性文化诗学对立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尽管他们都在争取各自的合理化和权威化,但是黑人性和新黑人性作家提倡通俗文学和艺术合法化,而木巴厘精英知识分子主张精英文学和艺术。因此,尽管他们在去殖民化的基本目的上保持一致,但是文化道路选择上自然会发生严重的分歧。木巴厘文化诗学主张兼收并蓄非洲和西方的文学艺术传统,而新黑人性文化诗学则是全面抵制西方文学艺术。正因为如此,新黑人性思潮的文化主张是“反现代性的”,新黑人性文学是反现代主义的文学,它不仅反对欧洲白人的现代文学,而且反对加入西方文化元素的非洲黑人现代主义文学,所以也是民粹主义的,这种艺术哲学给非洲文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木巴厘俱乐部文化是一种逆势潮流,它在反思新黑人性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西合璧”的艺术创作构想,主张艺术家进行先锋实践,以此达到艺术走向世界的目的,最终实现“艺术自治”的理想。但是也应注意到,这种非洲黑人文学内部发起的自反式文化运动本身就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了使非洲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必须将殖民文化中的精髓本土化,比如法制和民主等,因而需付出巨大努力;二是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又不得不与民粹主义者进行文化论争。就前一任务而言,从木巴厘俱乐部成员的作品广泛在欧洲主流出版社出版,随后又被大量引入非洲为止,就已基本完成,而后一任务却异常艰巨,这主要是因为“黑人性”是一个极具鼓惑性的字眼,它甚至能够迷惑一些文化精英。除了钦维祖、杰米和马杜别克,当时的反对者中还包括伯恩斯(Bernth Lindfors)、阿姆斯塔等著名的知识分子,甚至阿契贝也表现出了摇摆不定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沃雷不得不为捍卫木巴厘俱乐部的文化成果而与论敌进行了长达40年的辩论。幸运的是,他们的诗学在辩论中逐渐被广泛认同,笔者也曾把它们看作“第三条道路”[15](P62-87)。
(三)社会影响大
木巴厘俱乐部吸引了广大的社会人群,起初参加俱乐部活动的主要是年轻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成员已经涵盖了老中青3个年龄层段,其中绝大多数是具有“文化自治意识”的艺术家。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分别位于尼日利亚的西部、中南部和东北部,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尼日利亚以及南非、中非和东非;《转型》杂志社位于乌干达,切姆切米创作中心位于肯尼亚。由于这些国家是非洲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影响很快就辐射到了非洲其他地区,甚至影响了欧洲和美洲。
此外,木巴厘俱乐部不仅在艺术实践上向现代先锋艺术挺进,而且把非洲文学和艺术推向世界的过程本身就是积极参与非洲文学艺术的现代性重建的过程,更是一个现代性启蒙的过程。索因卡等人积极与新黑人性的文化主将进行论争,引发了非洲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争鸣,以至于多林认为木巴厘俱乐部拉开了非洲文学革命的序幕, 并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修正黑人性以及新黑人性之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工具[2](P41-52)。从朗文和诺顿出版的《世界文学作品选》以及非洲人编写的《非洲文学选读》中也可以看出,新黑人性文化主将的文学作品已经被排除在“文学经典”之外,而反新黑人性文学却在其中。正是这些反新黑人性文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批评家。
综上所述,木巴厘俱乐部文化显然超越了“俱乐部文化现象”的范畴,它倡导的艺术精神是对新黑人性文学的反对,是在非洲去殖民化的背景下由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对新黑人性诗学的深刻反思,启迪了一大批艺术家和文学家,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爱德华·赛义德是在黑人性和新黑人性文化启发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大师的话,那么霍米·巴巴、拉什迪、马里切拉等都是在反新黑人性思潮影响下的新生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这足以证明木巴厘俱乐部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大。
社会学家萨姆•宾克利(Sam Binkley)认为,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进程相重叠,如果具有革命性,如果能够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并能产生自反性社会效果,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那么它就超越了文化现象的范畴,就已经达到了“文化运动”的高度[19](P650-652)。在研究非洲的早期文学机构时,只要把三家木巴厘俱乐部、切姆切米中心和《转型》杂志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目标一致、组织形式相似、领导层互有交叉,因此属于一个文化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四家文化机构都是木巴厘俱乐部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共同参与了非洲去殖民化的文化进程,承担着现代性启蒙的作用,并改变了非洲中心主义的认知方式,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些文化机构不仅掀起了非洲现代“文学的革命”,而且还在“文学生产和社会政治学领域内促进了公共观点的形成”[2](P5)。鉴于此,笔者认为这种反新黑人性文化思潮应当被视为“木巴厘俱乐部文化运动”,即非洲的“新文化运动”。只有这样看待木巴厘俱乐部文化,才能够厘清非洲现代文学形成中民族文学与民族主义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评估其在非洲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才能毫不偏颇地为“黑人性/新黑人性”诗学定位。
注 释:
①“本真性”(authenticity)是一个有争议性的术语。在非洲诗学大系之中,它被新黑人性的拥趸者用来反对具有欧洲文化元素的非洲艺术和非洲艺术家,为此,沃雷·索因卡曾经就“何为非洲艺术”的问题专门撰文进行了讨论,以捍卫木巴厘俱乐部的艺术成果。本文在这里用“本真性”来概括该俱乐部艺术家以及学徒们艺术作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