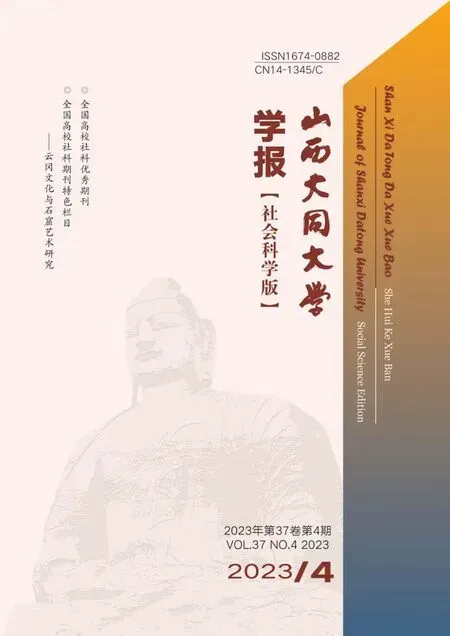由出口商品的变迁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许宁宁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自西汉开辟以来,丝绸便是由此远销海外最主要的中国商品;唐代以后,瓷器又经此运销海外,并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商品。自此近千年间,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便一直经由这一通道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正是由于以丝绸和瓷器为“物”的代表的古代中国经济文化高居世界之翘楚,海上丝绸之路才能跨越漫长的历史持久不衰。
16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稍后的荷兰人、英国人竞相东来,又为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1567 年“隆庆开关”准贩东西二洋以后,长期抑制下的中国民间商业活力喷涌而出。一条条新开辟的航线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精巧绝伦的中国商品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欢迎,而附着于这些商品之上的中国文化也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伴随着人与物的频繁往来,西学东来,东学西渐,承载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鼎盛。然而也正是从这个全球范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文明加速发展的引擎已然启动,而古老的中国文明则越发沉寂。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的节点已经悄然来临。
一、丝织品出口:由盛转衰的征兆
海丝之路上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最重要的丝绸出口领域。“丝绸”一词原本是由“丝”与“绸”合构而成的复合词。“丝”指的是制绸的原料生丝,“绸”指的是由生丝制成的丝织品。自古以来的丝绸出口,既包括丝织品这种制成品的出口,也包含生丝这种中间产品的出口。中国的丝织品以其轻柔绚丽著称于世,一直是异国商人们来华寻求的主要商品;生丝尽管也以其洁白优质闻名遐迩,但长期以来在出口贸易中仅仅是作为丝织品交易的补充。然而当16世纪“丝银”贸易兴起时,“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1](P5438)生丝开始变成海丝之路上的主角,丝织品出口反而退居到次要位置。此后直到海上丝绸之路退出历史舞台,生丝都是中国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完全取代了丝织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发生在丝绸出口领域的这种结构性变化与16世纪全球范围的社会经济变迁密切相关。中国生丝出口的兴盛,不仅得益于美洲、日本白银大量开采所带来的国际购买力激增,更源自这一时期国外对中国生丝的旺盛需求。而这种生丝需求的背后,则是在中国丝织技艺长期外传影响下国外丝织技术的显著进步与丝织业的日益成熟。其中,尤以日本和欧洲的丝织业表现得最为典型。
日本丝织业的发展与中日间文化交流紧密结合在一起。据传中国的蚕丝技艺早在秦代便开始传入日本。到魏晋时期,自称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率其部众将中国的养蚕和机织技术带到日本,仁德天皇“以百二十七县秦民,分置诸郡,即使养蚕织绢贡之”,[2](P435)日本丝绸业自此开始发端。5 世纪中叶,雄略天皇又两次派使者到江南招徕丝织工匠传授技艺,并下令“宜桑国县殖桑”,[3](P233)促进了日本丝绸业的进步。到了隋唐时代,随同遣隋使、遣唐使前来的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学习中国文物典章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丝织技艺并购买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回国仿制,极大带动了日本丝织业的发展。此后历经宋、元、明三代,日本丝织业在不断地汲取中国丝绸技艺的基础上渐趋成熟,在16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划时代的勃兴。传统的京都西阵和作为学习中国先进丝织技艺窗口的堺市成为日本丝织业的两大中心,其“所制金襕、缎子、唐织物、红梅、绮罗,先代未闻也”。[4](P295)进入17 世纪后,日本的丝织生产由京都西阵向周边扩展,博多、丹后、桐生、足利、仙台等地亦纷纷崛起为新的丝织中心。与此同时,日本丝织业开始更加注重本土技艺的发明和推广,先进的丝织“高机”得到普及,代表日本传统丝织工具最高水准的“织锦机”也发明了出来。这一切都使日本的丝织技术与生产规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与日本相比,欧洲丝织业更显示出一种独立发展的特性。由于中国的丝织品并不适合地中海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早期罗马人在购得中国丝绸后往往将其拆成丝线,然后重新织成适合当地需要的轻薄织物,即所谓“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5](P861)当时的丝绸在西方价比黄金,罗马人为夺取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商道曾数次发动“丝绸战争”。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在被称为“丝绸皇帝”的查士丁尼将中国的蚕种和丝织技艺引入君士坦丁堡之后,种桑、养蚕和丝织技术才在小亚和希腊地区传播开来。7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小亚地区之后,将蚕桑生产推广到阿拉伯地区,又由摩尔人带到了西班牙。到10世纪,西班牙的安德卢西亚已发展成为欧洲的丝织中心。12世纪中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从希腊半岛虏回大批丝织工匠,极大刺激了西西里丝织业的发展。不久之后,丝织业沿着意大利半岛一路向北扩张。到14至15世纪,意大利已发展成为欧洲新的丝织中心。此后,丝绸生产进一步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法国南部安家。在法国王室的大力奖掖下,到17 世纪初法国的丝织业已能与意大利并驾齐驱。17 世纪下半叶,随着《南特敕令》的废除,包括许多丝织技工在内的胡格教徒移居英国、德国、瑞士等地,又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到18 世纪中叶,丝织工厂已在西北欧遍地开花。法国的里昂,英国的伦敦,瑞士的苏黎世,德国的克雷菲尔德与荷兰的哈勒姆等地都已成为了欧洲丝织生产的重镇。[6](P95-96)
随着日本与欧洲丝织业的日趋成熟,其生产的丝织品质量已能不逊于远渡重洋而来的中国织物,而其花纹样式则更适应本地居民的需求。16 世纪,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对日本的丝织品使用情况做过这样的记载:“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7](P414)中国丝织品此时在日本已被“自有成式花样”的本土织物所取代。虽然仍能出口日本,然而也不过是“但充里衣而已”。及至18世纪中叶,随着日本丝织业的进一步成熟,江户幕府更制定海舶条例明告华商:“药材自余物件,惟下品者多带前来,匹头等项地素尺寸及阔狭等止不宜者,是之载带,其于本处乃不中用。……无用之物着令载回。”[8]中国商人运来的丝织品已被视为并不适合日本市场需要的“无用之物”。而在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丝织业的发展,各国也纷纷颁布法令禁止进口中国丝织品或对其课以重税。由此,曾为各国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丝织品逐渐丧失了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随着各国丝织业对原料的旺盛需求而被中国生丝所取代了。
生丝出口与丝织品出口虽然都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意义却截然不同。作为制成品出口的丝织品,其背后是中国先进的丝织技艺,是各国对中国丝绸文化的仰慕与追求;作为中间产品出口的生丝,其背后是各国丝织技术的长足进步,是各国丝织业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对丝织原料的旺盛需求。运送丝织品的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国际市场的主导;输送生丝的海上丝绸之路,装载的是各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是国际市场的附庸。由丝织品出口向生丝出口的转变无疑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正在丧失其长期保持的优势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在极盛的16世纪已然敲响了走向衰落的警钟。
二、瓷器出口:盛衰易位的标志
发生在丝绸出口领域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中外经济文化关系转变的开始。不久之后,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又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另一主要商品——中国瓷器的出口贸易中昭显出来了。与中国丝织品一样,在瓷器的出口过程中,也伴随着制瓷技艺的外传和外国对中国瓷器制作技术的模仿。不过由于瓷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对原料与火候的要求异常严苛,因此外国对中国制瓷技艺的学习首先是从相对简单的陶瓷技艺开始的。
以日本为例。早在唐代,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各种手工艺能的日本工匠们便将中国的陶瓷技艺带到了日本,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招募工匠到日本试制陶瓷。在留学的日本工匠和渡日的中国工匠共同努力下,日本模仿唐三彩的制法烧出了奈良三彩,使日本陶瓷技术跃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 年),被尊为日本“陶祖”的藤田三郎又在福建潜心钻研陶瓷技艺,归国后成功烧制出被称为“濑户天目”的黑釉陶瓷,大大推动了日本陶瓷业的进步。进入明代以后,随着景德镇青花瓷的大量输入,已具相当陶瓷制作水准的日本工匠们开始真正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正德年间(1506-1521年),五良大甫化名“吴祥瑞”在景德镇刻苦钻研多年,学会了烧制青花瓷的整套工艺,并将中国的瓷土和釉料带回日本,在肥前的伊万里烧制出日本的第一件青花瓷器。五良大甫由此日本人奉为“瓷圣”。“庆长·文禄之役”(1591-1598 年)时,丰臣秀吉又将千余名朝鲜匠人虏回日本。其中一位名叫李参平的制瓷工匠在肥前的有田发现了优质的瓷土矿并在此开窑,开始大规模烧制名为“有田烧”的纯白瓷器。及至17 世纪中叶,喜三右卫门又从经常出入长崎的中国商人手中获得了中国的赤绘调色法,并经反复试验,用赤绘技术成功烧制出日本的第一件彩绘瓷器。随后,柿右卫门、色锅岛、古七谷、七宝烧、京烧、清水烧、萨摩烧等独具日本特色的彩绘瓷器纷纷面世。随着制瓷业的日益兴盛,日本的瓷器生产不但能够实现自给,而且逐渐具备了出口海外的能力。明末清初厉行海禁之际,供销海外的中国瓷器几近绝迹。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50年开始将日本的伊万里瓷和有田烧运销欧洲,很快盛行一时。此后,运销欧洲的日本瓷器不断增加,甚至动摇了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
相比于日本,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艺很晚才开始传入欧洲。而在中国瓷器大量输入之前,大多数西方人日常使用的都是粗糙而厚重的石制、陶制器皿。因此,当16 世纪初葡萄牙帆船首次将精巧的中国瓷器运抵欧洲时,整个欧洲为之倾倒。从国王到普通百姓都将其视为珍宝,以瓷器作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中国瓷器由此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吸引力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开始试制瓷器。但由于无法获悉中国制瓷的秘密,在很长时期内只能烧制出一些简单的陶瓷。直到18 世纪初,一位名为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士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得以长驻景德镇并自由出入当地的大小作坊。他由此深入了解到烧制瓷器的各项工序和技术,并将其写成报告,与中国的瓷土样本一道寄回欧洲,直接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诞生。1708 年1 月15 日,被誉为“欧洲瓷器之父”的德国人伯特格尔在实验室里烧制出欧洲的第一件瓷器。凭借其制瓷技术,著名的迈森瓷器工厂很快建立起来,其生产的白瓷精美多样,风靡全欧。此时的欧洲正值工业革命前夜,技术传播与产业扩张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迅猛。及至18 世纪中叶,欧洲的制瓷中心已从德国迈森扩展到法国。法国的摩利日被誉为“欧洲景德镇”,其生产的白瓷与塞勒夫生产的软质瓷小雕像共同引领了18 世纪欧洲的瓷器潮流。稍后不久,被称为“英国陶瓷之父”的韦奇伍德创办了他的第一家陶瓷工厂,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相继开设工厂生产瓷器。到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皇家维也纳、意大利卡波迪蒙蒂又成为欧洲新的制瓷中心。
由此,随着日本制瓷业的日益成熟,中国瓷器在17 世纪中后期逐渐淡出了日本市场;而在欧洲制瓷业的迅速成长中,到18 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又结束了出口欧洲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发生在丝绸出口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还只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征兆的话,那么瓷器出口的衰落则是一个明确的标志。在工业革命中蒸蒸日上的欧洲自不待言,即便是对于同样处于传统社会中的日本,徐光启在17 世纪初时尚能不无得意地宣称“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1](P5442-5443)及至18 世纪中叶,也已被前述的“药材自余物件,惟下品者多带前来”所取代,中国经济文化的领先优势不复存在。
国际领先地位的丧失从根本上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贸易格局。那些曾支撑海丝之路千年不衰的、作为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物”的代表的传统手工制品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中间产品和原料产品开始成为海丝之路上的主角。由此撑持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再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与技术优势,而是极易被移植和取代的原产地优势与价格优势。当以“优美精良”享誉世界的中国商品被“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所取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已在衰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三、生丝出口:先进落后的分野
导致海丝之路上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出口地位逆转的“丝银”贸易在16世纪中叶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贸易之一。由于各主要丝织生产国的蚕丝生产水平无法满足本国蓬勃发展的丝织业需要,从中国进口生丝就成为它们的必然选择。然而与需要高超的丝织技艺才能织出精美织品的丝织业相比,蚕丝业的移植显然更为便易。因此在进口中国生丝的同时,各国也分别走上了蚕丝本土化的道路。其中,尤以日本蚕丝业的成长影响最为深远。
对于日本来说,“丝银”贸易虽然满足了丝织生产的需要,但也造成日本白银的大量外流。尤其是在16 世纪后期到17 世纪早期,穿戴丝织品曾一度成为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时尚,“以至现在已然形成从中国、马尼拉贩来的全部生丝亦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现状。”[9](P136)因此“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7](P414)巨大的利润将各国商人纷纷吸引到中日“丝银”贸易中来,仅葡萄牙商船在1599至1637年间就将5800万两白银运出长崎。[10](P150)白银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甚至连作为国内货币流通的白银也出现短缺。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德川幕府在颁布“贞享令”(1685 年)限制贸易规模的同时,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民植桑养蚕。地方各藩府和生丝批发商们也都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到发展本土蚕丝业的事业中来。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植桑养蚕事业迅速在日本各地推广开来。及至“贞享令”颁布30 年后,日本的主要产丝藩国已增至16个;到了德川时代晚期,大部分农村都已实现了向“农耕为主、桑蚕为辅”的转变。与此同时,日本的蚕丝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德川时代中期起,不仅夏蚕饲育已在日本各地普及,秋蚕饲育也逐渐为农户所采用,清凉育蚕、温暖育蚕等养蚕技术日臻完备。[4](P313)在缫丝工序中,传统的“胴取”法已为“手挽”法、乃至更为先进的“座缫”所取代,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日本蚕丝业的迅猛发展,1737 年以后来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已不能用生丝换购日本商品,必须支付相当数量的金银;[11](P45)而到文化年间(1804—1817 年),日本的生丝产量已比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3 年)增加了八倍之多,[4](P310)彻底摆脱了对中国生丝的依赖。
相对于日本蚕丝业的快速成长,欧洲的生丝生产一直落后于丝织业的发展水平。尽管植桑养蚕已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农村地区逐渐推行,但其生产的生丝绝大部分仅能自给,无法满足欧洲蓬勃发展的丝织业需要。加之西属美洲殖民地墨西哥丝织业的兴起,更令欧洲市场上的生丝供应捉襟见肘。于是自16 世纪中叶起,欧洲商人开始利用从美洲开采的白银大量购买中国生丝。通过经巴达维亚到欧洲与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两条航线,中国生丝连绵不绝地运往欧美,欧美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就是中国与欧美的“丝银”贸易。这项贸易延续了三百多年。直至19 世纪中期,中国生丝仍牢牢主导着欧美生丝市场。
然而到19 世纪60 年代,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亦开始被打破。19 世纪中叶,蚕微粒子病的爆发对欧洲蚕丝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对欧生丝出口由此急剧扩大。然而中国蚕丝业未能把握住这一机遇,其出口质量反而随着出口数量的剧增日渐下降。人们“或将劣茧和杂草混入,或以湿气和洒水使生丝增重,或以普通丝、劣质丝混充优质丝……种种投机取巧、蒙混作弊的行为公然行之”,[12](P255-256)严重损害了中国生丝的国际声誉。而与此同时,日本生丝则在“安政开国”(1858 年)后开始涌入国际市场,向中国生丝发起了挑战。为避免重蹈中国生丝的覆辙,日本在主要的生丝出口港都设立了“生丝检查所”,对生丝的出口质量严格把关,使日本生丝很快在欧洲站稳了脚跟。70 年代后,中日生丝较量的主战场又从欧洲移至美国。这一时期,随着欧美丝织业中动力织机的普及,对生丝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量低下的中国手工缫丝越来越无法满足欧美丝织业的发展需要。而日本蚕丝业则通过大规模兴建缫丝工厂和改良传统手工缫丝提高生丝质量,获得了欧美丝织业的青睐。由此,中日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当19 世纪60 年代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时,其出口量不过是中国生丝的七分之一;而到1882 年日本生丝便已夺取了中国生丝在美国的市场地位;1903 年日本生丝出口量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丝出口大国;20世纪30年代日本生丝更囊括了国际生丝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三,[4](P551)彻底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丝业霸主”。
可以说,面对近代化浪潮,应对的快慢直接改变了中日两国生丝出口的命运。而两国生丝出口的盛衰,更是近代两国先进与落后的缩影。众所周知,生丝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由其创造的外汇为日本近代化建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生丝出口的没落尤令人叹息。如果说丝织品与瓷器出口的衰落是中国经济文化丧失了世界领先优势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生丝出口的衰微则标示着中国经济文化已日益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从丝织品到生丝,当中国的丝绸逐渐淡出以“丝绸”命名的海丝之路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也即将走向终结。
四、茶叶出口:最后的余晖
在海丝之路上,茶叶是最后一种广为称道的中国商品。自1610 年荷兰商船第一次将中国茶叶运抵欧洲之后,饮茶之风在西方日益盛行,茶叶与咖啡、可可一道被称为欧洲人最喜欢的三种进口饮料,又伴随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传播到美洲、澳洲和非洲。随着西方人对饮茶的热爱与日俱增,自康熙年间起,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迅速增加;到嘉庆、道光年间,茶叶已取代生丝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由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出口茶叶的国家,茶叶出口又为中国及海上丝绸之路赢得了“茶叶之国”与“茶叶之路”的赞誉。经营茶叶贸易获利巨丰,是当时欧洲各国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手段之一。曾有法国商人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宣称:“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3](P72)
茶叶贸易不仅为西方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也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得以延续。然而到这一时期,日益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已远不满足于经营茶叶贸易所获得的利益。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他们更渴求将茶叶的生产利润也掌握到自己手中。为此,欧洲人不遗余力地尝试将中国茶叶引种到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内。
最早试种茶叶的是荷兰人。早在1827至1833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先后六次派人到中国学习种茶与制茶技艺,并带回茶师、茶种和器具在爪哇试种茶叶。而真正大规模引种茶叶的是英国人。18世纪末,马戛尔尼在率领使团访华时就曾在信中透露:“如果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17](P73)1834年,英国人在印度成立了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并授命雇员戈登到中国搜集大量武夷茶籽秘密运回加尔各答,并聘请到十几位四川雅州茶师向印度人传授种茶、收茶和制茶技艺,由此在印度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生产基地。183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将印度茶叶输入英国,中国茶叶一家独大的局面由此被打破。此后,印度的茶叶生产迅猛扩张,到1869 年输入英国的数量已突破1000 万磅,约占当年英国茶叶消费总量的10%。1870 年后,英国人又在锡兰(斯里兰卡)建立了新的茶叶生产基地。此后数十年间,锡兰的茶叶产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 年时,锡兰还仅有茶园13 个,产茶1300 箱;而到1886 年,其茶园已扩张到约900个,占地72万亩,年产茶叶2.88万吨。[6](P95)
印度和锡兰的茶园实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许多茶园还建有铁路,可以将茶叶直接运抵港口销往海外,其效率是仅仅将其作为茶农副业的中国茶业无法比拟的。加之此前粗制滥造之风已使中国茶叶的国际声誉严重受损,最终导致中国茶叶的对欧出口在印度茶和锡兰茶的夹击下败下阵来。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曾经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中国茶叶同样受到以近代工业武装起来的日本茶的猛烈冲击,一步步被排挤出美国市场。由此中国茶叶的出口量日渐萎缩,从其顶峰时(1886 年)的13.14 万吨滑落到1902 至1917 年间的年均9.57 万吨,再跌落为1918 至1940 年间的年均4.98 万吨,直至1945 年落入谷底,其出口量仅为0.48 万吨。[14](P160)短短五十年间,中国茶叶便从独占国际市场,坠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相比于丝织品、瓷器和生丝,中国茶叶的出口兴起得最晚,也衰落得最快,表明了中国的前近代手工业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面前已全无招架之力。生丝出口与茶叶出口相继没落之后,步履蹒跚的中国已无法再向世界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商品。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豆类、棉花、芝麻、植物油、猪鬃、羊毛之类的农产品原料成为了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曾经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中国,此时已彻底沦为向西方出口农矿产品与工业原料的半殖民地国家,绵延千年之久的海上丝绸之路最终走到了尽头。
结语
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约350年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由极盛走向极衰的巨大变动。这一变动是漫长的、渐进式的,与中国由一个向世界出口高端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到一个只能向西方(包括日本)提供初级产品的落后国家的历史转变互为表里。正如贡德·弗兰克所说,当16世纪西方人来到亚洲时,他们根本拿不出有竞争力的商品与中国进行贸易,只能依靠美洲白银“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而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展开,不久之后他们便“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到19世纪更“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15](P36-37)将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中。而在这一历史转变中,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由原本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变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供给养分的“输血之路”。随着其性质的根本改变,最终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场始于16世纪的巨大变动中,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主要中国商品,先是由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制成品变为了生丝、茶叶等中间产品和农副制品,最后又变成了豆类、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由高端到低端,呈现出一条明显的衰变轨迹。而不同商品出口的衰变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中国商品出口-生产技艺外传-本土商品发展-中国商品替代。在这一模式中,生产技术外传是导致中国商品出口衰落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国出口商品由高端向低端的衰变过程,正是西方(以光彩或不光彩的手段)对中国商品制作技艺的学习过程。也正是由于日本和欧洲对中国经济文化的长期不断汲取,掌握了中国商品的生产技术,才具备了与中国商品一争高下的能力,最终将其挤出了国际市场。
日本和欧洲之所以能在传统产业领域实现对中国生产技术的赶超,更在于中国自身的固步不前。日本人曾评价中国的丝织技术早在汉代便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大改进。正因如此,日本在掌握中国丝织技艺之后才能青出于蓝,到了近代反而将其丝织品销往中国。丝织品如此,瓷器、生丝、茶叶亦是如此。由于自身生产技术的发展停滞,近代以后,那些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中国商品非但丧失了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上也开始受到异国“学生”们的挑战,越发举步维艰。正是在这种进步与停滞的强烈对比中,海上丝绸之路走到了它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