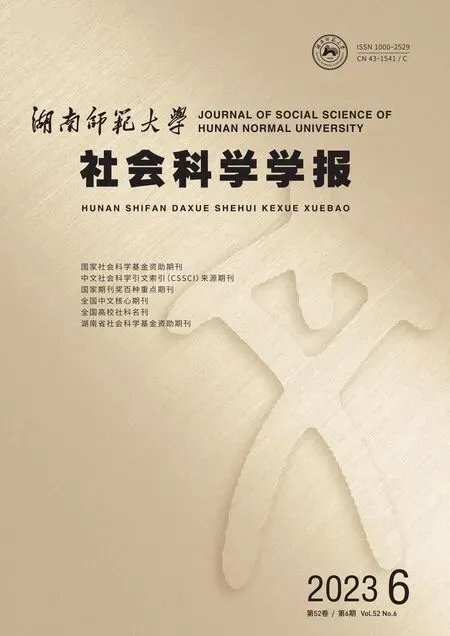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
渠嵩烽
明代诗歌瑰丽多姿,流派纷呈。在明代理学家中,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在探究心性义理的同时,阐发诗学思想,且热衷诗歌创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致力于将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因此形成了明代诗坛颇具特色的性理诗派。早期以薛瑄为代表,中期以陈献章、胡居仁等为代表,晚期以东林学人为代表①,东林学人中又以高攀龙诗歌影响最大。虽然他们的性理学说不尽相同,但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同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性理诗人的诗作多迥于时格,很少受到当时各种文学思潮兴衰嬗替的影响,也极少为文坛主流文学风尚所左右。将明代性理诗人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置于诗歌传统的视野中去考察则不难发现,他们秉持的诗歌传统大致可分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宋明理学家内部承续传统。
一、义理与性情:对《诗经》风雅传统的高度推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风雅传统的源头。汉儒对《诗》的经典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诗教思想,尤其《毛诗序》“温柔敦厚”的诗学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至深。宋代《诗》学的典型特征是以义理释诗。到了明代,《诗经》更是被理学家们奉为不容置疑、完备无缺的经典。他们认为,风雅传统自诗《三百篇》始,后世诗人承袭这一传统呈代际递减的趋势。元代理学家郝经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写道:“观圣人之所删定,至于今而不亡。《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1]他接着论述了历代优秀诗人的诗歌风貌,认为西汉苏、李之诗犹有三代遗风;唐代李、杜之诗力追风雅,但高古不及苏、李;而宋代苏、黄之诗又风雅不及李、杜;至于时人所追捧的前代其他诗人之诗更在以上几位之下。明代理学家陈献章亦云:“南朝姑置勿论。自唐以下几千年于兹,唐莫如李、杜,宋莫若黄、陈,其余作者固多,率不是过。乌乎!工则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遗意欤?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赞毁欤?发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欤?明三纲、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不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2]6随后得出“诗之工,诗之衰”的结论。陈献章在这里对李、杜、黄、陈的诗歌成就均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歌创作应秉持诗教传统,宗尚《诗经》遗韵,追求性情之真,裨补世教之用,不计赞毁,不媚世风。他也认为诗歌越是体制工整、声律严明,则越不能因承《诗经》风雅传统。与陈献章同出吴与弼之门的胡居仁也有类似的看法:
至周,则有《风》、有《雅》、有《颂》。《风》《雅》《颂》之中,又有赋、有比、有兴,则诗之体制已备。故说者以为三经三纬,又以六义名之。厥后世降风移,变而为骚,又变而为排韵,为顺体,为调,为律诗、联句,则诗之体制义理,性情风韵衰坏尽矣。[3]180
胡居仁认为《诗经》的体制已然完备,为诗歌创作和诗学审美的最高标准。后世诗歌在体制、义理、性情、风韵等方面均不及《诗经》,并呈逐渐衰弱之势。同时他还称:
世之谈诗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诗,清新飘逸,比古之诗,温柔敦厚,庄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乡人邦国,以风化天下者。殆犹香花嫩蕊,人虽爱之,无补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诗,有爱君忧国之意。论者以为可及变风,变雅。然学未及古,拘于声律对偶,《淇澳》《鸣鸠》《板》《荡》诸篇,工夫详密,义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仿佛也。[3]180
胡居仁对李诗的“清新飘逸”及杜诗的“爱君忧国”表示肯定,但在将李、杜诗歌与《诗经》比较后,却得出李诗“无补生民之日用”以及杜诗拘于声律对偶、失于工夫义理的见解。胡氏认为“温柔敦厚”“庄敬和雅”“工夫详密”“义理精深”,均为《诗经》风雅传统的品格,因此可以感人心、正性情、化天下。随后他给出了作诗的正确方法:“绝去巧丽对偶、声律之习,熟读三百篇,玩其词,求其义,涵泳讽味,使吾心之意与之相孚而俱化。”[3]180胡氏反对创作中对诗歌外在修辞、秩序和法度的过分关注,提倡通过反复吟咏《诗经》,使得诗心与《诗经》义理相符,从而达到融合无间的境界。
东林学派主要领袖高攀龙亦同样认可《诗经》的绝对经典地位,他认为诵读《诗经》就是涵濡义理,贯通其中的是统摄天地万物的自然之道。他在《〈言诗新艺〉序》中说:“吾读《三百篇》而知声音之道也。”[4]945又说古人“发之乎不得不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夫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自然之道也”[4]945。在他看来,先民作诗的内在驱动力就是“自然之道”,它具有形上意义,是统摄天地万物的最高秩序,这不同于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归纳出的认知经验,所以在道学未明的上古时期,先民无法以理性的方式感知,但他们用《三百篇》为后世树立了诗从道自然流出的最佳典范。高氏所言的“自然之道”无疑指向天理,所以他称此道“天地不能违,圣人不能违,万物不能违”[4]945。就高氏诗歌创作而言,清人王澍曾赞誉他对《诗经》风雅传统的继承,称其诗“能令顽廉懦立,无屈子之怨怼,而通乎《三百篇》温柔敦厚之遗”[5]。
《诗经》在明代理学家眼中成为后世诗人难以企及、不可逾越的高峰,他们多秉持“删后无诗”的诗学理念,认为天道弥贯流衍于《诗经》之中,故而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以风化天下。后世诗歌在形式上愈发追求精整,则去高古风雅的传统愈远。诗歌创作是否能得《三百篇》遗意,不仅成为明代性理诗人的自身追求,也成为他们诗歌批评的主要标准。明代性理诗人之所以高度标举《诗经》风雅传统,主要是基于理学对诗歌义理层面的规约。其中,“得性情之正”是其核心意旨,并最终引向政教风化,后文会详加阐论。
二、诚真与近道:对效陶传统的赓续与实践
陶渊明诗歌不仅多为世俗文人所推崇,而且也是性理诗人热衷效仿的对象。宋儒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云:
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邪?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尔。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6]
时人认为,陶诗虽然文辞高妙,但思想主旨源于老庄;邵雍诗歌虽然在文辞上平庸无奇,但主旨源本儒家六经。真德秀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渊明之学恰从儒学经术中来。真德秀对陶渊明的作品和人品均从儒学正统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陶渊明的自得心态与人格操守素来为理学家所看重,而他“豪华落尽见真淳”[7]的平淡诗风,与理学家天然本色、不着意安排的性理学说又不谋而合,故而被认为是最符合理学家理想的道德文章楷模。陶渊明在生活中对德性和善的追求乃是出于心性自觉,他独立率真、笃实诚悫的性情与平淡自然、质朴无华的诗风被理学家认为是存乎天理的表现。天理乃天然自有之理,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干预和操控的,性理学家认为人的本性即与天理相通。陶渊明其人其诗所显现的无伪、真率、潇洒的品格即理学家所追慕的与天理相通的自然天性。就常人如何恢复被遮蔽的天性,高攀龙就曾云:“果放得下时,即是直心,即是浩气,即是天然本色。稍着丝毫造作,即与本色天地悬隔。”[4]1293将这句理学论述视作陶诗发生的原理无疑也是妥帖的。薛瑄曾将四书、六经及宋代理学家著述比作雅声,而将百家小说、淫词绮语比作郑声,认为雅声澹而郑声甘,并总结说:“澹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8]748按照薛瑄的标准,陶诗当划为雅声之属。陶诗味淡,乃乐道者之言,读之能使人心平和,故而得见天理。薛瑄又云:
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词》、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8]816
薛瑄在这里将陶诗与《诗经》《楚词》并称,而对成就卓然的唐宋诗歌只字未提,可见陶诗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认为陶诗之所以经久不衰,乃是出于真情而作,是“不求工而自工”。陈献章同样推尊这种诗风:“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装缀,藏形伏影,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使人不可模索为工。”[2]100陈氏此处宗慕的诗风正是陶诗的特点,他的诗歌渊源,同样被认为主要来自陶渊明和邵雍[9]。胡居仁在诗歌创作中亦反复引陶入诗,无论是“羸却当年陶处士,萧然一枕卧皇羲”[3]224,还是“单父琴归闲宓子,浔阳菊绽老渊明”[3]241,均流露出对陶渊明的钦慕之情。
高攀龙似乎比前述性理诗人更加钦慕陶渊明,他称陶氏为“古大圣”[10]52“皭然不滓之人豪”[4]813。“千载怀同心,陶公调可仿”[10]20,慕陶自然会效陶,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陶诗为宗尚的文学群体,成员大致包括归子慕、安希范、陈龙正等人,效陶由此成为高氏诗歌的最大特点。高诗随处可见对陶诗语词的效仿、艺术化的处理和意象的袭用。比如高氏拟陶诗中有大量直接袭用陶诗成句的例子,如《题欧阳宜诸素风堂四首》其三“主人复何为,历览千载书”[10]15,后句引自陶诗《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11]184,均表达了通过读古人之书以追慕前贤之意。再如高诗《有鸟》“行止千万端,何能一其事”[10]22一句,借鸟能任情飞翔来说明人之趣舍万殊,进而引申出“人生各有志”的道理,前句直接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11]223袭引而来。高诗除了直接袭用陶诗成句,还有不少在引用过程中仅变更一字或两字的情况。如高诗《山居》“百营良有极,庶以善自悦”[10]14句申以人当知足行善为乐之义,陶诗《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则有“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11]128,同样表达了富莫大于知足的思想。再如高诗《舆中》“远望欲何为”[10]23与陶诗《饮酒二十首》其八“远望复何为”[11]226、高诗《独坐》“悠然见远山”[10]56与陶诗《饮酒》其五“悠然见南山”[11]220、高诗《八月四日从伯兄游山》“抚景有深怀”[10]54与陶诗《岁暮和张常侍》“抚己有深怀”[11]148等,不难发现,前者近乎直接袭取后者。高诗对陶诗的效仿,还多体现在对陶诗诗句和语词的艺术化处理以及对陶诗意象的袭用上,如高诗《水居》《水居漫兴》《采菊》《白云辞》《有鸟》等诗,通过对陶诗的改造,将其化为己用,无斧凿痕,妙趣横生,足见高攀龙对陶诗的喜爱②。钱穆先生曾编选《理学六家诗钞》,选录高攀龙诗歌近百首,并赞其“高淡近渊明”[12]。
高攀龙挚友归子慕乃归有光之子,与高氏一样,“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13]。如《城北初夏》云:
三见草木荣,栖栖犹未旋。偶与城市远,因耽此地偏。独馆背清池,一无俗事牵。晨兴课书罢,日午蛙声喧。出门见新秧,微绿映远田。久晴初得雨,稚子亦欣然。田父说岁占,今兹定有年。物情既如此,予乐复何言。[14]
此诗清新自然的诗风、质朴无伪的语言以及首尾多哲理的布排方式与陶诗颇类。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描写远离尘嚣的清幽孤寂,而是以看似散缓平淡的语言,提炼出初夏时节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日常场景,毫无着力地描绘出充满人性温暖的诗意田园,从而将诗人的性情显现出来,这恰是陶诗风神气度的关键所在。因归氏追慕靖节风范,故以“陶庵”为号,在当时已延誉江南士林。安希范经高攀龙介绍,曾慕名拜访归子慕,在目睹归家衡门流水、短墙疏篱的隐居风致后,感叹道:“周行篱落,徘徊庭户,默诵渊明诗,真无一语不合。”[15]63安氏同样讲学东林,素好为诗。他早年作诗步武唐人,晚岁踵美靖节,诗风为之大转,何乔远称安诗“清通简劲,无一毫尘心尘事”[16]14。如《法喜庵》:“道见三松秀,纡径聊停策。空庭何荒秽,窥户阒然寂。抚松久盘桓,一僧乃肃客。为煮阳羡茶,澹然意自适。”[16]47此诗虽为访僧之作,但体貌特征拟陶痕迹明显。“停策”“荒秽”“抚松”“盘桓”乃陶诗经典语典,略带荒寂的图景却不乏生趣,尾句同样自然而然地提炼出人生哲理,体现出诗人平和超逸的性情。此诗虽不及高攀龙、归子慕拟陶诗生动,但叙事、写景同样天然入妙。为了表达对陶渊明的钦羡,安氏曾筑一室,“名曰‘咏陶’,四壁尽列渊明篇什,讽咏其中,偶好有所合也”[15]135。连他出游时乘坐画舫的绮窗之上也置有陶渊明的画像。
陈龙正是高攀龙的门生,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效陶,而且还编选《陶诗衍》一书。他曾如此总结性理诗人高度推崇陶诗的原因:“陶性近道,故有道者之诗多近陶”[17]189,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诗宜以渊明为正宗”[17]188的观点。陈龙正还将高攀龙纳入历代效陶诗人谱系,极力表彰高氏的效陶诗:“豳风可以终变,则高诗可以终陶。”[17]189宋明理学家的诗歌创作观念相对保守,能为他们普遍推崇的中国古代诗人寥若晨星,而陶渊明便是其中一颗。“陶诗近道”是明代性理诗人崇陶的根本原因。
三、诗教与诗心:对崇杜传统的多维阐释与接受
与明代主流诗坛崇唐诗风不同的是,明代性理诗人往往对唐诗风韵表示不满,且对诗宗盛唐的文坛风气表示反感。如南中王门学派代表薛应旂曾云:“余尝谓唐人之诗独尚乎风,宋人之诗则雅、颂为多。间以语今之名能诗者,则以数百年来胶于见闻,皆不甚信。一则曰唐,二则曰唐,而三经六义几于湮灭矣。”[18]薛应旂对宗唐之风不满的原因是当时诗坛主流反对理学对文学的渗透,他们既关注诗歌真情实感的表达,又强调诗歌的体制、声律等外在形式。从李东阳的“格调说”到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观念都在试图以宋代之前尤其是唐诗的经典艺术形式消除宋代理学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明代性理诗人则认为宗唐之风有碍于理学的传播,因此,即使对李、杜这两位成就斐然的大诗人也颇有讥评。前文谈到胡居仁对李诗“无补生民之日用”及杜诗拘于声律对偶、失于工夫义理的批评,其《复叶怿上舍》诗云:“每怜汉士训诂苦,更悯唐人诗句磨。”[3]237怜悯唐人研磨诗句的言外之意是对唐人诗歌成就的轻视。与高攀龙交契甚密的东林学人许世卿同样“不屑屑习唐人声韵”[4]1319。陈献章观点与此相类,其称:
晋魏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2]13
陈献章和胡居仁认为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最大的问题在于“无补于世”,这显然是从诗教着眼进行评价的。他们对唐诗的声律、兴味、风神等文学质素或表示不满,或视而不见。然而陈献章在不同的情境下对杜诗又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曾说:“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19]在这里,杜甫诗和邵雍诗成了古代最优秀诗作的两个代表。杜诗既有格律精切的诗法,又有痌瘝斯世的情怀,而邵雍诗平淡自然、天机自露的道学兴味更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陈献章诗歌数量丰富,在创作上于杜、邵二家之妙有明显兼而得之的愿望。然而,“子美、尧夫之诗,其可得而兼乎”[20],这不过是陈氏设想的诗歌创作的理想状态罢了。陈氏又云:“作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予尝爱看子美、后山等诗,盖喜其雅健也。”[2]97雅健在这里又成了作诗的第一要素。与俗弱相对,雅健的意涵不仅含括诗歌审美趣味上的典雅雄健,而且带有对诗人刚强清劲的人格精神的强调,杜诗无疑是诗歌雅健之风的代表。胡居仁虽然认为杜诗拘于声律对偶且工夫义理不及《诗经》,但通过“圣贤名教外,细玩杜陵编”[3]226诗句的描写,仍可看出他对杜诗的格外关注。“细玩”一词说明他对杜诗是相当喜爱和熟稔的。薛瑄则对杜甫及其诗作推崇备至,他在《游草堂记》中称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8]558,故而在兵戈扰攘、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依然用诗歌抒发伤时悼乱、忧国爱民的情怀,这些诗歌在千载之后读之“尚能使之愤懑而流涕,感慕而兴起”[8]558。薛瑄不仅褒扬杜诗中具有诗史意义的部分,而且对除此之外的诗歌同样大为赞赏:
少陵诗曰:“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从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少陵诗:“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8]733
薛氏此处对杜诗的品评道味十足,“从容自在”“物各付物”的道学气象指诗人在无我的状态中洞察万物之理、饱享观物之乐的生命体验,这恰是前述邵雍诗歌的典型特征。不难发现,他虽然没有像其他理学家那样明确对杜诗工于声律对偶的特点表示不满,但依旧从道学角度品评杜甫及诗作。同样的角度,另一位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在谈杜诗时却多了一重经世致用的面向。顾氏友人朱肖桂笃好少陵诗,朱氏出守怀庆时,顾宪成作赠序:
夫诗者,心之精神所寄也,通乎政矣。子试举其所自为诗读之,其脉脉而来者,慈惠之所从生也;其泠泠而来者,法禁之所从生也;其浑浑而来者,德礼之所从生也。三者具矣,即怀庆运之掌上耳。夫少陵氏非工于诗者也,工于所以为诗者也。其忠君恻怛,爱君忧国,故自天性而终其身,偃蹇憔悴,郁郁无所托,乃时发之乎诗。至于今读之,靡不咨嗟叹息,徘徊而不忍舍,藉令生是时得当一郡,以彼其素,其建立宁在龚、黄诸君下也?伯子行矣,无论其诗,当遂并驱少陵,即龚、黄诸君且逊伯子矣。[21]
顾宪成认为诗“通乎政”,即诗歌和政理相通。朱肖桂效慕杜诗,其诗歌“脉脉”“泠泠”“浑浑”的特征并非仅指风格,更多的应指向诗歌的体性,因此能孳生出关乎政治方略和社会治理的“慈惠”“法禁”和“德礼”。这样一来,杜诗的功用就不仅仅停留于风教层面,而是在内质结构上与政事治用有款曲互通之处。究其根源,在于杜甫终身忠君忧国的天性。基于此,顾宪成在这里大胆假设倘若杜甫当年能得一郡而治,建树应不在汉代循吏龚遂、黄霸之下,并以此激励即将赴任的朱肖桂。学习杜诗,从而能更加有效地与政理相通是顾宪成崇杜诗论的发明之处。
高攀龙晚年重获起用,历任光禄寺少卿、太仆卿等职,他在京城写给友人的信中曾多次借用杜诗来抒发心绪,如“弟出山一念,实以君亲朋友三事,留滞经年,只诵得老杜两句:‘腐儒衰晚谬通籍’‘衮职曾无一字补’,辄汗浃背而已”[4]1298。此处高氏以杜诗自省、自励。未几深陷党祸,高氏辞任归乡,在功名遭削夺以及“东林六君子”被逮遇害的严酷政治环境中,他写信给友人缪昌期:“老杜云‘心弱恨穷仇’,此时正用得着。”[4]1173此处高氏以杜诗自怜、自叹。虽然高氏极少直接评论杜诗,且中年以后诗以效陶为主,但他早年修习性理学说时所作的诗歌,学杜痕迹较为明显。早期诗歌如《清流县登高》《西湖》《揭阳道中二首》等写得沉郁顿挫,雄强雅健,颇得杜诗真味。接续高攀龙主盟东林书院的另一位东林学人吴桂森则称赞老杜“忠愤有离骚之思”,其诗“含意深远,读之有无穷之感”[22]424,可见东林学人在诗歌崇杜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东林学人中深得杜诗精髓的应属黄尊素。黄尊素是黄宗羲之父,虽然他从未讲学东林,但因学术思想与东林学术相通以及他在东林党争中的特殊地位,黄宗羲将其划归东林学派。复社领袖杨廷枢在黄尊素逝后为其诗集作序,称自己在读过黄诗后不由地发出了“凡音之生,岂不系乎人哉”[23]25的感慨。杨氏认为诗之盛乃“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故,并盛赞杜诗曰:“三代而降,诗莫盛于唐,唐之诗无过少陵。吾尝取其言读之,至于琐尾流离、驱驰穷恶而不忘君国之难。缠绵激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今读其诗,慨然见其为人。”[23]25作为东林后学,杨氏在这里主要想表达的还是黄尊素诗歌所继承的杜诗忠君爱国的思想。就诗风而言,黄尊素在天启末年党争岁月中创作的诗歌慷慨孤直,激愤痛切,如《送万元白劾奄魏忠贤廷杖归》《闰六月朔》等名篇。而此前的酬赠、行役、怀古、咏物诸作,或实大声弘,或沉郁蕴藉,亦颇合“杜样”,如《大年兄可师不与考选》“从来天地为名累,到底河山急倚才”[23]54、《登金柱山》“山横天末云头迥,塔落波心日脚斜”[23]54,皆写得雄强逸荡,气格高壮。再如《早发中山》《大观亭望雨》等诗,则又呈现出杜诗的另外一种风格。《早发中山》云:
早发中山睡眼初,长堤浓柳隐征车。病多合为侵风起,马涩终因带雨余。陇麦渐黄怡妇子,村头正绿苦耘锄。况逢缺饷增输日,天意将何慰蔀居?[23]56
此诗乃黄尊素在行役途中所作,诗风以深沉和慷慨并举。诗人在描写自身多病、行路艰难之余,对国计民生表现出深刻关切。颈联所描绘的百姓一喜一愁的两种画风形成了强烈反差。尾联首句交待百姓愁苦的原因来自因国家缺饷而不断增派的税赋,最后则以对上天何以慰劳苍生的追问束尾。诗歌创作的背后正是明王朝因辽东连年战事严重缺饷而不停向下加派赋税的史实。黄诗对少陵“诗史”传统继承非常明显,除上述诗歌外还有很多,如《五月五日石臼湖中忧东事》写天启二年(1622)明朝军队在辽东战败事,《和李仲达骑马吟》写魏忠贤矫旨恢复宫中骑马之制事等,本文不再一一缕述。黄尊素将时事推见至隐,毕陈于诗,加之个人的生死沉浮与晚明政治紧密相关,使得黄诗的厚度优于其他东林学人。
明代性理诗人普遍反感宗唐的诗风,但于杜诗又难以割舍,所以在不同情境之下表现出疑杜和崇杜两种倾向。疑杜出于道学,崇杜同样出于道学。无论他们对杜诗作何品评,杜诗已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中所遵循的或隐或显的一种传统。
四、观物与体性:对《击壤》—白沙传统的内部承续
所谓《击壤》—白沙传统,是指以推崇邵雍、陈献章为代表的,同时涵括周敦颐、朱熹、薛瑄等理学诗人在内的,长期流衍于宋明理学家内部的一种诗歌传统。它具有独立于主流诗坛之外的创作特点和审美价值。南宋诗人刘克庄曾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24]可见当时文坛就已对理学家的诗论以及诗歌创作情况颇有微词。四库馆臣在薛瑄《读书录》提要中说:“自北宋以来,儒者率不留意于文章。如邵子《击壤集》之类,道学家谓之正宗,诗家究谓之别派。”[25]理学家创作的诗歌在世俗文人眼中并非诗歌正宗,而是旁门别派,其艺术价值自宋至清普遍不被主流诗家认可。无论世俗文坛对理学家的诗歌看法如何,后世理学家对前代理学先贤的诗歌一般都会鼓吹风尚,因此在理学家内部形成了因承有序的诗歌传统。方孝孺在理学思想上尊崇程朱,其《读朱子感兴诗》云:“其于性命之理昭矣,其于天地之道著矣,其于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系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无愧,虽谓《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亦可也。”[26]方孝孺认为朱诗可以昭性命之理、著天地之道且有功于道德人伦,即使与《诗经》相比亦不逊色。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云:
夫道以天之为至,言诣乎天曰至言,人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尧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颜孟大儒欤!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张、曰朱,其言具存,其发之而为诗亦多矣。世之能诗者,近则黄、陈,远则李、杜,未闻舍彼而取此也。学者非欤?将其所谓大儒者,工于道不工于诗欤?……夫诗,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2]6-7
陈献章认为周、程、张、朱皆为宋代大儒,他们是合乎天道之人,因此必有合乎天道之言,以上几位理学大家的诗歌正符合这种情形。虽然陈献章承认世俗文人多学李、杜、黄、陈而不以宋理学家诗为正宗的客观现实,但他并不认同当时学者所谓“大儒者,工于道,不工于诗”的说法,而是从道学的角度极力为宋代理学家辩护。他认为诗歌创作有大小用之分,宋代理学家的诗歌是“诣乎天”之言,其创作是大用,而世俗文人所追捧的“能诗者”之诗,是小用。此大彼小,宋代理学名儒诗歌在白沙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他又称:“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2]100陈献章此处仅选取程颢、邵雍作为学诗的榜样。
古代优秀诗歌数不胜数,但高攀龙在著述中提及的前人诗作少之又少。除了前文提到的《诗经》、陶诗、杜诗外,其诗论基本为性理诗派张目,引用的也多为宋明理学家创作的诗歌。他曾在《幽居四乐》诗中直抒胸臆:“我爱邵尧夫,缅怀发清吟。”[10]16高氏仰慕邵雍,罗宗强称高诗“有邵雍体的道味”[27]。“道味”即邵雍诗歌中以物观物、物各付物的思想。邵雍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则明,情偏则暗。”[28]意指以物的本性去观物,而达到去私无我的状态。而且,万物之间具有差异,不可以此观彼、同等类推,否则在认知事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偏差。高氏深谙此理,曾在讲学时数次提及,比如他在驳斥佛教慈悲观时曾云:
圣人因物付物,处之各当,而我无与焉,所以经世宰物,万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飞蠕动无不慈爱,顾使天下善恶是非颠倒错乱,举一世糜烂盅坏之不顾,而曰‘清静无为’也。呜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谓无理也。[10]223
高攀龙认为世间万物各得其所,虽有善恶是非之分,但将万物平等相视并不加分别地施以慈悲之心只会不辨善恶、颠倒是非。例如对蜎飞蠕动无不慈爱,于世道人心却冷眼旁观,这种慈爱和无为是“不仁”和“无理”的表现。高氏诗歌创作受邵雍观物论影响很大。如《水居诗五首》其一:
到此情偏适,安居兴日新。闲来观物妙,静后见人亲。啼鸟当清昼,飞花正暮春。呼童数新笋,好护碧窗筠。[10]57
“以物观物”的思想反映到诗人身心状态上最大的特点即闲、静二字。高氏此类诗歌基本都呈现出闲适安静的生活情态,而没有以人之复杂的情感去附会、比兴眼前所见之物,从而使万物本真的生命状态得以彰显。如颈联“飞花正暮春”句毫无悲凉之致,反而生意盎然。在理学家看来,一般诗人感时伤春的描写,势必以“我”之私情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难以窥见衍化其中的生生之理。再如《见月》《题画》等诗,基本上都描写了各类景物各得其所的自然状态,诗人藉此体悟天理并饱享观物之乐。
高攀龙爱引前辈理学家诗歌自省、勉友或励人。如薛瑄易箦之际的《临终口号》一诗被他多次引用③。高氏对陈献章诗歌也颇为欢喜,其《书左泉刘君扇中》云:“陈白沙先生诗曰:‘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余每诵之,以为安乐法。夫千休者,休其妄,一持者,持其正也。”[4]998晚岁归乡之后,曾在与友人的信中以陈诗互勉:“白沙诗云:‘廊庙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知吾丈闲忙总不徒然矣。”[10]525作为以程朱正脉自居的理学家,朱熹诗歌自然是高攀龙崇拜和模仿的对象。朱熹《日用自警示平父》诗云:“圆融无际大无馀,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时勤猛省,却于何处味真腴。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更莫疏。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29]此诗完全阐发性理,主要强调了收敛整肃的主敬工夫在平常日用中的重要性,高攀龙曾反复引用,不仅以之与顾宪成讨论格物之理,还抄录此诗勉励季子高世宁④。受朱熹影响,加之“人心至闲,自有无腔之韵悠然而来”的心口相念,高攀龙创作了大量的言理诗,如《静坐吟三首》《戊午吟二十首》《丁未三月水居静坐》《庚子十月作括语二首》等,构成了高氏诗歌的另一大特色。如《静坐吟三首》其一:
静坐非玄非是禅,须知吾道本于天。直心来自降衷后,浩气观于未发前。但有平常为究竟,更无玄妙可穷研。一朝忽显真头面,方信诚明本自然。[10]116-117
静坐是高攀龙理学思想极为重要的工夫实践,此诗首联开宗明义指出儒家静坐与佛道静坐的本质不同,颔联讲静坐的目的是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性,颈联给出静坐的方法即平常自然,尾联交待静坐的结果是复见天性而获得“真头面”。与朱熹《日用自警示平父》一样,语言通俗,说理邃密。再如《戊午吟二十首》组诗,作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时高攀龙五十七岁,理学思想已醇熟圆融。诗歌均以七律写成,几乎浓缩了高氏性理学说的全部精要,阐发了天、人、生、死、诚、敬、心、性、动、静、本体、工夫等理学经典命题。这些专以举道的学术诗,与高氏讲语、序跋、尺牍等著述中的性理学说相互呼应,继承了宋明理学先贤诗歌纯粹说理的一脉传统。
同样创作了大量学术诗的还有晚明著名理学家冯从吾。冯氏既是东林学人,又是关学领袖,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相比,他有着更为严厉的文道观,对文学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时表现出否定文学的倾向。冯从吾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时,文名颇盛,时人赞其“既擢上第,游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竞相手录”[30]123。虽然“庶吉士的日常考试,也多以诗文为主”[31],但冯氏现存文集中,留传下来的文学性较强的诗文作品极少。“少墟并不关心诗文的技法修辞和审美风格,而是力求从创作理念等思想层面进行干预”[32],因此,他编著《理学诗选》,并在序跋中说明选录标准及理学诗与唐人诗之异同。其称:“选理学诗与选唐人诗异。选唐人诗,论诗不论人,所谓人以诗重也;选理学诗,论人方论诗,所谓诗以人重也。呜呼,学者将人以诗重乎?抑将诗以人重乎?读是编,可以自悟矣。”[30]325冯氏选诗重人而不重诗,此处“重人”并非仅指重视诗人的品性,而更多的是指理学家诗人的为人、为学之道。序中理学诗与唐人诗之辨,暗含的是冯氏崇尚前者、贬黜后者的诗学理念。冯从吾的诗歌实践显示了与这一理念的一致性。冯氏现存诗70首,除《喜晴》《寄怀邹南皋先生》《七十自寿》等几首外,其余皆为纯粹的学术诗歌,且从一些诗题就能反映出所写之大概,如《善利图》《自省吟》《勉学》《读〈易〉复卦》等。高攀龙、冯从吾对宋明理学家学术诗歌创作传统的实践,其目的乃陈龙正所言“譬如禅家之有偈,术家之有歌诀,不过假借宫商明宗传要”[33]2236。由此可见,诗歌不过是传播理学的一种工具,功利性和实用性是学术诗的主要功能,但从反面也印证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理学传播中的显著优势。
吴桂森同样标榜宋明理学家诗人,他在《息斋笔记》中多述宋明性理诗论,在比较理学诗和唐人诗优劣高下时,吴氏比冯从吾更加直接、果断:
今之论诗家曰:“愁苦怨恨,非佳境也。惟入诗,则无不成佳”,此唐人活计也。自《击壤集》出而尽翻此境,满目乐趣,四者只字不入口。我朝白沙继其响,脱换无复此态,盖其方寸间迥乎霄壤别尔。乃知诗家所云唐以后无诗,有识者正谓宋以前真是无诗耳。[22]439
吴桂森认为以愁苦怨恨入诗是“唐人活计”,这显然不符合性理诗人抒发性情之正的创作要求。邵雍、陈献章之诗一改唐人境界,私欲净尽,天机流行,故而“满目乐趣”。吴氏遂以“宋之前无诗”来抗衡“唐以后无诗”的主流诗论。唐后诗人灿若星辰,他在这里仅将邵雍、陈献章悬为榜檠,仍旧不出性理诗人的范围。就“满目乐趣”、天然自得的诗歌美学脉络,陈龙正同样认为“此脉自莫春咏归以来,《击壤》、白沙跻其巅矣”[34]。
前辈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是留给后辈理学家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虽然它们被主流文坛轻视,但在性理诗人内部却成为讽咏、效仿和赓扬的对象,流风未沫,代代因承,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个关注度不高且较为封闭,但生命力异常顽强的诗歌传统。
五、明代性理诗人诗歌传统的四重理路
明代性理诗人兼有理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深入考察他们的诗歌传统,就必须充分观照他们的理学思想。高攀龙称:“学不在多言,只变化气质,涵养性情。一切五常百行,皆以此为本,然非见道不能。”[10]537“见道”是理学家生活中一切活动的宗旨和目的,这其中自然包括诗歌创作。道成为明代性理诗人统摄诗歌创作的总纲,他们认为优秀的诗歌必须是见道者之言,是道的自然流露。据此,诗歌成为性理诗人体会性道的一种工夫。然而,诗歌的本质是人自由情感的表达,而理学的旨趣是对自由情感的克制,两者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廖可斌就曾指出理学与文学关系的实质:“文学本质上是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它必须以人们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作为反映和表现的对象。从思维的旨趣到方式,理学与文学都是相互排斥的。因此,自理学诞生之日起,它就与文学势如水火,互不相容。”[35]但与上述结论全然相悖的是,基于理学家身份的性理诗人认为两者是本末分明而又浑然一体的关系,以上四种传统恰好体现了这一关系何以成为可能的四种理路。
其一,性理学家对诗歌情感内核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朱熹《诗集传》序:“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36]朱子在这里将二南与“性情之正”相标榜,对明代理学家“性情”诗论影响深远。如与东林学人过从甚密的理学家邹元标曾如此强调“性情”的重要性:“《三百篇》出自里巷歌谣妇人女子,学士经生鲜或之及,谓其有得性情之正故也。”[37]在朱子之后,“得性情之正”成为性理诗人对《诗经》情感接受的普遍认知。虽然他们对“性情之正”的阐释各有侧重,如前文提到薛瑄推赞发自肺腑的“真情”,而高攀龙重视爱憎不栖、忧喜不留的未发之情,但这种“性情”基本上指性体约束的正情,而非气质杂驳的凡情,最终有伸向政教和道德的意涵。到了明代后期,东林学人将程朱理学重新拉回学术思想主流论域,为了抗击王学末流空疏狂荡、滥情纵欲的风气,他们对性情观的持守似乎比明代早中期性理学家更为严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得性情之正”是性理诗人对诗歌情感质素的根本性改造,是诗歌与理学能够得以融合的第一要义。
其二,性理学说中暗含了潜在的文学思想。明代理学家的性理学说极为丰富,有些并非特指文学而言,但理一万殊,它们与文学思想之间存在转化机制。比如,明代理学家经常强调自然本色的体认工夫,它本指在性道的体悟和践履中要遵循天然本色的原则,反对刻意安排,反对矫揉造作,否则将难以见性。而这种自然本色观既是性理诗人诗歌发生的原理,又是他们诗歌创作的方法。再如,晚明理学家本体论中高度重视“淡”的思想,如冯从吾称:“‘淡’之一字原是性体。吾性中一物不容,何其淡也!无物而万物皆备,又何厌之有?”[30]156冯氏将“淡”作为本体的存在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即一切后天修饰。因此,冯氏理学中所崇尚的“淡中滋味”反映到诗歌审美中指平淡而不加过度修饰的风神体貌。此外,性理学说中的乐、仁等思想也同样能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他们的诗歌审美领域,兹不赘述。自然、本色、淡、乐、仁等既是本体,又是工夫。换而言之,它们既是道本身,又是见道的方式,这种体用思想落实到文学的批评和创作层面就有了相对直观、具体、简便的操作空间。由此重新审视陶诗,即便不谈陶渊明的高尚品格和自得心态,其诗歌就已然兼得以上性理学说中的各种“潜文学思想”,故而深为明代性理诗人所推崇。但在理学家看来,陶渊明其人其诗是不可二分而论的,因此引出他们诗歌传统的下一重理路。
其三,重人不重诗的诗歌批评观。明代理学家在为他人诗集作序时,有一种近乎程式化的评价范式:对诗歌的修辞手法、艺术风格几乎不谈,特重对诗人德行和品节的描写。可以说,他们对诗歌作品的批评从来不会独立于品评作者的品性之外,这源于性理诗人“人伦即理”的理学思想。高攀龙《气心性说》称:“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为,如五德、五常之类,生民欲须臾离之不可得。”[10]222高氏认为,天理是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能干预。人性来自天理,故而人性本善。人伦中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与五常(亲、义、序、别、信)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是人们须臾不得离开而必须遵循的天理所在,它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恪守人伦即恪守天理。值得一提的是,理学家对人伦纲常中的忠义思想尤为重视。杜甫诗歌中的君臣观念、社稷意识和民生忧虑无一不是从这种思想衍化而生。在明代性理诗人看来,杜甫的忠义思想与天理相通,或者说就是天理的组成部分,因此杜诗被他们高度推崇。而疑杜则因杜诗对诗歌技法的重视与上述第二重理路相悖。不过,越到明代晚期,性理诗人的疑杜风气越发式微。社会形式的急剧恶化,使得他们不得不借鉴杜诗去表现沉重、雄伟和沧桑的历史现实主题,而闲适自得的诗风显然已不再适合历史潮流,尤其在明清鼎革之际,东林后学复社、几社的主要成员将崇杜传统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其四,理学家身份的特殊意义。因为以上三种理路的思想渊源均在理学,所以很容易理解明代性理诗人对宋明理学家诗歌传统的内部因承。前文提到,文学和理学在性理理论上是高度融洽、浑然一体的关系。为了保证自我诠释理论的完备性,在理学家的语境中,性理诗歌就不可能劣于其他诗歌,性理诗人似乎具备创作优秀诗歌作品的天然优越性。这种优越感并非他们的主观自信,同样有其学术渊源。高攀龙云:“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10]199高氏认为天下大本在学术,因为学术关乎人心正邪、政事兴衰。他在晚年起复入朝后给首辅叶向高写信时又说:“龙腐儒,以学为事,出山一番,何可不劝皇上以学?实则天下事以君心为本,若谓为迂,孔、孟当年更迂矣。”[4]1240高氏称君心为天下事之本,而学术是天下事之大本,君心同样需要学术来规范。高氏所言学术并非其他,即程朱理学思想。按照他的观点,理学家所建构的道统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源,君统、政统、文统均要受其制约。事实确是,他们中的一批学者在思想界和政治界都有着崇高地位,掌握着官方思想解释权,在维护社会世教纲常、引领社会主流价值等方面发挥着一般文人不可比拟的作用。鉴于道统论对社会各向度的统摄,理学家在获得道统合法性的同时又要获得文统的权威性,也可以说是他们对理学和政治之外的最重要的一种言说权力的攫取。诗歌仅为文学之一种,因此自在其列。这是宋明理学家诗人内部承续传统的深层原因。
结论
明代性理诗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接受和实践是基于理学家身份进行的,背后有其深厚的学术渊源。通过考察他们遵循的《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宋明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我们可以找到其背后支撑的学理依据,而这种依据恰为理学视阈下诗歌和理学能够完美融合的四种理路。明代性理诗人从理学思想上规约了诗歌的内质结构、外部体貌以及诗人的德行品格、学术素养,在理论上有效解决了哲性与诗性的本质冲突。由于《诗经》兼备理学与文学双重经典的特征,因此其风雅传统更多的被他们奉作一种完备无缺、不容置喙的经典诗论。但正因对经典的极度推崇,《诗经》对性理诗人的影响多局限于精神指导与价值判断等宏观层面,在具体诗歌创作中反而体现得较为隐微与内敛,故具有“悬置”的意义。效陶传统在明代,尤其在理学工夫内转的中晚明时期大受性理诗人追捧,但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仍旧是有限度的。如东林学人钱一本称:“陶大节著矣,然圣贤达有达之事可做,穷有穷之事可做,寄情诗酒,未脱江左余习。”[22]428陈龙正对陶诗推崇备至,但也曾略带遗憾地对其人发出“性与天道犹未知何如”的感慨[33]2250。就崇杜传统而言,因伴随着一些理学名家较为明确的疑杜诗论,自然立于这一圈次的最外层。综上,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揭示了理学在他们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中的根本性和优先性。假使我们脱离理学谈论上述诗歌传统,就无法获得它们在理学家眼中的“真实”性状,从而无法进入相对深邃的阐释空间。因此,理学家的学术和文学并非孤立的两个领域,两者的关系也不仅是前者影响后者的简易模式,而是呈现复杂共振的状态。从《诗经》到陶渊明,再到杜甫以及宋明理学诸家,明代性理诗人自我建构的诗学谱系虽然见绌于主流文学论域,却寓示着理学家自有诗学传统和学术精神的传衍不绝。
注释:
①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最先提出“东林学派”概念,他在《明儒学案》的“东林学案”下开列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顾允成、史孟麟、刘永澄、薛敷教、叶茂才、许世卿、耿橘、刘元珍、黄尊素、吴桂森、吴钟峦、华允诚、陈龙正等十七人,用四卷篇幅缕述学派的思想学术精要。按照黄宗羲的界定,东林学派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以东林书院讲会的参与者为主体构成的明代江南地区的区域性学术流派。在成员构成上,尹楚兵在《明儒学案》所列十七人外,增补安希范、冯从吾二人(《东林学派著作集成·前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据此,本文所称“东林学人”主要是指上述东林学派的十九位成员。
② 参见渠嵩烽《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 详见《高攀龙全集》中《高子遗书》卷之八上《答曹真予论辛复元书》以及卷之十《薛文清公传》。
④ 详见《高攀龙全集》中《高子遗书》卷之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其三、《高子未刻稿》射部《书朱文公“圆融无际”诗示季儿》以及高氏后人高汝琳辑《高氏三世诵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