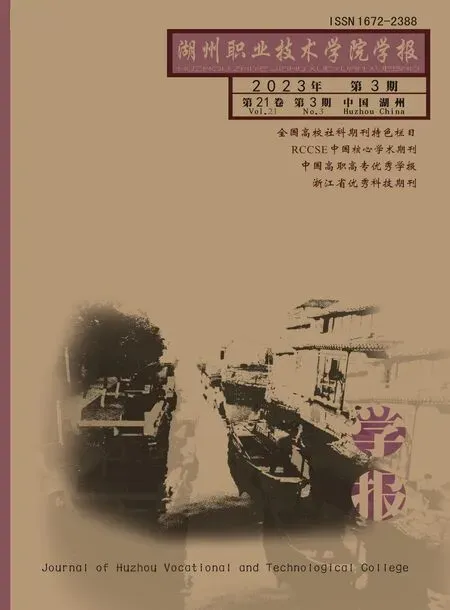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火男面具》中的面具意涵考述
赵海涛 , 邓淑琴
(江西师范大学 日本学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学术界关于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的研究,多认为发表于1915年9月的《罗生门》是其文坛亮相之作。事实上,早在1914年12月,芥川龙之介就完成了小说《火男面具》的创作。随后,该小说发表在翌年5月号的日本文艺杂志《帝国文学》上,这比《罗生门》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时间还要早4个月。但是,该部小说鲜为人关注。《火男面具》讲的是一个名叫山村平吉的戴着面具的中年男子,醉酒后在船头跳舞,骤发脑出血并猝死的故事。
百余年来,《罗生门》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文学影响力,被奉为经典。相比之下,《火男面具》则常被忽视或鲜少被关注。对其难得一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3年的日本学术界:西座理惠将《火男面具》与日本江户时代的怪谈物语相联系,勾勒出二者之间隐含的复杂而多维的关联性[1]62-78;水野亚纪子则着眼于作家所处的日本大正时代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从芥川龙之介早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往前追索,指出《火男面具》所折射出来的批判意识[2]73-85,等等。这些研究有的讨论作品对日本传统文艺的传承和接受,有的发掘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批判与关切。对于此时尚未形成稳定的文学创作风格,在写作上尚未火力全开的芥川龙之介而言,这样的论调是合理且中肯的。外在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起主导作用的终究是内因。作家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来呈现自身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认知。《火男面具》通过戴在主人公脸上的“面具”和言行举止中无形的各种面具渐次展开叙事,讲述了山村平吉与面具之间存在着的人格面具化和面具非人格化的复杂关联性,并使其贯穿于小说主人公逃避自我、表现自我、丧失自我,最终重建自我的整个动态过程。
一、戴上面具的原因:逃避自我
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年)在《面具之道》(1975年)中对面具有着精彩的论述:“单从造型方面来看,一种类型的面具是对其他类型的一种回应,它通过变换后者的外形和色彩获得自身的个性”,这种被赋予了社会的或者宗教的功能的面具,“存在着一种跟面具本身的造型、图样和色彩之间的相同的变换关系。”[3]19诚如斯言,《火男面具》的主人公山村平吉在戴上面具前后,其在行为举止、语言表达等自我与外在关联性的应对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个性。而面具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戴面具之前的男主人公山村平吉。小说用三件事来呈现男主人公早年的人生际遇。第一个故事发生于平吉11岁时。此时,他在南传马町的纸店当学徒,他的老板狂热地信奉法华宗。为了祈求合家安宁,纸店老板一日三餐都得先念诵一通“南无妙法莲花经”。尽管他如此虔诚,他的老婆还是与店里的一个伙计私奔了。“这下子他大概觉得法华宗一点也不灵,就突然改信门徒宗,忽而把挂着的帝释画轴扔到河里,忽而把七面的画像放在灶火里烧掉,闹得天翻地覆。”[4]25而身为旁观者的平吉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第二个故事是平吉二十岁前与一位妓女私下来往,委婉拒绝了妓女提出的两人去殉情的想法,却在三天后获悉妓女已经和首饰店的工匠殉情自杀的新闻。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平吉二十岁之后,此时他的父亲已亡故,被父亲一代雇佣的掌柜卷走了店铺的一大笔资金并逃之夭夭。而就在事发前,掌柜正是让平吉代笔写信向老相好通风报信,为偷盗财产和逃跑作了准备。平吉早年经历的这三个故事,不论是纸店老板笃信宗教最后落得一败涂地,还是与自己交好的妓女转身就和其他男子殉情,亦或是以为是忠心耿耿的老掌柜席卷家里的钱财后逃遁,皆从事业、爱情和家庭等三个维度对平吉进行了全面打击。其中的辜负和背叛、虚伪和算计,使得原本对生活、对世界充满信任,对自身充满自信的平吉对生活逐渐失去了信心,对周围的人和事充满了疑虑,甚至通过各种“瞎编的”谎言来与外在世界周旋。
对于经历了各种被算计、被欺骗之后的早年平吉,小说是这样描述的:“要是从(人们所知道的)平吉的生平中抽掉这些谎话,肯定是什么也剩不下了。”[4]26此言不虚,身处背叛和欺骗旋涡且无力自拔的平吉,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但是强烈的自尊心又不允许自己承认失败,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了逃避自我的态度。而要做到自我逃避,就只能通过隔断或者割裂与外部世界各种联系的方式,达到自我隐藏或者在他人的已有认识中消失或者发生改观的目的。而戴上面具就是山村平吉逃避现实自我的最好手段。
二、面具的作用:重构自我
《火男面具》中的山村平吉既是一个具备自我意义上的个体,也是一个具备社会性意义的社会成员。他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企图在群居社会中隐身匿迹和自我逃避,也无法割裂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关系,也无法抹杀自身固有的社会性。小说中的山村平吉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自处、如何与社会相处。如前所述,面具既是一个具备遮蔽功能、有利于山村平吉自我逃避的媒介,又是一个有助于男主人公以一个崭新的、不同以往的面貌表现自我的工具。
荣格在《心理类型》一书中写道,人格面具(persona)“是由于适应或个人便利的原因而存在的一种功能情结”[5]394,其“具有与外在世界缺少联系的特征”,而且“极其容易受无意识过程的感染和影响”[5]395。山村平吉在乏善可陈的前半生中遭际了无数次的背叛和欺骗,但他还需要面对接下来的社会生活。因此,他需要借助面具来遮掩或者屏蔽不理想的生活以及不希望为人所知的信息,展示出自己想要表现出来和希望被他人关注到的信息,甚至需要戴面具来抵御外在威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火男面具》中的山村平吉正是通过面具这一形式,来完成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合作,以及在搭配层面上的某种意义上的妥协。这亦是一种企图重构自我身份的伪装术。
小说对于山村平吉的外貌介绍很具体:圆脸盘,头顶略微有些秃,眼角上亦有细碎的皱纹。他待人一向谦恭和蔼,但是还有那么一种滑稽劲头。而山村平吉戴着的火男面具(日语原文为:ひょっとこ)是日本近世平民社会中流行的一种“火男舞蹈”中的面具,其造型呈现为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噘着嘴的丑男子模样。这种传说是根据男子吹火时的表情设计出来的火男面具,表情浮夸滑稽,与虽然称不上是美男子,但是模样仍算周正的山村平吉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将原型“丑化”的面具除了自带的娱乐功能外,所具有的意义是复杂多元的:一方面,作者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面具后的主人公本来面目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以一个新的“山村平吉”形象取代原有形象,使得周围的人们无法看清楚面具后面的山村平吉真正的喜怒哀乐,看到的只是展现火男舞蹈表演的“山村平吉”的一个虚像。除了具体的实物火男面具,小说中不戴实物面具时候的山村平吉却又戴上了无形有实的隐形面具,即他的三个代表性行为----扯谎、醉酒和跳舞。
扯谎是山村平吉在社会交往中戴的第一个隐形面具。小说坦诚地指出再也没有比平吉更爱扯谎的人了。一方面,扯谎没有给平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但是他在扯谎的时候,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扯谎,完全来不及考虑后果;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自然而然又不由自主地扯谎,平吉并不感到苦恼,也不认为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情。现实生活中,谎言的发生多基于撒谎者自身的虚荣、自尊、自信、自卑等心理,以及掩饰、牟利、泄欲、爱慕、仇恨等动机。但无论是基于何种出发点,谎言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即促使撒谎者与真理事实越行越远,甚至会为了遮蔽真实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与选择,使自身的利益受损、情感受到伤害,甚至让自身人格尊严被贬损、自身价值功能遭到损伤与崩坏。
醉酒是山村平吉在社会交往中戴的第二个隐形面具。与常人出于生理需要的喝酒不一样,平吉喝酒是心理上的非喝不可。因为他一喝酒胆子就大了起来,觉得醉酒后对谁也不必客气了,“想跳就跳,想睡就睡,谁都不会责怪他。平吉对这一点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4]24。山村平吉的醉酒并非是生理需求,而是为了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他只要醉了酒就可以从现实中的种种被动中解放出来,就能打破各种教条规矩,无视等级荣辱,使得平日中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因此,深谙醉酒妙用的平吉通过醉酒来消除横亘在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并谋求真正意义上的跨越。正如《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言:“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在这里,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臻至‘太一’最高的狂喜满足。”[6]26平吉在醉酒刺激中忘却俗世的纷扰困窘,在麻醉中品尝欲望的腾空释放和自由的彻底狂欢,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酒神哲学家”。
跳舞是山村平吉在社会交往中戴的第三个隐形面具。平吉在早年纸店学徒期间跟着老板娘学会了跳舞。虽然学的是日本祭祀神乐中的巫女舞,但是平吉学得走样,他所跳的舞并没有达到歌舞伎中的僧侣舞蹈喜撰舞那般淫乱下流程度。然而,在周围人眼中,跳舞的平吉俨然是乱跳一气,活脱像个小丑。没喝酒的平吉老实本分,决不跳舞,一旦喝了酒,“马上就把手巾扎在头上,用嘴来代替笛鼓的伴奏,叉着腿,晃着肩,跳起所谓火男舞来”[4]23,继而得意忘形,不论旁边的伴奏是歌舞伎的三弦还是民乐的谣曲。除了与醉酒相同的体验感受外,任性舞蹈促使山村平吉大尺度地释放了自己的欲望,这也为接下来他醉酒后在船头舞蹈中的骤病猝亡埋下了伏笔。
三、戴上面具的后果:丧失自我
面具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祭祀、悼亡等表演活动中,期间表演者佩戴面罩或者面具,面具因此成为一种物质化和符号化的存在,后来被运用到了舞蹈、剧作等各种文艺演出活动中。面具既是一种伪装术,也是一种迥异于原型的变形,它既有物化、符号化的存在形式,亦有抽象化、精神化的存在形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另一本代表作《面具的奥秘》中主张“一个面具的类型,在与那些线条、色彩上起了变化的其他类型作反复地比较之后,才能被人认识,才能假定它自身的独特性”,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转换关系”[7]13-1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里提到的“存在着共同的转换关系”的实质是佩戴面具的人和所佩戴的面具之间存在的某种“同源共生”关联性,只有具备这个关键的相同点,二者之间的转换才能发生并完成。
《火男面具》中的山村平吉由于早年的不幸遭遇而怀疑世界、不信任他人,对自身抱有自卑感,企图通过扯谎、醉酒和跳舞等方式来麻痹和隐藏自己。这些方式与面具具有同样的功能。面具通过遮蔽表演者的真实面貌长相,或夸张或简化或淡化或渲染其表演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地摒除表演者个体自带的斧凿痕迹。山村平吉在日常生活中(不戴面具时)和蔼近人,待人接物唯唯诺诺。没喝酒的时候别人逗他跳舞,平吉都会打个哈哈敷衍过去;一旦醉酒之后(戴了面具时)他就忘乎所以地跳起来,不在乎节奏,也不关心舞蹈的类型,成为前文所说的进入醉酒之境的“酒神哲学家”。在这个时候,面具的佩戴正是小说主人公山村平吉与火男面具舞蹈演员之间能够形成“共同的转换关系”的必要条件。
但是,面具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有助于小说主人公山村平吉有效地隐藏自己的原型,通过扮演新的人物形象,让自己向理想的新社会形象的转型,使自己与现实中存在感较弱的原型自我划清界限。然而,面具也给人物本来面目带来了不可逆的破坏性损伤。虽然佩戴着面具,但是山村平吉并非是戴着面具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而是借助面具重建自我的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个体的平吉和作为“物”的面具在发生交集之后又产生激烈的抵牾和对抗:一方面,酒醉后戴着面具的平吉期待通过在船头跳火男舞蹈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新面貌、新形象;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特定条件和场合,人格面具又不得不符合其身份及社会环境的期待与要求。男主人公山村平吉在船头醉舞是小说的高潮,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场盛装表演。小说中写道:“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褪下了秩父(日本地名)铭仙和服上身,露出里面那件漂亮的友禅内衣。内衣的袖子是白地蓝花,黑八领子邋里邋遢地敞开来,深蓝色腰带也松了,在后面耷拉着,看来他已经酩酊大醉。当然是乱跳一气,只不过是来回重复神乐堂的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而已。而且酒喝得行动好像都不灵了,有时候只能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为了怕身体失掉重心从船舷栽下去才晃动手脚。”[4]21-22平吉虽然醉酒,但此时盛装舞蹈的他既尽兴又卖力,即便是反应都有所呆滞,仍然竭尽全力地舞动手脚继续舞蹈。而对于眼前小丑般的表演,岸上观众却始终只是报以无穷的嘲弄和起哄。甚至有观众喝倒彩,喊叫道“还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呢”。如果说戴面具跳舞是平吉企图重建自我的一番努力,那么来自观众的喝倒彩和嘲笑则是对他这番努力的完全否定,可谓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胜酒力且体力不支的平吉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在船头的表演中重重跌倒,穿着棉毛裤的平吉两脚朝天,一个跟头滚落到驳船的篷子里去了。对于平吉的意外跌倒,岸上的观众依然报以哄堂大笑。这一方面说明了平吉重建自我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外在的社会期待与要求对于平吉这种面具人格的全盘否定。在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之下,正如蹉跎挫败的前半生那般,成年后的平吉即使让自己的人格面具化,即便认为戴上面具后醉酒舞蹈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也依然无法符合外在环境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念。
四、摘掉面具:还原自我
山村平吉滚落到驳船的篷子之后,大家都以为这是他有意设计的恶作剧,船上的头头以为平吉又闹着玩,正准备发脾气时,才发现平吉纹丝不动。就在大家对平吉的意外情况不知所措时,火男面具底下传来低微的不知是呼吸还是说话的声音:“把面……面具摘了……面具……”[4]27在帮平吉摘掉面具后,众人惊奇地发现火男面具下面的脸,已经不是平吉平时的脸了:鼻梁塌陷,嘴唇变色,脸色苍白,还淌出来黏汗。这张让人陌生的脸使大家觉得现在的平吉与平素那个和蔼可亲、喜欢打趣、说话娓娓动听的平吉完全是两个人。戴上面具是平吉谋图改换已有形象的手段,那么在生命最后时刻请求卸下面具的平吉则是对戴面具的人生进行了否定和颠覆。这是在经历俗世沉浮之后对自己人生的深刻沉淀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定位的再一次确认。如果说山村平吉在船头丧命之前的面具人格,发端于人物对外在环境的积极迎合,是一种特定环境、特定语境下的,不得不削足适履的行为转换的话,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拆除遮蔽的面具,露出本来面貌的山村平吉更具现实意义,虽然这张脸在众人眼中根本不是日常生活中平吉的那张脸。这既是平吉一生中最后自我确认和自我认识的高潮阶段,也是主人公对逼迫弱者要戴着面具生存的虚伪的人世间的决裂与反抗。
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芥川龙之介与同窗好友共同推进《新思潮》的复刊工作,并成为该杂志的同人。1914年1月21日,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的芥川龙之介在新宿给同窗好友恒藤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我是新思潮的一个同人。没有发表过作品,只是准备发表作品。……我翻译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短篇小说,然而至今对我的文章没有帮助,实在无奈。在同人中,文章最糟糕的是我,心情甚为不快。”[8]46从芥川龙之介的书信可知,他虽然积极参与《新思潮》杂志的第三、四次复刊工作,但并未在文学创作上有所突破,甚至产生了和《新思潮》同人分道扬镳的想法。不论是参与《新思潮》两次复刊的经历,还是希望通过翻译外国小说获得灵感,抑或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散文《大川之水》(1914年1月),都触发了他对《火男面具》的创作欲望。《大川之水》中有两个段落预告似的描述了隅田川上吾妻桥日常的熙熙攘攘,“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几乎天天都望见这条河。那水,那船,那桥,那沙洲,还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每日忙忙碌碌的生活。盛夏的午后,踩着灼热的河沙,下河学游泳,无意中河水的气息扑鼻而来。这种种,现在回忆起来,那份亲切似乎与时俱增。”[9]3在这里,芥川龙之介对隅田川上自然风景的由衷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后文也多次提到不同时期隅田川上的人(江户时期净琉璃木偶戏的作者们)、事(日本上古和歌作者在原业平笔下的风景、传统能剧《班女》等)、遗迹(浅草寺的钟声)。这些也都让年轻的芥川流连忘返,使其寂寥之心得到慰藉。而此时的芥川还要继续蛰伏11个月,才能完成以“吾妻桥上,凭栏站着许多人”开篇的《火男面具》。
总之,通观1914年到1915年芥川龙之介给友人、文学界同人的书信,不仅可以发现他在生活中的不安、写作上的焦虑,还可以发现他从初恋、谈婚论嫁到失恋的整个恋爱过程。在前半年(1914年5月19日)写给恒藤恭的信中,芥川龙之介满怀期待地写出自己对爱情婚姻的憧憬,“我心中时常萌生恋情,如同虚无缥缈的梦幻般的恋情”,并自嘲为“幸福幻想家”[8]45。此时年22岁的他正与吉田弥生相恋。
在同年8月30日写给恒藤恭的信中,他甚至称弥生为“我的妻子”,并给恒藤恭的妹妹准备了礼物。然而,这场幸福的爱情不到4个月,就因为芥川家庭的强烈反对而终结。在1915年2月28日写给恒藤恭的另一封信中,芥川直言:“周围的人们很丑恶……目睹这些丑陋而活着是一种痛苦……但是,有一种东西强迫我不能回避现实,这个东西命令我直面周围和自己的丑恶。我当然害怕毁灭,而且我在不得不倾听这个东西的声音时,就预感到毁灭。”[8]62此时芥川向好友恒藤恭的倾诉是否与他的失恋,是否与已经完成且即将在5月份的《帝国文学》发表的《火男面具》有关,在相关的资料中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是,比对芥川的人生经历和《火男面具》中山村平吉的最后结局,可以确凿地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关涉与牵连。在《火男面具》的结尾,被摘掉面具后的平吉没有了呼吸,而他戴过的噘着嘴的火男面具被弃置在船舱的红毯子上,以滑稽的表情安详地仰望着已然死去的平吉。但是,由于期刊主要流通于小范围的文学同人之间,《火男面具》的发表,包括4个月后《罗生门》的发表,并未在当时的大正文坛收获太大反响。1915年12月,芥川龙之介参加“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得此机会拜在夏目漱石的门下。1916年2月,他在第四次复刊的第一期《新思潮》上发表的改写小说《鼻子》,得到夏目漱石的大力推荐。在这种情况下,芥川龙之介方才确立了新人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