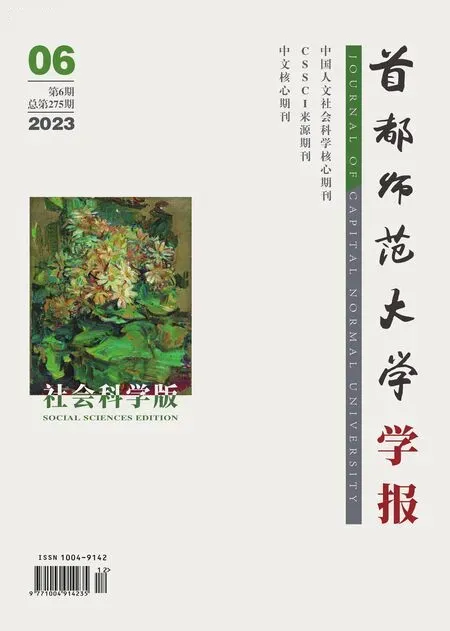功能对等翻译中的俄罗斯精神表达
许传华
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卡里尔·爱默生的《剑桥俄罗斯文学导论》(下简称“《导论》”)于200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一出,斯拉夫研究主流杂志《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俄罗斯评论》(TheRussianReview)、《斯拉夫和东欧杂志》(TheSlavicandEastEuropean Journal)、《加拿大斯拉夫论文》(CanadianSlavonicPapers)、《现代语言评论》(TheModernLanguage Review)等均撰文评论,认为此著作的思想和架构具有一定的新意和难度,堪萨斯州立大学卡莫教授写道:“为非专业读者写出如此条理清楚的俄罗斯文学综述是一个不小的任务。”①W.J.Comer,“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by Caryl Emerson,”The Russian Review,vol.68,No.2,2009,p.321.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员科克雷尔亦说:“以如此有限的篇幅,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架构看来是令人怯步的。”②R.Cockrell,“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by Caryl Emerson,”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104,No.4,2009,p.1200.
一、对话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抑或“对比”?
爱默生是西方斯拉夫学界知名斯拉夫研究专家,教授俄语、俄罗斯文论、俄罗斯宗教哲学,系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语言教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Languages)和斯拉夫、东欧及欧亚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Slavic,East European,and Eurasian Studies)会员。他于1981年出版与迈克尔·霍尔奎斯特合译的《对话的想象:论文四篇》(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译著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与加利·莫森出版合著《反思巴赫金:续编与挑战》(西北大学出版社)和《巴赫金:一个散文作家的创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专著《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第一个百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主编《巴赫金批评文集》(G.K.Hall出版公司),此外她发表诸多如《巴赫金诗学问题》(载于《斯拉夫和东欧杂志》1988年第4期)、《俄罗斯东正教和早期的巴赫金》(载于《宗教和文化》1990年第2-3期)等关于巴赫金的论文。
因此,从学术历程看,爱默生将巴赫金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是她重点研究的文论家。同时,巴赫金的相关思想对她以及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理解巴赫金成为她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她写道:“巴赫金作为‘一个倾听者’和作为一个能够为将死之辩证法重建对话内核的人,他的形象提出了一种特别的挑战。”①C.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7.她认为利用二元模式(binarymodel)可以包含巴赫金三种最为本质的思想:独白与对话、作者对主人公的关系以及自我意识问题。②S.M.Gary and C.Emerson,Rethinking Bakhtin:Extensions and Challenge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p.151.另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爱默生所使用的英语术语“the binary opposition”“binary”该没有争议,翻译成“二元”或“二分”都可,但是“opposition”是“对立”还是“对比”或“对别”呢?这值得思考。
爱默生所使用的“the binary opposition”是作为一种文化范畴(as a cultural category)进行使用的,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且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美学、哲学、价值观、习俗等内容。因此,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将之翻译成“二元对比”或许比“二元对立”更为合适。也就是说,“the binary opposition”应该含有两种意义:其一是“二元对立”,这里的二元或看作两极,非此即彼;其二为“二元对比”,即为对比、对照,此便不应是一种对立,更是一种“对话”。原因有三:
第一,从俄罗斯文学发展史来看,俄罗斯文学清晰地显示了这种“二元对立”和“二元对比”。
18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宫廷诗人与讽刺诗人虽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但都没有摆脱对西方古典文学模仿的窠臼;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走向的论争,虽意见相左,但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俄罗斯更好地发展;19世纪60至90年代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争论,其意都在探讨文学的功能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并存,各有所趋;苏联时代官方文学与地下文学、境外文学的疏离,虽相互攻击,却都没有脱离俄罗斯情结;后苏联时代,后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虽没有标榜对立,但创作方法亦不完全相同。
在俄罗斯文学的书写中,如此清晰的二元对立和对比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对立的双方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极,他们虽然思想相异,但都是相互“对话”的。于是,如果简单地进行二元对立书写,俄罗斯文学就变成非黑即白的矛盾冲突。实质上,俄罗斯文学中相互对立的任何一极都是相互依存的。爱默生看到了这一点,写道:“每个极端互相依存,讽刺的是,两者又无法避免此消彼长。只有在最后三十年,这种支持或反对的思想基础最终才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对称却合理共存的后现代思想混合体。这让人既感到莫大的欣慰,又陷入深深的困惑。”③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9.这就意味着,从翻译等值的角度,爱默生的“the binary opposition”应该回归到“binary”本身的含义,亦即不仅仅是“对立”,更具有“对话性”的意蕴。这样一来,将爱默生的英语表述翻译为“二元对比”更符合俄罗斯文学事实,使得具有主观性的阐释变成了客观性的解读。
第二,爱默生将这种“二元”对比思想贯穿于《导论》的书写中,将俄罗斯文学置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对比论述。一方面,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既聚焦于历时的主线发展,也注重共时的对比论述;另一方面,个体与集体相呼应,既对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进行阐释,又不放弃文学流派的解读与论述。
作者在阐释中世纪俄罗斯文学时,运用对比的写作思想从人物形象(人:圣者、愚者及不容于社会的欧式人等)和传统叙事(事:圣人生活、民间故事以及民间史诗与浮士德故事的混合体等)写起,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印证俄罗斯民间传统的圣徒、圣愚等,对比古今、俄西,呈现一幅中世纪俄罗斯文学画面。在分析18世纪俄罗斯文学时,重点阐释了俄罗斯文学中的西方影响,对比了俄罗斯与西方的语言文化现象,论述了俄罗斯感伤主义与西方传奇小说的异同,梳理了俄罗斯其时的剧作与法国流行的“性格喜剧”和“风尚喜剧”之间的关系等。在对浪漫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进行解读时,根据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极端编排,一种是“普希金一端”,其中充满公共法则、博弈和荣誉决斗的公共世界;另一种是“果戈理一端”,其被相反的力量所支配,形成一个充满逃避与隐匿,描写个人困境和秘密揭露的私人世界。但作者论述更多的则是“两端”所进行的对话。在梳理现实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时,对独白式的“肉体幻想家”托尔斯泰和对话式的“精神幻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对话型作家强调横向关系和分散的、离心的、竞争性的观点;相反,独白型作家则强调纵向的、向心的、绝对的观点”①C.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34.。其他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莫不如此,采用二元对比兼对话的模式进行书写。
第三,将“二元模式”在对话中放大,进行多元阐释,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更加广泛而深刻,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表达的可能。在《导论》中,爱默生选取的理论立足点之一便是结构符号学理论的代表批评家尤里·洛特曼及其塔尔图文化符号学学派,文中写道:“洛特曼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要贡献便是‘二元对比’。”②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8.洛特曼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一种符号体系,是人类思维结构的反映。在文化符号体系中,符号是相互关联的,每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形成网络,这种网络构成了文化体系。文化符号系统体现了一个文化群体的共同意识和价值观,是文化中认识、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他在《艺术文本的结构》《诗歌文本分析》等著作中提出“文本”与“思想”、“结构”与“思想”等二元对比分析模式,诚如他自己所论述的那样:“勾勒艺术语言结构及其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关系,对比语言学范畴的异同,亦即解释艺术文本如何成为特定思想的承载者,文本结构如何影响这种思想结构。”③Ю.М.Лотман,Структур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текста,Анализпоэтическоготекста,СПб.:Азбука,2016,C.13.换句话说,洛特曼的艺术文本分析旨在运用二元对比的方法解释艺术语法规则,通过文本意义的分析揭示文本结构的功能。但是到了晚年,洛特曼开始质疑二元模式的局限,对二元模式进行反思。他的《文化与爆发》在坚持二元论的同时有所突破,认为任何符号体系的原点都不是单独的符号,而是至少两种符号的关系,他称之为“符号空间”④Ю.М.Лотман,Культураивзрыв,М.:Гнозис;ИздательскаягруппаПрогресс,1992,C.266.。如此一来,洛特曼的“符号空间”体系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局限,完成从二元到三元甚至多元的转变。
关于洛特曼“二元”的嬗变,爱默生是有深刻认识的。她对洛特曼通过一些对立的二元意象来解释其学说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如神圣与魔鬼、高与低、东方与西方、旧与新等,但同时意识到,在洛特曼晚些时期或更复杂的文本中,二元对立学说可能会被曲解,认为“他将俄罗斯比作一把两条腿的凳子,既有处在边缘状态的刺激性,又不稳定,总是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在一次冲击下倒塌”⑤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8.。因此,爱默生基于俄罗斯文学中的二元对立(二元对比),将写作结构和论述方法拓展至三元甚或多元对话。可以说,爱默生的《导论》书写是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多元话语体系。
二、例外论中的“自我反思”“自我指涉”还是“自我映射”?
众所周知,相比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起步较晚,其作为文学大国为西方和世界所熟知仅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如此年轻的俄罗斯文学是如何进入西方视野并虏获西方青睐的,这或许是“例外论”(exceptionalism)所致。“例外论”认为:“俄罗斯是特殊的,不能根据正常的(亦即西欧的)进步、繁荣或者成功的标准来进行判断。”①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需要提及的是,“例外论”下的俄罗斯文学是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切入的,相对于俄罗斯,西方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世俗的、“先进的”、进步的。因此,于西方文学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例外”于西方的文学。所以,在整部《导论》中,如何处理俄罗斯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表述的差异,如何处理其中的汉译问题也特别值得思索。
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习惯和概念等元素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这值得注意,尤其是没有等值词汇的情况下,不仅需要具备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要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
《导论》开篇即言:“Russian literature is compact,intensely self-reflexive”(俄罗斯文学的结构紧凑,具有强烈的自我映射性)。这里的“self-reflexive”是翻译为“自我反思性”“自我指涉”还是“自我映射”呢?
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结合等值翻译的思想,这里的“self-reflexive”指俄国文学具有强烈的虚构性和纪实性特征,使读者难以分清虚构与写实。关于“self-reflexive”,《导论》中解释道:“(这种自我映射)使人忘记它仅仅是由文字构成的。想象出来的人物走出虚构进入到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被抬高到神话般的地位。”②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也就是说,“Imagined characters”、“real-life”和“myth”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想象出来的人物”进入到“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却又上升至“神话”(虚构)。简而言之,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汉语的思维角度来看,“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虚构作品本身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是作者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然而,虚构作品又常常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它们常常反映出作者的观察和感知现实的方式,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此一来,“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反思性”、“指涉性”还是“映射性”呢?
自我反思性在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和表现手法,作品通过描述主人公对自身想法、情感和行为的反思,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并感受故事背后的主题和思想。显然,反思性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意在让读者沉浸式地进入作品中,感受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这与文中的“使人忘记它仅仅是由文字构成的”貌似匹配,但后文展示的则是俄罗斯文学叙事的现实意义,“首先围绕圣愚展开,然后围绕城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接着围绕作家生平,最后围绕伦理和思想体系展开”。③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因此,从翻译目的论的连贯性来说,“自我反思性”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自我指涉”涉及指称自己或自己的属性、特征或行动的概念,在语言学、逻辑学、数学、哲学、文学等领域使用,其英文或为“Self-reference”更为确切。在文学中,当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思想发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是指“文学语言将读者注意力指向(refer to)文学自身(self)的特性”④步朝霞:《自我指涉性:从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外国文学》2006年第5期。。因此,从原文的用词“self-reflexive”来看,“自我指涉性”也有些牵强,其更适合从语言学的层面表达意义。
最后,“映射”是一个数学概念,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出是某个物体投射到另一个物体的过程。在数学里,映射其实就是一个“投射”的过程。《牛津文学术语词典》(TheOxfordDictionaryofLiteraryTerms)中指出:“自我映射”(self-reflexive)是一种文学术语,经常出现在现代小说或诗歌中,意指公开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其中反复提到自己的虚构地位。在早期文学中,其叙述者也被称为“自我意识的叙述者”(self-conscious narrator)①Chris Baldick,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3 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display/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00453429.2023年4月23日。。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符合原文表达的“虚构”与“现实”的相互“投射”,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俄罗斯文学的“自我映射”反映在俄罗斯文学中便是作家的自我民族认同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矛盾。俄罗斯文学关注俄罗斯自身的特点,认为俄罗斯与西欧的发展道路是相异的,应遵循俄罗斯传统的发展道路。故19世纪的斯拉夫派、根基派、民粹派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不同;苏联时代更甚,与西方直接拉开冷战的大幕,就连异见者索尔仁尼琴对西方亦是排斥有加,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说时,他坦言:“恕我不能将你们的社会推荐为我们社会改革的理想模式,因其现在的精神衰竭,西方体制并非是令人神往的。”②А.Солженицын,Публицистика(том1),Ярослваль:Верхне-волжскоекниж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5,C.319.对于这种现象,爱默生写道:“各派小说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廖沙以及索尔仁尼琴不满于这种不公平的比较,一致对欧洲贪得无厌、道德败坏的‘进步’嗤之以鼻,无情批判。”③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导致如此结果或者说产生此种后果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作家需要实现自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必要解释的是,“民族”和“国家”在俄语中可用一个词“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表示。从翻译角度来说,可以翻译为“国民性”,它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地理、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形成的特定的和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如此一来,俄罗斯作家的自我认同过程就是国民认同的过程,亦即对国家和民族的双重认同。
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的“国民性认同”大多是通过文学实现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具有文史哲的多元功能。因此,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问题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小说、托尔斯泰的独白小说等,它们都脱离单纯的审美性表达,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因素。诚如爱默生在《引言》中所论述的那样:“充满形而上的思想,功利性明显,使得读者阅读故事不是为了获得乐趣和愉悦,而是道德教诲。”④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也正是这种“功利性”使得俄罗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写出了“小人物”“多余人”“新人”等诸多形象。其实,爱默生对这些俄罗斯文学形象的论述是通过俄罗斯作家“例外论”和“国民性认同”进行的。关于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多余人”,爱默生阐释道:“其实他们也许是不如意的人,但绝不愿意被归为在生活中无用或多余的人。数十年之后的作家和评论家们认为,一个更具社会责任感、有更大社会贡献的(即“积极的”)人物更符合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道德需求,因此他们创造了这个有反面意义的词汇,并用在这些文学人物身上。”⑤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
三、“俄罗斯性”中的“装饰性散文”还是“唯美散文”?
文化史学家史蒂文·马克斯出版了一本题为《俄罗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从艺术到反犹太主义,从芭蕾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HowRussiaShapedtheModernWorld:FromArttoAnti-Semitism,Balletto Bolshevism)的书。他认为,判断俄罗斯文学是不是属于俄罗斯的标准不是通过作品长度、小说场景、人物形象、精神性或道德要求。换言之,不是通过一系列固定特点或明显事实,而是通过“俄罗斯性”(Russianness)。这是一种对外部世界不屑或谴责的特殊态度。⑥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科罗拉多大学劳拉·奥森教授用“俄罗斯性”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认为“农民是整体性和无依附性的体现,是托尔斯泰式的俄罗斯性的理想,也是如何实现真正幸福的典范”①L.J.Olson,“Russianness,Femininity,and Romantic Aesthetics in War and Peace,”The Russian Review,56,No.4,1997,p.517.。剑桥大学弗罗洛娃-沃克教授用“俄罗斯性”讨论音乐,认为俄罗斯音乐中存在“一种内在的俄罗斯性的美好信念”②M.Frolova-Walker,“On‘Ruslan’and Russianness,”Cambridge Opera Journal,9,No.1,1997,p.21.。这些论述说明,“俄罗斯性”包含了与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相关的许多方面,它可以根据使用它的具体环境而有所不同,不仅仅在文学、艺术方面起作用,而且与俄罗斯传统、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以及民族团结有关,与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文化和传统价值保护相联系。
可以说,这是俄罗斯“例外论”的升级版,如果说“例外论”是西方强加于俄罗斯的,那么“俄罗斯性”则是俄罗斯自我强加给自己的,是对俄罗斯文学特殊性的一种体认。在这方面,俄罗斯报刊评论家对俄罗斯文学独特性的导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爱默生在《导论》“文学评论家及其社会贡献”一节中写道:“俄罗斯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国家的自我认同感愈发重要,因此文学活动变得高度自觉。”③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4.在俄罗斯文学的“自觉”(self-conscious)中,俄罗斯评论家及其创办的杂志功不可没。俄罗斯批评家舍尔古诺夫曾在1870年写道:“我们所有的艺术家都将走向不同的道路,因为只有报刊批评家能给他们指引方向”,“小说家只不过是给生活的发动机拾柴、填火,而报刊批评家却是驾驶员”。④M.Charlesa,Esthetics as Nightmare:Russian Literary Theory 1855-187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29.舍尔古诺夫的评论虽有些偏激,但却体现俄罗斯文学的特定的时代特征。俄罗斯作家大多不是职业作家,而是身兼多职,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同时还是杂志主编。例如,普希金1836年在彼得堡创刊《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杂志上刊登过果戈理、屠格涅夫、丘特切夫等人的作品,至1846年由文学家涅克拉索夫接管,对俄罗斯社会现实进行猛烈批评,后被政府查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于1861年创办杂志《当代》(Время),1863年该杂志被关闭之后,随后创刊《时代》(Эпоха)阐述“根基派”的创作思想和文学主张。爱默生在论述中密切关注到这一点,在《诗人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一章中,作者除了论述二人的文学创作之外,还关注到二人的杂志批评作用,她评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小说家,还是个新闻工作者。”⑤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31.
实际问题是,俄罗斯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为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导论》中所提到的“ornamentalist prose”是具有“俄罗斯性”的一种独特体裁,虽然在1934年苏联作协第一次大会后逐渐式微。但是,作为“俄罗斯性”表达的诗性散文,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翻译的角度看,“ornamentalist prose”的俄文为“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是一个与俄语同根同形的术语。这对于同属于印欧语系的两种语言是非常便于对译和理解的。但是,“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的汉译却有一定困难,翻译为“装饰散文”“华丽散文”在汉语的语境之下都较为难以理解。
梳理文献可知,“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最初指的是大约1920年至1925年期间苏联散文的主要风格,起源于别雷的创作,其情节作为组织叙事的方式处于次要地位,而形象重复(повторыобразов)、主题词(лейтмотивы)、节奏(ритм)、隐喻(метафоры)和联想(ассоциации)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问题在于,关于“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的起源尚有争议。米尔斯基认为尼古拉·果戈理是俄罗斯“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проза”之父,其他诸如尼古拉·列斯科夫、阿列克谢·雷米佐夫、叶夫盖尼·扎米亚京、伊萨克·巴别尔和尤里·阿廖沙等作家则作为重要代表。但不管如何,“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оза”作为一种文体,强调意象、象征和隐喻,注重自我展示和设计的原则等则被广泛承认,而且对俄罗斯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百翰大学教授加里·布朗宁说:“在‘ornamentalist prose’中,作者的创作热情主要是针对表达方式,而不是针对叙事兴趣、人物或信息,至于风格,散文被认为是装饰性的,像诗歌一样,显然是为了声音、节奏和形象的效果而制作的。创作者沉醉于世界的听觉丰富性。”①Gary L.Browning,“Russian Ornamental Prose,”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vol.23,No.3,1979,p.347.汉堡大学斯拉夫文学教授沃尔夫·施密特则言:“在‘ornamentalist prose’中,就好像作者在叙述者的背后,可以说是在文本上撒下了一张形式和主题联系的网,推翻了叙述者和他的观点,并赋予文本以诗意的结构,具有中和所有个别语言观点的效果。”②Schmid Wolf.“Poetic or Ornamental Prose,”In:Hühn,Peter et al.(eds.),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Hamburg:Hamburg University,2013.http://www.lhn.uni-hamburg.de/article/poetic-or-ornamental-prose.2019年2月12日。
这也就意味着,“ornamentalist prose”的特点是注重设计、自我呈现、富有意象和隐喻意味。如此散文明显具有“装饰性”特征,其汉语翻译成“唯美散文”该是可行的。
在汉语的语境之下,“唯美散文”可以理解为一种追求美感和艺术性的散文,与传统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稍有区别,它注重表达情感和意境,可采用意象和象征的手法来塑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体验。“唯美散文”通常不拘泥于情节和客观事实,而是让作者的情感和想象力发挥自由的创作力,或注重韵美感,采用平仄、韵律等手法来增强表达效果;或注重画面感,用生动的画面来传达特定的情感和意境;或注重对于哲学和思想的探讨,通过散文的形式提出文化上的疑问和思考。
四、俄罗斯文学翻译中的俄罗斯精神
整体而言,文学不完全需要属于它自己的民族,因为文学应该是开放的,跨越国界的。文学的主题和内容应该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局限性,反映全球人类的共同关注和热点问题,包括人际关系、自我认同、生命的意义等。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应该是超越文化、语言和民族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文学充满形而上学思想和道德说教性因素,也具有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其作品以强烈的民族性和文化特色为特点,反映出了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历史事件和人文思想。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采用忠实于源语言的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和风格,更加注重保留源文化的特色和语言风格,这是《导论》作者爱默生所倡导的,她写道:“一个非俄罗斯作者邀请非俄罗斯读者进入到这个领域就必须选择那些文学经典文本和工具,以便利于‘从外围’进入。它们必须存在于优秀的译作中,像艺术原作一样,在其目标语言(这里,指英语)里获得生命,能够在俄罗斯之外增加文化厚重感。”③C.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7.因此,在《导论》中保留了大量的音译词,“lik”(лик)、“lichnost′”(личность)、“sobornost′”(соборность)、“tselostnost′”(целостность)、“Ivanushka-durak”(Иванушка-Дурак)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均体现了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和精神价值,如果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其文化意义可能会大打折扣,但是直接放上去,却实难理解,爱默生采用的策略是等值翻译,除了所提倡异化翻译策略之外,还进行了适度的归化释义。也就是说,除了关注词汇、句法、篇章、文体对等之外,如何从目的论的角度进行翻译归化,将源语转译为与本土文化和习惯相符、更容易被当地人理解的本土语言,使阅读者能够消除外来文化和语言带来的陌生感和阅读障碍,促进文化的沟通与理解。
在阐释俄罗斯的文字和空间之后,爱默生提出俄罗斯文学的第三个思想:“the concept of lik”(圣容理念)。文中直接使用俄语词“лик”的音译,也就是所说的异化翻译策略。这样一来,“lik(лик)”本身所包含的语义一点都没有损耗和丧失,若没有接下来的阐释与解读,很难理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观念。在汉译中,如果将其翻译为“‘力克’理念”则更无从理解。这就需要追究该词的文化意义。
其实,爱默生文中列举了表示“脸”之意的三个俄语词“litso(лицо)”、“lichina(личина)”和“lik(лик)”。在俄语中“litso(лицо)”表示普通的脸,“lichina(личина)”是面具,是虚伪的面孔,“lik(лик)”则具有特殊精神文化意义的“面容”。在俄罗斯文化中,“лик”不仅指代人的面容,同时也代表了文化和精神的标志,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基本意义有二:第一,古语词,在俄罗斯史诗中被广泛使用,有庄重意义,为“面容”、“面颊”或“容颜”之意;第二,宗教文化词汇,是圣人、圣像的面容,或为“圣容”之意。对此,爱默生解释说:“这个单词意为面孔、容貌,表示有知觉和反应的脸,这样一张面孔上的双耳能够听到别人的话,双眼可以凝视别人的面孔,且散发着圣洁之光。”①C.Emerso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30.通过异化翻译策略的“lik”,加上这样的解读,英语读者才能理解“圣容”的含义。但在汉译的处理过程中,直接翻译为“圣容理念”或许更为直接一点,汉语中的“圣”字能够涵盖俄罗斯文化中的“神圣宗教”之感,“容”字也能包含“面容”“面庞”“容颜”等意义。因此,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容理念”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爱默生通过对表示“脸”之意的三个词的辨别与解读,阐释了俄罗斯精神中的“lichnost′(личность)”和“sobornost′”(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两个词也是不可译的,在《导论》中保留了英语的音译。因为“Личность”和“Cоборность”这两个俄语词汇在俄罗斯文化和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在东正教基督教传统中扮演重要角色。
“Личность”,通常被描述为具有意识和自我定位能力的个体,这可以包括个性的独特特征,如智力、情感、直觉、道德信仰等等,爱默生解释道:“在英语中大致可译为‘个性’,但在俄罗斯的精神哲学中,它意味着道德和人与人之间的责任。”②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0.关于英语中的个性“personality”,《剑桥词典》(Cambridge Dictionary)解释为:“一个人身上的特殊品质组合,使其与他人不同,表现为该人的行为、感觉和思维方式。”③“Cambridge Dictionary Personalit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personality.2023年4月27日。如此一来,如果采用“personality”的译法,其中的“道德责任”之意则会失去;汉语的“个性”一词则译自英语的“personality”,其先是指希腊罗马时代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所戴的面具,也就是俄语中的“личина”,代表剧中人的身份,后来指演员,也就是“лицо”,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最后才具有“лик”的“圣容”之意和精神文化象征。“Cоборность”则更为复杂一点,爱默生给出的英语为“conciliarity,togetherness”(共同性,团结性),汉语给出的翻译也是多种多样,“聚合性”“协同性”等,在不同的知识、宗教和文化背景下使用,表示拥有共同价值观或理想的“个性”的聚集或团结。这样一来,“Личность”和“Cоборность”本身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爱默生对此解释说:“这个复杂概念的核心是整体性,它不是指同质性或同一性。每张脸都不尽相同,每个人的个性都各有特点,但每个个体都需要通过别人来认识自身。很重要的是,俄语里没有‘隐私’一词,而且俄罗斯文化并非像其他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样,具有认为灵魂困于肉体这样的形而上学思想。身体(尤其是脸)不是禁锢,而是媒介,就像一面能反射的镜子。”④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1.
《导论》中其他诸多不可译词,如“pravedniki”(праведники)”意味“Righteous persons”(正直之士),“yurodivy(Юродивые)”可理解为“圣愚”,“blazhenny(Блаженные)”可阐释为“圣者”。诸如这些包含俄罗斯精神的词汇之不可译的背后是西方学者对俄罗斯文化的不理解,也是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误解。“这是由自贬的例外论所导致的,诸如倦怠、感伤癖、不断期望灾难,还有一种惊人的排外情绪”。爱默生如此解释道,同时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具有排外情绪的沙文主义者,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眼中,“俄罗斯文学对于世界来说就是一个公分母,但是只有俄罗斯人才有特权去理解它”⑤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9-10.。
基于这种“误解”,爱默生试图理解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和“排他性”。例如,在第二章中,作者论述了“主人公及其情节”,讨论了“遵守教规者”“圣愚”“边民”“无赖与恶棍”“不容于社会的欧式人”各类人等,重点关注的便是这些主人公的苦难意识和内在的排他性。“遵守教规者”常常变为一个朝圣者,“这种人最关键的是他们总是自愿承受苦难——但是无论面对的是自己引发的还是被强加的痛苦折磨,一个遵守教规者是不会动摇自己的想法或者灵魂的。他不能够动摇,因为他与他自己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①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6.。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大师以及高尔基《母亲》中的母亲都是此类人的化身;“圣愚”更是如此,虽然展现出行为的愚蠢、怪诞及思想的混乱,但圣愚却能被俄罗斯人所敬重,“圣愚的角色是矛盾的。他必须永远生活在危险中,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蔑视一切等级,将自己的重点放在此世而非彼世”②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41.。至于其他类型的主人公,诸如作为“无赖与恶棍”的守财奴普柳希金、小犹大波尔菲里、政治恶棍以及“不容于社会的欧式人”等,他们也是被从“苦难”和“排他性”的视阈中窥探发掘的。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民族文学,俄罗斯文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他的道德说教性和功利性使得文学的纯审美功能降低,但其哲学性功能和文学性意义则被无限放大,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作为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亦具有世界文学所具有的总体特征,蕴含人类的共同精神,反映了人类精神的趋向统一。因此,俄罗斯文学的“例外论”是西方话语权之下的“例外”文学,它只是反映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对俄罗斯话语体系的胜利而已。
爱默生这部作为《导论》的俄罗斯文学,具有“导”的性质、“史”的观念和“论”的成分。《导论》之“导”(introduction)作为引入性、介绍性的文字,使读者能够初步了解俄罗斯文学,爱默生自己在《致谢》中说道:“此书主要面对高等初学者(advanced beginner),假定对象为没有学过俄罗斯文学或俄罗斯历史课程以及没有学过俄语的人。”③C.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xiii.正因为如此,《导论》没有谈及诸如莱蒙托夫、冈察洛夫、肖洛霍夫、纳博科夫等重要作家作品。这也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但克莱门森大学拉夫教授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说:“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爱默生本人反复强调,导论不是包罗万象的,它尽力涵盖了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④J.Love.“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by Caryl Emerson,”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Vol.53,No.3,2009,p.478.这也同时说明《导论》之重在导引的作用与意义。与此同时,爱默生提出了《导论》之“史”的观念,以“史”为纲,重在对比、考证与阐释。另外,其写作思路是按照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以时间顺序为轴,从18世纪到本世纪初,集中论述了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文学流派及代表作家,这也就是爱默生所说三大“批评模式”之一。此种横向写法能够使读者置入到时间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感与厚重感。“论”的成分是《导论》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爱默生以深刻的“问题意识”,发掘俄罗斯文学的主题性,讨论了诸如城市与农村、莫斯科与彼得堡、罪恶与救赎、中心与边缘等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导”的缺陷,使得《导论》的可读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