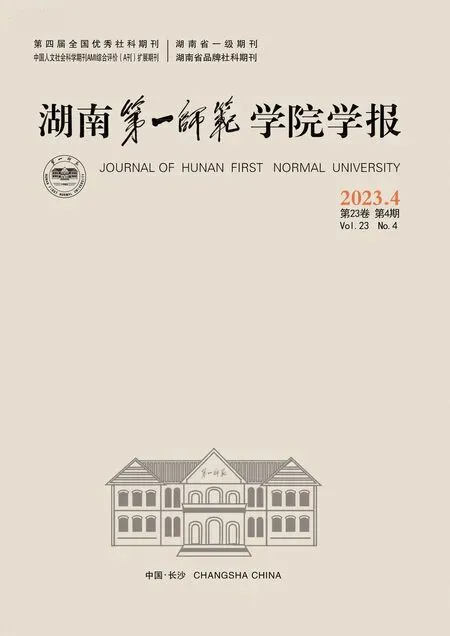记忆与想象:古代朝鲜文人的湖湘胜景书写
蔡美花,李 倩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相对稳定且极具传承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文明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朝鲜半岛古代诗话所呈现的中国古代文明画卷中,“湖湘”也占据着亮丽的一页。朝鲜“文章四大家”之一的张维曾感慨道:“潇湘八景之胜,擅名海内,古今诗人赋咏,不胜其多。”[1]123足见以“潇湘八景”为代表的湖湘自然风物在朝鲜文坛的普及度与影响力。古代朝鲜文人笔下的潇湘自然风物,绝大部分源于“潇湘八景”,其中又以“潇湘夜雨”“洞庭秋月”“平沙落雁”三个主题居多[2]83,因而潇湘、洞庭湖、衡山也成为古代朝鲜文人的重要书写对象。作为“自我”的湖湘胜景,被作为“他者”的古代朝鲜文人进行了极度的“缺席想象”,并常常作为湖湘文化的某一种“隐喻”而被赋予了相对稳定的意旨,表露出古代朝鲜文人对两宋以来湖湘文化的极高认同度。
一、古代朝鲜文人的潇湘书写
“潇湘”既指湘水和潇水,又指湘江全流域的广阔空间。陆放翁曾言“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不论是缠绵不断的夜雨,抑或是蜿蜒曲折的潇湘之水都十分契合文人墨客那百转千回、绵延不绝的愁思,雨落潇湘的夜景也成为旧时中国文人借以寄情的著名景观。由此生发的诸多吟咏之诗也成为中国古代叙写愁志哀情的经典之作,进而进入朝鲜诗家论诗的视野。如崔致远《无染和尚碑铭》中借南梁柳恽《江南曲》中的“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谓唐恩浦相遇之事,写道“而沧海外,蹑潇湘故事,则亲旧缘固不浅”[3]167;许筠评价明人山东参议黎民表所作“地近潇湘多暮雨,雁来湓浦少乡书”为“工诗”、赞其“此诗流播东方”[4]1458;姜浚钦《三溟诗话》辑录思斋金正国与慕斋金安国两人关于唐代钱起《归雁》诗的讨论:
钱仲文《归雁》诗曰:“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首二句,人问雁也。末二句,雁答人也。夫两岸莓苔,水碧沙明之地,何事等闲回者,虽不用问字,而自然是问语。二十五弦之瑟,弹于月明之夜,不胜清怨却之声,而却飞来者,虽不用答字,自然是答语。何必有问答字,而后为问答乎哉?[5]4926-4927
自上述引文可知,金氏二人不仅熟知钱起《归雁》一诗的内容,对于《归雁》一诗未见问答二字却尽写问答之情的艺术技法也能够做到很好的鉴赏与批评。描绘潇湘胜景的中国诗歌,声名赫奕如柳恽、钱起所作诗文,稀松平常如黎民表所作诗文,都是古代朝鲜诗家能够信手拈来,或用事、或评点、或赏析的论诗素材。
“潇湘夜雨”作为潇湘八景组诗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成了古代朝鲜文人效仿拟次八景诗歌的重要选题。古代朝鲜文人笔下的“潇湘”是充盈着哀伤忧愁的悲剧空间。这种悲剧意味首先是“断肠人在天涯”的羁旅思乡之愁。元代马致远曾作《寿阳曲·潇湘夜雨》云“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以声声落雨喻示涟涟清泪,极写其身处天涯,心念故乡之愁苦。“潇湘”,特别是雨夜的潇湘,也因此成为思乡怀友的经典场景。羁旅思乡的“潇湘”在古代朝鲜文人的笔下得以延续传承,古代朝鲜文人借助中国的“潇湘”诉说着别样愁思。益斋李齐贤(1288—1367)曾作著名词作《巫山一段云》之《潇湘夜雨》:“潮落蒹葭浦,烟沉橘柚洲。黄陵祠下雨声秋,无限古今愁。漠漠迷渔火,萧萧滞客舟。个中谁与共清幽,唯有一沙鸥。”[6]608潇湘的秋夜总是阴雨绵绵,客人滞留他乡的无限愁思却只能与江面上的一只沙鸥共享,李齐贤笔下的潇湘是羁旅不归后,充盈着清幽愁楚的审美空间。“潇湘夜雨”的书写范式以及由此生发出羁旅愁楚的审美意蕴,在古代朝鲜文人的心中是相对稳定的,大文豪李奎报写潇湘也不由慨叹“零陵江上雨连天,寄舶游人思悄然”[7]201;李承召的“云暗潇湘雨送凉,蓬窗月黑响琅琅。舟中多少远游客,尽向灯前说古乡”[8]461更是将潇湘夜雨中的思乡愁苦泛滥为广大游子的普适情怀。
回看中国的情况,不论是宋代宋迪的八景山水图,抑或元代马致远的八首《寿阳曲》小令,“潇湘夜雨”的书写内容多是由湘水、夜晚、雨水等核心要素组合而成,古代朝鲜文人题为《潇湘夜雨》的文学作品基本也沿袭该创作传统。令人瞩目的是,部分古代朝鲜文人在《潇湘夜雨》书写范式之下,还叠加了舜妃泣竹的神话意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舜帝、二妃、斑竹等元素极大丰富“潇湘”历史内涵的同时,也为“潇湘”增添了传奇性与厚重感。“潇湘斑竹”甚至一度是古代朝鲜文人习作练笔的重要论题,任璟《玄湖琐谈》对此留有记载:
洪斯文柱世,号静虚堂,为文专尚儒家,不务词华,而诗亦闲远,有陶、韦遗韵。尝制月课,其《咏潇湘斑竹》曰:“苍梧愁色白云间,帝子南奔几日还?遗恨不随湘水去,泪痕犹着竹枝斑。千秋劲节凌霜雪,半夜寒声响玦环。啼罢鹧鸪人不见,数峰江上露烟鬟。”词极清高。时湖州蔡裕后擢致上考,称赏不已。[9]2908
由此足见,“潇湘斑竹”作为古代朝鲜文人的月课题目之一,与古代朝鲜人才擢升选考具有密切联系,舜妃泣竹的“潇湘”在古代朝鲜文人笔端之分量及“潇湘”在朝鲜古代文坛的接受程度与普及范围也由此可窥一斑。对于舜妃泣竹的“潇湘”,古代朝鲜文人深受感动,喜爱有加,并将这种情感共鸣流淌于文学创作当中。同样题为《潇湘夜雨》诗歌,怀揣“无限古今愁”的李齐贤也曾发出“枫叶芦花水国秋,一江风雨洒扁舟。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10]525的嗟叹;容斋李荇也为湘妃泣竹所感,留下“竹林动哀响,二妃应涕滂。涕痕湔不尽,千古断人肠”[11]394的诗句;东溟郑斗卿则将夜雨与斑竹双重因素糅杂,喟然而叹:“夜雨萧萧斑竹枝,至今瑶瑟使人悲。千年帝子无穷恨,只在湘江夜雨时。”[12]409
“潇湘”在朝鲜古代诗话中诗意呈现的另一种内涵为屈子报国的家国情怀。屈子曾作《湘君》《湘夫人》,借神为对象寄托纯朴真挚的情感,故在“潇湘”这个叙事空间内很难将屈子与湘神、舜妃、斑竹等元素完全分离开来。在古代朝鲜文人的行文中,这两种情愫往往交织混合在一起,营造出极具浪漫色彩且悲壮凄美的氛围感。如李齐贤云:“二女湘江泪,三闾楚泽吟”[13]608,“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又如郑宗鲁云:“萧萧夜雨湿斑篁,帝子遗踪隔渺茫。最是三闾终古恨,湘流不断楚天长”[14]119;柳楫云:“黄陵祠下莫停舟,斑竹千年不尽愁。造物何心添夜雨,萧萧应白楚臣头”[15]14;洪柱国云:“凄迷暗锁虞妃恨,断续频回楚客肠”[16]245。秉承着屈子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古代朝鲜文人对“潇湘”的理解与阐释带有浓厚的爱国报国情怀。如“潇湘江山共我清,楼台到处管弦声。若非细马驮红粉,谁识三韩更太平”[17]18,都是诗人某种家园情怀的诗意传达,而这与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观之家国情怀、家园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潇湘”在朝鲜古代诗话中的诗意呈现是十分常见的,同时其内涵又是丰富多样的。不论是“断肠人在天涯”的羁旅怀乡,还是舜妃啼竹的坚贞不移,抑或是屈子报国的悲壮凄美,“潇湘”在古代朝鲜文人的精神世界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其寄托哀思,存放理想的自由处所。
二、古代朝鲜文人的洞庭湖书写
洞庭湖因广阔浩大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动人的神话传说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的目光。随着古代中朝交往的不断密切,洞庭湖及其相关的诗歌佳作自然也成为古代朝鲜文人的关注对象。十五世纪朝鲜朝文人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言道:
洞庭、巴陵天下壮观,骚人墨客题咏者多。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过却如闲”,俱见称于世。然不若孟襄阳“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又不若少陵“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未知此老胸中藏几个云梦欤?牧隐《吴中八景》一绝云:“一点君山夕照红,阔吞吴楚势无穷。长风吹上黄昏月,银烛纱笼暗淡中。”其旷漠冲融之气虽不及老杜径庭,岂足多让于前数联哉?[18]189-190
上引所论,僧可朋《赋洞庭》、许棠《过洞庭湖》、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登岳阳楼》皆为中国诗人观洞庭湖所作,所言李牧隐《吴中八景》一诗则为朝鲜文人之作。徐居正在此不仅对中国诗家所作进行比较评点,还将中朝两国诗人针对同一对象——洞庭湖所作诗文进行了横向比较。不论评价客观与否,此论都足以展现朝鲜诗家对于洞庭湖及以洞庭湖为创作背景的诗歌作品的关注程度与熟悉程度。
在古代朝鲜文人的心中,洞庭湖是适合入诗的绝佳素材,单就“洞庭湖(别名云梦)”之名称都是古典雅致、令人羡慕的。许筠在《惺叟诗话》曾记录道:
赵持世常曰:“我国地名入诗不雅。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凡十字,六字地名而上加四字。其用力只在蒸、撼二字为功,岂不省耶?”[19]1493
对此,洪万宗在《小华诗评》中也有相似的论述:
世谓中国地名皆入文字,诗便佳。如“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等句,只加数字而能生色。我东方皆以方言成地名,不和于诗云。[20]2337
以赵纬韩为代表的朝鲜“世人”对洞庭湖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南羲采甚至在《龟磵诗话》中的“湖”“羿屠巴蛇、轩皇凿湖”“泉井·楚田云梦”条中,将洞庭湖的水系概况、民俗传说、历史渊源、文学传统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记录与介绍。
实际上,受地理位置影响,洞庭湖在朝鲜古代汉文诗歌中往往伴随着岳阳楼、君山一同出现,构成了“君山-洞庭湖-岳阳楼”即“一山一水一楼”的群体意象。洞庭湖与这些意象的共同组合不是简单的叠加与组合,而是历代诗家对物象形态与属性的识别与选择,凝聚着东方特色的审美联想与哲学思辨。同时,秋月也成为这个群体意象中很重要的一环。由于“秋月”意境的加持,不论是泛舟洞庭,抑或登高(岳阳楼或君山)望月,诗人总是难免心生慨叹,生发出或怀古伤今,或忧国忧民,或思乡怀人之感,感伤忧思仍是洞庭湖群体意象的情感底色。相应的,杜子美之《登岳阳楼》、孟浩然之《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范希文之《岳阳楼记》早已为深谙中国文学的古代朝鲜文人奠定了忧思情绪的基调与主旋律。
南羲采于《龟磵诗话》中言道:
宋滕宗谅左官守巴陵,重建岳阳楼,增旧制极雄伟,范文正为之记,时庆历五年也。余谓岳楼题咏,少陵后无人,政所谓“此诗题后更无诗”者也,独希文记笔力极其闳肆,其曰:“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等语,直与少陵“吴楚乾坤”之句争雄,其曰:“去国怀乡,感极而悲,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等语与少陵“亲朋老病,凭轩涕泗”之意同忧感也。前辈以为范老胸襟与洞庭同其广大者,诚非过语也。[21]8082-8083
上引文字足见,朝鲜朝后期博物学家南羲采对于岳阳楼改建始末及题咏岳阳楼文化了然于胸。杜子美所作《登岳阳楼》被视为题咏岳阳楼诗文作品的极致,范希文所作《岳阳楼记》被南羲采及其“前辈”看作是可以比肩杜子美《登岳阳楼》的作品,其中关捩在于范希文“与洞庭同其广大”的胸襟,即范希文与杜子共通共有的“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天下情怀。这种忧国忧民的悲患意识是杜子美、范希文在内的中国文人雅士于登临岳阳楼,纵览洞庭秋月的特定环境中做出的共同的价值选择,也是遥在海东的朝鲜文人在“洞庭秋月”特殊文学“记忆”感召下的同声相应。“洞庭秋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悲患意识”的具体外化。值得注意的是,洞庭湖群体意象中的这种“忧国忧民”式的家国情怀与上文言及的潇湘意象中所蕴含的屈子“忠君爱国”式的家国情怀各自侧重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综上,“洞庭湖”在朝鲜古代诗话中的诗意呈现具有群体性的特征,以洞庭湖为核心的自然名胜群在古代朝鲜文人的心中创设出一幅秋月登高的联动式风景图,在古代朝鲜文人的笔端生成为怀古感今,忧国忧民的悠然情思。
三、古代朝鲜文人的衡山书写
除此之外,潇湘八景之一的“平沙落雁”也是古代朝鲜文人笔下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主题。“平沙落雁”景观在南岳七十二峰之首的回雁峰,由于地理思维的局限性,古人误以为雁到衡阳不再南飞,至此越冬,待来年春暖而归。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佳句。杜甫曾居衡阳,留下了“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的诗句。钱起、刘禹锡、柳宗元、杜荀鹤、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等都留有脍炙人口的诗文。文因景成,景借文传,衡山的回雁峰也由此名扬海内外。
“衡山”最初以“南岳”之名出现在中国文学当中。舜帝南巡而崩,二妃双双殉情奠定了衡山形象的悲情底蕴。屈原《天问》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记述了泰伯、仲雍假称采药,避国让贤于季历的历史故事,使得衡山也初具归隐色彩。秦时开凿灵渠,衡山一脉成为中原内陆与荒蛮南境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后期迁客骚人们北上南下的必经之地,由此生发的贬谪失落与羁旅孤苦之情,也成为衡山(衡阳、南岳)最经典的、最常见的文学内涵。初唐诗人宋之问左迁岭南,舟行衡山之时,曾作诗:“五岭恓惶客,三湘憔悴颜。况复秋雨霁,表里见衡山。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唯余望乡泪,更染竹成斑。”[22]639秋雨之中,宋之问既无力“鹏南转”,又无法“雁北还”,贬谪之愁苦与羁旅之辛酸在舟行衡山之时,宣泄而出。另一经典佐证,即中唐诗人李绅所作《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一诗,李绅写道“衡山截断炎方北,回雁峰南瘴烟黑”,更是鲜明直接地将衡山描写成中原文明与南境荒蛮的分界特质。“雁不过衡阳”之说似乎更为“衡山”的分界特质添上了有力注脚,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在“衡山”分界之感中还原出人类原始的别离思归之情,使得“衡山”之隽永流淌于诗词世界。
朝鲜诗家在诗歌创作中也延续了“衡山”这一经典文学内涵,将“衡山”延伸发展为划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身份界限、阻隔忠臣直士与帝王君主间的空间障碍。汉诗家郑希良(1469—1502)身处政治黑暗、党争严重的朝鲜朝燕山君时期,几经贬谪之后,郑希良怨叹道“湘水沉骚客,衡山滞直臣。凄凉今古事,况复更轮囷。”[23]23湘水、衡山本为自然之物,但于贬谪者郑希良看来,这些自然之物却早已成为有意“沉”没屈子、“滞”留范仲淹,阻碍自身仕途、割断君臣之心的有情之物。在“衡山”意象的加持下,郑希良时下心境愈显“凄凉”、愈发“轮囷”。同时期的汉诗家鱼得江(1470-1550)在欣赏“平沙落雁”之时,也不免发出:“木落南翔稻正腴,群游饮啄恣江湖。恐渠饱暖忘虞处,枉害忠诚直谏奴”[24]478的感慨。暮秋时节,稻腴水美的衡阳平沙引得雁群南翔停驻、恣意快活,观此乐景,鱼得江却心生哀情,责怪雁群遗忘了那位投江的忠臣直谏之士——屈子。
“衡山”在分隔庙堂江湖、阻碍君臣关系的同时,也为同流友人分路时的离别之苦平添几分愁思。中唐诗人柳宗元在衡阳与好友刘禹锡分路道别,写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子厚劝慰与自己同为清流之派的梦得不必学李陵、苏武那般临河取水,自己的千行泪水便足以替代河水濯洗长缨。“垂泪千行”既是对两人受冤流放的愤懑不平,也是对两人怀才不遇的惋惜悲哀,更是为两人共同进退的感动不舍。古代朝鲜文人笔下的“衡阳分路”也不曾缺席,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衡阳分路”主题在朝鲜诗家的笔端仍保留了基本的送别惜别主旋律。朝鲜朝仁祖时期文人李昭汉(1598—1645)与其父李廷龟、其兄李明汉被视为朝鲜版“三苏”,写与友人分别之,他道“桥头立马更深杯,泽畔骑驴怅独回。最是衡阳分路处,不堪风雨晩来催”[25]259。不论是立马桥头踟蹰不前的远行者,还是水泽之畔骑着驴独自徘徊的送别者都禁不住晚来风雨的阵阵“催促”,离别之情在“衡阳分路”的指代性话语中得到了极大的渲染。同样写“衡阳分路”,朝鲜朝中后期诗家任埅(1640—1724)调动“衡阳雁”参与其中,言道“秋风落叶散飞飞,分路衡阳涕自挥。却羡寒空南去雁,叫群能作一行归”[26]126。与过往关注“雁不过衡阳”的诗家不同,任埅突出放大了大雁成“群”与分路衡阳之后人“单”的对比,佐以秋风、叶落的意境烘托,将“衡阳分路”主题下的衡山书写推向极致。
朝鲜诗家笔下“衡山”的另一重要诗意呈现则为心驰神往的理想家园,具有归隐回乡的意蕴。朝鲜潇湘八景组诗创作奠基者之一的陈澕写“平沙落雁”云“惊寒不作戛天飞,意在芦花深处宿”[27]283,其后,李齐贤(1288—1367)更是直言“心安只合此为家,何事客天涯”[28]608。两人试图为“雁不过衡阳”之说做出解释,认为“雁不过”的本意在于衡阳平沙即为雁之“家”,雁之归“宿”,似与宋人黄庭坚“更看道人烟雨笔,乱峰深处是吾家”遥相呼应。朝鲜朝诗人柳楫(1585—1651)补充说明道“含芦何事远飞过,惟恐人间缯缴多。晩向江头还欲下,孤心只是爱平沙”[29]14,在历经仁祖反正、丁卯胡乱最终隐居修学的柳辑看来,躲避“人间缯缴”则是衡阳雁南飞平沙的主要缘由。对此,朝鲜朝后期学者宋来煕(1791—1867)则从性理学出发,提出另一番见解,他认为“白苹风露满江秋,惊起一声更唤俦。飞向清沙闲取适,生涯不作稻粱谋”[30]107,雁飞衡阳绝非为了“稻粱谋”,而是只为求取内心的“闲适”。事实上,躲避“人间缯缴”,渴望“闲取适”“心安”的衡阳雁,又何尝不是激烈党争缝隙中,艰难求仕求生的朝鲜文人士子的写照,衡山也好、平沙也罢,真正疗愈抚慰的,从来都是英雄失路、报效无门、无奈落寞的朝鲜士子之心。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也存在认为衡阳雁是因“稻粱谋”而落平沙的朝鲜诗家。朝鲜朝前期文人姜希孟(1424—1483)作《平沙落雁》直言“冥路通云汉,低飞为稻粱。排空点点字千行,去意在三湘”[31]66;郑希良(1469—1502)云“何处稻粱惊网弋,急向芦花深处宿”[32]13;李廷馣(1541-1600)云“岂不恋稻粱,其如避矰弋。前身诸葛侯,布阵依沙碛”[33]253,言雁落平沙虽为稻粱,但并不是一味贪婪,欲壑难填,而是为了在网弋扑杀下,寻食果腹,维持生命。容斋李荇对此更是清晰解释道:“非无稻粱谋,恐有矰弋加。举群一饥忍,双双下平沙。沙际少人行,暮雨响蒹葭。相呼复冥飞,云水真吾家。”[34]394因而,不论是清闲取适,抑或是谋生立命,衡山的那摊平沙都是朝鲜诗家精神与物质双重向往的理想家园,这点与先秦时期衡山意象中的归隐内涵存在着内在关联。
综上,“衡山”在朝鲜古代诗话中的诗意呈现是鲜活丰满的,它即是古代朝鲜文人贬谪失意时失落悲愤的见证者,也是古代朝鲜文人苦闷无奈时聊以自慰的陪伴者。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解释是古代朝鲜文人在士祸频发,政局动荡的文学生态下,艰难求生但却内心纠结苦闷的历史写照,体现出古代朝鲜文人结合自身独特的生存环境及国情背景对中国“衡山”意象内涵的选择与阐释。
四、结语
潇湘、洞庭湖、衡山作为极具湖湘地域文化特征的自然胜景,吸引国人目光的同时,更成为海东文人稔熟于心的书写对象、心驰神往的诗意空间。实际上,湖湘胜景深处中国腹地,与朝鲜半岛远隔千里,潇湘、洞庭湖、衡山等湖湘胜景能够跨越时空,成为古代朝鲜文人诗歌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得益于文学塑造的魅力与文化传播的增殖功用。细而论之,古代朝鲜文人的湖湘胜景书写出自“记忆”与“想象”两支“笔”。
尽管历史上中朝两国交流频繁,但绝非所有朝鲜文人都能有幸亲至中国,游览湖湘风光。更不论,朝鲜使臣出使路线多以陆路为主,远涉深处中国腹地的湖湘地区对于行程紧凑、路线固定的朝鲜使臣而言,绝非易行之事。据现有文献可考,除了李齐贤、金九容、崔簿等寥寥数人之外,鲜有朝鲜文人涉足长江以南的中国区域。实地实景的潇湘、洞庭湖与衡山对于古代朝鲜文人而言是陌生的、抽象的,存在空间阻隔与空间异质。但是,诗意化的、文学化的湖湘胜景对于古代朝鲜文人却是极为熟悉的、可感的。湖湘胜景借助诗文绘画等艺术加工手段,经由中朝文人交往及诗歌酬唱,流播于朝鲜半岛的文艺世界,生成为朝鲜汉文学的重要创作素材,塑造了历代朝鲜文人的文学“记忆”。
未曾亲临湖湘的缺憾得以在历代描写湖湘胜景的诗文诵读之中得以弥补,神游湖湘、对话先哲的欲望则通过“想象”在篇篇诗文创作中得以舒展。事实上,多数朝鲜文人作品中记载的关于湖南的自然风物,大都是受到中国文人诗作影响的再创造,是一种艺术性的虚构与想象。古代朝鲜文人是通过中国古代文人之眼来看湖湘山水,看的并非实地实景,而是诗画作品中已经交融了中国古代文人情感的湖湘意象。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朝鲜文人对于湖湘胜景的诗意书写可以视作一种情感嫁接与文化转译。
古代朝鲜文人对潇湘、洞庭湖及衡山的诗意呈现在与中国传统意象内涵大体保持一致的同时,于细微之处也展现出符合朝鲜风情及审美传统的选择与认同。潇湘、洞庭湖、衡山所代表的湖湘胜景既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也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迁客骚人自遣愁思、对客挥毫的文学空间,更是经典传诵之间,引发海东诗家共鸣同感的审美空间。古代朝鲜文人的湖湘胜景书写既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印痕,也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助力,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平等对话交流中进行彼此理解,进而促成各自文化意义的增殖与再生的鲜明例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