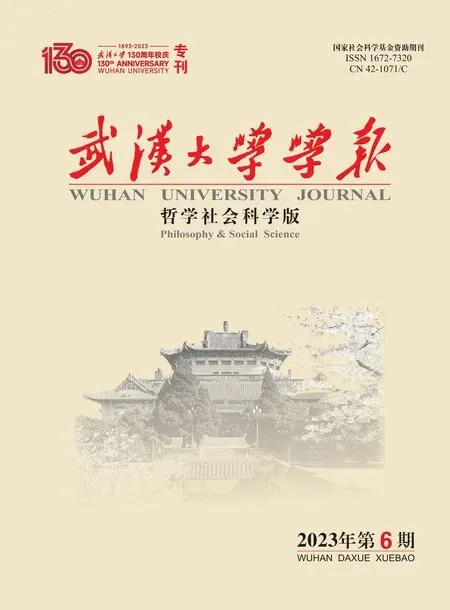吴于廑的大历史观
蒋 焰
1982年10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吴于廑前去参会,并在滇池西山龙门的中途看到了一副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据吴于廑亲述,“这既是描述攀登龙门半途上的情景,也反映了作联者的一种人生哲学。但在归途中,我忽然又想到世界历史”[1](P85)。作为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吴于廑敏锐地意识到了对联中所蕴含的特别意义,并在保留上联的同时将下联改写,是为“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2](P40)。在对改写后对联的解释中,吴于廑说道:“这里说的极高处,是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虽不易达到,但仍应努力。而“能够站得高一点,就便于放开眼界,开阔视野,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同时,他还特意提到了“大”字的用法,虽然“从旧诗词的用字来说,‘大世间’的这个‘大’字有点生。但也无妨,要表达一点新意思,就不妨用一个生字眼”[1](P85-86)。笔者认为,也正是在这一用词中,透露出了吴于廑所具有的一种“大历史观”①关于我国当下“大历史观”的内涵或特征,学者们已有不少讨论。综合而言,其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长周期、大空间、整体性、多学科等视角把握历史发展,同时探究规律,关照时代等。实际上,吴于廑在以往治学中也已具有上述大历史观特征。这也为笔者的考察提供了基础和可能。[3](P7)[4](P43-45)[5](P3-5),既凸显了吴于廑追求的极高的治学和人生境界,同时也是其学术思想的又一集中体现。
那么,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有何内涵,其又是怎样形成并体现在治学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与意义?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知和理解吴于廑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特征,而且也有利于充分挖掘吴于廑等前辈学者思想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以往讨论吴于廑学术思想的论著已有很多,但较少从“大历史观”视角展开①关于此问题的专题讨论尚不多见。不过亦有学者对吴于廑大历史观中的部分思想有所涉及,这也为笔者的考察提供了有益参考。[2][6](P81-87,128-131)。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此为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内涵与形成
何谓“大历史”?学者们通常是见仁见智。据研究,以往主要有三种“大历史”的说法。第一是18-19世纪兴起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第二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Macro History)”;第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史学观念“大历史(Big History)”,以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D. Christian)为主要代表。上述三种“大历史”各有特点和不足,如普遍史“把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按照共同目标和同一路线向前发展的”,但却是先验的,“丧失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黄仁宇的“大历史”主要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强调“从长时段和大范围来研究上自宇宙诞生下到当今时代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将人类的历史融入宇宙起源、地球诞生和生命演进的漫长时段之中”,但也会“弱化历史中人的因素”,“无法展示历史的多样性”[7](P108-109)。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大历史”观念,而是具有特定内涵。从根本上说,吴于廑的大历史观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就如吴于廑所言,研究世界历史首先要站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大”理论作为指导。这是吴于廑大历史观的根本特征,也体现出其“大历史观”所具备的理论高度。
其次,从背景上看,吴于廑的大历史观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这个“大”背景。这也是吴于廑在自己论著中经常突出的一点[1](P64-65),并且还特意强调世界历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而是要将“中国”包含在内[1](P33)。
再次,从视角、方法和主题来看,吴于廑明确提出,要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多用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研究世界历史,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
顾名思义,纵深即是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观察世界历史,不局限于一时一代;宽广即从历史的横向发展上,从“广大世界”视角看待世界历史,不局限于一国一域,由此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全局”[1](P19,47-48)。当然,这么说并不代表放弃或轻视国别、地域、断代、微观研究,或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在上述对联的解释中,吴于廑就提到,“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1](P86)。学科领域的交叉、各种主题的比较以及综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要打破研究方法中学科、领域等方面的界限,为考察世界全局提供路径。这也是吴于廑一贯所强调的,诸如要多学习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古文字学[8](P1-3)、地图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1](P40,332-333,432-437)。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心得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主题时,吴于廑也多次谈到“比较”“综合”方法的运用,即从事世界史,“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1](P457)。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即抓住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或“大运动”。在诸多著作中,吴于廑都体现出了对此类“大事件”“大运动”的关注[1](自序P1,目录P1-3,正文P461-463)。
最后是研究目的,要多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最终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大势”提供关照和参考。总结经验或规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这点吴于廑从不讳言。在谈及世界历史研究时,他明确说到要“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1](P40)。当然,寻求规律并不等于排斥多样性,“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1](P48)。而总结历史经验或规律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现实乃至未来发展提供关照和参考。“研究历史不仅应当为现实问题提供发展的线索和背景,而且应当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9](P2)。
综上可知,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有着自身的独特内涵。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最终关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
那么,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其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吴于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中有关世界历史方面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十分到位。吴于廑曾多次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语[1](P455,328-330,99)。他与齐世荣共同主编的经典性教材——六卷本《世界史》也被评价为中国世界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6](P56)。同时,其个人也被看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史话语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分析框架的建立”,肯定了吴于廑在此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10](P197-198)。以上均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吴于廑的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为其形成上述大历史观提供了思想原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理论性和宏大的视角,它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对象,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远景,实现了历史研究和理论的紧密结合。无论是对社会演进规律的描述,还是对社会联系和交往理论的勾勒都体现出这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P3)。“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P168)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已经初步展现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并常为吴于廑所强调,从而为其大历史观的构建奠定了理论、视角、目的等多方位的基础。
其二,对相关学术思想的辨析和借鉴。吴于廑一贯重视对史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在其主要著作中,有诸多对史学史或史学家的关注。如在探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体系时,他总要先谈及各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或世界史编写的不同观点[1](P3-66);在“自选集”中也将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单独列出,如《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形态学派三家说略》等[1](目录P1-2),并对我国史学史研究有过讨论[1](P420-426)。而考察史学史恰为其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提供了条件。在对自古以来各种不合理的世界历史观批判的基础上,看得出吴于廑对“世界”和“世界史”的初步构想,即其必须是“体现世界的观点”,而不是某个“中心”的观点[1](P3,12)。虽然伏尔泰的世界史观有缺陷,但能注意到基督教世界之外还有中国、印度、阿拉伯诸国,特别是他能重视中国的历史,视野已经超越前人[1](P240-241)。以朗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既不客观,又带有浓厚“西欧中心论”,但却与时代和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还影响了19世纪后期西方专门史及专题史的发展,为以后的历史综合和概括提供了条件[1](P257-263,266-276)。形态学派的斯朋格勒和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周期论”带有命定色彩,但却是较早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他们把世界史看成是多文明的历史,并力图从全局或“完整的历史”角度看待历史①据王敦书的考察,吴于廑的世界史观还受到雷海宗形态史学观的影响。[1](P31)[13](P31-34)。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于廑就已注意到同时代巴拉克劳夫的思想,并辩证分析了其中的缺点和有益启示,即要抛离西欧中心论,对西方史学进行重新定向,从而“放眼世界,展示全球”[1](P181-182,32)。此外,苏联史学特别是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引进,从学术思想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1](P17)。最后,国内学者周谷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也富于启发意义[1](P46)。这些学术思想同样从背景、视角、主题、目的等方面促发了吴于廑大历史观的最终形成[2][6](P218-227)。
其三,得益于吴于廑自身的生平经历。吴于廑在自传中大致叙述了自己求学和学术思想,特别是世界史观形成的过程。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学术上的转弯。所谓学术上的转弯指的是“踏进一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多转几个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1](P451)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招收吴于廑读研究生的陈序经。对于大学读历史的学生,可以进经济研究所吗?这是吴于廑当时的疑问。但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吴于廑在读研期间,读了经济史、经济学说、经济地理以及历史,开始了最初的学科交叉,同时也打下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基础,为以后开展关于农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吴于廑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赴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跟随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家麦凯尔文教授学习,接触到了中古前期西欧的政治和法律史,实现了自己的又一次转弯,进一步推进了在学科领域方面的交叉[1](P452)。在吴于廑回国任教后,因教学及教材编写又接触到了世界古代史这一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这种“转向”亦对其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多有惠益[1](P453,自序P2)。而这些学术上的转弯,好处在于能够开阔其视野,“不以一隅自限”,“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就连吴于廑自己也提到,“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1](P451)。除了转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吴于廑对“比较”方法的重视。按吴于廑自己的说法,这一思想萌发于读研究生时。因为看的西方知识多了,就希望能与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因此得出“学历史宜作比较研究的思想”[1](P451)。这一方法一直为吴于廑所贯彻。其硕士学位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虽然主体是写中国,但仍有中西封建时代比照的大背景,并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14](P315)。其博士学位论文则更进一步,副标题中直接标出了中西对比之意,即《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对比封建欧洲探讨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在该文中,吴于廑先用一章论述了中世纪欧洲的王权和法律,然后再分用两章考察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最终得出比照性结论,说明封建欧洲和封建中国在王权和法律观念方面的类似发展,但同时亦有差异[15](P165,173,170)。
无论转弯还是对比,往往都要突破以往的学术乃至人生界限,使得自己的观念更加开放,视野更加宏大。亦如吴于廑在一封私信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时所言:“讲通达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肤泛,但通达的本身是一种教养,它可以孕育宽容,蔚成一种胸怀广廓的风格。”[14](P312)这或许也是个人经历给其学术思想打上的印记。由此不难看出吴于廑的个人经历对其大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影响。
二、吴于廑大历史观在治学中的体现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是如何体现在其治学中的?为了系统地说明这一问题,下面从吴于廑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的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考证三方面展开。
谈及吴于廑的治学,首屈一指的当属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笔者认为,这是展现其大历史观的最主要方面。首先从理论基础上,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大历史观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诚如吴于廑所言,在他回国工作后不久,碰到两个涉及史学思想的问题,为了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需要另寻他途。为此,吴于廑便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所以才引发了他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和“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大,……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等经典话语的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已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1](P453,455)。这一点在吴于廑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中被经常提及[1](P48-49)。
在背景层面,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探索同样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这个“大”背景。从学术方面说,无论是解放前(以“剑桥三史”为代表),还是解放后一段时期内(以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表),中国的世界历史理论或体系都不令人满意。欧洲或西方中心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关注不够等问题较为常见。因此中国人“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同时“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1](P15-19)。此外,恰逢当时国外史学界出现了新变化,如前述巴拉克劳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都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编写方式,这也对中国的世界史理论构建提出新挑战。如何在辩证认识西方史学发展优缺点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同时创立中国的世界历史体系是当时学界的共同任务[1](P45-47)。从现实看,无论是新中国初建[16](P158),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17](P57),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面对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如了解世界,与他国建交(连毛泽东主席都发出了“学一点世界史”的指示),以及国际新形势的发展,如二战后非殖民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理论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
在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构建中,吴于廑在视角、方法和主题选择上也同样鲜明体现出了大历史观印记。纵深和宽广的大视角是吴于廑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核心,他提出的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理论即是代表。“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1](P47-48,40)。当然,这种纵横的考察是建立在具体问题研究之上的,也就是前述提到辩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之上的。正如吴于廑所言:“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1](P39)
学科交叉、比较综合是吴于廑考察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时的重要方法。这点从他对“世界历史”的界定中就可看出。世界历史是“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1](P40,22)。在实践中,吴于廑也积极利用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成果探究世界历史体系。如考古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早期历史上农耕中心及其拓展过程。多种古文字的释读,可以推进各个古代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研究[1](P36,29,51) 。与此同时,在世界历史体系的构建中,探讨的主题一般都要超出国别和地区范围,其中既展现了比较和综合方法的必不可少,同时也能反映出对历史“大事件”或大势主流的把握。吴于廑就曾举例说过三种代表性的重大主题,分别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如亚欧大陆的宗教传播与影响);“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进行综合比较(如中亚地区与世界历史全局的关系);还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要“对这类共同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如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说明各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即“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1](P20-22)。
在吴于廑看来,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总结规律,学以致用。他批评朗克史学讳言规律,重申苏联世界通史编纂中对人类历史中存在着规律这一说法的正确性[1](P29,32)。在讨论纵、横发展时,通过对演变过程的探讨,吴于廑揭示出二者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且二者发展并不是平行和各自独立的,而是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1](P49-50)等规律;探索出了规律或有了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应对现实,甚至展望未来。在面对世界历史的纵横发展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并行阶段时,吴于廑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工业世界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但如能进行改革,吸取人类历史经验,则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而来的前景或许是两个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世界形势的改观。并且就长期趋势看,当资本主义制度因其自身固有矛盾而实现对其自身否定的历史蜕变后,当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自身完善后,世界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工业世界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趋向扩大的全新趋势。世界历史的纵横发展也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新时代[1](P62-66)。
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的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是吴于廑治学中体现其大历史观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吴于廑关于此方面的探讨也是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构建的延续。吴于廑主要用了四篇鸿文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诸大历史运动,即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及其对形成世界史的影响、世界历史上由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及其转折性意义、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新兴工业世界对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及传统农耕世界的反应。这四篇文章围绕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的主线,首尾相连,环环相扣,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逻辑整体。
与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探讨一样,对诸大历史运动的讨论首先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在系列文章开篇,吴于廑就用“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来说明此诸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1](P70)。随后又多次利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如进入农耕世界后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农耕世界业已存在的国家,如马克思所说,都是以农为本的社会;马克思“关于封建制下农民及其家庭生产可变量的论述,提出市场扩大是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于封建社会母胎的内部,其意也在于指出历史上近代工业世界的出现,并非突发的现象”[1](P83,99,120)。中国与世界变革的大背景亦贯穿于对诸大运动的讨论中。无论是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时,还是农耕世界转向工业世界中,作者一直将中国作为描述重点之一①据笔者统计,在这四篇文章中,提及“中国”一词的次数达70余次,还不算其提到的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名称的词语,并且在论述篇幅上并不少。,特别是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时的经验教训,关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1](P148)。
不仅如此,吴于廑在四篇论文中也展现了大历史观的视角、方法和主题。这四篇文章描述的各大运动,从纵深角度说,无一不超过了百年,有的甚至达到千年以上。如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时涉及了约三千多年的时段,世界历史上由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大概也有四百年的跨度,而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亦涉及六七百年。如果通看起来,则是“自远古以迄19 世纪”[1](自序P1)。从广度方面论,这些运动涉及的地域、国家、民族较为繁杂,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用具体史实和数据论证的基础上,突破国别和地域视野,站在亚欧大陆乃至全世界视角下看待历史上这些运动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构建整体世界时所有具有意义。就正如作者所言,“我试图从放大观察广度着眼”,扩大视野,真正做到以世界全局看待历史的发展[1](P70)。
交叉、比较、综合的方法在上述研究中也不胜枚举。在系列文章伊始,吴于廑就说到楔形文、甲骨文、古代文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等考古学、古文字学新发展对史学研究具有的重要作用。在考察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时,吴于廑利用对迈锡尼线形文字乙的释读,了解印欧人对希腊半岛的冲击形式;利用对中国商代的考古发掘,佐证当时车马的形态[1](P69,76)。在《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一文中,又提到了经考古等发现的金银窖藏屡见不鲜等论断[1](P143)。而“比较”不仅涉及地域上的东西、南北对比,国别上的外国与外国、中国与外国的对比,而且还有时间上的前后时代对比,以及具体问题的对比等。如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农耕世界在面对北方游牧世界冲击时的状态异同;以农本为重的封建时代,西欧与中国在耕织结合上有什么差异,这种情况又会对西欧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产生何种深远影响;近代工业世界和传统农耕世界在时间、数字、效率等方面观念有何不同,造就了工业世界什么样的新特征;面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西欧内部、中东欧、亚洲主要大国反应有何异同,结果如何等[1](P69-86,91-92,139-145,149-177)。“综合”则更无须多言。在比较的基础上,吴于廑最后都回到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这个主题,客观评价了游牧、农耕、工业世界等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说明了诸大历史运动是如何从纵横两个方面向前演进,并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推动了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至于“主题”,诸“大”运动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同时在展开具体论证时,文章也抓住了各个时代的核心对象。如古代的主要游牧民族,几大农耕文明区域,英、法、德等工业世界大国,亚洲主要大国等。当然贯穿于诸大运动最根本的还是物质生产方式变迁这个核心,才能反映发展的“大势”①这些特点在这四篇文章的开始和末尾,以及整体构架中均有反映。。
接下来是目的,这点同样透露出大历史观的印记。如在相关文章中,吴于廑总结了传统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应对规律和启示,即“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者,反应多有成效;否则反是”。他还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对无限利润的追求会导致其近代工业无限扩展的特性,进而指出“近代工业世界是一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1](P177)。对于未来前景,吴于廑做了较为开放的估计。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后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如何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可能会有新的变化[1](P117-118,177)。论及中国,吴于廑也表达了自己的冀望和思考:“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的来自西方工业世界的冲击,应当从历史上知彼知己。知彼乃所以取彼之长,舍彼之短;知己乃所以益已之不足。这样就庶几能在饱经冲击和饱尝忧患之中,找到自己的,而非照搬的,进入工业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新路。”[1](P148)
最后,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上,我们再来看下吴于廑是如何体现其大历史观的。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在考察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时,在讨论封建主义经济规律时,在探索文艺复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历史作用时[18](P24,26),再到评价史学史论著等,都可看到吴于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关理念的理解和成果运用[1](P358,368,335-336,423,426)。正如其所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P394)立足于中国背景和问题这一特点同样突出。如在对中世纪西欧的法律和君权以及日耳曼马克公社考察时,提到了对中国农村公社残余问题的思考;对西方人本主义与中国封建痼疾关系的探讨放在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思想潮流变动的大背景下;《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一文则基于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讨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启示[1](P330-331,392,396,407)。
其次是大历史观中的大视野、大主题和大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更为显著。诸如《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等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让人感受到吴于廑写作时纵深而又宽广的大视野[1](P382,371),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大主题。当然,这种大主题在其他论著里亦有体现。在自己平生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19](P334),吴于廑于“卷头语”处就点出了写作此书的想法和目标,“对任一史实的叙述,总不要让它脱离历史发展的大势;既要透过史实来显示历史的归趋,也要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实的意义”[20](P1)。选定15、16世纪世界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也是因为吴于廑抓住了世界历史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阶段之一[21](前言P1-5)。如其所言:“世界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状态’‘愈来愈彻底’的消失,从世界全局说,这个过程也要到15、16世纪才算真正开始。”[1](P457)此外,交叉、比较和综合的大方法也十分常见。在考察中世纪西欧法律和君权的文章中,吴于廑就综合运用了语言学、法律史、法理学的成果。在谈到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涉及了古文字学、建筑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此外还在《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一书的编纂中,尝试利用地图、插图等来展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主线[1](P311,308,324,382-391,432-437)。而对比和综合更是俯拾皆是。在讨论希腊城邦时,吴于廑在对比东方古代城邦的基础上总结了希腊城邦的特点。《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于见同中说异——〈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序》等文的标题即显其意[22](P26-29)[1](P369,441-442)。而将这种对比和综合体现得更为明显是《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寥寥数语,吴于廑便勾勒出了15、16世纪变革之际东西方的异同,并从全局视角综合分析了世界历史是如何由分散走向整体的[21](前言P1-3)。
最后是研究目的,同样体现出了大历史观中探寻规律、关照现实这一特点。在《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中,吴于廑通过考察得出了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点结论。在评论《欧洲近代史学史》时,吴于廑谈到了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的观点,并指出它在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目的是探求人类历史的规律方面具有的拓新意义[1](P357,425)。而在给《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等书作序时,吴于廑一再强调了研究西方历史对其时现实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中国发展和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意义。“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包括路德宗教改革在内的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以及这种思潮在形成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作用和影响,无疑会为我们揭示可资借鉴的历史得失和利弊”;“合理借鉴西欧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实现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而研究西方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出中国自己的路[1](P440,444)。
三、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影响与传承
吴于廑的大历史观在后世影响与传承意义方面有三点尤为值得关注。
其一,形成了具有自主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作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吴于廑以其大历史观不仅对世界历史学科进行了明确界定,而且还从纵、横两个维度构建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理论和体系,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等创见,并编纂了多部世界通史类教材,影响深远,被看成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3](P26)。对此,有学者评价道:“我们的欧美同行如果把吴于廑教授提出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与《剑桥世界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和斯塔弗里阿诺斯‘环球通史’体系等等相比较,都不难发现前者独有的新意。可以说,它也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在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24](P11)而且相比而言,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还更有明确的体系[6](P16)。此外,亦有国外学者在外刊上介绍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理论[25](P19-26)。不仅如此,其大历史观及理论成果也为不少学者所吸收或借鉴,在学术上得以承继和发扬。如在吴于廑开辟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学者、高质量著作和研究机构,在学界独树一帜①如《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及其续编、三编等的出版,以及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研究所、15-18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等。[26][27][28]。同时,还有学者将其贯彻到教材编写、史学理论和专题探讨以及教学研究中,显示出这一观念的持久影响力②如《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5卷本)教材的编写,以及《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2023年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对吴于廑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的讨论等。[29][6][30]。
其二,有助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这点可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如上所示,在大历史观下取得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以整体世界史观为代表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以及围绕此而形成的独特传统,具有广泛影响力,同时更凸显出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自主思考和中国创见。而这正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时可以汲取的重要理论与宝贵财富[31][32][33](P20-23)[34](P54-57),从而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基础。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吴于廑的大历史观在理论导向、背景、视角、主题、目的等方面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也均有启示。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吴于廑大历史观的理论指导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是其打破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关键,也是提出创新性观点的基础,同时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方面的准确性和重要意义,从而为当下创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树立了理论导向和榜样。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化特点也为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所吸收。大历史观下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更在于考察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理论化创见或体系。这种理论探讨和具体问题研究的高度结合无疑也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启发性。因此,与大历史观一样,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引。
以中国历史或问题为背景和关照核心,“发中国之声”,是吴于廑大历史观的又一特点。首先吴于廑强调世界历史并不是排除了中国之外的历史。“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1](P40)。这对于我们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分类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当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情势下,对构建包含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在内的“世界历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亦有启发。其次,吴于廑大历史观突出对中国问题的关照。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现实中的中国,抑或是未来的中国都是吴于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特点也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核心之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虽然有时考察的是外国或世界问题,但仍要有中国关怀。尤其是结合世界之大背景,为中国发展提供经验或教训,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另一种体现。最后,“发中国之声”。吴于廑在尽力考证的基础上,总是带着中国人的视角去分析、鉴别国外的相关研究,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和跟随他人亦步亦趋。因此,吴于廑从不讳言自己和他人看法的不同。这同样是我们在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时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笔者认为可以分三个角度予以阐释。第一,吴于廑大历史观中纵深广阔的大视野以及站在全局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提出的创造性思想,是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大视野,站在人类全局高度上为人类共同发展指明的方向。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强调全局,特别是世界历史这个全局①例如仅在吴于廑的《自传》中,就有约15次之多。[1](P449-458)。并且也正是因为全局视野的存在,吴于廑才有了对世界历史整体理论和体系的把握,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的憧憬[1](P66)。因此,二者皆是立于全局的高度审视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未来。而这种相通性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在学理上也有着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深入理解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意义。第二,吴于廑大历史观从宽广的大视角强调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性,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经验和实现路径。吴于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历史观弥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理论内容[6](P81),并进而勾勒出了人类历史在横向发展方面由古代至现代的“大图景”,肯定了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横向交流,尤其是互鉴、合作的积极意义②虽然吴于廑也提到暴力也是一种交往形式,但并不等于他对此种方式表示认同。和平、公正等才是其所追求的交往方式。[1](P177),最终揭示这些横向发展如何与纵向发展相结合,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正需要坚持交流与合作,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最终推动世界和人类的整体发展。因此,如何更好地以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为指导,将横向发展理论持续推进,通过研究更多之前未有探索的历史和现实,不断总结交往规律和世界发展大势,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参考、启示及实现路径。第三,吴于廑大历史观中的比较、综合之法和某些敏锐的见地也为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和线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尊重世界各国或各种文明,因此要打破“西方中心论”,平等地了解、对待每一个国家或文明。不仅如此,它还要在单个国家或文明研究基础上进行多国家或多文明对比和综合,去探寻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共性价值。在这些方面,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也可发挥积极作用。如从世界历史角度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用之理据;倡导多用比较、综合之法去研究各文明和国家的异同也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价值观基础。此外,吴于廑大历史观下所展现的某些十分深刻的见地,为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发现及其解决提供了线索。例如通过对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特别是近代工业社会的考察,吴于廑很早就认识到人类面对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破坏等共同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谈到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利用科技的力量及全世界的通力协作[1](P65)。这无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涉及的当下重点关切,如环境、能源、健康等问题的认知及其解决提供了思路。
四、结 语
综上,吴于廑的大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同时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历史纵深、广阔世界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并通过学科或领域的交叉、比较、综合等宏观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主流,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总结历史共性、规律及经验,最终为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提供关照和参考。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熏陶,同时也得益于经过多次“转弯”锤炼的独特经历,以及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思想的辨析与借鉴。这一观念体现在吴于廑治学的诸多方面,包括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诸大历史运动的探讨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中,并在学术观点、方法论、经验启示等层面为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而通过对吴于廑大历史观的考察,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吴于廑学术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和一些以往较少强调的新特征,从而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的丰富性、创见性和新意义。同时,还为我们思考当下大历史观的学术源流,以及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挖掘、借鉴和传承我国世界史学科前辈学者的重要学术思想,乃至中国本有的优秀传统或文化,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取得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让中国学派屹立于世界之林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此外亦如前言,大历史观不仅是吴于廑的一种学术思想,同时也象征着其极高的治学和人生境界。每逢著述,吴于廑常以虚心口吻求教于人;每谈成就,又以谦逊态度表示微不足道;每待后学,则多有鼓励和爱护,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位“大先生”的风骨。这或许也是大历史观在其人生上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