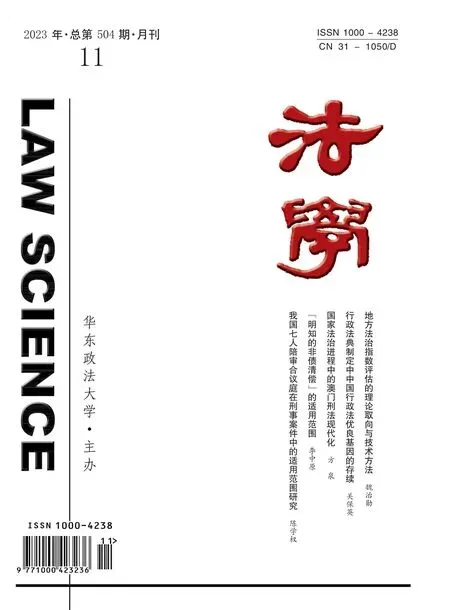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探究
●孙靖洲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是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工具,包括使用肖像推销产品或服务,或者直接利用自然人形象谋取利益。所有类别的许可使用合同都是通过将生产要素许可给他人使用而获得物质或非物质收益,其目的是通过契约自由优化资源配置。然而,我国《民法典》为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设立了特殊的规则,具体包括禁止转让肖像权、要求法院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以及赋予肖像权人基于“正当理由”的特殊解除权(《民法典》第992 条、第1021 条、第1022 条第2 款)。不难看出,这些规则不仅限制当事人自治,而且偏离合同法一般原则。对此,我国学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优先于财产利益,即相对于肖像使用的财产利益,肖像权人的人格权益应当被优先考虑。〔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53 页;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 页。第二种观点认为,肖像权人在与商业实体进行谈判时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法律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以弥补双方的权力差距。〔2〕参见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241-242 页。这两种观点均存在可商榷之处。
人格利益优先的观点虽然道明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特殊规则的立法本意,但没有说明何种人格利益应当如何被优先保护,这导致实践中鲜少适用肖像许可使用特殊规则,〔3〕例如,有关“练习生”的演艺经纪合同通常会包含长期且独占的肖像许可使用条款,但法院对此基本不会给予特别关注。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 民终3998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5)虹民一(民)初字第3275 号民事判决书。虽然上述纠纷发生在《民法典》颁布前,但在《民法典》生效后,法院依旧未考虑“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以及赋予肖像权人基于“正当理由”的特殊解除权等法律规则。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 民终14881 号民事判决书。而在仅有的相关判决中,人格保护水平不一、交易安全性较低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关于肖像权人的处分权能、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以及肖像权人基于“正当理由”的特殊解除权等法律规定均亟待理论澄清。须特别保护弱势肖像权人的观点实质上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护属性无关,而是为了维护交易的实质公平。换言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规则的运用完全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强弱之势。这与《民法典》设置该规则的初衷不符,也与现今流行的肖像商品化场景不相匹配。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作为肖像权人自治高度发展的产物,对其人格利益予以保护何以必然?应如何设置其人格保护规则以合理解决自治和人格尊严的冲突?正因为针对这些问题的学理研究付之阙如,学界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设立和调整尚缺乏共识,〔4〕参见李宇:《十评民法典分则草案》,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6 页;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页。也导致实务界极易陷入或者过度保护人格权益而忽视交易安全,或者重视交易安全而弱化人格权益保护这两种境地。鉴于此,本文首先探究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属性,阐明人格保护规则的目的和特征,后者为现有研究所普遍忽视,却为后续形塑人格保护规则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反思既有相关规则的价值预设和保护效果,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可撤回的同意”规定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影响,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区分缔约和合同履行两个不同阶段,在充分吸收比较法经验且遵循已有立法和解释构架的基础上,运用法教义学充实和调整既有规则。
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溯源及其属性
在肖像商品化场景中,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体现了肖像权人以一种受拘束的方式处分其人格利益的意思表示,是其与相对人基于共同意志而对合作关系的形塑。通过履行合同,肖像权人既能获得财产收益,又能实现向外界展示和表达自我的精神利益。可见,承认肖像权人针对其人格利益的自主决定即体现了对其人格的保护;相反,过度偏向肖像权人的人格保护规则会显著提高肖像权人寻觅合作伙伴的难度和成本,其甚至不得不通过让渡更多的财产利益以换取合作机会。〔5〕See Brian Bix, Contracts, in Franklin Miller & Alan Wertheimer (eds.), The Ethics of Consent: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1-280.从这一点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恐将成为限制肖像权人事业发展和人格自由的桎梏。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明确在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引入人格保护规则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一)人格权一元理论的基础与内在要求
我国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立基于人格尊严价值优先的立法选择。〔6〕参见王利明:《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1 期,第9、12-13 页。一方面,当个人自治与人格尊严发生冲突时,个人自治须让位于人格尊严。因此,肖像权人不得转让肖像权,其与相对人自愿排除特殊解除权的合同约定亦应无效。另一方面,当财产利益的实现与人格尊严的保护产生冲突时,后者亦被优先保护。于是,在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时,应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人格权保护而非有利于相对人债权保护的解释,肖像权人也可基于人格发展的需要随时解除有期限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
然而,个人自治是人类尊严的应有之义。限制个人自治,即否认每个人是其个人事务最好的管理者,本身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理性和人类尊严的贬低。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承认人作为理性和自主性的存在,进而认可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自主决定和自我负责。〔7〕Vgl. Immanuel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Einteilung der Rechtslehre, 1797, zitiert nach der von Wilhelm Weischedel (hrsg.),Werksausgabe, 1997, Bd. VIII, S. 345.与之相应,立法者应当以尊重个人自主决定的方式维护人类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即法律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和追求其目标,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该目标。〔8〕Vgl. Heinrich Hubmann, Das Persönlichkeitsrecht, 1967, S. 175.换言之,尊重人格尊严也即尊重肖像权人自主和多样的利益排序和追求。
正是源于人格尊严与个人自治的内在关联,以及人格权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维护的密切联系,一味强调人格尊严和人格权益相对于个人自治和交易安全的优先性,既不能合理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利益平衡,也难以实现法律保护人的主体性和优先性的目标。诚然,完全承认自主意愿对法律关系形成的决定作用,秉持“意志高于理性”的自治原则,极易使人格利益受制于财产利益,进而导致人沦为商品。〔9〕See Jennifer Roth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Publicity, 101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85, 205 (2012).以美国的人格利益保护二元模式为例,其通过隐私权保护自然人独处的精神利益,将“公开权”(the right of publicity)即商业性利用个人肖像、姓名等身份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设定为财产权,允许其自由流转。〔10〕See Edison v. Edison Polyform Manufacturing Co., 73 N. J. Eq. 136, 67 A. 392 (1907);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97 Supreme Court 2849 (1977);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3-223 (1954); California Civil Code, Section 3344.这种二元模式虽然通过充分尊重个人自治而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优化,但会使人们终局性地丧失对自己身份标识的控制力,进而严重制约其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的能力。例如,美国法院认定包含10 岁童星裸照在内的公开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11〕See Shields v. Gross, 58 NY 2d 338.平台可以通过“用户协议”免费或以极低的报酬永久地获得用户所有的公开权〔12〕See Dancel v. Groupon, Inc., 940 F. 3d 381, 383 (7th Cir. 2019); Perkins v. LinkedIn Corp., 53 F. Supp. 3d 1190 (2014); Fraley v.Facebook, Inc., 966 F. Supp. 2d 939, 944 (N. D. Cal. 2013).即为著例。
概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个人自治的终极目的,内在于人格权利的积极利用之中,而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正是实现该价值选择的保障措施。换言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设置,关乎能否合理解决个人自治和人格尊严的冲突,以及充分平衡人格权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维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则需要剖析人格权的本质以及权利主体处分人格权的目的。在为权利主体保留不可让渡的人格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其个人自治空间随着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伦理道德观的变化而持续拓展,以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方式处分人格利益并最终达致促成人格发展与成熟的结果。
我国的人格权保护取径于德国的人格权一元理论(monistische Theorie),即由于人格权所蕴含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不可分割,因此人格权也必须同时涵盖其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即一元权利。〔13〕Vgl. Horst-Peter Götting, Persönlichkeitsrechte als Vermögensrechte, 1995, S. 138 f.; Benedikt Buchner,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Privatrecht, 2019, S. 218 ff.自然人不能转让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因为其与精神利益相互交融且相互影响。肖像商品化的运行逻辑正是将消费者对肖像主体的注意、喜爱或信赖“转移”到产品或服务上,其价值基础是肖像权人的形表、身份、人品、声誉和影响力等完整的人格利益。〔14〕参见杨立新、林旭霞:《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第78 页。因此,对人格标识的利用也是对整体“人格利益的许可使用”(我国《民法典》第993 条)。〔15〕参见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55 页;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3 页。譬如,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尽管具备财产利益,但也是自然人形成自我、认识自我和表达自我的工具,对它们的使用在具体场景下会影响自然人人格的形成和社会身份的建构,因此,权利人不能与肖像权、名称权等已经客体化的人格权利相分离。〔16〕参见孙靖洲:《德国肖像商品化权:渊源与流变》,载《德国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134 页。
以作为普遍现象并被广泛接受的肖像商品化为例,一方面,为防止他决,即肖像权人只能被动接受他人的商品化行为并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获得救济,法律应当允许民事主体基于自主意愿而积极利用肖像,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展示和表达个人形象;〔17〕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 页。另一方面,为维护自决,法律必须确保肖像权人的处分符合其真实的自主意愿,并且永远保有人格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于是,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旨在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18〕Vgl. Götting/Schertz/Seitz, Handbuch Persönlichkeitsrecht, 2018, § 10 Rn. 16.
不少美国学者也认识到权利主体保有公开权对实现个人自治的重要意义,认为将公开权定性为财产权属于对其正当理据的误认。就权利基础而言,无论是洛克的劳动理论还是以市场失灵为基础的激励理论都不能证成公开权。〔19〕See Dogan & Lemley, What the Right of Publicity Can Learn from Trademark Law, 58 Stanford Law Review 1161 (2006). See also Michael Carrier, Cab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a Property Paradigm, 54 Duke Law Journal 43-44 (2004).根据劳动理论,明星在成名之路上的劳动即使值得保护,其价值也难以全部归功于名人自身的努力。运营团队的“包装”和“粉丝”对“爱豆”(idol)的贡献通常是偶像商业价值的主要来源,因而劳动理论难以解释公开权缘何由明星独享。激励理论的正当性在于公开权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娱乐产业,从而促进文化娱乐市场的繁荣,而如果允许第三方不付成本、坐享他人的明星价值,则会使社会公众承担“搭便车”行为的负外部性,即文娱市场的萎缩。姑且不论是否需要激励如此之多的有生力量进入娱乐市场,单就公开权阙如而言,文娱市场大概率也不会陷入缺乏明星的困境,因而激励理论难以立足。
探究公开权的起源,可以发现其与隐私权是人对人格标识自决权的一体两面。“隐私权之父”沃伦和布兰代斯从作者享有决定是否公开自己作品的权利入手,证成个人有权决定是否和如何公开私人事务是一项普通法原则。〔20〕See Waren &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8 et seq. (1890).但由于沃伦当时备受小报记者的侵扰,其仅讨论了该普通法原则在消极防御层面的意涵,未能论及个人自治的积极利用层面,即公开权的权利基础。〔21〕See Felix Cohen, 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35 Columbia Law Review 815 (1935).质言之,公开权保护人们选择对外展示个人事务以及以多少对价进行公开的权利。因此,仅关注公开权的财产属性就会遮蔽其在流转过程中对权利主体精神利益的影响。例如,当脱衣舞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模特的照片宣传其场所,某医生的肖像被用来给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物做广告时,权利主体的隐私权和公开权就会同时受到侵害。〔22〕See Geiger v. C&G of Groton, Inc., No. 3:19-CV-502 (VAB), 2019 7193612 WL (D. Conn. Dec. 26, 2019); Lopez v. Admiral Theatre, Inc., No. 19 C 673, 2019 WL 4735438 (N. D. Ill. Sept. 26, 2019); Underwood v. Doll House, Inc., No. 6:18-cv-1362-Orl-31GJK,2019 WL 5265263 (M. D. Fla. Aug. 15, 2019); Yeager v. Innovus Pharm., Inc., No. 18-cv-397, 2019 U. S. Dist. LEXIS 18095 (N. D. Ill. Feb. 5,2019).于是,有美国学者主张限制公开权的永久转让,并赋予权利人在特殊情形下解除合同的权利。〔23〕See Jennifer Roth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Publicity, 101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85, 205 (2012); Barbara Bruni,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s Market Regulator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41 Cardozo Law Review 2231-2232 (2020).究其原因,公开权的行使亦有边界,即人不能以放弃自由的方式实现自由。〔24〕See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Batoche Books, 2001, p. 212 et seq.; 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5 (1971); Gerald Dworkin, Paternalism, 56 The Monist 64 (1972).
(二)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法律家长主义属性
美国学者詹姆士·Q.惠特曼关于欧陆法上的人格权维护尊严而美国法上的隐私权捍卫自由的观点固然正确,〔25〕See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113 Yale Law Journal 1151-1221 (2004).但是忽视了自由与尊严的内在联系。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就是以对个人自治一定程度的否定来扩充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选项,进而促成人格尊严作为终极目的在法律上的实现。〔26〕参见杨立新、林旭霞:《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第78 页。这种像父母保护孩子一样,通过否定个人选择以防止其受到伤害并使其过上“好的”生活的法律安排,具有鲜明的“法律家长主义”(legal paternalism)特征。〔27〕See John Kleinig, Patern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6.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并积极运用具备正当理据的法律家长主义。〔28〕“法律家长主义”规范多见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劳动法》等保护性法律和法规。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保护债务人,认定其与银行签订的高利贷合同无效;〔29〕Vgl. BVerfG 19.10.1993, NJW 1994, 36 [3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干涉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30〕See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 U. S. 379 (1937);Owen Fiss, Why the State?, 100 Harvard Law Review 790-794 (1987).另一方面,具备正当性的法律家长主义也会因超出必要性或一味迎合立法者的价值偏好而丧失合理性。〔31〕See David Shapiro, 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74 Virginia Law Review 546 (1988).法律家长主义的滥用不仅忽视了个人追求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而且极易因过度保护而成为人们理性发展的桎梏,甚至会因罔顾社会现实而适得其反。因此,学界普遍要求严格审查法律家长主义的设立条件,确保其具有正当理据、积极的保护效果和必要性,以避免法律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不当干预。〔32〕参见黄文艺:《作为一种法律干预模式的家长主义》,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5 期,第13 页以下;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5 (1971).
鉴于此,须参考家长主义的设立条件,谨慎设定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护规则,以协调私法自治所保障的消极自由和法律干预所追求的积极自由。〔33〕参见易军:《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6 期,第57 页。为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在设立上应遵循下述原则。
其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旨在尽可能将人格权利的自决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这种对肖像权人的特殊保护与肖像权人在合同关系中的强弱地位无关,但在解释和适用规则时仍需要考虑双方在信息掌握和法律地位上的对称性,因为一个人越难以作出理性判断,其错误选择的后果越严重,法律家长主义保护的正当性也就越强。〔34〕Vgl. Eidenmüller, Eきzienz als Rechtsprinzip, 4. Aufl., 2015, S. 384 f.例如,在韩国“偶像练习生”产业中,大多数“练习生”都是未成年人,其对复杂的演艺经纪合同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更难以准确意识到动辄上百万元的违约金和十几年的合同期限对其人身的拘束力乃至对其人生发展的影响。〔35〕在韩国发达的“偶像练习生”产业下,年轻人为获得专业训练和参加比赛、演出的机会,通常不得不与大型的经纪公司签订长期、无报酬且包含巨额违约金的“奴隶契约”。See Lucy Williamson, The Dark Side of South Korean Pop Musi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760064, last visit on May 20, 2023.此时,法律可以考虑介入当事人的缔约过程,通过设置权利保留规则帮助肖像权人充分理解其权利处分变动和后果,并在合同履行阶段通过解释规则保障肖像权人对其人格利益的控制力。
其二,肖像权人理性自治水平的提高是人格保护规则具备积极保护效果的体现,即肖像权人可以通过管理肖像利益控制行为后果并承担自主责任。在实践中,通过宽泛解释“正当理由”,或者以肖像权人事后的主观标准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虽然可以强化对肖像权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使其免于承受错误决定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于挫折中锻造心理韧性也是自治能力发展和人格成熟的重要方式,对肖像权人的过度保护无疑会使其谈判能力和缔约理性难以进步和发展。〔36〕See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Batoche Books, 2001, p. 252; Duncan Kennedy, 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 41 Maryland Law Review 640 (1982).因此,人格保护规则应尽量避免对合同法律效果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事前规则和柔性规则丰富肖像权人管理肖像利益和控制相对人行为后果的方法。
其三,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应当通过学理和教义学予以构造,仅在必要时对肖像权人的自主意愿作出限制和调整。在实践中,艺人经常会与经纪公司签订“一揽子”人格标识独家许可使用合同,将其所有依法可以商品化的人格标识全部许可给经纪公司使用,由后者经营管理,包括与企业和广告商的营销合作,以及针对第三人侵权行为的维权诉讼等。〔37〕参见张红:《人格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246 页;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 民终14881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 民初25623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1 民初1035 号民事判决书。该类许可的优势十分明显,不仅能显著简化双方的交易过程、提高交易效率,还可以使二者各司其职、丰富文化娱乐产品的供给。因此,不问是否存在其他更为缓和的手段亦能实现防止肖像权人让渡重要人格利益的目的,而是直接禁止肖像权人给予此类许可,不仅可能违背肖像权人的真实意愿,而且有超出必要性之嫌。〔38〕See David Shapiro, 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74 Virginia Law Review 546 (1988).
其四,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既要与合同法等民法教义相协调,也要关照肖像商品化的发展。在实践中,艺人与经纪公司签订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条款)一般包含在演艺经纪合同中,而后者涵盖范围广,还包括有关职业规划的委托合同、培训和演出合同等,所以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护规则不应严重偏离合同法的一般规则,而应以合同整体作为依据,根据具体情势进行调整,力图形成与其他权利义务协调一致的解释方案。
二、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价值预设的反思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不仅来源于《民法典》中特殊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规则,还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虽然两者都基于人格保护的目的而干涉肖像权人的自治,但亦存在严重冲突。于是,既需要对《民法典》中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规则的价值预设进行阐释和反思,也有必要分析并应对《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同意规则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提出的挑战。
(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价值预设及其反思
在我国《民法典》中,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虽然仅有3 条,但是分别在缔约和合同履行两个不同阶段保护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在缔约阶段,肖像权人不得转让肖像权,只能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而不能许可他人制作和公开肖像(《民法典》第1018 条第1 款)。在合同履行阶段,当对“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民法典》第1021 条);在合同存在明确期限时,肖像权人可基于“正当理由”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民法典》第1022条第2 款)。
上述人格保护规则的价值预设即在于精神利益需要绝对保护,以及一般性地将肖像权人定位为合同关系中的弱者。〔39〕参见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6 页。详言之,由于肖像的制作、使用和公开所指向的肖像利益性质不同,所以似有必要限定许可的客体以保护精神利益完满无虞。通过将原本处于私密状态的肖像置于可被不特定且数量不少的人接触到的状态,肖像的公开关涉肖像权人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不宜作为许可的客体。〔40〕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1 页。肖像的制作是指将自然人的外部形象固定在有形或无形载体上的再现行为(《民法典》第1018条第2 款),其关注的是肖像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因而保护的利益宽泛且抽象,甚至可以包括自然人不受监控或偷拍的行动自由和隐私利益。〔41〕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83 页;BGH GRUR 2009, 150 - Karsten Speck; GRUR 1957,494 - Spätheimkehrer; GRUR 1967, 205 - Vor unserer eigenen Tür.因此,肖像的制作也不适宜直接作为许可的客体。在实践中,商业实体与肖像权人经常面临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所以有必要以牺牲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为代价保护肖像权人,实现利益平衡。〔42〕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2 页。肖像权人的特殊解除权即是著例。再如,法院通常认为,除非有明确约定,否则不承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包含了对商业使用肖像的许可,以防止肖像权人因不了解行业规则而错误处分了人格利益。〔43〕参见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京0491 民初20902号民事判决书。
然而,反对上述价值预设的理由更为充分。其一,依据行为所关涉的利益性质“分而治之”的做法,看似可以使肖像权人的精神利益不受许可拘束,但是该理解既不符合人格权一元理论,也难以与生活实践相契合。肖像权人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可分割且相互交融地构成了肖像利益。在典型的肖像商品化案件中,也只是肖像权人的财产利益立于台前而精神利益隐于幕后;〔44〕所谓典型的肖像商品化案件是指使用者以积极和美化的方式,未经同意而商业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Vgl. BGH GRUR 2000, 709 - Marlene Dietrich; BGH NJW 2021, 1311 - Urlaubslotto.而且允许他人商业使用肖像亦可基于肖像权人的精神需求。在实践中,大量的肖像商品化合同均包含肖像的制作和公开,如广告肖像合同、人体模特合同等。〔45〕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2035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 民终17807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永中法民三终字第465 号民事判决书。人为割裂商业实践以寻求不同类型的授权实不可取。其二,肖像权人并不当然处于弱势地位。明星等专业人士普遍具有较高的谈判地位。随着网络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传统的经纪公司不仅要与新出现的多频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MCN)竞争,而且要与自主运营账号的“网红”争夺商业资源,它们在娱乐产业和广告宣传上的垄断优势逐渐被削弱。〔46〕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3 民终984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22)豫1424 民初1743 号民事判决书;崔国斌:《姓名商品化权的侵权认定思路》,载《清华法学》2021 年第1 期,第121 页。与此同时,许多新兴MCN 机构的专业程度和资源优势均较低,经常会因没有明确约定合同履行时间、范围等重要内容而承受法律上的不利益。因此,商业实体相较于肖像权人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显著。
究其根源,既有规则的价值预设产生于对司法裁判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因而偏向于采用原则规定和事后干预对不平等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进行纠偏。然而,为实现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目的,与其预设“资强劳弱”的交易环境而强调合同实质公平的形塑,毋宁通过弹性和柔性的规则保障肖像权人对人格利益自决的控制,并提高其实现个人自治的能力。
(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价值预设与冲突化解
在肖像商品化场景下,对肖像权人和相对人契约自由更为极端的干预可能来自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 条第1 款第1 项和第15 条第1 款)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条例》(GDPR)都允许信息主体随时撤回同意,以终止信息控制者的信息处理活动。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GDPR 都没有在法律协调适用方面作出特别规定,〔47〕德国旧《联邦数据保护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规定了有关肖像权法律的优先适用性,但由于GDPR 没有类似的法律适用条款,其与德国法上肖像权乃至人格权的冲突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且肖像属于个人信息,所以可撤回同意的强制适用可以让肖像权人随时从有期限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解脱”出来,并且无须给出任何理由。换言之,如果认为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在适用上具有优先性,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对肖像权人而言将不再具有拘束力,人格保护规则亦无创设之必要。〔48〕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06 et seq.
可见,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目的一致,均旨在使人格利益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两者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价值预设不同。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场景下,信息主体囿于其专业知识和风险预见能力,难以充分理解信息处理活动对自身的影响以及信息控制者提供的隐私保护水平的高低;〔49〕Vgl. Hans Peter Bull, Sinn und Unsinn des Datenschutzes: Persönlichkeitsrecht und Kommunikationsfreiheit in der digitalen Gesellschaft, 2015, S. 75 ff.而且让信息主体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理解和比较不同信息控制者提供的隐私保护承诺,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作出理性选择既难以实现,也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50〕See Daniel J. Solove, Privacy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onsent Dilemma, 126 Harvard Law Review 1892-1893 (2013).因此,立法者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处分模式限制为可撤回的同意,使信息主体在认识到信息处理的问题后可以即时撤回同意以保护个人信息。可见,可撤回的同意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信息控制者头上以警示其极其不稳定的法律地位。反观在肖像商品化场景中,交易双方的专业水平和风险承担与预见能力大致相当,结构性矛盾也并不突出。更为重要的是,稳定的法律关系亦符合肖像权人和商业实体共同合作、互为成就的利益诉求。
职是之故,不应将“数据家长主义”(Datenpaternalismus)的规制毫无保留和修改地套用至肖像商品化场景中。〔51〕Vgl. Christoph Krönke, Datenpaternalismus, Der Staat 3 (2016), 319.据此,有学者提出通过限制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适用范围,〔52〕参见施鸿鹏:《任意撤回权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与协调》,载《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0 期,第174 页;Malte Engeler, The EDPB’s Guidelines 02/2019 on Art. 6(1)(b) GDPR, Privacy in Germany, 151-152(2019).或是确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规则的优先适用性,〔53〕参见杨芳:《肖像权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冲突与消融》,载《清华法学》2021 年第6 期,第126-127 页;Schantz, in:Simitis et al., Datenschutzrecht, 2019, Art. 6 Rn. 32.排除可撤回的同意在肖像商品化场景中的适用。然而,上述观点未能明确可撤回的同意与许可合同的关系及其适用范围。在前述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案中,平台就主张将隐私保护协议认定为包括公开权的许可使用或转让在内的合同,从而确立信息主体承诺的拘束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学者提出将同意视作肖像权人基于许可使用合同而负担的给付义务,进而肖像权人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随时撤回同意,但在无正当理由时,可能会因怠于履行许可使用合同的给付义务而产生违约责任。〔54〕参见林洹民:《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5 期,第41 页;郑观:《个人信息对价化及其基本制度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2 期,第497-498 页;Riesenhuber, Die Einwilligung des Arbeitnehmers im Datenschutzrecht, Recht der Arbeit (2011), 257, 258.该观点的可商榷之处在于,可撤回的同意应有独立的法律基础和地位。一方面,在生活中大量的照片分享场景中,肖像权人的同意都不具备其愿意受该意思表达拘束的含义。另一方面,对使用许可过于宽泛的认定很可能导致信息主体动辄承担违约责任,这并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设置可撤回同意的本意。〔55〕同上注,郑观文,第498 页。
为给予同意独立的法律地位,有学者主张重新定义同意,认为其包含可撤回的同意和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两个含义:当肖像权人的同意意指后者时,就不能随时撤回同意;而当肖像权人的同意不具备拘束意思时,就可以类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56〕参见程啸:《论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1 期,第52 页;杨立新:《人格权法通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348 页。细究之下,该观点也存在可斟酌之处。其一,肖像权人给予的是可撤回的同意还是使用许可仍有待确认。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肖像商品化过程中发生争议时,肖像权人可否主张其给予的是可撤回的同意而非使用许可,且因该争议属于对使用条件的争议而要求法院采取有利于其的解释。其二,可撤回的同意源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其在民法教义体系上的地位从何而来也有待说明。
“同意”(Einwilligung)指当事人不得就自己同意遭受的损害获得补偿。〔57〕法谚“volenti non fit iniuria”出现在《学说汇纂》(Ulp. D.47.10.1.5)中,所涉及的案例是一个自愿为奴隶的人就不能再主张别人对他的侮辱具有违法性。See Terence Ingman, A History of the Defence of Volenti Non Fit Injuria, 26 Judicial Review 2 (1981).因此,同意一直作为排除行为不法的理由而鲜少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然而,同意之所以能够排除他人行为的违法性,是因为自然人有依其意志处置事务的权利,并且他人的行为是根据其要求实施的。〔58〕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S. 428; Mayer-Maly, Fikentscher & Lübbe-Wolf,Privatautonomie und Selbstverantwortung, in: Lampe (hrsg.), Verantwortlichkeit und Recht - 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89, S. 277.换言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可以通过同意处分利益或者行使权利,同时需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59〕Vgl. Joerden, Drei Ebenen des Denkens über Gerechtigkei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einiger rechtsethischer Regeln und Prinzipien, Das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1988), 307, 314;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3.这也被称为同意的积极含义,〔60〕参见刘召成:《人格权法上同意撤回权的规范表达》,载《法学》2022年第3期,第83页及以下;万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1 期,第177 页。并通过“允诺的阶梯”(die Stufenleiter der Gestattungen)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教义化。〔61〕Vgl.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3 ff.
具体而言,根据权利人的允诺对其自身拘束力的强弱,“允诺的阶梯”理论将其由高至低地排列为“继受让与—设权让与—设定负担合同—可随时撤回的同意”。详言之,“继受让与”(translative Rechtsübertragung)是指使权利人完全丧失权利的转让行为。“设权让与”(konstitutive Rechtsübertragung)是指在权利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只转让使用权、用益物权等从原始权利中派生出的子权利。设定负担合同意味着权利没有发生转移,相对人仅获得了针对权利人的债权。对权利人拘束力最弱的是可撤回的同意(狭义的同意)。〔62〕Vgl.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7-177.可见,允诺即广义的同意,可以涵盖民事主体所有的行权模式。我国《民法典》也在广义的语境下使用“同意”一词。例如,共有人的同意可以实现对共有的不动产的处分(《民法典》第301 条),民事主体通过同意可处分身体权和健康权(《民法典》第1006、1008 条),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可以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生效(《民法典》第145 条第1 款)。
据此,狭义的同意(或称可撤回的同意)也是权利人处分自己利益的方式之一,即权利人向相对人表明其虽然可处分自己的利益,但自己亦得随时撤回同意而使其后续的处分行为转为非法。狭义的同意的可撤回性意味着权利人既不受法律对意思表示撤回的限制,〔63〕例如,患者无须在同意到达医生之前撤回,而是可以随时撤回针对诊疗手段的同意。这同样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同意的定义。也不能与法定解除权混淆。〔64〕例如,欧盟第29 条工作组(数据保护工作组)明确要求,数据主体在撤回同意时无须负担任何赔偿责任,以防止数据主体惮于行使撤回权。See WP 29 Opinion 4/2010 on 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of FEDMA for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Direct Marketing (WP 174) and the Opinion on the Use of Location Data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Value-added Services (WP 115).由是观之,可撤回的同意可以显著增强权利人对相对人行为的控制力,通过塑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法律效果,确保权利人的决定得到实时贯彻。譬如,对亲密行为的同意就是可撤回的同意,而且相对方不能在伴侣撤回同意后要求其赔偿自己的损失,因为可撤回的同意没有为其创造出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相对方对可撤回同意的接受就意味着其接受了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
在肖像使用的场景下,如果肖像权人给出的是可撤回的同意,那么其撤回无需类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亦无须给出正当理由或承担违约责任。与之相反,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成立基础必须是肖像权人具有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可撤回的同意虽然能使相对人的行为合法化,但其特性排除了成立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民法典》为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设立的人格保护规则不能适用于可撤回的同意,因为肖像权人不能既主张自己订立了合同,又认为自己的同意不具有拘束力。诚然,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如果相对人认可,可撤回的同意也可作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础,但是这与肖像商品化的价值预设和追求的稳定法律关系不相符。换言之,可撤回的同意虽然从法律上强化了肖像权人对人格权益的控制,但很可能“迫使”肖像权人通过让渡更多的核心利益来补偿相对人失去的交易安全。基于上述考虑,除非存在明确的约定,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础应排除可撤回的同意。
立基于“允诺的阶梯”理论,本文建议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中可撤回的同意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进行体系解释,将可撤回的同意作为肖像权人处分肖像权益时的“安全网”:当作为合同主义务的肖像制作、使用和公开等行为为履行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所必需时,该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即为信息控制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 条第1 款第2 项),可撤回的同意不能适用;在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肖像处理活动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必要性要求时,对超出必要范围的肖像处理活动适用可撤回的同意,允许肖像权人随时撤回同意以保护其对个人信息的强控制力。〔65〕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40 et seq.; Andreas Sattler,Personenbezogene Daten als Leistungsgegenstand, JuristenZeitung (2017), 1036, 1043.值得注意的是,仅凭在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有所约定,并不能证明具体的肖像处理活动是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而应当遵循信息处理的必要原则,审查具体的肖像使用行为与实现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所期达成目的之间的相关性和必要性,确保肖像权人仅在必要范围内受其使用许可拘束,而此处的协调性可以通过“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来实现。〔66〕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42.
三、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缔约阶段的人格保护规则及其调整
为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可以提前介入当事人的缔约阶段,通过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提出弹性要求,使交易双方在合同订立之时,就充分知晓肖像权人愿意以何种方式让渡何种肖像利益以实现何种人格发展目的。与此同时,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还应明确肖像权人不能让渡的人格核心利益,即对肖像等人格标识的自决权,并通过缺省规则丰富肖像权人管理其人格利益的方式,保障肖像权人在授权后仍然可以施加对人格利益的持续控制,而不是只能在“忍无可忍”后解除合同。
(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成立的必要之点
《民法典》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成立要件并无特别规定。《广告法》虽有广告主须获得肖像权人书面同意的规定,〔67〕《广告法》第33 条规定:“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或者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书面同意。”但因其旨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第1 条),所以书面性作为对广告主和广告发布者施加的合规义务,不应成为民法上的效力性强制规定。〔68〕参见王绍喜:《〈民法典〉时代肖像权保护解释论》,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11 期,第30 页。由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属诺成合同,而肖像商品化往往涉及拍摄、(广告)制作、宣传等一系列商业活动,并且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此双方经常就是否存在商业许可使用发生争议。对此,法院的判决也迥然不同:有法院认为肖像权人参与选美比赛即是对后续商品化的许可;有法院则主张接受“宣传大使”证书不能使企业对肖像的商业利用合法化,肖像权人对广告制品的称赞也不表示其给予肖像使用许可。〔6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57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湖民终字第458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号民事判决书。
这些实践难点皆源于人们尚未就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成立的必要之点达成共识。通说认为,合同的成立不需要当事人就《民法典》第470 条列举的所有合同内容达成合意,仅需在必要之点上达成一致即可,并且应当根据合同的类型确定该类合同的必要之点,以实现私法自治。〔70〕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3 页。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作为肖像权人愿意以何种方式让渡何种肖像利益以达成何种人格发展目标的意思表示,肖像的使用范围、许可类型和对价构成其成立的必要之点,而其中又以对价最为重要。
首先,对价关系(quid pro quo)作为契约最核心的要素,能够说明肖像权人为获得对价,愿意以一种受拘束的方式处分肖像利益。〔71〕See Jed Lewinsohn, Paid on Both Sides: Quid Pro Quo Exchange and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129 Yale Law Journal 3 (2020).有观点将肖像权人的职业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职业模特因了解行业规则而接受拍摄邀约即意味着许可合同成立。〔72〕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20354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潭中民一终字第46 号民事判决书;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页;张红:《民法典之肖像权立法论》,载《学术研究》2019 年第9 期,第67 页。然而,以商业授权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专业模特应更注重授权内容,不会含糊其辞地放弃其“生存利益”,何况以职业为判断基准的观点已稍显过时。在一起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也认同“童星”原告及其母亲的观点,认为一审法院将原告同意拍摄认定为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成立存在错误,因为双方尚未就费用达成一致。〔73〕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 民终4354 号民事判决书。
其次,对价的高低也可以帮助判断肖像许可使用的范围。例如,国际明星受邀参加宣传活动和接受小礼品,当然不能被认定为给予了相对方代言许可,〔7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57 号民事判决书。但公司可以将明星的照片挂在宣传栏里。〔75〕Vgl. BGH GRUR 1992, 557 ff. - Joachim Fuchsberger.又如,100 元的报酬不能构成将照片印在2 万张音乐节门票和数个巨幅展板上的授权,但可以使经纪公司的宣传册合法化。〔76〕参见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号民事判决书。对价不等同于报酬,而是包括任何财产性利益。以刚入行的模特常与专业摄影师签订的“免费约拍”合同为例,前者获得后者的专业指导和免费提供的场地、服装,应当认为其许可包含允许摄影师使用前者肖像宣传自己的工作室,否则,后者无法利用其作品补偿自己付出的时间和劳动,这种互惠的商业实践将不会再存续,初出茅庐的模特也更难以发展事业。〔77〕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 民终16859 号民事判决书;LG Frankfurt am Main, Urteil vom 30.5.2017 - 2-03 O 134/16 - Time-for-Print-Vertrags.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相对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肖像权人为什么愿意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允许其商业性使用肖像。〔78〕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申4015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京0491 民初20902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1)川2022 民初65 号民事判决书。
最后,对价的内容也与许可类型紧密相关。在仅创设负担义务的普通许可模式中,相对人支付的对价往往仅为金钱或其他金钱性给付,例如拍摄和底片服务。而获得排他许可或独家许可的相对人通常需要支付的对价更为复杂。具体而言,艺人为从庞杂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注于演艺工作,会通过授予相对人(通常是经纪公司)排他许可或独家许可的方式,赋予被许可人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乃至对抗肖像权人自己商业使用肖像的权利。与之相应,相对人需要履行经营管理艺人形象、规划演艺事业和维护合法权益等义务。可以说,商业使用肖像的对价内容越丰富,肖像权人与相对人的利益关系就越复杂,所选择的许可类型也可能呈现对肖像权人更强的拘束力。
由此,通过对相对人支付的对价进行综合考量,可以判断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是否成立,即肖像权人是否以一种受拘束的方式处分了自己的肖像利益。这相当于在肖像商品化的场景下对一般合同成立要件进行了简化适用,以顺应日益频繁和“生活化”的肖像商业使用之发展趋势。尽管这可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认定存在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不会影响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其更加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形象。一方面,这可以促使相对人积极主动提供报酬,让肖像权人了解自己的肖像在市场中的价值,并使其参与肖像使用的谈判而提升理性自治的能力。另一方面,无期限合同中的随时解除权实际上赋予肖像权人随时反悔的权利。在相对人未明确期限利益但给予肖像权人报酬时,例如,餐厅要求顾客在社交媒体上发送用餐照片,推广、宣传餐厅以获取优惠,应当认为双方之间成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肖像权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且其在履行合同义务之后要求解除的,餐厅不能要求肖像权人返还优惠。
(二)“拘束性权利转让”许可的缺省规则
如前所述,排他性或独占性的肖像许可使用在商业实践中屡见不鲜。虽然有学者持禁止肖像权人给予此类许可的见解,因为设权让与模式不仅会使肖像权人与创设的子权利相分离,而且会减损肖像权人因人格保护规则而享有的保护水平;〔79〕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7 页;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1 页。但是排他性或独占性的肖像许可使用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它可以通过为相对人提供更为独立和稳定的法律地位,鼓励其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实现权利人的自主意愿。作者与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关系即为著例,前者需要后者投入大量的出版和宣传资源以实现自己“名利双收”的愿望,而出版社也需要作者提供相对完整和长期的授权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为解决作为一元权利的著作权不能与著作权人分离,且需要特别保护其中人格利益的问题,德国学者为著作权许可发明了“拘束性权利转让”(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模式,以实现著作权人对转让的使用权的控制。根据“拘束性权利转让”模式,被转让的子权利在内容、时间和空间上都受权利人目的的拘束,而且与保留在权利人手中的母权利紧密相连并受后者的影响和控制,因而权利人在有充分理由(正当理由)时可以随时收回其转让的子权利,而且子权利在其所保护的利益丧失后也自然回归至母权利的主体手中。〔80〕Vgl. Forkel, 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en, 1970, § 6 VII, S. 44 ff.
由此,可以考虑在同为一元权利的肖像权许可使用类型中引入“拘束性权利转让”模式,即在肖像权人给予相对人排他性许可或独家许可时,被许可人虽然获得了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但是其所获得的权利范围须受肖像权人目的的拘束,而且受始终保留在肖像权人手中的肖像权的影响和控制。〔81〕Vgl. Forkel, Lizenzen an Persönlichkeitsrechten durch 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988), 491, 494;黄芬:《商品化人格权的定限转让》,载《河北法学》2017 年第1 期,第67 页。“拘束性权利转让”不仅可以顺应肖像商品化实践需求,而且能在扩大肖像权人自治空间的前提下有效保护其人格利益。需要注意的是,“拘束性权利转让”的前提是人格利益的客体化。从目前来看,它只适用于肖像、名称和姓名等已经被普遍承认的、作为商品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事主体分离的人格标识。
设权让与类许可合同对肖像权人的拘束力极强,且合同履行时间一般较长,所以有必要在缔约阶段就引入人格保护规则,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为提示肖像权人审慎处分权利,实现理性自治;二是为在一段较长的周期内使肖像利益仍尽可能地保留于肖像权人自我决定的范畴;三是为合理平衡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从提示肖像权人权利变动的范围和效果角度出发,可以考虑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中将合同成立与合同内容、形式相关联的规定,要求设权让与类许可合同应为要式合同,强制要求该合同列明许可使用人格标识的种类以及使用权的可转让性(第27 条),并且要求再转让须获得肖像权人的同意。由此不难看出,书面合同实际上赋予肖像权人在签订肖像许可使用书面合同前的反悔权,旨在督促其谨慎、严肃地对待权利。当然,将设权让与类许可合同规定为要式合同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口头协议无效,而是对后者适用对肖像权人拘束力更弱的处分模式,即债权合同,这意味着此时相对人不得主张该许可的对世效力,而只能获得债权请求权。
在恢复肖像权人的自治地位层面,可以参考德国有关肖像商品化合同的司法实践,为肖像权人创设一些合同权利以丰富其管理和控制肖像利益的方法和手段,用以对抗经纪公司因过于注重商业和短期利益而作出与艺人价值观抵牾或违背其身份认同的商业决策。〔82〕Vgl. Götting/Schertz/Seitz, Handbuch Persönlichkeitsrecht, 2019, § 38 Rn. 44 f.; Pfaff/Osterrieth, Lizenzverträge:Formularkommentar, 2018, S. 407 ff.在实践中,因投资的阶段性和手中艺人资源的丰富性,经纪公司很容易忽视单个肖像权人的人格发展和长期利益,所以授予排他性许可的肖像权人急需对自身形象规划的最终同意权,以防止“营销翻车”“偶像失格”的情况出现。〔83〕例如,某对明星夫妻分别代言不同品牌的奶粉,并表示他们的孩子只喝自己所代言品牌的奶粉。这种明显虚假的产品代言会严重损害两位名人的可信度。参见《郎朗和妻子吉娜代言不同品牌奶粉,网友:他家孩子到底喝哪个》,https://www.sohu.com/a/477418700_99930840,2023 年5 月20 日访问。除此之外,关于账目信息的知情权对于长期合同而言也较为重要,因为它既可以保证肖像权人随着自身形象价值的提升而获得相应的合理收益,还可以在违约纠纷发生时有效抗辩相对方索取畸高的违约金。〔84〕Vgl. Schertz, Merchandising: Rechtsgrundlagen und Rechtspraxis, 1997, Rn. 405.
总体而言,相对于事后的解释规则和解除权,事前的形式要求和权利保留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肖像权人的声誉。一方面,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合同可以证明被许可人享有肖像使用权或转授权的权利,方便其经营管理和后续授权;在发生争议时,书面合同还能够帮助法院还原双方的谈判过程和目的,使其根据合同目的解释双方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解除权的行使无疑会破坏交易相对方的市场预期和双方的信赖关系,肖像权人在市场中的声誉通常也会被损害。相反,肖像权人的最终同意权和对账目信息的知情权均有助于使相对方的使用行为服务于肖像权人的人格发展目标,不必以两败俱伤的代价保护其人格利益。
四、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履行阶段的人格保护规则及其调整
相较于合同缔约阶段的柔性和弹性规则,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履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虽然能够有效保障肖像权人对人格利益自决的控制,但因属于事后规则而极易损害交易安全。因此,仅应在必要时对肖像权人的自主意愿予以限制和调整,以实现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本旨。同时,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也需要与合同法的一般规则相协调。
(一)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
针对《民法典》第1021 条规定的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规则,有学者主张排除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以加强人格权益的保护,〔85〕参见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2 页。也有学者提出仅在肖像权人与相对人地位显著不平等时适用该条规定,〔86〕参见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页;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241-242 页;张红:《民法典之肖像权立法论》,载《学术研究》2019 年第9 期,第67 页。还有学者针对具体争议作出回应。〔87〕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297 页。可见,目前学界不仅对该条的立法意旨认识不同,而且在有利于肖像权人的判断标准上也存在分歧。这导致实践中对争议条款的解释,时而以某一类人的价值偏好为标准,片面认为对精神利益或财产利益的保护有利于肖像权人;时而以肖像权人的事后主张解释合同条款,忽视其在订立合同之时的意思表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亦是对肖像权人在合同订立之时自主决定的否定。尤为重要的是,《民法典》第1021 条虽然仅要求对“肖像使用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但其涵盖范围可谓相当宽泛,包括使用类型、内容、时间、对价和效果等,甚至赔偿责任、竞业禁止条款亦可被纳入其中。因此,有必要明确和统一“有利于肖像权人”的判断标准,以形成适用于所有“肖像使用条款”的解释标准;否则,对肖像权人的保护极易导致“赢了战斗,输了战争”的结果。
依据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本旨,对合同的解释应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这意味着对发生争议的“肖像使用条款”的解释,既要以具体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目的为基础,确保肖像权人能够实现当时处分肖像利益的具体目的;又要将肖像权人处分的人格利益限制在实现合同目的绝对必要的范围内,以保障对肖像等人格标识的自决权尽可能地保留在肖像权人的手中。
具言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是肖像权人实现个人自治并确立社会身份的工具,其目的具有自主性、多元性和多样性。因此,首先需要根据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确定发生争议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目的,具体的方法包括分析合同内容,考察合同订立的背景以及行业内和双方的交易习惯等因素。〔88〕参见谢鸿飞:《〈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 年第6 期,第26-27 页。需要说明的是,合同的具体目的是指当事人双方追求的一致的私法效果,即肖像权人愿受义务拘束而希望达成的具体的人格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对发生争议的肖像使用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认定肖像权人仅在实现合同目的绝对必要的范围内处分了人格利益,除非其明确地表示允许相对人以超出合同目的的方式使用肖像。〔89〕Vgl. OLG Köln ZUM 2014, 416; OLG Köln AfP 1999, 377; OLG Hamburg ZUM 1996, 789, 790.
由此可见,“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应当是对合同一般解释规则的补充而非替代,〔90〕Vgl. Christian Donle, Die Bedeutung des § 31 Abs. 5 UrhG für das Urhebervertragsrecht, 1993, S. 51; Ansgar Ohly, in: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6. Aufl., 2020, § 31 Nr. 52.而且该解释路径有利于肖像权人。其一,它尽可能地将肖像利益保留在肖像权人的手中。其二,在发生争议时,它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除非后者能够证明争议内容为实现合同目的所必需,或是肖像权人给予了明确授权,否则一律认为肖像权人未授予该使用许可。
通常而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双方都因专业性、长时间的合作关系等不会对合同目的进行细致说明。因此,根据合同内容和双方的交易动机判断合同的目的尤为关键。首先,如果肖像权人通过肖像商品化获得财产收益的动机非常强(如专业模特),而签订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却没有约定报酬或者报酬极少,那么在有争议时就不应当认为该合同包含了肖像商品化,因为这样的授权条件无法实现肖像权人的目的,除非相对人能够证明肖像权人为了专业指导或是曝光机会免费授予了商业许可。其次,当肖像权人与经纪公司就授权的排他性存在争议时,根据“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规则,经纪公司(被授权人)须主动证明排他性的授权方式、授权范围和时间为实现合同目的所必需。换言之,仅在权利人想要让相对人获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的目的非常明确时,其才可以选择以“拘束性权利转让”的方式处分其人格利益。譬如,艺人(肖像权人)明确想要从繁杂、琐碎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更专注于演艺工作;经纪公司为防止初出茅庐的艺人遭遇不公平待遇,需要获得转授权许可,以代表艺人与广告公司等其他商业实体谈判。与之相反,动辄长达十几年的许可期限,乃至对肖像的低俗呈现等,都明显超出了实现合同目的的必要范围,甚至无助于肖像权人实现人格发展的具体目标,因此当属未获得肖像权人的许可。
(二)肖像权人基于“正当理由”的特殊解除权
针对《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有学者主张宽泛解释解除的“正当理由”,允许肖像权人为维护特定形象和保持外界良好评价而随时行使解除权。〔91〕参见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3 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0 页。也有学者要求严格解释“正当理由”以防止其破坏合同信守原则,主张肖像权人(或其亲属)仅在受许可人的违法行为致肖像权人死亡或肖像权人遭受生命威胁时,方可解除合同。〔92〕参见郭少飞:《新型人格财产权确立及制度构造》,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第52 页;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1 页。还有学者提出对《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和规制法定解除权的第563 条进行体系解释,将“正当理由”理解为合同生效后发生的“重大事由”,主张在个案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判断该变化是否导致履行合同义务对肖像权人而言已无期待可能性。〔93〕参见王洪亮:《民法典中解除规则的变革及其解释》,载《法学论坛》2020 年第4 期,第27 页;刘召成:《人格商业化利用权的教义学构造》,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3 期,第132 页。另有学者借鉴比较法经验对“正当理由”进行类型化,包括可以源于肖像权人自身的重大事由,譬如信仰和观念的重大改变、雇佣关系的结束,以及诸如相对人的重大丑闻、对肖像权人形象的丑化等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94〕参见杨芳:《〈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有期限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评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第44 页。
综合比较后可以发现,严格解释虽然有助于纠正宽泛解释的过度家长主义保护倾向,但将人格利益限制在人身利益的范围内会显著减损法定解除权的保护效果,而且难以与《民法典》第990 条对多元化人格权益的广泛保护相协调。在实践中,我国法院早已通过创设“酌定解除”,允许艺人以其演艺才能和活动受到严重制约为由解除合同。〔95〕参见刘承韪:《论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4 期,第132 页及以下。肖像商品化合同虽不及演艺经纪合同综合性强,但其对肖像权人的形象以及人格发展的拘束不亚于后者,因此不宜过分限制“正当理由”的解释而造成对两类合同的“保护差”。体系解释的优点在于回归解除权的教义基础,这有利于实现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但有狭隘理解“正当理由”构成类型的可能性,有弱化人格权益保护之嫌。此外,如果完全依据个案的利益衡量,那么法院不仅要将合同履行时间、权利人的年龄纳入考虑范围,还需要考量经纪公司在组织培训、营销管理以及监管评估上所投入的大量资源和承担的商业风险。这很可能导致肖像权人依据相同的人格限制理由而主张特殊解除权的结果不尽相同。一方面,这似乎未能体现《民法典》以人的主体性和优先性为基础的理念;另一方面,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可以通过酌定肖像权人的损失赔偿金额来实现,无须否定肖像权人的特殊解除权。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主张将解除的“正当理由”置于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治的整体脉络下进行解释。一方面,肖像商品化作为肖像权人实现社会身份和发展事业的重要方式,在其结果与肖像权人对自己所展示形象的预设发生冲突时,必然会对肖像权人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前景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为维护肖像权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可以相对宽泛地理解正当理由的构成类型,允许肖像权人基于自身或他人的原因,以及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从具有拘束力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之前具有拘束力的许可是由肖像权人自主决定的,所以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对其个人自治的否定。于是,肖像权人必须证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护规则为什么应当允许其推翻之前作出的针对人格利益的拘束性决定,以实现法律保护个人自决的目的。〔96〕Vgl. BAG, Urteil vom 11.12.2014 - 8 AZR 1010/13.质言之,肖像权人“出尔反尔”的理由必须要使法院相信如果不允许肖像权人以相反的方式行使其自决权,法律将人格利益自决权保留在肖像权人手中的目的就会落空。
举例而言,在德国有女明星曾试图通过主张解除权阻止杂志社再度刊登其多年前拍摄并许可公开的性感照片。然而,德国法院虽承认肖像权人信仰和观念的重大改变可以构成解约的正当理由,但是不认为法律有必要通过允许解除合同的方式保护其后续塑造的相反“人设”。一方面,该女星订立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决定是自觉、自愿的,其当时能充分了解该决定的含义和效果,并且寄希望于通过性感照片开拓事业。另一方面,对人格利益的自决并非赋予每个人按照意愿删除其过往经历的权利,更何况早年的性感照片并不妨碍其后续改变和发展新的“人设”。肖像权人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照片的再度出版会严重影响乃至压制其人格的自由发展。〔97〕Vgl. OLG München, NJW-RR 1990, 999 - Wirtin; LG Köln, AfP 1996, 186 - Model in Playboy, 188.
为缓解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治之间的矛盾,平衡人格权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维护,本文主张在宽泛理解肖像权人解除的正当理由构成类型的前提下,严格审查以此为理由解除合同的必要性,即为维护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是否必须否定其之前的自我决定。由此,《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中的“正当理由”应当指在合同签订后出现的、具体而紧迫的、严重损害人格利益的事由。例如,如果肖像权人只出现在其受雇公司广告的背景中,并且在离职后的长时间内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在对相对人具体的合同履行利益与肖像权人受到的一般抽象风险的衡量中,法院需要偏向前者。〔98〕Vgl. BAG, Urteil vom 11.12.2014 - 8 AZR 1010/13.此外,《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对解除合同理由正当性的要求体现了利益平衡的属性,即法院需要在肖像权人与相对人的对抗性利益之间权衡,以确保在该具体情形下排除肖像权人的违约责任具有客观正当性。
五、结论
作为规制肖像商品化的制度创新与其他人格权益处分的准用规范,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规则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格权保护理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反映了《民法典》对实践经验的制度化。立基于人格权一元理论,立法者以对个人自治一定程度的否定来扩充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选项,使自然人在充分享受物质与技术发展福利的同时,实现理性自治和人格多样化发展。质言之,作为个人自治的终极目的,人格尊严内在于人格权利的积极利用之中,而人格保护规则正是实现该价值选择的制度保障。
基于人格权一元理论,人格保护规则不应建立在精神利益需要特别保护或是一般性地将肖像权人视为弱者的基础上,而应当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在具体设置人格保护规则时,应尽量避免对合同法律效果的直接干预,通过事前规则和柔性规则,发掘和实现肖像权人的自主意愿,丰富肖像权人管理肖像利益和控制相对方行为的方法,并尽量通过学理发展和教义学构造使其与合同法等民法教义相协调。
为厘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中可撤回的同意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适用范围,本文主张借助“允诺的阶梯”理论对两者进行体系解释,在信息主体明确以拘束性方式处分其个人信息时,应优先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同时将可撤回的同意作为信息主体处分个人信息的“安全网”,即在合同约定的肖像使用范围超出了实现合同目的所必需的范围时,默认当事人可随时撤回关于这部分信息处理的同意。同时,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成立基础必须是肖像权人具有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可撤回的同意虽然也可作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础,但因其既不能实现肖像权人的真实意思,又不能给其带来实质利益,所以除非存在明确的约定,否则不应认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础是可撤回的同意。
为使肖像等人格标识尽可能地保留于主体自我决定的范畴,并仅在必要时对肖像权人的自主意愿予以限制和调整,在梳理比较法经验、反思本土已有立法和解释架构的基础上,本文建议区分缔约和合同履行两个不同阶段,运用法教义学方式充实和调整既有规则。具体而言,在缔约阶段,应将肖像许可使用范围、许可类型和对价作为合同成立的必要之点,以对价关系作为考察的核心,解释和判断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引入“拘束性权利转让”模式为排他性许可设置必要的形式和内容要求以及缺省规则,保护肖像权人对人格利益的控制和自决能力。在合同履行阶段,对争议条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即意味着在发生争议时肖像权人仅在实现合同目的的绝对必要范围内处分了肖像利益,并将解除的“正当理由”置于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治的整体脉络下进行解释。在宽泛理解解除的“正当理由”构成类型的背景下,应严格审查其必要性,并将其限定在合同签订后出现的、具体而紧迫的、严重损害人格利益的事由上。通过保障肖像权人始终控制对人格利益的自决权,实现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护规则的制度功能,即合理解决个人自治和人格尊严的内在冲突,并平衡人格权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