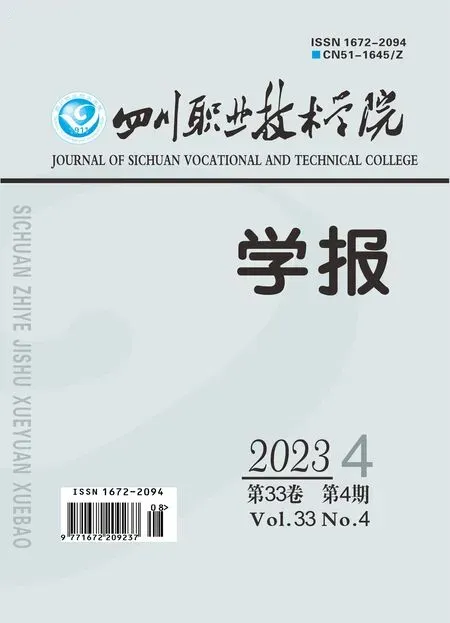克里斯塔·沃尔夫《卡珊德拉》的女性乌托邦书写
南 方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托马斯·莫尔擘画的“乌有之乡”扩展了人们对理想国度的文学想象空间,“乌托邦”从此成为洞天福地的代名词。“乌托邦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而这种精神冲动正是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1],其内蕴的反抗精神和对二元对立的批判正契合女性主义对超越对立的和谐性别秩序的追求,女性主义思想与乌托邦精神的内核存在高度同构性。在承继乌托邦小说深刻批判性的基础上,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关注女性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以对乌托邦的超越性追求观照现实生活。
著名战后德语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 1929-2011)的小说《卡珊德拉》(Kassandra, 1983)表现出明显的乌托邦思想,她在独立于特洛伊战场的斯卡曼德河畔为逃离战争的女性构筑了诗意栖居的异度空间:“伊达山前那片闪闪发光的平原,还有那天然港口的海湾,这是尘世间唯一可设想的好地方。”[2]43卡珊德拉在此找到了自我意识与超越阶级、民族和性别对立的真实生活,在对特洛伊战争的神话重构叙事中增添了女性视角的反战话语。在工业文明危机与战后文化废墟上升起的女性乌托邦为陷入困境的现代人建构出和谐生活的图景,为解救冷战期间核军备竞赛造成的战争威胁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系,更充分挖掘了乌托邦精神所天然具有的生态主义思想与反战内涵,竭力在反思与审视中为当下世界的弊病提出疗救的可能性。小说因对女性身份认同危机的深刻思考及其神话重构叙事策略广受关注,但对其乌托邦书写的研究尚不充分,从思想来源、文本表现与意义蕴含三方面探究《卡珊德拉》的女性乌托邦思想,对战后德语文学、乌托邦文学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均有参考意义。
一、思想来源:萌发在文学传统与危机现实的交汇点上
“乌托邦精神是女性主义的根本精神”[3],对女性乌托邦的探索是乌托邦精神与女性主义碰撞融合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现代文学中女性乌托邦书写的思想来源。沃尔夫女性乌托邦思想的来路脉络清晰,在乌托邦思想传统的奠基之上,她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女性思想的浸润,在时代环境中屡遭冷遇却仍怀抱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美学与核威胁的时代环境交汇在希腊女性的命运悲剧中,造就了沃尔夫独特的女性乌托邦思想。
首先,德国文化素有乌托邦思想传统,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为沃尔夫廓清了乌托邦思想的基本理路。不仅席勒认为古典主义美学能够使人到达审美乌托邦,歌德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愿景也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以色列国父西奥多·赫茨尔撰写《犹太国》(Der Judenstaat, 1896)表达对自由家园的渴望,20世纪的科幻小说更拓展了乌托邦想象的边界,保罗·歇尔巴特在《列萨本迪欧》(Lesabéndio, 1913)的星际乌托邦中思考科技、美学与艺术三者的关系,德布林《山、海和巨人》(Berge Meere und Giganten, 1924)在对虚构世界的讽刺中批判技术文明时代的种种荒谬。在这些文化潮流的推动之外,沃尔夫直接见教于主张“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布洛赫[4],接纳了“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的观点,通往自我的内在历程开始于当下的黑暗,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成为理想生活的灯塔,“希望将给我们带来那照亮当下的黑暗的乌托邦之光”[5]。沃尔夫对内在精神的深度也有天然的追求,在乌托邦中探索现实世界以外的另一个向度,这种乌托邦思想在文本中表现为伊达山的洞穴,它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在对当下的否定中表达对未来的期待。
其次,浪漫主义女性思想与女性空想乌托邦想象为沃尔夫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资源。早期浪漫主义者认为女性具有除旧布新的力量,因此将女性视为浪漫主义诗学的化身,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消解界限的浪漫主义哲学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可能性,“浪漫主义女性理想既是‘对这个被具体化了的世界进行美学反抗’,又是对男权传统和现实市民社会的反抗。”[6]卡罗琳娜·贡特罗德追求真实性与创作的独立个性,关注女性自我实现的过程,贝蒂娜·封·阿尼姆构想的“悬浮宗教”更富乌托邦精神,“希望人类从现实的束缚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进入自由澄澈的世界”[7],沃尔夫的女性乌托邦思想直接承继了浪漫主义者的女性空想乌托邦,相似的处境更使她们产生了跨越时代的共鸣,历史与现实在斯卡曼德河畔交错,在写作中寻找女性共同的母亲。
再次,德语文学以“矿山”喻象表现灵魂深度的传统为沃尔夫笔下的卡珊德拉提供了追寻自我的勇气与乌托邦的“洞穴”形式。德国学者在地理学的领先地位及矿业学院对采矿业的科学研究使生机勃勃的“矿山”成为备受浪漫派文学家青睐的母题,灵魂与被浪漫化的矿山相连,为乌托邦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喻象资源。其一,由矿山题材拓出的表现灵魂震动的“内在”(Innen)以及进一步形成的“深度”(Tiefe)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它们朝向灵魂内部求问,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在体验,指向“不可穷尽的、不可贴近的”[8],特奥多·茨尔科夫斯基在《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制度》(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1990)中将“灵魂的图像”与“矿山和洞穴”之间的关联固定下来,认为人类开采洞穴般的矿山正如探索灵魂和内在体验,使得“深度”这个晦暗不明的浪漫概念有了更具象的空间化表达,这些从浪漫派传统沿袭而来的对灵魂内在深度的追求使沃尔夫和她笔下的卡珊德拉有了寻找自己真实声音的勇气;其二,由于洞穴也与女性文学中常见的监禁题材和子宫隐喻相连,因此其象征的毁灭性力量更为女性乌托邦的构建提供了极恰切的外在形式,卡珊德拉来到洞穴乌托邦之前被囚的阁楼和离开后被关押的英雄墓都是洞穴的变形,“我不得不继续装疯卖傻。那黑魆魆的洞穴之口在不断地一张一闭,把我吐出来,吸进去,又吐出来,又吸进去,我要动弹一下小指头都很困难,我还从未有过这样费劲的感觉。”[2]82当她想要寻找帕里斯被遗弃的真相时也只能看到充满黑暗、暴力与恐惧的洞穴:“我来到的地方,那儿根本没有门,只见到那洞穴似的住所前面挂着兽皮。”[2]61“矿山”与“洞穴”既开放又封闭的空间特征使其生成了异质空间的意义,怀疑、批判并冲击着在充斥暴力与罪恶的现实空间中占绝对地位的父权逻辑与秩序。
最后,冷战造成的生态危机引发了沃尔夫对异度空间的渴望。作为民主德国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沃尔夫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里拥抱社会主义思想,期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解放,但1976年的比尔曼被驱逐事件使她对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路径产生了怀疑,幻灭的现实迫使她在乌托邦中寻求理想国度的慰藉,其后发表的《茫然无处》(Kein Ort. Nirgends, 1979)的题名就是对“乌托邦”的希腊文“ou topos”的转述,作品借诗人贡德罗达与剧作家克莱斯特之口,谈论对艺术创作与时代的见解,认为人类为法国大革命以降的科技进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吁请人们警惕战争的威胁,作者自述“希望未来的现实世界是没有原子弹威胁的世界”[2]193,沃尔夫的写作典型地体现出了女性主义作家常有的“对拘禁状态的一种着迷的想象,这一想象透露出女性艺术家因令人窒息的无奈选择和创造它们的文化而被逼堕入陷阱、变得病态的具体形态。”[9]83就像《卡珊德拉》中独立于特洛伊战场的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在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不确定与危机感中,对女性乌托邦的怀想满足并安慰了由不安现实引发的心理防御机制。
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所体现的女性乌托邦思想不仅体现出德语文学与文化的乌托邦思想脉络,也闪耀着浪漫主义女性思想的光芒,在此二者提供的生长土壤之上,沃尔夫还经历了战后反思文学的洗礼,冷战带来的生态危机与她深厚的文学传统积淀交汇,催促她将渴望和平的反战力量融汇在女性乌托邦的批判精神中,从人自身出发探索感性世界与深层心理,由此构造出了富有意味的女性乌托邦景观。
二、文本表现:在盼望和谐的反英雄叙事中实践“主观真实性”
通过对荷马史诗原始故事的反英雄叙事改写与女性主义重构,沃尔夫在各阶级、种族、国别与性别和谐相处的洞穴社群图景中具象化了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设想,以意识流手法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从卡珊德拉的视角重述被规训的处境,在对经典叙事文本的女性主义重构中实践了自己“主观真实性”的创作主张,在对语言、话语、文本与世界之关系的质疑与诘问中探寻真正的自我。
首先,女性乌托邦在反英雄叙事中表现废除等级制的反阶级特征。作为父权社会之“他者”的女性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只是史诗宏大叙事中可有可无的存在,赋予她们智慧与美貌的意义也只在于衬托男性英雄的勇敢和伟大,国王普里阿摩斯以非正当手段获得权威,为个人私欲将民众拖入战争,用欺骗手段维护统治,战争英雄阿基琉斯为了尊严玷辱彭忒西勒亚,英雄叙事所代表的父权制社会仍将延续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因此沃尔夫通过刻画英雄的反面解构史诗中的英雄形象,使目睹了权力罪恶的卡珊德拉为脱离英雄叙事而拒绝了埃涅阿斯的求爱,因为“面对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我们无计可施”[2]190。在来到伊达山腰上这个主张和谐与平等的女性乌托邦之前,卡珊德拉生活的皇宫等级森严,强调君臣、主仆与男女等对立身份之间统治支配的权力关系,而在伊达山坡上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中,卡珊德拉在臣子与女性身份下所遭受的痛苦都不复存在,因为“天高皇帝远,城堡管不到这里”[2]181,在平等的社群关系中失去了贵族身份的卡珊德拉终于感受到了作为自己本身存在的自由:“没有人呵护我,然而也没有人强迫我。”[2]168这是一个有着明显母性特征的社会,歌舞和艺术构成了斯卡曼德洞穴社会的核心,完全的爱照亮了生活的黑暗,斯卡曼德洞穴像女性乌托邦在特洛伊的使馆,“在城的周围则是别有天地,可说是一个相反的世界,比之用石块建造的宫殿和城池,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那里的庄稼生长茂盛,人民生活富裕,无忧无虑,仿佛那个世界并不需要王宫,仿佛他们远离王宫之外”[2]65,与以希腊社会为代表的父系秩序下的血腥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女性乌托邦主张群体价值观,着重表现群体意识,个体的自我认知也不再因性别决定。在来到洞穴社区以前,卡珊德拉已经决定为免于在成年后被挑选而“不惜任何代价要成为一名女祭司”[2]21,主动选择成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女性,然而,她虽然拥有准确的预言天赋却不被允许成为祭司,在屡次发现了男性祭司的不称职后,卡珊德拉开始质疑祭司是否应被限制为男性的职业,并着手为成为女祭司而努力,这是卡珊德拉自我意识成长的最初一步。费尔斯通在吸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的基础上提出“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认为性别的自然生物差异直接导致了作为阶级根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因此成为等级制的范例,伊达山洞穴中的女性乌托邦彻底取消了社会分工的性别因素,已经接近费尔斯通设想的“控制论共产主义”社会模型,来到洞穴中的女性彼此谈论、学习、跳舞并尝试书写自己的历史。群体价值观与女性的群体意识在这个洞穴社群中得到充分彰显,这里不仅有从特洛伊赶来避难的百姓,有赫卡柏、阿里斯柏和卡珊德拉这样的贵族女性,也有玛尔佩莎、基拉和来自希腊营地的女奴,还有安基塞斯和埃涅阿斯等在战争中饱受创伤的男人,乌托邦中的女性抗拒父权秩序但并未排斥男性,这些被父权中心社会的价值体系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洞穴中形成了和谐的集合体。虽亦将爱好和平的自然天性作为构建女性乌托邦的逻辑起点,但融合式乌托邦避免了对“女性气质”的过分强调,因此未落入分离主义女性主义常面临的本质主义陷阱,也脱离了女性乌托邦易走向停滞封闭的窠臼。
最后,卡珊德拉对自由与女性乌托邦的追寻是沃尔夫追求“主观真实性”的文本表现。沃尔夫认为作品的创作核心在于“主观真实性”,意即作者不应满足于简单地反映客观现实,而要使自己的主体意识参与叙述过程,以个人经验积极介入文本,“力求作品深入读者的内心,实现文学的帮助人们主体生成、实现自我的功能。”[10]《卡珊德拉》是沃尔夫对自己艺术主张的创作实践,小说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但却反映着当时世界所受到的战争威胁,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在小说中融合,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卡珊德拉不被信任的痛苦、面对战争的恐惧、对特洛伊人民的担忧以及被监禁与无法发声的绝望,小说以卡珊德拉的濒死回忆作为展开叙事的起点和中心,“现在我讲着故事走向死亡”[2]1,并从她的视角结构全篇,在她碎片化的回忆中左右勾连各方人物和故事线索,使读者从先知卡珊德拉强烈的个人视角感受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强化了卡珊德拉的叙事权威,从而彻底颠覆了原始神话中无足轻重的卡珊德拉形象。沃尔夫要求描写与反思相融合,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也应具有“非情节化”特征,按照作者的主观真实决定文本的呈现方式,利用意识流方式将自己的女性经验与视角融入对洞穴中的女性乌托邦的叙述中,从而实现“主观真实性”的写作要求。
三、女性乌托邦的意义:超越对立的反战话语与生态关怀
在冷战的时代环境与霸权主义盛行的国际政治形势下,沃尔夫敏锐地发现三千多年前的特洛伊战争与当时的情形相差无几,战争与和平、女性的自我意识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仍然复杂尖锐,小说在对自我声音的发现与对性别权利的追求之外,更有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人类生态平等关系的憧憬。
首先,女性乌托邦超越了性别、民族与阶级的对立。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几不可见,她们只有在扁平化为受难者符号、为家国利益呼吁时才能被允许发出声音,通常情况下,这也都是她们死亡悲剧的序章,甚至这声音也并非自我的宣告,而是依附于并出于男性的喉舌。欧里庇德斯的卡珊德拉不仅将自己战死沙场的同胞称赞为死于希腊人之手的英雄,还在得知自己即将成为阿伽门农的侍妾后跳舞庆祝,视这桩屈辱的婚姻为复仇的机会,但其结果也仍未脱离仇恨与战争侵略的恶性循环。沃尔夫虽为卡珊德拉挣脱了男性权力话语的捆拘,又在隐含文本中建构了与男性权力话语的平等对话关系,但她笔下的特洛伊与希腊在几近伦理崩溃的权力斗争中仍是如此相似,出于对自己政治权威的不安全感,普里阿摩斯为防篡位下令杀死儿子帕里斯,阿伽门农也牺牲了女儿伊菲格涅亚以确保航道通畅。卡珊德拉抗拒从对希腊人的敌意中构建的特洛伊民族意识,她视为家园的女性乌托邦“拒绝被纳入或包含在国家叙事中,不再根据国籍建构身份”[11],在去父权中心的世界中重塑了以往的民族想象,创造出超越了民族对立身份的新世界。
其次,卡珊德拉在女性乌托邦的“我们”中找到了“我”的声音,确证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寻找“我们”以完善对“我”的意识时,卡珊德拉意识到必须重新融入一个存在真实意义的社群中,才能赋予自己不受约束的自我意识,进而彻底摆脱特洛伊皇宫强加给自己的角色定义。特洛伊无法满足卡珊德拉对“自我”的困惑与追寻,逃离象征等级制的特洛伊皇宫、来到斯卡曼德河畔伊达山的洞穴后,卡珊德拉回应了长久徘徊在心中的“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恰好找到了空间,这空间就是为这声音作准备的。”[2]168在对父亲普里阿摩斯的抵抗中,卡珊德拉极富隐喻性地与整个父权社会决裂,在伊达山的女性乌托邦中找到了新的“家”,“终于,这时我又说了‘我们’”[2]170。在希望哲学中,将人提升到彼此相通的境地之后,布洛赫继续追问是否能够实现用“我们”替代“我”,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惺惺相惜的、高于单个人的状态,沃尔夫在斯卡曼德河畔实现了布洛赫的构想,“女性将她们对母亲或姐妹般的前辈的渴望之情转化为对亚特兰蒂斯这块大陆的想象”[9]127,伊达山上的洞穴这一混沌暧昧、不可言说的女性空间同时存在着“被放逐之地”与“独属女性自己的世界”这两种截然相反却并未割裂的所指,这片独立于特洛伊战场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上在父权中心社会逻各斯话语的断层中生长,身披子宫隐喻的洞穴也就被赋予了成为女性乌托邦的可能性。在此终于获得独立自我意识的卡珊德拉决定主动赴死,虽仍未能改变特洛伊的悲剧,不能逃脱终将死亡的个人命运,但在疯癫中逐渐面对真实的自己,在越来越清晰的声音中认识自己,选择以死亡从崇尚战争与英雄的父权制文化中主动退出, “死亡作为此在的毁灭并不是人的命运,而是拓宽了生命的乌托邦意义。”[12]卡珊德拉在走向死亡的废墟上彻底摆脱了“他者”身份,实现了自身主体性的独立与圆满。
再次,脱离了战争、权力与名誉的捆拘之后,女性乌托邦在父权社会秩序之外探索出“生活”的真正意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女性社群,这些外在的或内在的理想之国,都为变革中的社会提供了‘女性气质’的解决办法。”[13]在饱受战争之苦的特洛伊人民质疑生命是否只剩下纯粹空洞之时,来自希腊的女奴使彭忒西勒亚与卡珊德拉等特洛伊女性看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真实生活:“到山上去。到森林里去。到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里去。毁灭和死亡之间还有第三条路:生活下去。”[2]162布洛赫认为当我们面对只剩下纯粹空洞的生活,如果依然能够坚持守住生活的责任,那么生活最终仍可以被我们拯救,因而人之为人就在于不断地追求意识对黑暗的照亮。布洛赫指向更高期盼的乌托邦思想深刻影响了沃尔夫,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社群中没有自我疏离、偶像崇拜或仇恨,各种身份下的人们都在诸神之母库柏勒的石像旁找到了理想的生活家园,“他们彼此渗透,而不相互抗争”[2]170,这个乌托邦世界中的人们多是为躲避战争而来,却在以互助代替竞争的洞穴社群中发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最后,女性乌托邦在核威胁的时代环境下更有生态关怀的意味,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与对父权中心社会秩序的反思都在对生态和谐乌托邦的追求中协调一致。《卡珊德拉》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苏军备竞赛背景下,工业文明危机与后现代思潮反映出人类精神世界在“上帝死了”的宣告之后几乎成为一片荒原,自然、文明与人类精神世界的生态和谐关系岌岌可危,人类之于自然、理性之于艺术以及男性之于女性等关系都被推向令人不安的对立境况,战争的威胁使得生态与女性同时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二者因同处于社会与文化的从属地位而具有了同源同构的特征,共享着相似的处境,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以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以乌托邦的建构实现对精神生态化、合理化生存的期望,以乌托邦的建构完成对精神生态危机的拷问、批判与内省成为‘乌托邦精神’与‘精神生态危机’顺势而动的自觉性选择。”[14]在工具理性思维无法解决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暴力与权力斗争等问题时,艺术家更完整地保留着对乌托邦的想象力,“因为艺术本身固有的幻想性,使艺术家还没有彻底同化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单一秩序里,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性,包含着被工业社会所排斥的乌托邦幻想。”[15]沃尔夫为觅求更美好的生存状态,尝试在文本中为自然、社会与人类精神,用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乌托邦化解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战争阴霾,卡珊德拉站在战后文化废墟上回忆特洛伊战争,不仅在特洛伊与希腊之间看到战争与文明的冲突,也在象征母系氏族社会的洞穴乌托邦和象征父系氏族社会的特洛伊战场之间见出法西斯主义与父权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倘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意味着毁灭,那么毁灭已埋没在我们的本性中了。”[2]170沃尔夫在伊达山这个荒芜的边缘之地为人类虚构了理想的精神栖息地,它不仅是远离城市文明与战争硝烟的自然生态乌托邦,也是存留了健全人性的精神生态乌托邦。
四、结语
战后德国的分裂景象使沃尔夫深切感受到每次文明与社会的转型都伴随着对女性的迫害,她像孤寂伫立在乱石废墟之上的卡珊德拉那般身处“分裂的天空”下,看到战争灾难的悲剧成因却无力改变,怀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冷眼审视战后德国的文化环境,在经典神话的观照中反思启蒙理性与国家权力操作,在神话重构中探索克服文明弊病的路径,颠覆性地质疑了民族主义与父权中心文化所狂热的战争欲望。沃尔夫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她如卡珊德拉一般悲哀地预见了权力斗争的悲剧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在《卡珊德拉》正式出版三年后发生爆炸,核威胁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将全世界人民置于恐惧之中,沉默的媒体加重了民众怀疑、不安与绝望的情绪,女作家在随后发表的小说《核事故》(Störfall,1987)中延续了批判工具理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从女性视角描写核电站事故对生活造成的直接威胁,探寻自然与女性如何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客体化,边缘化,成为被操纵、束缚和压迫的对象”[16],追问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取得的胜利如何分裂着本该和谐发展的人类共同体,坚持实践“主观真实性”的创作主张,虽深知女性亚特兰蒂斯大陆之不可实现,仍努力在文本空白中挖掘女性乌托邦的反战话语意义,为战后德国社会构建起了实现现代人全面自由的具体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