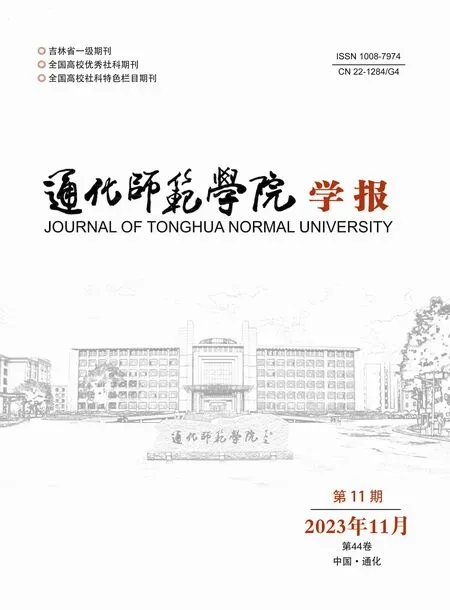从“感性对象性原则”到“感性活动”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眼中费尔巴哈“伟大功绩”探寻
刘芳铭
“感性活动”作为马克思开启全新哲学境域的理论基点,也是其经济哲学思想的理论根基,但它并非马克思的独创,而是与费尔巴哈哲学、黑格尔哲学思想有着深刻渊源。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性原则”为依据,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系统批判,发现了人是社会存在物,但费尔巴哈并没有领悟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这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那么马克思眼中费尔巴哈的主旨贡献即“伟大功绩”究竟何在,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重读《巴黎手稿》,其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三重界定清晰地勾勒出彼时马克思眼中的费尔巴哈,在高度概括评价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理论嬗变的思想号角就此吹响。
一、费尔巴哈揭示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形成了“感性活动”的理论源流
梳理这条理论源流,首先需要就理论界一直以来对马克思就费尔巴哈进行理论判断的误判进行澄清,翻开马克思于1845 年春创作的这篇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政治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理论家们往往聚焦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的赞许,却有心或者无意地对“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的理论研判视而不见。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家们的理论视域依然框限于自然唯物主义。而一旦从这一视域出发,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便被严重低估,作为所谓“半截子的唯物主义”的代表,在某些理论家的眼中,费尔巴哈仅仅是重拾旧唯物主义的权威,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贡献,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冠之以“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如此名实不副的评价——只能说明彼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尚未形成。由此,我们不难推理出哲学家们在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行理论点评时,容易摒弃尚未成熟但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观点,而截取自以为成熟的内容。
实际上,彼时马克思眼中的费尔巴哈,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其重建了以“自然界的先在性”为本质的自然唯物主义,也不在于恢复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唯物主义,而在于他“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奠基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早已摆脱了哲学家们框限的理论视域,完成了自然唯物主义的超越,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把人视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境界。
翻开1841 年首次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对人何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进行了环环相扣、丝丝入缝的理论推演,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1]29,因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皆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当你把自己的本质投射到任何物体上时,任何物体都承载着你的对象性存在,上帝也包含在此,即所谓“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1]30,费尔巴哈接着进一步明确:“所以,不管我们意识到什么样的对象,我们总是同时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不能确证任何别的事情而不确证我们自己。”[1]31完成上述理论判断后,费尔巴哈的阐释徐徐展开,“机智、敏慧、幻想、感情、理性等一切所谓的心灵力量,那是人类之力量,而非单个人的力量,乃是文化之产物、人类社会之产物。”[1]113“别人就是我的‘你’——虽然这也是彼此的——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是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只有借别人,我才体验到和感到我是个人;只有在对他的爱里面,我才明白他属于我和我属于他,才明白我们两人缺一不可,才明白只有集体才构成人类。”[1]193不难判断,没有“感性对象性原则”作为依据,就不会有“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理论表白,《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的高度评价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就彼时马克思的理论视域,费尔巴哈“一战成名”的关键在于奠基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并非“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互动共鸣铺垫了“感性活动”的理论根基。
二、费尔巴哈开启并引领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度批判,推动了“感性活动”的理论发展
一部久负盛名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举奠定了费尔巴哈在德国思想界的理论权威,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基督教的本质》折射出的是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进行哲学批判时闪现出的理论光辉。在成书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如是,德国宗教批判的历史宿命是谁来界定的?如何界定的?1844年9月到11月间,马克思与恩格斯首次合著的《神圣家族》为我们披露了答案:“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3]177马克思与恩格斯接着指出:“(费尔巴哈)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3]177这说明彼时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眼中,早已摆脱了德国宗教批判终结者的身份框限,在宏大叙事的哲学批判领域拥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他“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4]我们不禁要问,始于宗教批判终于哲学批判的费尔巴哈式的哲学气质究竟从何而来,答案还是要回归到“感性对象性原则”。
第一,一部《基督教的本质》把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上帝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勾连,抑或人的感性本质的对象性异在,还是“宗教异化论”均在“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关照下一览无余。费尔巴哈指出,“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些,正就是人的本质。”[1]39当我们以“感性对象性”为视角,费尔巴哈上述观点可以翻译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威力。”[1]30费尔巴哈接着明确:“我的这个学说用几个字来表明,这便是:神学就是人本学”;换言之,作为宗教对象的上帝或神,所表明的“不外就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的神不外就是人的被神化了的本质”。因此,“宗教史,或者神史(这是一样的),正是人的历史。”他又强调说:“人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1]518-519
尽管费尔巴哈对上帝的本质做出了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在“自然神”之本质的归纳提炼上,他依然无法摆脱理论家们对其的指摘,对此,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进行了明确的回应,在这本“分量虽小而内容甚丰的小书”里,费尔巴哈开展基督教本质批判的依据依然是“感性对象性原则”,也正是沿着这条逻辑主线,始于黑格尔宗教批判、历经黑格尔哲学批判、终于整个哲学体系批判的新范式被费尔巴哈历史性地呈现。
第二,1842—1843 年,随着《改革哲学的必要性》《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三部专著的相继登场,此时的费尔巴哈业已熟稔地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展开了系列哲学批判。当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哲学乃是转化为一种逻辑过程的神学史”[5]164,“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类学”时,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不过是“理性化了的,实在化了的,现实化了的上帝的本质”[5]103,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秘密就这样被费尔巴哈所洞悉——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如同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5]104,所有这些结论,无一不是建立在“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基础上所得出。
再读《基督教的本质》,两大命题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一是“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二是“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而当我们据此观照《巴黎手稿》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对第一个命题的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进而延伸拓展,对第二个命题则采取了直接引述的方式,以此作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之依据,就彼时马克思的理论视域而言,“感性对象性原则”直接与“感性活动”画上了等号,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同频共振下,马克思顺理成章地对费尔巴哈冠之以“伟大的功绩”的盛誉。
三、费尔巴哈基于“感性对象性原则”为“感性活动”做了最初的理论表白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素以艰深晦涩著称,但在费尔巴哈的眼中,黑格尔哲学不过是哲学与神学矛盾的诠释,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劳动的本质”这一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精髓,却被费尔巴哈有心或者无意地忽略。事实上,彼时的费尔巴哈完全遵照“感性对象性原则”对黑格尔把绝对理性视为人的理性的观点进行解构——如同他解构黑格尔把上帝与绝对精神画等号一样——继而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终极批判。可惜的是,费尔巴哈止步于此、裹足不前;对此,马克思可谓洞若观火,他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163时,费尔巴哈则“完全”没有意识到黑格尔用思辨的逻辑和语言表达了“劳动的本质”。行文至此,以“感性活动”和“感性对象性原则”为标志,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差距豁然呈现,纵观整个《巴黎手稿》,这里马克思用唯一一次“仅仅”的表述为日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振聋发聩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肯定费尔巴哈发现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时,必须指出,是基于费尔巴哈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但这一操作的前提是费尔巴哈抛开历史进程的一种非历史的抽象,是一种呆板无声、纯粹自然的一种共性提炼,并没有发现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具有的丰富鲜活的内涵,至于众人追问“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以及“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的理论原因究竟何在时,费尔巴哈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仅仅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直观的感性推论。
彼时只有26岁的马克思尚未意识到费尔巴哈理论的局限,但这里采用“仅仅”的话语表达,已经微显了对费尔巴哈的理论怀疑,但总体上还是冠之以“伟大功绩”,对费尔巴哈不吝赞美,实际上,此时马克思虽浑然不觉,但已然完成了由“感性对象性原则”到“感性活动”的理论嬗变。这意味着:
第一,费尔巴哈在此时马克思的视野中是黑格尔哲学批判者,更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非自然唯物主义者或单纯的宗教批判者,这里的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冠之以“真正的”,是因为费尔巴哈式的话语体系触动了马克思的理论神经,让后者对前者的理论高度进行了情理之中的误判。
第二,1843 年的马克思正在系统地阅读斯卡尔贝克(Skarbek)、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撰写笔记,还忙于研究法国国会公民史和资产阶级革命史,同时为《德法年鉴》撰稿,著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虽然他曾经向费尔巴哈进行约稿,表达了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兴趣,但直到《巴黎手稿》问世,此间不过一年,难以对费尔巴哈给予充分的了解与认知,也就意味着此刻要求马克思精准老到地把握费尔巴哈的理论观点,着实有些勉为其难。因此,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甫一触及马克思的理论神经时,随即就将其误判为达到“感性活动”高度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精神的劳动”,却据此得出了“实体即主体”这一重大命题时,费尔巴哈却把黑格尔哲学视为“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当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6]163时,费尔巴哈却以“感性对象性原则”对“实体即主体”的重大理论命题进行了浅白无力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称赞为“伟大功绩”,毋宁称之为“理论局限”。由此我们不难研判,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不吝赞美,但从未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一笔抹杀,反而给予客观审视并充分肯定,把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6]163称之为“伟大之处”,这说明“对象性活动”作为黑格尔思辨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已经渗透并入到“感性对象性原则”范畴内,成为建构“感性活动”这一哲学话语的关键因素,从而开启了思辨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
由此可见,《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对费尔巴哈给予盛赞,其原因,与其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达到自身“感性活动”的高度进行了理论误判,毋宁说费尔巴哈在开展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系列批判中,并非有意实则无心地为马克思创立真正的唯物主义——现实的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我们咀嚼“仅仅”这一意味深长的用语时,就会发现彼时的马克思已经隐约表达了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遗憾,沿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融入“感性对象性原则”,接续完成了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本质的解构和超越,“感性活动”这一崭新的哲学视域就此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