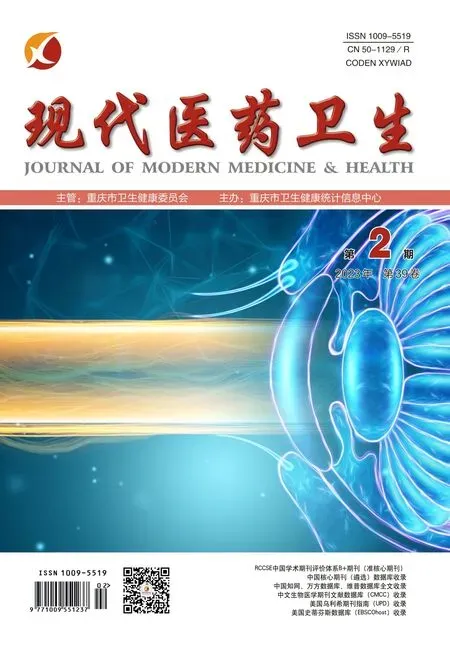小儿肾盂输尿管连接型肾积水的临床评估研究进展
李怡萱 综述,李志鹏 审校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云南 昆明 650101)
小儿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阻(UPJO)是发生在输尿管进入肾脏处部分性或完全性尿流排泄障碍进而导致集合系统扩张并可能引起肾功能损坏的一种泌尿系统畸形[1]。常规超声筛查检出率约为1/1 500,男女发病比例约为2∶1,且左侧病变比右侧更常见,双侧受累率约占10%[2]。产前肾积水最常见原因为肾盂输尿管连接型肾积水(UPJHN),其他原因包括膀胱输尿管反流、输尿管膀胱连接部梗阻、后尿道瓣等[3]。目前,UPJO病因尚未明确,最常见病理和解剖学原因为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典型的自身狭窄[4]。但是目前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区分梗阻和非梗阻[5],对小儿泌尿外科医师最大的挑战是判断哪些上尿路扩张患儿需保守观察,哪些需外科干预[6]。现将最近几年小儿UPJO产前、产后诊断评估综述如下,以期为泌尿外科医师提供一些更佳的评估策略,在最大限度地保留患肾功能的前提下避免非必要的手术干预。
1 产前评估
1.1超声检查 随着常规产前超声检查的普及,在妊娠18~20周通过常规产前超声检查大大提高了产前肾积水检出率[7]。50%~70%的产前肾积水是动态的生理性肾积水,产后一段时间内可自发消失[8]。产前病理性肾积水最常见的是UPJHN,但是目前没有预测UPJHN患儿未来肾功能变化趋势的可靠指标。产前最常用的评估UPJHN严重程度的指标是依据超声检查测量肾盂前后径(APD),指肾脏中部横断面上肾门水平2个实质边缘之间的距离,通常在孕中期(16~27周)即可根据APD评估产前UPJHN程度[9]。2010年美国胎儿泌尿外科学会(SFU)在共识中将孕中期(16~27周)APD≥4 mm、孕晚期(28~40周)APD≥7 mm诊断为产前肾积水,并分为轻、中、重度3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见文献[8]。为确定泌尿系统扩张的原因,产前超声检查评估应遵循解剖顺序,从肾实质厚度及回声情况开始,到肾盂、肾盏扩张程度,最后到输尿管、膀胱的异常和胎儿羊水情况,一一进行系统性评估。2014年KREMSDORF[10]和2017年CHOW等[11]在2010年SFU共识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产前尿路扩张(UTD)分级系统,分为UTDA1级(低风险)、UTDP2级(中风险)和UTDP3级(高风险)3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见文献[12]。UTD分类标准可同时评估产前和产后UPJHN,指出了胎儿期肾积水与产后泌尿系统持续异常的关联性,因此,认为其是预测UPJHN患儿预后的良好指标[13-14]。随着产前UPJHN评估指标不断地完善和更新,提高产前指导的准确度和及时提供适当的产前干预有助于对UPJHN患儿制定产后管理计划,尽早干预肾功能恶化可能性大的患儿,最大限度地保住患儿肾功能储备,为患儿本身及家庭减轻经济和身心负担。
1.2胎儿磁共振成像(MRI)检查 随着影像技术不断更新,有研究证实,胎儿MRI在诊断胎儿UPJO预后的评估具有较好的前景[15]。目前,超声检查仍是产前筛查和随访的一线检查方式,具有安全、实惠、实时评估等优势[16]。当孕母肥胖、子宫及胎盘异常、羊水过少及可疑复杂畸形胎儿而超声检查诊断价值有限时可对胎儿进行MRI评估[17]。胎儿MRI可使用快速序列对移动的胎儿进行交互式扫描,具有视野大、多平面成像、分辨率高等优势[17]。不仅能更好地识别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和输尿管膀胱连接处解剖结构[6],还能根据肾实质信号强度评估其损伤情况,清楚、客观地呈现合并输尿管病变和重复集合系统等复杂UPJO病例的尿路形态[16]。MRI的弥散加权成像通过检测人体组织中水分子扩散运动所受限制的方向和程度间接反映胎儿组织微观结构。胎儿正常肾脏表现出与母亲肾脏相似的扩散限制,而功能受损的肾脏则表现出较低的限制。因此,当UPJHN合并发育性肾异常(如异位肾、肾发育不全等)时可采用弥散加权成像鉴别诊断[18]。尽管超声检查仍是主要的诊断方式,但产前超声检查诊断的准确性与诊断者的经验和水平密切相关。在超声检查怀疑梗阻性肾积水但不能明确梗阻部位的患儿、怀疑重复肾肾积水但不能确诊的患儿及在超声检查因技术因素(如不良声学窗)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建议进一步进行胎儿MRI检查,且产前超声检查与MRI检查的诊断结果可互为佐证[18-19],不仅有助于评估羊水量、肾脏外观形态、肾盂、输尿管及膀胱扩张的程度和胎肺发育情况[20],还有助于产前咨询和评估宫内干预的必要性。在产前建议尽可能与儿科泌尿外科医师共同评估这些病例,多学科联合管理将对UPJHN患儿出生后预后大有裨益[21]。
2 产后评估
2.1超声检查 对产前确诊为羊水过少、严重双侧肾积水、后尿道瓣膜、孤立性肾积水的患儿推荐出生后48 h至1个月内进行泌尿系超声检查[22]。对患儿出生后的肾积水评估最常用的仍是SFU、UTD分级系统[3]。产后SFU肾积水分级标准根据肾盂分离程度、肾盏扩张数目、肾实质厚度等指标将患儿肾积水分为0~Ⅳ级[23]。产后UTD分级标准也将患儿分为UTDP1级(低风险)、UTDP2级(中风险)和UTDP3级(高风险)3个等级[23],具体分级标准见文献[3,23]。BRAGA等[24]对401例产前诊断为肾积水的患儿进行队列研究发现,UTD分级系统与SFU分级系统具有相似的评估精确度。如将末次超声检查随访时APD≤10 mm定义为肾积水缓解,基于这两种分级系统评估,平均随访观察2年,在SFUⅠ~Ⅱ级/UTDP1级患儿中约90%的患儿得到缓解,然而SFUⅢ级/UTDP2级、SFUⅣ级/UTDP3级患儿中分别仅有75%、50%的患儿得到缓解。不出意料的是,较高级别肾积水缓解率比较低级别肾积水更低。NELSON等[25]针对不足3月龄494例产前诊断为肾积水患儿进行产后超声检查发现,当将利尿性肾核素显像(DRG)检查作为UPJO的诊断标准时,超声检查UTD分级为P2级的患儿被确诊为UPJO者不足5%,但UTD分级为P3级的患儿被确诊者几乎达20%。因此,不论在产前超声检查还是在产后超声检查方面,UTD分级系统均能更加全面地评估集合系统扩张程度、肾脏实质情况、输尿管及膀胱情况和产前羊水情况[15]。此外,还能评估UPJO自然病程发展的解剖序贯性[26]。
2.2DRG检查 DRG是指肾动态显像与利尿实验的结合,其独有的优势既可比较左、右肾提供的肾功能差异和清除时差异,与其他诊断成像检查比较,具有吸收辐射少、无过敏反应和无持久毒性等优势[27]。常使用的示踪剂有锝99m-巯基三甘氨酸(99mTc-MAG3)和锝99m-二乙基三胺五乙酸,前者可广泛地与血浆中的蛋白质结合,具有光子发射、6 h半衰期且主要通过肾小管分泌清除等特点;后者主要是一种肾小球滤过剂,其排泄量与肾小球滤过率直接相关。使用99mTc-MAG3的DRG是基于注射利尿药(通常呋塞米0.5 mg/kg)显著提升尿流量的原理对99mTc-MAG3从集合系统中排泄情况进行可视化评估及解读[28]。TAYLOR[29]研究表明,半排时间(T1/2)<10 min可排外梗阻,T1/210~20 min为可疑梗阻,T1/2>20 min可确诊为梗阻。尽管该检查方法主要针对成人患者,但所涉及内容同样适用于患儿。目前,DRG仍是评估UPJO患儿分肾功能(DRF)和上尿路引流情况的首选诊断工具[30]。然而有时一些无法控制的操作因素,如被检者水合状态、膀胱充盈情况等,根据DRG得出的结果可能会高估实际DRF[31-32]。因此,临床医师已开始考虑使用新的影像学方法作为患儿DRF的辅助诊断工具。最近CHEN等[30]报道了对比增强超声(CEUS)检查在定量评估UPJO儿童肾血流灌注的诊断价值,说明CEUS是一种灵敏、快捷、经济、无创监测肾功能的新兴影像学方法。因此,尽管DRG仍是评价各年龄段患者尿路梗阻和肾功能的首选方法,但CEUS由于没有辐射暴露或使用肾毒性造影剂的风险,相信未来在小儿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2.3磁共振尿路造影(MRU)检查 MRU在没有电离辐射的情况下既可通过冠状面、矢状面、水平面显示泌尿系解剖的形态学结构,又可准确评估UPJHN患儿DRF[33]。MRU在小儿中最常用于评估肾脏和尿路先天性异常,如先天性肾积水和肾发育性畸形。有研究证实,MRU甚至可准确计算小儿肾小球滤过率[34]。OTERO等[35]通过对比研究102例UPJO患儿118个正常肾脏与22个异常肾脏后发现,UPJO肾脏与较低的各向异性分数和较高的表观扩散系数(ADC)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然而,BEDOYA等[36]将35例受试者30个UPJO肾脏和40个正常肾脏对比后发现,UPJO肾脏ADC与功能MRU的形态(肾盂扩张分级、皮质变薄、皮质髓质分化和APD)或功能(肾增强、排泄、DRF等)均无关。此外,肾盂无扩张时ADC也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最近的一项关于18例婴儿在没有使用任何镇静或麻醉药物情况下仅采用“喂食或包裹”法安抚婴儿,成功进行了MRU检查并获得泌尿道解剖结构及功能成像的研究表明,“喂食或包裹”法磁共振尿路成像针对婴幼儿可能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新方法[37]。在小儿泌尿外科领域中应用MRU进行肾功能成像可识别和量化不可逆肾单位丢失和潜在可逆的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评估疾病进展,以决定何时需手术干预,并监测术后疗效。
2.4尿液生物学标志物 尽管超过一半确诊为UPJHN的新生儿能自行消退,但仍有30%左右的病例面临肾功能进行性或永久性丧失的风险[38]。一些学者越来越担心目前影像学检查评估梗阻标准的局限性,开始研究无创尿液生物学标志物描述小儿肾积水严重程度和预测肾损害进展。由于UPJO致肾小管扩张、间质炎症,进一步致肾小球损伤和间质纤维化增生,这一系列的失代偿病理生理过程促使梗阻肾脏释放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蛋白(NGAL)、转化生长因子β1、单核细胞趋化肽1、调节激活正常T淋巴细胞表达和分泌、碳水化合物抗原19-9等尿生物学标志物,是目前研究的一个切入点[9]。NGAL是一种中性粒细胞明胶酶共价结合的蛋白质,梗阻时在受损肾小管上皮细胞中大量合成并释放NGAL到尿液中。PARABOSCHI等[39]对38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后发现,9项研究表明接受UPJO手术患者尿NGA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2项研究表明接受UPJO手术患者尿NGAL也明显高于非阻塞性肾积水患者。其他尿生物学标志物,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1、单核细胞趋化肽1、调节激活正常T淋巴细胞表达和分泌、碳水化合物抗原19-9等在接受UPJO手术患者尿中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虽然尿液生物学标志物作为UPJO患者的评估作用仍缺乏可靠的研究,但这些标志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无创手段评估UPJO患儿肾损伤风险和术后随访指标仍具有潜力。
3 小 结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目前,小儿UPJHN最新的术前评估主要聚焦于影像学成像评分系统的升级和尿液生物学标志物的兴起。基于常规的超声检查,SFU分级系统和UTD分级系统对小儿UPJO管理均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采用DRG及时评估小儿肾功能仍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诊断方式,因其一些操作局限性,应运而生的CEUS对小儿患者肾功能的评估具有巨大潜力。对小儿泌尿外科医师而言,如何精准地诊断梗阻及何时实施手术干预才能使患儿获益最大仍存在争议。随着新兴尿液生物标志物的引入和影像学检查精准评估的升级,开发出早期、精准、微创的诊断模式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