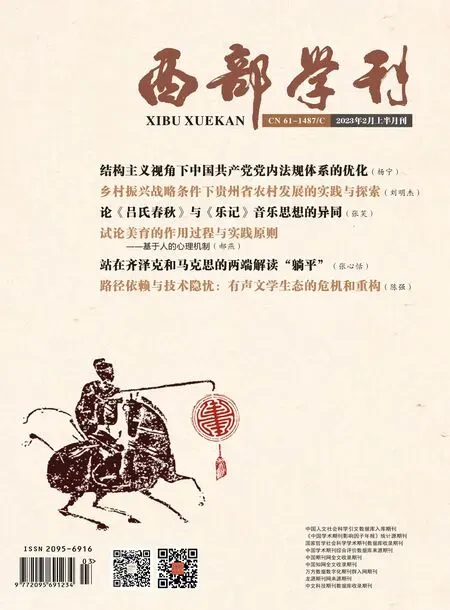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及其局限性刍议
粟 凯 庞 楠 姚思泉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其民生史观从哲学角度对民生进行了新的诠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身处困境之中的孙中山从马列主义中发现了新的希望,于是在1924年他对其“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重点强调“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一新的诠释在后来被称之为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从哲学基础上看,孙中山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太极”的宇宙论以及“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以近代西方进化论为核心,具有可贵的唯物主义偏向性;从主要内容看,注重民生,强调民生是历史的重心,将民生视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这种诠释,使得其民生史观具有了认识世界以及认识社会规律的方法论意义。然而,由于孙中山对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导致了英雄史观的偏向性,贬低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以及主观能动性。
一、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
孙中山十分关注和重视作为历史主体“人民”的地位,他的民生史观的产生有丰厚的哲学基础。在孙中山看来,于国家的政治层面,统治者要将“养民”放在突出位置,认为是否重视“养民”关系到国家的兴盛、政权的稳固与否等。这一观点契合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思想,如《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离娄》中“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儒家治国思想。在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中能发现他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设想:“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观点,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
(一)宇宙论
在宇宙论上,孙中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太极”观念,并从唯物主义角度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太极”是世界的原初物质,另一方面他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进化论的影响,将宇宙、生命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物质进化之时期、物种进化之时期、人类进化之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关系到人类起源和生命起源的问题,在哲学界长期以来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两个不同派别斗争和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孙中山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通过对人类起源与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表明地球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自然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只是自然演进在漫长而又悠久的岁月之后出现的。这是具有浓厚唯物论和无神论色彩的观点。
物质进化之时期,孙中山认为作为原质的“太极”运动生成电子,无数的电子在运动的过程中相互吸引而凝聚在一起,形成所谓元素;无数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物质;最后,地球的形成正是无数的物质聚集。在这里他是肯定物质作为一种世界的原初物质是先于意识的,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体现着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
物种进化之时期,孙中山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现的生物基本结构细胞创名为“生元”,据此进一步提出“生元说”,认为生物之原始为“生元”,即细胞,“生元说”肯定生物进化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顺序,进而从根本上否定“神创说”。他在生命现象和精神现象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未能正确地理解精神或者意识是人脑的一种特殊物质机能以及对客观世界之反映的一种产物,故而他并不能正确理解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人类进化之时期,孙中山认为这一时期是物种进化的终点,是人类之自身进化阶段,在“生元说”的基础上否定了“神创说”,并将这种反对神权的认识与其革命思想相结合,强调“神授之君权”必将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战胜。在否定君主之政治权力是神授的基础上,必然将目光转向“人民”,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宣言中可以看到,他明确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种转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原有的以“君主”为中心变为以“人民”为中心。
(二)认识论
发生于1913年的癸丑之役亦即“二次革命”的失败,给革命党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的人产生了“纸墨之力终究不如刀枪之灵”的感慨,这反映出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关于“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错误认识,事实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关系的讨论一样,一直都是中国哲学中认识论所关注的重点,只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更关注道德的体悟与实践。
孙中山在跳出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局限的同时,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对“知”与“行”赋予了新的理解。在孙中山的新解中,“知”不再是道德的体悟,而是用一种理性思维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行”则是指范围广阔的人类活动,包括社会生产、科学研究、日常生活及革命活动等。基于这一新的理解,孙中山对知行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这一观点符合唯物主义关于实践决定认识的观点,具有现代认识论的特点。据此孙中山将人类“知行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不知而行(认识始于实践);行而后知(实践得到的经验可上升为理论认识);知而后行(理论认识可以指导实践)。
基于其“行先知后”的认识论原则,孙中山指出“知难行易”,针对当时革命党内部关于“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认识,强调“行之非艰,知之维艰”。其内涵一是如“知行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不知而行”所说明的不知亦能行,证明行易于知;二是虽然“行而后知”,但如不思考,则行亦无知,证明知难于行,同时强调“知而后行”,即用思考后得来的理论认识指导实践则事半功倍。这一认识肯定了正确认识的来之不易,但过分夸大“知难”,而这种夸大导致孙中山根据经济学分工原理而提出“分知分行”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将人进行等级划分,认为这世界有人天生圣贤“先知先觉”,有人愚笨“后知后觉”,更有人昏昧“不知不觉”,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就是由少部分的“先知先觉”者,预先对社会问题想出来许多办法,带领着“后知后觉”者与“不知不觉”者去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先知先觉”者的领导,人民群众就无法自觉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一划分隐含着“英雄史观”的倾向性。
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内容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根据建立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进化论基础之上的宇宙论,他认为物质是进化的、物种是进化的、人类亦是进化的。这种对于“进化”的认识成为孙中山民生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客观来看,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主要内容是他对“民生”的理解。关于民生,孙中山是这样说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167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在孙中山这里“民生”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其次它体现了人们渴望生存的诉求,正是这种诉求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两点:“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一)历史的重心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之所以提出并强调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正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流行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的重心”方面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中“物质”才是历史的重心之观点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浅尝辄止,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构成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2]。他直观地认为“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1]176-177。因此,在孙中山当时的认知中,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社会问题是历史的重心,于是经过推理,所谓民生问题,其实质就是生存的问题。
既然民生问题的实质就是生存的问题,那么对于所谓“民生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就不能偏重于道德、感情层面了,要从经济层面着手,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质,也就是满足生存的需要。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以至于不能生活,或者是能得到部分需要但不能充分满足,也只能是半死不活,因此他认为需要的满足是人生存所必须的。第二级是安适。安适是在人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之上去追求安乐、舒适。第三级是奢侈。奢侈是在安适的基础之上的极致追求。在孙中山看来,解决民生问题不是要解决“安适”或者“奢侈”,而是解决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需要”。
(二)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孙中山认为“民生”体现了人们渴望生存的诉求,也正是这种诉求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他说:“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1]177孙中山的民生史观首先是肯定社会进化的,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进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他在这里提到的定律,事实上也就是规律的意思,是事物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共生共长的关系,这也是某种必然的趋势。在这里他的思路是:“人类只有不间断地求生存,社会才有不停止地进化。而这种不间断进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人类不间断之求生存。
在孙中山看来,地球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自然演进的过程中,不仅自然界处在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人与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是一个由简入繁、由低到高,连续且不间断发展进化的一个过程。他用带有浓厚进化论色彩的标准把人类史由古及今进行了四个时期的划分:“第一时期,人与兽相争,非是用权,用气与力。第二时期,人与天相争,乃是神权。第三时期,人同人相争,国与国相争,此民族与彼民族相争,乃是君权。及至今日之第四时期,于国内相争,人民与其君主相争。在这一个时代之中,简而概括则为善人与恶人相争,公理与强权相争。及至今日之时代,民权渐生且日益发达,可称作民权时代。”[3]
孙中山还提出:“人类本身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唯物史观中,社会的基本矛盾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孙中山显然是用生存欲望和需求等社会意识层面的内容取代了物质层面的社会劳动实践,将意识层面的东西视作是“第一性”的,然后将民生归于意识。这就否定了物质层面的社会存在决定思维层面的社会意识,也否定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更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三、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局限性
作为时代的产物,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毋庸置疑地受到那个时代所代表的阶级以及自身认识的影响,其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在与唯物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比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一方面受其影响,另一方面背道而驰。针对近代中国民生问题,孙中山提出经济上“均分地权”“控制资本”等措施,表现出他对劳动者的同情,具有一些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是他用生存欲望和需求等社会意识层面的内容取代了物质层面的社会劳动实践,将意识层面的东西视作是“第一性”的,然后将民生归于意识,把人类求生存的这种“愿望”当作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而陷入了社会意识决定论,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所存在的内在之矛盾,就在于他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孙中山认为要实现社会革命需要一定的武力。但在终极意义上他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他提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发生的一种病症。”[4]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互助原则”用来取代“竞争原则”,即“阶级战争”,具体到近代中国的国情,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都处在贫穷的阶段,区别只是一般贫困和特别贫困,既然都是处于贫穷阶段,因此就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这一观点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同时说明孙中山没有意识到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采用“阶级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等手段实现“无产专制”的。
(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英雄史观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事实上与英雄史观是存在着联动关系的,这一联动主要基于他根据经济学分工原理而提出的“分知分行”观点,将人进行等级划分。在他看来,人类文明以及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是“先知先觉”者先于社会的发展就预想出了方法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众多贡献;而“后知后觉”者是社会的大众群体,先天禀赋不足,没有创造发明能力,只能随着社会发展的大潮;“不知不觉”者则更是需要别人的引导,不能“知”只能“行”。虽然孙中山并未对这三者的人数进行描述,但“先知先觉”者毕竟只可能是少数。在这一观点下,少数“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带领着大多数的“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一观点与“英雄史观”一样,极大地贬低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以及主观能动性。
四、结语
虽然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但应该看到他在国家的政治层面,要求统治者将“养民”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是否重视“养民”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否、政权的稳固,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他强调从经济层面着手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强调统治者要关注并且解决民生问题。他以进化论为基础,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作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历史,对民生问题进行新的解读和诠释,作为一种认识和理解社会的方法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