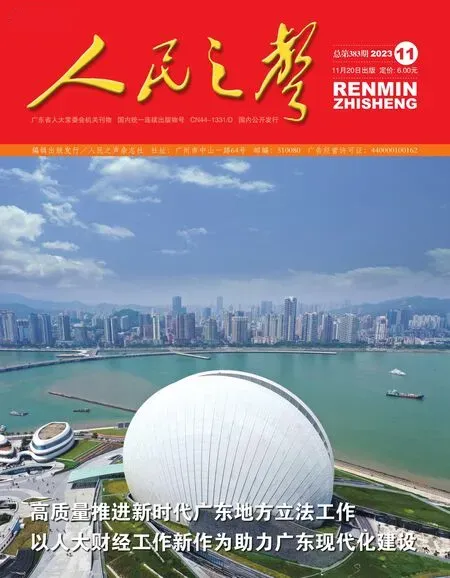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应立足公益最大化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法治部署。与之相呼应,近期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明确列入了第一类立法项目。这意味着,近年来日积月累的公益诉讼立法建设,即将掀开专门立法的崭新篇章。
追溯起来,我国公益诉讼从个案探索到蓬勃发展,始终伴随着立法的破冰和演进。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创设了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连袂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实体法层面,十多部单行法律先后植入了公益诉讼条款。此外,相关司法解释、地方立法等等,也在不断丰富着公益诉讼的法制供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分散立法的模式高效满足了公益诉讼初创时期的制度需求,但随着公益诉讼实践的不断深入,立法重复、冲突、空白等不足也日益显现。公益诉讼立法由“碎片化”转向专门化,进而构建起系统协调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系,已势在必行。
就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路径选择而言,当下的法制框架虽然赋权多主体提起公益诉讼,但其发展并不均衡,覆盖不同主体、类型等等的公益诉讼法尚不具备成熟的立法条件。其中,检察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队”,其公益诉讼起诉案件已占总量的95%以上。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公益诉讼格局,以及相关制度资源的相对充足,无疑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另一方面,高歌猛进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法制短缺之间的矛盾也最为突出。比如,国家立法中的检察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大多原则、简约,只是确认了其合法性,具体运作则主要依赖于位级较低的司法解释,并不足以破解所遭遇的实践难题。可见,人大立法规划将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列为优先选项,既蕴含着现实可行的立法智慧,更彰显了急用先立的立法谋略。
同时应当看到,追求“利他主义”的公益诉讼,旨在弥补立足“利己主义”的私益诉讼局限,从而避免公益受损却无人追究的“公地悲剧”。这就意味着,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并非依附于传统法制框架下的简单制度整合,而是应当厘清公益诉讼独特的价值目标、诉讼肌理、运行规则等等,设计出有别于一般诉讼、有利于公益最大化的制度构造。尤其是,检察公益诉讼作为富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兼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相较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仅权能更大、责任更重,还呈现出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这些特质有必要充分融入专门立法的细节层面,以最大程度地焕发检察公益诉讼的活力和功效。
比如,受案范围标示着检察公益诉讼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多部单行法律的持续授权,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已由早期的生态环保、食药安全等4个领域拓展至13个。专门立法除了继承既有的立法成果,还有必要合理划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边界,并以开放的立法思维,为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的未来扩容预留广阔的空间;再比如,取证难是公益诉讼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专门立法除了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还有必要重构契合公益诉讼特殊性的举证责任制度,尤其是在行政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领域,更需合理配置、分担举证义务,从而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捍卫公共利益;还有,诉前程序作为检察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具有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调动社会组织积极行权的独特价值。专门立法除了确认实践中已经成功探索的磋商、评估等机制,还有必要赋予检察建议等以更强大的司法效力,提升诉前程序的刚性力度,进而更有效地激发相关主体守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从更长远的视角而言,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率先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是公益诉讼立法建设的破局之举,也迈出了“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一步。其所积累的立法经验,当能为未来制定统一完备的公益诉讼法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公益诉讼从一枝独秀走向集体发力,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维度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由此铸造的维护公益共同体航船,驶向的正是公益诉讼的理想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