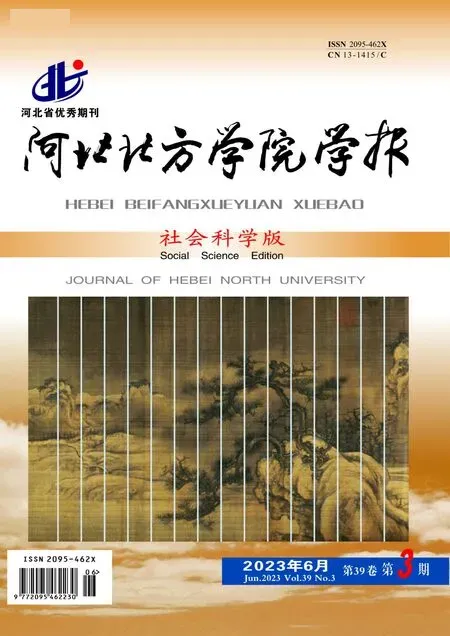河北赤城话“(N)V的/də33/了”结构
李 文 张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在河北赤城话中有这样的结构句式,如:洗洗手吧,饭吃的/də33/了(洗洗手吧,该吃饭了)。天黑了,咱们走的/də33/了(天黑了,咱们该走了)。在赤城话中,上述结构可以概括为“S,(N)V的了”。S是一个表示已有现状的命题,“(N)V的了”可以表达情态,包括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表示“应该做某事了”“做某事的时间到了”或者“某事情将要发生”。这类结构对应普通话的平行结构“(应)该+VP+NP+了”或者“VP+NP的时间到了”或者“NP快VP了”。在赤城话中,这类表达可以不借助动词“(应)该”或者偏正结构“做某事的时间”,而是在具体动词后使用“的了”标记表达。Tsang将现代汉语助动词表达的意义分为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贺阳称情态为语气,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语法意义。他将语气分为功能语气、评判语气和情感语气。关于赤城话“(N)V的了”结构,学界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在汉语中通过动词后加“的”标记表示情态的情况也不多。笔者经过田野调查发现①,在晋方言区,类似的结构语义还有晋方言大包片中的大同话,晋方言张呼片中的宣化话、康保话和沙城话等,总体而言“(N)V的了”结构在张家口方言中比较常见。
一、“(N)V的了”的句法分析
赤城话中“(N)V的了”结构对“N”和“V”有较为严格的句法限制,除了“(N)V的了”这一典型结构外还具有变式结构,且“(N)V的了”结构的成句需要特定条件。
(一)对V的选择
“(N)V的了”结构中的动词主要表示动作行为,具有实在意义。从动词配价的角度看,可以进入到赤城话“(N)V的了”结构中的动词主要有以下3类。
第一类是一价动词,如:
例1.天黑了,咱们走的了。(天黑了,咱们该走了。)
例2.我记得他是前年上的高中,他毕业的了吧!(我记得他是前年上的高中,该毕业了吧!)
例1中,“走”只需要“我们”这样的主语与之共现即可成句。例2中,由于“毕”和“业”合起来使用的频率高,词汇化程度深,因此“毕业”可以整体作为一价动词进入此结构。
第二类是二价动词,如:
例3.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洗的了。(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该洗了。)
例4.孩子放学回来了要,饭做的了。(孩子放学回来了要,该做饭了。)
二价动词进入此结构的情况较为常见,从现代汉语语序的角度看,二价动词的宾语一般都置于动词之后。但在此结构中,宾语在动词前。
第三类是三价动词,如:
例5.你借他书好久了,还的他了。(你借他书好久了,该还他了。)
例6.快放假了,你没收的手机给的他们了②。(快放假了,你没收的手机该给他们了。)
根据笔者田野调查,在赤城话中,一价动词和二价动词进入“(N)V的了”结构的较多,三价动词进入此结构较少。如例5和例6中,一般赤城话更多情况下表达为“你借他书好久了,快还给他吧”和“快放假了,你没收的手机快给他们吧”。由于“的”作为情态标记和动词结合紧密,因此“的”一般置于三价动词和与事宾语之间,但这样会造成语音上的发音困难。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使用三价动词时,赤城话会更多选择“(N)V的了”的替代性说法,即与普通话类似的“该做某某事了”。
根据带宾语的情况,黄伯荣和廖旭东将动词分为名宾动词、谓宾动词和名谓宾动词3类。可以进入赤城话“(N)V的了”结构中的及物动词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名宾动词。如:过年呀,房子打扫的了(过年呀,房子该打扫了)。第二类是真谓宾动词。如:今年雨水来得早,种地打算的了(今年雨水来得早,该打算种地了)。
(二)对N的选择
在“(N)V的了”结构中,除了一价动词外,其余动词和前面的名词都可以构成动宾结构。根据宾语的语义类型,可以将宾语分为施事宾语、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处所宾语、工具宾语和存在宾语等。经考察,可以进入“(N)V的了”结构的宾语主要是施事宾语、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和处所宾语。如:
例7.施事宾语:正席开始呀,客人儿来的了吧!(正席开始呀,客人儿快来了吧!)
“客人”既是所搭配动词的宾语,在语义角色上又是动词的施事。
例8.受事宾语:过年呀,房子打扫的了。(过年呀,该打扫房子了。)
“房子”既是所搭配动词的宾语,在语义角色上又是动词的承担者。
例9.结果宾语:你们孩子结婚呀吧,房子盖的了。(你们孩子结婚呀吧,该盖房子了。)
“房子”是动词“盖”的宾语,在语义角色上,“房子”是动作“盖”产生的结果,即“盖成房子”。
例10.处所宾语:到点了,单位去的了啊,要不迟到了。(到点了,该去单位了啊,要不迟到了。)
在赤城话中,可以进入“(N)V的了”结构的宾语主要是受事宾语,表示动作的承受者,NV之间的动宾支配语义关系较强。而施事宾语要想进入“(N)V的了”结构,对动词的语义就有较高要求,一般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出来”和“来”等词。对结果宾语和处所宾语的使用则存在明显的年龄变体,年轻一代的赤城话母方言者倾向于选择普通话的平行说法,即“该干什么什么了”。
(三)“(N)V的了”结构的变式
“(N)V的了”结构具有“V的N了”和“V的了”两种变式结构。其中,“(N)V的了”结构是比较典型的结构,由“宾语”“动词”和情态标记“的了”三部分构成,该结构之前有语义完整的小句,整个句子以复句的形式呈现。如:
例11.你洗洗手吧,饭吃的了。(洗洗手吧,该吃饭了。)
例12.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洗的了。(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该洗了。)
例11中,前面小句为主谓宾结构;例12中,前面小句为主谓谓语句。
第一种变式结构为“V的N了”结构:在赤城话中,大部分的“(N)V的了”结构都可以通过变式转换为“V的N了”结构,意义没有差别,赤城话的母方言者都可以接受并使用。如:
例13.开学呀,书包收拾的了。(快开学了,该收拾书包了。)
其变式为“开学呀,收拾的书包了。(快开学了,该收拾书包了。)”在“(N)V的了”结构变式为“V的N了”结构的情况中,动词V一般是二价动词,变式难度较小。
第二种变式结构为“V的了”结构,该结构省略N保留了“V的了”。这类结构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词V为一价动词,如例12和例13。一类是该结构之前的小句主语为“(N)V的了”结构的宾语,采取承前省的原则,如例14和例15。如:
例14.干了这么久,休息的了。(干了这么久,该休息了。)
例15.天黑了,咱们走的了。(天黑了,咱们该走了。)
例16.手表坏了,修的了。(手表坏了,该修了。)
例17.汽车的油没了,加的了。(汽车油没了,该加油了。)
例14中,动词“休息”是一价动词,需要主语与之共现,该例句省略了主语。例15中,“咱们”并不参与“(N)V的了”结构的构成,此处“咱们”做主语,和“走”之间是明显的主谓关系,与该文讨论的“(N)V的了”结构不具有同构性。因此,该文将此结构处理为“V的了”结构。此外,从上一节内容可知,“咱们走的了”并不能变式为“走咱们的了”,由此可看出“咱们走的了”不是“(N)V的了”结构。例16和例17中,动词“修”和“加”分别与前面小句的“手表”和“汽车的油”构成动宾关系,采取承前省的原则。
(四)“(N)V的了”的成句条件
张斌认为:“句子既叙述客观现实,又表示说话人对事实的主观态度。主观方面主要是语气,每一个句子必定有特定的语气。客观方面主要是时间因素。”许立群认为:“现代汉语句子成立的条件是具备命题结构和景深适宜的参照结构”,“句子成立条件可通过语境信息获得”。考察发现,“(N)V的了”结构成句需要语境信息、特定语气和时间因素。语境信息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一是语言语境。如:
例18.草长这么高了都,地锄的了。(草长这么高了都,该锄地了。)
例18中,“草长这么高了都”既是当时说话双方的情景语境,即说听双方都可以看见草长得很高;又是说话人提供的语言语境,是说话人被当时的特定环境触发而产生的话语。
例19.作业做的了。(该写作业了。)
例19没有语言语境,主要是整句话暗含的情景语境和时间因素共同起作用,如“放学后”“开学前”“上课前”和“晚上休息前”等,都可能激发“(N)V的了”结构的成句。
例20.过年呀,房子打扫的了。(过年呀,该打扫房子了。)
例20的成句是语言语境和时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年呀”在形式上提供了语言语境,在意义上提供了时间因素。
例21.手表坏了,修的了。(手表坏了,该修了。)
例22.汽车的油没了,加的了。(汽车油没了,该加油了。)
例23.抹布用的时间长了,换的了。(抹布用的时间长了,该换了。)
上述3例中的情景语境是不确定的,有明显的语言语境和时间因素。“手表坏了”“汽车的油没了”和“抹布用的时间长了”都是目前已然发生的事情,时间性明确。但说话双方当时共同的场景中是否有“手表”“汽车”和“抹布”是不确定的,所以情景语境不明确。笔者认为这3句话成句的主要机制是说话人提供的语言语境刺激了听话人的联想,使得“(N)V的了”结构在交际中具有成句的可能性。
二、“(N)V的了”结构的语义特征
“(N)V的了”结构有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等语义范畴,同时又伴随着其他语义特点。
(一)“(N)V的了”结构的语义特点
“(N)V的了”可以表达情态,表示“应该做某事了”或“做某事的时间到了”。经考察,有如下两组语义特点。
第一组语义特点为[+表应然而未然][+道义情态]。如:
例24.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洗的了。(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头发该洗了。)
例24中前面小句句义为头发脏了,应该洗了,属于应然义,表示道义情态;但是还没有洗,属于未然义,由此提供了“头发洗的了”结构的语义环境,促使“头发洗的了”语义特点的实现。
例25.刚刚都大学毕业了,对象找的了吧。(都大学毕业了,该找对象了吧。)
例25中前面小句句义为大学毕业了,年龄不小了,按道理应该找对象了,属于应然义,表示道义情态;但是还没有找到,属于未然义,由此提供了“对象找的了”结构的语义环境,促使“对象找的了”语义特点的实现。
例26.汽车的油没了,加的了。(汽车油没了,该加油了。)
例26中前面小句表示汽车的油没有了,应该加油了,属于应然义,表示道义情态;但是还没有加,属于未然义,由此提供了“加的了”的语义环境,促使“加的了”语义特点的实现。
第二组语义特点为[+表时间来不及][+道义情态]。如:
例27.孩子放学回来了要,饭做的了。(孩子放学回来了要,该做饭了。)
上例表示应该要做饭了,表示道义情态。否则孩子放学回来没有饭吃,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例28.天黑了,咱们走的了。(天黑了,咱们该走了。)
上例表示天快要黑了,咱们应该走了,再不走天就黑了。既表示道义情态,又表面不走来不及的语义。
例29.你要坐席的话,可去的了啊!(你要坐席的话,可该去了啊!)
上例表示要坐席的话现在就应该走了,表示道义情态。再不走坐席就要迟到了,应该去了。
上面3个例子都有时间来不及的语义特征,与第一组语义特点中[+表应然而未然]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组例句的句义中,听话人可以按照应然的要求去做,如果不做也没有什么影响,而第二组例句中,前面小句和“(N)V的了”结构有明显的时间关联,有强烈的“不如是做时间就来不及”的语义。
第三组语义特点为[+表将来][+认识情态]。如:
例30.快五点呀,太阳出来的了。(快五点呀,太阳快出来了。)
例31.正席开始呀,客人儿来的了吧!(正席开始呀,客人儿快来了吧。)
例32.这房子可有年头了,塌的了。(这房子修建多年了,应该要塌了。)
例30是表示说话人对太阳出来时间的认识和推测,例31是表示说话人对客人来的时间的认识和推测,例32是表示说话人对房子可能坍塌的时间的认识和推测,这3例都具有认识情态,表示将来可能会发生,即事件还没有发生。[+表将来][+认识情态]的语义特点在“(N)V的了”结构中并不常见,而且和“N”的语义角色密切相关,只有在“N”的语义角色为施事宾语或者“V”为非自主动词时,这种认识情态的语义才会被凸显。笔者认为,第三组语义特点的产生要晚于第一种和第二种语义特点,第一种和第二种语义特点为此结构的核心义,第三种语义特点为延伸义,第三种语义特点是受到前两种较为显赫和强势的“(N)V的了”结构的语法类推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在“(N)V的了”结构中,“N”的语义角色为施事宾语的情况并不常见,这种[+表将来][+认识情态]的语义特点也不常见。
(二)“(N)V的了”结构与前面小句的语义关系
“(N)V的了”与前面小句的语义关系有因果关系、果因关系和承接关系3种。
1.因果关系
前面小句与“(N)V的了”结构构成因果关系是比较常见的语义关系,也是比较符合语言使用者认知特点的关系。如:
例33.这院子乱的,清理的了。(这院子好乱,该清理了。)
例34.刀钝了,磨的了。(刀钝了,该磨了。)
在例33中,“院子乱”是“清理”的原因,“清理”是“院子乱”的结果。在例34中,“刀钝”是“磨”的原因,“磨”是“刀钝”的结果。
2.果因关系
前面小句与“(N)V的了”结构构成因果关系的不多。如:
例35.你洗洗手吧,饭吃的了。(洗洗手吧,该吃饭了。)
因为该吃饭了,所以洗洗手吧。“饭吃的了”是“洗洗手”的原因。
3.承接关系
前句与“(N)V的了”结构有明显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通常先发生前句事件,紧接着会发生“(N)V的了”事件。如:
例36.天黑了,后天爷出来的了。(天黑了,月亮该出来了。)
“天黑”不是“后天爷(月亮)出来”的原因或者结果,而是存在时序上先后关系的两件事,两者之间是承接关系。
(三)历史文献中的类似结构
在明清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结构形成的痕迹,即用“的了”表示将然或应然义。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众人道:“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儒林外史》:“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九尾龟》:“若果然遇到了这样的人,这却没奈何,要用奇兵取胜的了。”这几个例句都是用结构“的了”表示即将发生的或者是应该要发生的语义情态或时间意义,可以看作是“(N)V的了”结构形成的过渡状态。
三、“(N)V的了”结构的跨方言考察
在现代汉语的官话和其他方言区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各方言中的类似结构可概括为“VP的了/得咧/得来/得溜”等形式,关于“VP的了/得咧/得来/得溜”这类结构中是“的”字还是“得”字,笔者通过和发音人交流尽可能选取与方言点语音一致且意义相关的音、形和义进行描写。其中,以山西大同话和河北赤城话为代表的晋方言以及黑龙江齐齐哈尔话中的“的”字没有明显的意义指向,笔者选用“的”来记录;陕西永寿话、湖南邵阳话、湖南洞口话以及贵州兴义话的母方言者对“的”的选取偏向于动补结构中的“得”;吉林长春话和山东日照话的母方言者对“的”的语音形式有所强调,认为其发音为/te214/,从意义上来看,更接近于情态动词“得”。但这些结构都有情态意义和时体意义。下文从“VP”的类型、情态意义和时体意义等方面进行跨方言比较。
(一)VP的类型
在“VP的了/得咧/得来/得溜”这类结构中,VP类型主要有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动词的价和动词的自主性等几种考察视角。被调查的方言点中动宾搭配的VP类型几乎都可以进入此类结构。除此以外,河北赤城话和陕西永寿话中的动补搭配也可以进入此类结构。但赤城话中此类结构使用动补搭配的频率较低,而在永寿话中使用频率较高。如:
例37.赤城话:吃罢的了。(快吃完了。)(使用频率低)
例38.永寿话:刷干净得咧。(快刷干净了。)(使用频率高)
从连动式进入此类结构的情况来看,只有湖南邵阳话中连动式的VP类型可以进入此类结构,其余被调查的方言点都不可以。如:
例39.邵阳话:骑车出门得哩。(要骑车出门了。)
从配价的角度看,一价、二价和三价动词都可以进入此类结构,但山西大同话、陕西永寿话和吉林长春话中的三价动词很难进入此类结构。因此,有三价动词参与的此类结构一般会采用普通话的平行说法。这种情况与赤城话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从动词的自主性来看,自主动词都可以进入此类结构,非自主动词在部分方言中可以进入此类结构,而湖南邵阳话、湖南洞口话、黑龙江齐齐哈尔话和吉林长春话中不能使用非自主动词。以邵阳话为例,如:
例40.邵阳话:感冒得溜③。(要感冒了。)
(二)情态意义与时体意义
从情态意义来看,与认识情态相比,各方言点中此结构更加倾向于表达道义情态,且这种情态表达与动词的自主性密切相关: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都可以进入此类结构的方言既可以表达认识情态,又可以表达道义情态,如山西大同话、河北赤城话、陕西永寿话、贵州兴义话和山东日照话。以贵州兴义话为例,如:
例41.这面墙塌得溜。(这面墙要塌了。)[认识情态][非自主动词]
例42.衣服小了,买得溜。(衣服小了,应该买了。)[道义情态][自主动词]
如果只有自主动词可以进入此类结构,非自主动词无法进入此类结构,那表达的情态意义就只有道义情态而没有认识情态,这也与唐正大对陕西永寿话的考察一致。类似的方言如湖南邵阳话、湖南洞口话、吉林长春话和黑龙江齐齐哈尔话等。以齐齐哈尔话为例,如:
例43.走的了。(该走了。)[道义情态][自主动词]
从时体意义来看,在所有参与调查的方言点中,此类结构都可以表达即将开始的意义,即将要做什么。只有在山西大同话、河北赤城话和陕西永寿话中,此结构还表示即将完成的意义。但在大同话和赤城话中此类结构表达即将完成的频率较低,而在陕西永寿话中频率较高,无其他标记,使用较为频繁④。
综上所述,在河北赤城话中,“(N)V的了”结构在语义上表现为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在语法构成和成句条件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在其他方言区也有类似的结构和语义特点,但在VP的类型、情态意义与时体意义方面又有所不同。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N)V的了”结构及相关结构体现了汉语各方言间的联系与区别。
注 释:
① 文中语料来自CCL语料库,BCC语料库以及笔者自省。
② 此语料使用频率较低或有些母方言者对这种说法不熟悉。
③ 此语料对于母方言者来说几乎不会使用或者语义不明。
④ 引自唐正大《关中方言的将来时间指称形式:兼谈时体情态的共生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