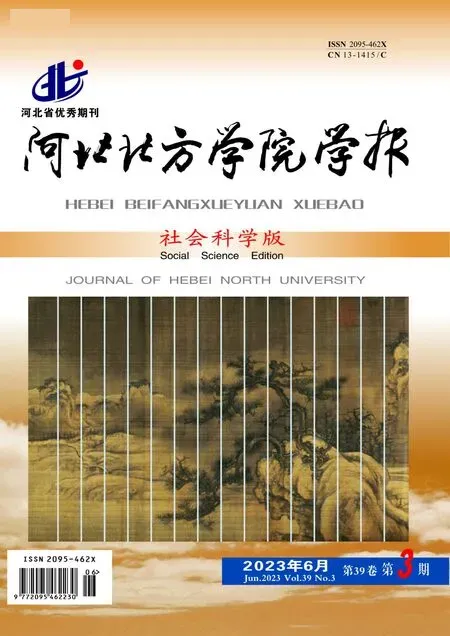试论中晚唐影占之弊与朝廷对策
林 张 兴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影占,又作隐占、影庇、影射或影复,是中晚唐时期规避税役的一种手段,以各阶层虚占人口或田地最为常见。关于中晚唐时期的影占之弊,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如陈仲安指出,影占群体的产生是负担不均的差科之弊所致。当时,各级官僚是法定的免役者,军人及专卖商人(官商)同样享有免役权。正是这些免役群体的存在导致富豪之家想方设法钻营,由此产生了所谓“影占”“伪冒”[1]。李春润在论述役纳课时提到,人户影庇于军政部门,由此逃避唐政府的差遣,仅向挂籍的各部门纳钱[2]。陈明光在列举职役的不同种类时指出,当时存在许多地主富豪借助经济力量以谋求职役的现象。同时,他们也凭借非法影占规避户内差役[3]。赵大旺则探讨了归义军的免役细节,认为服役人自身虽无需承担杂役,但无法影庇户内其他丁男,归义军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与中原地区的政策类似[4]。上述成果尽管已经注意到影占问题,但仅是对这一现象的宏观分析,未对影占进行细化梳理。鉴于中晚唐影占之弊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以及社会阶层秩序,国家的应对又关涉唐宋之际的制度变迁,故下文尝试对中晚唐影占之弊与朝廷对策进行梳理。
一、中晚唐时期影占的表现形式
两税在唐中后期的财政领域中属正税范畴,与租庸调制“按丁征收定额税”有所不同。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5]1351,即按土地面积征收谷物,按户等征收铜钱。关于役的规定,颁行诏令中有明确说明:“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6]3418按照两税法的设立初衷,税役负担本应有所下降。但从唐后期的史书记载判断,人们依然需要承担繁重的税收与差科。可见,利用影占手段与朝廷博弈并获得免役身份的行为在唐中后期盛行,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
(一)寄名军籍
唐代中期,府兵制逐渐败坏。为应对边境的战争,唐廷采取广泛的募兵制。与府兵不同,唐代中后期的职业兵被称为“食粮官健”,即依靠唐廷财政的供养,以宿卫征战为职业的群体。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田产,只能世代占籍从军,以食军粮谋生。《全唐文》中有记:“辕门委质,营垒分师,有役干戈,无由耕稼。况自天宝已后,屯兵七十余年,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7]705《新唐书》亦称:“悍卒顽夫开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于本业者也。”[5]3957可见,在唐中后期,军人群体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养兵费用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财政的重大开支。服役于唐廷的军人虽需承担戍卫或参战的义务,但由于其拥有规避税役的特权,这使得许多豪强大户寄希望于影占军籍,用以获得利益。此外,影庇于军籍还能使奸猾之人横行一方,这一现象在德宗初年已显露弊端:
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5]1323。
兴元年间,朝廷抬高神策军地位,其待遇有了显著提高,豪强便选择出资获取神策军的身份特权。因此,时至贞元年间,挂名军籍这一现象已然严重:“初,白志贞为神策都知兵马使,募禁兵东征,死亡者皆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8]7338神策军战死的军人并不上报,而通过收受富户的贿赂售卖军籍,这为寄名军籍的现象提供了温床。此现象持续到元和初年并未有所好转。如白居易在奏议中提到,新募之军“占旧额、张虚簿”[7]6838已是常态,如去虚取实,则损失20%~30%的兵额。招募的新兵占据着旧有的簿籍,究其根本,依然是源于影占行为背后的利益。军将通过虚张军籍获利,富户则通过向其行贿而获得规避税役的特权,逐渐形成上下相护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不仅侵蚀税基,也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动摇唐朝的统治根基。
(二)寄名官府
与寄名军籍类似,寄名官府在中晚唐也成为财政时弊之一:
文宗太和五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云:“应属诸使内外百官、度支、户部、盐铁、在城及诸监院,畿内并诸州监牧、公主邑司等将健所由等,准承前列,皆令先具,挟名敕牒,州府免本身色役。自艰难已后,事或因循,多无挟名,自补置,恣行影占,侵害平人。”[9]1781-1782
“艰难”指安史之乱。平乱后,唐廷的户籍管理能力下降,加之两税法以户籍与资产作为征税依据,导致文宗时期,影占现象发展到给财政和平民造成严重困扰的程度。富户豪强通过寄名于院司等政府机构规避本应承受的税役负担,从而将税负转嫁给普通百姓。到武宗朝,情况并未好转。以《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文》为例:“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多属仓场、盐院,以避征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以此富屋皆趋幸门,贫者偏当使役,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7]814唐后期,随着唐皇室物资需求增大,替宫廷采买的“茶油盐商人”身份随之提高,进而发展成可以规避税役的群体。此时,影占不再局限于获得官府公职和差役的身份,甚至开始通过影庇于特殊商人行列来获利。
唐前期存在“诈为杂任”的现象,严格意义上讲这亦属于影占范畴。“杂任”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受公家驱使而并无品级的群体,影庇于这一群体同样能起到规避国家正役的效果。因此,在唐律中设有专门打击此类现象的法律:“谓诈为杂任之类,而得复免役使者,徒一年。其见供作使,谓权充杂役,而诈自脱及知情脱之者,各杖六十。”[10]471在唐后期也有与杂任性质类似的“衙官”,可以帮助豪富规避税役。如《太平广记》记载:“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11]具体数目可能言过其实,然足以证明这一现象的泛滥。
(三)依傍豪族
如果说寄名军籍和寄名官府属于依附于朝廷势力之下,那么依傍豪族的影占人口便是将名籍寄于私家之门。豪富之家通过财力得以影占于官府或军籍,继而影庇所依附之人。如唐后期京畿诸县的太常乐人及和金吾角子,一门之内皆可规免朝廷差役[7]1814。准确地讲,依附豪族以求影庇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自唐中期以来均田制被败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被豪强侵夺土地的百姓仍未摆脱繁重的税役负担。因此,他们或是出于难离故土之情,或是饱受债台高筑之苦,只得选择留在原籍,依傍于豪族。史载:“(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8]9488豪强大户取得营田户资格,由此获取免役权,进而驱使没有田产的农民为其耕作。而这些被招揽而来的贫民则选择为豪强耕种,以此躲避官府催征。
不过相较于豪强大户的影占避税,影庇于豪族的百姓并未有负担减轻之感,生活状况甚至雪上加霜:“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5]136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唐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富户与贫下户的矛盾激化,国家财政的压力不减反增,只得将税收负担转移至尚未影占的百姓,从而形成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
二、中晚唐时期影占的弊端
安史之乱后,代宗朝掌控人口仅余1 600多万[12]1550。与开元和天宝年间相比[13],人口缩减了2/3。在人口锐减的形势下,如何保证财税的正常征收就成为唐后期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而影占则是唐后期财税体系运行之下的一个顽疾,其所带来的弊端对财政乃至社会经济都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一)纳税群体减少
唐中后期,豪强大户的影占行为导致“征税皆出下贫”[5]1361的现象愈发普遍。《资治通鉴》记载:“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民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8]7275两税法以大历年间税额最高的一年为定税依据[14]721,而受影占的困扰,唐廷实际能征税的人群大多局限于贫下户,如此一来,国家财政收入便难以保证。为不触动豪强富户的利益,各地官员只能选择在任职地区实行摊征:
近日已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今色役殷繁,不减旧数。既无正身可送,又遣邻保只承,转加流亡,日益艰弊[12]1565。
“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可。摊逃之弊,苛虐如斯。”[15]4437
由于实际承担税役的人数锐减,被摊征的百姓只能被迫承担成倍的税役压力。如此一来,纳税群体减少的趋势便更加难以控制。尽管朝野上下对摊逃之弊有目共睹,唐廷也屡屡下令禁止摊逃,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难免会出现强制摊征的现象,毕竟税役征派任务的完成情况与官员的赏罚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机制下,官员将农民逃欠税额强行摊征亲邻的做法便成为普遍现象,“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甿”[14]727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影占之弊未妥善解决,百姓担负税役之苦越发深重。因此,白居易在《观刈麦》中提到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16]4并非仅是文学的夸张,而是对广大贫下户真实生活的写照。当百姓无力负担税负之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贫富差距扩大
在经济生产能力有限的小农经济时代,一旦税负出现不均的情况,必将引起贫富差距增大的后果。由于有能力承担税役的富户往往选择影占规避税役,普通百姓反而成为承担重负的受害对象。加之影占带来的摊征,税负越发向贫苦百姓倾斜。元和时期,柳宗元奏称:“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15]832富豪勾结官吏转嫁赋税,出现“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的现象,导致唐中后期的贫富差距愈发拉大。
唐末,贫富差距问题在官员奏疏中依然有所体现。如杨夔上奏称:“富者称物产典贴,永绝差科。贫者以富籍挤排,助须从役。”富户与衣冠户互相勾结串通,致使赋役差科不均,出现“富者既党护有人,贫困者即窜匿无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资。嗟怨之人,因伤和气”[7]9075的状况。由于影占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因此晚唐贫富差距持续增大,社会矛盾已难以缓和。
(三)军队战力下降
影占不仅带来社会经济方面的危机,还对军事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早在代宗时期,这一弊病便已初露端倪:“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6]3457由于禁军多为挂籍之人,因此兵额不实,造成军队战力低下,不堪一击。在东有藩镇和西有吐蕃压境的形势下,唐军的内部情况又是如此,自然可以理解代宗和德宗御驾离京的无奈了。
到文宗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杜牧向皇帝所上《战论》一文指出:
夫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筑垒未乾,公囊已虚[7]7814。
寄名军籍现象的泛滥导致唐军对外难以抵御侵侮。到了晚唐,唐军战力已无力维持摇摇欲坠的国内局势,这给了饱受剥削的贫下户反抗的机会。史载:“广明元年十一月,巢陷东都。上发神策兵欲守潼关。时神策军士皆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马,任势使气,未尝更战阵。”[8]8358唐朝军队在黄巢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唐朝陷入风雨飘摇。
三、动荡时局下的朝廷对策
中晚唐对影占现象的重视不减。自德宗至宣宗朝,多位帝王都对影占现象及其带来的弊端非常重视,并通过诏敕或是赦文的方式对影占行为进行约束或打击。
(一)厘定军籍
影占是唐后期凸显的税役规避问题之一。为了打击寄名军籍以规避税役之举,无论出于军事角度或是财政角度,唐后期的君臣都在不断寻求应对手段。贞元十年(794),由于诸军影占编户的负面影响,京兆尹杨於陵建议“请致挟名,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6]4293。然而,该策仅限于个人建议,实际上并未付诸实施。至长庆元年(821),唐廷正式颁布限制之策:“其京兆府百姓属诸军诸使者,宜令各具挟名,敕下京兆府:一户之内,除已属军使余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并令京兆府明立籍簿,普同百姓一例差遣。”[12]1187-1188该敕文下令明立簿籍,将寄名军籍的人户纳入税役征派的范围内。但从后来杜牧向文宗所上的《战论》[17]650来看,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税役规避方式已形成较完整的利益链条。首先,对军将而言,可通过收取其中的代役金以牟利,代役金收取数额全凭掌兵者欲念之大小而定。其次,若挂籍的人数增长,军官便能支取更多衣粮,从而将支取财物中的“余赢”收入自己囊中,这成为诸军将官乐于外人挂籍的重要原因。到晚唐,权宦把持军权,更是将出卖军籍作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8]8358。而那些不在军籍之人,上至“恃其多藏”的富人,下至普通市井之人,都寄望于通过挂籍躲避征赋。各阶层皆有所得,形成两厢情愿的局面。因此,影庇于军队的现象屡禁不止。
(二)审定户籍
为解决影占所带来的税役不均问题,早在代宗朝便尝试通过禁止割贯改名和保证名籍一体来打击影占行为[12]1849。除了对户籍的规范化管理之外,元和之际,宪宗屡下诏书以调整各阶层的税负。元和十四年(819),唐廷先是针对赋役不均的现象下令每3年定一次户等,京兆与地方一例遵行[7]677。数月之后,宪宗再次颁诏,规定官员所购置的田产不得影占,须依法缴纳正额两税[9]5836。不仅是中央,在地方上,部分官员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影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南陵令崔祾以死刑相逼,核实该地豪强所应缴纳的税赋,使得南陵之人“莫敢隐匿”[7]6656。再如衡州刺史吕温查出隐藏的不输税户1万6 700户,使得“庶得下免偏苦”[7]6325。宪宗朝以后,中晚唐诸帝虽仍在尝试解决这一弊病,但由于朝廷对地方的管控进一步削弱,因此终究难以摆脱“征税皆出下贫”[5]1361的蠹政。
(三)整顿院司
对于影庇于院司或名属仓场的群体,唐廷也不断采取审查和裁减的措施进行管理。早在两税法之前,代宗朝的常衮便建议减省官府人员。对隶属于诸司诸使的人户,除确实所需人员保留名籍之外,朝廷可结合和雇的方式满足官府差遣的需求[7]4244。这一做法对影占具有一定的限制意义。但常衮在代宗朝任相较短,德宗继位后便被贬官外放,因而这一政策的后续执行受阻。这一建言虽在短期有所成效,但并未取得长远效果。故而至德宗朝,陆贽仍就这一问题上奏:“应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委御史大夫即与诸司诸使长官审商量,据见所掌事之闲剧,定额闻奏,仍挟名送中书门下,务宜减省。”[14]35宪宗同样尝试改善这一积弊,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敕:“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12]1294敕令虽有禁绝之意,然此举似未取得显著成效。因此,武宗时期对影占现象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强。武宗在《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继续对影占行为进行约束,该文严格规定诸使诸司不得影占,已影占在籍的人户解送回本县[7]817-818。但该措施是否有效落实,可参考宣宗时期的记载:“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5]1362-1363在收复河湟之地后,国家所收税费不增反减,失去近三成的财政收入。可见,这一举措成效并不显著。
(四)抑制豪强
豪强大户对税役的侵损引起中晚唐朝廷的重视。大历四年(769),代宗下令将寄田、寄庄及前资、励荫和寄住家一并征税,史称其“如晋宋土断之类”[13]107。此前,这些人户本是可以规免税役负担的群体,而此令实行之后,至少在法律上他们的特权已被依法褫夺。代宗之后的历朝皆对此问题非常重视。德宗初继位便委派清强官至各州府巡查,不允许酋豪或官吏侵扰百姓,如有闻奏予以严惩[18]583。这一敕书下达后,为德宗赢得了良好声誉。然而时过境迁,文宗朝的一封奏议却与德宗意愿相违背。大和五年(831),中书门下上奏称,豪强大户侵害平民,兼并土地,影占百姓。元和二年(807)、长庆元年(821)、宝历元年(825)以及大和三年(829)的多次敕令约禁影占,但相关院司皆不能有效执行[7]10033。可见,至少从宪宗到文宗4朝,唐中央政府在处理豪强鱼肉百姓方面都曾采取过措施以求厘革,但是似乎都以收效甚微收场。
根据史料记载,中晚唐只有在中央集权有所恢复和君主强势的时期,朝廷才能对影占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而君主荒僖和国家动荡之时,朝廷往往对此不甚重视,只在少数诏令中有所提及,且不重视执行效果。但即便是宪宗和武宗时期一度采取了强硬政策,实际结果也不甚理想,这与中晚唐中央集权被削弱有关。
虽说唐后期社会矛盾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影占始终是唐后期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子,这属于承担税役的人口数下降所带来的摊征难题。两税法对地方各级单位有税赋数额征派要求。一旦影占不附籍者日增,朝廷所规定的税额难以足额收取,便会带来无穷尽的摊征,进而拉大贫富差距。影占的富户坐享其成,贫民百姓终年劳作而难以果腹。唐后期虽然存在许多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员,在对税役方面的整顿中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任期时长有限,他们离任之际往往是豪强大户卷土重来之时。大多数地方官并不将民生视为头等要务,他们无休止地在辖区内摊派税役,甚至将一县之税摊及周围县城,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税役规避现象。总而言之,赋税的征收与王朝兴亡息息相关。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和朝政的腐败等一系列因素,影占之弊始终难以得到根治,其带来的财政困境也始终困扰着中晚唐的君臣,最终间接导致了王朝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