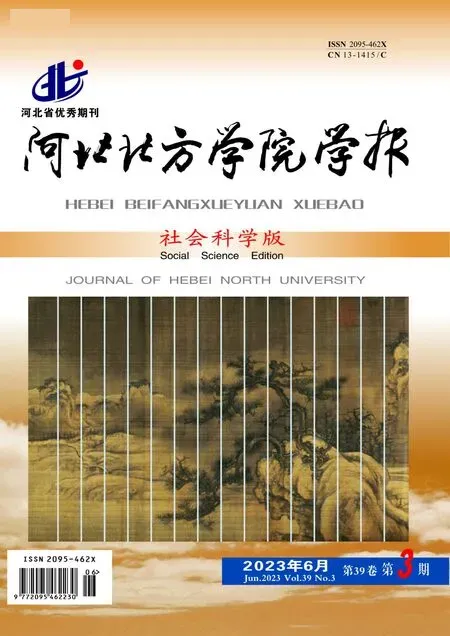论屈赋的双重空间及其关联艺术
米 国 春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空间是一种与时间相对的客观物质存在形式。文学空间是指摄入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包括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一方面,幻设空间不可能凭空生成,而是有一定的现实原型或映照;另一方面,文学中的现实空间也并不是对现实原原本本的复制,而是加入了诗人主观情思的艺术化的现实空间。屈原所创作的新诗体——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其辞采瑰丽、想象奇特、情感热烈且境界高远,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屈赋即屈原诗歌的总称,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和《招魂》。屈赋中既描写了真实的的现实空间,又营构了想象与神话传说中的幻设空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双重空间。
一、屈赋的双重空间
从写实性角度可以将屈赋中的空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实性的现实空间,如沅湘和江夏等。该类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且大多为诗人所亲身经历过的;另一类是非写实性的幻设空间,如昆仑和咸池等。该类空间具有极大的非现实性,多为神话或传说中的空间。此外,有些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之间界限并不清晰,需要一定的标准予以界定。
(一)现实空间
现实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空间,虽然在作品中浸润了诗人的情思,但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因素。据《史记》中的《屈原列传》和《楚世家》记载,屈原曾在郢都怀王和顷襄王身边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等职,也曾两次出使齐国,还曾被君主流放到汉北和江南,故其许多作品都是在流放之地完成的。沅水和湘水是楚国境内两条重要的河流,屈原曾长期被流放于沅湘之地。据《惜往日》载曰:“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因此,屈原的作品有大量以沅湘为中心的空间书写,如沅湘、苍梧、九嶷、江水、洞庭、涔阳、江皋、北渚、醴浦、芳洲、江皋、西澨、汀洲、极浦、南浦、江湘、枉陼、辰阳、溆浦、鄂渚和江南等。屈原还曾从郢都出发到达陵阳,并在《哀郢》中写道:“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其作品中有一些关于这段历程的空间书写,如鄂渚、江夏、故乡、国门、郢都、闾、夏首、龙门、夏浦、故都、州土、陵阳、郢路、修门和故居等。此外,屈赋中的现实空间还包括高丘、旧乡、空桑、九坑、九河、汉北、北山、江潭、北姑、嶓冢以及清江等。
(二)幻设空间
幻设空间是指想象中的空间,一般来源于神话或传说,具有较大的非现实性因素。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识”[1]2481,想象力丰富,因而他在作品中营构了一个宏大而奇诡的幻设空间。首先,屈赋中出现次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空间是昆仑。“昆仑”是中国神话中的名山,记载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和《列子》等典籍,且基本都具有神话色彩。“昆仑”在屈赋中共出现5次,如《悲回风》:“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以昆仑为中心,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地理空间如县圃、白水、阆风、天津、西极、流沙、赤水和不周等也都具有神话色彩。其次,屈赋中还有一系列与太阳神话有关的空间,如崦嵫、咸池、扶桑、若木、阳之阿、汤谷和蒙汜,大都是太阳的出入、升降和止息之地。再次,屈赋中还有一些与天及天帝有关的幻设空间,包括阊阖、春宫、瑶台、梁津、天门、帝郊和九天等,如《大司命》:“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最后,穷石、洧盘、九州、西极、龙堂和朱宫等也是屈赋中营构的幻设空间。
(三)现实空间与幻设空间的界定
“《离骚》中昆仑虽为神话中地名,但也反映了古人一定的地理观念和上古史的传说,是古人朦胧记忆的实录。”[2]神话也并不完全是虚构或凭空想象出来的产物,而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它保留了原始先民对自然与社会的古老记忆。屈赋中的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极其容易被混淆,甚至难以区别。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现实空间有非现实性的成分,幻设空间很大部分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由于古代不同典籍甚至同一典籍不同篇章之间对同一空间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分析判断,因此可以从宏观角度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对空间进行界定,即确定一个主要空间的属性,与之相关的空间就可被归为同类。如昆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出现,且绝大部分都具有神话色彩,故将昆仑界定为幻设空间比现实空间更合理,那么与昆仑相关的一些其他空间基本就属于幻设空间。此外,楚地多江河湖泽,屈赋中有大量关于水的描写。“浦”是水边的意思,含有“浦”字的就有极浦、醴浦、南浦、溆浦和夏浦等。对“南浦”一词,姜亮夫认为“《九歌》为现实之用,而后世为设想之词”[3],即南浦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屈原曾长期放逐于江南之野,其所到之地众多。以上带“浦”字的地理空间即便屈原不曾真正到达过,其也必定有所耳闻,故将以上带“浦”字的地理空间以及屈赋中一些写在沅湘地域的其它空间界定为现实空间比较妥当。众所周知,楚地巫文化盛行,祭祀活动频繁。“然南人以巫鬼祭祀之俗,擅声乐之天性。男女相逐,歌咏舞蹈于川谷之间,平原之野,造为美人香草之辞。”[4]其中,“川谷”和“平原之野”为现实中的祭祀场所。而《九歌》中出现的中洲、江皋、北渚、芳洲、汀洲、幽篁、原壄和平原等空间大多是与祭祀有关的场所,都应被视为现实空间。
二、屈赋双重空间的关联艺术
屈赋建构了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双重空间,且双重空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屈作在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关联和互渗上大有学问”[5]。屈赋建构了从现实空间转移到幻设空间、现实空间出现于幻设空间以及从幻设空间转移到现实空间3种空间模式,且每一种空间模式各有其特点和发生的契机。
(一)从现实空间转移到幻设空间
《怀沙》载曰:“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时世昏乱,小人专权,屈原等贤臣的主张不被采纳,现实中的艰难处境使他想将“美政”理想转到幻设空间。再加上屈原想象力丰富,在描写现实空间时也会将创作思维转移到幻设空间。如《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和“言己朝发帝舜之居,夕至县圃之上,受道圣王,而登神明之山”[6]20。屈原渡过沅湘之水来到舜帝所葬的苍梧之野,在现实空间向帝舜陈辞后,便驾着龙凤、掩着尘埃来到了神话中昆仑山的县圃之境。又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在经过巫咸降神和灵氛占卜后,屈原得到吉卦,于是他再一次从现实中的楚国出发,以瑶象为车,驾着飞龙来到了幻设中的昆仑仙境,想要遍览天下来为国君求取贤臣。再如《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和“屈原幽居草泽,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则愿命驾腾驰而往,不待侣偶也”[6]52。“江皋”为江边高地,“西澨”为江水西边,两者都是现实空间,屈原希望得到湘水之神的召唤,奉命前往神灵所居之地,进入幻设空间。《大司命》载曰:“君迴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屈原修履忠贞之行,而身放弃,将愬神明,陈己之怨结,故欲逾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6]54。“空桑”一词在《楚辞》中共出现两次,王逸在《大司命》中释为山名,在《大招》中释为楚地名。以此观之,“空桑”似为楚地一山,大概为祭祀司命之地。屈原想越过现实中的空桑山而追随大司命进入天门,向天帝陈诉冤情。《河伯》载曰:“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在黄河这一现实空间想象自己与水神河伯为友,同登西北昆仑神山,无拘无束,观望四方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与痛苦。
屈赋从现实空间转移到幻设空间,或随神灵而去,或神游进入到以昆仑为中心的幻设空间,可见昆仑在屈原心中的神圣地位。其原因在于昆仑是神仙所居之地,且为升入天庭拜见天帝的唯一通道。帝舜是现实中的帝王,屈原在现实中的苍梧之野向帝舜陈辞,但心中的忧愁与哀苦仍得不到排遣,于是他神游昆仑,想进一步向天帝陈辞。如《离骚》载曰:“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阊阖”为天门,“阍”是为天帝守门之人。帝舜为现实中的最高神,天帝是幻设中的最高神,屈原想进入天门向天帝陈辞,无奈却被拒之门外。由此可见,屈原在幻设空间和现实空间中的处境极为相似,都郁郁不得志。
(二)现实空间出现于幻设空间
在屈赋所营构的幻设空间中,不仅有神灵、异物和幻景,还有现实空间的存在。如《离骚》载曰:“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是楚国地名,“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虽去,意不能已,犹复顾念楚国无有贤臣,心为之悲而流涕也”[6]23。屈原渡过白水,登上阆风山,在神游中突然悲伤不已,哀叹楚国没有贤能之臣。《离骚》载曰:“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旧乡,指楚国也。此章言己周流天上,正欲西涉之际,忽因天光之赫曦,视见故国而不忍去也。”[7]屈原在皇天神游,想要“远逝以自疏”,但忽然看到了现实中的故乡楚国,因对其无比思念而不忍离去。《大司命》载曰:“吾与君兮斋速,导帝之兮九坑。”“坑,岗同。郢地志有九岗山,今在松滋县。”[8]“九坑”为现实中楚国的地名,屈原本和司命之神一起拜见天帝,并想引导天帝来到楚地并观察楚国政治得失。《河伯》载曰:“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极浦”也是楚国之地,昆仑山上多玉树和奇珍,屈原登上此神境流连忘返以至于到了日暮之时,但又想到楚国现实而不能释怀,惆怅忧思。《河伯》载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谓也。愿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归楚国也。”[6]62屈原同河伯游览其所居住的朱宫与龙堂后,想要回到现实,希望河伯送自己返回楚地。《招魂》载曰:“魂兮归来,入修门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魂兮归来哀江南。”“修门”即楚郢都的城门,“故居”是楚国代称,“江南”位于楚地。在《招魂》中,屈原反复陈说“修门”“故居”和“江南”这些楚国地名,希望魂灵能够从幻设空间返归到现实空间。
在屈赋中,现实空间出现于幻设空间大多发生于诗人在幻设空间中神游达到高潮或尾声时。如《离骚》“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和《河伯》“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表明诗人的忧愁与思念在幻设空间中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而这些出现于幻设空间的现实空间,如高丘、旧乡、九坑、南浦、修门、故居和江南等都为楚国之地,由此可以看出屈原深深的思君恋国之情。
(三)从幻设空间转移到现实空间
屈赋双重空间的关联不仅是从现实空间转移到幻设空间,还从幻设空间转移到现实空间。这不仅源于屈原丰富的想象力,还更便于他排遣愁思。如《云中君》载曰:“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云神从其住所驾龙车、披帝服,降临人间,又迅速从人间返回天上的住所,此处即为幻设空间中的云神来到现实空间。《湘君》载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湘夫人》载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此言帝子之神,降于北渚,来享其祀也。”[6]51《湘君》和《湘夫人》是一组祭祀湘水之神的诗,在诗的开端就写明湘水之神从幻设空间来到现实中的“中洲”和“北渚”享用祭祀。《湘君》载曰:“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此处既可理解为湘水之神享用完祭祀后驾飞龙辗转到达洞庭,也可理解为屈原想象自己驾飞龙从沅湘之地到达洞庭,都是从幻设空间到达现实空间。《九章》虽然具有很强的纪实性,但也有对幻设空间的营构。如《涉江》载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屈原与舜帝同游昆仑瑶圃,但想到国人不理解自己的贤明,于是决定第二日渡江湘而去,此处即为从幻设中的昆仑转移到现实中的江湘。
屈赋中从幻设空间到现实空间的转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屈原神游有关,即屈原或从想象中的幻设空间转移到现实空间,或想象自己跟随神灵转移到现实空间;一类与降神仪式有关,屈赋中有许多关于祭祀的描写,如《九歌》中描写了迎神、降神、享神和送神等祭祀仪式,《山鬼》中“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写的就是山鬼女神降临山上,这些描写都是从幻设空间到现实空间的转换。
三、屈赋双重空间关联的原因
屈赋中的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能互相发生关联,这和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巫文化浸润下的想象思维以及受上源性文献《诗经》的影响息息相关。
(一)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之情
屈赋所建构的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能发生关联,是因为有一条情感主线将两大空间相联接,这便是屈原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之情。他在君王身边任职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2481,是君王信任的股肱之臣;被君王流放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1]2485,仍眷恋和牵挂着国家和君王的安危。屈原的流放经历既是忧愁迷惘的四处流浪,更是九死不悔的爱国之旅。他在《惜诵》中写道:“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不论得志还是失志,屈原对国家和君王的眷恋与热爱始终没有改变,并将忠君爱国之情渗透在作品中。
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中的情感状态具有一致性,都浸润着作者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屈原在现实空间中被群小嫉妒、忌恨乃至谗毁,被君王怀疑、疏远乃至流放,其依循先贤、举贤任能和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因此,只能转移到幻设空间中,即通过在神界中远游和拜见天帝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在幻设空间中虽能够乘龙凤和掩尘埃,役使雷神和雨师,忧愁悲伤的心情似乎得到了纾解,但对现实中的君国始终不能忘怀,以至于现实中的楚国、楚都和楚地时时出现在其所营构的幻设空间中。又如《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屈原渡过白水,登上阆风,进入到昆仑神境,但却忽然想到楚国没有了贤能之臣,为此悲伤不已。
(二)巫文化浸润下的想象思维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9]作为荆楚大地孕育的文化产物,楚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10]楚地巫风盛行,多占卜、祭祀和巫术,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巫文化。巫文化极大影响了楚地诗人,进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巫术在想象中可支配神灵,并与神灵合二为一。巫术仪式也饱含着浓烈的情感因素,巫师通过想象或与神灵进行沟通,或幻化为神灵,或担任传达神意的使者,最终达到一种“迷狂”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降神、享神和送神这些巫术仪式都伴有想象的参与,而想象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来源。“文学靠想象和创作来激发和宣泄情感,巫术活动靠仪式和参与来激发和宣泄情感,两者极易产生共鸣,而想象是连接两者的桥梁。”[11]
屈原长期在楚国生活,其思维方式必然受到巫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想象。最典型的就是其在屈赋中将神灵与所在之地重新组合,营构了一个宏博广大、奇幻瑰丽且光怪陆离的幻设空间。如《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将原本属于黄河流域的洛水女神宓妃置于昆仑神境,表达了诗人对贤臣的渴求。诗人在山水之间纵横驰骋,辗转于月夜和白昼之间,片言之间即可转移万里,这便加强了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关联。屈赋中从沅湘转移到昆仑,从地面升入仙境,现实空间出现于幻设空间往往只是瞬间之事,思维具有极强的跳跃性。
(三)对《诗经》等文献的艺术接受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12]屈原所开创的楚辞这一新诗体打破了中国诗坛自《诗经》之后几百年的沉寂,并和《诗经》一同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学创作。楚庄王时,申叔时列举的教育楚国太子的科目就有《世》《书》《诗》《礼》和《乐》等。《诗经》作为楚辞的上源性文献,必定在形式、语言以及风格等方面影响了屈原的诗歌创作。“《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6]2王逸认为《离骚》采用了《诗经》中比和兴的手法,以此点明了楚辞与《诗经》的艺术渊源。《诗经》中有些篇目也出现了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并且双重空间之间发生了关联。如《泉水》第三章“出宿于干,饮饯于言”[13]652一句,“干”和“言”都是卫国地名,此处写的就是嫁到别国的卫国女子设想回到卫国的饮饯之处,表达了浓浓的思归之情。再如《豳风·东山》第二、三章都是想象之词: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
町畽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13]845-846。
诗人在第二章想象家中现时黯然凄凉的情景,第三章想象家中妻子想念自己归来的情形,表达了浓浓的思乡怀亲之情。还有广为流传的《蒹葭》一诗,其首章写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13]791。
该诗为诗人思恋并追求意中人不可得而作,开始以“蒹葭”起兴,奠定了全诗凄清和缥缈的基调。现实中的主人公追求想象中的伊人,这个伊人似近实远且虚无缥缈,处在幻设中的“水一方”,现实空间与幻设空间难以分辨,表现出作者惆怅的情思。
屈赋现实空间与幻设空间的关联也出于诗人对《诗经》的艺术接受。如《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诗人原本在“江皋”和“西澨”现实空间中行进,但听到湘水之神的召唤便腾驾而去,随神灵进入幻设空间。《大司命》“君迴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随着司命之神翱翔而来,诗人逾越空桑山,随司命之神进入幻设空间,想要拜见天帝来陈诉冤结。《诗经》中的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的区分还不是很明显,幻设空间多为想象中的现实空间,现实性成分比较突出。而屈赋则进一步发展了空间关联艺术,使现实空间与幻设空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界限,且幻设空间的非现实性更强。因此,相较于《诗经》,屈赋更加瑰丽奇谲,且双重空间之间的关联性也进一步加强。
屈原在继承《诗经》等上源性文献的基础上,并在楚地巫文化的浸润下创作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新诗体——楚辞。屈原的足迹遍及楚国的许多地方,因而作品中有大量现实空间的书写。此外,还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营构了瑰丽奇异的幻设空间,从而建构了现实空间和幻设空间,且都浸润着诗人的主体情思。双重空间的建构及其关联造就了屈赋高超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