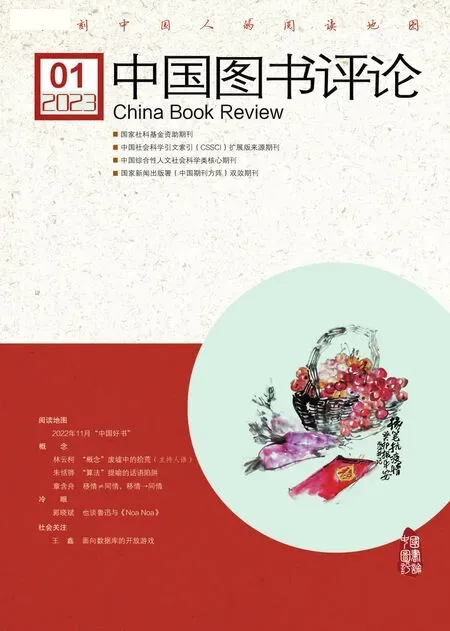也谈鲁迅与《Noa Noa》
——与袁洪权教授商榷
□郭晓斌
【导 读】袁洪权在《“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一文中,根据野苡一篇文章中的说法,认为鲁迅译《Noa Noa》曾出版过。袁文的这一结论值得商榷。野苡的书讯,其实主体内容是根据鲁迅的出版广告修改润饰而来的,性质与一般的出版广告无异。野苡文中的很多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正说明他并不了解“文艺连丛”。1936年10月才印出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附录的广告,确凿无疑地证实《Noa Noa》在鲁迅生前并未出版,可见野苡的说法确实只是广告之词,其实并不可靠。结合一些材料从常理来推断,也可以佐证《Noa Noa》未曾出版。
近来偶见袁洪权教授《“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一文(刊《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4期),读后不能苟同,觉得袁文的论证和结论颇有可以商榷之处,遂援笔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首先,袁教授认为,根据他发现的《铁报》上的一则文章所提相关细节,“可得出罗怃译《Noa Noa》已经出版的结论”[1]。但是文史考证的一个最基本的重要原则是“孤证不立”,故袁先生仅仅据此一点,便率尔得出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袁教授发现的所谓新材料,是发表于《铁报》1936年5月29日第2版的《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一文,作者署名“野苡”。袁教授说:“按照这篇文章的文字说明,包括《Noa Noa》译书的内容简介、书籍装帧、定价、印数等的细节描述,给人的印象是《Noa Noa》这本译书已经出版。承接引文所说‘已经出版的有’ ‘还有一本’等词句,笔者的判断倾向于认为,‘野苡’是见过《Noa Noa》这本译书(或者是熟知出版内情)才写下这些文字的。”[1]但细读这则文字,笔者认为所谓“内容简介、书籍装帧、定价、印数等的细节描述”,并不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和说服力。
这就不得不谈到“文艺连丛”本身。朱金顺、姜德明、陈建军、葛涛等先生都曾撰文谈及这一丛书的情况,所言甚详,兹不赘。按目前的普遍看法,“文艺连丛”实际出版的有三种,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坏孩子与别的奇闻》。在这三种书后,都附有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广告的文字内容,由于每种图书的出版进度不同等原因而有相应的适当调整。顺便指出,袁教授说鲁迅所拟的出版广告标题为《“文艺连丛”的过去和现在》,实际上是错误的。他并未查阅“文艺连丛”的三本书,甚至也没有查核《鲁迅全集》,而是轻信和照抄了葛涛《再谈鲁迅为“文艺连丛”撰写的出版广告》一文(刊《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的结论。葛文考证精细,但在提及标题时产生了笔误。葛涛照抄出版广告时,标题正确,但在文中提及这一标题时,大部分地方都写错了,以致文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所谓“过去和现在”,无论是在“文艺连丛”的每则出版广告中,还是在各个版本的《鲁迅全集》里,都作“开头和现在”。 “过去”,系“开头”之误。葛文给人以一种错觉,仿佛是《鲁迅全集》将其改为“过去”,实则并非如此,纯系笔误而已。此外,葛涛在梳理各版本《鲁迅全集》的标题时,说明亦有不准确之处。[2]
将鲁迅的出版广告与野苡的文章进行仔细比对,不难发现,野苡的这则类似于书讯的报道,其实正是以鲁迅的出版广告为蓝本,其主体内容是根据出版广告修改润饰而来的。将两文并置,即一目了然。
不妨先看《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中刊载的鲁迅撰写的广告[3]:
“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
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首先是印一种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就是“文艺连丛”。为什么“小”,这是能力的关系,现在没有法子想。但约定的编辑,是肯负责任的编辑;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总而言之:现在的意思是不坏的,就是想成为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现在正在校印的,还有:
2.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在其上。日本译有选集一册,所记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风俗习惯,译者曾选译数篇登《奔流》上,颇为读者所赞许。这是选集的全译。不日出书。
3.《Noa Noa》法国戈庚作,罗怃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画十二幅。现已付印。
本丛书每种印有道林纸本子三百本,较为耐久,而且美观,以供爱书家及图书馆等收藏之用。本数有限,购者从速。[4]
再看野苡的报道:
“文艺连丛”
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
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
“文艺连丛”,就是连续出版文艺丛书的意思,这“文艺连丛”出版社,由曹靖华等所组织,专出翻译书籍,介绍世界名著,为野草书屋发行。
“文艺连丛”所出版的书,大概与天马丛书相仿佛,集子印得很小,每本最多不过二三万字的样子。他们所出版的书籍,选择的标准,非常严格,务使读者化了三四毛钱买了一本书,而不可有所损失,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什么突破“×万部”的雄图,预备每本书籍只印数千本。
现在,已经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国的一般读者,大多数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写作的技巧与内容上,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鲁迅先生的译笔,忠实可靠,亦为我们所知道的。《死魂灵》的译笔,早已有口皆碑了。
还有一本是法因[国]戈庚作,罗怃译的《Noa Noa》,作者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画师,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切,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的是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这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岛山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翻译自然也靠得住。 《Noa Noa》中有木刻插画十二幅。
以上的两种的译本,为道林纸精印,颇美观,但每种仅有一千本,后购者恐难免有向隅之憾。
《山民牧唱》及《Noa Noa》定价低廉,无论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均有可观。在这投机之风弥漫了出版界的现在[,]“文艺连丛”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给读者的一个优越的贡献。[5]
为醒目起见,不妨将其中的重要文字摘出,比对如下:
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鲁迅)
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什么突破“×万部”的雄图,预备每本书籍只印数千本。(野苡)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鲁迅)
现在,已经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国的一般读者,大多数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写作的技巧与内容上,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野苡)
《Noa Noa》法国戈庚作,罗怃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画十二幅。(鲁迅)
还有一本是法因[国]戈庚作,罗怃译的《Noa Noa》,作者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画师,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切,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的是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这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岛山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翻译自然也靠得住。 《Noa Noa》中有木刻插画十二幅。(野苡)
由上可见,野苡文章的主体内容是参考出版广告,而非来自自己亲见其书后的阅读感受。尤其是内容介绍,有不少语句甚至一字未改,完全照搬。而且,正因为照搬,我们还可对校出袁教授并未发现的野苡的错字[6]——所谓“毒用”,系“毒害”之误。全文中唯一说明野苡可能见过原书的叙述,仅仅是“已经出版”四字,以及对纸张和印数的描述。
二
我们不妨继续追问。野苡是否有可能在未见原书的情况下,认为书已出版?答案是完全有可能。有不少人正是看到了出版广告中的“已付印”字样而以为书已出版的,袁教授在文中也谈及了这种情况。但其实,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仅仅是一种出书计划和预告,正如朱金顺先生所说:“在新文学书刊中,过去常有‘即日付印’‘现已付印’的话,但那是广告词,不能完全算数,连鲁迅先生也不例外。”[7]袁教授也说“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推销书籍的广告用语”,其实不必谨慎小心地说“倾向于”,因为这是完全可以考证清楚的事实。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最早出现于1933年3月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其中说《山民牧唱》 “现已付印”,但一年多以后的1934年7月,鲁迅在致韩白罗的信中仍然说:“《山民牧唱》尚不知何日出版,因为我译译放放,还未译成。”[8]这足可以证明朱先生所言不虚。
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野苡这篇文字本就是介绍新书的书讯,性质与出版广告无异。出版广告既然可以夸大其词,在书尚未出版之时即宣称“现已付印”,野苡自然也可以这样做——无论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关于纸张和印数的描述,亦可以作如是观。此前已出版的“文艺连丛”图书附录的广告里,本就明确说明每种书都会印一定数量的道林纸本,而且《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印数恰为一千册。依照丛书中已出的图书的情况,大体推断一下其他书的纸张和印数,并非难事,且不至于大谬,因丛书在这些方面会保持大体的一致。也就是说,所谓的纸张和印数不一定是实际情况,是算不得数,当不得真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野苡其实并不了解“文艺连丛”。事实上,并不存在他所谓的“‘文艺连丛’出版社”,更非“曹靖华等所组织”。“文艺连丛”实为鲁迅主编的丛书,而且该丛书名也并不是都由“野草书屋发行”。丛书中只有一种,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由野草书屋发行,其他两种则由上海联华书局发行。背后的出版者虽然都是原北新书局职工费慎祥,但是以不同的书局名义发行的。所谓“道林纸精印”,也不完全符合此前的出版预告和丛书的实际情况。此前出版的该丛书只有大约三百册是道林纸本,大部分是白报纸本,显然是考虑到不同阶层和身份的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所谓一千册都是道林纸本,恐怕是野苡自己比较随意的揣测,因这句话(“以上的两种的译本,为道林纸精印,颇美观,但每种仅有一千本,后购者恐难免有向隅之憾”)的口气,与一般的出版广告的推销口气毫无二致。其强调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实际的印数和纸张如何,而在于告诉读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鼓动读者去关注和购买。
要检验野苡是否见过《Noa Noa》,还有另一种方法,即看他所说的其他事情是否真实。按照其文章中的说法,“文艺连丛”已经出版的图书除《Noa Noa》之外,还有《山民牧唱》。如果他见过《Noa Noa》,那么也必定见过《山民牧唱》一书。然而,《山民牧唱》在鲁迅生前并未出单行本,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并无争议。1942年,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曾向许广平询问鲁迅“是否有未发表的或未完成的译稿”,许广平回答:“先生大病后,自以为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译稿,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译至第三章发表在刊物里,呈于读者之前时,先生已不及披览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时,曾译过西班牙巴罗哈作《山民牧唱》,陆续刊载于《译文》杂志,原计划不久出单行本。倘照日文译本看,还缺一篇未译,不知是未完成的呢,还是有意舍弃。”[9]话说得十分清楚,《山民牧唱》在鲁迅生前并未来得及出单行本。《鲁迅全集》增订多次,而对于出版广告中“《山民牧唱》”一词的注释,一直维持原来的说法:“中译单行本在鲁迅生前未出版。”[10]至于未出版的原因,因为鲁迅的出版预告中有“全译”的说法,故笔者更认同许广平的第一种猜测,即《钟的显灵》一篇还没来得及翻译,全书尚未译毕。朱金顺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斯人已逝后,《鲁迅全集》的出版提上日程,出版单行本已无太大必要, 《山民牧唱》遂纳入《鲁迅全集》第18卷,与读者见面。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后记》中,许广平明确说道:“其他未经付印,由先生编定辑录者,有《古小说钩沉》 《嵇康集》《山民牧唱》及《集外集拾遗》。”[11]她撰写的《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也明确将《山民牧唱》列入“所未印行之著译”。国家图书馆已在2014年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第二卷收入了《山民牧唱》。翻阅鲁迅的影印手稿,上面亦看不出任何与出版有关的标记。
《山民牧唱》既然在鲁迅生前从未出版,那么野苡并未亲见两书、仅据广告而撰文的可能性就更大,甚至可以说基本坐实了。
三
早在1933年, “文艺连丛”的第一种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就已出版,为何迟至1936年5月,野苡才撰写这一丛书的介绍文字?袁教授之所以认为野苡的说法可信度高,也正是由于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但其实,这个时间点恰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野苡并没有见过《Noa Noa》一书。
“文艺连丛”的第三种《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虽然于1935年“印造”,但到1936年才由上海联华书局发行。许广平在《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也将其列于“一九三六年”之下。查阅鲁迅日记、书信等资料,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确实在1935年9月15日就已编完此书,并写了《译者后记》,但迟至1936年7月26日,他才托内山完造将此书的纸型交给费慎祥。1936年10月17日,鲁迅在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记道:“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12]直到鲁迅去世前,他才见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样书。也就是说,1936年10月才印出的这本书附录的出版广告里,依然明确表示《Noa Noa》 《山民牧唱》两本书“正在校印中”“现已付印”“不日出书”,那么,5个月之前的1936年5月,野苡又怎么可能见到这两种并不存在的书?
所以,“文艺连丛”第一种书已推出两年后,野苡才撰文介绍,并不是因为此时该丛书真的有新书出版。这恐怕只能说明,野苡对文坛消息的关注和接受比较滞后。野苡在书讯中只谈《Noa Noa》 《山民牧唱》,避而不提“文艺连丛”已出的其他两种书,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显然是有意为之。已出的图书大家早有所知,此时在报纸上再炒冷饭已无意思,而《Noa Noa》 《山民牧唱》这两种将出而未出的书则系新品,他重点介绍,这则书讯也就带有了及时预告的新闻性和时效性。
查阅《铁报》上野苡发表的所有文字,不难发现,它们多是一些文坛书讯或作家介绍,但都不是什么独家秘闻,而且多有粗疏和错误之处。[13]他还撰写过一则关于鲁迅编苏联木刻版画集《拈花集》的书讯预告[14],而最终也只能停留于宣传式的预告,此书实际上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野苡的这则关于“文艺连丛”的报道,性质本也与一般的出版广告无异,系采集二手资料编写而成,并无珍贵而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实,即便从常理来推断,《Noa Noa》一书之未出版也是基本可以断定的。如果鲁迅进行了系统的翻译,而且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好友不会一无所知,鲁迅日记也不会毫无记述,翻译手稿更不会在许广平的眼皮底下离奇消失。许广平在《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不提,已说明鲁迅生前绝无系统翻译的可能,更不要说出版。从“文艺连丛”拟定的出版顺序而言,鲁迅先翻译的也应该是《山民牧唱》,而此书尚且没有译完,也就更谈不上翻译《Noa Noa》了。至于鲁迅未曾着手翻译《Noa Noa》的原因,除了时间上还未来得及之外,更主要的可能是鲁迅一直没找到更理想的可据以翻译的德文本。姜德明先生对此原因的阐释详细且合理[15],也可以作为此书并未出版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从方方面面来看,野苡的文章绝不能证明当时《Noa Noa》一书已经出版,他的话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可以说, 《Noa Noa》一书之未出版,已经确凿无疑,铁证如山。姜德明、朱金顺、陈建军等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笔者还想再附带说一下袁文中的两个小问题。袁教授说野苡不知“罗怃”是鲁迅的笔名,恐怕是误解了野苡的话。野苡说“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所谓“名字不很熟”,显然是针对普通读者而言,并非他自己,否则就不会有后面的转折和“一定知道”的表述了。野苡当然是自居于“熟悉文坛的读者”之列的。他的话也是对鲁迅的广告原文“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的一种转写和呼应。袁教授还说:“从全文的阅读来看,其对于‘文艺连丛’丛书的相关评价,还是显得比较客观而中肯(‘在这投机之风弥漫了出版界的现在,‘文艺连丛’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给读者的一个优越的贡献’)。”[16]但实际上,鲁迅撰写的广告中已有“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等语,野苡的话无非是对鲁迅广告的一种转述,是书讯的一种撰写套路而已。
袁教授在文末说:“借写这篇小文的机会,笔者也借此善意提醒一下研究界,不能看到一则材料就立即下判断、做结论,并以此自勉。”[16]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袁教授的这篇论文。
注释
[1]袁洪权.“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J].现代中文学刊,2022(4).
[2]1938年版《鲁迅全集》,此文标题并不是作“‘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文艺连丛”单排,“的开头和现在”另起一行,且前后各有一道竖线,即破折号。
[3]袁文引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中的出版广告,由于存在版本差异,并不适合对比。笔者引用的这一版本,即“文艺连丛”第一种图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附录的版本,才更可以看出野苡文章的材源以及它与出版广告的重叠度。
[4]鲁迅.“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A].不走正路的安得伦[M].上海:野草书屋,1933:73-74.(原书页码标注为“Ⅰ”“Ⅱ”)文中的书名和期刊名原加引号,现笔者改为书名号。
[5]野苡.“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N].铁报,1936-05-29.文中的书名原加引号,现笔者改为书名号。
[6]除此之外,袁教授在整理抄录野苡文章时,还存在多处问题。原刊本“画师”,误作“画家”;“人情风俗,神话等”,逗号误作顿号;“老大家的笔名”后,逗号误作句号;“法因戈庚”,袁教授直接校改为“法国”,而未保留原文并加以说明。
[7]朱金顺.试说鲁迅先生编的“文艺连丛”[A].新文学版本杂谈[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188.
[8]鲁迅.340727致韩白罗[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7.
[9]许广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A].许广平忆鲁迅[M].马蹄疾辑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153.
[10]《鲁迅全集》第7卷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5.
[11]许广平.编校后记[A].鲁迅全集(第20卷)[M].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653.
[12]鲁迅1936年10月17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7.
[13]野苡有一则报道《〈中国呼声〉:英文版的救国刊物鲁迅陶知行等都有作品发表》,刊于1936年5月21日的《铁报》。《中国呼声》曾刊载译成英文的鲁迅旧作《一件小事》,野苡却将英文回译成一个奇怪的新名字,称之为“一个小事件”,似乎误以为是新作。野苡另一则报道《“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板画兴味》(刊《铁报》1936年5月11日),说《引玉集》“到现在共销去,三版,计八百余本”,然而一个多月前,鲁迅在致曹白的信中已明确表示,此书“再版卖完后,不印三版了”。显然,此时再版本尚且没有销完。查周国伟编著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等资料,皆可证明此书只有初版本和再版本。
[14]参见野苡.“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板画兴味[N].铁报,1936-05-11.
[15]参见姜德明.鲁迅和戈庚的《诺亚·诺亚》[A].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59-266.
[16]袁洪权.“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J].现代中文学刊,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