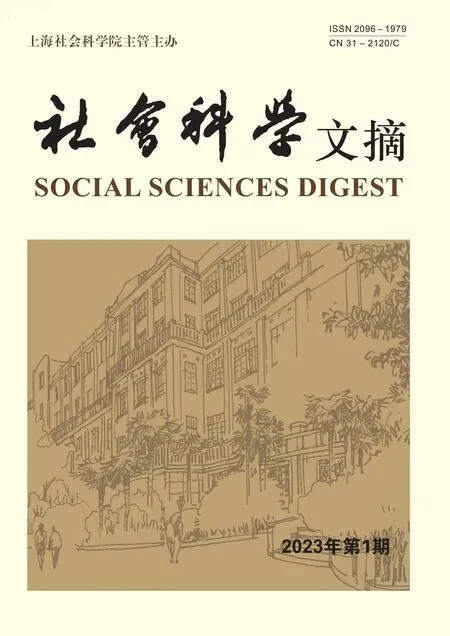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
文/卜宪群
史学体系是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综合体现,也是社会需要在史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客观反映。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要不同,史学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转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学说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推动了近代史学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转化。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这个古老的史学大国的史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史学体系发生了千古以来根本性的变化。郭沫若既是这两个转化的亲历者,又是实践者。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郭沫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也为今天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关于史学的性质、任务与指导思想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郭沫若对史学性质、任务与史学指导思想、史学学科、规划发展均有系统思考。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史学的性质是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是区分不同史学体系的关键。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将史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并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体系对史学性质的全新认识,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梁启超在历史观上最终还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并没有能够给中国近代史学体系奠定科学的理论。近代中国对史学性质的理解,以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实证派观点占据了主流,而真正开始构建科学的史学体系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的学科性质、架构、作用,以及史学与社会、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作了系统分析,构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于李大钊为革命牺牲较早,他的很多思考没有能够继续下去,而郭沫若继承了他的遗志,承担起这项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郭沫若对历史学的性质有着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1929年9月,他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所写的《自序》中说“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又说:“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1950年,他在《中国奴隶社会》一文中曾经指出:“旧的历史家对于历史的看法,认为历史是过去的,固定的,死的东西,或者把过去看成比现在还好。他们不知道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用新的历史观来看,‘历史’就等于‘发展’。”历史学的性质是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着的,历史学研究应当面向未来,这些都十分准确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本质 特点。
第二,关于历史学的任务。为人民研究历史、研究人民的历史、站在人民的立场研究历史,始终被郭沫若视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他强调他是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他认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认为“特别是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他写曹操、写王安石、写李自成、写李岩,观点未必都十分完美,但都是出于“人民本位”这一思想。特别是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不仅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了明朝灭亡与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也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避免骄傲自满的生动教材,要求全党学习,充分发挥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第三,关于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学科理论是学科体系的基石,只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学科体系方向的正确。郭沫若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确立的史学体系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郭沫若真诚信仰唯物史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翻译、研读过马恩《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重要著作,并将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阐释唯物史观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成中文,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郭沫若始终将社会形态研究作为观察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这已经是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经济基础”一词正是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观念。此外,他还在《奴隶制时代》一书的开篇中说:“中国历代的生产方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一直发展到现阶段,在今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这样的叙述贯穿在他很多论著中。
第四,关于历史学的学科规划。1949年前由于政治原因,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能登上讲坛,学科规划更无从谈起。1949年后不久的1954年,郭沫若不仅提出要加强研究汉民族史、少数民族史、亚洲各民族史和世界史,还提出要研究通史和专门史。他说:“我们在目前还得不到一部完整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精密的专史。”1959年,他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对通史、断代史、专业史、专题史以及历史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意见。关于通史,他指出:“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的。”关于断代史,他认为,断代史研究的根本不是看以不以朝代为段落,“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旧的方法是以朝代为段落,而新的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也就是把断代史放在五种社会形态演变中来研究。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既保留了断代史的传统方法,又赋予了断代史研究新的内涵,十分有新意。文章中他特别提到要重视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戏剧史、诗歌史、小说史、工艺史等专门史的研究,对“最近出现的崭新的事物”如工矿史、公社史研究也要重视,“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写好,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又指出,撰写这些工矿史、公社史的目的是“提供材料”,不能代替通史、专业史的研究,更不能与通史、专业史对立起来。这是十分有见地的看法。
关于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他认为应当扩大业务范围,应该“从文献中研究以前的历史”转而“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在研究的组织形式上,他“欢迎个人撰述”,但他更主张“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如果脱离任务,孤立地进行研究,是不容易搞出成绩来的”。实际上,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历史研究所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动的一批集体性质的大课题,如《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等,其成果不仅奠定了历史研究所近70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是任何不带偏见者都应该承认的事实。尤其是郭沫若对历史研究所工作性质与方向的界定,今天仍有深刻借鉴价值。
关于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史学体系建设除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外,还需要有自身的研究方法,有明确的研究方向,郭沫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过许多探讨。他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重视史料。众所周知,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前,他不仅广泛涉猎传世文献资料,也阅读了大量新发现整理的甲骨金石文献。在该书《自序》中,他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故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所谓“罗、王二家之业绩”指的就是罗振玉、王国维在史料学上的贡献。该书1954年的新版引言中,他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他还特别强调:“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959年,他在答《新建设》编辑部问而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有“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更加完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历史研究应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辨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他同时强调“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绝不能代替历史学”,那种“整理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二步是整理史料。整理史料时要分清主次,“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他特别强调“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不仅要重视文字资料,物质资料也要重视,“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东西,比文字记载还可靠”。第三步是运用史料。他认为如何运用史料“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但是他绝不主张以论带史,他指出:“固然,史料不能替代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我们很少在郭沫若的论著中看到单纯抽象谈理论,正是他践行这一原则的反映。郭沫若是最早科学阐释理论与史料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郭沫若的史学论著中,“二重证据法”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随处可见,因为新史料的发现,郭沫若多次修改自己的看法也是事实。有人说郭沫若是“史观派”,其实这个看法未必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也未必符合他的研究事实。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但历史学的方向并不只是追求史料,不能只是“知其然”,而是要“知其所以然”,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是历史学的真正目标。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进而指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明确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既反对以“国情的不同”拒绝承认中国历史与唯物史观所发现的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相吻合的错误观点,又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积极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郭沫若一生在历史学上的追求。正是秉持这种观点,郭沫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林甘泉、黄烈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谢保成撰写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等论著已经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这里不再一一 叙述。
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贡献当然远远不止以上内容。譬如说,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考证了史料中记载的殷周直接生产者的社会身份,首次提出了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说”。他从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考察社会制度的变迁,提出了划分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具体时间,即所谓“古史分期说”。他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断定为原始社会,并强调中国也经历了这一阶段,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演变的完整性。他科学区分了三代的“封建”与秦汉以后“封建社会”两个概念,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辨析清楚了“封建”的名与实问题。他既运用唯物史观歌颂劳动人民的活动,又认为不能盲目否定王朝体系,不能不写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坚持了历史研究应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既汲取中国传统史学考据学的精华,又十分重视批判借鉴西方学者的有益成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境界。郭沫若这些史学思想都极大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内涵。如果没有郭沫若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那么,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入,中国历史学也不可能在世界历史学界拥有今天的地位。
最后,我谈一点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杰出贡献,及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其实,如同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史学家,其史学精神总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散发出新的魅力,郭沫若也是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对新时代中国历史学提出要求,这就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郭沫若就是一位坚持唯物史观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学贯中西,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构建的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精神实质、内涵要求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今天仍然要认真学习,继承弘扬郭沫若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