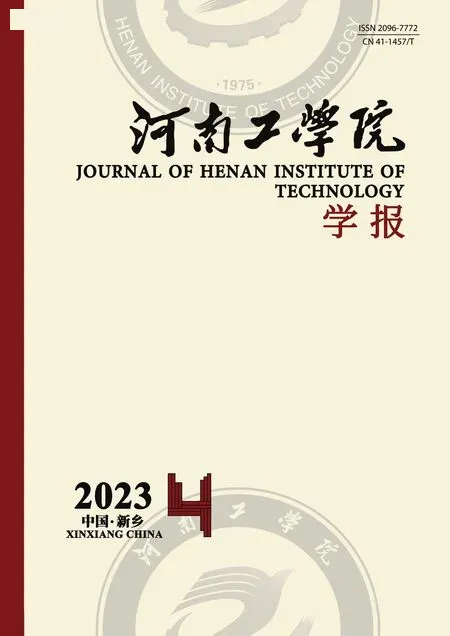自然人·社会人·觉醒者
——劳伦斯小说中的生态思想解读
李东君
(河南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生态批评起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础,对文学、艺术、文化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讨论、批评[1],具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的属性。在劳伦斯所处的时代,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前所未有的“机械化”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劳伦斯亲眼目睹家乡英国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由安宁恬适的小镇变成了煤矿开采地,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自己也深受环境污染之害,患上了肺病,在生命后期,他辗转欧洲各地,寻找理想中的栖居之地。特殊的成长环境、早期乡村生活的影响和辗转欧洲多年的经历,使劳伦斯对以矿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生活有着深刻的认知,这也引发了他对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他清醒地意识到,工业文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鲜活的情感关系,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这与生态批评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中,劳伦斯表现并批判了工业文明导致的人性“异化”,表达了他对自然和谐之美的向往,并提出只有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够实现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回归与重构。
1 人的最佳向度:自然人
早期的乡村生活,使劳伦斯享受了大自然带给他的和谐与宁静。劳伦斯认为人是自然的儿女,人只有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才能精神富足、充满活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是“自然”的人,表现出人的最佳向度——自然本性。劳伦斯在多部作品中都对多姿多彩、充满生机的大自然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热切向往。
在工业文明入侵之前,《虹》中布兰文家族世代居住的农场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景象。蓝天清澈,河流蜿蜒,草原丰茂,土地肥沃,小路上盛开着“黄花的水仙,在房子的两侧,是一些紫丁香、绣球花和女贞”[2]16;在这片农场上,布兰文家族世代过着朴实平静又有滋有味的生活。在这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
劳伦斯笔下的自然不仅仅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春天,“土壤打开它的垄沟接受他们种下的种子”[2]9,让人感觉到这循环往复的“生命的液汁在奔流”[2]8,等到秋天收获的时节,他们“无时不在地感觉到这土壤的脉搏和它的身体”[2]9。布兰文一家能感觉到“他们的血液中,在大地和天空、野兽和绿色的庄稼之中,有那么多的温暖、生殖力、痛苦和死亡,他们和所有这些东西有着那么频繁的交流和交往,因而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充实”[2]10。可见,劳伦斯笔下的大自然被赋予了主体性,花草树木、家禽牲畜都充满了生命的灵性,人在这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中得到了生命的传承和心灵的满足。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充分释放,人是“自然人”,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出自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用其解释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认为“栖居”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居住在某个地方”,而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栖居”意味着把事物保存在其本质之中。“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人作为“自然人”本真的生活方式:人是属于自然的,与自然同属于一个整体。这种观点重新定义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也是生态批评最核心的议题。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高度,把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是居住者,不是主宰者,这从根本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以“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去解释世界[3]69。“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人和社会所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认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只有各个部分和谐相处才能使人真正“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劳伦斯作品中描述的理想的自然生态世界是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解和表述,这与“生态中心主义”所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人不是自然中仅有的主体,自然与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及其存在的价值,“生态之美在于人、自然、社会这个有机整体系统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达到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4]。
2 人的异化向度:社会人
“异化”是指在外力作用下,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发生改变时,“人类整体或个体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5]。“异化”现象和“异化”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劳伦斯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也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这从本质上了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精神欢愉是一时的,而人与自然的隔离,则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出现扭曲和异化,使“自然人”异化为丧失自身内在价值的“社会人”。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异化”的工人和资本家,借用“社会人”形象表现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控诉了社会发展、生态失衡对人的“异化”。
2.1 工人的“异化”
劳伦斯认为工人“异化”为“社会人”是资本主义扩张导致阶级分化、对立的结果。工业文明使机械化代替了人力,但矿工的劳作却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成了变本加厉的强制性劳动。在资本家眼里,矿工就是物,是机器,是煤矿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就是机械地、被动地生产;在强制劳动下,矿工们面色苍白,像从煤矿中钻出来的怪物,成为“分解矿物的生物”[6]197。在这扭曲的世界中,矿工怎么能有真正的“自然”生活呢,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终日与冰冷无情的机器为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机械化工作。矿工们的“希望似乎已消失殆尽”[7]199,逐渐丧失了自然本性,散发出死亡的气息。他们受尽鄙弃也毫无反应,对自己的遭遇变得“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他们仿佛不是人类,而更像是毫无生机、四处游荡的“鬼魂”。在他们身上,人类的自然本性被戮杀了,他们只是“半个人”,毫无生机和活力的“灰色的半人”。如果深入剖析“灰色的半人”这个概念,不难发现所谓的“半人”是指失去自然本性,没有了自身的内在价值,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矿工们,而“灰色”则体现出矿工们绝望无助、空白虚无的情绪特征。处在工业文明社会底层的矿工不再是身心统一的“自然人”,人性也发生了分裂和扭曲,出现了“异化”,沦为丧失自身内在价值的“社会人”。
2.2 资本家的“异化”
劳伦斯对资本家的批判态度是坚决的,也是贯穿整个写作生涯的。劳伦斯小说中对资本家“异化”的描写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资本家既剥削工人,导致工人“异化”,同时自身也在“异化”。
资本家享受着工业文明社会带来的一切物质利益,并不断思考着如何能够将收益最大化。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接管了家族的煤矿,成为新一代的资本家,在畅想发展图景时,他认为要寻找一种自动化机器,让“地下无生命的物质从属于他的意志”,[7]273。他坚信架构在人类的意志和自然之间的机器才是“永恒的、完美的上帝”,而自己“便是机器的上帝”[7]273。杰拉尔德把矿工当成工具,将一个个包括矿工在内的“小工具”组成“一个巨大、完美的统一体”[7]273,打造这样的自动化机器才是他最重要的使命。杰拉尔德在追求物质欲望的过程中成为“机器的上帝”,但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变成了带着“假面具”、眼窝黑暗的“怪物”。他感到恐惧,但似乎对恐惧也不能做出反应,他对自己也无任何情感可言。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支配着工人和机器,自己在无形中也受到了机器的支配,成为更大的“奴隶”,自身也由主体变为客体,难逃被“异化”的命运,由“自然人”异化为“社会人”。
资本家的“异化”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3]15。“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在其指导下,人类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指责。劳伦斯作品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工业化的发展逐渐使人的主体意识膨胀,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敬之情被物质和权利的优越感代替,资本家把自己和工人、大地、自然割裂开来,认为自己是“机器的上帝”。资本家的这种认知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表现,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一切价值的尺度,工人、大地、自然在其眼中只有工具价值。资本家的征服对象从自然扩大到人类自身,人的“自然本性”被工业化的贪婪吞噬,发生了“异化”。异化的“社会人”割裂了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抛弃了自然之源的滋养,无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其最终命运只能是毁灭。劳伦斯为杰拉尔德安排的结局是冻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之中:一个被工业文明“异化”的资本家死在了大自然的怀抱中,这是作者对工业文明破坏自然、扭曲人性的讽刺和抨击。
3 自然本性的复归与升华:觉醒者
劳伦斯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会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精神生态的重重危机。同时,劳伦斯洞察到大自然强大的内在价值,坚信只有借助自然的力量,才能够拯救人类,实现人性的复归。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有一批在工业文明压榨下艰难生活、努力寻求生机的人,他们在“自然力量”的指引下,内在的强大“自我”意识被激发出来,实现了“自然本性”的复归,成为“觉醒者”。劳伦斯始终强调人要“发现自我,正视自我,完善自我”,而寻找“自我”也贯穿了劳伦斯的创作生涯,“觉醒者”自我反抗、自我觉醒、自我实现的过程与生态学理论中的“自我实现”有相似之处。挪威著名生态主义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使人真正成为人。奈斯认为,自我实现需要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即大我(Self)”[3]13-14。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不断认同的过程,当人达到“大我(Self)”阶段,便能在与之认同的自然物中找到自己。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就是劳伦斯塑造的寻找自我的“觉醒者”。她出身于一个有艺术氛围的家庭,本是个朝气蓬勃的女孩儿,和克利福德结婚后,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婚后不久,克利福德参战负伤,丧失了生育能力,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身煤炭开采事业,成为工业文明下“异化”的“社会人”。身体残缺的克利福德内心也被工业文明所侵蚀,变得扭曲。他借助权欲向康妮灌输传统思想,并以空洞无物、阴冷无情的婚姻生活来控制她的思想,试图把康妮变成听他指挥的“机器”,这使康妮感觉“真实的、充满活力的世界”离自己越来越远,生命失去了“自然本性”,越来越“空洞无物”。康妮的自我认知陷入了困境,她渴望得到重生,开始了自我反抗。为逃避现实生活,康妮来到了树林中,从最初把树林当作逃离现实生活的“避难所”,到逐渐感受到自然带给她“生命”的力量:树林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处处都是蓓蕾,处处都是生命的跳跃”。康妮在与自然的不断接触中,感受到了大自然带给她“有力的、向上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慰藉了康妮心中压抑的自我,自我意识开始萌芽。这时改变康妮命运的猎场看守人梅勒斯出场了,而梅勒斯正是劳伦斯小说中“自然人”的代表。康妮在与“自然人”的接触中,觉察出他身上有一股生命的活力,具有一种活生生的、没有被工业文明“异化”的力量。梅勒斯的柔情也让康妮的肉体和精神开始重新焕发生命力,灵魂深处开始发生震荡,已经消失的自然本性开始复苏觉醒。在大自然的滋养和“自然人”的感召下,康妮长期被压抑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了抚慰和满足,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感觉“体内生出另一个自己”,这个新的“自我”是一个完整的、更富有生机活力的全新的自我。最终,康妮选择远离被操纵的婚姻以及物欲横流的上等阶级社交圈,与梅勒斯一起在乡下开始全新的生活,实现了复归自然的“觉醒”,完成了“自我实现”,达到了身心合一的境界。
在劳伦斯笔下,“觉醒者”的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觉醒者”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朝气蓬勃、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自然,逐渐融入自我,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劳伦斯塑造的“觉醒者”追求自我,使人性得到解放和自由,精神和生命得到新生,这一过程和阿伦·奈斯提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相契合的。在奈斯看来人类的“自我实现”是一个在自然中形成和发展的、充分体现出人的潜能和主动性的过程,是自我从社会向自然延伸,人与自然不断认同的过程。生态学中的“自我实现”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将自我从个体延伸到了整个生态系统,这也是整个生态学理论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自我实现”从世界观的角度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人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人和自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自然是自我实现的土壤,使人达到身心与自然相一致的境界,人和自然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与我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共鸣。
概言之,在劳伦斯看来,处在“自然状态”的“自然人”是人性中最理想的状态,“社会人”是人类过度依赖工业文明、迷失自然本性的“异化”状态,“觉醒者”是人的自然本性觉醒复归后的状态[8]。劳伦斯通过对这三种人物群像的塑造,表达了他的生态思想:人和自然中普遍存在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人与自然形成有机整体,工业文明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的天然纽带,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不平衡的对立趋势,导致人类失去了活力,人性发生了异化。劳伦斯认为,在工业文明中受到压抑和趋向“异化”的自我,如能重回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就能实现“觉醒”,恢复自然本性。他热切呼唤人类回归自然,呼唤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平衡关系。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思想,重新认识自然的主体性,对唤醒世人对自然的生态保护意识,用心去感悟生态与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陈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