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西域水道记》地图编绘理念探析
滑 铎 吴轶群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地图作为文化的产物,不仅是表述地理要素最直接的工具,也是绘制者对所选空间信息的结构性再现,体现着个人的观念。 马克·蒙莫尼尔认为:“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它只是一种中介。 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1]即地图作为一种中介,体现着人们对地理地貌的主观认知与再现,“这些‘主观’内容,来源于绘制者的目的与所处的时代、文化、政治背景等,而这些才是古代舆图真正的史料价值之所在。”[2]《西域水道记》作为道光年间徐松编纂的水利专书,前人研究集中于对文本内容的探讨和版本的整理,鲜有关注地图本身①。 本文通过《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地图反映的地理要素,参考清时期新疆的地图、方志与徐松及其周围交游者的著述、书信等文献,探讨地图背后的编绘理念,在解读清人对西北地理的认知上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嘉道时期新疆方志地图的绘制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一、经世与考据并重的治学观念
中国古地图重视实用性,在河道治理、经学研究等社会活动中具有广泛的作用。[3]徐松在《西域水道记》自序中直言“耕牧所资,守捉所扼,襟带形势,厥赖导川,乃综众流,条而次之”,业已表明以水道为核心著书绘图的目的,正是因为河流关系农业生产与军事安全,与边疆治理息息相关,而下文所写的“虽城郭之已改,考川流之实同”,则表明着其对于考据的重视。[4]
经世致用讲求务当世之务,《西域水道记》地图中对嘉道年间西北政事的展现即徐松关心时局的显例。 十九世纪前后,青海蒙古诸部因受藏族各部的侵扰向北迁徙,清廷屡派大臣查办案件,时任陕甘总督的长龄与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也多次“筹酌剿抚机宜”以安定地方,[5]徐松在《西域水道记》稿本“罗布淖尔重源图”中即展现了这一时期青海的蒙藏纠纷。②该图图名虽为“罗布淖尔重源图”,但地图绘制的主题并非河源,而是侧重于表现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间西宁与其周边的营堡、关隘,以及住牧河湟地区的蒙、藏各部分布情况。③此时蒙藏纠纷日益加剧,留至黄河南岸的蒙古诸部仅有4 旗,黄河北岸则有25 旗,[6]与《西域水道记》地图所绘基本一致。 此外,徐松在戍期间曾参与办理孜牙墩事件,不仅文中记载有相关经过,在“罗布淖尔所受水弟二图”中也标识有与事件密切相关的地点与部落。 孜牙墩所藏匿的“伪塔克山”在此前新疆地图中并未被标注,徐松将其与此事件密切相关的希布察克布鲁特、冲巴噶什布鲁特二部均绘入图中,尽可能地反映了西北的新情况。 而地图与现实政事之间联系的背后,不仅源于徐松对其蒙师左眉“讲求治天下之事”这一经世理念的继承,[7]也是嘉道时期现实社会对学术经世的新要求。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在政策上重视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屯点与水渠也为徐松绘入图中,传达着其经世理念以及对边疆开发的关心。 在《西域水道记》稿本地图中,徐松以“田”字图符突出标识乌什屯区、喀喇沙尔屯区和伊犁屯区中屯点的方位。 稿本“罗布淖尔所受水弟三图”中毕底河南标有耕种“五千亩”的宝兴、充裕、丰盈三个屯点,其原本有“八千亩”,[8]嘉庆四年(1799)因乌什仓贮粮食增多,乌什办事大臣乌尔图纳逊奏请“裁撤屯田兵丁一百五十名”,[9]将“所出空地请交回子耕种”并免征赋税,[10]反映着嘉庆初年新疆已出现裁撤兵屯的情形。 在稿本“罗布淖尔所受水弟七图”中除标识耕种有“六千四十亩”的头工、二工、三工三处屯点方位,[11]也标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喀喇沙尔派遣官兵教习土尔扈特和硕特等种地”时所开垦的田地,[12]反映着游牧部落从事农耕的情形。 此外,稿本“巴尔喀什淖尔所受水弟一图”中标识有自嘉庆七年(1802)以来松筠主持加种的锡伯正黄旗田、惠宁城北镶白正蓝旗田、惠远城东镶白旗田三处旗屯与乾隆二十八年(1763)商民张尚义垦种的商屯稻田,但刻本地图中并未标识。④同时,徐松也关注于巴尔楚克与伊犁附近水渠的修建,将其标识于图中。 如“罗布淖尔所受水图弟三图”中巴尔楚克附近绘有嘉庆五年(1800)所浚的“支渠”,徐松又于文中提出“玛拉尔巴什庄北数十里,即乌兰乌苏所经,若开新渠以达于庄,迭相灌输,有事半功倍之利”的建议,[13]与道光十二年(1832)壁昌所呈“毛拉巴什、赛克三一带荒地,地高水低,必须设法疏通水道”的奏议一致。[14]在壁昌呈奏后又经过两年的水利建设,“原属荒地”的巴尔楚克屯田“垦种二万余亩,已于本年升科纳粮”,[15]开垦地亩数量可观,成效显著,也可见徐松对于新疆水利开发的远见卓识。 文中关于新疆水利的记载还包括喀什噶尔、库尔喀喇乌苏等处的渠道,但并非所有的水利建设都能有所成效,嘉庆十九年(1814)松筠欲引玛纳斯湖水灌溉鱼窝铺田地,但“渠成,水不流”,最终作罢。[16]此外,地图中也反映着清时期新疆的生态环境,稿本“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图”中乌鲁木齐至奎屯北部绘有大量密集单线示意苇湖,所绘头屯河、塔西河、和尔郭斯河、安济哈雅河皆流入此处而止,体现了当时天山北麓潜水溢出带上普遍存在“苇湖”的地貌。
中国自古即有“左图右史”的治学传统,《西域水道记》地图中对考据的重视一方面源于地图在传统考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与新疆地图本就侧重表现历史内容相关。 徐松在遣戍伊犁前即强调地图对于治学的重要性,在《唐两京城坊考》序中写到“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书中也以《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17]在戍期间受伊犁将军松筠所嘱修撰《新疆识略》,其中也有写到“考证地理,非图绘不明”,[18]不仅南北各城均附有地图,在“新疆总图”中也附注《汉书》地名,以援古证今。 同时,从目前留存于世的西域地图来看,自宋代至清代中期的地图内容“主要绘制的是曾经在西域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对当时的现实地理情况只给予了极少的关注。”[19]《西域水道记》成书于道光年间,此时新疆地图虽已重视表现现实地理,但其中也不乏有对历史内容的示意,而徐松在地图中对于古河道与遗迹的绘制也有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
徐松在利用地图考证西域古河道与遗迹时以目验相佐证,具有实地考察与文献考索相结合的特征。 《水经注》为清代地理著述考据的重点,《西域水道记》仿《水经注》体例著书,其中也不乏有对这本“圣经贤传”的考订,并通过所附地图来反映古今河道之异。 在“罗布淖尔所受水弟五图”中徐松以黑色单线示意《水经注》中的“东川水”“西川水”,结合实地踏勘考证二河即为“头道、二道、三道河”与“渭干河”,并在图中注记“水经注云,东南流水分为三,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水经注云,右会西川支水注入东川水”。[20]同时该图以矩形方框标识“古龟兹城”,方框留有四处缺口以示意城门,但其遗址方位被徐松移至库车城南,并形变放大,并不符合古城的现实方位与规模。 徐松以此形式绘制的目的则是为了反映《水经注》中龟兹东川在龟兹城中“入自城东,出自城南,与西川未入河之左一支会”的河道走向而有意为之。[21]在“哈喇淖尔所受水图”中,徐松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今三道沟东里许有枯河宽百许丈,两岸有冲突形变”,推测该处为苏勒河故道,[22]并以黑色单线示意。 此外,“四十里城”“旧沙州”“苦峪城”等遗址也被徐松标于图中,并在文中逐一考证,以使文献记载与现实地理相互印证。
二、大一统的政治内涵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至清朝被赋予新内涵的同时,也被更加深入地付诸实践。 而《西域水道记》地图将新疆地区置于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与传统文化中,则是清朝继承和发展“大一统”观念的具体表现。
《西域水道记》地图既是清廷将新疆纳入版图的具体象征,同时也直观地展现了清廷对新疆的治理成效。 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序中即写道“西域二万里既隶版图”,[23]“版图”一词本就具有疆域的象征,“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24]徐松在描绘地理景观时已然将新疆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徐松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必然受到乾隆时期西域战功与“一统无外”观念的深刻影响,其地图在彰显清廷昄章式廓的同时,也描绘着清廷统一西域的功绩。 如徐松在实地踏勘时,途经班弟与鄂容安殉节之地乌兰库图勒岭,他“策马留连,怆焉悲楚”,作《经伊犁双烈殉节地有感》一诗,[25]并将此地绘于图中。 而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其他重要的军事地点,如明瑞追击大小和卓的和什库珠克岭,兆惠与阿睦尔撒纳余部交战的库陇奎山,追擒达瓦齐的格登山等,也均被绘入地图中,在回顾大一统历史进程的背后,正是徐松对其“权利、责任和感情” 的表达。[26]平定天山南北后,清廷确立军政合一、以军统政的行政管理制度,并在以边养边的政策下兴屯田、修水利,《西域水道记》地图中即展现了乾嘉时期清廷对西北疆域的治理与开发。 徐松以统一有序的体例与分类方式绘制新疆地理景观,标注图符具有一致性,聚落、军台、屯点等人文地理要素分别以矩形、圆形、田字形等图符示意。其中既有较为齐备的军台、营塘、卡伦、驿站等军政设施,也标识有乌什、伊犁等地的屯点与渠道等,将伊犁将军治下的各民族及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纳入大一统的疆域内,展现了新疆统一后在军府制下清廷对新疆的有效治理。
《西域水道记》地图中对新疆各民族的标识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体现着各民族对疆域的共同开拓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对于“南路之回子”,徐松认为其“类属服役,皆以编氓,固不得谓之外夷也”,地图中所绘回庄图符形状、大小同各大臣驻扎城镇与州县一致,均为矩形,被划归为一类。[27]对于布鲁特等部,徐松将其视为清朝屏藩,并在图中标识大致方位。 而对边外诸部如安集延等,则认为“虽贸易时通,而荒远僻陋,又非边防所急”,因此并未将其绘入图中。[28]徐松对清朝所属各部及藩属的不同关系采用不同的地图示意方式,既达到为治疆地方官员提供地理知识和民情的“守边之要,首要熟悉夷情”之目的,[29]也展现了新疆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面貌。 随着清代新疆地区的民族迁徙流动,中原地区的民间文化与新疆原有的地方文化相互交融发展,徐松在地图中也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 龙王庙在新疆治水兴农中具有重要地位,徐松图中所绘龙王庙包括叶儿羌东部“乾隆四十年二年办事大臣高璞捐盖”的龙神祠,[30]以及安西州北部的龙王庙,此外图中还标识有叶儿羌附近的显佑寺与哈密北部的帝君庙、石佛寺。 而文中所记载的寺、庙、祠等建筑则不止图中所绘5 处,还包括沙雅尔东部的礼拜寺、叶儿羌南部的显忠祠、巴尔库勒南山中的壮缪祠等。 寺、庙、祠等建筑在《西域水道记》地图中的广泛分布不仅体现着“事神治民,吏之职也”,同时也是乾嘉时期新疆社会多民族文化交互融合后的结果。
地图的形变通常体现着绘制者的观念,《西域水道记》地图中雅璊雅尔河与哈喇库勒湖的形变,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源伏流说”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藉此将中原与西域以黄河为纽带连结为一体,体现着文化上的大一统。 “重源伏流说”源于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山海经》,认为黄河的源头分别为葱岭河和于阗河,自罗布泊伏流于地下,东至积石山而出。 乾隆时期清廷在对黄河河源勘察后,依然遵循“重源伏流说”的观点,并以文字和地图的形式宣扬黄河河源位于新疆,如同平定天山南北后的立碑纪功,一并作为清代大一统的重要象征。 徐松在“罗布淖尔重源图”中,标明星宿海上游即阿弥达等人所探明的黄河河源阿勒坦郭勒,并以喀什噶尔河为黄河“最远之初源”,哈喇库勒与雅璊雅尔河为其上游,[31]将乾隆帝钦定的“重源伏流说”实际应用于地图中。 徐松实地考察后虽然认为雅璊雅尔河“自疏渠以来,灌溉浸广,水至雅普尔古庄东,涓流每断,所谓水不给用也”,并未注入喀什噶尔河,[32]但在“罗布淖尔所受水第二图”中所绘二河依然相连,图文并不相符。 地图中雅璊雅尔河的形变即徐松秉持“重源伏流说”的观点所致,以使地图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政治认同相呼应。 后世虽已有更正这一信息,但仍有较多的地图与文献将雅璊雅尔河作为河源,认为其“得龙池真源,容纳众流,洋洋千馀里,虽未能达于北河北源,亦西域一大川也”,其“自应仍列为北河一源”,[33]至宣统年间《新疆全省舆地图》中所绘的雅璊雅尔河仍是汇入喀什噶尔河,也可见“重源伏流说”的影响深远。 此外,徐松考证雅璊雅尔河、哈喇库勒即唐代的波谜罗川与大龙池,并将地图中哈喇库勒湖形变放大,以对应《大唐西域记》中所载的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34]藉此以彰显汉唐与清朝政治的连续性。
三、融会中西的思想意识
《西域水道记》成书于清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也处于传统地图学接轨西方地图学的时期,其地图虽以传统绘图法绘制,但业已受“西法”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的影响而有所嬗变。 正如邓廷桢所称赞的“又况中西法备,分野不爽毫厘”,[35]虽有溢美之嫌,但确实具备中西特征。
徐松在图中既采用计里画方以便于对距离的直观展现,同时也参酌中国传统地图定位的多向性,依据不同的分类原则与观察视角对其所绘西域地理进行再现,体现着其因地制宜的观念。《西域水道记》中所附的19 幅地图均以“每方百里”示意距离,对于流域面积较小的水系,徐松选择将其图幅放大,例如“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图”以每方五十里绘制,对应胡渭“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36]兼具量度作用。同时,《西域水道记》地图的方向并不一致,单幅地图的方向均为上北下南,组图则以河流右岸为上。 单幅地图的方向是徐松在伊犁受松筠“图幅方向皆以南为上,以敬协辅座向明之义”的观念影响所致,[37]而在松筠主持编纂的《西藏图说》与《西陲总统事略》中所附地图也均为上南下北,以“缘取拱极之义也”,[38]表示尊君之意。 此外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写道“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其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以坐阅多向明也”,[39]其中也应当有便于案牍资政之意。 但徐松并未完全受此观念的限制,在组图中,即8幅“罗布淖尔所受水图”、3 幅“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图”、5 幅“宰桑淖尔所受水图”与稿本中的2幅“罗布淖尔重源图”,因地制宜的按河流流向,自右向左绘制,以便于翻阅使用。 以河流右岸为上绘制地图在水系水利图中较为常见,如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黄河源图”,[40]乾隆时期《黄运湖河全图》中的“海口并二套图”也均为自右向左,[41]按河流流向绘制。 此外,在地理要素的标识上《西域水道记》继承了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图式符号,相较于此前清代新疆地图注重写景和绘画技巧的表达,徐松将图幅简化绘制,使地图的属性得到增强。
徐松重视《永乐大典》中的地图,在《西域水道记》校补中多次援引《经世大典图》,而张穆也正是在徐松的建议下抄录该图。 校补中记载“《经世大典》久佚,其西北地图一篇,载《永乐大典》元字韵,《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即据此图为之。 今所引皆称《经世大典图》,以从其朔”,[42]又在考证叶儿羌与吐鲁番两地时援引《经世大典图》,[43][44]可见徐松对于不同类型地图的参考。 此前认为徐松所参考的《元经世大典图》为张穆抄录,并将其作为校补内容的时间依据。[45]但实际情况应该是张穆从徐松处得到此图的信息,而后受徐松影响将其抄录,并不能作为时间依据,原因有三:其一,就徐松生平而言,其遣戍前后均从事《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且一直关注于其中的地图。 徐松于嘉庆十四年(1809)入全唐文馆“奉诏纂辑唐文”,[46]期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图》等作,在《唐两京城坊考》中也多次以“永乐大典载太极宫东宫图”等考证唐长安城。[47]释还后在任京官期间,徐松不仅在与汪远孙的书信中关注《永乐大典》的辑佚情况,“惟近日许珊林偶窥《永乐大典》狱字韵,即得宋元人判一种,现拟刊行”,[48]道光二十年(1840)又亲自抄录大典中《宋次道洛阳志图》并“藏于好学为福之斋”,[49]既可以看出其辑录《永乐大典》时间之久,也可以看出其对于大典中地图的重视。 其二,就张穆生平而言,其难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且开始辑录大典佚书的时间较晚。 《永乐大典》于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而张穆于道光十九年(1839)应考顺天乡试时因夹带纸条而“不复得应试”,[50]一生未有功名,难以接触到《永乐大典》。 同时,史广超认为张穆“辑《大典》中佚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51]并不如徐松开始辑佚的时间早。 其三,就张穆与徐松二人往来的书信而言,张穆是受到徐松的影响而开始辑录《永乐大典》中的佚书,《经世大典图》也是在徐松的建议下所抄录的。 徐松在致张穆的函札中写到“日来曾得暇钞书否? 大典目四册送阅。 夏字韵实有西夏五卷,望急检之。 梦想几于不成寐也。 《江东十鉴》不知有传钞本否? 字数不多,钞出为妙。”[52]其中的“大典目四册”为张穆参与辑刻的《连筠簃丛书》所收录,从二人书信来看“大典目四册”应得自于徐松,并且徐松在信中又建议张穆辑录《永乐大典》中的西夏五卷与江东十鉴。 在另一封寄给张穆的信件中,徐松写到“《经世大典西北图》纵不甚精,亦人间未有之奇,亟宜录之”,[53]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徐松已看过此图,而且认为该图具有一定的价值,而张穆此时仍尚未抄录,正是在徐松的影响下,这幅地图被张穆抄录并起名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 因此这幅图应当经历了徐松发现,而后建议张穆抄录,最后由张穆赠予魏源,并被刻入《海国图志》的过程。 而从此图的辑录与刊刻过程,也可以一窥西北史地作为当时的一门显学在士人间的交流情况。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西域水道记》地图采用传统绘法,文中则记载地物的经纬度以补充地图在信息示意方面的不足。 从经度上看,《西域水道记》刻本与《乾隆内府舆图》皆以1°为中央经线,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源关系。 《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经纬度的记载并不相同,为对比其差异性,下表选取二者文中所共载的山川、政区及聚落共40 个地点,分别以稿本中所载某一地经纬度值减去刻本中同一地经纬度值,得出相应差值,如表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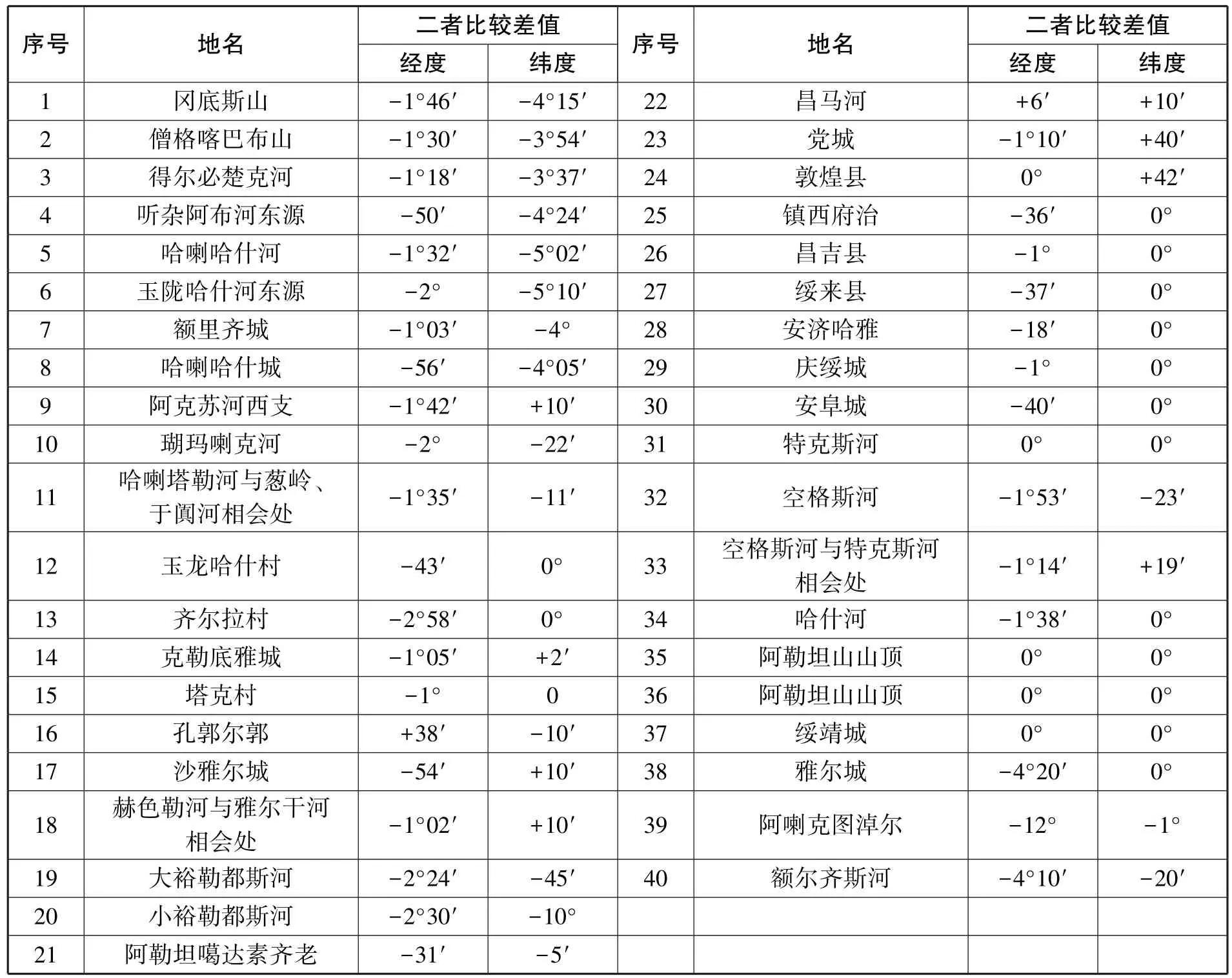
表1 《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经纬度差值
其中稿本与刻本中所载的绥靖城均沿用《西域图志》的经纬度,特克斯河与阿勒坦山山顶、山尾均沿用《水道提纲》的经纬度,因而没有变化。其余36 个地点稿本与刻本的经度平均差值为1°41′5″,其中经度差值为负的占91.67%,稿本经纬度多取自《西域图志》“晷度”,[54]《西域图志》所未载之处则以《河源纪略》与《水道提纲》补充,三者中央经线皆为0°,而刻本中所载经度普遍较稿本高1°,其原因当是以中央经线为1°,与《乾隆内府舆图》一致。 此外,刻本卷一的纬度平均较稿本高4°18′23″,徐松的修改并未使其更为精确,且与卷二所载内容相矛盾,当为作者所误。 而徐松重绘地图的原因也并非是山川、聚落经纬度的修改和补充,其图中地理要素的方位与稿本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且刻本卷一所载纬度与实际纬度相差较远,反而是稿本更为精确。
徐松释还归京后确实藏有《乾隆内府舆图》,并将其用于《西域水道记》中考证西北史地与地图绘制。 沈垚在初次面见徐松时即“见先生所藏乾隆十三排舆图”,[55]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以十三排图考订蒙古各部,并记载“徐星伯太守藏有内府十三排图”,[56]而汪士铎也认“星伯之精确以此图贵也”。[57]《西域水道记》中虽未明确指明参考此图,但卷四中记载“巴尔喀什之东北千余里有慈谟斯夸淖尔,慈谟斯夸之西北九千里有额纳噶淖尔”,与《乾隆内府舆图》中所标识的巴尔喀什淖尔、惹谟斯夸鄂谟、额纳噶鄂谟的方位基本一致。[58]魏源在致徐松的信函中曾询问上述地名的出处,而从《海国图志》中“据乾隆十三排舆图,塔尔巴哈台之西有巴尔噶什泊,又西千余里有慈谟斯夸泊,又西北九千余里又额纳噶泊”的记载,可以得知魏源已获悉此处记载正是源于《乾隆内府舆图》。[59]在地图的绘制上,《乾隆内府舆图》与《西域水道记》所绘的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以及巴尔喀什湖、罗布泊等地相似度较高,徐松应当有参考前者绘制。 二者图中所绘额尔齐斯河水系形态与河流走向基本一致,乌伦古河水系皆呈现为U 形,河流名称与周边聚落的重合度较高,如图1 所示。 略有不同的是徐松图中斋桑湖被形变放大并略去附近部分河道,斋桑湖与乌伦古湖之间河流分布密度与《乾隆内府舆图》相比较低。 同时,二者所绘巴尔喀什湖湖泊形状相似,且湖中皆绘制有山;刻本地图与《乾隆内府舆图》所绘罗布淖尔相仿,稿本地图中罗布淖尔下方湖泊也与《乾隆内府舆图》所绘湖泊相似,显示了两种地图在以上区域的同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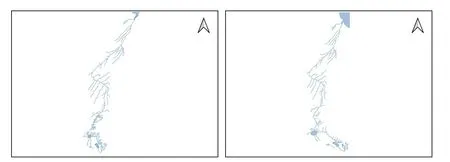
图1 《乾隆内府舆图》与《西域水道记》中的额尔齐斯河水系与乌伦古河水系
结语
《西域水道记》地图在直观展现嘉道时期新疆地理景观的同时,其所蕴含的编绘理念业已反映在图中地理要素的分布与相互关系之中。 首先,徐松身处乾嘉朴学向经世学问转型的阶段,因而既重视地图的现势性,饱含对新疆农业与水利的现实关怀,同时也有兼顾地图的考据作用。其次,《西域水道记》地图在疆域、民族、文化等方面与现实空间的政治认同相呼应,体现着大一统的政治内涵。 最后,徐松对中西方法绘制的地图兼有借鉴,在绘图方法上继承中国传统地图学,重视《永乐大典》中的地图,同时也参考西法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并在文中记载地物的经纬度以补充地图在信息示意方面的不足。
地图的功能体现在知识、观念的汇聚与传授,《西域水道记》作为清代新疆方志地图,注重归纳和总结,对于新疆水系的划分在新疆地图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私修刻本地图,其价值不仅是对西域地理知识的整理与补充,更重要的是在刊刻后流传于世的作用,对后来《皇朝一统天下舆图》《新疆图志》等一系列的地图和书籍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关于《西域水道记》文本内容的研究主要有:秦佩珩.《西域水道记》简疏——罗布淖尔和哈喇淖尔水源的初步追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4-11;冯锡时. 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2):59-72;朱玉麒. 清代西域地理中的吐鲁番——以《西域水道记》为中心[A]. 殷晴主编. 吐鲁番学新论[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747-756;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J]. 敦煌研究,2010(5):92-98;朱玉麒.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42-298;李军.徐松敦煌考察说献疑[J].文献,2016(3):160-171;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D].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李军. 徐松西域调查行踪稽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4):184-196。 关于《西域水道记》版本的研究主要有:周振鹤.早稻田大学所藏《西域水道记》修订本[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86-95;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J].文献,2004(1)172-194;朱玉麒. 《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A]. 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83-404;朱玉麒. 《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J]. 西域研究,2010(3)76-80;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4-241.
②此本地图具体参见(清)徐松著《西域水道记》,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善本书号:03869。
③图中袭爵时间最晚的是台吉索诺木旺吉勒(索诺木旺济勒),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台吉吉克济扎卜(济克济札布)之子车伯克多尔济于道光元年(1821)袭爵,但图中仅绘制吉克济扎卜而并未绘制其子,因此该图表现的时间为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
④稿本“巴尔喀什淖尔所受水弟一图”中仅标识屯点图符,并未标注文字,比照《西域水道记》与《新疆识略》所载内容与地图,可知为以上四处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