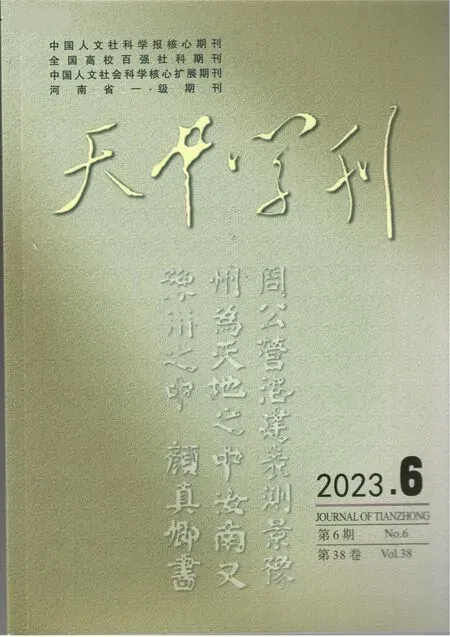“以明”与“两行”——《庄子》帝王形象的建构基础与理想形态
吴铭慧
“以明”与“两行”——《庄子》帝王形象的建构基础与理想形态
吴铭慧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明王是庄子理想中的帝王形象。庄子以政治视角为切入点,以帝王个体存在为落脚点,反对帝王用“非人”方式劳形怵心地以知治理天下。庄子认为,帝王应以无为方式使世间万物自齐而达于“明王之治”,以实现安闲境界为理想目标、“胜物而不伤”为旨归。明是虚静无执的生命境界,庄子主张用“以明”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以达到“两行”并立并质的状态,在肉体上既不伤己亦不伤人,在精神上不被名所伤,使个体存续更合乎人的本然状态。对明王的解析,从新视角深入考察庄子哲学的内蕴,有助于我们洞察庄子全身远害、轻松自然的生命态度。
庄子;《应帝王》;明王;帝王形象
关于政治问题是不是庄子关注的重要对象,学界仍有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庄子》未谈及政治。如闻一多在论《大宗师》篇时提出:“‘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宁得为庄子语?”[1]他认为庄子并未谈及政治问题,因而否定了“圣人之用兵”一句出自庄子。也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问题是庄子关注的重点,并对庄子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2]45–52。庄子从不同立场出发,为复杂的社会角色寻找最佳存在方式,故在内七篇中谈及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政治为其中之一。从《大宗师》《人间世》等篇来看,庄子谈论的政治问题并非国家政治建构,其重心在于关注政治环境中个体的生命状态。《应帝王》篇即是政治视角下对帝王生命存续问题的集中讨论,若将关注重心放在治理天下的方式上,则偏离了《庄子》内七篇的整体论述思路。庄子将明王作为理想中的帝王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王之治”的政治观。那么何为明王,庄子为何提出“明王之治”的政治观,其与儒家政治观有何异同以及表达了庄子怎样的生命态度,这是《庄子》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些问题也是理解庄子哲学的重要途径。
一、何为明王
庄子在《应帝王》篇中提出明王概念,但并未正面描述其内涵: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3]301–303
在此,庄子通过阳子居与老聃的对话,从正反两方面描述了心中的帝王形象。阳子居所谓行动果决、鉴物洞彻、疏通明敏、学道专心勤奋的形象是儒家帝王,而老聃认为欲学为儒家帝王之道,便会劳形怵心,致身心受损。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仅是自然优势就会使自身受到侵害,如虎豹因毛色美丽而招致众多猎人围捕,猕猴因跳跃敏捷、狗因捕物迅猛而招致绳索拘缚,何况劳形怵心地学为帝王之道以治天下呢?这均不是庄子所谓的明王。通过老聃对“明王之治”的描述可见,庄子的明王观与《逍遥游》中的无功、无名、无己相类。在自我认知层面,明王虽功盖天下,却不以之为功;在社会交往层面,明王并非以天下万物为教化对象,而是使万物各居其所、各自欢喜;在精神境界层面,明王“立乎不测”,即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游于无有者”的灵魂自由。概而言之,明王是行动上的无为、思想上的无己、个体上的无功、社会上的无名,即庄子所谓至人、神人、圣人的形象与境界。
庄子的明王意涵与儒家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二者对“知”的迥异态度。儒家提倡学道不倦以增长聪明才智,物彻疏明而治理国家,庄子对此不以为然。《应帝王》开篇即有“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3]293的故事,啮缺因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大喜,认为自身之“知”超越了王倪之“不知”,然而蒲衣子的回答却与啮缺的期待完全相反: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3]293
蒲衣子先以“而乃今知之乎”的反问,否定了啮缺之“知”,而后通过有虞氏“未始出于非人”和泰氏“未始入于非人”两种人生状态的效果对比阐明原因。在此,庄子提出“非人”的概念,即以他人为非,或者非难他人。有虞氏以仁义得到拥戴,且以自我之标准治理他人,庄子称此为“非人”;泰氏以己为马为牛,安闲适意且悠然自得,反而进入了与“非人”相反的、物我一体的生命状态。在此状态中,个体在认知上获得了齐物我、无是非纷争的指引观念,在心灵上获得了天真自然的舒适感受。庄子对两种不同生命状态的比较,意在说明“知”的学习与接受使个体生命劳苦,以“知”令他人正而后行,伤己伤人。
在“肩吾见狂接舆”的寓言故事中,庄子强化了“非人”对主体造成的伤害。“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3]296经式义度是学为“知”后产生的秩序框架,“非人”便是以此约束他人,达到使他人不得不听从且为之改变的效果。然而,庄子立刻否定此行为,并借狂接舆之口表示此“非人”行为是欺德的表现:“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3]297飞鸟、鼷鼠尚且知晓躲避祸患、趋利避害,何况人呢?他以“曾二虫之无知”表明用“知”非人,将使人生归于焦虑与危殆,其效果则是“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均是徒劳而无功的。
“非人”和明王是两个紧密联系且相互对立的范畴。“知”为“非人”的前提,以“知”处世即有高下之分,这便远离了齐物我的状态,故啮缺因比王倪有“知”而自喜是非必要的。因此,欲达到明王状态,须摒弃“非人”的态度与行为,以“立乎不测”的方式治理天下。
“不测”并非深不可测之意,而是以无为保持原有状态,不以“知”教化治理他人。庄子以季咸、壶子与列子的故事说明了“立乎不测”的原因与效果。神巫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所预卜的日期都准确应验,似乎若神人一般无事不晓。他以全部智慧四测壶子,却无一准确,只能仓皇而逃。在此,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构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关系和过程,庄子意在说明任何“知”在面对世界本真与大道之时都是苍白无力的,这即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最终表现。因此,“不测”他人,便可达到舒适自得、远离是非的状态。向壶子学道的列子明了此道理后,放弃所学且自以为未始学,归家后“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3]312。他抛弃所学,放弃“知”之后,在认知上获得了时间无长短、物我无区别、世事无亲疏的感受。此时一切复归自然,他固守此态,将齐物我状态作为人生选择,不再追求深不可测的“知”,仅是寻求平淡自然的人生,从一而终。此故事说明,个体苦心焦虑、学道治人是徒劳而无效的。此处,列子是不是帝王身份的隐喻,暂且不知,但此故事无疑是对“立乎不测”方式与效果的生动诠释。
而后,庄子用“混沌之死”的故事说明了以“知”治理天下的严重后果。部分研究者认为,此故事与全篇关系甚疏,甚至安置欠妥,如许地山认为这个故事是“窜入底章节”[4],然梳理此则故事与全篇的关系便可明了庄子用意。倏与忽因混沌曾待之甚善而欲报混沌之德,他们认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而混沌独无有,便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混沌之死则为“知”之死。他们抱持善意,欲使混沌更加聪慧,然不仅未达预期之效果,反而导致相反结果。从《应帝王》全篇来看,混沌之死所表达之意与行文主旨联系紧密,同时也是季咸、壶子、列子故事主旨的有力支撑。
帝王以“立乎不测”的方式治理天下,在精神上便达到了“游于无有者”的自由状态。庄子在“天根游于殷阳”的寓言故事中对此状态有具体描述: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298–301
庄子认为帝王不需为治世而烦忧。作为帝王,应以出于六极之外、处于圹埌之野、游于逍遥之宇的安闲境界作为最高的理想与追求,而非被职责限制。帝王处于无所挂碍、清静无为的状态,天下也就自然而治了。游是主体状态,治为客观效果,一切事物自然地存在,表明了庄子“以天下人自治的方式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观念”[2]45。
从《应帝王》来看,不劳形怵心地以“非人”和“知”的方式治理天下,而以逍遥为理想目标,以“立乎不测”“顺物自然”的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任其自齐,即为庄子心中的明王形象。
二、何为明
庄子以明王为理想目标,那么,何为明,明从何而来,在其观念中,明与虚密不可分。
庄子在不同篇章中对虚的状态有不同表述。他在《人间世》中言:“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3]152“心斋”即心灵的虚静,亦即获道的状态。其实,“心斋”亦是《大宗师》中“外天下”“外物”和“外生”后的“撄宁”,“忘仁义”“忘礼乐”后的“坐忘”,是《逍遥游》中“无功”“无名”后的“无己”,这均是无待于己的虚静的获道状态。在此状态中,主体忘记自我,世间万物都与主体无关。
其中,达于“撄宁”的“外天下”“外物”和“外生”、达于“坐忘”的“忘仁义”“忘礼乐”以及达于“无己”的“无功”“无名”都是获道的前阶段,这在庄子哲学中被称为“损”的工夫,“外”“忘”“无”的过程即是“损”的过程,亦即修道的过程,修道须以工夫剥除外在欲望。个体通过“损”的工夫将外在欲望摒弃之后,便达到了虚静的状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类被不同层面的物欲执着所裹挟,“损”即是丢弃对生命无用且有害的欲望,是对个体生命一切外在事物的遗弃过程。个体生命在破除社会价值观念限制的基础上,放下对自我生命的执着,最终使生命主体达到真正的无执。此无执是就个体而言的,具体表现为在个体内心虚明时,对自身与外界均无所欲求。
个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进入虚静状态后,忘记肉体与认知,心境通达明亮,获得“朝彻”“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的永恒感受。庄子在《人间世》中道:“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3]155“虚室生白”的意义与过程应如元人陈高所言:“室也者,心也;虚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无所不照也。心无物累则静,静极而明,道之所在也。”[5]白以虚生,维许乃明。达到虚静后,个体内心空明,心境瞬时觉悟明亮起来,因而有“吉祥止止”“坐驰”的闲逸舒适感受,此为庄子追求的至高美妙境界。毕竟“有碍则不虚,不虚则灵明不通”[6],无执则无碍,只有去除有碍,达于无执,个体才能拥有灵明通达之感。“朝彻”描绘了达到明的状态后个体心境的变化,即像太阳初生,大地立刻明朗;亦如人之心境茅塞顿开,生命主体因无执而忘怀生死、感到永恒。
以此,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以明”与“两行”两个因果概念,用“以明”即虚静无执的态度观照万事万物,使世界达到“两行”的状态。在社会中,人们因观念与立场不同,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正如庄子所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3]61–62庄子承认“成心”与是非的客观存在,也认识到“成心”与是非是由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正如学者所言,“从万物互殊的本然到异名对举的不齐,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的介入”[7],有“成心”的主体在认知方面存在区别与是非,从而造成了世界之不齐。而人之“成心”和是非的表达是通过言说实现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3]57从用言语表达“成心”开始,生命主体之间就会逐渐产生区分,并最终导致人们陷入是非争端之中而无法自拔。个体是非标准的不同会引起“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现象,分歧自然就产生了。而作为主体的人的局限性又使其不能够挣脱是非与争端。庄子在此提出解决方案,即“莫若以明”[3]68,用“以明”的态度对待社会中的成心与是非。
“明”在构字上为日与月的组合,“以明”即道如太阳、月亮普照大地般照人于天,在日月的普照下,万物无区别、无优劣、无高低。“以明”是道的超然态度,生命主体以此态度处于人世间,在面对世界中的成心与是非时,便具有了包容性与超越性,世界便会达到“两行”。庄子道:“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3]76“两行”即并行之意,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即回归个体与世界之本然。“两行”并非去除“成心”与是非,而是在万物并行之下,生命主体虽有自身的是非标准,却不以此标准非他人之是非。这样各种“成心”、是非均有存在的权利与可能性,却又互不干扰。故而庄子主张用“以明”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最终达到“两行”效果,万物一任自然,互不干涉,两不相伤。
“两行”结果的延伸便是“天均”与“天倪”。庄子曰:“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3]942“均”“倪”为圆与空之意,“莫得其伦”即不能对其进行分类与切割,庄子取其意,并从一人之事推广至天下万事万物。他认为每一物均是一个种类,万物以不同形式相禅,通过物化实现彼此的相互转化,从而达到始卒若环的效果,即人类社会像圆环一样循环旋转,无始无终,是为“天均”。另外,庄子以薪火相传的故事再次阐释此道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3]135生命如同薪火,个体生命必然消失,但生命整体不会消失,个体生命有限,生命整体无穷,且可无限制延续。生命是没有终点、立场和是非的圆环。所以,“损”掉自我执着,以明的态度与万物并处,经由曼衍便可穷年,生命便得以轻松自在地延续。
综上,“明”有两个方面,即个体的虚静空明和对待万事万物的“明”的态度。个体通过“损”的工夫使自身达到“心斋”“坐忘”“无己”的虚静无执的获道境界,便会有瞬间明朗的豁然。用“以明”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达到“两行”,个体与万物均回归本然状态,各不相伤。作为主体的人,我们既是“融入世界的言说者和外在事物秩序的建构者”,又是“疏离外在的沉默者和既有秩序的解构者”[7],只有忘记自我的主体性,才能破除对自我生命的执着,达到精神的逍遥。与《应帝王》篇相联系,帝王以“以明”的态度自处与治理国家,便可达于明王状态。
三、胜物而不伤:明王之旨归
在《应帝王》篇中,庄子主张帝王沿袭“无己”“心斋”“坐忘”的虚静无执境界,藏天下于天下,保持生命舒适,任万物自齐,此为明的生命态度和“胜物而不伤”的生命状态。
而由明到“胜物而不伤”是修道的过程与结果,正如庄子所言:“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3]313在此过程中,个体以“用心若镜”的态度面对万事万物,“损”掉无为的智慧聪明,复归于自然,不被名、谋、事、知所羁绊,最终达到“体尽无穷,而游无朕”的空明无执,自身亦不受损害。镜子本身需要借助光线反映物象,否则一切均处于黑暗之中。自身的空明是为光线,明亮后映射他物,此即用“以明”的态度对待他物,万事万物都毫无隐藏地反映在镜子当中了。
庄子以镜子映射事物原貌的道理进一步说明了“以明”处世态度的特征及其对生命的思考。其所言“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亦是《大宗师》中所谓的“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3]258。以镜子似的态度审视世界,万事万物都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既不互相屈就,亦不主动迎合,万物各得其所、各不相伤。此即“胜物而不伤”,是“两行”的结果。
另外,“胜物而不伤”包含两个层面:不伤己与不伤物。此两层面均得到保证后,生命才会“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3]229,这是庄子理想中生命完结的最佳路径。不过,这只达到了庄子在肉体层面的要求。在庄子的观念中,不仅肉体生命需要保全与安顿,精神也不能受到危害。他在《养生主》中提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3]121的观点,刑是对肉身的伤害,而名则是对精神的损伤,远离刑与名,生命诸体才能远离伤害。庄子提出帝王以余事治理天下,可达到肉体不受伤的目的。他在“明王之治”中亦提到有所成亦不以之为功,不追逐名利便不会因此而受到侵害。
再则,“胜物而不伤”是有次序存在的,庄子主张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在《人间世》中,颜回欲有所作为,孔子建议其以“端而虚,勉而一”“内直而外曲”等方式应对政治。至于原因,庄子借仲尼之口加以阐明:“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3]140仲尼并非反对颜回的所想所为,而是提醒他要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即首先保全自己,此为保全他人之前提。如若生命无法保全,制止暴君的恶行便无从谈起,那么又何以作用于社会?何以游于无何有之乡?在这里,存诸人为自然达到的效果,并非其首要追求方向。
在庄子的世界里,生命个体与社会角色二分,社会赋予的身份仅决定其生存视角与社会功用,无论是帝王、臣子,还是普通个体,其生命态度应当一致,个体在自我存续及与人交往中均应以存诸己为前提。庄子在《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故事中,以作为臣子的蘧伯玉的态度说明了生命的平等。颜阖问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3]169蘧伯玉认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3]170蘧伯玉教颜阖顺从卫灵公大子的意愿,随之为婴儿、为无町畦、为无崖,只要生命无疵,便是最佳结果。庄子亦以栎社树、支离疏等故事说明无用之用才是存诸己最好的方式。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帝王、臣子,他们均是平等的个体,应先存诸己,全身远害,保护肉体与精神的自由,此为庄子理想之“知”。
其实,结合《庄子》内七篇的内容,便可显见庄子所期待之帝王的最佳存在方式。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是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代表,亦是其理想中的明王形象。在存诸己的前提下,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有超越常人的能力,他以秕糠塑造几个尧舜,但并不以之为功;他化成天下,却并未影响其生命的存在与质量,状态依然若处子。然帝王与神人不同,神人脱离了社会角色的束缚,帝王却仍为社会中的角色,且无法达于神人状态,故其生命存续仍以存诸己为要。
庄子从几个方面来描述明王的无为、使物自喜等状态,收归一处,即可见庄子《应帝王》篇的主要写作倾向。其落脚点为帝王个体的存在,希望帝王将政治作为余事,以达到“胜物而不伤”、游于逍遥之宇的生命状态。
综上可见,政治是讨论帝王问题绕不开的话题,因此以政治为切入点建构理想中的帝王形象是解决帝王个体安顿的必经之路。就《庄子》内七篇的写作倾向而言,庄子将个体生命作为首要考虑要素,其全部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安顿展开。由于现代学科的精细划分,研究者将庄子思想分为不同层面进行重点论述,将《应帝王》篇的主旨引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忽视了此篇是以帝王个体为论述对象的前提。另外,众多研究者以社会和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帝王与政治有关,甚至帝王是政治的符号与代表,但帝王不等于政治,帝王虽是一国之君,然亦是普通个体,其身份以个体的存在为条件。因此,我们对庄子笔下帝王形象的分析,应首先从政治角度切入,在此视角下探究庄子的生命态度。
[1] 闻一多.古典新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6.
[2] 张华勇.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以《应帝王》为中心[J].武汉大学学报,2015(6).
[3]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许地山.道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2.
[5] 陈高.虚白室铭[M]//陈高集.郑立于,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219.
[6] 宋濂.云寓轩诗并序[M]//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447.
[7] 程乐松.物化与葆光:《齐物论》中所见的两种自我形态[J].中国哲学史,2020(3):52.
B223.5
A
1006–5261(2023)06–0030–06
2023-05-11
吴铭慧(1993―),女,河南浚县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姬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