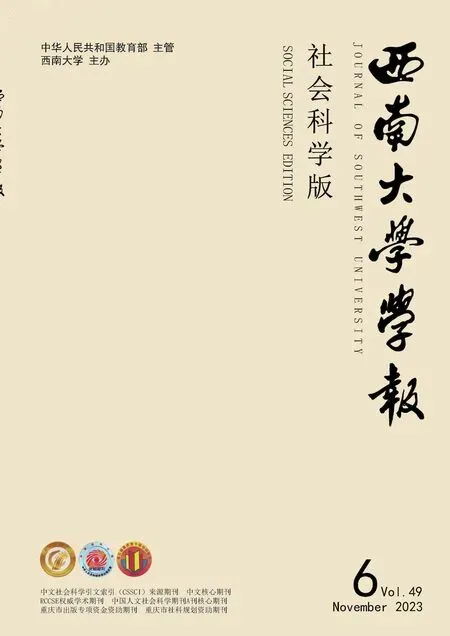“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阐释
——基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视域
赵 光 辉,张 海 波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5)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说明》中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47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4],“生命共同体”思想经历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飞跃,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生命共同体”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高点”[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深刻、最科学的揭示”[6],这一范畴受到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成为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从知网数据看,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现有文献基本都是从认识论角度阐释这一范畴的相关问题,如探讨其理论渊源与实践路径[7],阐释其生成机理与精神实质[8],分析其内在逻辑与显著特征[9],解读其基本原则[10]、实践意义[11]以及方法论意义[12],等等。张云飞教授是为数不多从本体论层面界定生命共同体的学者,他认为生命共同体奠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13],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本体论依据”[14],但其研究侧重从对深层生态学“内在价值”理论的批判、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多样资源等维度阐释生命共同体何以具有“本体论基础”的地位,而没有专门深入阐释“生命共同体”这一范畴本身所具有的本体论意蕴。可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是囿于认识论或者从认识论出发研究“生命共同体”,缺乏对其本体论意蕴的研究和揭示。
如果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还是一个基于系统观点的认识论命题,那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则已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回答了“人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对于一个本体论命题,如果不从根本上阐释清楚其内涵,或者只满足于纯粹的认识论判断,那么其本真的深刻含义也就无法巩固住,因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15]561。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和掌握群众。而只有掌握了群众,理论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6]11。“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概念为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开辟了新天地”[17],“《自然辩证法》堪称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宣言”[18]。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澄清这一命题的本体论内涵提供了理论框架。只有真正理解和领会了这一命题的本体论内涵,才可能让“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融入每个人的“生命”中,才有可能把生态环境理解为“我们的眼睛”,才有可能实现“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8。
一、自然的规律性:生命共同体的原初依据
虽然“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16]200的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恩格斯“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9]275,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止步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当黑格尔学派解体后,虽然费尔巴哈是“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19]266的人,但在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就“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时,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16]201,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0]22的人,进而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16]218的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将辩证法奠基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承接唯物主义辩证法之要义,把认识理解为“这个过程(现实世界发展过程——引者注)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应”[19]270,把“头脑中的辩证法”即思维辩证法理解为“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15]454,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全新领域——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为我们从本体论层面理解“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的成就证明了自然界是一个运动的整体。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运动将自然研究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使得自然研究成为科学、系统、全面发展的自然科学。近代数学、天体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中取得的自然科学成就证明了一个事实: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和植物,它们不仅有空间上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一句话,那就是“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15]415。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为自然辩证法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提: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证明了“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已经作为一个“科学事实”而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细胞学说论证了生物界结构上的“同一规律”;生物进化论则进一步说明了人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体具有同源性,也说明了自然界的自然发展历程。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不断地打破着“僵硬和固定的界线”——脊柱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鱼和两栖动物、鸟和爬行动物……的界限,都在不断地证明着这个世界是一个各种存在物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依赖的运动着的整体。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鲜明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性”[13]。
其次,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的成就证明了自然界运动的辩证性质。
自然科学的成就不仅证明了整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依赖的运动整体,而且还证明了自然界运动的辩证性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成就已经证明物质的运动是从一种质态转化为另一种质态的发展过程,证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的两极——差异和同一——在相互作用中把差异性纳入了统一性之中,在相互作用中偶然性蕴含了必然性,在相互作用中包含了因果联系,实现了事物从肯定走向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同样遵循着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辩证法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两个方面(自然界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思维本身的一般规律置于唯物主义地平之上,进而总结和表述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三大规律。这三大规律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原因、状态和趋势,也为我们继续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如果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同样要符合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呈现出来的应当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不应“彼此耗损”[21]的物质变换基础上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再次,恩格斯得出了自然界的规律性是自然界固有的本质特性。
自然辩证法说明了自然界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是人主观臆造的产物,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15]463。这种规律性不是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15]458的产物和结果。恰如后来列宁所言:“(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22]在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性面前,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16]211,也正是这种“受动性”要求人类要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这也就为“我们以平等身份看待并善待自然界、自觉主动地建设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实践遵循”[23]。恩格斯并没有满足于这种自然科学的证明,他还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性,证明了“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15]538。因此,作为思维的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15]470,即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
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争论而出现的“马恩对立论”。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莱文曾经直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流派,第一个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称为恩格斯主义(Engelsism)。”[24]“马恩对立论”的焦点就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恩格斯的辩证法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我们不去进行详细的论证,因为这不是本研究的侧重点,本研究仅仅是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谈论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意识[das Bewuä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ä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6]525对于意识这一“副本”来说,存在的“原本”就是“现实生活过程”。同理,如果说主观辩证法是“副本”,那么客观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则是“原本”[16]4。如果离开了自然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恩格斯将辩证法理解为“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15]539,这种科学不仅适用于思维运动的领域,同样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领域。如果说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要贡献是从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中剥离出了辩证法这一“合理内核”,那么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则在于将辩证法的适用领域从思维领域中解放出来,从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原则高度”为辩证法确立了坚实的自然基础。用恩格斯的话说,那就是“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15]15。因此,“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而恩格斯则通过‘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完成了这一颠倒”[25]。
最后,自然规律性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生命共同体”。
我们在上述理论视域中透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无论是整个地球,还是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一切动植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实现了从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发展,实现了从外在否定到内在否定的转化,实现了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的飞跃,实现了从原因到结果的转化,实现了从有限到无限的变化……没有自然界的沧桑巨变,就没有我们现在直观到的现存的自然界。没有现存的山川河流、星辰大海、芸芸众生,也就没有自然界的历史。总之,在相互作用中呈现为了我们今天生存于其间的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在这种内在规律性的自然运动中,人得以生成和发展。换言之,人自身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如果没有自然界的规律性运动,就没有人这个物种;如果没有自然界的规律性运动,也就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现代“人”。不仅我们今天所直观到的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都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16]528。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压根就不是一个外在于自然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其本质上就是自然界与其自身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哲学中讲的世界观,世界观并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去“观”世界然后得出一个整体的看法和根本观点[26]。自然界自身的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不仅生成了现在的自然界,生成了现存的人本身,而且还制约着自然万物的运动,还制约着人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1]24。换言之,自然界不仅是一切动植物的存在场域,同样也是人的生存场域,作为自然界的产物的人,也要遵循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人不能人为地创造规律,只能在发展中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从而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理解为自然界与其自身的关系时,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自然界不同程度地铭刻了生命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活动轨迹”[27]。在自然规律性中所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原初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为前提的生命共同体,是前反思、前逻辑的生命共同体。
如果我们止步于此理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共同体”学说,如利奥波德认为“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28]等。如果仅仅从人与其他一切存在物共同构成了自然界并且都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尤其是从生物起源的统一性上来论证这一命题,这不仅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跌落性理解,更是对人的“降格”。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把人“降格”以实现人与动物的平等,提出动物权力论、动物解放论等,进而要求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环境。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自然的哲学框架”[29],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从其“理论内部的自洽性和外部的普适性”[30]这一逻辑困境,立见其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决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之的边界,明察从西方环境伦理学或西方环境哲学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理论基础溯源可能存在的问题,虽然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误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13]。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我们也不能遗忘了“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16]530,我们更不能忘记了“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31]——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性。人何以成人,人以何为人,人何以成为主体?这同样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需要直面并且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如果回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命题上来,上述论述仅仅在原初意义上阐释了人与自然就是生命共同体,当人脱离了动物界,当人成为与其他一切生命体有区别的存在之时,这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真正“关系”[16]533。
二、人之实践特性:生命共同体的现实达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尤其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人不仅是劳动的结果,还是劳动的前提。说人是劳动的产物或者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人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劳动使最早的猿类开始了直立行走,从而“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5]551,劳动使猿手转变为人手,猿手与人手区别开来的标志就是制造工具——“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15]551。换言之,在劳动的过程中猿手转变成人手,人手不仅是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劳动的器官。劳动过程中交流的需要促使猿类的喉头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是从人类劳动中产生并和人类劳动一起发展起来的。劳动和语言的发展,最终实现了猿脑到人脑的过渡。人脑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和劳动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社会”的人。劳动产生了人的同时,劳动也成为人特有的活动,也就是说人是劳动的前提。如果没有劳动就没有人,同样没有人也就没有所谓的劳动。从根源上来说,是劳动产生了人,只是自从人产生之后二者变成了彼此成就的关系。因此,恩格斯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15]555。在恩格斯这里用的是“劳动”这一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就是“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就是“生产”范畴,这三个范畴在本质上一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进行了对比,进一步说明人的劳动的特殊性。
第一,从总体上来看,动物是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的生命活动,而人则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15]408即生产的生命活动。动物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适应自然界维持生存并一代一代地不断复制自己,而人“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或者说一旦作为人而存在,人的“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15]408,人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而且这种正常生存条件在劳动中生成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的意识,因为“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15]483是人的思维发展变化的最本质的基础。
第二,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性的活动。恩格斯认为虽然动物的活动也能改变外部自然界,但动物对环境的改变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例如,山羊的进食活动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对于山羊而言这只是一个出于本能的活动,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进食活动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活动,而且能够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15]558。山羊在进食活动中消灭了某地的植物,这仅仅是个本能的、无意识的活动,而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获得土地,在土地上耕种自己需要的粮食。人和山羊从而拉开了距离:人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16]534。恩格斯的观点和马克思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都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并且认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0]56。恰恰是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15]421,进而使自然界变成属人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界。
第三,人的劳动是历史性的活动。动物的生命活动从属于自然史,只能是自然史的组成部分。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人的历史”。恩格斯认为,当人脱离了动物界,当“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的时候,人“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5]421-422。在人类劳动发展的过程中,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逐步脱离“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6]534的生活,自然界的“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逐步变小,人类实践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15]42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把自然界改造为“同人的存在相适合”的自然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的形成过程即历史,正是因为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形成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过程,所以“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6]211。
第四,人的劳动是社会性的活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自己并不否定动物也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意识的行动,例如狮群进行围猎。但是这些动物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只是在外界刺激下发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应激行为,而这种有意识也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即“畜群意识”[16]534。人的劳动是社会性行为,恰恰是在社会生产组织中,“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5]422。人类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不仅把人从动物界中区别开来,同时还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又给人的发展提供了规定性。
第五,人的劳动是普遍性的活动。动物只能依据自己的本能在其生存的场域内直接利用自然界的存在物维持生存,例如采集——这是动物最多能做到的方式;而人则从事生产,人不仅能够直接利用自然界的存在物,还能改变自然界进而让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如果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6]161。虽然自然界在更为原初的意义上决定着人们的最广义的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却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不能自我生产出来的。
综上可知,动物与自然界之间是一种直接的统一关系,而人在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社会性劳动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虽然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但人们在劳动中将“自在世界”改造成为“人化自然”,赋予了自然界以人的属性。经过人的劳动改造后打上人的印记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的世界,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正是在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既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却又是自然的光环和荣耀,是它的真正的规律性和目的性。”[32]当然,并不是人把自然界作为外在于人的纯粹客体进行改造,否则我们就把恩格斯退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16]499立场上去了,因为人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样生成着人自身。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即双向作用中,实现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6]500。在“受动”为前提的人的能动改造世界的劳动过程中,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人成为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建构起以否定性为基础的统一性关系,将原初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实现为人的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
三、支配的外在性:生命共同体的历史塌陷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5]559这意味着恩格斯在肯定劳动“支配自然界”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支配自然界”的异化。
恩格斯一方面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11]560,是自然界辩证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不仅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场域,还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自然界同自身的关系。如果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161另一方面,恩格斯也看到了虽然人的劳动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但人之劳动依然创造了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或者没有人自然界无法产生的生活资料,将自然界变成了属人的世界。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无论在原初意义的生命共同体还是劳动生产中达成的现实的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界都是内在的统一关系即“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15]560。
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随着劳动能力的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提高,这种“内在的一体性”异化为“外在的对立性”。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绝对化、膨胀化,开始站在“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这时候,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于内在统一性基础上的生命共同体就遭遇了历史性塌陷。当人们站在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的时候,自然界不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人成为主宰、裁制自然界的主体,自然界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内在的统一关系变成了外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人类不断向自然界胜利进军的时候,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时,结果却遭到了自然界的无情的“报复”。恩格斯通过这种“主体‘陶醉’和自然的无情‘报复’揭示了人与自然紧张对立的深层根源”[27]。“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1]9意蕴即在此。在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危机还不是很严重。因此,自然界的“报复”在恩格斯看来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消除了,例如恩格斯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的人为了开垦土地而毁灭了森林导致这些地方后来变成了不毛之地。但在今天看来这种“报复”岂止是消除了最初的结果,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断裂”[33]。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造成的所谓“癌症村”不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我们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无视自然规律地“支配自然界”[15]560。
恩格斯并没有满足于上述劳动一般意义上的论证,毕竟这种“劳动”还是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类似于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然后到了政治经济学中进行市民社会的解剖一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就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进行了分析,虽然恩格斯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换言之,恩格斯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站在自然界之外”支配自然的劳动活动,他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逻辑,认为在所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一个生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而生产都是以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这就导致长远利益被忽视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可以说是将这种‘短视’的生产方式发挥到极致”[34]。资本家的利益是生产的推动因素,而资本家只关心生产的“最直接的效益”——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说就是价值。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恩格斯认为就连制造的或者交换的产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都完全退到次要地位了,利润即剩余价值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的动力”。换言之,生产什么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什么能够获得剩余价值。这就导致资本家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为了获得利润,不会去考虑长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支配下,西班牙种植场主才会在古巴焚烧山林以种植能够直接获得利润的咖啡树,而若干年后因为这些地方被热带大雨冲毁之后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而失去肥沃的土壤,这根本不在资本家的考虑范围内。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证,但是恩格斯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短视行为、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对立现象。这种外在的支配直接表现为工业的周期过程,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这种外在的对立根源于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方面人变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一个纯粹客体,二者构成了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得眼前的利润而不顾人类的长远利益。在这样的双重异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内在的统一关系彻底异化为外在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获取利润的内在冲动,导致自然界变成获取利润的纯粹手段,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遭遇了历史性的解构,生态危机的出现同样成为历史性的必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洞穿了生命共同体遭遇历史性塌陷的根本原因,这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四、生产的变革性:生命共同体的再度重建
恩格斯认为人优于其他一切生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之所以出现站在自然之外去支配自然的异化状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没有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没有认识到自身干预自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到自身的生产行为对自然产生的较远的影响。而这只是“估计”到,要正确地“预见”自身的生产行为对自然产生的较远影响需要更长的时间。人类经历了长时间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在对人类生产经验的总结和生产历史的反思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从而具有了对较远影响进行控制和调节的认知能力,但私有制又让人类走上站在自然之外征服自然的道路。
在指出不断认识规律的同时,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探寻到了解决异化的办法——对生产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变革。这是一条“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35],同时又是一条复归和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根本之路。虽然恩格斯没有直言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生命共同体的解构,没有明确这种破坏性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无法自我解决,但其论述中已然内嵌了这样的逻辑。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和逻辑关联,恩格斯才会提出调节和控制这些影响,“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5]561。如果没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就无法控制自己活动的长远影响。因为这不是由资本家的道德品行所决定的,也不能由资本家个人来负责,资本家不过是这种生产方式中资本的人格化。
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需要有现实的路径,否则就容易陷入“乌托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仅指出了调节和控制这些影响的根本路径,还找到了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实践路径。这一路径就隐藏在恩格斯对“生存斗争”的分析中。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方面社会制造出大量不能被消耗掉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另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又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离,这就必然导致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面对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采取了“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这样的方式来“重建平衡”[15]548,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们要实现“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15]548这一目标,就必须剥夺资本家手中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这个领导权交给生产者即广大的工人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换言之,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对生命共同体的破坏和解构,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路径就是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中蕴含了这样的生态内涵,福斯特认为:“恩格斯的分析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可以称之为‘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的概念。”[36]
由恩格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成就生命共同体,而且是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关系的根本原因。因此唯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根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实现人的复归与自然的复活、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关系的根本途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恩格斯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非官僚化’和‘分散化’”[37]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之间的根本差异。可见,“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38]。
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不仅具有现实基础,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和现实意义都源自我们当前的生产方式即经济发展状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39]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分配方式,所有制性质和分配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经济体制即具体的运行模式。三者从不同维度阐释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特征。当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在新时代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命题的现实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积极的现实基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虽然仍然进行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但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们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纯粹地追求剩余价值,劳动产品更重要的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满足人们的需要。虽然生产中依然存在剩余,但这种剩余不是作为“剩余价值”而存在,是公有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物资储备,是国家和集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物质财富。总之,公有制经济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意:不是需求,而是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起点差别)。没有了剩余价值追求的冲动,人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愚蠢而片面”[16]189的个人,整个社会生产才能合理地调节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人们才能把那些“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15]562作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才能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依然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和相应的分配方式,这是我们现在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消极的现实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依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生产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其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形成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换言之,剩余价值生产是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的目的。这种以剩余价值为追求的非公有制经济,或者说这种由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的短视性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势必会不断地瓦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也正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这种解构性质,我们才需要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
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非公有制经济,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对自然的消极影响等负面作用,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形式,能够有效地调动生产的积极性,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同时,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但其生产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仍然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6]18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非公有制经济,重要的是在经济运行中如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发展,有效避免非公有制经济的消极作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资本,而是要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限制资本,“使资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40]。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合理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效引导资本运行的一个重要理念。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落实为具体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时,这一理念的引导作用也就现实地凸显出来。
恩格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全变革理解为恢复和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的途径,把社会主义革命定位为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实践路径。恩格斯的上述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本体论上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体”这一论断的原则高度,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同体的复归。这种复归不是原初意义上共同体的复归,而是在更高生产水平、更合理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积极复归;这种复归意味着我们探索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开始,意味着我们走向“人道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开始。
五、结 语
我们在生命共同体的原初依据、现实达成、历史坍塌、再度重建这样一个历史辩证法理论域中澄明了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理解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科学判断的深刻内涵和提出这一判断的历史必然。在此论域中,我们深刻地领悟到这一命题具有“巨大的历史感”[41]——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平行的关系,具有鲜活的时代感——是新时代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历史环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是人类历史发展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当我们把历史理解为“始终处在形成中的过程(becoming)”[42]时,当我们把握了生命共同体这一范畴的本体论意蕴,真正把自然界理解为我们自身,真正像保护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身体一样去保护和爱护生态环境,我们才能在承担起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这一历史使命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其他国家“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16]11的实践引领时代、开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