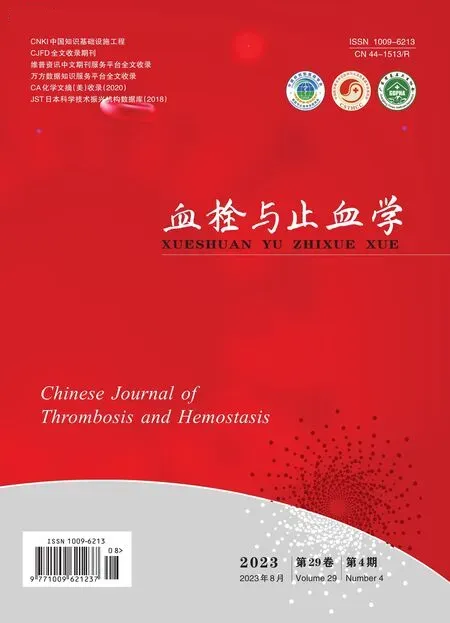妇科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的研究进展
宋丽娜(Song Lina),李娜(Li Na)
1.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妇产科,甘南藏族自治州 747000;
2.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南开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妇瘤科,天津 300100;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是妇科围手术期及妇科肿瘤常见的并发症,易对患者预后造成不良影响[1]。据统计,我国妇科手术后DVT 的发生率约0.13%~6.78%左右,妇科癌症患者发生DVT 的风险约为17%(比非癌症患者高约14倍)[2]。因此,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和防治依然是妇科术后恢复的重点之一,本文就妇科围手术期相关深静脉血栓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以期为临床妇科术后DVT 的防治提供参考。
1 DVT 的危险因素
1.1 手术干预因素
手术本身就是DVT 发生的危险因素,手术所造成的组织破坏会引起血小板粘附聚集能力增强,激活凝血因子并释放凝血酶,启动外源性凝血途径导致高凝状态,促进DVT 发生。手术中无论全麻或椎管内麻醉均可导致下肢肌肉完全麻痹,失去收缩功能,使静脉回流缓慢,同时,麻醉使周围静脉扩张,静脉壁平滑肌松弛,内皮细胞脱落而胶原纤维暴露,是诱发DVT 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麻醉方式对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相较于全麻而言,椎管内麻醉可减少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出现DVT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妇科经腹手术通常会造成更多出血和盆腔血管损伤,而腹腔镜手术常用的截石体位使患者的下肢屈曲固定,在重力作用下影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造成血管内压力升高,血管内膜破坏,导致DVT 发生。两种手术方式均会增加患者DVT 风险,但具体哪种手术入路对DVT 影响更大,目前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3-4]。Susan 等[5]对94 940 例患者进行分析,发现与腹腔镜或经阴道等微创子宫切除术相比,腹式子宫切除术后DVT 的发生风险更高。Wang 等[4]发现妇科开腹手术DVT 发生率(62.2%)显著高于腹腔镜手术(37.8%)。与之相反,Yang 等[3]则发现腹腔镜手术是患者发生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
腹腔镜气腹压力、手术时间以及卧床时间均是妇科腹腔镜术后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ian等[6]对455 例(41 例DVT,414 例非DVT)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进行分析发现,手术持续时间≥60 min、气腹压力≥15 mmHg、卧床天数>3 d 是术后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邱炳云[7]纳入275 例(26 例DVT,249 非DVT)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气腹压力>15 mmHg、手术时间>60 min、术后卧床时间>7 d 均是术后DVT 的独立危险因素。韩星梅等[8]研究结果表明:手术时间≥2 h、卧床时间≥3 d是妇科盆腔术后DVT 的主要危险因素。正常情况下人体的下腔静脉压为2 ~5 mmHg,腹腔镜手术时,需将气腹压维持在12 ~15 mmHg。气腹增加腹内压,不利于下腔静脉血液回流,血流速度减慢,容易造成血液瘀滞;手术时间长致使机体较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引发应激性血小板数量增高,血液呈浓缩状态;术后卧床时间长导致血液瘀滞时间过长,可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激活血小板功能,诱发凝血反应及血栓形成。Janelle 等[9]研究表明,妇科手术时间每增加60 min,可使术后30 d 内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增加35%。因此,要尽量减少手术操作时间,同时腹腔镜手术要注意控制气腹压不宜过高,术后鼓励患者尽早开始下肢活动,以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DVT 发生。
1.2 恶性肿瘤
肿瘤细胞可直接释放促凝物质如组织因子和癌症促凝素,前者可激活外在凝血途径的级联反应,是肿瘤相关血栓的主要驱动因子,癌症促凝素则通过启动内源性凝血途径导致血栓形成。体外实验显示,肿瘤组织和癌细胞均可释放凝血活酶、抗凝血酶Ⅲ等促凝物质;肿瘤细胞还可释放炎性因子、激活并诱导血小板聚集,同时减弱内皮细胞的抗凝功能,多方面相互作用促进DVT 发生[10]。
除肿瘤本身因素外,妇科手术部位位于盆腔,盆腔静脉丰富,吻合成丛,回流速度慢易发静脉淤血。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术范围与手术时间一般大于良性肿瘤,且由于下腹部静脉丛丰富,术中淋巴结切除以及长时间的器械操作增加了对血管的破坏与刺激,加剧了凝血反应。手术造成的血管壁损伤、脱水、活动减少,肿瘤造成的高凝状态、肿瘤压迫导致的静脉回流障碍等均显著增加DVT 的风险。因此,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比良性疾病手术更容易发生DVT。
1.3 患者因素
研究显示年龄≥50 岁是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6]。随着年龄增大,机体功能逐渐下降,血管壁的收缩能力及弹性减弱伴随不同程度的血管内皮细胞损害,静脉瓣萎缩、血管内膜粗糙、血小板的聚集性增高、血液黏稠度增加、凝血功能亢进、肌肉泵血功能降低使得老年患者更易形成DVT[11]。
文献报道,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5 kg/m2是妇科术后诱发 DVT 的高危因素[3,7-8]。Tan 等[12]对人体测量特征遗传项目GIANT(339 224 名参与者)和FinnGen(1 785 例DVT,8 446例对照)的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了BMI 与DVT呈正相关的因果关系。过高的体重会加重下肢负担、影响血液循环,长期肥胖会损伤下肢血管,肥胖引起的促炎状态还可能导致纤溶功能受损、凝血强度和功能性纤维蛋白水平明显升高,增加DVT 发生的风险。
2 DVT 风险评估
2.1 DVT 风险评估模型
目前在妇科领域研究较为广泛的DVT 风险评估模型包括: Caprini、Autar、Rogers 及Khorana 模型等。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主要根据患者罹患静脉血栓的危险程度不同,对40 余项危险因素进行评分,将患者分为低、中、高和极高危组,针对不同危险分层采取相应预防干预措施。后续验证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在骨科、胸外科、整形外科及其他危重手术中对DVT 高危患者具有相对可靠的预测价值[13],但由于该模型包含过多风险因素致使其评估复杂且耗时,因此局限了其在临床的应用。鉴于此,通过结合中国数据,我国建立了适合妇科术后风险等级划分的妇科Caprini(Gynecological Caprini,G-Caprini)模型[14],相比较Caprini 模型,GCaprini 模型简单易掌握,医护人员可快速、准确地完成评估,但是目前尚缺乏验证性试验对其临床效果进行验证。Autar 风险评估模型是由英格兰护理学专家Autar 基于骨科术后护理制定的,包括患者年龄、关节活动度、BMI、手术方式、创伤风险、高危疾病和特殊风险7 个模块的评估模型,该模型预测骨科术后DVT 的可靠性较好[15]。高阿芳等[16]研究发现Caprini 和Autar 模型对妇科手术患者DVT 风险评估均具有临床价值,Caprini 模型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对预防DVT 更有优势。
Rogers 风险评估模型的危险因素评分细则不够简易,且未将DVT 高危患者的个人或家族史等因素考虑在内[17]。Heft 等[18]将该模型用于接受盆腔手术的泌尿科和妇科手术患者DVT 的评估,多数DVT患者被错误评估为低危或中危患者,而高危组中发生DVT 的患者仅占0.1%。因此,Rogers 风险评估模型难以有效地对患者进行充分的危险分层。Khorana 风险评估模型主要用于肿瘤患者的DVT 风险评估,其对妇科肿瘤DVT 高危患者预测的可靠性尚不明确[15]。
国际上应用的其他风险评估模型,如:Padua、Kucher 和Intermountain 模型在美国的危重手术患者中进行了临床验证,发现三种模型预测DVT 的可靠性较差,其一致性指数范围仅为0.58 ~0.64,而且纳入人群也存在局限性,Kucher 模型验证主要集中于癌症患者,而Padua 模型系单中心的小样本验证[19]。
综上,妇科领域采用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预测患者DVT 发生风险的实用性较好,但仍需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此外,由于东西方人种特征、疾病特点等的差异,基于西方国家数据而制定的量表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群,加快对国际上应用的基于西方国家数据而制定的DVT 风险评估模型的本土化验证,有助于科学地制定我国妇科手术DVT 的识别体系。
2.2 凝血标志物预测价值
D-D 是临床中常用的评估凝血功能的重要指标[20],文献报道D-D ≥500 ng/mL 是妇科术后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6-7]。日本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1 729 名妇科术前患者,对D-D≥1 000 ng/mL的患者进行下肢血管超声检查,筛查出94 例DVT患者[21]。因此,对妇科术前D-D≥1 000 ng/mL 的患者进行下肢血管超声检查有助于提高DVT 的检出率。
3 DVT 的预防
临床上DVT 的预防策略主要包括:物理预防和药物预防。物理预防包括: 梯度压力弹力袜(graduated compression stockings,GCS)和顺序充气加压装置(sequential compression devices,SCD)或间歇充气加压装置 ( 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IPC)等有助于减少静脉淤滞并可能促进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从而改善血液高凝状态从而预防血栓形成,但单纯的物理预防并不能完全替代药物预防。
药物预防主要包括普通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H)、低分子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LMWH)、维生素K 拮抗剂华法林以及新型抗凝药物(Novel Oral Anticoagulants,NOACs)。其中,普通肝素使用过程中需监测凝血值标,如: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LMWH 对凝血功能影响较小,且已有研究证实LMWH 的预防疗效要显著优于普通肝素[22]。华法林由于有引起出血的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NOACs 类药物(如:依度沙班或利伐沙班)所替代,后者具有抗凝作用强、剂量固定、不需常规抗凝活性监测等优点。
物理和药物联合预防可提高DVT 的预防效能,2021 年最新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共纳入1 990 项研究(4 970 例患者),结果表明SCD 与LMWH 联合对于预防妇科肿瘤术后DVT 的发生效果极佳,且术后出血量无显著增多[2]。因此,对于妇科手术患者术前需详细询问病史,了解有无个人或家族DVT 病史或其他诱发血栓的高危因素。此外,具有发生DVT高危因素的妇科患者建议SCD 与LMWH 联合应用,可辅以抬高下肢、足踝活动等综合措施预防DVT 发生。
4 DVT 的治疗
4.1 抗凝治疗
深静脉血栓的管理分为初始(最初的5 ~21 d,3 周内)、长期(最初3 个月)和延长(在最初3 个月之后)三个阶段[23]。对于非癌症患者,欧洲心脏病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共识建议没有禁忌证的情况下首选NOACs 类药物[23];对于癌症患者,静脉血栓最初阶段(前5~10 d)的治疗应首选LMWH。近年来,NOACs 类药物的使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荐[24-25]。此外,2019 年由美国和日本联合开展的一项纳入2 527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可能会降低子宫内膜癌患者发生DVT 的风险[26]。2020年新英格兰杂志发布的一项多国、随机的临床试验(Caravaggio 试验),纳入伴有静脉血栓的癌症患者1 155例,随机给予口服阿哌沙班(或皮下注射达肝素),治疗周期为6 个月,结果表明:口服阿哌沙班组患者复发性DVT 发生率为5.6%,达肝素组为7.9%;两组大出血发生率相似(阿哌沙班组:3.8%,达肝素组:4.0%),表明阿哌沙班至少和达肝素具有一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亚组分析显示:对于65岁以下复发性DVT 的预防,阿哌沙班比达肝素更有效[27]。因此,阿哌沙班也被纳入了2021 年ESC 共识[23]。
综上,目前深静脉血栓的治疗除了低分子肝素类药物(那曲肝素、依诺肝素、达肝素等),NOACs 类药物(阿哌沙班、依度沙班或利伐沙班等)亦是抗凝治疗的理想选择。然而,如何选择恰当的药物,应根据患者自身特点以及原发疾病的特征和治疗方法进行个性化治疗。
4.2 溶栓治疗
深静脉血栓的溶栓治疗是治疗急性深静脉血栓非常重要的手段,也是消除血栓、溶解血栓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溶栓治疗分为全身溶栓治疗和局部溶栓治疗。溶栓治疗适用于伴低血压但没有高出血风险的急性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患者以及在开始抗凝治疗后病情恶化但尚未出现低血压、且出血风险可接受的特定急性PE 患者。
4.3 其他治疗
除抗凝和溶栓治疗外,对于腿部急性近端DVT且有抗凝禁忌证的患者,通常推荐使用下腔静脉过滤器。
5 DVT 的随访
静脉血栓在抗凝治疗停止后1 年内复发率较高,复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但不会完全无风险。因此,为避免复发风险以及DVT 本身和抗凝相关并发症,需要对患者进行随访。妇科DVT 患者通常于出院后2 周进行首次随访,出院后一个月完成第2 次随访,出院后3 个月进行第3 次随访,第4 次随访在出院后半年左右完成,此后,每年随访至第5年。同时,在停止抗凝治疗之前,对患者进行静脉彩超评估其基线残余静脉血栓,必要时进行下肢静脉造影,有助于新症状出现时区分新旧血栓。
6 小结
妇科DVT 重在预防,对具有DVT 高危因素的患者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本文对妇科术后DVT 发生的高危因素、风险评估、预防及治疗加以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然而,临床实际工作中仍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期望未来有更多的临床试验和研究为妇科围手术期DVT 的管理提供临床指导。
作者贡献声明宋丽娜负责文献检索及全文书写;李娜负责审校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