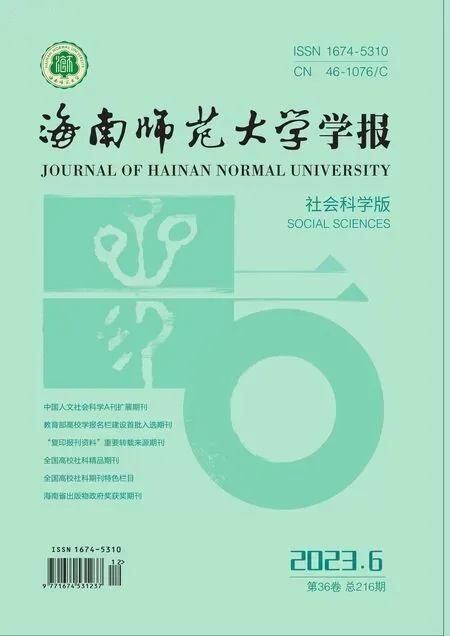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论析
段曹林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关于杜甫七律艺术的特点和创新,钱志熙从题材的大幅开拓和风格的极大丰富两个方面概括了杜甫对初盛唐七律的“巨大发展”,并指出其两大突出的艺术特点,一是“杜甫的七律,绝大部分都用一种浓重的抒情笔法来写”①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8页。,“以思想、情意驱遣情事景象”②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第284页。,在抒情强度、情感类型、抒情方式上均有显著的突破和创新;二是“叙述性的增强和白描艺术的发展”③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第279页。,“大量采用宽对的形式”④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第282页。追求意脉的连贯和表达的自如浑成。马茂元先生则从谋篇角度做过评说:“作为杜甫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他能在尽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⑤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新一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597页。
杜甫七律这些突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源于修辞的创新和成就,其具体表现只有结合代表性作品来分析和梳理,才能得出相对明晰而真切的结论。本文拟从抒情能效的发掘、审美世界的创造、篇章内涵的扩容、诗体惯例的突破等四个大的方面,选取相应诗作(文本以中华书局1999 年版《全唐诗》(增订本)为依据),对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及对诗歌修辞史的贡献展开探讨。
一、点染与留白:修辞对抒情能效的成功发掘
“沉郁顿挫”在杜甫七律的情感特色和抒情方式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多样化修辞手段的针对性选用对抒情效能的发掘可谓是居功至伟:一方面,表情词语(伤、悲、愁、可怜、叹息)的点缀,感叹语气的流露,映衬、夸张等辞格的渲染,为诗歌涂抹上浓烈的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叙述句、描写句、评议句等主导下的内容表达,用典、婉转、比喻、比拟、双关等辞格的运用,使情感抒发更厚重、更深沉、更委婉。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前人对这首诗加以评说,突出其强烈的抒情性和感染力:“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那么这一抒情特点是如何体现的呢?且看其修辞。
该诗虽借助于用典、映衬、夸张等辞格,但主要还是依靠词语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白描)等消极修辞手法来写人、叙事和抒情。
首联写人,直呼“郑公”,包含敬重和年长双重意;“樗散”用典,喻写其为人厚道;“酒后常称老画师”也表明他安分守己;“鬓成丝”用白描,突出其年老。
颔联抒情,上下句均用倒装形式,常规顺序为“严谴日万里伤心,中兴时百年垂死”,状语后置,满足了对仗需要,更突显了“伤心”和“垂死”、“严谴日”和“中兴时”的鲜明对比,“万里”用夸张,强化“伤心”;借助多重映衬,蕴含了深刻的同情和愤慨:“垂死”正衬“伤心”、“严谴”对衬“垂死”、“中兴时”反衬“严谴日”。
颈联叙事,采取“苍惶”“邂逅”分别前置的句法,继续聚焦于“严谴”,由此叙事也不再是冷静客观的,而是寄托了强烈的同情和不满。
尾联抒情,在前面“垂死”“严谴”“邂逅无端”的铺叙基础上,直抒“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悲叹和只能寄望“九重泉路尽交期”的痛楚。称呼“先生”显真情,“永诀”沉痛不忍卒读。
从篇章修辞角度看,此诗主要是将情感色彩涂抹、贯穿在字里行间,层层推进,在写人、叙事中蕴含情感、间接抒情,并为直接抒情作铺垫。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此诗叙述回成都后的打算和别后三年的奔走,却以抒情为主,以抒情带叙述,叙中也含情,见出杜诗写作手法自由融通的一贯特点。词语修辞、句式修辞和双关、夸张、拟人、借代等辞格的结合,强化了该诗的抒情性,丰富了诗歌的意蕴,风格含蓄、自然。
诗的首四句写重新修整草堂的设想。一二句述说经常苦于药栏被毁,“常”“苦”突出忧虑之频繁,“损”和“落”点明药栏所遭遇的严重毁伤,以言情方式叙说修理药栏的计划。三四句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表明整理松竹的计划,“恨不”“应须”相对,“高千尺”“斩万竿”相对并用夸张,用感叹形式表达对“新松”和“恶竹”爱憎分明的态度,用双关格言此意彼,兼表面对新生事物和恶势力的鲜明立场,“兼寓扶善疾恶意”(杨伦《杜诗镜铨》)。
五六句写生活方面的展望。“只凭”突出对朋友的信赖感激,“衰颜”借代身体(保养)、“欲付”拟人,显示轻松的心态。叙事中包含情感的抒发。最后两句从瞻望转到回顾,“三年奔走空皮骨”叙事,“信有人间行路难”抒发感叹,“行路难”双关,“信”借以强化感慨。
全诗扣题,围绕自身的事和情展开,重在抒情,但又不局限于个人的遭遇和情感,而是巧妙、自然地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态度融入、寄寓其中,由此拓展、深化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杜甫这首重九名作抒写年老悲秋的感慨,用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映衬、用典、设问等曲尽其意,风格自然、刚健。
起首即抒情,直述“老去”“悲秋”“强自宽”,用自己一向的情感状态,映衬、突显“今日”难得的“兴来”和“尽君欢”,叙中言情。
次联叙事,反用孟嘉落帽的典故,紧承第二句,具体刻画“兴”和“欢”。“短发”写年老,“正冠”写雅“兴”,将“羞”和“笑”两个表情词语置于句首予以突出,暗点“强自宽”。杨万里《诚斋诗话》评价此联:“孟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
颈联写景,描绘山高水远的壮美景色,视线和关注点都一下摆脱了眼前的喜乐悲愁,但这只是暂时的、表面的,不可能真正让人忘情,这里的景因而同样也成为了情的一种映衬。
尾联抒情,用设问委婉表达感叹:山水常在、人事难料,“醉把茱萸仔细看”描状“醉”态,以此特殊情态表现诗人内心境况,照应起首两句的抒情叙事。
颈联用工对,首联颔联皆用宽对,尾联散行,这种整中有散的句法结构及篇章模式,既凝练、突出了诗意,又保持了意脉的流畅自然,强化了抒情表意的厚度和力度。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杜甫《曲江对酒》)
这首诗借助词语修辞和映衬、拟人、婉转等辞格叙事、写景、议论、抒情,表现诗人不为所用、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心情,情感深沉,风格含蓄。
首联叙事,“坐不归”表明诗人久坐江头不归,“不”表明诗人不归是因为主观上不愿回去,暗示情绪不佳。“转霏微”写天色晚而迷蒙,“霏微”叠韵,给人虚幻寥落的评价色彩。
颔联写景,“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用自对格,句间句内皆用对,工对、映衬、拟人兼用,凸显了所写春景的特征:色彩美、声音美、动态美兼备。“细逐”“时兼”刻画落花的轻盈美好,飞鸟的活跃轻松,生动而传神。此等乐景恰恰反衬了诗人的心绪:心事重重、难以排解,仕途失意、懒散无聊。
颈联议论,用婉转格述怀,表面说自己因为纵情于饮酒而甘愿被弃,因为“懒朝”“与世相违”,事实上因果则是倒置过来的,诗人借此委婉含蓄地抒发了不为理解、不为所用的抑郁和愤懑。
尾联抒情,“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沧洲”借代隐居,“拂衣”代指辞官,“更觉”“徒伤”相对,凸显老大伤悲却又抱负难展、报国无门而又不忍弃官的矛盾心理和两难处境。
二、合作与融通:修辞对审美世界的创造
除了抒情效能的大力发掘,修辞还在杜甫七律的写人、叙事、绘景、说理等各类实践中各擅胜场,将丰富独特的情感内容与整齐灵动的话语形式融为一体,合力创造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境界宏阔、魅力深厚的审美世界。
(一)送别类诗,往往由人及己,对人物特征进行白描,融入议论,寄托情感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刘熙载《艺概·诗概》)。律诗受声律和对仗束缚,易流于板滞,杜律的高明之处在于往往总能做到纵横自如而又脉络分明,这首诗也如此。总体上围绕人来写,从对方写到自己再写到彼此的离别。修辞上多用典故,并借助词语锤炼、句式变化和映衬、示现、借代等辞格来写人寄情,风格典雅、庄重、含蓄。
诗的前半篇概写李剑州,描摹其形象,颂扬其政绩。前两句从正面写,“使君”用尊称,“高义”“驱”“坐”都对李剑州加以肯定和夸赞,“寥落”则表达对其未受重用的不平和同情。三四句借用典故从侧面写,用古人来映衬。“能化俗”强调其治理能力,“未封侯”表明其用非其才,“但见”“焉知”前后呼应,一开一阖,彼此映衬,用反问句进一步凸显这一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及其未受重视,从中寄寓了诗人的评价和态度。对偶句中融入虚词,显化了逻辑关联,整中有散,在凝练的结构中增加了流动性。
后半篇从自己着笔写离别,寄托身世之感。五六句用示现,描写想象中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用“路经滟滪”的风涛险恶、“天入沧浪”的烟波浩渺来映衬前行路的艰险难测,暗含诗人对于人生迟暮飘零的忧虑和哀愁。“双蓬鬓”借代垂老的诗人,和“滟滪”相对照,“一钓舟”和“沧浪”相对照,包含鲜明的画面感和象征义。尾联用设问,抒发离别之情,再用典故,借王粲虚写自身未来可能的处境,言而未尽,令人回味。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杜甫《送韩十四江东觐省》)
这首送别诗,主要借助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借代、用典和映衬等表现离愁别绪,寄寓深沉的家国之恨,风格谨严。
首句点题,“兵戈”借代战争,名词独立成句突出“觐省”的背景,借彩衣娱亲的典故侧面点题。第二句紧承第一句,直接抒情,发出忧国忧民之叹息。
三四句,接“万事非”,写诗人与弟妹们的分离苦况,引出对韩十四江东觐省前景的关心。“我”和“君”相对、“已”和“今”连贯,两句构成流水对;疑问句增添了形式的变化和语意的波澜。
五六句,写分别后的景,景中寓情。“黄牛峡”对“白马江”,巧用地名构成工对,“静”反衬响和动,暗示船已走远,“寒”和“稀”,暗点天晚和秋意变浓,映衬诗人此时内心的孤独凄冷。
最后两句,鼓励彼此应各自努力生活,即便如此,“犹恐”前程未卜,不能等到同归故乡的那一天。与开头的“叹息人间万事非”前后呼应,意味深长。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棉。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这首送别诗主要借助句式修辞和拟人、映衬抒写聚散离合之情,寄托迟暮飘零的身世之感,叙事、抒情、写景都统贯于“情”,抒情浓烈,风格谨严、刚健。
首联叙分别,突出了“童稚情亲”和长相思,“童稚情亲四十年”直述儿时旧情的深厚,“消息两茫然”与此形成映衬,凸显了下文相聚的不易。
次联叹重逢,突出“相逢是别筵”、后会遥无期的感受。“相逢”和“后会”时序颠倒,用句子间的倒装形成逆挽之势,看似为了押韵需要导致了衔接突兀,实则更能激发接受者的好奇和探索,对于诗人因相逢不易而特别关心相聚时间长短、期待“后会”的内心活动,也就体会更深,诗歌本身也增添了波澜。设问句和感叹句的连用,前者明显包含了“后会”杳然、茫然之意,后者则使抒情表意更强烈、更深沉。“更”“忽”相配,加强了人生如梦、世事难料的感慨。
诗的后四句写景,给景物涂抹上显著别样的主观色彩。颈联用移就,将“不分”“生憎”等人的性状加于无情之物桃花、柳絮,又用明喻、较喻,拿锦、棉来比况它们色彩的明艳、外观的美好。尾联用拟人,把剑南春色描述成“无赖”并“触忤愁人”的不受欢迎者。这种表面的矛盾和异常,究其根源,全是出自诗人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特殊心境。景衬情,情衬景,写景和抒情就此融为一体,景语也都成为了情语。
(二)记事类诗,通常即事述怀,叙中含情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杜甫《客至》)
这首纪事诗借助词语修辞和映衬、迭映、互文等辞格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待客的过程和场景,从中可见出诗人的真率热情、宾主的融洽和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风格明快、自然。
一二句写户外的景色。“舍南舍北皆春水”用迭映,强调居所外环境优美怡人,“皆”“但”相对,用转折复句,突出只有“群鸥日日来”的美中不足,反衬少有人来。暗示诗人对客人光临的盼望和喜悦心情。
三四句写客人到家。用互文格记录与客人的对话,每句前后又构成映衬,表达对来客的高度重视和格外欢迎,也表明主人不轻易延客的闲适恬淡性格。
后四句实写待客。五六句正面描写主人抱歉招待简朴和频频劝菜劝酒的宴客场景,“无”“只”相配,有强调意味,话语显得诚挚而亲切,字里行间透露着主客之间真诚融洽的欢悦氛围。七八句从侧面描写邻翁也受邀参与共饮,将席间的气氛推向高潮。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主要借助语音修辞、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夸张,即事写情,表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捷报传来后诗人的惊喜和憧憬,激情迸发,气势畅达,风格明快、刚健。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首联突起,写好消息从天而降的反应。“剑外忽传收蓟北”,“忽传”凸显了捷报来得非常突然和意外。“初闻涕泪满衣裳”用夸张格形象传神地刻画“初闻”捷报瞬间的情感大爆发:喜极而悲、悲喜交织、悲喜交错。
颔联紧承,写妻子儿女和自己的心情。“却看”和“漫卷”相承、“愁何在”和“喜欲狂”相对,两句构成流水对,分别从动作和表情上,表现整个家庭洋溢的狂喜过望、喜气洋洋的氛围。
颈联顺转,写对祝捷和返乡的畅想。“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仍然用流水对,“须”和“好”相对,呼应前文的“喜欲狂”,“白首放歌”“青春作伴”凸显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畅想。
尾联收结,写回乡旅程的飞速畅想。连用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是句内对,又是句间对,构成工整的地名对;而“即从”“便下”关联词的绾合,则使上下联一气贯注,构成流水对。“穿”“向”的动态描写形成示现的景象。
语音修辞方面,江阳韵的选取、“峡”和“阳”的迭映、三个流水对的连用,不但带来了音乐美,而且促成了情感色彩的强化、画面的流转和气势的贯通。
(三)纪游类诗,多为借景言情,叙议结合,情溢于表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甫《九日》)
此诗写诗人重九登台的见闻和忧思,修辞上主要通过词语修辞、句式修辞和婉转、映衬等辞格的运用,将叙事、议论、写景和抒情“打通”,借以寄托怀乡思亲、伤时忧国的情怀,言语风格以自然、含蓄为主。
词语的选择和使用上,首联“独酌、抱病、起、登”,颔联的“无分”集中刻画了诗人的身心状况,颈联的“殊方”“玄猿”“哭”和“故国”“白雁”“来”相对照,用于揭示突出景物的特色,彼此映衬并用于映衬诗人的情感,尾联“萧条”“衰谢”对举,凸显弟妹和诗人共同面对的艰难处境,而这一切根本上则源于“干戈”(借代战事)。
句式的选用上,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将整句(对偶或准对偶)和散句(散行、形式)配合起来,整中有散,散中有整,既收凝练之效、集聚之功,又得灵动之美。从格律的处理来看,这种整散配合跟这首诗全篇用对仗但以宽对为主的用对格局,呈现出大体对应的关系。其次,颔联多用虚词,也打破了律诗的一般惯例,介词“于”和“从”、连词“既”、副词“不”、否定动词“无”和能愿动词“须”,进入诗句中各司其职,丰富了对仗的形式和表意。从中也可见出诗人对仗技巧的高超和创造。再次,在陈述句中参用感叹句,虽属律诗常见句法技巧,同样也有力地配合了该诗结尾转入直抒胸臆,对诗意的升华。
辞格使用上,颔联在结构上用假对,借“竹叶青”酒的“竹叶”二字与“菊花”相对,用对巧妙,新颖别致。这两句在表意上用了婉转格,借议论兼抒情的方式,去实现叙事和写景,以此显化了主观情感色彩,也增添了诗歌语言的情趣。“菊花”“不须开”,恰恰说明菊花实际上开了,而且开得很盛(这才会引发诗人的牢骚使气)。“菊花”以及颈联的“猿哭”和“雁来”,都对环境有烘托作用,也自然被借来映衬诗人的忧思悲情。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杜甫《登楼》)
这首诗写登楼所见所感,即景抒怀,主要借助词语锤炼和倒装、夸张、映衬、借喻、婉转等修辞格凸显景物特征,抒写诗人深沉、浓烈的思想感情,风格刚健、含蓄。历代诗评家对这首诗评价极高。
首联写登楼所感。一二两句间因果倒装,为的是突出“伤”情,起势突兀。“花近高楼伤客心(即客心伤,为押韵而倒装)”触景生情,同样是借乐景来反衬、突出哀情。“万方多难”用夸张,概说、强调现实困境,显明整首诗抒情的背景和基点。
颔联写所见壮丽景色。“春色”美,“浮云”“变”,“来天地”表现空间阔大,“变古今”表现时间久远,两句对仗工稳,营造了一个雄浑、壮观、深邃的意境。
颈联承上联即景抒情。自然的满目春色反衬了人世的“万方多难”,浮云虽然古今变幻,大唐的气运长在。“西山寇盗”用来借喻吐蕃,“终”和“莫”相对,凸显诗人的鲜明的爱憎和立场。此联用流水对,增加了语势的变化和流动。
尾联咏古抒怀。先用婉转格,借对后主的评判暗讽当朝的昏君,后用《梁甫吟》代指所作《登楼》,表达对贤相的仰慕,暗寓报国无门的伤感。其中的“可怜”“聊为”,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
此诗借登高写景抒怀,胡应麟《诗薮》推重该诗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指出该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
全篇皆用对仗,且为排比、对偶的整齐形式构成的工对,同时还借助词语修辞、句法修辞和夸张、摹状、映衬等辞格,描写所见壮丽秋景,倾诉悲秋伤时、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气势磅礴雄壮,感情慷慨激越,风格刚健、谨严。
前四句写登高所见景物。首联对起,用句内排比分别描写高处和水边的三个景物,节奏急促,意象密集。“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全用主谓结构的描写句,六个形容词的选用准确传神地体现了各自景物的特色,组构成精美的画面。
颔联着意描绘两幅特写。“无边”“不尽”用夸张,“萧萧”“滚滚”用摹状,仰望只见木叶茫无边际、萧萧而下,俯视则见江水奔流不息、滚滚而来。自然景象的写意勾勒和工笔刻画,显然对接下来情感的抒发起到了烘托、映衬的作用。
颈联叙述人生遭际,“万里”“百年”都是以实代虚的借代,叙述中点明了“悲秋”“多病”“独”等情感,纵(时间)横(空间)交错,营造了开阔深广的意境。
尾联写眼前的处境,诗人有意将“艰难”和“潦倒”分别置于句首加以突出,并引出白发日多、护病断饮的具体表现。而“艰难”不光属于个人,借此点明了时世的艰难,这既是个人艰难潦倒的根源,也是诗人始终不忘伤时忧国的表现。
三、七律组诗:修辞对篇章内涵的扩容
以上我们对杜甫七律修辞特色和创新的考察,着眼于单篇代表性作品,还必须要提到的是他的七律组诗。《咏怀古迹七首》《诸将五首》和《秋兴八首》这三组七律都作于诗人晚年,一方面代表了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成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杜甫在七律组诗创作上的开拓和成就。诗人将组诗在主题、题材、思想、形象、结构和风格等方面的整体性与单篇诗歌在内容、章法、句法、字法和风格等方面的多样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在七律组诗抒情、表意、造境的高度上独领风骚,在艺术风格、修辞表现的丰富创新上独树一帜,使七律组诗在他笔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惨淡经营的艺术巨制。
以《秋兴八首》为例,前人评价极高,认为是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的巅峰之作。就其主题而言,即诗题“秋兴”,也就是秋日所感、秋日所思、秋日景象和秋日人事所引发的想象、记忆及情怀。内容上,前三首写眼前的景、事、情,后五首写悬想、回忆的景象,与现实对比。结构上,不仅有基于内容联系的“意合”,而且借助时空词语、表情词语、动作词语等作为线索和纽带,在形式上构成首尾呼应、上递下接、总分交错。从修辞角度看,该组诗注重章句间的衔接连贯,讲究词语和句式的锤炼,主要用到的修辞格有映衬、双关、示现、比喻、用典等,言语风格含蓄、绚烂、谨严、典雅。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杜甫《秋兴八首》)
第一首总写夔府秋景,“孤舟一系故园心”点明客中思乡,开启了组诗的序幕。用“凋伤”“萧森”“兼天涌”“接地阴”写景,赋予景物人情,凸显其壮阔险恶,并用“他日泪”“故园心”两个名词句的“情语”分别置于“景语”后,加以突出,使得这首诗景中蕴情,写景对于抒情具有突出的烘托、映衬作用。
第二首写夔府暮景,叙事和写景交错交融,并与抒情相映衬。“落日斜”和“月”“映”“花”在写景中叙述时间更移,“望京华”在组诗中有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颔联“实”“虚”相映,叙事凸显抒情;颈联一写想象虚景、一写眼前实景,彼此映衬;尾联用祈使句写景,交代时间,引出第三首。
第三首写夔府晨景,是第二首的延伸。首联以自然的“静”反衬内心的不静,次联用连用重叠摹状,凸显诗人的飘荡江湖无所依归之感,后四联借用典(用事和引语)暗写自身不得志、不如愿的遭际。
第四首写长安变局,在组诗中居于过渡区间,承上启下。布局上,前有“闻道”引领,后有“有所思”收束,中间四句用示现,描绘亲历过和想象中的变化及困境。“似弈棋”比喻兼用典,意指众多文武官员背弃唐室,局势多变。“悲”“思”明点、“鱼龙寂寞”暗衬,加上中间四句景中蕴情,诗人的家国情怀也得到了一定表现。
第五首写宫廷早朝,回想蓬莱宫阙和早朝场面。前六句均用示现,借用典故描绘皇宫的壮观和早朝的盛况,增其典雅色彩,末两句委婉表达不能报国的失意和忧虑之情,用“惊”点出只能不时地沉醉于美好的回忆中,聊以自慰。
第六首写曲江亭苑,表现昔日繁华不再。中二联用示现,描绘今昔对比的景象,前后映衬,鲜明的景物对照又与诗人的情感相映衬。“接素秋”引出对曲江的想象,“回首”与之照应,点出抚今思昔,“边愁”“可怜”“自古帝王州”,表达了无限惋惜的同时隐含对帝王一味追求歌舞享乐的斥责。
第七首写昆明池水,从回顾到想象再到眼前。前两句借古言今,以汉时壮盛写唐朝当年的盛景,接着两联用示现,“虚”“动”“沉”“坠”四个动词紧扣景物的特点,描写想象中昆明池冷落荒凉的秋景,今昔对比,映衬今时局势的衰败。最后两句仍用对,“关塞极天惟鸟道”用夸张,极言长安遥不可及,“江湖满地一渔翁”用借喻,把自己比作漂泊在无边江湖的一个渔翁。
第八首写渼陂风光,前六句写景,后两句抚今追昔,为组诗作结语。前三联用示现,描绘回忆中的景象,首联连用地名写渼陂的环境,“逶迤”点出其特点;次联用倒句,将“香稻”“碧梧”前置加以突出,彰显物产丰美;颈联写春游的盛景,“拾翠”“同舟”表现游人的雅兴、和美。尾联今昔对照,“彩笔昔曾干气象”,回忆当年渼陂春游的诗情,“彩笔”用典;“白头吟望苦低垂”,今天在远望长吟中,白头却痛苦地深深低垂。“末二句收本篇,兼收八首”(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七)。
王船山曾评价《秋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船山遗书·唐诗评选》卷四)。单从八首诗在修辞方法运用和言语风格的表现上看,也充分体现了整体性和丰富性的统一。
四、拗体七律:修辞对诗体樊篱的突破
杜甫晚年在拗体七律的创作上也有重要探索,并影响了以宋代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等众多的后来者。所谓“拗体”是指在平仄上有意突破格律要求,拗而不救的一种特殊的近体诗,有绝句和律诗,后者也被称为古风式的律诗。王士祯《分甘余话》说:“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族筛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赵嘏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唐代李白、王维、杜牧、崔颢、李商隐、陆龟蒙、皮日休等都写拗体律诗。宋人继承唐人,也写拗体律诗,如苏轼、黄庭坚、陆游等。
从修辞角度说,拗体律有意识地在局部打破律诗以对称为原则的结构定势,在字法、句法、章法的讲究中增添了声律的变化,避免了过于圆熟滑易的局限,也有利于顺应表情达意的某些特殊需要。
杜甫在七律中有意识地尝试打破诗体的惯例,采用这种偃蹇生硬的声律,表现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其《白帝城最高楼》《崔氏东山草堂》《白帝》《愁》《昼梦》《暮归》《晓发公安》都是拗体律的名篇。以《白帝城最高楼》为例。
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杜甫《白帝城最高楼》)
作者以古体诗的语言入诗,除第三句外,其他各句没有一句完全合律,二四六句皆用古体标志性的三平调,犯律诗大忌,是典型的通篇拗体律。这一独特的声律模式应该说跟诗歌内容是协调一致的。此诗写诗人登高望远,所见之楼高、峡险、江流无限的突兀奇崛之景象,所生之独立苍茫、忧国叹世之感慨。主要用拟人、夸张、用典等辞格,此外两个散文句式的选用也有特殊作用,风格则是谨严、绚烂的。句式修辞上,首联“独立缥缈之飞楼”和尾联的“杖藜叹世者谁子”分别为二五、五二的节奏模式,不合于七言律诗的四三(或二二二一),尾联用设问句。与通篇用拗的特点类似,既带来整首诗与众不同的新奇变异,又和一、三、四句的拟人和五、六句的夸张一道,合力塑造了奇异独特的诗歌意境和诗人形象。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又呈吴郎》)
这首诗的“拗”主要体现在篇法上,用诗的形式来劝告吴郎同情、体谅一个寡妇邻居的“扑枣”行为。修辞上主要用词语修辞、句式修辞和夸张,将叙事、议论和抒情融为一体,以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风格明快、自然。
标题用“呈”,有庄重的书面色彩,表达尊重之意,更易于为对方所接受。
开头四句叙述、说明自己的做法和想法,以实际行动和朴素道理来现身说法。“任”表明明知而放任,“无食无儿一妇人”单列,刻画人物极为贫穷、无依无靠的处境。“不为”和“宁”、“只缘”和“转”相配相映,“困穷”“恐惧”相对相合,再用设问句形式,使作者的解说带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颈联委婉地批评吴郎的做法。“即”和“便”、“虽”和“却”两对关联词语配合使用,表达双重的让步关系,曲折达意,入情入理,“多”和“甚”强化局部的表意。
最后一联叙述妇人的诉告和自己的忧思,用眼泪来感动对方。由个人“征求”到“戎马”现状,用“贫到骨”“泪盈巾”对说,带夸张色彩而又有事实基础,更能打动人。
整首诗融虚词和典型的散文句式入诗,使叙述、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各种写作方式自由切换,各善其场,不但内容上表达更为细腻自如、意脉连贯,而且在形式上化呆板为活泼,将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和散文的灵活美、自然美,有机地兼容,沉郁顿挫而又韵味无穷。
综上所论,杜甫七律在修辞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成就主要表现在发掘抒情能效、创造审美世界、扩容篇章内涵、突破诗体惯例等四个方面,而这些修辞功能得以体现和强化,则离不开众多修辞手段的分工与合作:点染、留白等婉曲类修辞手法的选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不同话语形式的合作与融通,形合、意合等多样化篇章修辞方法的配置,声律、句式、篇法等诗体变异要素的渗透。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和成就,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创新性品格,并且奠定了其在七律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本文对于修辞和文学之间关系的观察,表明这一领域还有更多未受充分重视的视角和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