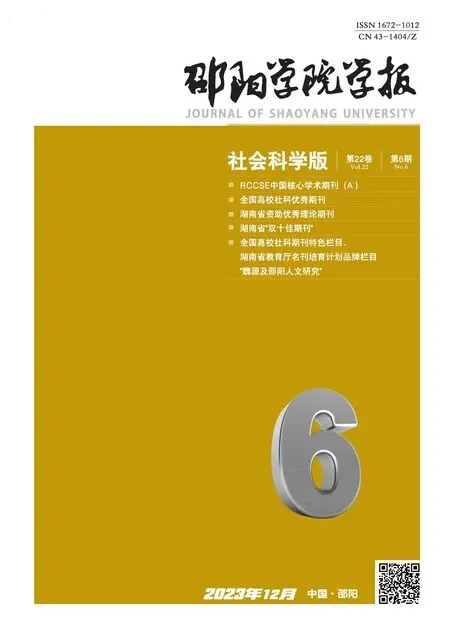林语堂共情翻译的触发因素探究
唐 瑛
(1.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邵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林语堂通过译、创、编对中国传统哲人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艺术进行现代化阐释,获得了西方受众的主动接受和传播,可谓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东学西渐的先锋人物。目前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作品翻译策略分析,如陈荣东[1]、郎江涛和王静[2]对林语堂翻译专论万字文《论翻译》的深度挖掘。王珏[3]及冯智强和庞秀成[4]对散见于副文本中的林语堂翻译观及翻译思想进行了概括总结,前者解读了其中所体现的译创动机、译创思想、译创策略等,后者提炼了林语堂对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原则、翻译心理及翻译伦理的独到见解。但目前从情感维度整合林语堂作品及其内、外副文本相关译论话语,探析其翻译思想的成果较为有限。
一、“共情翻译”的内涵
德国审美心理学派创造并发展了“共情”这一概念及其各种学说,尤其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施坦因(Edith Stein)、舍勒(Max Sheler)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围绕“自我”“他者”“世界”对“共情”的内涵进行了不断的深化和丰富。其中,施坦因的观点强调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互惠的关系,肯定“共情”中包含认知活动[5]42-43,最接近翻译传播活动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古典文论中也不乏关于艺术、艺术与情感关系的讨论。中国式的“共情”主要基于“天人合一”美学观的“移情”或“表现”等核心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黄侃将其解释为“心境相得,见相交融”之“移情”。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中首次出现这一概念。“庄周梦蝶”则是对这样一种主客体关系的最经典诠释。陆机的“诗缘情”,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白居易的“诗者,根情”,汤显祖的“情生诗歌”都表达了艺术源于情感,是情感的表达。梁启超的“趣味”,王国维的“境界”,朱光潜的“情趣”,宗白华的“情调”,丰子恺的“真人生,真善美”都彰显了审美的情感内核,强调了审美和情感的本质关联。
“情”是中西美学思想的精神特质之一,也是林语堂翻译传播思想的重要表征。在《论翻译》中,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以“情”为核心的“美译”思想,认为美译需“达意”“传神”,“神”即字词所带“情感之色彩”,语言不仅“表示意象”,而且“互通情感”[6]335。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未对“情”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其主张与作者、读者“互通情感”的翻译思想散见于其译作副文本及文评话语,并贯穿于其翻译传播行为始终。从“共情”的内核和特征及中西美学情感论主要观点,可见林语堂所主张的情感互通就是“共情”,即基于译者与原作(者)的情感共鸣及与译者对译入语读者的同情关照,实现译者与原作(者)对译本情感的共建,使译入语读者和译者对译作达到情感共享,最终实现译者、译作、译语读者对原作(者)的情感共传。“共情”的特征表现为主动性、双向性及流动性。在中国翻译史上,林语堂在翻译创作实践中本着对作者、目标读者、艺术所应负的三重责任[6]327谱写了一曲有着特别韵味和特殊意义的共情篇章。林语堂的共情翻译观在其大量副文本译论话语尤其是序跋、后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笔者在另一篇文章[7]中已统计相关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在此不赘述。本文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总结相关译论话语,深入考证和分析林语堂共情翻译的触发因素,探索情感、审美、认知三元共情相互渗透对译者翻译观和翻译策略的影响以及对译作传播效果的优化作用。
二、林语堂共情翻译传播的触发因素
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最神奇的力量就是能够赋予作者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能量,使其能与理解他、欣赏他的每位读者随时、随地进行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一位能深入作者灵魂深处的译者必能透彻理解、欣赏作品,经由语码转换阐释作品,通过叙事调适传播作品,让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读者熟悉、了解、理解、欣赏作者,使作者和作品的生命得到不断延续和丰富。然而,因为个人的情感、认知、经历的差异性,共情的触发因人而异。林语堂与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共情触发也具有其内在的特点。
(一)译者与作者--精神的会合
基于副文本话语的分析,可发现林语堂所喜好的作者几乎都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和谐共存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都生存于生活的现实和诗意的看法的冲突之中[8]ⅩⅧ。具体说来,林语堂与作者之间的共情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触发的。
1.圣人的思想
林语堂不仅是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求真的愿望。[9]59他所喜好的作者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通透的思想,无论是哲思大师老子、孔子、庄子等,还是文学高士陶渊明、苏东坡、袁宏道等,都是慧心独具、才思敏捷、文思涌动之人,对社会和人性有着自己独特而又深刻的洞察,同时又崇尚自然和本真。林语堂曾用“赋性颖悟,见解超群,胸中有万丈光芒”[9]61来形容他们。虽历经坎坷,他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超凡脱俗而又真诚质朴。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人如何为人”进行了深刻思考并呈现出不同视角,在不同层面和林语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文化和理性,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追求自然和本真,而陶渊明、苏东坡、袁宏道等文人的思想是对两派思想的选择性接受和吸收。我们能看到他们崇尚文化和理性的一面,也能看到他们追求自然和本真的另一面。这也是自称为“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本身的显著人格特征。因此,林语堂与他们之间的共情是自然而然的。
2.诗人的远方
林语堂认为人生不仅需要理智冷静的思考,还需要热情美好的想象,二者和谐共存才是理想人生。他所译介的作家都满怀浪漫主义的情怀,无论现实境遇如何,对生活总是充满热情和希望。林语堂推崇老子,因为“老子的格言传达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情绪”[10]4。林语堂敬佩苏东坡,因为他具有“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11]6。林语堂喜欢沈复,因为沈复身上具有“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恬淡自适和知足常乐的天性”[12]ⅩⅢ-ⅩⅣ。林语堂力推张潮,因为“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13]。他译介给西方读者的还有“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14]4等。林语堂的这些“朋友”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快乐生活,对生活不失热情和热爱。他们所诠释的正是林语堂所推崇的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
3.世人的日常
林语堂的译创从未离开过对生活日常的关注。林语堂本人也可谓生活达人,既会对一本精绝的诗词爱不释手,也会迷恋一块香喷喷的红烧肉。林语堂译介的孔子并非高高在上的圣人,他风趣幽默,会在雨中唱歌,能演奏乐器,对饮食很讲究,对穿衣搭配有自己的眼光,甚至还对衣裳有过小发明,孔子所过的生活是充实而快活的。林语堂译介的苏东坡除了文采横溢,还是“酿酒的实验者,工程师……瑜伽术的修炼者”[11]5-6。《浮生六记》深受林语堂的青睐,他不仅对该作细心品读、精心翻译,还多次将其收录在其他编译作品中,因为沈复夫妇“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12]17。对生命和生活真谛的思考和浪漫的遐想最终需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归属,知足常乐、淡泊名利、闲适轻松的生活观念正是林语堂和他所推崇的大多数作者所毕生追求和信奉的。
(二)译者与作品--审美的契合
林语堂博览中西作品,尤爱中国文学,遇到自己钟爱的作品常爱不释手,异常珍惜,并会用自己的笔进行推介和传播,向生活在动荡的时局之中或机械化、快节奏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模式中的西方读者呈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和生活艺术,带给人们亲近、清新、真实、自然的感觉。纵观其译介作品,几乎都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它们触发了译者与作品之间的共情。
1.文字的真实
林语堂推崇性灵文学,在翻译材料的甄选上,他“都精心地选择具有‘个性’和‘性灵’的作品,来实现文学的解放”[11]62。林语堂对“性灵”的解释是“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表达之文学,便叫性灵”[15]238。换句话说,林语堂推崇的是能表达作者真实情感和思想的作品。真实是林语堂评判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林语堂所欣赏的真实主要表现在内容和情思两个方面。从副文本的译论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free/freedom)和“原创”(original)高频出现。他倾向于选择传记、小品文、诗歌、传奇故事等文体,因为它们更能反映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更富有审美的内蕴。他编译《苏东坡传》,因其诗词文章皆为“自然流露,顺乎天性……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11]6。他精译《浮生六记》,因“其体裁独特,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12]ⅩⅣ。他认为杰作必然“真纯”,就像“宝石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11]12。叙真实故事,抒真情实感,这是林语堂心目中佳作的重要品质。
2.意境的唯美
林语堂的美译观要求形式美和内容美的和谐统一,他对原作的要求也是如此,认为作品意境的唯美就是用美妙的文字记录美好的事物。在叙事特征上,如《幽梦影》采用了议叙参半的闲聊叙事模式,苏东坡诗文体现了刚猛激烈、遒健朴茂的语言风格,《聊斋志异》运用了精细的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在文风艺术上,如《古文小品译英》中《兰亭集序》隽妙、《祭震女文》温情、《莺莺札》深情、《声声慢》愁情、《志林书札选》幽默、《琵琶行》感人、《说散记文》清雅。在文体艺术上,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ChineseShortStories)中的传奇故事,其中半数来自唐朝,林语堂认为唐朝不仅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传奇的经典时期,人们的想象更大胆、更自由、更有活力、更轻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浪漫、最富有想象力的时期。在主题上,众多作品中包含中国经典文学和高雅文化,前者如儒、道典籍以及诗词、小品、传奇等,后者如中国人如何品茗、行酒令、游山玩水、看云鉴石、听雨吟风、赏雪弄月、养花畜鸟等生活艺术。作品的风格、情感、文体、主题共同构建的唯美意境和林语堂的美学思想不谋而合。
3.普世的情感
林语堂一生追寻对人性的准确理解,极力推崇人道。他偏爱的作品皆表达了充沛的情感。在《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序言中,林语堂说“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怜悯、爱或同情,而带给读者以愉快之感”[8]ⅩⅢ。这段话语可以说明林语堂对作品情感因素的强调。情感是普世的,不分国界,能与所有读者分享。在众多情感之中,他最推崇的当属“乐”: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趣之“乐”,颠沛流离中的苦中作“乐”,无论顺境逆境都能知足常“乐”。这也是他想要传达给西方读者的东方生活艺术。“乐”在《浮生六记》译者序中出现了14次,在其他作品中也高频出现。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出现9次,在《古文小品译英》序言和作品介绍中出现7次。除了“乐”,林语堂还倾心于“爱”。男女之间的爱情是被他选中的很多作品的主题,其中他最爱的当属描述夫妻之爱的《浮生六记》。蕴含着充沛而真实的情感的作品触发了林语堂的共情,他坚信这种作品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三)译者对读者--心理的迎合
林语堂对读者的关照、与读者之间的共情,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更是他融通中西文化的内在追求的一种外化表现。他的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他的作品在国外受到好评,甚至成为西方读者的枕边书。每当问及中国的文化与思想时,西方读者常以“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回应。这足以说明林语堂与读者之间的共情效应。他的作品能增加中文读者学习英文的兴趣,也能让西方读者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体会中华文化的优美与价值。基于副文本的译论话语,可发现林语堂与读者共情的三种触发方式。
1.精选翻译文本
林语堂热爱生活,追求个性自由,崇尚性灵。如前文所述,个人的价值观念无形中影响了他对作者、作品的评判,也成了他选择翻译文本的主要标准。同时,对美好生活和自由随性的向往也可视为人之共性。这样的选择本就很容易和读者产生共情,再加上林语堂自始至终在翻译、编辑的过程中观照读者接受心理,这种共情就显得更为强烈。如在《英译重编传奇小说》的序言中“读者”(reader)一词出现10次之多,每一次提及都在阐明基于对读者的观照选择所译传奇故事。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中传达的普世情怀,如对人性的洞察,对人生的思考,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中的异域文化特色和历史真实性或是其奇幻色彩、幽默笔调,能满足西方受众的猎奇心理[8]ⅩⅢ。林语堂的文学才华和中英文造诣出众,选择的文本雅俗共赏,既诠释了中国文化之精华,可供研究者研读,又呈现了中国文化中怡情养性的生活艺术,适合普通读者在闲暇时翻阅欣赏。
2.活用翻译策略
副文本话语中关于翻译策略选择的陈述也表明了林语堂对目标读者的共情考虑。鉴于文化差异,他习惯于从叙事角度通过译写、编译、改译、译述[16]142等手段对原作内容进行变译。他曾在写作《生活的艺术》时说:“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却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14]5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他也表达过相似的思想:“原文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11]9在《英译重编传奇故事》的序言中,他也坦诚地说,鉴于读者的不同,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大部分故事做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在《白猿传》的翻译简介中读者可知他将故事的主题凸显为欧阳纥失妻之痛和对妻子的钟情[8]24,在《简帖和尚》[8]44《碾玉观音》[8]68的翻译简介中他也对故事结局的改编进行了说明等。
3.类比中西文化
副文本话语中对西方文化的类比是林语堂与目标读者共情的另一个表现。如在《浮生六记》自序中介绍作品人物芸时,为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其恬淡自适的生活的美好,他把芸代入到了英国的生活场景,“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12]ⅩⅢ?为了表达他对沈复和芸夫妇的敬慕和哀思,他借用了西方的艺术作品来抒情,“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帕凡舞曲(Pave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马斯奈(Massenet)的小调(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12]ⅩⅣ。他又将作品中夫妻的安乐比作“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12]ⅩⅣ。他为说明孔子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将《论语》比拟成中国的“圣经”;为说明唐朝传奇故事的魅力,将其比拟成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文学。此类比拟不胜枚举。这种中西文化类比诠释有助于激发异域文化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和共鸣,并易于理解和接受。
三、结语
对林语堂共情翻译触发因素的探究应深入译者与作品、作者和译语读者的情感、审美、认知的互动关系中。生发于译者自身经历经验、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共情能力对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译本效果具有极大影响。它产生于译者的内部意识,通达作者的思想内核和作品的内涵意蕴,满足了译语读者的内心需求,是优化译本质量及其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