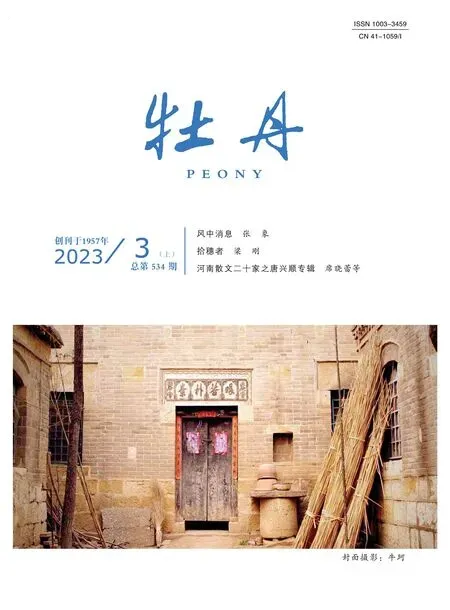筒子楼记忆
刘丽华
我算是筒子楼里最后的房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因离家较远,小县城也不通公交车,一点儿工资也不够租房用,于是向厂里打了三次报告,才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二人职工宿舍。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筒子楼。一条长廊,连接两面的各家各户;一方门帘,保护着各家的隐私。每户门对门,门口支着蜂窝煤炉、小橱柜或杂物,白日里视线也不好,因为两头才有窗户。楼道一侧是水房和公厕。
走廊的墙体漆黑,墙顶很高,悬着一只昏黄的电灯泡。若是都关上门,楼道就像一条隧道。门若是敞开,房间内又一览无余,因此,半截布帘发挥着大作用。
一到做饭时间,走廊和水房里人来人往,盆桶锅壶当当作响,洗菜淘米提水的人排起一字长龙。人穿过走廊,身子得侧着,你让我我让你的。孩子们可不管这些,东躲西藏跑着疯玩。整个筒子楼,既热闹又拥挤,充满人间烟火气息。
大家早习惯了,做着饭,聊着天。哪里的蜂窝煤好用了,哪里的蔬菜新鲜了,哪里的鸡蛋便宜了。若谁家炸猪油,整条走廊都香喷喷的。若谁家油爆辣椒,保准集体咳嗽。谁家酱油没了,一张嘴,一只酱油瓶就递过来了;谁家煲汤,缺了生姜,一吱声,一坨洗好的鲜姜飞了过来;谁家清炒苋菜,没蒜瓣儿佐炒,嚷一声,一小碗肥白的蒜瓣儿就传递到了跟前。一到过节,各户拿出一道好菜,桌子一拼,就是一场欢宴。
晚上起夜,每户必备的工具是手电筒。早上洗漱又是挤挤挨挨,人声鼎沸。最煎熬要数夏天,筒子楼真成了铁筒子,闷热不堪,最难受的是晚上,关着门睡吧,就算吊扇成夜转,汗水也不曾干过。打开门吧,也不见凉快多少,还睡不踏实。
我住在顶楼,到了梅雨季节,会漏雨。房间内的两张行军床,好比两颗棋子,移来移去,挪东挪西。住着一大家子的人家,房间塞得满满当当,衣服被子被打湿是常事,辛苦不堪多言。
天气多变,有时突然下雨了,有人一想到晾晒的衣物没收,便从岗上急匆匆跑回楼顶,却发现所有物什早有邻居给收拾停当了。
各家的小孩好得像是一家子弟,一早爬起床,脸也不洗,串了左邻串右邻,串了东家串西家,在一起玩耍,到了饭点儿,大人叫都叫不回。一个孩子有了零食,等于每个孩子都有了。
谁家做个好菜,量都备得足足的,指不定哪个孩子会去蹭一块儿讨一勺的。谁家孩子磕着碰着烫着摔着了,大人不在家也不要紧,总有在家的邻居会帮你妥善处理;谁没时间去幼儿园接孩子,等会儿就有人给你家的孩子一起带回来了;谁家深更半夜有急事,把孩子从热被窝里抱出来,随便敲开哪家的门,只需将孩子塞进人家的被窝,心放肚子里走人得了。平时里大家买瓜,不管西瓜冬瓜南瓜,都挑最大个儿的,为的是给大家分着吃——分享的哪是瓜呀,是一份难得的邻里情。
互帮互助中,筒子楼的孩子渐渐长大。谁家孩子考得好,是整个筒子楼的喜事,各家各户一商量,凑份子钱买辆自行车作为奖励。孩子也懂得感恩,一到厂里分福利,就用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帮大伙把物资托运回来。大伙会说,咱筒子楼的娃娃就是好。
一层筒子楼就如一个大套间,同住一个屋檐下,牙齿舌头难免有个磕碰的,但谁都不会过多计较,一句话,一杯酒,和和气气话说开,不愉快就算过去了。
后来,筒子楼随着城市的改建拆了,厂子也随时代的改革变卖给了商家,筒子楼的老街坊也为生计奔波而天各一方。但偶然街头相遇,谁都会停下来,站到街边亲亲热热说一会儿话,相互问问各家的情况,彼此道一声珍重。提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自己创业了,都一脸的欢喜,感叹说,咱筒子楼里走出来的孩子,一个个的心胸豁达,生存能力还强,有出息得很!
如今回想起筒子楼的生活,好像就在昨日。不由我想起当下住在单元房的邻里之间,多像同一空间下生活的一群熟悉的陌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