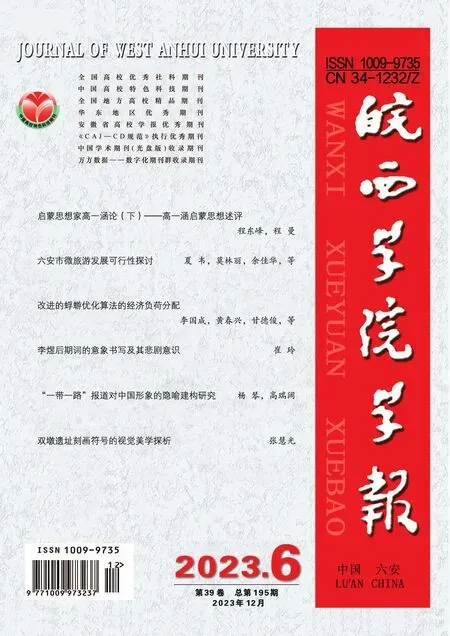网络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异化
欧阳杰,张 军
(1.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41;2.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化转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流行和关注的热点话题。调查报告显示,网络直播中女性主播占主导,占比高达78.8%。职业主播中男女主播比为1∶5[1]。诚然,女主播是网络主播第一大群体。现实中,依据网络直播内容可将女主播分为娱乐类、生活类、游戏类、健身类、医疗保健类、教育类等等类型。其中娱乐类直播门槛低、受众广,直播内容具有简单、随性、自由的特征。因其社会属性和社交属性较强,受到广大女性用户的追捧,并日益成为一门新兴职业而备受广大年轻女性青睐。而女性形象也愈来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一、网络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一)“他者”的建构:新媒体与受众的促动
人工智能与网络技术的融合促使了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社交场域。网络直播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它为女性用户提供了新的空间场域,即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流动和即时交往互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媒体,它也牢牢掌握了信息传播中“形象符号”建构的主权。波伏娃曾指出在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东西称之为女性气质,男性意识和思维就等同于全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思维。女性形象依然是“他者”所构建出来的,利用新媒体这个巨大资源库,女性在自我参与和自我表达中获得话语权和主体性意识,塑造出“新”的形象。
网络女主播形象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观众的影响。一方面,资本的驱动加剧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人被高强度和高压力工作所迫胁同时,又被闲暇时的百无聊赖所充斥,网络直播被身处网络时代的现代“打工人”当作消解与慰藉情绪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受众作为网络直播中的参与者,从新兴媒体中来接受的消息更加多元。消费享乐观念促使直播受众通过直播消费或者礼物打赏的方式对主播的直播表演进行自我反馈,来满足自身的替代性幻觉和情绪的消遣。而网络女主播“被迫”根据受众需求特征和喜好习惯做出人情和面子导向的回馈—进行自我形象的改造和构建。
(二)自我的建构:身份认同与主体性的表达
1.个体身份认同的获得
现代社会正处在卡斯特所言的“流动空间”,网络构建了我们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是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等构建起来的,而支撑流动的空间形式也应该是流动的[2]。相较传统的被动性、归属性认同而言,在多元且流动的网络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和形象具有虚拟性和建构性的特点,并且认同是主动性、建构性的,认同的维度也更加多元化。在以网络直播为媒介的活动中,主播在网络场域中进行自我展演并与观众进行交往互动,获得多种形式的身份认同。
认同过程是一种追求与他人相似或相区别的过程,表现为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两种形式[3]。一方面,网络女主播借助各种先进的网络工具和美化技术,在“前台”呈现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表演。女主播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自我形象,满足观看者视觉享受。女主播会在直播活动中获得观众或粉丝的虚拟礼物与称赞之词。另一方面,女主播通过直播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直播和受众关系网,比如观众在直播间里的点赞、分享、评论及打赏行为。同时,女主播还在网络直播中与观众展开有选择的互动,比如感谢粉丝的礼物,回答粉丝的问题,鼓励粉丝送出礼物,帮助粉丝蹭热度上头条等行为活动。促使粉丝产生进一步互动需求,获得陪伴感和存在感,满足观众被理解和被需要的需求以及“出人头地”的胜欲心,构建出他人认同的身份特性。
2.个人主体性的表达
网络直播是当代女性自我呈现、情感表达的重要介质,又是个体日常生活、价值意义、人格个性的重要投射。当代女性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创造出虚实交织的个人主体性活动。
身处网络时代,女性主播们通过直播活动构建形象表征的同时,也经历了新的内心体验与价值位移。首先,掌握话语权的现代女性逐渐开始为自己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传统思想文化中对于女性“理想人格”形象地刻画充分体现了温顺隐忍、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的女性气质,突显出女性的依附特性。这种固化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传统社会中女性社会角色的统一性和个人话语主权的消失。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默”且固化的女性角色以及人们对女性的“一致性”认同。现代女主播正是以网络直播为媒介创造出大量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语表达和个人诉求。在网络直播中可以看出,众多的女性对化妆品、服饰、旅游等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而且直播中也不断涌现出很多的商业精英女性、女明星、女网红等“新时代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运用自己的女性逻辑和思维方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中“失语者”到现代社会中“建构者”的转变,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并且利用这种话语权自主地进行自我身份形象的建构。同时,作为直播活动的主体,女主播在创造活动中充分展现着自己的潜能和个人特质,生产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彰显出现实社会中“意义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4]。另外,主播通过网络直播获得话语权的同时享有愈多的主体性自由和行动。网络直播中,女主播对于内容取材、选择场地、背景布置、展演方式、自我包装等“后台”活动都是自发且自由的自我选择、编辑及想象。在直播场域中,主播拥有不受限制的个体私人自由。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日常活动、生活经历、趣味知识、文化认知等等进行自由展演。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主播私人的“自我场域”,在这个疆界内自由自主地表达和行动,展现自我人格个性,分享个体自主性。
二、网络直播中女性形象的异化
异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含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了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并在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异化理论。异化有“分离,疏远”之意涵。马克思认为,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的活动结果,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统治人、制约人的力量可以称之为异化[5]。在当代社会和网络空间中,很多现象发生了异化。
身体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为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它更为关注社会变迁对身体的影响。身体作为一种媒介,逐渐成为网络互动中的一个要素,释放并接受新的连接和装配,是链接个体与社会有效通道。互联网延伸了身体的存在意义,在塑造身体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相分离的同时使身体呈现出新行为与新特征,构成新式的身体娱乐景观文化。在娱乐化时代的网络空间场域中,身体成为凝视的焦点,形象的建构从“主体虚构”向“符号异化”转变,身体不再是本真意义上的身体而是被欲望化、物化、符号化以及被规训的客体。
(一)消费化的客体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身体不单单是生物意义上的构成物,更是虚拟场域中的视觉消费资源和价值图景。以网络直播为媒介与载体的身体图像呈现出即时性、流动性和瞬时性的动态特性,有力地冲击着观众的视觉体验。在网络直播文化中,女性的身体被视为直播中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成为有价值的视觉消费对象[6]。身体与环境将观者置于当下,上演着身体的沉浸式狂欢。
身体展演在吸引观众关注的同时,也使身体在直播中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正如陈伟军所言:“网络直播放大了身体景观的视觉效应,身体的意义结构承载了性感、消费、享乐等内涵,参与其中的用户找到了一种欲望的简单替换物。”[7](P25)在以流量为主导的网络直播中,主播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和目光,竭尽所能地展现身体魅力。高挑的身姿、精致的妆容、光鲜的装扮甚至“网红脸”等女性形象成为女性追求直播观看者爱慕的“理想化”对象,并成为一种视觉和欲望的身体符号。网络媒体与性别的结合,促进了虚拟空间中女性与色相结合[8]。网络直播中,部分主播不惜以暴露、走光展示身体,使身体逐渐退却理性审美而成为魅惑的符号。更重要的是,性色化的视觉符码既会造成现实生活对身体的过度解读,也会使个体走进网络直播的误区。
(二)物化的客体
现代网络直播相较于其他的传统社交媒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屏幕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主播通过镜头展现出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姿态,在直播界面屏中呈现身体图像的特写,与观众实现身体“在场”的互动。物质身体通过网络直播被编码为视觉文化资源成为直播中的景观,在网络直播这种营销手段和消费情境下,身体被客体化为一种物品,成为可供观看和消费的身体景观。
消费始终是伴随着情感介入的,身体成为消费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主动的身体消费,在直播中观众的打赏行为就是身体消费的最直接体现,身体的商品化已经成为她们吸引和维系粉丝社群的重要因素。部分主播通过不断地变换服饰、装扮外貌、调整镜头、言语诱惑等来建构出“完美形象”,满足观看者的要求,以求得高额打赏和虚拟礼物,实现自己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此一来,在不断迎合他人眼光和要求中,身体便主动地成为一种可供观赏、品评和消费的物品。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直播平台,将身体物化为商家与消费者间的交流工具以此招徕观众的注意力。比如一些商家选择和利用女主播直播宣传一些生活日用品和奢侈品,将主播获得打赏打造成一种独到的经济模式。网络市场化的运作加剧了身体的商品化倾向,以网络直播为媒介的消费生产满足了观众的视觉消费、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身体在这种物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被开发和利用到了极致,加剧身体被消费化的程度,造成身体形象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符号化的客体
女性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部分,通过社会生活中女性的身体言说、行为表现,展现出个性、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促进了我们对于女性的认识。网络直播的发展和运用给予了每位展示者和受众新的空间和平台,更多的女性通过网络直播表达着精神意识,进而丰富自我形象的建构。然而以图像叙事为主导的网络直播在改变和修正了传统文化中女性单一脸谱和形象认识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社群对女性身体的崇拜和过度解读,忽视了本真意义的身体价值所在,逐渐使女性变为符号化的存在。
“女性美”的标准在网络冲击下逐步发生变迁,网络直播环境绘制出众多符合大众审美的形象符号。越来越多的女主播遵循着尖下巴、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以及卖萌的动作、娇弱的言语等大众化标准来形塑和展现形象,构成女性美的代表符号,成为符合大众审美的价值存在。正如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提到的印象管理策略,女主播会努力表演出与他人和大众所认同的标准和规范相一致的行为,不断改变自己的印象策略,塑造出大众认可的“理想美”形象。另外,网络直播强化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女主播通过镜头前的自我表演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主体形象,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开始对网络女主播外貌、身材和服饰进行模仿,这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于这种虚拟形象的审美认同和价值追求,同时使得受众将女主播视为一个美丽的、可满足欲望幻想的、可消费的影视符号。正如费瑟斯通所说:“消费文化中,……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9](P56)造成人们对女性身体符号的崇拜与消费。网络直播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符号转换被赋予了一种符号价值,在符合社会审美系统的同时更容易造成人们对女性固化和片面化的认识。
(四)规训与窥视
现代的个体身处网络空间中,满足于符号、虚拟带来的享受与快感。身体自以为窥视的客体成了实现观念规训的生产者,他们以身体异化的日常实践推动着自我规训与他者规训。网络直播中的女主播在某种程度上构建出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实际上女性身体在网络情境下不断被规训。在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直播所属的消费和交易属性,网络中的女主播在被观众观看、要求、打赏、赞美、诉求中不断地调整自我,构建出迎合他者的身份认同,沦为了被规训的客体。
网络直播的兴起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关系,人们可以在参与线下社会场景的同时可以即时地参与到线上场景之中,比如人们在教室里上课的同时观看线上直播课堂、在饭桌吃饭的同时观看电影娱乐。由于社会资本的推动,网络直播中女主播选择的直播时间更具随意性和碎片化。不难发现有大量不分时间昼夜直播的女主播,同时其直播场景的选取逐渐向客厅、厨房、卧室等私人空间延伸,直播内容也不断向私人领域窥探。本该闲暇自由的生活时间被直播工作所侵占,女主播在失去时间自主权的同时也造成私人时间的异化。置身于混合空间中的女主播在直播展演过程中,不断被凝视。
三、结语
从农业时代到机械时代再到网络时代以及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新的社会表象又会继续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从研究来看,网络直播作为彰显数字生活的一种基本社会事实,其为女性角色的社会性建构提供了新的社会场域。我们需要承认,在现代数字化社会,网络直播使女性从传统文化的“失语者”转变为能自我呈现和言说的“建构者”。这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主体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网络空间为依附载体的网络直播也对女性的身体产生了异化作用。更值得深思的是,虽然网络空间是一种新型且以流动时空为基础的场域空间,但其和在场空间并非相互豁裂,彼此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生、互构谐变的关系。即是说,任何一类空间变化都不可避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另一类空间变化。在此意义上,公众基于刻板印象对女性直播形成的主体认知会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这既不利于女直播者发展,亦有违于美好数字生活的价值理念。
时至今日,网络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典型特征,数字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趋势,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逐渐向数字元宇宙社会和数字元宇宙生活持续迈进。甚言之,我们不能畏惧甚至否定网络直播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但我们在欣喜其为日常生活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时,也需进一步思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研究认为,未来促进网络社会有序运行、网络直播良序发展、积极建构以美好数字生活为价值导向的直播生态,需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市场主体(互联网集团)以及女性自身相融合的空间治理体系。于政府而言,应尽快完善针对不同主题、特色数字空间的法律法规建设,让承载网络直播的各类空间都能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蓬勃发展。于市场主体而言,要始终把自身的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意。于女直播者而言,要积极提高自身数字素养,积极创造因应美好数字生活的数字文化,制作适合新兴媒体传播的精品文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