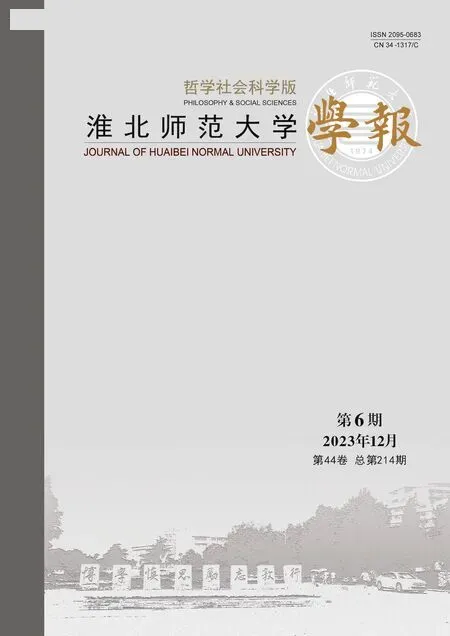奏议在古代书目中的归类变迁
王甜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奏议,是中国古代臣僚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一种上行公文的统称。它在我国目录学著作中的归类变迁暗含着奏议观念的变化过程。学术界主要从奏议的政治实用性或文学性的角度来分析它在古代书目中的部类变动情况,如孙董霞认为先秦行人词令和游说劝谏之辞向文学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大量极富文学性的政论文和文学辞章的产生,正是奏议史、集两栖性的根源[1];王志华指出奏议的著录历史形态决定了奏议兼具史学与文学特征的文体性质,也进一步造成了其在史部和集部中的游移[2];张守卫、武建雄认为从强调奏议的文学性到看重其政治性或史料价值是奏议类文献由集部调整到史部的缘由等等[3]。但是前辈学人并未从文本生成和发展的角度,深层次地挖掘奏议最初的性质和不同历史时期、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奏议的认识。故笔者不揣谫陋,分别考察奏议在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形态和部类归属情况,并结合时代背景探究其变迁根源,以期为今后的奏议文献研究提供目录学领域的支撑。
一、奏议在汉代史传和子书中的生成与保存
奏议的运作过程关系到我国古代政治的良好运转。章奏文书是经修改审定完成,进呈给君主的奏书文本,在运作程序完成后会被中央官府作为重要的文书档案整理保存。一般认为,档案与史书关系极为紧密,古时君臣之间的重要谈话、言论等都可能被史官记录下来成为档案。史官再将这些档案进一步整理,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被摘录到史书中的奏议而言,多是群臣上奏到中央被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故合理地猜测,章奏文书被保存在中央官府档案库中,并被史官适当地载录到史书之中。
作为我国记言记事之祖的典范——《尚书》《春秋》中所收录的奏议文书为此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4]13指出了《尚书》《春秋》的编纂正是来源于我国古代史官所记的档案文献。其中《尚书》作为我国第一部档案史料的汇编,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例,主要是史官对春秋以前重大史事和君臣言论的记录。《尚书》中诸多篇章都可以看成是后世“奏议”的雏形,如《皋陶谟》中皋陶为舜帝出谋划策、讨论治国大事的言论,显然是臣子向君主上书言事的源头。《高宗肜日》《伊训》等也均是记录臣子训诫、劝导君主之言论。以《春秋》为本的《左传》也记录了许多先秦时期群臣上言劝谏献策的事迹言论。
文章最早的存世方式是以“成文”而被史官作为史料保存的[5]。在奏议文初步成熟的两汉时期,史类文献保存的奏议最为丰富,其中以“正史类”保存的奏议数量最多,这主要集中在《史记》《汉书》《东观汉纪》等纪、传体史书中。总之,奏议是君臣之间沟通交流政治事务的媒介,是统治稳固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政治治理发挥积极作用,故其本质功能是社会政治功能。而正史是被中国古代政权一直奉为正统的史书,代表了编修与发布的官方权威性,因此,奏议文书档案被集中载录到正史中是政教正统观念主导下的必然。
但是,正史并不是奏议文书所依附的唯一载体。根据《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书类”“礼类”“论语类”和“孝经类”中,除了“春秋类”中的《奏事》二十篇,据其按语“秦时大臣奏事”知悉是秦朝廷臣上书言事的奏议外,其余每类都有的《议奏》篇章均是汉代石渠阁会议中讨论五经经旨异同的诸位儒生的奏疏。“诸子略”的“儒家类”“法家类”“纵横家类”等中的私家著述中也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录的奏议文有:“春秋类”:《奏事》20篇,《议奏》39篇;“书类”:《议奏》42篇;“礼类”:《议奏》38篇;“论语类”:《议奏》18篇;“孝经类”:《五经杂议》18篇,多为汉代石渠阁会议中讨论五经经旨异同的诸位儒生的奏疏。诸子略载录的奏议有:“儒家类”:《陆贾》23篇、《贾山》8篇、《董仲舒》123篇、《公孙弘》10篇等;“法家类”:《晁错》31篇;“纵横家类”:《主父偃》28篇等。这些篇章虽不是专门的奏议集,但从保存下来的篇章来看,大部分是群臣向皇帝进言的奏议。这些奏议除了有正式的奏议文书外,应当有部分奏议草稿。对此,王充《论衡·对作》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谓之造作,上书奏记是作也。[6]1181-1182
从此段可知,王充的《备乏》《禁酒》篇章是他向皇帝进献的奏疏所留下的草稿,再加上一个标题所转换而来的,即从“奏”转易为“书”。余建平在考察《新书》《汉书·贾谊传》中贾谊奏议的文献来源时,指出贾谊上书所留下的奏议草稿应是《新书》的重要文献来源,而其上奏到中央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则是《汉书·贾谊传》所载贾谊奏议的重要文献来源[7]。故除了正式的奏议文书外,奏议草稿应是私家著述中奏议的重要来源。
总之,汉代中央保留的奏议文书是正史类史书的文献来源,一些奏议草稿则通过添加标题的形式和个人奏议文书一起被编入私家著述中,成为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故奏议生成于史传和子书之中,并依附于史传和子书保存并流传至今。
二、魏晋南北朝奏议集的编纂和“子书入集”现象的出现
魏晋时期,朝廷政论活动活跃,奏议文激增。任子田、王小盾根据严可均的《全三国文》所引录的资料统计出了三国时期近二百位作者所创作的五百多首奏议文[8]。与此同时,奏议集的编纂兴起,开始著录于集部文献中。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的末尾著录了16部表奏性质的文集,包括7部奏议总集和9部奏议别集,但均已亡佚。幸运的是,《太平御览》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了陈寿编撰奏议总集《魏名臣奏事》的相关篇章。任子田、王小盾辑录《魏书》《汉书》《周礼》等相关史料,考证出《魏名臣奏议》是应诏于正始年间根据中朝秘书所编撰的,后经陈寿编辑,成为定本,其资料来源是被谨慎保管在国家秘府中的众多奏议性质的文书。从而进一步指出,《魏名臣奏议》的编纂早于《文章流别集》和作为文学总集的杜预《善文》,是中国第一部按照“采擿孔翠,芟剪繁芜”[9]方式编纂的,以名臣之美文来造就所谓“博达之士”为目的的中国文学总集。更具体来说,《魏名臣奏议》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彰显“经国之枢机”的奏议总集。
关于“子书入集”现象,可以《诸葛亮集》为例进行论证。陈寿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有言:“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10]927这里陈寿将“言教书奏”之类的文章专门编为一个集子。后又进书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10]929-930再由其前所附的《诸葛氏集目录》,推知陈寿“删除复重”的这二十四篇集名为《诸葛亮集》。此外,《晋书·陈寿传》也言:“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11]2137所以,《蜀相诸葛亮集》即是《诸葛亮集》。
既然陈寿是在奉敕编写《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过程中,又承荀勖、和峤旨意,编定了《诸葛亮故事》。那么,《诸葛亮故事》和《诸葛亮集》是什么关系呢?对此问题的厘清有助于《诸葛亮集》性质的确定。虽说《诸葛亮集》已不存,但由该二十四篇的篇名,知悉其主要包括律令类、政令类、表奏类、杂言类四大类内容。《诸葛亮故事》所涉文献内容可以从“故事”一词着手。《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云:“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12]967《旧唐书·经籍志》曰:“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13]1963《国史·经籍志》史部“法令类”又云:“汉初,萧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一代之制粲然矣。晋令甲九百余卷,杜预、贾充删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还官府……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14]91由“品式章程”“朝廷政令”“梁科”等词,可知“故事”大体指涉典章条例之类的书籍,属于史部性质。再结合陈寿在《诸葛亮传》中所言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所编的二十四篇的《诸葛亮集》,故可认为《诸葛亮故事》与《诸葛亮集》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陈寿从《诸葛亮故事》中摘取的能够彰显一代贤相资政经验的“言教书奏”之类言论,专门编为集子,命名为《诸葛亮集》。因此,《诸葛亮集》虽以“集”命名,但实际上是子书。章炳麟、程千帆、刘明等人都肯定了《诸葛亮集》的子书性质,刘明更是指出,陈寿在编定诸葛亮故事的基础上,发现“亮言教书奏多可观”,但史传容量有限无法承载,遂在史传外编集子名《诸葛亮集》以解决此矛盾。[15]然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书目均认为《诸葛亮集》是文人集子,将其著录于“别集类”。这种脱胎于史部文献的成一家之言的子书专著又被归入别集中的现象正是早期文人集形成的一个路径,即“子书入集”。同时刘明还指出《诸葛亮集》受到汉魏之际辞赋、文章之学的影响和侵染,出现四部兼涉的情况,在名称体例上又与子书类同,造成了其从子部到集部的游移[15]。这从一个侧面也正印证了章学诚所说的汉魏之后的文学著述情况,即“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16]58
换言之,这种“子书入集”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风尚和文章观念的变化。魏晋时期极为重视文辞和人才,其整体的文学倾向是重“文”轻“笔”,尤为强调文章的审美性和艺术品格。曹丕在《典论·论文》按四科论文学,表达当时人的文章观念:“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720将奏议置于文学之首,享有高于诗赋的重要地位。陆机《文赋》也主张“奏平彻以闲雅。”[18]241刘勰《文心雕龙》专列“章表”“奏启”“议对”三篇,并详细论述了不同奏议文体的生成发展、用途以及写作规则。“章表”篇更言:“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19]263并且,“章奏”篇还提到了早在东汉时期,在人才察举制度中就有増试章奏,并夸赞左雄的奏议文,是台阁文学写作的范式;胡广的章奏,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他们的奏议都是当时杰出的文笔。
在对文章审美艺术品格格外重视的文论时潮下,魏晋时期对奏议文的审美关注自然由朴素的史实色彩转向雅丽的文辞,奏议集在书目中的部类归属也向集部倾向。从总集的编纂角度看,奏议集作为按照某一文学观念所选辑的文献,既不同于六经所代表的辑而不选的方式,也不同于《楚辞》所代表的以别集为骨干的方式,其编纂具有明显的审美色彩。总之,这一时期出现的奏议总集以及“子书入集”现象是奏议文归属于集部文献的肇始,且一直延续到明清。
三、唐宋奏议专集的激增与奏议在集部的单独立目
《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总集类”“别集类”分别著录了许多奏议总集和“独出别行”性质的个人奏议集。此后宋元官私书目,如《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也均遵循其例。南宋郑樵率先在《通志·艺文略》文类第十二中设置“表章类”和“奏议类”,专收奏议类文集,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遂初堂书目》以及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集部专门设置“章奏类”。《直斋书录解题》小序言“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别为一类。”[20]634它明确指出了“独出别行”的奏议集的编纂与兴盛促进了“章奏类”类目的设立。对此,谢保成认为,唐代奏议集逐渐由集部转而入史部,是以唐代奏议专集的大量出现和宋元官私目录单独立目为发端的[21]1157。此表述语焉不详,未深入探讨唐代以来奏议专集的激增和“章奏类”在集部中的设立是如何造成“文之将史”的新趋势。
奏议政治价值和史学价值的提高当是唐宋奏议专集激增与奏议在集部中单独立目的重要原因。这在史料文献中有许多踪迹可循。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与监修国史房玄龄的交谈中,对两《汉书》中所载录的诗赋提出批评,认为“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并指出“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2]222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在翻阅《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又指出“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2]224可见,唐太宗认为臣僚上书要“词理切直”“直书其事”,要有益于劝诫,充分发挥其处理朝政事务的实用功能。对此,魏徵称赞道:“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22]224这是点明了包括奏议在内的史料的书写要有端庄典雅之气,需遵循“雅正”的“至公之道”。
尽管唐太宗竭力推动文学的“雅化”,到唐高宗、武后时期,选拔人才时仍出现了重文倾向,推崇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之文。这引起了刘晓、王勃、陈子昂、刘知幾等有志之士的不满,刘晓、王勃上疏陈述科考重文之弊,陈子昂则以复古为新变,推崇建安、正始文风,明确提倡汉魏风骨,抨击“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稍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所表达的“文学的史化”的文学观,不仅是对绮靡文风的反击,更促进了魏晋以来奏议集的大量编纂。在《载言》篇中,对于《史记》《汉书》中记事载言“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所造成的“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的问题,刘知幾从体例和史料选材角度考虑,主张应当取法《尚书》《春秋》,言、事分载;在纪传体史书表、志之外,专设“书”类,将“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奏、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书类”是在诏令、奏议类等朝政文献增多、政治、史料价值提升的情况下为之设置的。虽然此后的史书中并未施行,但刘知幾“言事分载”的主张,似乎正预示着此时期奏议文献编纂的新变。在《载文》篇中,刘知幾指出“周诗”“楚赋”可以与《春秋》一样进行道德批评,教化天下;屈原、宋玉可以像南史、董狐一样秉笔直书,创作“不虚美、不隐恶”[23]90的赋类作品,进而直接提出了“文之将史,其流一焉”[23]90的文章发展态势。中唐的韩愈、柳宗元等发起的以“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为核心的古文运动一直延续到宋代,并在欧阳修的大力倡导下得到全面兴盛,文章创作更为注重政教价值和实用功能。顺应趋势,宋代官私目录书中也开始将“章奏类”文献于集部单独创设,将刘知幾所提出的“文之将史”的文论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唐宋时人对奏议文写作的重视和提供写作范本的现实需求是奏议在唐宋书目集部中著录数量的增加和单独立目的另一原因。唐代奏议正在摆脱魏晋以来的绮靡之弊,主要用散体文写作,以叙事和说理为主。如《旧唐书·魏徵传》收录有5篇魏徵的奏议文,被认为是“匡过弼违”“可为万代王者法”。[24]2562-2563采用骈体写作的奏议,其浮辞和赘典也在逐渐减少,论事恳切,说理严密。到中唐的陆贽,其《陆宣公奏议》虽用骈体,却尽扫绮靡之弊,被公认为“正实切事”。总之,唐代的奏议政论性倾向显著,史料价值颇强。到了宋代,奏议写作虽多用骈体,但多俪语精工、格律精严,极富文学性。元代刘壎《隐居通义》卷二十一《骈俪一·总论》言:“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诸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为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大则培植声望,为他年韩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是取人,盖当时为一重事焉。”[25]177这表明了章奏写作已经成为宋代士人为官、晋升的必备技能。可见,不管是用散体文,还是骈体文,优秀的奏议因其本身的政论性和实用性,都被认为是士子学习和模拟的范本,这也是唐宋奏议集编撰兴盛的主要原因。
概而言之,刘知幾“言事分载”和“文之将史”的论点、唐宋古文运动的激发、唐宋时人对奏议写作的重视以及提供写作范本的现实需求,使得奏议集的编纂大量增加,也预示着明清时期奏议归属史部的趋势。
四、明清奏议在史部中的独立
逮至明代,官修目录《行人司重刻书目》和私修目录《世善堂书目》《万卷堂书目》《笠泽堂书目》直接将“奏议(疏)”于史部中单独立目。清代集大成的古典目录专著《四库全书总目》将奏议于史部“诏令奏议类”独立,至此,奏议摆脱了史部和集部中的游移不定,最终在史部中定型。由于奏议在史部中的独立是从明代开始的,因此我们先着重分析促使明代奏议独立于史部的原因。
保存史料,为时人和后人提供资政经验是明代编纂奏议集的重要原因。明成祖永乐年间,黄淮、杨士奇等人奉敕编撰的《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是我国第一部通代奏议集。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朱棣在此书成书时,曾对身边的侍臣言:“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赐皇太子、皇太孙及大臣。”[26]1972可见,此书编撰的初衷是为明朝的官僚阶层提供治理国家的借鉴和参考。《历代名臣奏议》在具体分类上也极力凸显这种政治倾向性,卷23-60的“治道”类,是全书着力论述的内容,也是明代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此外,唐顺之编纂的《荆川先生右编》称“奏议者,奕之谱也。”[27]1他把奏议看成是古今天下棋局中的棋谱,后人可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策略,与《历代名臣奏议》编撰动机不谋而合。
明代正德、嘉靖以来,兴起了以收录经世言论、名臣奏疏为主的“经世文”的汇编热潮。这类经世文编极为强调奏议的实用价值,重视其实际的经世功用。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所择选的文章体裁主要是颂、表、策、疏、碑、记、序、跋等实用性的公文文体,其中以奏疏的数量为多。同时,他还提高了奏议在其著述中的位置。《凡例》即言:“兹编体裁,期于囊括典实,晓畅事情。故阁部居十之五,督抚居十之四,台谏翰苑诸司居十之一,而鳞次位置,则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牍,又其次杂文云。”[28]57陈子龙还称赞邹元标的奏议“《谟》《训》之亚也,格人元龟,非一世之宝。”[29]1406可见,陈子龙将奏议放在了“经国之枢机”的重要位置,这是对奏议经世思想的肯定,也是明代士人的首创,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现世关怀。
明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强调奏议经国济民的实用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倾向实际上是当时兴起的阳明心学思潮下的产物,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在现实中的投射。阳明认为达到“致”得“良知”的途径是“率其本然”和“着实用功”。“着实用功”就是通过外在的努力来恢复本心的良知,即所谓“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刻致矣。”[30]94关于“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常用通俗的语言阐释日用常行中的一些情境,“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簿书讼狱之闲,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30]95等表述,也是着重强调阳明心学形而下的具体的实践意义。而晚明的经世类奏议文典型地反映了经世史学思想的实学化倾向,实学也正是我国充满现实关怀的传统儒学的固有成分。概言之,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独特理论形态和重要文化思潮[3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奏议的经世倾向、史学实用价值自然就得到凸显,将其独立于史部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明朝在建国之初就加强对奏议等公文的制度改革,推崇质朴庄重的文风,重新确立奏议文的书写规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奏议文献向史部的靠拢。明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以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为法,反对晋宋以来骈俪绮靡的文风,要求奏议之类公文应以质朴为尚,“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32]1513“凡文武官于朝班奏对之际,言辞当详雅切实,勿为浮溢之语。”[32]1509为此,朱元璋曾多次颁布禁止繁文缛词的禁令,并将其写入《大明律》:“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33]在上奏制度上,为了更好地遏制绮靡文风,优化公文运行机制,提高公文处理效率,推动朝廷政令的顺利执行,以树立皇室权威,朱元璋命人拟定了奏本和题本写作的固定格式:
奏本式
某衙门某官臣姓某等,谨奏。为某事。备事由云云。今将原发事由,照行事理,备细开坐,谨具奏闻。某事云云。缘由毕,前件事理拟议某律科断施行,某事云云。缘由毕,前件云云。伏侯敕旨,如有勾问,职官或支拨钱粮之类。则依此式写。(以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计字若干,纸几张。)
右谨奏闻,如一事奏请,则于此下,写伏侯敕旨谨奏。洪武印,年月日某衙门某官臣姓某,某官臣姓某,年月日下。止列。见在某官臣姓佥名。不得于背后书写或有差故缺页者,不必列衔某衙门某官臣姓某。[34]1209
题本式
某衙门某官等官臣某等,谨题,为某事。备事由云云。谨题请旨。如不用请旨,止用谨具题知。余同。[34]1210
有了此种固定套式,臣僚在上奏时,只需将进奏事宜填入此中即可。这种奏议写作固定模式的推行极大地限制了官臣的语言自由和书写权力,扭转了明代前期的骈俪文风,强化了奏议处理朝政的实用功能。
然而,从明代嘉靖以后,奏议公文写作并没有遵照洪武朝所制定的书写规范,骈俪文风卷土重来,语言表达也繁富冗长,“章奏之冗繁,至一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十不止,皆枝蔓之辞”。[35]648敷衍不实、晦涩不明等文风也充斥在奏议公文中,上到朝阁重臣,下到一般官员无不沾染此习气。如王世贞《荐举贤能方面官员疏》全文均用骈体,浮辞雕琢,还穿插一些晦涩难懂的典故[36]5042-5046;方逢时《陈虏情以永大计疏》更是用近5000字的篇幅反复陈述边疆抗夷狄之事[37]。甚至连当权者明世宗嘉靖帝一边多次下令规范奏议写作,一边在实际行动中又助长了这种奏议写作的弊习。嘉靖帝喜祥瑞,又喜华丽的文辞,使得当时进献祥瑞之风盛行,侍臣为其奉玄所作的青词多骈俪绮靡之气。而且嘉靖帝还对直言劝谏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故朝堂上下多是阿谀奉承之词。规范奏议书写的政令仅流于表面,并未得到很好的施行。
正是在这种奏议公文写作失序的情势下,万历三十年(1602),行人司正徐图根据司中藏书重编了一部《行人司重刻书目》,分为典部、经部、史部、子部、文部和杂部六大类二十二小类,并在史部中首次单独设置“奏议类”。尽管《行人司重刻书目》仅著录了《历代名臣奏议》《范文正奏议》《陆宣公奏议》《包孝肃奏议》《李忠定奏议》《大儒奏议》六部奏议总集和别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陆贽、包拯等人都是人们一直推崇的贤臣良相,他们的奏议自然也是最好的模仿范本。行人司是一个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官府机构,其书目编纂和类目设置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或稍后的朱睦 、陈第、王道明等私人藏书家所编纂的私家书目或是受其影响,也将“奏议类”文献独立于史部。
到了清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奏议文书形式——奏折。相比于奏本来说,奏折不仅运行程序简便,直接封寄上奏,由皇帝亲自审阅;而且语言更加简明扼要,极力凸显了奏议处理朝政事务的实际功用。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诏令奏议类”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奏议“政事之枢机”的政治功用。
至此,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经过几千年中国古典书目的演变,奏议由史入集,又由集入史,终于在史部的二级类目中占有一席地位。
结语
奏议在我国古典目录中的归类变迁,有着深层的学术背景,集中反映了奏议观念的时代变迁。尽管从魏晋时期开始,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最终将其锁定在史部之前,奏议归属于集部一直是占据主流的观念。但奏议最初是以档案文书的形式在史传中生成的,并在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经部“春秋类”有著录。故不论奏议文献在后世的集部中如何逐渐壮大,它总归有归属于史部的基础条件。到了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对于“心即理”和“致良知”的强调,奏议“着实用功”的实践品格占据主流,显著表现就是经世文编的编纂成为热潮;再加上统治者对于奏议绮靡文风的遏制,奏议公文制度的改革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奏议的经世倾向、史学实用价值得到凸显。因此,从明代中后期的官私目录起,奏议开始在史部中独立。直到清代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以官方权威形式将“奏议类”文献最终定型于史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