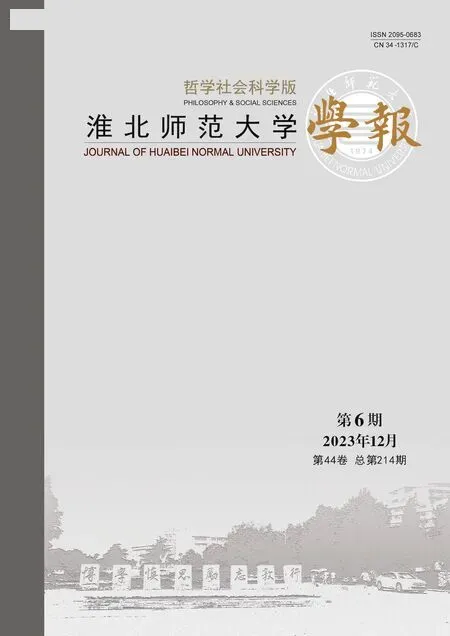重探欧阳建“言尽意论”
刘芝庆
(湖北经济学院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205)
欧阳建,字坚石,渤海南皮人。历任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期间甚得称誉,政绩不俗,后因政治倾轧,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时为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仅三十余岁。在魏晋哲学史上,欧阳建最为后人所重者,当是其《言尽意论》。本文的研究,即是针对《言尽意论》所环绕之问题,作出解读分析,重在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因此也与当前学界之观点角度,颇有不同。对现有之研究,或引用承继,或批驳弹正,兼亦有之,故名为“重探”,冀能对魏晋思想之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有所贡献,也期待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一、从言不尽意到言尽意
首先,录出短短百余字的《言尽意论》全文:
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锺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
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
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回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1]1151-1152
关于言意之辨,先秦诸子如儒、道、名、黄老等家已有讨论,或谈得意忘言,又或是谈循名责实,皆是就此问题发挥。至于魏晋时期论言不尽意,从荀粲以来,主张理之微者,非言所能尽,荀粲又用《庄子》谓六籍乃圣人糠秕为证,以明己说。[2]319-320而王弼更提出“得意忘象”,同样是继承道家的主张。在王弼这些人的看法里,言似乎已是不得已而发,是“有”的流韵,只能是表相俗见,不可能上升到“无”或者是“意”的层次。《世说新语》记王弼与裴徽的对话:“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3]107体无,却难以为训,不得已只有言有,这也是名言的必要性,但重点在于无,而不是有,正如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4]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正是王弼强调的。言既然难以尽意,也难怪会出现乐广的行为:“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3]111旨不至,语出《庄子·天下》:“指不至,至不绝”。此类举止,虽不为禅法,却颇有禅机意味,“辞约而旨达”,是以最精简精炼的语文表达最大空间的涵蕴,更实指言难以尽意的层次,故言不必多,重点在于当事者之悟。当事者能悟,辞约足矣,当事者不能悟,就算是皓首穷经亦无用。当然,这也跟乐广个人说话的方式有关,如《世说新语·赏誉》记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注引孙盛《晋阳秋》:“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3]386皆属此类。
到了欧阳建的时代,“言不尽意”已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看法,所以他才说以言不尽意为论,由来已久,通人才子者,皆以为然。又以蒋济论观眸知人,钟会、傅嘏等言才性四本,皆以为谈证。《三国志·钟会传》就说:“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刘孝标注引《魏志》云:“会论才性异同,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锺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2]345学者对这段话多有解释,汤用彤说蒋济等人:“均引言不尽意以为谈证,尤可见此说源于名理之研求,而且始于魏世也。”[5]蜂屋邦夫更认为汉末以来,士人品行相离,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之类,人物评价失去标准,需重新设立订定,鉴识论与才性论,于是因运而生,其中便有言不尽意的主张。因为人皆有“意”,却又是最难捕捉与言说,所以要重新找方法来论人析事;[6]牟宗三亦曾撰文论及,他认为言意之辨实起于汉魏间之名理,又与当时臧否人物之风有关,即所谓识鉴人伦之事:“但在才性名理,则既是品鉴人品、才性,则在原则上,名与实即不能一一相对应,此即含:名言不是指谓的名言,而是品鉴的名言,欣趣的名言,而‘实’亦不是外在的形物、一定的对象,而是生命之姿态。如是,此种品鉴名言即无一定之形物为其对应之实。虽足以指点而透露出生命姿态之内容,然此内容是永不能为那名言所尽的。如此,由品鉴才性,必然有‘言不尽意’之观念之出现。此为‘言不尽意’兴起之直接理由。”[7]牟宗三之说,要言不烦,敏锐地指出言意之辩与识鉴品评之关联。所以欧阳建才以观眸知人、才性四本论文为说。由此可见,言意之是当时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王导过江,才会以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为三个最重要的谈资[3]114。
二、言如何尽意?
但细看欧阳建《言尽意论》的前几句话,却充满许多问题。前引牟宗三所说,生命姿态难为名言所尽,需以眸鉴识知人。但蒋济著论,虽谓观眸足以知人,与孟子所言:“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8]可谓同辙,孟子相眸一事,在后世广为人知,影响颇大,所以王充才说:“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了,心浊而眸子眊。”[9]但孟子听言与观眸是并行的,且按常理来说,“听言”者,自然不会只以时人为主,也包括了历史人物,最好的例子就是司马迁写项羽,说他是“重瞳”,其相非常,此为观眸;司马迁又引项羽死前语:“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评其谬哉,可见性格优劣,此为“听言”。观眸当然不会自孟子才开始,应该这么说,听言与观眸,甚至是整个言行举止,其实也是历来相人术的一环。[10]“听言”一事,蒋济自然也不陌生,他也常就这个角度观古今人,例如他谈庄周妇死而歌、项羽不能听范增言等等,定其人之得失优劣。魏文帝曾有诏书给夏侯尚:“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蒋济觉得用辞不当,发言应谨慎小心才是:“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2]451甚至认为文帝的诏书,文语失据,是亡国之言,故天子无戏言,应该字斟句酌,细察注意,名言为重,这显然不是“言不尽意”的思维与心态,而是谨慎“听言”。
再者,若不以识鉴人伦,而只就言意来看,蒋济谈“土”与“地”之本义、论“娣姒”为兄弟之妻相名,有此名故有此意,内容与形式相符,不正是言尽意吗?[11]343-344说他主张言不尽,恐怕有再商榷的必要。更进一步来说,蒋济又何止观眸知人听言而已?他是以整个形象外在来观人的:“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难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幼主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敌也’。不过以眸观人,也未必全为当时人同意,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11]342由此可见,光以“观眸”来看蒋济,是不够全面的。另外,傅嘏、李丰、钟会、王广等说,文虽已不存。但才性同、异、离、合,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又该如何皆以言不尽意为证?如果说品鉴名言即无一定之形物为对应之实,则才性离与异已难相符,又何必再多此一举,以言不尽意为据?若生命姿态之内容,永不能为名言所尽,则所言之“才”与“性”又该如何能尽?才性同与合,又怎么可能?
因此,欧阳建文章开头的话,恐非全如牟宗三等人所言,是因为言语难尽,故从才性、观眸等处论之。刚好相反,蒋济等人未必都是赞同言不尽意的,他们也可能主张言尽意,只是今文皆已不存,难已明确论断。他们之所以“莫不引此为谈证”,很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论述的谈资材料,而所谓“证”,既可以证明“言不尽意”为是,自然也可能证明为非,只是现存资料不足,殊难论定。倒是“言不尽意”是当时流行的学理,故皆引以为谈说罢了。
对于“言不尽意”,不管他们是赞成也好,反对也罢,恐怕都不是欧阳建所能同意的,故曰:“而先生以为不然”。[1]1151那么,欧阳建到底是怎么看待言尽意的呢?他引了言不尽意者的话:“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1]1152一般多以为此段乃欧阳建之论点,实非。汤用彤与楼宇烈早已指出,这段是欧阳建引“言不尽意”的话,是欧阳建作为批驳反对之用,因为诸如张韩、王弼等人,多以孔子“余亦无言”“天何言哉”为据,证明“言不尽意”的合理性。[12]欧阳建却认为,言如果不能尽意,则圣贤不但不能去言,反而多有言说著墨,那也未免太奇怪了,所以他说“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1]1151如此文脉才能畅通连贯。
只是,究竟怎样才能言尽意呢?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所说:“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13]凡物必需要名,否则难以指认,更难以沟通讯息,正如欧阳建所讲的“无以相接”。[1]1152所以要正名,更不能废言,欧阳建说圣贤不能去言,亦因此故。但正名也好、辩物也罢,必定是名实相符的,有实有名,反之亦然。用索绪尔的语言来讲,能指与所指(或意符与意旨)是相合的,虽然索绪尔认为两者相合常是武断的,而雅克·拉冈更进一步指出意符底下的意旨是不断滑动,难有永恒不变的结合。[14]
欧阳建却非如此,他认为心有所见,得其理,终究还是要以名言表达,而所见之理,亦需要藉由言来定名,故曰:“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1]1152此处虽标出“理”,但欧阳建只是作为一种常识性的叙述,并未特别深究。他又指出,也唯有辩物正名,才可能理解与沟通,而品评人物生命姿态之“鉴识”,虽各有种类高低不同,但彼此间仍有标准可言,“鉴识”之所以得以成立,都是因为“言称接而情志畅”[1]1152的缘故。如果说王弼、何晏标榜以无为本的思想,以贵无为重,言不尽意进而要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欧阳建则是反过来,指出言与意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毕竟我们细思,意要靠什么表现?不仍是言吗?故所谓意,同时即是言,形式即是内容,言意不必离为二,也不可能划分为二,这是欧阳建的立场:“此犹声发回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1]1152原因所在,不是“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1]1152而是“非言不畅”“非名不辩”[1]1152的缘故,言与名是不能舍弃,也不可能得了意就要忘言忘象的。就欧阳建看来,如果说“意”是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存有实在之层次,那么用来认识这个实有的方法与手段:名言,重要性显然不遑多让,甚或犹有胜之。更进一步来讲,凡事物皆有名言指涉之,物有其形其意,命其形者定其意者则为名言,也就指此物之实与意,是讲究具体事实与命物之名的相符合,“言”或“名”即是指具体名称,事物都是由名言而组成,而一事物皆有其具体称呼,两者相成,即是“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再从语意学来看,言意已定,就是使用的词语已具有指谓定义,因此只要符合这个“言”或“名”的事物皆可为此所称,除此之外,更可以反过来,用“言”来认识此具体事物,依言而探究其物其理,层层开拓言中之意。也就是说,名言之所以为名言,就是此物之所为此物之意,因此名与意是一体、密不可分的。
再者,因为欧阳建之所以认为言之所以可以“尽”意,是因为“言”非固定不变的,可以逐物而迁、可以因理而变,我们不妨以《荀子》为例,以期更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荀子·正名》:“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15]名实之所以有约定成俗的可能与实践,用欧阳建自己的话说,正是因为“以理得于心”“言称接而情志畅”的缘故,但名言是可以因物因理而变化的,正如荀子所谓单名、兼名、共名之类。因此,对治言不尽意的的方法,就是以更多更丰富的语言去“尽”,来描绘形容那难以言说之理之物,想办法促成“约定俗成”的“实名”。言可尽意,其关键在此,当然“尽”的先决条件当然是“以理得于心”“言称接而情志畅”,也才能以名说物、以言尽意。换句话说,圣人之所以不去言,便是担心造成“失语”,认为其祸更甚,而要突破“不尽”的困境,最好的回应就是以更多的名言语文投入其中,名言立,鉴识才能显,品类方能殊,人文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得已彼以相接。故名言不是造成“失语”的罪魁祸首,刚好相反,名言才是正路,以名言拯救名言,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正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欧阳建所谓之“言”,恐怕也是要加上文的。言可尽意,亦非自然质朴的语文所能尽,重点在于如何体物畅理,《晋书》称他:“雅有理思,才藻美赡”[16],他曾作《登橹赋》,写登船所见,或见天际渺邈,或见平原旷荡,或欣赏暮春时节,或心悦微风拂面:“登兹橹以遐眺,辟曾轩以高眄。仰天涂之绵邈,俯平原之旷衍。嘉苍春之令节,悦和风之微扇,傍观八隅,周览四垂,面孤立之峻峙,岨曲岸之条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终日,情亹亹而忘疲。”[1]1151可见欧阳建富有文采,不但言可尽意,更是言之有文的。他又有《临终诗》,深刻描写自身心境与经历:
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
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回圈。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17]
诗中从孔老谈起,古人遭逢灾难乖蹇,该如何自处;又谈到自己生平,不料亦逢困阨,古人今人同命不同时,皆因世情险恶,人情难豫观。只是上有母亲,下有儿女,恐难以照料,不免忧心忡忡,临纸涕泗。本传说他:“年三十余。临命作诗,文甚哀楚”[16],其诗文情辞相达,哀楚感人,言之以文,言能尽意,或皆类此,显然都是从言与文、言尽意的方面著手的。
三、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如果说言不尽意论者,认为名言只是筌筏,名言永远难以尽意;欧阳建则反之,提倡名言的必要性,名言之于物,未必是永久固定的,也可能是变动的,重点在于言意之间,能否达成“言称接而情志畅”[1]1152的理想状态。如果说言不尽意的影响是得意而忘言,却不免有“失语”的危险;欧阳建则认为这是因噎废食,言意的问题不在于名言的浮动与不稳定,而是在于我们能否意识到名言作为“相接”与“鉴识”的必要性。如果说连圣贤也不能去言、如果说名言绝不可能废,那我们应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言尽意的问题,而不是转向去谈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得鱼而忘筌,这就是他强调理得于心,言称志畅的原因。
至于心如何得理?情如何畅达?言要如何文?短短数百字的《言尽意论》里,实难看出究竟,在欧阳建现存的其它文章中,也看不太出端倪。可能是欧阳建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只是有意无意间提出了这层思考,也可能在佚失的资料中,有所解答,因为《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文集二卷,但今可见者,不过《言尽意论》《临终诗》《登橹赋》等寥寥数文而已。甚至也可以这么想,此问题不应该由欧阳建回答,而是要放到整个魏晋思潮中来看,诸如《文心雕龙》谈“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巧言切状”“曲写毫芥”“巧构形似”,像是诗人雕琢刻画,镂金错采,如窥情风景,钻貌草木的山水诗;又或是歌咏女性主、写女人之宫体,举凡眼见、耳闻、鼻嗅、体态、妆扮、皮肤等身体感官之经验,体察细腻,声色大开,虽未必皆与鉴识人物有关,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在回应言意之类的问题。
当然,欧阳建虽提出言可尽意,但这个问题终究未得到解决,阮裕与谢安谈白马论,阮裕就感叹:“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3]117便可见一斑。约略与欧阳建同时的庾敳,更有名言: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3]140
究竟言可尽意为是?还是言不可尽意才是对的?中外古今者论之多矣,言人人殊,此是一是非,彼是一是非,是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六经为先王之陈迹、圣人之糟粕? 终未能有明确的定论。而言与尽之关系,或许都可以笼统地说“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