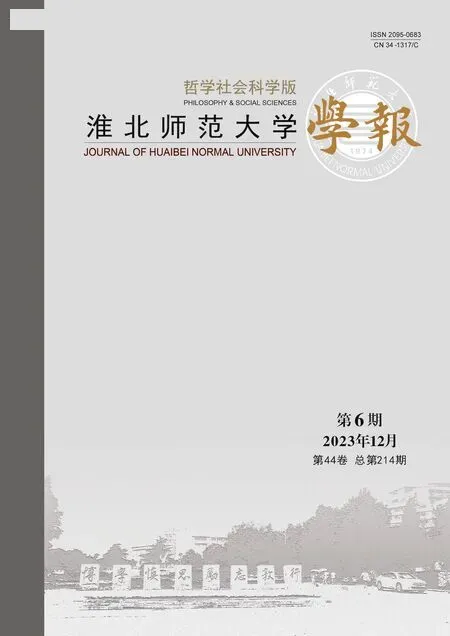革命与学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生革命的理论探索(1921—1927)
刘海军
(成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随着近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学生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救国救亡”的时代语境下,革命成为学生不得不面临的政治课题,学生也是革命必须考察的重要对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对学生革命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其革命话语中,学生常与工人、农民并列,是主要的革命群体。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学生运动上①相关论著有: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郑师渠.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J].史林,2018(1);岳谦厚,李卫平.“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11(7);岳谦厚,贺福中.再论“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J].安徽史学,2014(2);黄金凤.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16(4);黄金凤.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中共早期动员策略再探讨[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5).其中,吕芳上的著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重要参考,但该书对中共与学生运动的关系论述有限;黄金风则集中论述了中共早期的学生运动模式和策略;而多数学者是就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展开宏观论述,间有涉及中共对学生运动的认知与动员问题。,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学生革命认知的全局性透视。此外,因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系,学界常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学生革命的认知涵盖在其知识分子理论之中②相关论著有: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J].历史研究,2015(1);齐鹏飞.中共早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探索[J].中共党史研究,1992(3);宿志刚.论大革命时期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创立和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是与知识分子并列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群体出现的。有鉴于此,本文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生革命的理论探索作为一个独立事件加以全面考察。
一、何以可能:学生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革命理论的探索与建构过程中,阶级分析法是重要的方法论范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1]199。因此,在阶级社会,任何个人、群体皆具备阶级性,而阶级性是分析其社会角色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的探索,便依循了由阶级性而革命性的认识框架。
学生的阶级性,首要问题在于学生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对此党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陈独秀认为,学生“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2]471。贺昌也说,“青年学生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绝对不能自成为一整个的阶级”[3]283。1926 年,共青团《学生运动决议案》中亦明确表示,“学生群众,因为没有经济基础,本身固不能成为一阶级”[4]210。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对学生革命性的分析。学生是“依附于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3]283,因各自出生的阶级不同,“遂使他们内部反映成了许多阶级形式”[4]210,“有资产阶级的倾向,有无产阶级的倾向,有其他的倾向”[5]270。所以,就理论上而言,学生没有明确的阶级利益,“对于一切的政治观念,极易动摇,他可以革命,亦可以从事反革命”[6]170-171,用瞿秋白的话讲就是“可左可右”[7]528。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绝大多数学生是倾向革命的。陈独秀表示,学生“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2]472。张太雷则认为,“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格外地趋向于革命”[5]146,除了少数领袖之外,“学生群众是没有反动的”,他们“只有革命觉悟程度的差别而没有革命与反动的分别”[5]280-281。贺昌也持相同的看法,学生“中间除了一部分已被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收买,甘心情愿去做奴仆以外,大都很容易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3]283。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如“工商业之不发展和封建阶级的专政,宗法社会的压迫”[8]364,加之“外交之不断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一再压迫”,从而“使多数学生为满足本身要求计,为改进民族前途计,不能不挺身而出,从事于本身解放与民族解放之运动”[4]61。总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生成为革命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其成为“非革命者”“反革命者”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对学生革命性的引领。1921年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在学生中建立核心、宣传和介绍我们的思想,努力赢得这个特殊集团对我方的同情,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现有学生组织有着革命的特性”[5]54。与此同时,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到,中国“青年学生们正在起来造反”,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处在歧路上”,要帮助和引领他们,“不能推给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9]131党的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10]153。共青团也规定,“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8]368。中国共产党人相信,青年学生是“最易受我们的宣传最易对无产阶级革命表同情的”,只要“宣传得法,投其所需,则必有多数人聚集于我们主义旗帜之下”。[8]278
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时常将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从而把对学生革命性的分析寓于其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界定之中。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即把学生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1]9。刘少奇也在1926 年表示,“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2]2。1927年初,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中国是革命的群众,他们从前演过重要的作用,此后也将如此”[13]29。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认知中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将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同样肯定了其革命性。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学生阶级性与革命性的认识,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又有着鲜明的现实阐释意味。从理论上分析,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其内部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学生在革命的过程中会产生分化,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学生不管如何分化,都改变不了大多数学生倾向革命的主流方向。概而言之,学生是一个高度聚集、组织性强的社会阶层,又因其年轻而掌握知识文化的特点,易于受新思潮影响而参加革命。
二、何以可为:学生的革命地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在界定学生阶级性与革命性的同时,也对学生的革命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学生革命地位与作用的认知,曾在党内产生过激烈的争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李大钊在1917年的《学生问题》一文中这样论述,“清之季年,政府当局所日夜孜孜以为戒备防范者,即学生是。卒以学生于社会不得同情,不得职业,不获本其理想顺其情感以表著于政治,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而清室以倾。袁氏帝制之念既萌,亦视学生如蛇蝎,而学生抗袁之运动,又复潜滋暗布,而袁氏以陨。故欧美之革命,泰半渊源于工人之呼号,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14]122李大钊将学生视为革命的“开创者”与“急先锋”,与欧美革命由工人肇始不同,中国革命全因学生而起,这是极高的评价。1920 年,陈独秀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指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2]63。在这里,陈独秀把学生与劳动者并列为最好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施存统撰文《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兵士”,但是“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要使他们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而学生之所以能宣传,是因为他们的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为社会牺牲”,总之,“没有了学生,无产阶级和兵士,就不能在同一主义下面联合起来”,因而“社会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15]280-281施存统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和兵士的力量,但并没有否定学生的作用,相反学生作为“宣传者”和“联结者”,是造就革命的关键部分,这与李大钊的认识有几分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汉俊就建议“集中全力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而“不急于建立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16]167按照他的思路,“应当先组织学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势力,然后组织工人就很容易了”,因为在他看来,“学生是党的基本势力”,蔡和森将其口号归结为“走入学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16]80当然,这种主张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否决,“组织一个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面向工人阶级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党”[16]168,成为党内的主流意见。李汉俊的主张在党内无法得到共识,自然是因为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党原则,但并不涉及也未有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学生的忽视或否定,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学生革命作用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学生革命地位与作用的考察,基本延续了这样一个认识逻辑,即学生是“革命的先锋”,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先锋”负有促进“主力”觉醒的重任。张国焘把学生看作是“中国社会最活动分子”,他希望学生“能够抛弃一切和平苟安的观念,认清自己的责任,毅然把为自由、为独立的革命搁在自己的两肩上才是”。[8]227-228施存统则发展了他之前的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既少,又无觉悟,所以力量非常薄弱”,要使无产阶级有力量,就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进行教育,而这种工作,“非借智识分子(尤其是学生)来担任至少非靠他们帮助不可”。[8]319与此同时,陈独秀认为中国“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所以青年学生“责任重大”,学生要做的事情便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2]471-472萧楚女则直截了当说到,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没有第二条生路可走”,而“革命必须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目前能负这个使命而且负到民众间去的”,只有青年学生。[17]82总体来看,学生是“先醒者”,是宣传的利器,是革命的发动力,已在党内成为共识。
五卅运动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地位的判断。正如陈独秀所言,“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18]253。张秋人也表示,“‘五卅’惨案起于工人,成于学生。起初只是学生对于工人底反抗运动表示同情,予以援助,可是帝国主义者一次屠杀,竟杀出一个普遍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学生在这运动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3]263还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扑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进攻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其次就是学生,“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国民革命里,学生与工人阶级是最后觉悟与团结及反抗的力量,真能领导一般平民作解放运动的奋斗”[3]165。至此,“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地位的重要,可以完全证实了”[19]323,学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中国民族的守卫军”[3]345的形象更加鲜明了。而中国共产党人也更加深信,“中国国民革命的工作,大部分要靠革命的工人与革命的学生来完成”[3]489。
五卅运动以后,关于学生革命地位与作用的单独论述逐渐减少,中国共产党人多从其整体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界定学生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国民大革命阶段,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合”,而在这个联合之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20]146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认识已经牢牢固定下来,“学生、小商人及许多知识分子”是作为革命帮手的形象而出现的。[21]20横向上看,在这些帮手中,学生的地位不同于知识分子、小商人。1926 年7 月,《中共第二次扩大会学生运动议决案》中指出,“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4]221。纵向上看,学生的革命作用已发生变化。1927 年5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学生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已不能有以前同样的作用,但是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仍是具有参加工农运动,到工农群众中服务,以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13]265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其革命理论中各种社会成分的位置并逐渐稳固下来,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更加凸显,工农是革命主力军不可动摇,学生虽仅次于工农但作用已不同以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地位与作用的认知有其延续性,即始终肯定学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学生也从革命的“开创者”“急先锋”“启蒙者”转变为革命的“帮手”,成为“工农之次”的革命力量。而且,五卅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集中而长篇的论述,而五卅运动以后对这个话题的关注逐渐减弱。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理论水平逐渐提高,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地位的极高评价是基于工农未觉醒的前提,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人、农民等革命核心力量逐渐觉醒,对学生重要性的认知就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三、何以行之:学生革命的主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际、自身实际、学生实际出发,认识到推动学生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支持学生加入政党、开展学生运动、组建学生军是学生革命的主要路径。其中,有些是学生革命的一般性问题,如与工农结合、学生入党、学生运动,在以后各个革命时期皆有体现;有些则具有阶段性特征,如组建学生军。
(一)推动学生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学生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学生并不能单独发挥力量,它需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革命作用,这也是学生参加革命最根本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张国焘认为,“学生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这是谁也承认的,但是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8]226。邓中夏分析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俄国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22]297,所以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学生到民众中去。这样的认识亦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件中。1923 年8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学生“若不与有经济政治实力之民众共同进行革命运动,必不能对于国民革命有所贡献”[8]365。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17]248。总之,在当时的中国,工农是“居于最受压迫的地位,其所受之苦痛极大,而其革命之要求亦最烈”,所以学生必须“与工农联合,参加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组织,如此才能使中国民族解放成功”。[19]326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具体办法。张太雷在1925年1月所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指示学生“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的责任”,面对工人,“学生应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帮助失学的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同时,“一切游艺会、体育运动会和政治讨论,学生应邀请工人参加,以增长他们的政治兴趣和建立学生和工人间的团结”,如果遇到工人罢工,学生可以“代找外面的声援和实际捐款帮助罢工者”,以此加深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促成“在国民运动中可得合同进行的可能”;而对待农民,学生可以利用暑假组织的乡间旅行,“到农民中用戏剧演说等做一种唤醒他们的工夫”。[5]149同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任弼时即刻写就《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时文,强调学生要到工人和农民两个群体中做宣传与组织的工作,这与张太雷的思路基本一致,但表述更为具体。学生应当“多注意与工人接洽,帮助工人的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灌输工人政治常识,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阶级能早日觉悟而团结”;面对农民,学生可以在每年寒暑假回到乡村的时候,“联络本乡同学组织讲演队、新剧团,开办平民学校,组织贫农农会,进行反对地主、乡绅及减租等运动”,并把一班先进农民及本乡小学教师组织起来。[23]12-13
(二)支持学生加入政党
众所周知,党的一大代表中就有学生,而后许多人也是学生身份入党。学生入党,于自身而言,接受思想主义的熏陶,而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于政党而言,不仅注入新鲜血液,而且促进其知识化。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生革命的路径探索中,学生入党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碰撞分歧亦多。有人便以学生政治运动要“不染党派色彩”“不为政客利用”[24]142为由,明确反对学生加入政党。对此,恽代英指出,“我们为革命,尤其要大的会党,尤其要加入一种组织,服从一种领袖”。[24]153还有人以为学生幼稚,不宜加入政党,恽代英反问到,“年龄长大了的,知识一定便不缺乏么?政治活动,原应由所谓知识不缺乏的人所包办么?”所以,“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是可以的,学生加入政党,亦仍是可以的”。[24]150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吸纳学生。1925 年10 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党和团“应当引导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同时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7]520与此同时,当时的江苏省长发布“禁止学生加入政党”的“通令”,《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对此予以了猛烈抨击,取缔学生加入革命组织,“这不是明明白白不要我们做‘人’,不要我们做中国的忠实国民;而要我们做帝国主义之‘顺民’,做军阀封建政治之奴隶”,文章还提出,“入党是现在中国学生从事于救国的唯一道路;禁止入党,便是叫中国最有革命知识的国民没有组织,而消灭了中国国民革命之重心:实际上,便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种巧妙的新压迫”。[3]503-504再则,学生本身也有加入政党的意愿。大革命失败后,“阶级斗争的激烈高涨,一般智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所以“一般青年智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13]711总之,学生入党,既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加入政党有利于学生革命价值的更大发挥。
(三)开展学生运动
什么是学生运动?李大钊认为,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25]230;而在任弼时看来,“各地反对学校当局及政府一切压迫学生的学潮”[6]219都是学生运动。因此,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中,学生运动不仅仅关乎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而与民族国家利益相连,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学生革命的重要形式和路径。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学生运动具有革命的性质”[8]364、“中国学生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发展,成正比例”[19]323,所以“对学生运动绝不可轻视”[8]240。1924年10月,恽代英发表《学生运动》一文,详细地阐释了做学生运动的目的,“在使学生不受反动派的影响,而且使他们能接受革命的思潮”;“在使学生为自己的利益而团结起来,以成为一种对抗压迫者的革命的群众”;“在使学生为农人工人的运动努力,以引起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军”。[26]510-5111925年,共青团三大对学生运动之意义的界定是,“引导学生来帮助青年工农运动”;“领导学生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注意学生本身利益的要求”。[17]481而要做学生运动,“首先还是要学生自己有群众的组织”[5]143,学生的群众组织就是学生会。学生会“是各个学校里面的全体学生为达到解放民族和解放本身目的而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它能够“集中学生力量,集中学生意志”,“在求谋共同利益之整个目的之下”共同奋斗,“为每个学校中之每个学生所必需的一种组织”。[4]63-64不仅要在每个学校里面组建学生会,还要在几个学校之中组建学生联合会,进而全省联合会、全国联合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对学生运动的指导。1926 年以前学生运动完全由共青团负责,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误。1926 年1 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宣布“以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以后党与团均须注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及团的组织”。[6]9当然,共青团在学生运动中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同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就指出,团“切不可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指导转交于党而减少其积极活动的成分,反而影响于学生运动的发展”,而“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获得更广大的青年工人、农人和学生群众,领导他们在党的指挥下去参加目前的革命斗争”。[6]315-316从此以后,学生运动便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指导,具备了更浓烈的革命色彩。
(四)组建学生军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组建学生军话题的讨论,主要是在五卅运动之后,他们对学生军的任务、性质、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作了有益的探索,并以之为学生革命的重要路径。“五卅”以后,“司法重查,关税会议,以及卖国的军阀逮捕爱国学生,封禁爱国团体,种种摧残爱国运动事件,都听他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军阀)为所欲为,我们虽然反对至再至三,结果还是毫无效力”,面对此种情形,“徒事摇旗呐喊是无关于事的,向帝国主义妥协和在军阀面前请命,那更是无异于跪在老虎面前,要求不要吃人一样”,最后便只得“由呐喊请命式的革命时期而转至以武装革命的时期了”。学生军之重要使命在于“领导全民众武装起来,集中人民势力,来打倒一切压迫阶毅——军阀、资本家、列强帝国主义”,更简单地说,“学生军的组织,就是我们实行革命的准备,也即是我们达到民族独立并得着真正平等的一个有力武器”。[3]482-483在学生军的操办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被投机的国家主义者和失意的军人政客借利用、影响,“这便是要学生军本身有一个坚定而明了的中心主义”,以“为世界被压迫阶级图解放,向国际资本主义复仇”为信仰,则学生军“一定可以成为中国之国民革命中一个很大的势力”。[3]480
至于学生军的组建方案,中国共产党人亦有相当的认识。1925年8月,恽代英发表《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对该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恽代英提出了编练学生军的具体办法,他认为学生军应“由各地学生联合会主持,各校学生自由报名,由学生联合会聘请军事专家,与以短期的真正的军事训练”,并且“由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借能容百余人之大屋为教练处,凡入学生军的在受训练时应搬到此中居住,完全过军队的生活”,时间为“三个星期乃至一月”,同时,“学生军最好每次以一连一百二十六人为训练的单位,一连学生军至少须聘用受过完全军事教育的训练员二人”,其余诸如学生军训练使用枪械问题、伙食费用筹备与训练员之薪金问题等都有论及。[27]213-214同年11 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公布学生军军事组织大纲10 条,在恽代英所列基础上又有细化。首先,不仅规定了学生联合会的主持之责,还规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负计划一切及监督进行之责”。其次,正式组织学生军时,“各地学生联合会先招十八人或三十六人编为教导队”,待“教导队毕业后,再正式招编学生军”。再次,学生军以四星期为训练期,期满即行退伍,“每半年由各地学生联合会召集各该地退伍学生军会操一次,每一年由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军事委员会召集全国各地退伍学生军举行大会操一次”。最后,各地学生军训练所需服装器械等,“概由各地学生联合会负责搜罗或向各地军事长官处请领”。[3]476-477尽管中国共产党人有相当的认识,也提出组织的思路,然而实施起来仍有相当的难度。就方案本身而言,学生军的组建高度依赖于学生会的组织,而学生会的组织在全国并未普及,力量也有限。再看当时的大环境,学生军的训练在许多地方难为当局支持,帝国主义亦可能横加干扰。所以,学生军的组建和训练并未成为大势,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组织训练学生军的计划便再难开展。最后,吸收学生参军,是为学生武装革命之现实策略。
结语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1]3。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话语中,学生是“革命的朋友”。在整体教育水平低下的近代中国,学生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文化优势”至为明显。他们不仅是外来思想文化的接收者,更是其传播者,如此,一方面造就学生群体之民族国家观念强烈、革命观念亦深;另一方面使学生成为“大众的启蒙者”,更因其有组织而聚集,学生革命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学生革命的理论探索,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又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在此时已初见端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的认识,并非没有分歧,前后亦有差异,这与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水平相关,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成长初期,对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调整、不断修正是常态。随着革命的深入以及自身的成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生革命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并更加符合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