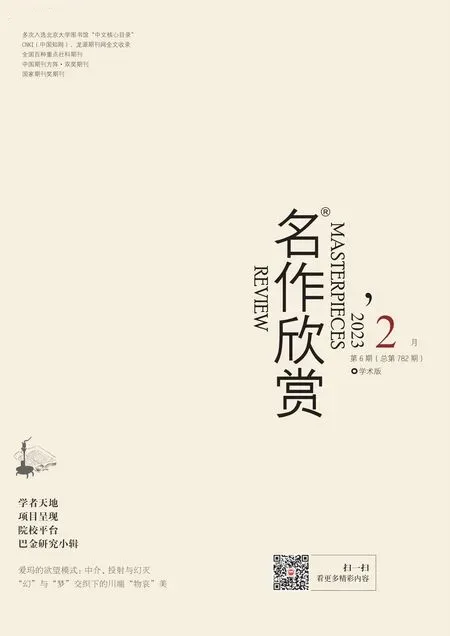爱玛的欲望模式:中介、投射与幻灭
——基拉尔“三角欲望”视域下的《包法利夫人》解读
⊙杜超逸[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江苏 苏州 215121]
一、欲望三角模型:爱玛的欲望构成
勒内·基拉尔提出以“欲望三角”为中心的“模仿欲望观”,这一理论认为“模仿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抄袭,是模仿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是最强的欲望,也是唯一真正的欲望。浪漫的谎言就在于强调欲望的“自发性”,将对欲望的唯我论定义投射到小说的真实——对模仿欲望的揭露上。①
“欲望三角”的基本模式如图1 所示,基拉尔将我们崇拜并希望与之相像的“楷模”称为“欲望介体”,追求客体,归根结底就是追求介体。主体通过介体选择其欲望的对象,这种欲望是既以他者为原因,又以他者为目标的。介体对主体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使得主体丧失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和判断力;
(2)使主体混淆欲望和保持自我的意志;
(3)主体借助欲望选择“模式”;
(4)造成两个相互竞争的欲望,也即产生“模仿竞争”。

图1 三角欲望模型
本文主要涉及前三个方面,因为在《包法利夫人》中,介体外在于主人公的世界,由于介体与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这种介体被称为“外中介”,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较大,彼此不接触。与此相对的另一种介体则是“内中介”,两个场距离较小,彼此相互渗透。这就是对以“爱情”为中心的三角欲望结构的说明。
《包法利夫人》以文本形式的独特性和阐释空间的多元性著称于世。爱玛想象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被法国评论家于勒·德·戈尔蒂埃(Juleo de Gaultier)称为“包法利主义”②,即幻想脱离现实条件而进入小说般的梦幻世界,“小说”是学界探讨爱玛欲望模式的核心之一。
尽管此前的讨论充分关注到文学作品对爱玛欲望的影响,但多数论者侧重强调欲望主体的主动性,强调其自身的虚伪、自私、拜金等因素对其文学选择的影响,对爱玛模仿欲望的过程重视不够,或忽视了爱玛欲望的复合特质,从而使得对爱玛这一人物的分析落入道德说教的窠臼,同时也脱离了爱玛与塑造她的特定时代之间的有机联系。
本文认为,爱玛的欲望应该放在主体、介体、客体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整体中考量,她的欲望符合勒内·基拉尔提出的“欲望三角”模式。基拉尔将我们崇拜并希望与之相像的“楷模”称为“欲望介体”,追求客体,归根结底就是追求介体。主体通过介体选择其欲望的对象,介体为欲望建立模式。③基拉尔将欲望介体看作一个具体的对象,如具体的人。但介体可以是抽象的,如观念、认知,或由它们复合而成。爱玛所想象的舞会上的“子爵”,其实是她将小说情节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特质赋予他并经过想象的结果,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子爵”。
有学者指出,介体建立的模式,也即概念,可以表现在广告里,也可以是书籍、报刊的信息,通行的观念,流行的叙述,或某种文化、某个意识形态。④本文认为这种界定是比较合理的。爱玛所阅读的小说及其情节、人物,代表资本主义庸俗精神的奢侈品等都是构成爱玛欲望介体的原料。基拉尔批评了浪漫主义小说所宣扬的直线欲望,认为要“破除人的自主性神话”,“坚持对自我的定义不能摒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⑤,这为我们探索爱玛的欲望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当然,对文学浅薄幼稚的理解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爱玛自身,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将爱玛的病症称为民主式幻想,在社会和政治维度上解构了爱玛的欲望。民主社会的到来打破了不同阶层各安其分的秩序,使得平民也开始追求不曾有过的精神刺激,并渴望将其变为现实,混淆文学和生活的界限,这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也是“爱玛的不赦之罪”。⑥这一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不仅点明了爱玛浪漫幻想的病灶,而且强调了文学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爱玛作为欲望主体的普遍性。正如福楼拜所言:“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泣。”
基拉尔的三角欲望模型充分考虑了主体、介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问题,并凸显介体的地位。本文将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探究爱玛欲望生成、投射,及至幻灭的过程。爱玛的天性与后天的环境,感受、探索生活与赋予生活意义,爱情与金钱的张力隐藏在福楼拜微妙的反讽和对细节精妙的设计之中,这正是《包法利夫人》作为经典的魅力。
二、文学与自我想象:爱玛的欲望介体
基拉尔认为,“爱玛·包法利也依着年轻时饱读的那些情感小说编织自己的欲望”。他指出,文学在这里具有“种子”的功能,她的欲望来自浪漫主义小说的女性人物,这些平庸的作品摧毁了她的自发性。⑦
本文认为,将爱玛的欲望介体归结于任何具体的人或事物都是不全面的,从小说中获取的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和爱情观塑造了她庸俗、混乱、不切实际的欲望介体,即对“完美丈夫”的幻想。这使她不再“感觉”这个世界,而是让实际的感情机械地模仿已有的感情,将她对生活意义的想象投射给现实。
在爱玛所看的故事中,爱情无一不体现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书中的男子个个勇猛如狮子,温柔如羔羊,人品世间少有,衣着考究华丽,哭起来泪如泉涌。”⑧在爱玛构建的欲望模式中,一个强有力的、可依附的,同时兼有名利的男性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这些完美的男性没有任何私利似的投入爱情,是与资产阶级社会中被金钱腐蚀的人际交往现实相对立的,爱玛主观上有忽视这种对立的倾向。她看小说的目的是“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贪欲”;她会选择性地看见巴黎中符合她想象的“两三种场景,却遮蔽了其他的场景,让她觉着这就是整个人生”;她看小说时看到的不是其中女性的独立精神,而永远只有华贵的装饰和地位(如玛丽·斯图亚特)。将“美”“高贵”等词语与拥有更多的财富简单相等的粗浅认识已经侵入她的意识深处,对此,小说中描写资产阶级和贵族糜烂生活的片段难辞其咎。
爱玛的欲望介体似乎是她自发选择的结果,但这一由她自发选择的介体反而使爱玛丧失了自己的“自发性”,这种丧失反映在现实与小说的混杂之中。在爱玛那里,现实与小说的秩序是混乱的,阅读小说是在经历现实,经历现实也成为她“阅读”的一部分,她随时准备将阅读到的东西转化成观念存放在介体之中。后文中,她在侯爵的宴会上所关注的,都是小说中那些庸俗的东西。叙述者在暗中将现实与爱玛的想象对置,暗示爱玛已经将现实也当作小说阅读:
他这一生从未安生过,荒淫放荡成性,不是决斗赌博,就是诱骗女人,家产被他肆意挥霍,家人为他担惊受怕。
爱玛……仿佛在看意见非常稀罕的,令人敬畏的东西。他居然在宫廷里生活过,还在王后的床上睡过。
小说与现实形成互文关系,爱玛经历现实的目的是弄清“欢愉、激情、陶醉这些字眼,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而她从书中得来的对欲望模式的认识,已经给她一种价值预设:财富、名利、激情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荒淫、赌博等低级趣味,诱骗、挥霍家产、不顾家人等违背道德的行为是无足轻重的。对于爱玛而言,思想先于经历,对感情的想法先于感情,在实际存在之前,想象中已经多次经历“幸运的随大流的感情”,实际感情就模仿已有的感情。⑨这就导致她的生活并非感觉、经历的过程,而是不断上演先验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过程,她清楚地知道“她的气质不是艺术型的,而是多愁善感的,她寻求的是情感,而不是景物”。正如朗西埃所言,“狂热从今以后似乎要和生活本身共享实体,正是通过其盲目的推动,生活抓住了所有文字和所有形象,以便不断建造欲望的客体”⑩。虽然表面上看,爱玛赋予意义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爱玛显然没有意识到,她所认为的求索过程其实是赋予过程,是将她所认为的意义赋予这些词汇,并投射在属于现实的人身上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爱玛的自发性其实是被介体褫夺的。
我们可以用李健吾先生的观点总结爱玛的欲望介体:“她(爱玛)给自己臆造了一个自我,一切全集中在这想象的自我,扩延起来,隔绝她和人世的接近。这想象的自我,完全建筑在她的情感上面。”⑪这正符合爱玛的内心独白:“按照书本上的描写去想象爱情,那种感情多么妙不可言,多么令她神往呵。”爱玛欲望介体的本质正是一种“自我想象”和“隔绝”,她在脑中预先想象一个欲望“模式”,将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奢华享受的生活、不切实际的爱情,现实中“阅读”到的风景混杂在其中,并坚定地将这种在想象中经历的情感模式投射到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变成先验的东西,本是用来感受、寻觅的生活世界被爱玛以“艺术化”方式想象的欲望中介侵占了,然而现实世界有其真实的秩序,爱玛的欲望最终在这个秩序中走向幻灭,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三、欲望的投射与幻灭:现实·小布尔乔亚·子爵的幻影
本文在前一部分认为:爱玛的欲望介体是一个混杂的爱情模式,她希望让介体变成现实。在现实的爱情中,她应该是文学作品中声名显赫、高贵富有的少女或贵妇,她欲望的最终对象应该是“未知的丈夫”——舞会上的子爵,绅士而浪漫,为爱情不顾一切。爱玛“把她赋予子爵的优点转而赋予她实际的情人”⑫,并“赋予感受和神秘形象一种具体外形,让其体现在真实的物品和人物中”⑬。这就是欲望投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爱玛逐渐被欲望介体彻底支配的过程。现实秩序在这个过程中阻碍并最终宣告欲望投射的失败和欲望的幻灭。这个过程有两个转折点,分别发生在向罗多尔夫发出“你爱我吗?”之问和最终发现莱昂的平庸之后。这两个转折点使得原本还有一些农民质朴务实天性的爱玛完全放弃贞洁和操守,变成她曾厌恶的庸俗而乏味的人,形成了反讽效果。而当她的欲望投射触及坚硬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狡诈的欺骗和利益至上的原则时,她才不得不从精神麻醉中醒悟过来,欲望也随之幻灭。本文接下来就试图对爱玛投射自己欲望的两个对象进行分析。
莱昂身上所具有的浪漫气质与爱玛类似,在永镇的第一次会面上,他们的谈话合如符契:“落日”“大海”“冰川瀑布”“悬崖边的小木屋”“对着壮丽景色弹琴的钢琴家”,这与爱玛想象的“无比明净的原始生活”“林中的阴影”恰好形成某种对位,前者宏大,后者雅致⑭,然而背后的空洞和浪漫幻想是一致的。无论拯救公主的白马王子还是面对冰川弹琴的艺术家,在现实中都几乎不可能出现。他们都喜欢沉浸于小说中的“冒险故事”“淋漓尽致的细节描写”,两个庸人在讨论平庸的时候成为“知己”,这是小说隐含的一层反讽,爱玛的欲望由此生长。此时,爱玛虽然受到欲望介体的影响,按照她欲望介体的要求寻找情人,但她仍然保持她的贞操。她想要私奔,但她“心头骤然出现黑黢黢望不见底的深渊”,“爱玛愈是意识到这份爱情,她就愈是后退,一心想别让它冒头,想让它的来势减弱些”。
然而罗多尔夫是一个属于现实的人,与和爱玛一样富有浪漫幻想的莱昂不同,罗多尔夫始终知道爱玛只是一个“漂亮的情妇”,为了满足他原始的性欲,他准确地识别出爱玛的欲望介体,利用她的虚荣心,并用浪漫的陈词滥调欺骗她:
责任是什么!当然是去感受高尚的情感,去珍爱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去接受社会的种种陈规陋习,以及它强加于我们的耻辱。
英雄气概的源泉,创作灵感的源泉,诗歌,音乐,艺术乃至一切事物的源泉,难道不正是激情吗?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一想起您我就悲痛欲绝。
爱玛却以为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她“回忆起从前看过的书里的女主人公,这群与人私通的痴情女子……圆了少年时代久久萦绕心头的梦”。她以为罗多尔夫是书中的那个在阴暗森林中拯救女子的男子,会爱怜她,听她哭诉生活中的烦闷;她觉得她就是小说中那个落难的女子,区别只在于她的苦难是婚姻,是那个平庸而不懂浪漫的丈夫查理。
为了配得上这个她想象中的“子爵”,她要把自己打造成小说故事中的那个贵妇,她精心穿戴昂贵的衣饰,并觉得只要有奢华的物件就能获得想象中的爱情。然而罗多尔夫真实的想法与她的设想大相径庭,对于她送的马鞭和印章,他只是觉得她专横,将她的欲望强加于他。在她的想象中,她的恋人不仅是专一的,而且愿为爱一个人而奋不顾身,付出一切代价和激情。当她向罗多尔夫询问他是否只爱她一个人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这让爱玛悲痛欲绝,几近癫狂:“我知道怎样刻骨铭心的爱!我是你的女仆,你的情妇!你是我的国王,我的偶像!你心地好!你模样俊!你聪明!你了不起!”
本文认为这是爱玛彻底被欲望介体支配的第一个转折点,她希望罗多尔夫能遵循她的欲望模式,表现出梦中子爵的模样。小说是这样标界的:“习惯成了自然,包法利夫人的举止做派完全变了。”她变得浪荡、随便,道德观念让位于欲望。她渴望这位“子爵”的化身将她救出婚姻,远走高飞,她已经开始想象旅途中美妙的夜晚,远方的沙滩、悬崖和海洋。但她不知道的是,无论她如何打扮,如何深情,都不能改变罗多尔夫对她的厌倦和轻浮的态度,她只是他用完即弃的玩具:“他把她调教成一个又柔顺又放纵的尤物”,“她的打扮让他觉得挺做作,那种暗送秋波的眼神更是俗不可耐”。
罗多尔夫是属于现实的,他知道爱玛的情感是荒诞的,他不可能放弃个人的幸福,拖着一个在他看来仅是长得更漂亮些的情妇和她的孩子去受苦受难。爱玛认为爱情只是去追求“快乐”“激情”“陶醉”这种词形容的生活⑮,她不知道的是,爱情不等于激情,红颜终会老去,她读的小说只告诉她最浪漫的爱情,却没告诉她浪漫背后的物质基础和情感支撑,或者她忽略了这些珍贵的启示⑯。罗多尔夫作为布尔乔亚的庸俗性就表现在,他放任爱玛进入“痴愚”的深渊,他知道爱玛无法辨别现实和想象,却任由她越陷越深,只为满足自己征服、玩弄一个人的粗鄙愿望。他一开始就在欺骗爱玛,利用爱玛的介体掌控她。对爱玛最终的陷落,他负有和那些小说一样的责任。
被罗多尔夫抛弃之后,爱玛在一场大病之后将她的欲望转向超验的事物,随后一场演出将她重新与莱昂联系在一起。这次,两人的行为都变得更加放荡,爱玛短暂地表现了犹疑,她发问:“这样做很不妥当,您知道吗?”在感情上一向懦弱的莱昂却从容地说:“在巴黎都这样。”爱玛在偷情中感受到了成为小说女主人公的快感,认为自己正在成为上流社会的女人。同时,由于不能和他时刻在一起,爱玛要将宣泄欲望时的感受固定下来,换成华贵的新东西,地毯、新套子,只有这些才配得上她的欲望模式。
与罗多尔夫不同,莱昂在爱玛的欲望中始终占据被支配的地位,当爱玛告诉他,她曾经爱过另一个人时,他的反应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感受到自己地位的卑微”,他懦弱、自卑、优柔寡断,当那欲望介体的幻影闪过,“骑马在树林里漫游,与子爵跳的华尔兹,还有拉加迪的演唱”,“莱昂在爱玛眼里变得像旁人一样遥远了”。莱昂的“布尔乔亚式”性格比罗多尔夫更为显著,他缺乏独立自主性,想法受到母亲掣肘。在激情过后,他剩下的只是厌倦,而没有责任,他更不可能成为爱玛想象中的白马王子。他为了事业和名利而放弃爱玛,并且丝毫不以此为耻,叙述者对这种性格的概括是很准确的:
每个布尔乔亚,在特别容易冲动的青春时代,总有那么个时期,会自以为浑身都充满了激情,自以为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爱玛最终发现,想和布尔乔亚产生她欲望介体中的浪漫爱情是不可能的,“爱玛在私情中又尝到了结婚的全部平庸和乏味”,这是爱玛彻底被欲望介体支配的第二个转折点。虽然爱玛认识到莱昂不可能成为她想象中的子爵,但她已经上瘾了,“她再怎么感受到这种幸福的卑鄙耻辱,也是枉然,她已经离不开它了,这是习惯使然,要么就是堕落使然”,这是欲望介体强力作用的结果。在写书信的时候,她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欲望介体,叙述者在这里暗示了我们,爱玛现在追求的不是莱昂,而是那个“子爵”的幻影:
可是她一边写着,一边依稀看见另一个男人的身影,这是一个由激情澎湃的回忆、无比美妙的阅读、贪得无厌的欲念生成的幻影,他最后变得如此真实,如此贴近。
这个转折点成为爱玛被现实秩序吞噬的开端,即使她知道莱昂不是那个幻影,她也要拼命留住他,她已经进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如果无法找到那个目的,那就把那个目的或先验的生活意义强加给欲望对象的客体,“赋予客体一种虚幻的价值”⑰。假想欲望的投射在现实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她加大花销,找最好的旅店,透支自己的消费,这是爱玛的欲望彻底庸俗化的时刻。莱昂在这里真正地被肉身化,只是爱玛肉欲的对象,是形而上学的替代品,而那些美好的特质都是爱玛自我麻醉的结果。
然而,爱玛的自我麻醉和假想无法改变她借贷欠下的债务,这是她追求本就虚空的欲望介体的代价。爱玛混淆了文学与生活,不只是文学中的白马王子在这个被无能、庸俗的小布尔乔亚支配的时代不存在,那种挥霍无度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奢华生活不存在,娇滴滴的公主与小姐在这个时代也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是爱玛这种出身的人。文学可以不告知读者故事中的人物是如何获取那些金银财宝,如何认识她的白马王子,而生活不行,这就是文学与生活的最大区别,没有空穴来风的生活,也没有未经过程就可先行获得的生活意义,想将这目的、意义强加给生活,那就只有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正如爱玛最后发现莱昂的平庸一样,她也知道她大量购买奢侈品和小商品的代价:
一个人穷到这地步,就不会在枪柄上嵌银丝!就不会去买镶玳瑁的挂钟!……也不会给马鞭配上镀金的银哨子……
她不是没有想过要算账,只是数额太大,她只能“撇在一边,不去想它了”;爱玛知道穷到一定地步就不应该再买奢侈品,但她为了支撑自己虚妄的爱情,为了得到自己梦想中的“子爵”,哪怕是将一个完全没有“子爵”品质的人想象、包装成“子爵”也在所不惜,她觉得麻醉自己就可以永久地拥有对子爵的爱。只有当现实中的债务逼上前来,她才终于知道这种麻醉失败了,他们都不是梦中那个为女主人公付出一切的“子爵”:“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跟别的男人是一路货色。”其实她的两个情夫一直都是那路货色,他们一直是平庸、放荡、自私的小布尔乔亚,和查理一样,爱玛天真的地方不在于不能察觉出他们的平庸,而在于用自我麻醉的方式去想象平庸,认为在想象中可以把梦变成现实。“爱情会经受阵阵寒风,而金钱上的要求风力最猛,能把爱情连根拔除”,而当债务无情摧毁她欲望的物质基础时,她只能带着她的欲望——关于“子爵”的梦服毒自杀。
爱玛欲望投射的过程是一个不得不承认“文学仅仅是文学”⑱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唯一恒久存在的不是爱情,而是厌倦。爱玛讨厌查理的平庸,厌倦查理不能给她带来新的幸福;罗多尔夫厌倦爱玛的陈词滥调,莱昂厌倦爱玛用金钱收买人心的乖戾举止,这些厌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活,就是从变化到变化、穿越一系列平庸单调的经历”,“厌倦、爱、享受、依赖、又是厌倦,这就是指挥福楼拜著作的深沉节拍”⑲。在这之中只有查理这一个例外,尽管他平庸,但他容易满足,他为拥有爱玛这个妻子而骄傲,从未感到厌倦。他资质平庸,但他那有点呆板却真诚的爱是不平庸的。所以爱玛唯在一点上遵循了现实,那便是以世俗的价值定义平庸。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在世俗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不平庸”,而只能自我欺骗,最终走向灭亡。
四、结语
在基拉尔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第一,爱玛的欲望中介是观念的混杂,是从生活、书本中“阅读”而得到的各种碎片拼接而成的“幻影”——子爵;第二,爱玛的欲望就是将在脑海中已经上演过的理想爱情投射到现实中去,现实与这种想象的错位使得爱玛不得不麻醉自己,把那个目的或先验的生活意义强加给欲望对象的客体,现实秩序最终证明了这种强加的意义的荒唐,并摧毁了爱玛的欲望;第三,爱玛并非自始而是经历了两个转折之后才被欲望介体支配,这在作品中有明确的标界。
本文将上述发现融入爱玛的整个欲望过程,并做如下概括:
(1)介体生成:文学阅读与修道院经历(在农村成长的过程与这些经历对比,起到了加强介体的作用,现实条件的匮乏既是爱玛幻想产生的源头,也是摧毁爱玛幻想的“凶手”)。
(2)投射欲望:爱玛追求莱昂、罗多尔夫的过程(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化,逐渐放弃贞操变得放荡,被介体支配)。
(3)欲望幻灭:现实的债务,或者说再也没有办法获得的爱逼迫爱玛自杀。
最后,《包法利夫人》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之一就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承认物质世界独立于我们的希望和欲望而存在。我们也不总是控制我们的身体和思想。”⑳福楼拜借爱玛深刻地展现了欲望对人的负面驱动,这种驱动有时是无意识的。如果经由欲望介体达成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欲望介体并让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它支配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
①③⑦⑰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4、10、15、16、17、24、25、43页,第1—166页,第2、12页,第68—72页。
② See Jules de Gaultier,Le Bovarysme:La psychologie dans l’oeuvre de Flaubert,2007.
④〔美〕童明:《现代性赋格:19 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93页。
⑤ 陶艳柯:《基拉尔“模仿欲望”概念的回溯及辨析》,《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6年第2期,第43页。
⑥⑩⑬⑮ 〔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9页,第93页,第79页,第92页。
⑧〔法〕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译本,后文不再另行标注)
⑨⑱⑲ 〔法〕让·皮埃尔·理查:《文学与感觉:司汤达与福楼拜》,顾嘉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6—298页,第300页,第220页。
⑳⑫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第106页。
⑭〔美〕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168页。纳博科夫对这种方法的命名是“多声部配合法”。
⑯ 据原文可知,爱玛所看的小说中不乏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如玛丽·斯图亚特等;也不缺少优秀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司各特的作品。
⑳ Laurence M.Porter,Eugene F.Gray.Gustave Flaubert’s Madame Bovary:A Reference Guide,New York:Greenwood Press,2002: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