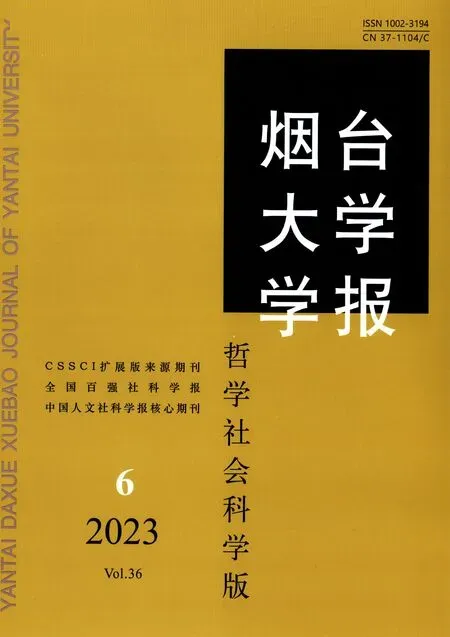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潘 威,刘其恩
(云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其决口、泛滥和河道迁徙给历代王朝都曾带来巨大灾难。岑仲勉、邹逸麟等学者详细研究过黄河变迁的大体过程,并将黄河河道研究由黄河本身推进到其背后的政治等层面。(1)相关研究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554页;邹逸麟、张修桂等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47页;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106页;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93页;邹逸麟:《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中国历史地理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218页;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4年版;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北京: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3页。明代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重要转折阶段,自嘉靖中期开启的黄河单股河形态至万历时期完全形成并持续至今,而其流路格局也维持到了清咸丰初年。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自弘治朝起,黄河下游河道向南分流,主要存在颍、涡、汴、睢等入淮入运河道,而这种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基本结束,故将明代黄河下游河道河型由分到合的时间节点定在1546年。(2)邹逸麟、张修桂等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231-232页。传统合流观点的支撑材料是《明实录》中万历二十五年(1597)河臣杨一魁的奏折,但该奏折在背景、内容以及与黄河合流的关系上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故而关于明代黄河下游河道的合流时间问题还有必要进行重析。对于明中后期的黄河分流与合流问题,需要跳出河道本身,进而对其背后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在疏理嘉靖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流路格局的基础上,分析该时期黄河河型转变的环境、思想、工程以及政治因素,探究明廷的河道治理经过及其历史动因,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为今天的黄河治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嘉靖以前的黄河下游分流河道
明嘉靖之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仍以分流为主,但以弘治朝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流又呈现出了不同特点。
(一)自然主导下的黄河下游分流河道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河之后,黄河南流,自泗入淮,开启了其新的长达四百余年的分流格局。金代时黄河缺乏治理,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黄河河道一方面“势益南行”,(3)《金史》卷二七《河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册,第671页。另一方面多股并存,互为主次,汇淮入海。终元一代,黄河以荥泽为顶点,河道呈扇形状态,在豫东和鲁西南地区不断摆动,南北分流,靡有定向。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决于曹县白茅堤,造成严重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4)④ 《元史》卷六六《河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6册,第1645、1646页。在此情形下,至正十一年(1351)贾鲁奉命治河,经其治理,“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5)③ 《元史》卷六六《河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6册,第1645、1646页。这条经贾鲁治理后的河道下经虞城、砀山、萧县、徐州等地,被称作贾鲁河道。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开封府兰阳县之上基本与现行河道相仿,至兰阳以下则主要走贾鲁河道。明弘治以前,黄河河患多发生在河南境内,尤其集中在开封段上下,决溢极为频繁。黄河经常多支分流下注,河道忽南忽北,极不稳定。该时期大的河道变迁主要有三次,(6)⑨ 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第16、17页。小的河道变迁更是不计其数,黄河纵横于大清河与颍河之间,基本上承继了元末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流路特点。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决于开封府原武县黑阳山,河水“经开城北,又东南经项城、太和、颍州、颍上至寿州镇阳卫入淮”,(7)《明神宗实录》卷三〇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772页。后人称之为“大黄河”,而微流经原贾鲁河道入运,被称为“小黄河”。永乐十四年(1411),“河南开封等府十四州县淫雨,黄河决堤岸”,河水南流至凤阳府怀远县,侵夺涡水入于淮河。(8)《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永乐十四年七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939-1940页。正统十三年(1448),黄河形成三股分流:北股决于“河南八柳树口,漫流山东曹州、濮州,抵东昌,坏沙湾等堤”,由大清河流入渤海;(9)《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八,正统十三年七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253页。中股决于开封府荥泽县孙家渡,南泛原武、阳武,由涡水至怀远县注入淮河;南股也由孙家渡决口南泛,经颍水下注后汇入淮河。(10)⑤ 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第16、17页。
弘治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虽经明廷大力治理,但仍旧频繁改道,河型多股分流,其整体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好转。该时期明廷对于黄河河性的认识并不充分,故在分流思想影响下,治河官员往往采取简单分疏的治理方法,任由水势多支分流下泄。朝廷对于黄河堵口工程并不积极,致使黄河时常或东北入运后危及张秋运河,或东南夺颍、涡入淮,贾鲁河道日渐式微,最终在黄淮海平原上形成了异常复杂的局面。通过疏理该时期的黄河分流河道会发现,这些分流大多由某次决口引起,黄河在具体分流线路选择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或南或北,难以简单判断,是一种自然因素主导下的分流河道。
(二)工程主导下的黄河下游分流河道
明代黄运关系自弘治以后更加复杂,两者经常相互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融为一体。弘治六年(1493),皇帝在下给刘大夏的治河诏命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11)《明孝宗实录》卷七二,弘治六年二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56页。万恭也说:“今以五百四十里治运河即所以治黄河,治黄河即所以治运河。”(12)万恭撰,蒋超整理:《治水筌蹄》,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治河任务的重点所在,十分明显。
弘治二年(1489),“河决开封黄沙冈、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冈、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入沁河”,(13)《明孝宗实录》卷二六,弘治二年五月庚申,第580页。使“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14)《明孝宗实录》卷三四,弘治三年正月辛巳,第750页。形成了三支南流河道,而北流河道再次冲入张秋镇,危及漕运。为此,朝廷派户部侍郎白昂修治河道,其治河主要措施是“北堤南分”,即人为地在黄河北岸“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15)⑥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册,第2021、2022页。而东南则以疏为主,先是“疏月河十余以泄水,塞决口三十六”,再“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16)⑤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册,第2021、2022页。从弘治三年(1490)开始,黄河下游已形成比较固定的汴、涡、颍三道,并以汴道为主流。(17)邹逸麟、张修桂等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229页。弘治五年(1492),黄河再决张秋,次年明廷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等人进行治理。(18)《明孝宗实录》卷八八,弘治七年五月甲辰,第1628-1629页。刘大夏首先在黄河北岸筑塞决口,接着建“大名府之长堤”和“荆隆口等处新堤”,(19)《明孝宗实录》卷九七,弘治八年二月乙卯,第1786-1787、1786页。通过北岸筑堤的方式遏制黄河北流。最后,他在黄河南岸疏浚“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20)《明孝宗实录》卷九五,弘治七年十二月甲戌,第1747-1748页。借助工程力量人为地“导河上流南下徐、淮”,使“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成(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21)⑨ 《明孝宗实录》卷九七,弘治八年二月乙卯,第1786-1787、1786页。“北堵南疏”自此成为明廷分流思想指导下的主要治河方略,黄河下游于是全部南流,河道逐渐稳定在颍、涡、汴三道,或入淮,或入运,分流格局相对稳定。
正德时期,明廷并未对黄河进行系统修治。筑堤以后,堤防固然起到了防止黄河北决冲淤运河的作用,但南岸的分流各道却因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22)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二,《潘季驯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点校本,第182页。原有河道相继淤塞,入运口不断北移。据史料记载:“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县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今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23)《明武宗实录》卷五六,正德四年十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56-1257页。黄河下游河道流路一方面“日渐北徙”,另一方面“合成一派,归入黄陵冈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运河”,(24)《明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2-73页。在整体格局上有迹可循,并呈现出由徐州经宿迁、淮安汇淮的合流趋势。
综上可见,弘治以后,明廷严格执行“筑北疏南”的治河方略,颍、涡、汴诸条黄河分流河道的空间格局十分明确,并在具体分流河道选择上受到当时治河工程影响,演变为一种工程主导下的分流。这种人为干预产生的南向分流河道,逆河之性,存在河浅、淤塞、北移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至嘉靖前中期时已空前严峻,成为黄河河型进一步变化的重要原因。
二、嘉靖前中期黄河上流河道合流的形成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大致以南直隶徐州为界,可以分为两段,徐州以上河段为上流,徐州及其以下河段则为下流。至嘉靖前中期,黄河对漕运的不利影响更加严重,因此黄河治理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但漕运问题及徐、吕水源危机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促成了其单股河河型的形成。
(一)嘉靖初年的治河议论
嘉靖初年,徐州等地水势异常,大水淹没田庐、损坏运道,朝廷为之震恐。治河之声遂起,大臣们各抒己见。嘉靖五年(1526),礼部尚书吴一鹏、大学士费宏请求浚通涡水以分杀水势。巡按御史穆相主张,在兖南徐北地区通过开一分流渠河来调节黄河水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戴金则主张逐一挑浚小坝至宿迁小河一带并贾鲁河、鸳鸯口、文家集等处。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栾主张疏浚“小黄河”故道。提督漕运总兵官杨宏、漕运都御史高友玑、河道都御史章拯等主张,利用归德州小坝河、丁家道口河、亳州涡河、宿迁小河等进行分流。工部认为疏浚南流河道的工程量太大,一时难以完成,且徐州水患并未对漕运产生致命影响,因此否决了大臣们关于开支河以分流水势的建议。(25)《明世宗实录》卷七一,嘉靖五年十二月丙子,第1620-1624页。
嘉靖六年(1527),在孙家渡河、涡河、睢河等分流河道中,总理河道侍郎章拯主张选择疏浚睢河一道。光禄寺少卿黄绾则主张在兖冀之间疏浚北行河道。明廷在诸多的治河议论中并没能形成一致的治河策略,而此时黄河再次水溢,最终奔入运河,阻碍了漕运。事发之后,詹事霍韬更是主张引河水注于卫河。兵部尚书李承勋、左都御史胡世宁都建议继续疏浚河道,导河使之南流。胡世宁在具体的分流河道选择上意见更加具体,他主张分疏三条河道,一是向南开孙家渡至寿州的河道,二是在自汴道东南出怀远、宿迁的两条河道中选择开浚一道,三是在自汴道正东出徐州小浮桥、溜沟的两条河道中选择开浚一道。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廷臣在治河事务上意见不一,大臣们在河道治理上也一时无法拿出最终决策,延误了治河事务,最终受到皇帝的责备。(26)《明世宗实录》卷八一,嘉靖六年十月壬申,第1819-1827页。
嘉靖七年(1528),工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潘希曾在赵皮寨河疏浚无果的情况下主张疏浚孙家渡河。嘉靖九年(1530),潘希曾又主张黄河不走飞云桥而复走归德故道。嘉靖十一年(1532),总理河道都御史戴时宗主张疏浚孙家渡河道、赵皮寨河道和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河道。嘉靖十三年(1534),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朱裳再次强调河道南向分流的重要性。(27)《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八,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第3554页。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刘天和则更进一步,他分析了黄河迁徙不定的原因所在,在分流上不再一味强调追寻“禹迹”,而是主张因地制宜,在保漕和护陵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有限分流来完成河道治理的任务。(28)卢勇:《问水集校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由上可知,在嘉靖初年的治河讨论中,明廷大多官员仍旧坚持“北堵南疏”的治河方略,主张通过人工疏浚的方法使黄河向南分流。故而此时治河讨论仍属于分流思想指导下的内部讨论,并未让明廷在治河思想上有质的突破。此外,分流河道淤塞已很严重,大规模的疏浚工程是明廷无法承受的,因此该时期分流说指导下的河道疏浚仅是部分河道的疏浚。在具体河道治理上,此时明廷的治河思绪仍十分混乱,治河事务迟迟无法有效展开。
(二)嘉靖前中期的黄运问题及其治理
正德末年,“涡河等河日就淤浅,黄河大股南趋之势既无所杀,乃从兰阳、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县之飞云桥、徐州之溜沟等处,悉入运河,泛滥弥漫,茫无畔岸”。(29)② 《明世宗实录》卷七一,嘉靖五年十二月丙子,第1621、1623页。愈演愈烈的河道淤塞问题至嘉靖前中期达到顶峰。嘉靖初年,明廷仍旧坚持“北堵南疏”的治河方略,一方面黄陵冈、金隆口一带的“北堵”工程每年都在进行,(30)① 《明世宗实录》卷七一,嘉靖五年十二月丙子,第1621、1623页。另一方面南流河道也在不停征发丁夫来疏浚。(31)《明世宗实录》卷七七,嘉靖六年六月丙午,第1710-1711页。但这些南流河道随浚随壅,实际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明廷深刻意识到疏浚工程的困难性,因此到了嘉靖十年(1531)前后,朝廷对疏浚工程的态度开始由支持转向犹豫。嘉靖九年(1530)时黄河曾决于曹县胡村寺东,河道重新回到贾鲁故道的同时还形成了一股入鱼台县济运的岔流,明廷认为该河道有利于黄河及漕运,这直接影响到之后的堵口工程。(32)《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丙午,第2841-2842页。嘉靖十二年(1533)以后,南流河道在淤塞的同时其北趋态势已无法改变,因此到了嘉靖十四年(1535),虽然赵皮寨河日渐充广,但明廷的主张还是如旧,闭塞渡口,使水不入涡河。(33)《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辛亥,第3884页。受河道淤塞影响,黄河日益北徙到贾鲁河道一线,黄河下游河道合流的自然条件初步形成。
至嘉靖十五年(1536)前后,明廷在治河上又陷入徐、吕水源问题的困境。徐、吕水源问题是指黄运交会的徐州段运河由于存在徐州洪、吕梁洪等险滩,如果黄河水量不足,漕船便会有倾覆之险。嘉靖以前的漕运问题大多受黄河冲运影响,黄河频繁决入运河,致使漕运受阻,解决方案主要是“避黄保运”,但“徐、吕而下,非黄河之来不能济”。(34)顾炎武撰,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6页。徐、吕水源危机使得运河黄运合一段因乏水而行漕不畅,该问题由来已久,但其对漕运造成的危害直到此时才达到顶峰。新的漕运危机使得明廷在黄河治理问题上更显复杂的同时,也让其治河目标再次清晰起来。总理河道都御史胡缵宗等人迅速导河入徐州,以解此时漕运燃眉之急,这直接加速了黄河河型演变的历史进程。(35)《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嘉靖十八年正月乙酉,第4538页。
嘉靖十九年(1540),黄河决于睢州野鸡冈,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漕运水源问题再次出现。周金、郭持平、魏有本、刘绘等治河官员主张以疏浚河道的方式来接济徐、吕二洪,以便通漕。而兵科给事中张翼翔则主张通过修筑堤防的方式来防止黄河南下,从而使河水全力接济漕河。明廷对此很快就形成定议,极力“并筑堤防,以止黄河南下”,(36)《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八,嘉靖二十年四月乙亥,第4985页。使黄河单走贾鲁河道,以便徐州至淮阴段的运河有足够的水源可以通漕。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筑塞睢州野鸡冈,浚兰阳李景高口,由萧县达徐州小浮桥,使“河之全力皆入于徐”。(37)万历《徐州志》卷三《河防》,明万历五年刻本,第72页。此后,明廷又实施过一系列的堵口筑堤工程,一面继续导水入徐州济运,一面在河北岸继续大筑堤防。(38)《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八,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第3554页。大致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徐州以上的黄河南流河道最终全部断绝,上流河道在堤防的约束下被初步固定在了贾鲁河道一线。
总之,该时期明廷在黄运治理上所遇到的问题难以解决,黄河下游河道北流趋势也不可避免,故此时明廷在治黄工程上虽然颇费苦心,但效果总是不佳。分流过多带来的漕运水源问题与以往的漕运问题完全不同,这既迫使明廷在治河事务上要迅速抓住重点,也要求明廷在具体工程实施上有所改变。因此,黄河分流河道的流路逐渐趋向徐州以接济漕河,颍、涡、睢、浍等黄河南流入淮、入运河道全部断绝,黄河下游河道的上流河段初步实现了合流。
(三)明代黄河合流时间问题重析
学界关于“分流”的定义相对明确,认为“分流”就是把黄河分为两支或者多支下泄。(39)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第85页。具体而言,是指按照禹疏九河的方式,把黄河分为两支或多支,借助不同的河道以分流入海,或者在分成多支以后又合流入海。所谓“合流”,目前尚未有一种明确的定义,但就明清废黄河故道而言,合流就是通过筑堤的方式把河流纳于一条河道里。与“分流”相反,“合流”在大多数时候只存在一条相对固定的河道,但是当遇到特大洪水漫堤时,持合流论者也会主张施以减水工程,或开泄洪道分流,不过在事后又需要及时进行堵塞。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至嘉靖二十五年已基本结束,故将明代黄河下游河道河型由分到合的时间节点定在这一年。认同此观点的学者甚多,其中尤以《中国历史自然地理》所收文章作者为代表。(40)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邹逸麟、李德楠、潘威、王兆印、刘成等。参见邹逸麟、张修桂等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231-232页;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德楠:《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兰州学刊》2008年第8期;潘威:《重析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改道”的形成》,《史林》2021年第5期;王兆印、刘成、何耘等:《黄河下游治理方略的传承与发展》,《泥沙研究》2021年第1期。但通过解读史料并联系嘉隆万时期黄河的具体流路来看,将嘉靖二十五年作为黄河合流的时间节点存在一些错误。首先,该观点的支撑材料相对单一,主要是万历二十五年总理河道尚书杨一魁的奏折。杨一魁在奏折中写道:“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或由秦沟入漕,或由浊河入漕,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41)《明神宗实录》卷三〇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第5772-5774页。明代黄河材料十分丰富,但却很难找到第二条能证明此观点的史料,故而将该条孤证作为这次重要事件的依据,在材料层面有所欠缺。其次,该条史料所说的“南流故道始尽塞”与黄河“合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始尽塞”并不等同于“合流”,该说法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再次,该史料初成于万历中期,编纂于天启时期,距离嘉靖二十五年已经过去至少半个世纪之久,在时间上跨度较长。最后,嘉靖二十五年之后,黄河在归德以下地区仍然存在分流河道,多时甚至河分十余股。(42)《明史》卷八三《河渠一》,第7册,第2037页。可见,“尽出徐邳”并不是说徐邳以上只存在一条河道,分流河道在嘉靖后期依旧存在,故该观点在事实层面也存在错误。
学界之所以会误将嘉靖二十五年作为黄河下游河道合流的时间节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杨一魁的上述奏折在清代被收录到《行水金鉴》中,(43)傅泽洪、黎世序等主编,郑元庆、俞正爕等纂辑:《行水金鉴 续行水金鉴》卷三九《河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册,第1433-1434页。而《行水金鉴》作为上世纪水利史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料,往往被老一辈学者作为一手史料直接使用。其次,《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受编写目的影响,全书内容的侧重点和编写的着力点大多聚焦在了气候等编,在黄河部分的投入稍显仓促和不足。最后,邹逸麟等老一辈学者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在史料的检索、发掘和校订上仍十分困难,故而只能使用有限的史料进行黄河下游河道的河型研究。传统黄河下游河道合流时间点的说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部分内容上出现错误在所难免。
总而言之,将杨一魁的这一奏折作为明代黄河合流的依据是不足取的,而明代黄河合流的时间节点也确实不在嘉靖二十五年。万历七年(1579)以后,黄河经万恭、潘季驯等人治理,河道被完全收束在大堤之内,黄河合流至此才得以最终实现。
三、嘉靖后期的黄河下流河道流路及明廷治河思想变化
自嘉靖二十五年起,黄河上流河道实现合流。但此时黄河下流的徐州段河道仍面临过窄、过浅、淤塞等问题,黄河频繁决口改冲,河道异常混乱。明廷一贯坚持的分流思想至此难以满足河型变化的需求,这时新的合流思想便应运而生。
(一)嘉靖后期黄河下流河道流路变化及成因
黄河自嘉靖二十五年后整体由徐州入运,“漕挽顺利,人力甚省”,(44)《明世宗实录》卷三五五,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丙申,第6391页。漕运一时十分通畅。但这种相对安稳的河道流路并未维持太长时间,新的河道问题又接踵而至。
黄河下流河道在嘉靖中期以前的变化大多有迹可循,或维持在贾鲁河道一线由徐州小浮桥入运,或循睢河河道由宿迁小河口入运,或逐渐北徙由飞云桥入运,总之,河道流路不算太复杂。但在上流河道实现合流后的短短二十年里,下流河道不断分流,最终变得混乱不堪。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黄河在曹县新集决口,新集以下河道淤积二百五十余里。黄河“趋东北段家口,析而为六,曰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曰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余里遂淤不可复矣”,(45)④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第7册,第2037、2038页。河分十一股,河道情况十分混乱。
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黄河下游河道的变化重点聚焦在了徐、邳、丰、沛地区。黄河自曹县新集决口之后河道情况一直十分复杂,但由于没有直接危及运道,因此明廷对黄河采取了放任态度,任由其散乱。这种局部散乱的河道大多较浅,不久就会再次淤塞。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溜沟、浊河等北股河道皆已淤塞,下流河道逐渐走向合流。但好景不长,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道又北徙,决于沛县飞云桥,运道淤塞,全河逆流,又分为十三支。(4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四《河决之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0页。这次河决造成的分流严重危及漕运,因此明廷在保漕政治任务压力下迅速采取行动,命朱衡、潘季驯整治河漕,(47)②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第7册,第2037、2038页。河分十一股,河道情况十分混乱。自鱼台南阳至沛县留城镇开新河(漕河)140 余里,并在沛县筑石堤阻遏河水。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廷又于秦沟北岸筑堤,迫使河水专走秦沟,至此嘉靖时期黄河下流河道的变化全部结束。
黄河下流河道在嘉靖后期之所以会出现散乱分流的局面,自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黄河原有南流河道分泄泥沙,嘉靖中期以后贾鲁河道独受全河之沙,致使“徐州以上河道淤塞”。(48)《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四,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第6941页。河床淤高非常迅速,一次洪水就很容易在薄弱处溃堤,黄河决口分流难以避免。二是归德、徐州地区地势较平坦,黄河一旦决口,河水不受拘束,大多会侵夺区域内其他河流的河道以入运河,极易呈现出分流散乱态势。三是黄河下游河道上宽下窄,河南境内河身宽4至10里,山东至江苏境内仅0.5到2里,而徐州境内河道尤为狭窄。上流河道实现合流,河水由宽入窄,奔向徐州,形成雍水,故而曹、单、丰、沛等地决口频仍,黄河分为多支,入运口也在鱼台至徐州之间南北摆动。“漕渠窄溢,洪闸束捍全河入运,势自不容”,(49)《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八,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第3553-3554页。难以避免的屡次决口最终将黄河下游河道流路格局推向了新阶段。
(二)合流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明代分流思想能够延续到嘉靖后期,在于它能够较好地处理黄运关系,维持漕运畅通。分流思想指导下的“北堵南疏”治河方略不符合黄河本来的特性,是以牺牲豫东为代价的。此外,明廷引黄济运虽暂时缓解了运河水源问题,但需经常疏浚,费时费力,因此朝廷亟需新的治河思想来解决黄运问题。至嘉靖中后期,黄河下游河患已经下移并主要集中在徐、邳、丰、沛地区,出现了前文提到的嘉靖四十四年河道洪水横流、运道敝坏至极的局面。明廷分流思想指导下的治河实践完全陷入困境,再难以处理好黄河与漕运的关系,治河者在治河思想上不得不谋求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分流思想遂被合流思想所取代。
合流思想大致产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是嘉靖中期以前分流思想越发难以解决黄运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治河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廷“筑野鸡冈口,挑浚孙继口、扈运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势东行”,(50)《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八,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第5166页。可见此时合流思想已经产生。此后,当河道发生变化时,明廷往往会通过具体工程尽量使河道回到贾鲁故道。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解决徐邳水患,严嵩“仍令工部行巡抚及河道官急将黄河下流设法疏浚,令水归故道”。(51)《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第6896-6897页。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隆庆六年(1572),朝廷在黄河两岸修筑大堤数百里,黄河下游遂初步并作一道,从而开启了以合流思想为主导的治黄新阶段。明代正统至嘉靖年间黄河过度分流,不但没有使河患减轻,反而造成了黄河此冲彼淤、靡有定向的局面,加重了黄河水患。采取合流思想的治河者,是要解决分流存在的问题,通过堤防把黄河固定在一条相对稳定的河道里,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合流思想在嘉靖末基本形成,但受条件限制,此时的合流思想无法及时作用到黄河合流工程实践上,故而嘉靖后期成为明代治河思想由分流转向合流的过渡时期。至万历初年时,合流思想更具优势,明廷的治河实践也因之发生彻底变化。在政治上,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内阁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完全掌握了话语权,河官制度日臻完善,河臣权力因此扩大并能够在治河事务上有所作为。在思想上,明廷内部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治河讨论。与嘉靖初年的治河议论不同,这次讨论之后明廷在治河上有了更全面的规划,充分关注到黄河水沙关系、水流情况、堤坝作用等,深刻认识到徐邳道的作用和黄河单股行水的必要性。在工程实践上,徐邳、黄淮等大的工程相继展开,黄河两岸堤防加高。至此,“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完全取代“北堵南疏”成为明廷新的治河方略,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合流也最终由上流的局部延伸到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
四、结 语
明代黄河河道治理工程不是单纯的河政、河工问题,治理黄河以保运道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嘉靖前中期,明廷在治河方略上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逐渐被人为地导向徐州,下游河道河型自此发生重大改变。但嘉靖二十五年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合流其实只限于徐州以上的上流局部河段,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大多仍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故学界传统说法中将嘉靖二十五年作为黄河合流时间节点存在一定错误。嘉靖后期,黄河下流河道散乱分流,这不仅是河道过窄、过浅、淤塞等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还与明廷治河的政治目标密切相关。受政治因素影响,明廷在治河的力度上可谓不遗余力,但直到嘉靖后期也未能形成一个清晰完整的河道治理规划。该时期明廷在治河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目的性,但为了满足这些政治性要求,治河官员往往需要刻意忽视一些黄河本身的河性特点,在河道流路上变得别无选择。但在这一时期,分流思想逐渐被合流思想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系统全面的合流工程作了准备。
嘉靖时期,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出现的内外部变化,是当时政治、环境、工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明廷在面对黄运问题时的具体态度。但在以人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运作对治理黄河这种大规模工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嘉靖时期的河道境况和治河思想上的变化并不能促使明廷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河道的治理,故而只有到了政治因素、制度设计更加完备的隆万时期,合流思想才能得以全面贯彻。总之,黄河下游河道合流的过程可被分为不同阶段,而嘉靖朝作为该过程的关键时期,其治黄的实践和具体河型变化情况可为今天的黄河治理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