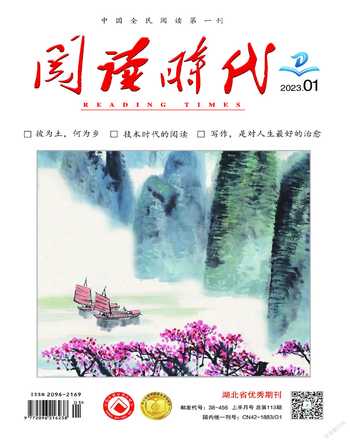神话叙述与神话原型
黄大荣
神话,现代文学批评使用频率最高的诗学术语之一。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尽管有些看法还不尽相同。
神话具有这些属性:1.固有的象征和隐喻性。2.神话“深蕴”人性——人的天性,因此神话具有普适性。3.“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弗莱),这种结构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共时性”。4.它是一种精神文明存在。
追溯神話的源头,可以发现它的本质属性或本义。在人类天真的童年,被希望和恐惧双重主宰的人的主体意识非常强烈,作为唯一具有反思和诘问能力的自然造化的人,幻象思维极其发达,他们用形象叙述(绘画、音乐以及后继的古歌谣),确认人与宇宙以及宇宙终极秘密的关系。有意思的是,随着人类年纪渐长,天真渐失,“世故”日增,“望星空”的兴趣和能力呈退化之势,坚持“问天”者寥寥。更奇怪的是,在大约公元前5、6世纪,神话叙述不知缘何戛然终止。其直接结果,所有后世的神话叙述,都失去了原创性的价值,都只是古人幻象思维的重复或变形。“神话原型”的宝藏,悉数保留在中国上古神话、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和《圣经》里了。
加拿大神话学者弗莱就从《圣经》里归纳了五种原型神话:天堂神话;原罪和堕落神话;“出埃及记”神话;田园牧歌神话以及启示录神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维能力全方位的衰退,事实上,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或跨越:从图形思维到玄性思维,再到理性思维和科学思维(复杂思维)。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神话原型之所以成了稳定的“共时性”结构(共时性是语言学基本范畴之一,与历时性对应。共时性是指,在历史长河不同的横截面上,保存着相对稳定的、不变的因素)而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是因为它深蕴人性,其中包括人的幻想、宗教情结和非理性非逻辑的玄思。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进步的是科学和技术,人性则是亘古不变,始终站在“原地”,仍然保留着上帝(科学家表述为“自然神”)的馈赠:一个伟大的多重悖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悖论;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悖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群居与独处的悖论。非但如此,我们甚至还无法判定,相比神话终止的前夜——那个所谓“轴心时代”,今天的人性,是更健全还是已经残缺?是更纯真还是已经堆积了污垢?这样反诘,当然不是要往回走,返回到农耕时代——那是假想的“诗意的栖居”,实则是更深的黑暗。来路早已被工业化淹没,去路尚可选择:走向智能时代。在历史的又一个出发点上,立一块防止人性沉沦的警示牌,绝不多余。
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神话原型结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补天,与西方创世纪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羿射日,带有某种程度的末日意识;嫦娥奔月则有人类强烈的孤独意识。也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诸子百家时期,中国的神话叙述就比西方提早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发达的寓言叙述。先秦诸子的著述里比比皆是(大量演化为成语故事)。寓言则比形而上的神话低了一个哲学层次,它实际上是诸子百家说理、辩论的另类的,即文学的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上古神话,有两个重大缺失。一是爱(实质是个人性)的缺失;二是末日意识缺失。后来的寓言故事同样如此。女娲神话含有的末日意识,被英雄母亲的补天壮举消解了,张扬了其世俗价值,忽略了其哲学意义。后羿神话含有的末日意识,同样被射日的壮举消解。什么原因?有待历史学者和神话学者深入研究。但毫无疑问,这笔有缺失的文化遗产,对后世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以及我国国民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难以尽述的影响。这里仅提一句:在人性论和乌托邦主义(“道德理想国”)这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上,似乎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