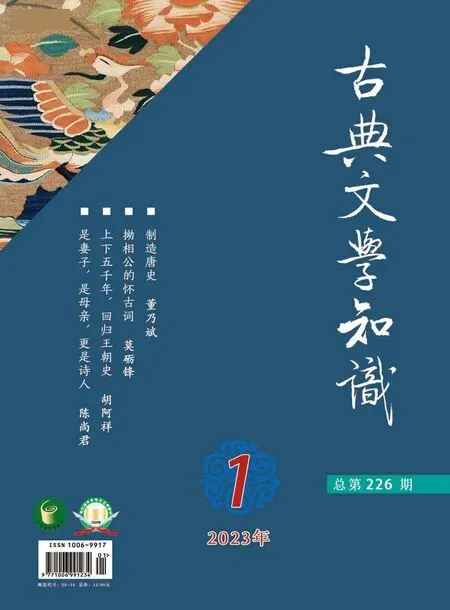《逍遥游》1
◆ 王景琳
◆ 徐 匋
〔题解〕“遥游”,作为庄子学说中一个如此重要的概念,有意思的是,这三字连用不仅从未在《逍遥游》乃至内篇中出现过,甚至在外杂篇中也寻不到任何踪迹。其实,就是用《逍遥游》作为篇名也不是庄子的原创。我们推测,最早《庄子》内篇传世时很可能就是一篇巨文,是后世的《庄子》整理者将其分篇,并从“逍遥乎寝卧其下”、“以游无穷”这两句最能代表庄子思想的语句中抽取了“逍遥”与“游”二字合在一起,这才有了《逍遥游》的篇名。
所谓“逍遥游”,就是人“心”可以“无所待”地“游”于社会、精神、自然等各个领域,没有时空限制,随心所欲,无往而不“游”,无境不可“游”,就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样的“逍遥游”尽管只是一种心的活动,但其中积淀至深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使人得以在“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境界中,无所牵挂、坦然自若地“游”于这个世界。这才是“逍遥游”思想所包含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

清 朱耷 《鱼镜心》 藏于北京荣宝斋
“逍遥游”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自魏晋开始,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便成了文人士子对抗、否定、逃避现实社会,不与当权者合作的一种精神力量,如果说,传统的文人士子“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传统是由儒家奠定的,那么,“穷则独善其身”的归宿则是由庄子完善的。而“逍遥游”世界恰恰为“穷则独善其身”提供了一个让人舔伤休憩的心灵家园。
庄子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今译
北海有一条叫作“鲲”的鱼。鲲鱼之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变化为鸟,名叫“鹏”。鹏鸟之背,不知有几千里。鹏鸟奋力飞起,翅膀犹如垂在天空中的云。这只鹏鸟,将乘着海动时掀起的大风飞往南海。所谓“南海”,是天然的大池。
说庄子
《逍遥游》一开篇,庄子便张力十足地渲染鲲鹏之宏大、描摹大鹏振翅起飞的雄伟壮观,先声夺人,带有令人震撼的磅礴气势。
鲲,原本不过是居于北海的一个鱼卵。可小小鱼卵却不甘于现状,向往起遥远的南海来。它终于等到了机会:趁着海运的大风化身为不知几千里的大鱼,然后又轰轰烈烈地化身为不知有几千里大的鹏,奋力一飞,翅膀高悬,犹如垂在天空中的云。不幸的是,虽然鹏尽了最大的努力,“怒而飞”,却偏偏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飞到南海去,它必须依赖海运的大风,必须骑在风背上,才能升上九万里高空。一旦离开了海运,失去大风的托举,鹏是很有可能跌个粉身碎骨的!后世《庄子》的读者,只看到了鹏的风光,看到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壮举(李白《上李邕》),却没有看到鹏起飞时的诸多外在因素。如果没有那场能搅得天翻地覆的大风,鹏能飞得起来吗?

明 周臣 《北溟图》 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庄子推出鲲鹏,其实是为“逍遥游”定下了基调。不论你是何等的庞然大物,能创造出怎样震撼人心的场面,你仍然“有待”,仍然得靠着他人的力量,这样的举动虽然惊天动地,却与“逍遥游”无关。尽管你可以“化而为鸟”,铆足了劲“怒而飞”,可惜这都不“逍遥”,离“逍遥游”更差得很远很远。
不可否认,相对于“小”,庄子似乎对“大”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所以他瞩目那么多巨大的东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树,“其坚不能自举”“瓠落无所容”的大瓠,“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的樗树,“不能执鼠”的嫠牛等等,这足以说明庄子在谈“大”时,内心是隐藏着深深的矛盾的。他不是没有想过要脱离现状,不是没想到过寻求改变,但最终他还是否定了自己,否定了“化而为鸟”试图南徙的意义。
这个“化”字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庄子《内篇》中,“化”是一个贯穿全篇的独特表述,有着特定的内涵,如《齐物论》中的“物化”,《人间世》中的“万物之化”,《德充符》中的“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大宗师》中的“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著名的子舆形体之“化”,以及《应帝王》中的“化贷万物而民弗恃”等等。这样的“化”是自然的无声无息之“化”,是道通为一之“化”,是“道”的动态体现。
然而,“化而为鸟”的“化”显然与上述众“化”有着明显的不同。鲲为什么要“化”?究其目的是不甘心一辈子做条小鱼,处心积虑地“化”为几千里之大的鹏。这样的“化”与“道”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只是出于自我的极度膨胀。所以这样的“化”也就绝不可能轻松自如、如同梦蝶那样惬意,而是要用尽全力才可完成,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怒而飞”这样拼尽全力、奋起搏击的场景。一个“怒”字,透露出这样的“化”是需要经过极力挣扎的。
可见鲲鹏之“化”不是自然之“化”,更不是万物一齐之“化”,而是潜藏着性命之忧的“化”。这样的“化”,闹不好是会丢掉卿卿性命的!就像辛弃疾所警示的那样:“似鲲鹏,变化能几?东游入海,此计直以命为嬉……嗟鱼欲事远游时,请三思而行可矣。”(《哨遍》)
庄子说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今译
《齐谐》这部书记载的都是怪异之事。《齐谐》记述说:“鹏鸟飞往南海时,翅膀拍击水面达三千里之遥,乘着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它凭借的是六月的大风。”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漫天的浮尘,都依靠气息的吹拂而浮游。仰望天空,莽莽苍苍,这是天真正的颜色吗?还是天那么高远根本就没有尽头?大鹏在九万里高空往下看,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说庄子
《逍遥游》开篇分明已经把鹏的起飞渲染得冲击力十足,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现在却笔锋一转,平实舒缓地说《齐谐》这部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看上去庄子引用《齐谐》关于大鹏南飞的讲述目的是以证自己所说不虚,实际上却是借《齐谐》作为上文所述鲲化为鹏之后的补笔,进一步渲染大鹏南徙时造成的巨大声势。“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更证实了大鹏虽然有了巨大的翅膀,海运和大风却仍然是它“化”和起飞的决定性因素。鹏的南徙,靠的并不是自家的本事,倘若没有扶摇大风的巨大支持,鹏的翅膀再大、再有力,也是飞不起来的。
那么,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北冥的鲲,化身为鹏飞上九万里高空之后,当它终于换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角度,不再受到身居一隅的局限,它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身处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第一个感觉天还是那么高不可测。在海里当鱼时,它仰望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见到的只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曾发出了“天之苍苍,其正色邪”的疑问。当它飞到了九万里高空时,发现天还是没有变化的“苍苍”,与在海里看天时“其远而无所至极”的想象并无二致。倒是往下看时,却有了新的发现,尽管野马、尘埃仍然飘浮在空中,但从海里看天上,与从天上看地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是何等的令人失望、沮丧!
鲲在北海时,曾期盼升上天空,它等来了六月的“海运”,“化而为鸟”,终于可以拍打着巨大的翅膀启程,奋力飞向那象征着拥有更多自由的天空,实现自己更大的南徙的梦想。可是,无论鹏怎样变换自己的位置,从海里到天空,或者从天空到大地,由于种种局限,鲲奋力所求的,未必就是适合它的世界。尽管鹏长出了令人羡慕的巨翼,飞上了他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可那又能怎么样?在九万里高空的鹏难道不是感受到了更多的束缚?更大的不自由?不过,鹏的高飞至少让它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得到了多大自由的同时也会得到同样大的束缚。鱼有水的局限,鹏有风的制约。谁也别羡慕嫉妒他人,也别想成为他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万物千姿百态,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使命,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本质上没有谁比谁更高,也没有谁比谁更大。恐怕这才是世界的“正色”!
无论庄子写鲲化鹏的寓意如何,“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毕竟飞起来了。从此,这只鸟成为人们仰慕、惊羡、向往的崇高精神形象,鹏程万里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中志向宏伟远大的象征。尽管这鸟大大偏离了庄子的航向。
庄子说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今译
水如果汇聚得不深厚,那么它负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堂前的凹地上,一根小草便可像船一样漂浮起来,假如放一个杯子,就会搁浅在地面上。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聚积的力量不强劲,就托不起鹏巨大的翅膀。鹏之所以能高飞九万里,是因为风托在下面,就如同鹏骑在了风背上。鹏的上面只有青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妨碍它,这以后鹏才可以筹划着飞往南海。
说庄子

元 华祖立 庄周像 出自《玄门十子图》 藏于上海博物馆
庄子不但想象力惊艳奇特,他的文思更是纵横跳跃,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说了“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句带有总结性的话之后,似乎庄子已经为鲲鹏的南徙之行作结,可是他忽然又把话题绕了回来。
大鹏分明已经起飞了,已经飞上了九万里高空,可是庄子似乎唯恐人们低估了大鹏起飞时所需仰仗的风力,用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比喻,再三再四地说风与鹏的关系。庄子说,堂前洼地上的一滩积水足够草芥那么大小的船只航行,可是如果放个杯子就动弹不得了。多大的水负多大的舟,多大的风托举多大的鸟。鹏之所以能够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完全是由于有着与之相应的强有力的大风的托举:“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几乎每一句都在强调着风对鹏的作用以及鹏对风的依赖。
可见鹏的起飞,就本质而言,犹如船的航行必须有水一样,都是有所依赖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鹏的动静闹得更大、更张扬而已。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庄子其实对大鹏的南迁之举颇有些不以为然,不认为有任何值得夸赞之处,相反,还暗示了好高骛远的鹏很可能会遭遇的悲剧!只可惜对鹏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它后来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也悔之晚矣。不管未来如何,既然已经飞了起来,就还得继续飞下去。至于鹏到了南海之后会怎么样,又能怎么样?恐怕连鹏自己也不知道。就鹏而言,它对自己的期望值越高,所争得的空间越大,所受的束缚也就越多、负担也就越沉重。不是吗?说到底,鹏游则游矣,却并不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