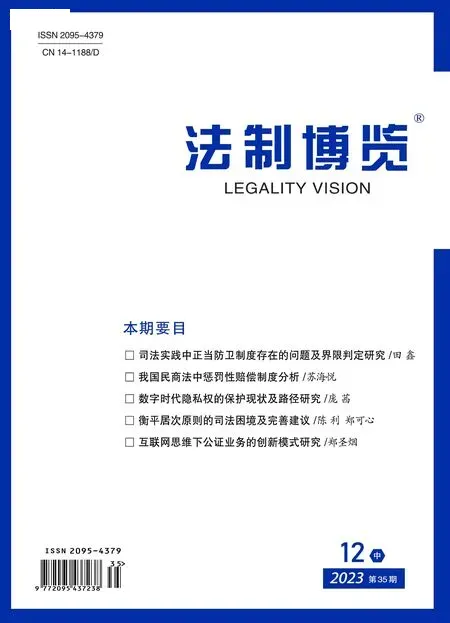合同无效后的所有权变动研究
严 慧 刘 辉
1.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 扬州 225000;2.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江苏 扬州 2250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涉及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中,如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已经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立法者没有指明此种返还是何种意义上的返还,而在当事人请求权基础不明确时,实务界和学界中出现了不同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后,基于合同发生的物权变动也丧失了基础,自然产生物权回转的效果,出卖人享有的是物权请求权性质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只有在原物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况下,返还原物请求权才转变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旦合同无效,财产的取得就失去了依据,此时当事人得以《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还有观点认为,物权已经完成公示,则成立返还原物请求权,若未完成公示则成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请求权基础的讨论意义
由于立法者并未明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返还”是物上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或是债法上的返还请求权。而认定为不同性质的请求权对于当事人的意义重大。
(一)在性质上有所差别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作为规定于《民法典》合同编“准合同”中的一项民事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债权的相对性决定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能由权利人向得利人主张,且作为一项普通债权不能优先于得利人的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最终受到清偿的可能性难以保证;相反,作为物上请求权之一的返还原物请求权虽然也是请求权,但其系为保护和救济物权而被创造出来,具有天然优先于债权请求权的属性[1]。原物返还请求权还指向占有人占有的特定物,其当然可以优先于债权请求权得到实现。
(二)在返还范围上有所差别
有观点认为,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比原物返还的范围更广。返还原物的范围及于原物及孳息,不当得利返还旨在将受益人所获得的一切不当的利益返还,包括实际所受利益、基于原物的占有而取得的收益,以及原物因第三人的毁损和占有而获得的赔偿金和保险金等[2]。
(三)在证明责任上有所差别
在证明责任上,构成要件越多的请求权所需承担的证明责任越重。在构成要件上,相比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要求的构成要件更少,请求权人既不必证明相对人有所得利(先于不当得利),也不必证明对方有过错(先于侵权),只要证明其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即可。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在涉及返还范围时,还需证明得利人的主观方面。返还原物请求权只要求权利人对标的所有权仍然存在,被告属于无权占有即可。
三、所有权复归问题的意义
在物权变动发生前,合同若被宣告无效,当事人的给付义务消灭。即使在不动产交易或所有权保留买卖中标的物已经转移占有,此时买受人的占有转化为无权占有,当事人自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原物。不能返还或者原物在法律或事实上毁损灭失,方可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者要求赔偿损失。
物权变动后,关于合同无效时的返还请求权,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我国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支持还是否认的争论。前者认为,当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效时,除非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瑕疵具有一致性,否则物权行为不因此归于无效。所以不当得利返还制度是对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必要的弥补;后者认为我国尚未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当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发生所有权复归效应或者物权变动自始不生效力,物权自始不变动,权利人得依所有权主张原物返还。
然而,在探讨该请求权究竟为何种性质时,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对结论有影响外,所有权是否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复归往往被忽略。而针对这一问题学界还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在合同被撤销后,所有权会发生回转效应。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由此可见,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请求权基础的争议,与物权行为理论和所有权复归问题均有关联。由此产生四种组合:否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且支持所有权复归观点、支持物权行为无因性且支持所有权复归观点、支持物权行为无因性且不支持所有权复归观点、否定物权行为无因性且否定所有权复归观点。下面逐一进行讨论[3]。
彻底否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认为,基于合同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效力,在合同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时,发生所有权复归效果,给付人有权请求受领人移转该物的占有,使其动产的所有权恢复至圆满状态;支持物权行为独立性学说的学者结论与此相似。在债权行为宣告无效时,根据物权行为的有因性,物权行为因此丧失基础,与债权合同保持同一效果。此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财产在性质上属于物上请求权。
若支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及无因性,即认为处分行为应当不问其是否基于某项有效的负担行为,而自行发生效力,则当导致合同无效的瑕疵不会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时,受领人仍然保有系争物所有权。此观点认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财产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
在支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以及所有权不会复归的前提下,若发生致使合同无效的因素同样也会使物权行为无效,例如行为人不具备行为能力,导致不动产登记的行为无效。此时即使物权行为无效,系争物的所有权也不会自动还原到给付人手中,其仅能依据不当得利规则要求返还。若瑕疵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仅及于债权行为,如在合同订立后行为人取得或者恢复行为能力,这时物权行为依然保有效力,更不应该认为给付人可以主张无效合同的返还原物请求权。
从否认物权行为无因性、所有权复归的观点出发,在这个前提下物权行为始终受合同效力的影响。一旦合同无效,移转系争物所有权的行为也归于无效,但恰恰因为无效的法律行为不足以使所有权自动回到给付人手中,实际上物权仍然处于受让人名下,给付人想取回原物仍然无法主张物上请求权,还是仅能通过不当得利制度来挽回损失[4]。
由此可见,是否承认所有权在法律行为被宣告无效后能复归于原权利人对于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请求权性质有决定性的意义。当否认所有权复归效果时,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得出的结论没有区别,那就是当事人只能向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四、法律行为无效后所有权不会复归
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不论是物权行为还是合同行为,一旦移转所有权的法律行为被宣告无效,所有权会转于给付人名下。但法学作为强实践性科学,其制度设计应以能够相对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同时使有过错者责任自负为宗旨。所有权是否真的会在合同无效后回归,并非一个等待人们去发现的真相,而是一个只有“应然”没有“实然”的问题。无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该观点,都是一种经过衡平后提出的“臆想”,倾向于哪一方观点,取决于依据其观点是否有利于最大程度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平衡、是否与当前民法已经存在的制度体系相和谐。从这一点出发,支持所有权复归的观点有以下问题无法解决。
(一)支持所有权会复归使利益保护失衡
当作为交易对象的动产权利已经通过现实交付或者简易交付的方式移转,此时占有人从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完成了圆满的控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动产权利人。应当分析在此肯定结论下给付人、受让人和第三人三方的利益状态。
对于第三人而言,主观状态决定了其能否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取得所有权。从日常生活经验考虑,凭借受让人已经占有该物,一般情况下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受让人有处分权,如果转移的是不动产,不动产登记簿强大的公信力就为第三人相信受让人有处分权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所以合同无效后受让人再次转让标的物时,受让人或占有物,或被登记为权利人,第三人想要主观善意并不难。即使第三人果真为恶意,而此时想要证明第三人主观为恶意,举证难度也极大。于是,不能证明其为恶意时,第三人事实上无论善恶都能善意取得系争物的所有权。可见,支持所有权复归反而会不加区分地保护恶意第三人的利益。
考虑到给付人在合同无效后,能够直接获得系争物在法律上的权利,得依所有权主张占有人(即买受人)返还原物。也许有人会认为,返还原物请求权拥有更优先的地位,可以优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更容易实现返还的效果。但不能忽视的是,给付人之所以订立合同,正是追求以物的所有权置换金钱债权的结果。当合同无效时,给付人不一定希望所有权回到自己的手中,相反不当得利之债具有与合同约定的价款请求权类似的效果。在受让人已经支付价款或者没有支付但其社会信用良好的话,让所有权回到给付人手中未必符合当事人的意思。只有在受让人无力履行对待给付时,让所有权在合同无效时回复于给付人才有保护意义[5]。而事实上,无论是恶意串通还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无效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对国家、社会、第三人利益产生了损害,极少是因为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冲突对抗致使合同无效,因此无效合同的受让方想要“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客观存在,但也能忽略不计。因此对于给付人的保护,所有权回归效果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此外,一般的移转所有权的合同,以所有权的转移作为风险转移的时间点,一旦交付完成权利移转,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转嫁给受让方。若承认所有权复归观点,则此时风险是否也应该随着所有权回转给给付人?若果真如此,承担一个不在自己占有或登记名下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对于给付人而言也未必愿意接受。
法律行为无效后,有权占有人转化为无权占有人。如果此时受让人未进行对等给付,则最多只需要另寻买家。若受让人已进行金钱给付,根据货币性质,受让人已经支付的货币已经为给付人所有。此时,支持所有权复归会直接陷受让人于财物两空的不利境地,牺牲了受让人的根本利益。
可见,支持所有权复归观点对于第三人的利益没有明显影响,对于给付人的保护也不会如期待的那样有力,甚至还可能因此承担毁损灭失风险。受让人的根本利益却无法得到基本保障,财物俱损。
(二)宣告无效不能成为物权变动的原因
虽然根据传统理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但无效合同的认定还是先由法院来完成,然后才能讨论合同无效的溯及效力。如果支持所有权复归的观点,则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确认判决则成为所有权变动的原因,而根据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法律文书可以导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然而,并非所有的法律文书都能引起物权变动。根据通说,民事判决可依当事人的诉求分为确认判决、给付判决和形成判决。笔者认为,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唯有形成权。与给付判决不同,形成判决不需要执行。不同于给付判决那样只是要求当事人承担配合进行物权移转的义务,形成判决生效即产生物权变动效力,没有可供当事人执行的给付内容和可供当事人承担的责任[6]。本质还是因为形成权行使的结果不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还具有对世性,可拘束第三人,且形成判决的公示力和公信力均要强于不动产的登记簿记载和动产的占有表象。
而在涉及合同无效的判决中,当事人在诉讼策略上常常会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要求法院判决双方相互返还财产。此类案件判决具有确认和给付的双重性质,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内容,而后的判决返还财产则有给付性质。但无论是确认判决还是给付判决,都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在当事人之间转移的后果。
物权的变动,或依法律行为,或依据事实行为,或依据包括法院判决、政府征收的公法行为。合同的无效并不属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任一种。认为合同无效后物的所有权会发生复归,没有法律依据。
从受让人角度出发,若其尚未支付价款,则承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若其已经支付价款,也能继续保有物之所有权,不至于沦为无权占有人而承担返还义务。而从第三人的角度出发,在否认所有权复归的背景下,受让人享有相应的处分权,第三人的主观方面不再重要。即使第三人为恶意,也不妨碍其从受让人处取得物权[7]。支持所有权复归与否,不影响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综上所述,所有权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不会复归,作如此安排也有利于公平保护受让人以及给付人的权益,更符合当事人内心的期待。但两种制度安排在第三人保护上没有体现出效果差异。此外,所有权不会复归也能契合当前的物权变动模式设计。基于所有权不会复归的论点,《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下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性质,也可以跨过物权行为之争的鸿沟,无论合同行为无效是否会引起物权行为无效,给付人都不能重新获得已经移转的物权,因此第一百五十七条下返还财产的应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