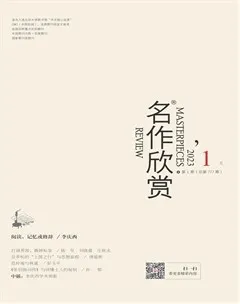《沉沦》:正视作为人性的情欲矛盾
北京 温儒敏
经典作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经典”,其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独创的艺术成就足以传世,其魅力弥久不变又与时俱新;另一种是“文学史经典”,艺术上有建树但可能并不圆熟,主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史现象,引起后人的关注。《沉沦》就大致属于“文学史经典”。1921 年10 月,收有这篇小说的短篇集《沉沦》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搅动了整个文坛和读书界。其内容的大胆和格式的特异,都让人震惊。而《沉沦》这一篇尤其引人注目,成了郁达夫的代表作。
《沉沦》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留日的中国学生,他在稠人广众之中总是感到孤独,总是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压迫,以至离群索居、自怨自艾。这其实就是青春期常有的忧郁症,不过比较严重,到了病态的地步。这种忧郁症表现为在性的问题上格外敏感,如主人公遇到日本女学生时的那种惊喜与害羞,那种忐忑不安,本来也就是青春期常有的对异性的敏感,不过小说突出了其中的夸大妄想狂症,又加上对于“弱国子民”地位的强烈的自惭,那复杂的病态情绪就带上了特有的时代色彩。
“弱国子民”的自惭与爱的渴求,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互相交叉的两个“声部”。读这篇小说时,如果把其中爱国的反抗的意蕴剥离出来,只能说是读懂了一部分,其实小说的大部分笔力是在写性的渴求、青春期忧郁的伤感,这是更吸引人的地方。对异性爱的渴望而不得,并由此生出种种苦闷,实在是青春期常见的心理现象,《沉沦》把这种心理现象夸大了,写出其因压抑而生的精神变态与病态,如窥浴、嫖妓等,在旧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情节,但在《沉沦》中出现,就特别注重精神病态的揭示,灵与肉冲突的罪恶感在其中得以充分地表现。
《沉沦》通常被看作是展现爱国情怀的小说。从作品主人公所感受到的“弱国子民”被欺凌的悲哀以及那种悲愤的反抗情绪来看,确实有这一层含义。特别是把个性解放的渴求与祖国强盛的冀望结合起来,明显加强了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然而这毕竟不是一般的宣扬爱国主义或个性解放的创作,其特色在于病态的心理描写。读这篇小说不能不格外注意其心理描写的大胆与真实。
《沉沦》写病态,其意却不在展览病态,而在于正视作为人的天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欲问题。“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促使人们开始尝试探讨这个敏感问题。郁达夫用小说的形式那么大胆地真率地写青春期的忧郁和因情欲问题引起的心理紧张,这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中都是罕见的,郁达夫因此被视为敢于彻底暴露自我的作家。《沉沦》正视作为人性的情欲矛盾,题材和写法都有大的突破。
稍微展开说说文学中的情欲描写问题。
“食色性也”,毫无疑问,情欲也是人类生命的基本需求之一。文学表现情欲,正视这一精神状况,让人返观、宣泄、省思,自有一种审美功能,也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心理健全的成年人,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对于青少年可能会有些副作用,所以一般不提倡。周作人所谓“受戒者”分析评判这一类描写,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要求情欲描写不是有意展览,更不是制造感官刺激以吸引读者,而应当有一种审美的过滤,是经过精神性的升华而有助于理解人性的。前面讲到文学可以有些“灵与肉”的纠结,而不光是展览“肉”,没有“灵”的渗透。如《金瓶梅》中有大量色情描写,赤裸裸的,读了可能给人感官刺激,会反感恶心,而《红楼梦》中的一些情欲描写,大都侧重于精神层面,是有审美过滤与升华的。郁达夫小说的情色描写有些确实太露了,但基本上还是为了揭示某种病态心理,表现一种颓废的“时代病”,一种带有社会历史原因的精神状态,是所谓“受戒者的文学”,有生活历练的成年人必不会觉得这篇小说的情色刺激的,而能从中看到一代青年的心理症候。
“五四”打破了“铁屋子”,里边昏睡的人都醒了,虽然开始感觉光芒耀眼,但很快就又发现无处安身,新的苦闷就出现了。这是现代人的苦闷,醒过来的新苦闷。特别是“五四”落潮之后,很多年轻人都是伤感的、苦闷的,甚至是病态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精神状态叫作“时代病”。郁达夫写情欲与颓废,揭示了这种“时代病”。
另外,郁达夫那么大胆地描写情色心理,也是有意向沉闷、封闭、非人性的假道学传统挑战。等于在宣称:性的解放与爱情的追求都是合乎人情事理的,用不着躲躲闪闪。我们要把郁达夫写情欲、病态与颓废放到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应当肯定郁达夫是在试用现代的眼光去表现和分析人的生命中所包孕的情欲问题,探究人的合理欲求的自然伸张及其可能挫折。
像郁达夫这样认真坦诚地描写情欲和性心理的,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当代文学有太多情欲与性的描写,可惜大都是撒“胡椒面”,意在产生刺激与市场效应,很少有郁达夫这样老实和认真的。
郁达夫写情欲产生了某种“反矫饰”效果。就像郭沫若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让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受作假的困难。” “反矫饰”在当时的状态,的确产生了这种暴风雨般闪击的效果。
《沉沦》骤然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阅读风气,这种风气使得读者能完全走进作者的生活,和作者一起直切地感受人生,痛快地发抒平时可能压抑的情怀,包括青春的感伤、生命的迷惘,以及对现实丑恶的反抗。郁达夫把生命和创作搅到一块儿,他的创作缺少艺术的过滤,拉不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往往显得粗糙,然而丝毫也不做作,是那样的率真与直切,读者一接触到作品,就会被那种率真所吸引,抛开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持有的神往与崇仰,也顾不上其粗糙的形式,而一头栽进作品情绪宣泄的氛围中,用整个身心去体验郁达夫的同时,也可能是自己的人生际遇。
后世读者读《沉沦》已经没有了那种共时的感同身受,距离感会有所拉开,但同样会强烈感受到郁达夫惊人的率真,以及那特有的忧郁感伤气氛。读《沉沦》用不着仔细推敲咀嚼,可径直进入作品所构设的艺术世界,让那情绪流裹挟自己,和作者——作品主人公一起歌哭,就会感觉到一份难得的真实,一份让世界与自我都赤裸裸地剥除了伪饰的真实。
《沉沦》的故事不曲折,全篇由八小节组成,每一节叙一事或一种心境,结构也不紧凑,叙述显得有些拖沓。郁达夫并不善于讲故事,这篇小说如果从叙事的角度看,是并不怎么高明的,这都显示着初期现代小说的稚拙,但也有很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抒情。如这样的描写:
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四面并无人声,远远的树枝上时有一声两声鸟鸣飞来。他仰起头来看看澄清的碧空,同那皎洁的日轮,觉得四面的树枝房屋、小草飞禽,都一样的在和平的太阳光里受大自然的化育……
郁达夫这样清新诗意的文字,已经脱离了古文的束缚,当时令人耳目一新。《沉沦》在描写主人公心境变迁的时候,常用抒情的笔调,有时是通过主人公特殊的感觉去捕捉和描绘事物,使描写富于情感色彩或象征含义。如第一节写主人公避世的心情,那种融会于大自然的浪漫情怀,甚至感觉得到周围有“紫色的气息”;最后一节写主人公投海自尽前种种神秘的幻觉也带有某些象征抒情的意味。
读这样的描写,会感到郁达夫是极富才情的诗人,他在用作诗写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不讲求结构,语言也少锤炼,如果从小说的一般要求来衡量,似乎写得“不到位”,但读起来又很觉随意和畅快。这种不拘形式的写法,也是郁达夫这篇小说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不拘”才彻底打破陈规旧习,就如同听惯了严整细密的“美声唱法”,偶尔听听“不经意”的流行歌曲,也会觉得很随意畅快。郁达夫带给“五四”一代青年和后人的不是什么“深刻”和“完整”,而是一种才情,一份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