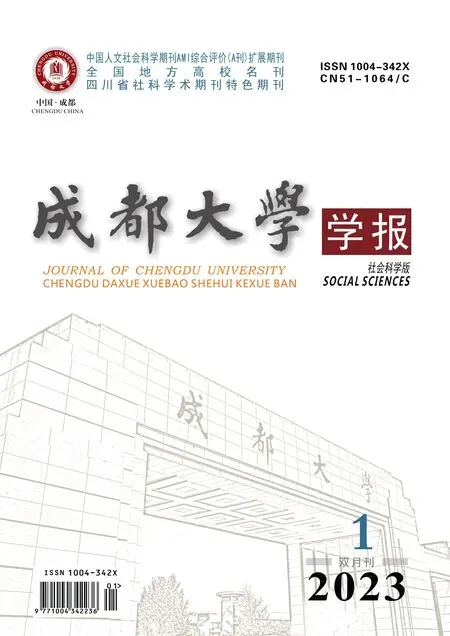大小戴《礼记》关于礼的起源论述
李佳喜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随着现代学科的兴起, “礼之起源” 成为20世纪以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相关论著已积累到汗牛充栋的程度。至少产生了礼起源于祭祀,起源于巫术,起源于俗,起源于等级分别,起源于父权制下的婚姻关系,起源于饮食,起源于仪式、动作,起源于交易,起源于生产,或认为礼有多元起源,是 “层累造成” 的等数十种观点。①参看曹建敦、郭江珍:《近代以来礼制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47-49页;惠吉兴:《近年礼学研究综述》,《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第131页;张弘、马婷婷:《中国古代礼的起源问题新探》,《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55-56页。
这些观点几乎都从 “历史溯源” 的视角展开,亦以探讨 “礼究竟起源于何” 为指归。以 “历史溯源” 为目的来考证礼究竟起源于什么,当然是重要的课题;但从观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人关于 “礼之起源” 的看法,也同样重要。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后者已被忽略太久,或只是在研究孔、孟、荀以及《礼记》等专题时被顺带提及,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统摄性的问题,并借此仔细研读、深入分析先秦文献,梳理先秦思想家们在探讨礼的起源问题时所形成的不同观点与论证方式。
本文的核心旨趣,是对 “礼之起源” 这个论题,跳出 “历史溯源” 的研究路径,做一个思想史与观念史的研究。具体而言,则是以大小戴《礼记》为基础,分析儒家传礼学者们对 “礼之起源” 这个问题的看法。①本文所引《礼记》原文出自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所引《大戴礼记》原文出自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本文想探讨的问题,不再是 “礼究竟起源于什么” ,而是在大小戴《礼记》中,儒者们对 “礼究竟起源于什么” 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得出了哪些观点,运用了怎样的论证方式?这些关于 “礼之起源” 的不同观点与论证方式,如何共同建构了一整套关于礼的 “起源话语” ,使 “礼” 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牢不可破地建立起来,并对后世从生活实践到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小戴《礼记》中, “礼” 和 “起源” 这两个概念都很宽泛,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指代各不相同。就 “礼” 而言,有时指上下尊卑的等级之礼,有时指日常生活中的丧祭之礼,有时又指人际交往中的相见之礼、宴饮之礼;就 “起源” 而言,有时指发生学意义上的 “最先发生” “最早开始” ,但更多时候还是指本质、根源上的起源。所以,本文对 “礼” 和 “起源” 这两个概念,也只能采取广义的定义,即本文所言之 “礼” ,包括礼制、礼仪等一切关于人的行为规范;本文所言之 “起源” ,既包含最先发生、最早开始义,也包含本质、根源义。具体所指,则根据思想文本本身的语境,随文释义。
一、礼起源于圣王制作
“圣人” “先王” “圣王” 等词,在大小戴《礼记》中基本是通用的,泛指有德行的君主,具体而言,即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等帝王。本文为行文方便,且明显突出德性层面的 “圣” 与政治权力层面的 “王” ,在表述中统一用 “圣王” 一词。
《礼运》云: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未有麻丝……后圣有作,然后……此礼之大成也。” 与《系辞传》一样,这也是儒家关于圣王制作的经典论述。在这个论述中,非但制度、文化层面的 “礼” 是由圣王制作的,就是物质层面的各项生活所需,亦是 “后圣有作” 之后才有的。人们由茹毛饮血、衣羽披皮的原始状态,进入有火金之利,有台榭、宫室、牖户之安,有养生送死之物,有琴瑟管磬钟鼓之乐,有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妇之别,有鬼神、上帝、先祖之祭的文明社会,其关键在于 “后圣有作” 。但这还只是概括性的叙述,具体有哪些圣王,他们分别 “制作” 了什么,都未论及。《五帝德》对此则有详细的论述,如表1所示:

表1 圣王制作表
至于为什么由圣王制作,且圣王为什么能制作的问题,《五帝德》认为这是由于圣王拥有最高的智慧与道德,且具有天生的能力:黄帝是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颛顼是 “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帝喾是 “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尧是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 ;舜是 “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 ;禹是 “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礼运》云 “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 ,《哀公问五义》也说圣人 “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 。总之,圣王不仅是人间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也是道德修养最好、智慧能力最高的人,同时还具有与天地沟通的神圣能力。并且,这种超凡的道德、智慧与神圣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说是上天赋予的。所以圣王可以 “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 。圣王既为一切之主宰,则制礼作乐便是应有之义。
“圣” 就有德而言, “王” 就有位而言,有德有位,方可言制作。《中庸》云: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都有德有位,故可有所制作。相反,蚩尤无德无位,故不能有所制作。非但不能进行制度、文化层面的 “制礼作乐” ,就连物质层面的器物(兵器)都制作不了。《用兵》云: “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 就无德而言,蚩尤 “及利无义、不顾厥亲” , “惛欲而无厌” ;就无位而言,蚩尤只是 “庶人” ,故不能作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以前,人们谈论 “圣王制礼” 这个问题,只会想到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史事,如《尚书·洛诰》称礼待周公而制,《逸周书·明堂解》云周公建明堂、朝诸侯、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宣公曰 “先君周公制《周礼》” 。在《周易》本经、《尚书》除《舜典》之外的篇章以及《诗经》《逸周书》《论语》《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上古圣王制礼的记载。但到战国初期的《系辞传》里,则开始出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制礼的记载;再到《大戴礼记》的《五帝德》中,这个圣王制礼的谱系则变成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整齐而有序,情节也更丰富而具体,后来被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沿用。
顾颉刚(1893—1980)发现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6页。王国维(1877—1927)也说: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②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4页。这些都是极具洞见的观察。儒家关于 “圣王制礼” 的论述,也有明显的 “层累地造成” 的痕迹。儒家所追溯的 “圣王制礼” 的清晰谱系,也是 “史实” 与 “传说” 的混合,不易区别,有一个 “信者愈多,其信更甚” ,最终 “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①冯友兰: 《大人物之分析》, 《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321页。,以致很多 “功绩” 都归附于他的过程。大小戴《礼记》说 “圣王制礼” ,并 “层累地造成” 圣王制礼的清晰谱系,即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论语》载子贡之言曰: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已经清醒地看到纣王的形象是 “天下之恶皆归焉” 的结果;同理,关于包牺、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制礼的记载,则是 “天下之善皆归焉” 的结果。
二、圣王效法天地以制礼
在大小戴《礼记》看来,礼虽是圣王制作,但圣王之制作,亦是有本有源,有理有据的,《礼器》云 “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 ,而非 “无中生有” ;且其制礼之缘由,亦非秘不示人之天机,而是可以通过 “述而多学” 习得的。《乡饮酒义》云:
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礼运》云:
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礼器》亦云:
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圣王制礼作乐,必以天地之间的自然秩序为根据,是对自然秩序的模仿。《王制》云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 ,必即天论,即与天地秩序一致。《孔子闲居》云: “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 礼之作,是圣王对自然秩序的模仿,故自然界的变化,皆可成为人类社会的教化之源。
自然秩序的核心,是天地上下之分。《乐记》云: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又云: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 具体而言,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现实生活中区分君臣、男女、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之礼,都是圣王效法天上地下、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而作。《郊特牲》云: “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 谓男先于女、君先乎臣的尊卑之礼,源于天先乎地的自然秩序。自然之最贵者莫过于天,人间之最贵者莫过于天子,所以天子之巾车,及郊祭所穿之祭服、所用之旗帜,皆法天而制。《郊特牲》云: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天子巾车、祭服、旗帜之礼均法天而制,除了 “郊所以明天道” 的寓意外,更象征着 “唯天子受命于天” ,天子 “与天地参” ,天子之尊高,与天相匹。
在为现实生活中的等级之礼找到了天尊地卑的自然起源之后,礼便成了自然秩序在人间的实现。这样一来,礼就超越了作为人间规范的层次,具有了与自然秩序一致的等级结构,也因此具有了与自然秩序一样的合法性。再往前推论一步,即可将 “礼” 视为天地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乐记》云 “礼者,天地之序也” ,便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礼本是模仿天地秩序而作,但现在本身也成了一种 “天地之序” ,即人间的等级秩序成为了一种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恒常不变,所以人伦等级秩序亦恒常而不可变。人们只能像遵循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一样遵守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尊卑、贵贱之分的等级之礼,而不能做僭越之事。否则,不仅是 “悖礼” ,更是 “悖天” “反天” ,即《虞戴德》所云: “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顺;有臣不事君,必刃。”
更往前推进一步,《仲尼燕居》云: “礼也者,理也” ,《乐记》云: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 “礼” 本身已是一种 “理” ,是 “不可易” 的。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长尊幼卑之 “礼” ,和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一样,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都是 “不可易” 之 “理” 。经过这个转换之后,礼便不再需要每次都从天尊地卑的自然化论述中获取合法性,其本身已可作为独立的论据,用 “礼也者,理也” 的论述方式来证明各种礼制之合法性了。也就是说,人间的 “礼” ,与天地自然秩序处在了相同的地位,它们都是更高层次的 “理” 的体现,自然秩序是一种 “理” ,人伦等级秩序也是一种 “理” ,在论及后者的时候,不再需要援引前者来证明自身,只需援引两者共同所属之 “理” 就可以了。
这种 “以理代礼” 论证方式的出现,当放到关于礼之起源的 “自然化” 论述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到比较妥当的理解。且这种论证方式的出现,绝非宋明理学家们的原创,而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是在探讨礼的自然起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乐记》云: “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昏义》云: “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 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别,以及强调 “妇顺备” ,都只是一种 “礼” ,但这里用的却是 “理” 字, “以理代礼” 可以消解 “礼” 作为一种人为社会规范的意涵,而赋予其超越、神圣、恒常的象征意味。又《祭义》云: “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 根据上下文意,可知句中的 “德” 指 “乐” , “理” 指 “礼” ,即直接把 “礼” 视为 “理” 。
大小戴《礼记》讲 “圣王效法天地而制礼” ,这和《易传》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 “从天上说下来” ,如《礼运》云:
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礼本于大一,圣王制礼,只是 “官于天” ,从天地、阴阳、四时、鬼神层层说下来,取 “其降之命” 而制之。但大小戴《礼记》比《易传》更多了一层 “从地上说上去” 的精义,即在论述 “圣人效法天地而制礼” 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拔高礼的位置,如表2所示:

表2 人间秩序(礼)与自然秩序关系演进表
礼从最初在下位 “效仿天地” 的被动地位,进而上升到与天地自然秩序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最后获得与自然秩序同等的地位,共同属于更高层次的 “理” ,其地位是在不断上升的。当礼还在下位、 “在人间” 的时候,必须援引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来论证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礼上升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时候,实际上也还是在用自然秩序来进行论证;只有当礼独立于自然秩序,成为一种 “理” 的时候,它才可以真正独立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虽然在 “从天上说下来” ,即圣王效法天地以制礼的层面上,传礼儒者们的理论体系不及《易传》之完备与精微,但他们却开辟了另一条 “从地上说上去” 的道路,把礼的地位层层拔高,并最终使礼成为 “理” 的一部分,可以脱离天地自然秩序而独立论证自己,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三、圣王因人情以制礼
《哀公问五义》云圣王 “能测万物之情性” ,《礼运》云 “圣人作则……人情以为田” ,又云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 ,《礼器》亦云礼 “合于人心” 。此皆谓礼源于人情,圣王因人情而制礼。《礼运》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进一步追问,人情又源自何处呢?《三年问》以 “哀” 为例,说: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
凡有血气者,必有 “知” 之性;有 “知” 之性,故有 “爱其类” 之情。人是其中之最 “知” 者,故人 “爱其类” 之情亦最深切。同类去世,人会有 “哀” 之情。同类中又以亲人之情最深, “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 。人有情感,源于人有 “知” 之性,能够感知。
关于 “因人情以制礼” ,还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制礼实例中得到验证,《曾子问》载:
子游问曰: “丧慈母如母,礼与?” 孔子曰: “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
本无 “丧慈母如母” 之礼,但鲁昭公少年丧母,由贤良之慈母抚养长大,鲁昭公视之如亲生母亲,所以慈母去世的时候,鲁昭公心有不忍,想为之守丧。两处 “弗忍也” ,即其心中之真情所在,遂不顾大臣反对, “练冠以丧慈母” 。后来此真情之流露亦为大家所接受, “丧慈母” 也从原来的 “非礼” 变成了一种礼,并与亲生母亲同等。《仪礼·丧服》云: “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三年者,父卒则为母,继母如母,慈母如母,母为长子。” 把 “慈母如母” 写入礼经,即正式承认了为慈母守丧是一种礼,这也是对人们心中真实情感的尊重与认可。《礼运》说礼起源于人情,只要 “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这便是一个经典范例。
《坊记》云: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节” “文” 二途,是圣王因人情而制礼的基本方式,过者则节制之,不足者则文饰之,使归于 “中” ,以达到 “情深而文明” 的境界。《仲尼燕居》云 “夫礼,所以制中也” ,《礼器》云礼 “不丰、不杀” ,《檀弓上》云 “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三年问》云愚陋邪淫之人 “朝死而夕忘之” ,修饰之君子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 ,二者皆不可从,故先王 “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 ,皆言此义。
关于礼起源于人情,大小戴《礼记》对丧、葬、祭礼的论述,最能凸显当时的社会情境以及儒者们的理想追求。《问丧》论三年之丧云: “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 又论杖礼云: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祭统》云: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 又云: “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 这是概论丧祭之礼源于心,源于 “人情之实” 。基于丧、葬、祭礼之重要性,大小戴《礼记》几乎对这些仪式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源于人情的阐释。
冯友兰(1895—1990)说: “吾人之心,有情感及理智二方面。如吾人之所亲者死,自吾人理智之观点观之,则死者不可复生,而灵魂继续存在之说,又不可证明,渺茫难信。不过吾人之感情又极望死者之可复生,死者之灵魂继续存在。”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6页。故丧祭之礼乃兼顾理智与情感,折衷于二者之间的仪式表达。至于丧祭之礼中明显涉及宗教的部分,儒者们都有意识地加以新解释,为宗教性的仪式赋予人文性的意义,即视其为情感之表达。如复礼、含礼、 “三日而敛” 之礼、明器之礼、飨祭之礼、 “忌日不用” 之礼,以及通过斋戒可与神明交、可与逝者见等,都具有明显的宗教意涵,但儒者们都对此进行了转化,赋予其基于人情的新阐释。
再如祭祀以求福,本是当时社会心理之常态,如《郊特牲》云: “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 ,郑玄注: “祈犹求也,谓祈福祥,求永贞也。报,谓若获禾报社。由,用也。辟读为弭,谓弭灾兵,远罪疾也。” 求福、免灾乃一体之两面,都是宗教式的祈祷,但儒者们却说 “祭祀不祈” ,《祭统》云:
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
这里特别突出 “贤者之祭” ,甚至连 “福” 字都给予了新的解释,以与普通人基于宗教理由的祭祀区分开来,即荀子所谓 “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礼论篇》)。在当时充满宗教性的社会氛围里,要取消这些宗教仪式是不可能的,且于情感亦不忍,故儒者之目的,只是将 “鬼事” 化为 “人道” ,为其赋予新的基于人情的解释,亦即冯友兰所谓 “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云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页。。
四、圣王制礼以定分别
《内则》云: “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 《郊特牲》云: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皆谓礼起源于分别,特别是男女之别。而男女之别,又源自人禽之辨,《曲礼上》云: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圣王为使人 “知自别于禽兽” 而为之制礼,即以礼作为人禽之别的标准。《冠义》云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若无礼,则不可以为人。如此,则通过辨析人禽之别,把礼界定成了人之本性,为其赋予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乐记》云: “礼者,天地之序也” , “序,故群物皆别” ,又云 “礼辨异” ,可见 “定分别” 是礼的核心精神所在。关于礼源自 “定分别” 之需要的论述,大小戴《礼记》讨论最详者,莫过于基于政治等级秩序的上下、尊卑、亲疏、贵贱之别。如《中庸》云: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哀公问》云: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
当然,这套等级秩序,是基于政治目的而被人为塑造出来的。《少闲》云 “唯不同等,民以知极” ,又《盛德》云 “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 。唯有制造不平等,划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形成特权阶层,民众才会服从权威,才会 “知极” 以敬事长上。天子便因从民众以至诸侯之层层 “尊上” 而维持其统治。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 ,无论是礼之常,还是礼之变,其核心精神,都是 “章民之别” ,呈显一种上下、尊卑、亲疏、贵贱的等级差别。
这种等级区分,是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衣服、饮食、宫室、车马等等,都有从天子以至庶人的一整套礼制规范,不可躐等;至于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九礼,不同等级亦有不同之礼制。《坊记》云: “贵贱有等,衣服有别” , “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礼三本》云: “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 分别之目的,在于 “别尊卑” ,使 “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
从这个角度来看, “礼” 给各个等级中的人都贴了一个标签,并让他们按照标签上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进而愈加巩固这套等级秩序。《射义》中的一段论述,便很形象地传达了这种意涵:
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
“鹄” 即是一种标签, “各射己之鹄” 即每个人按照自己身份标签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安守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 “莫敢相踰越” ,便可从这套等级制度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即《礼运》所言: “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
从这种思路来探讨等级之礼的起源,进而论证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便使礼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强制性与压迫性,个体的人在这个等级制度里没有价值,也没有主体性,永远处在服从、顺承的被治地位。君长教民 “行礼” ,即教民服从、顺承、恭敬自己,其方法亦以利诱、威逼为主,即 “悬贵爵重赏于其前,悬明刑大辱于其后” (《荀子·议兵篇》),如此一转即成法家。
五、圣王制礼以报恩
上文说丧祭之礼起源于 “人情之实” ,但并非所有的祭祀之礼,都起源于人情,其中亦有远于人情者。《礼器》云:
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是故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郑玄注: “近人情者亵,而远之者敬。” )
人是吃熟食的,故郊祭、大飨之礼以血、腥为祭,乃不近人情者。圣王制此郊祭、大飨之礼时,必非 “作而致其情” ,而是另 “有由始” ,亦即 “报本反始” 。丧葬之礼主哀,故与情近;报天之礼主敬,故离情远。《礼器》云: “礼也者,反其所自生” ,又云: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乐记》亦云礼 “反其所自始” , “报情、反始也” 。此皆言制礼以 “报本反始” 之意,即受恩思报,不忘所自也。
《祭法》云: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于民众有恩,则制祭祀之礼以报之。又《礼三本》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施恩者有天地,故制郊祭之礼以报之;有先祖,故制家祭之礼以报之;有君师,故制忠敬之礼以报之。这样一来,君长便和天地、父母处在了同一被报答者的位置。更进一步,则直接视君长为天,为 “民之父母” ,即通过同构性的比拟,把君长对民众的恩情视为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君长基于其君长的身份,便对民众有恩,因此民众需要礼敬君长以报恩,而不论其实际作为。 “礼三本” 的表述又见于《荀子·礼论篇》,当是战国末年 “尊君” 思潮下的产物。其 “宠君师” 的倾向,与孟子高扬君民关系之对等义,明显不同。
恩之重莫过于天,故祭之重莫过于祭天,《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虽然人人都受天之恩情,但并非人人都有祭天之权利。祭天之权是被天子垄断的,诸侯都不得僭越,普通人更不得问津。此外,天子祭天,还会以先祖配之。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人要报天,必须先报天子,通过天子方能报天,天子垄断了与天地沟通的神圣性;天子以先祖配天而同祀,意味着天子之先祖具有仅次于天的地位与神圣性,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之授予。故通过一年一度的 “报天” 郊祭之礼,现实世界中的天子,不断强化其源自于天的神圣性、主宰性以及 “君权天授” 的合法性,同时也暗示着自己像天一样恩惠万民,万民要像自己 “报天” 一样用 “报礼” 来感恩自己。
这种从 “施—报” 关系来理解礼之起源的思路,具有明显的政治等级意味:在上位者永远是 “施恩” 者,在下位者永远是 “受恩” 者,故需以忠敬之礼 “报” 之。在上位者之恩泽如雨露一般,层层下注;在下位者之礼敬如云气一般,层层上升。施恩之最大者莫过于天,但报天之礼已被天子垄断,所以落实到具体的 “施—报” 关系中,报恩之最重者便是报答天子,甚至连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 “天功” ,亦被视为天子 “顺天治民” 的政绩,需要下民感恩戴德,以礼报之。先秦典籍中常见把天子、君长视为 “民之父母” 的说法,将这种说法放到层层 “施—报” 的思维模式中来理解,便不难把握其中的等级关系与政治意涵。
在下位者对在上位者的 “报” ,主要表现为 “敬事长上” 。对天子而言, “敬事长上” 即敬事上天。《祭义》云天子亲耕,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统》云: “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言天子亲耕,以其所出祭祀天地,以表诚 “敬” 之心,此天子之 “事” 也。
天子 “敬事” 上天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天子以亲耕所出事上帝,是理之当然,非但不能有怨言,还要有恭敬之心;同理,众庶以劳力所出事君长,亦是理之当然,非但不能有怨言,还要有恭敬之心。《表记》云:
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
这里的 “义” ,指下事上、卑事尊、贱事贵之礼。贵贱皆有 “事” 于天下,但每个人的 “事” 是不同的,天子是 “事上帝” ,诸侯是 “辅事于天子” ,众庶则是事于长上。《乐记》云: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 ,故天子事上帝需 “敬” ,诸侯事天子需 “敬” ,众庶事长上亦需 “敬” 。
问题的关键便在这里:在从天子以至庶人都要 “敬事” 其上(天子事天,亦是以下事上)的逻辑里,其中的差别便被忽略或掩盖了。众庶事士,士事大夫,大夫事诸侯,诸侯事天子,其所事之对象,都是明确的,且有实际的权力支配关系,其不事之后果,亦是明确的。《虞戴德》云: “有臣不事君,必刃” ,是具体政治层面的 “事” ;但天子郊祭以事天,却无明确之实体,亦无实际之权力支配关系,只是抽象宗教层面的 “事” 。从庶人以至诸侯之 “敬” ,亦是具体政治等级中的恭顺、服从关系,而天子之 “敬” ,只是自尽其心而已。传礼儒者将两者 “混为一谈” ,其目的即在从后者推导出前者,用天子 “敬事” 上帝之虚礼,谋求从庶人以至诸侯均 “敬事” 长上之实际政治顺从,亦即以宗教祭祀层面之 “敬事” 谋求政治层面之恭顺与服从。
《表记》云: “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斋戒以事鬼神” 是洁诚之 “敬” ,其目的是使民 “敬” 其长上。又云: “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 第一个 “敬” 是洁诚之 “敬” ,第二个 “敬” 则是恭顺、服从之 “敬” 。传礼儒者们作此论述,绝不是逻辑混乱下的 “混为一谈” ,此中必有深意焉。其深层次的意图,即在以祭祀明教化,《祭统》云: “祭者,教之本也已” 。当然, “教化” 之内容,便是教民众顺从有明确上下、尊卑、贵贱之分的政治等级秩序,且这种恭敬与服从,不仅要做到外在的礼仪,更要从内心里产生认同,就像祭祀一样,要有洁诚之 “敬” 。这就利用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心理,把区分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等级之礼深深地嵌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了。
余论
对自己生活其间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规范、风俗习惯、道德文化源自何处的探索,是人类的基本 “心智” 之一。但是,人们对这些 “起源” 问题的探索,往往不是纯粹 “知识” 意义上的,还与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关切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们探索过去,其主要目的往往不是求 “历史之真” ,而是通过追溯起源,建构历史,进而为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关切提供辩护的依据,追溯历史只是证明自身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的氛围下,大小戴《礼记》为了证明 “礼”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尤其倾向于追溯 “礼之起源” ,共形成了五种关于礼的起源论述:礼起源于圣王制作,圣王效法天地以制礼,圣王因人情以制礼,圣王制礼以定分别,圣王制礼以报恩。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建构了儒家关于礼的起源学说,为礼之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礼起源于圣王制作” 是儒家共享的命题,但其中也有差别。在战国以前, “圣王制礼” 仅意味着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史事;但到了《大戴礼记》中,则 “层累地造成” 了一个远古圣王制礼作乐的清晰谱系。
“圣王效法天地以制礼” 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孔子之前,即《左传》《国语》中子产、晏婴等人为礼赋予 “宇宙义” ,将人间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的政治等级之礼视为 “天经地义” 之事。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传《易》儒者们通过对《周易》本经的全新解释,建立了从 “天道” 到 “人道” 的一一对应关系,体系完备而具体。这样一来,人间的等级秩序(礼),便和人间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圣王效法天地的作品。但《易传》中的 “礼” ,还处于 “模仿” “效法” 天地的被动地位,需要时时援引自然秩序来证明自身。大小戴《礼记》一方面吸收了《易传》的成果,将 “礼” 视为圣王效法天地自然秩序而作。另一方面又往前更推进了两步:将礼视为 “天地之序” ,即自然秩序本身;进而将礼视为 “理” 本身,使人间秩序获得与自然秩序同等的地位。这样一来, “礼” 的地位就被拔得更高了,并且不再需要援引自然秩序来证明自己,因为它本身已成为更具永恒性、真理性的 “理” 的一部分,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了。
“圣王因人情以制礼” 的论述方式,可以追溯到孔子和孟子。大小戴《礼记》则在此 “人情义” “本心义”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对丧、葬、祭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去宗教化的解释,为其赋予纯粹情感化的意义。这便使儒家的丧、葬、祭礼成为极具诗性美学与情感意涵的仪式过程,温情脉脉而韵味无穷。
“圣王制礼以定分别” 的说法具有悠久的传统,大小戴《礼记》讨论最详的,是基于政治等级秩序的上下、尊卑、亲疏、贵贱之别。《少闲》云: “唯不同等,民以知极” ,唯有制造不平等,划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形成特权阶层,民众才会服从权威,才会 “知极” 以敬事长上,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这和荀子的思路是一致的。
“圣王制礼以报恩” ,即从 “施—报” 关系来探讨礼之起源,是大小戴《礼记》的特殊讲法。圣王制郊祭之礼以报天,制家祭之礼以报父母,制忠敬之礼以报君长。这样一来,君长便和天地、父母处在了同一被报答者的位置。更进一步,则直接视君长为天,为 “民之父母” ,即通过同构性的比拟,把君长对民众的恩情视为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君长基于其君长的身份,便对民众有恩,因此民众需要以礼报之,而不论其实际作为。此外,天子还会通过 “远于人情” 的祭天之礼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地位,强化 “敬” 的意涵,强化层层 “上报” 的等级之礼。特别是为 “敬事” 赋予双重义,通过天子 “敬事” 上天之虚礼,谋求从庶人以至诸侯均 “敬事” 长上之实际政治顺从,即以宗教祭祀层面之 “敬事” 谋求实际政治层面之恭敬与服从。这便利用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心理,把区分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等级之礼深深地嵌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