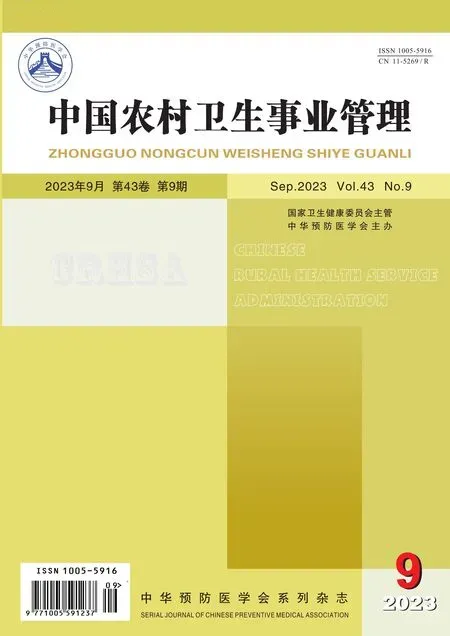职业病危机的病机寻绎与医学模式创新
孙宗岭,于敏
1.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2. 临沂市中医医院,山东 临沂 276000
2022年4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到:“全国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数从2012年的27 420例下降至2021年 15 407 例,降幅达43.8%”[1]。由此,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人民健康至上、健康优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2]。如何夯实现有的职业病防治成效,并对中国新兴职业病危机进行及时预防与应对,以健康中国建设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是中国疾病控制管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文章首先归纳国内学界在职业病危机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展望进一步发展方向;其次聚焦《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健康观,梳理马克思关于职业病危机的病机与诊疗的相关论述;最后基于马克思健康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炼现时代中国职业病危机的产生原因与应对方案,建构中国特色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化推进增添理论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疾病控制管理研究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贡献智慧方案。
1 职业病研究的新视角:《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健康观
近年来中国职业病问题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国内学界对职业病危机的产生原因与应对方案进行了多元研究。胡荣山从法律制度领域出发对职业病危机进行研究,认为:“制度和法规上的缺失与政策上的偏差”[3]是导致职业病危机的重要原因,必须将视野从具体的医疗卫生行业扩展到法律制度层面,职业病危机才能得到更好处置。赵卫华聚焦农民工职业病具体问题对职业病危机进行研究,指出:在中国劳动生产一线中的工人占据大多数的是农民工,在现有《职业病防治法》不断实施的背景下,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原因是现今的职业病防治“没有有效地把这些真正的工人包括在内”[4]。裴松认为企业不认真彻底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自我保护意志不强,我国职业病法律体系和监管能力不足等多重原因“导致劳动者健康危害问题日益突出,各种职业病的发生居高不下”[5],针对性处理上述问题,职业病危机便可以得到较好化解。楚安娜等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从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企业因素等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目前职业病的影响因素,认为:只有解决了环境、制度与企业等维度存在的多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的健康”[6]。任国友分析了工会在助力职业病危机化解问题上所具备的独特作用,指出:工会有两个主要方式参与职业病防治,例如“通过源头参与方式参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职业卫生立法和政策制度等……通过启动相关应急预案主动参与突发事件救援等”[7]。樊晶光等提出了九大方面的具体应对措施[8]。王业英从法律法规、管理模式、职能布局、人才队伍等多个角度探索了职业病危机的应对方式[9]。蔡敏指出:“消灭职业病从根本上应立足于预防”[10],具体要依靠政府、企业与职工三大主体共同发力。
国内研究形成了基于法律制度、政府监管、企业责任与劳动者个人意识等四重进路在内的观点结论,展示出国内学界对职业病危机问题研究的关注与成效,也正是在这四重进路的各自赋能中,中国职业病危机才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在看到国内职业病危机问题研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深度反思其中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维度与方向。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现时代中国“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11]。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先进机器技术的应用推动生产方式正在或已经发生时代性变革,在此背景下的中国职业病危机也发生着时代性演变,“表现为传统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带来的职业卫生问题逐渐减少,新的问题不断出现”[12]。由生产方式改变引发的职业病危机成为社会突出问题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详细考证与深刻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马克思健康观。在关于职业病危机的研究中,虽然杨善发等学者积极引领着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医学的交叉性研究,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职业病危机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与参考。但是,从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在关于职业病危机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健康观这一理论武器的自觉运用相对不足。因此,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健康观,重新发现马克思对职业病危机的病机寻绎与诊疗设计,以指导当下中国职业病危机的有效应对。
2 面向生产方式的病症:职业病危机问题的马克思诊疗
在马克思健康观视野中,职业病危机意指:由机械或自动机器的使用导致工人健康受到多元侵害的可能与现实。基于工人劳动时间与工人劳动强度两个维度,马克思深刻剖析了机器的使用-工人劳动时间-工人劳动强度-工人健康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对职业病危机的全面诊疗。
对工人劳动时间-工人健康危机之间关系的预先诠释,是马克思探讨工人健康危机的第一环节。马克思将工人劳动时间指称为工作日,并且深入分析了工作日-工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个体工人与工人阶级都希望自己的工作日能限定在“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13]之内,以便形成劳动过程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动态平衡。但是,个体资本家与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并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延长工作日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工作日不断延长的社会背景下,英国产生了周期性复发的流行病,甚至德法两国的青壮年身高都变得低于以往时代。马克思关注的医生-查理·帕森斯认为,在陶工患病的多种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13]。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到每天12小时以上则会损害工人健康,甚至使工人早衰、早死。资本家为了更多地占有剩余价值却努力宣扬“机器劳动是轻松的”[13],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13]的工人欲求。一旦工人们对延长了的工作日进行言语和行为上的个人与集体抗议,资本家们便简单粗暴地用解雇工人这一致命手段迫使工人接受工作日的延长。资本家认为工作日只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13]。资本家开始“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13]。因此,通过延长工作日,工人在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走向萎缩状态,工人本身势必走向一种未老先衰、先亡的生命方向。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才迅速且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13]。
马克思认为,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3],如果社会不对工作日进行主动的强制的限制,作为国家生命力的广大工人阶级将会遭到根本摧残。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英国首先制定了工厂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工人每日的最长劳动时间,寄希望于这一政策行为,减缓工人健康危机与工人的各种反抗活动。但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语境中,国家限制劳动时间-工作日的延长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形成一种冲突。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促使资本家们开始以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取满足自身的贪欲。这时机器的使用便成为资本家们可以选择的有力手段,然而机器的使用-工人健康危机之间同样有着系统性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对机器的使用-工人健康危机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是以工人劳动强度为支点的,机器的使用致使了工人劳动时间与工人劳动强度的双向增加,在工人劳动时间与工人劳动强度的双向作用下,形成了机器的使用加剧工人健康危机的现实效应。一方面,在工人劳动时间的向度上,机器的使用与工作日的延长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本家们将机器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是为了延长工人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日部分,从而机器成为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13]。在这一背景下经济领域的反常现象出现了:机器的使用原本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在现实中却成为了将工人生命时间转变为服务资本增殖时间的武器;机器的使用可以缩短工人劳动时间,但在资本家的手中却成为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法宝。这种反常现象催化着机器的使用-工人劳动时间-工人健康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生成与呈现。另一方面,在工人劳动强度的向度上,机器的使用与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一般而言,随着机器技术的进步与操纵机器的工人经验提高,“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13]。在工厂法得以制定并实施的背景下,资本家会刻意加快机器运转速度,扩大单位工人操作机器的数量,从而实现对缩短了的工人劳动时间的补偿,资本家将促使工人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13]。但是面对这样一种工人劳动强化的生产的现实状态,马克思借用工厂视察员的论断:虽然工厂视察员肯定了工厂法对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意义,但是“已使劳动的强度达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地步”[13]。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与传统手工或工具劳动相比,机器劳动会极度损害工人的神经系统,并且“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13]。不仅如此,机器劳动所依赖的机器工厂本身的温度、空气与噪音同样对工人的各种感觉具有摧残作用。虽然,从理论内容上马克思对机器的使用-工人劳动时间-工人劳动强度-工人健康危机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了系统性探索,建构起了职业病危机的多维理解框架。但是,马克思始终秉持着独特的方法论,即面向社会的病症思考职业病危机问题。一方面,从现象上看,职业病危机是由机器的使用造成的工人多元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职业病危机有着特殊的社会情景,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正是由于社会病症的存在,劳动生产过程才病态化演变进而产生了难以解决的职业病问题。江宇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的健康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以资本为中心、以 GDP 为中心、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方式”[14]。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无限制的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具体的劳动生产才成为一种引起职业病危机的触发点与导火线。而真正实现对职业病危机的诊疗,必须消除职业病危机得以不断生发的社会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研究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加深入地挖掘马克思主义,寻找其与各学科之间的契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学科的交融”[15]。面对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职业病危机,马克思对职业病危机的病机寻绎与诊疗设计成为新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对职业病危机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医学模式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实践效能。实现对当下中国所秉持的医学模式的充分认知与了解,全面掌握其优点与可以优化之处,并基于马克思健康观予以创新发展,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
3 聚焦生产方式的诊疗: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创新
自现代医学诞生以来,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这一模式是当代医学哲学的经典命题。乔治·恩格尔(George L.Engel,1913—1999)在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模式: 对生物医学的挑战》(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 一文,提出医学模式应该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标志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诞生。从医学模式视角看,国内学界对职业病危机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政府、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还是从法律法规、制度设计与执行管理三维之内对职业病的产生原因与应对方案的探索,都体现出一种明确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医学观,正如刘月树所言:“医学模式将人们规约在某个稳定的框架中来理解和治疗疾病”[16],医学模式可以具象化为分析疾病的产生原因与诊疗方案所依托的宏观进路。恩格尔认为新的医学模式应该超越旧有的生物医学模式的顽疾,在对疾病的诊疗中要运用整体的综合的方式,特别关注心理、社会方面。认为对疾病的观察与诊疗应该从宏观的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考量。美中不足的是,恩格尔并没有详细地阐释出社会这一维度所应该囊括的具体向度,虽然威廉·坎贝尔( William H. Camp-bell,1955-)[17]与罗纳德·爱泼斯坦( Ronald M.Ep-stein,1955-)[18]等学者在社会这一维度进行了精细化的补充,但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临床实践中依旧乏力,必须寻找资源推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实现新发展。
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哲学基础看,贝塔朗菲( L.Von.Bertalanffy,1901—1972)的系统论是重要理论资源。得益于系统论的助力,恩格尔最终推动了理论层面的医学模式转型。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本身源自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库萨的对立协合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19]。同时“医学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发展,无不与在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对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20]。杨善发认为“马克思的健康观是超越生物医学的社会健康观,是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民健康生命损害的革命健康观”[21],马克思“全面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健康的伤害”[22]。马克思提出的基于生产方式审查职业病危机的思想观点可以成为现时代中国职业病危机的病机寻绎与诊疗设计的理论资源,也可以成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聚焦生产方式的诊疗,现时代中国职业病危机的病机寻绎与诊疗设计可以进行如下阐释与建构:第一,在病机层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走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崭新形式,资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虽然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并不占据主流,但是资本逻辑的弊端依旧在中国社会中显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职业病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形势愈加恶化,导致未在公有制体制内的劳动者深受职业病侵害。对未在公有制体制内的劳动者来说:8小时工作制逐渐被“三八制”“12小时制”“24小时制”乃至“996”“007”等多样式的工作制所替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明显延长,劳动强度显著增加;无法享有法定节假日与休息日,无法享受各项福利待遇-高温补贴、带薪休假、健康体检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加剧了劳动者患上职业病的风险。第二,在诊疗层面,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从而化解资本无序扩张产生的劳动者职业病危机。例如,“在人人各尽其能的‘共建’和个个各得其所的‘共享’中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23]。推进未在公有制体制内的劳动者能够真正地成为公有制体制内的劳动者,从而能够享受到与现在公有制体制内的劳动者相同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与助益,才能化解职业病危机不断生发的社会风险困境。
另一方面,聚焦生产方式的诊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未来发展可以进行如下规划与展望:将生物-心理-社会的逻辑排序调整为生物-社会-心理。作为疾病与健康直接载体的人,本身便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24]。其中自然属性可以归结为生物属性,精神属性可以归结为心理属性,社会属性是链接生物属性与心理属性的纽带与桥梁。需要将社会属性提升至生产方式的理论高度,而不仅限于将社会属性理解为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理解一个社会归根结底是理解一个社会的主流的生产方式,医疗卫生政策模式的选择“本质是对不同类型社会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25]。那么,不仅是在分析职业病危机问题的时候可以运用彰显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在分析其他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一医学模式也能够从根本上作为有效指导。例如,作为现时代多发且日益普及的脊柱疾病问题,众多研究都指出是由于身体长时间固定在同一地方,精神高度紧张与集中,过度加班与不科学的生活方式所致。试问上述原因的根本解释为何?只有归结为强调无限竞争、无限“内卷”,充满巨大压力、多元催力的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资本发展模式。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根本解决,首要的不是医治“生物”的人,也是不医治“心理”的人,而是聚焦于医治“社会”的人,也就是人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病态的生产方式得到诊疗,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才能得到诊疗。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