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我照亮了一个人(组诗)
许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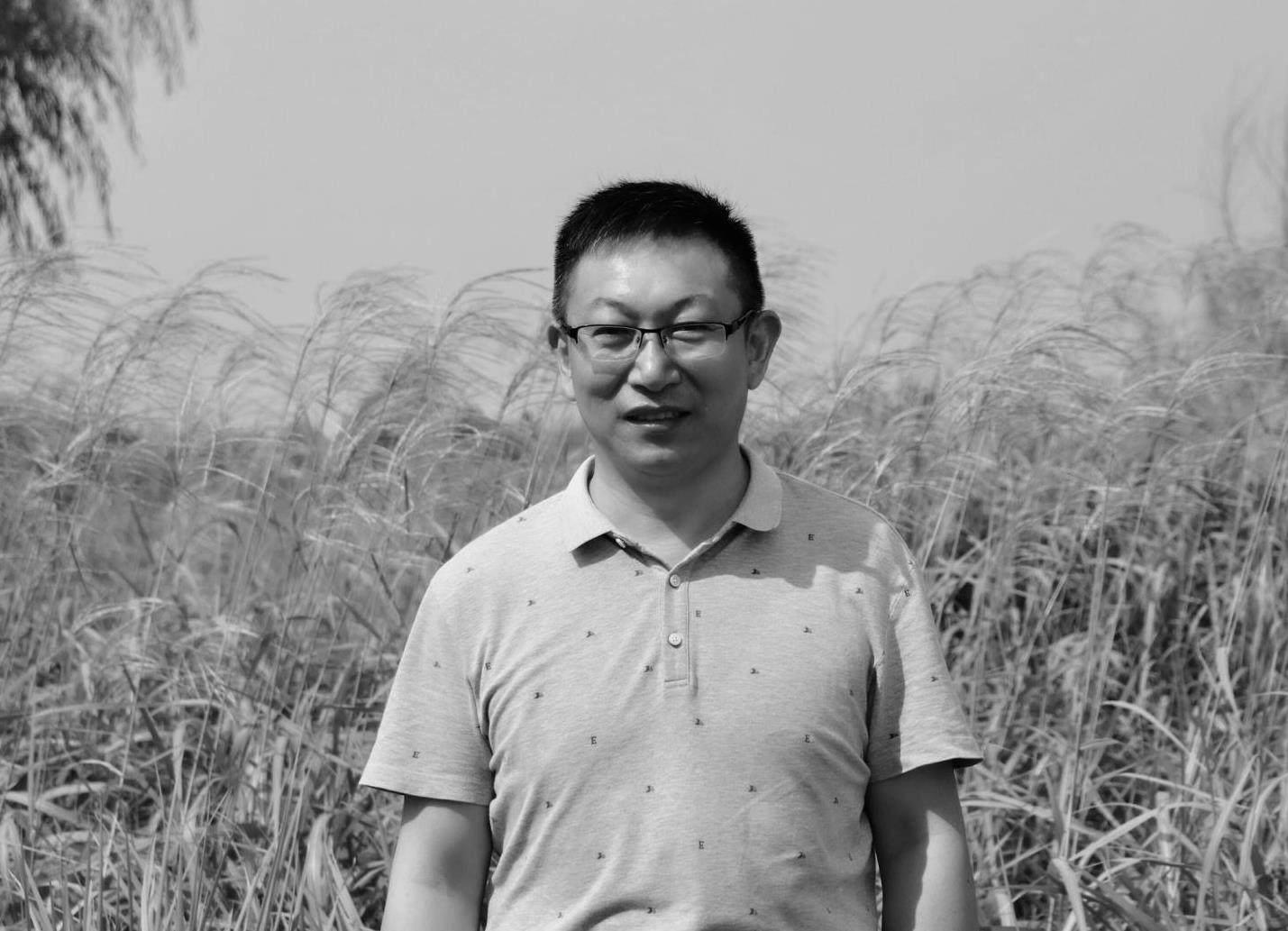
男,安徽宿松人,居合肥、泉州两地。媒体广告人,主编民刊《翼象》《安徽诗歌》,著有诗集《玻璃那边的风》《间隙》。
我宁愿落叶是一枚尖锐的铁蒺藜
我宁愿它们都是从树上摔下来的
我宁愿它们叮叮当当,伤痕累累
我宁愿它们能在林荫道上
认真拦住我们的路
我宁愿你踩上去时
能把一半的尖叫声分给它们
我宁愿它们离开故园时
都能大哭一场
雷声让我想到哑巴店
秋天的雷声向原野发出问候
闪电把枝头上的留恋照白了
窗外骤雨如箭,尘埃和眺望纷纷坠落
谁能知晓忽明忽暗的哑巴店
在一个守林人荒凉的酒盅里
有时是疼痛的树,有时是愤怒的草
有时是哐当哐当挖掘不尽的羇途
两个杮子携手坠落
坚强也有累的时候
譬如荷。譬如在虫鸣抵达高潮之后
两个杮子携手坠落
它们放弃了硬的部分
寒露來临之前,月光被黑吃掉了
整栋整栋的灯火也在骤然熄灭
限电之后,湖水变回它本来的颜色
夜晚在衰变,只剩下潮湿的雷声
还在问候那些不肯说话的人
哑巴店的镰刀已经开始生锈了
我担心没有镰刀的哑巴,他的笑容
将随亢奋的梦境一起坍塌
在五谷庙
没有哪一串成熟的稻子不是表达谦逊的
它们在庙宇四周,犹如我的父老乡亲
今夜星星无数,我只铭记了流亡的那颗
四十多年的愧疚,究竟能够滑向何方?
无须辨识谁的车辆停驻庙前,三分钟的静默
灯光吸引了一群又一群带有稻香的喜庆飞虫
我承认我是一棵曾经长坏了的稗子
我承认我是一棵立于稻林被众神宽恕了的
轻飘飘的稗子。我的母亲曾经跪在蒲团上
一次又一次地等着西边的金光照进庙堂
稗子
父亲曾教我怎样决绝地拔掉它们
齐腰深的稻禾缠住我,每移动一步
都会留下一些悲壮的花絮
陷入似乎没有边际。伪装无时不在
识破一棵稗子与识破一个人的感受迥异
我暗自钦佩对手扎下的庞大根系
蚂蚱从一片叶子跳到另一片叶子
欢快似与我们无关。父亲把稗子抛到岸上
落地的泥浆炸飞了一些憎恨和疲累
多年以后,我仍记得父亲的手势
我希望自己不是被他拔漏掉的那棵稗子
我还能保持一股淡淡的稻香味
但愿人长久
月亮不只看我,也看千里之外的女子
高山上的月亮照亮高山,流水中的月亮
追逐流水。我倚立窗前,想偷听火车的声音
可是风太轻了,难以载动远方的消息
饮过几杯桂花酒,月亮便在心头晃了起来
她晃啊晃啊,又晃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我痴痴地盯着她,像盯一件久违的瓷器
我确信我照亮了一个人
把心事打上一个蝴蝶结,让它飞,让它消失
但心事又会回来,又会沾上潮湿
沾上苦难,沾上孤独
今晚的月亮很圆,她照亮了那些潮湿
那些苦难,那些孤独。她照亮了我
照亮了那些平常难以深入的迷途
现在我很亮堂。我确信我也照亮了一个人
你们嫉妒我吧,因为我还能照亮泪痕
照亮疾病,照亮那些悬浮人世的虚空繁华
不相信
不相信哑巴店的云彩是被挖掘机
反复挖掘过的。不相信那些鱼儿
会在暴雨天私奔。不相信模糊的
泪眼其实是清澈的。不相信闪电
反复撕裂的天空仍然呈现蔚蓝色
不相信刺猬会跑到农庄门口哭诉
不相信小黄狗还会蹿回我的怀里
不相信大平塘有朝一日就不是塘
不相信在栾树林里发誓的人愈来
愈少。不相信南瓜会像企图一样
烂在地里。不相信梦想跟红灯笼
似的正逐渐褪色。不相信一个人
不打招呼就直挺挺躲到鲜花丛中
间隙之二
祷告声随乌石天后宫黑面妈祖屋顶滑落下来
下午柔和的日光,正适合祈愿反复萌芽
而此刻,后山的紫薇花已开始谢幕了
花瓣如浮尘,又如前山的朦胧暮色
偶尔打动我一路向北的豪华梦境
一切都在路上。每一口气都无法完整地
穿过鼓志山隧道。哪怕你有意憋着
像憋住委屈气愤幸福心酸甜蜜或自豪
但另一口气,肯定在后面推搡
它们如排队等候的敬香者
心神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