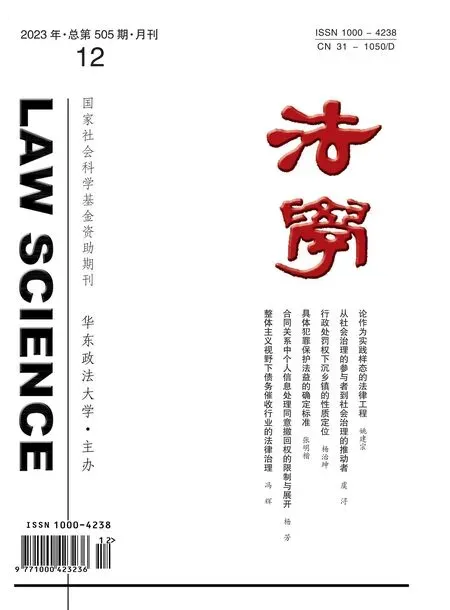涉外法治视域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
●黄志慧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法院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其所采取的管辖依据(jurisdictional basis)。〔1〕参见黄进主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2 页。需说明的是,在国际法上,一国的管辖权通常包含立法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执行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enforce)。决定一国法院审理案件权能的司法管辖权是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问题。本文使用的“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概念是指一国司法机关审理具有涉外因素民事案件的权限,即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管辖权。是故,文中所指国际民事管辖权如无特别交代,不包括有关民事实体法适用范围的立法管辖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管辖依据的多元化及其跨国分布使得国际民事争议不再局限于受单一国家法院的管辖,加之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仅与当事人私法利益的保护密切相关,也关涉一国司法主权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故实践中不少国家纷纷采取扩张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场。〔2〕See Kevin M.Clermont and John R.B.Palmer, Exorbitant Jurisdiction, 58(2)Maine Law Review 474 (2006).本质上说 ,国际民事管辖权涉及司法管辖权在不同国家的地域分配,这意味着不能单纯以国内地域管辖权的概念予以逆推,而应重视国家与国际民事案件的联系,以更宏观、更切合个案需求以及更具弹性的角度建立国际民事管辖权之标准。〔3〕参见林恩玮:《国际管辖权理论的法典化省思:以比利时国际私法新法典为例》,载《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 年第4 期,第183 页。也因如此,近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争议中也以“适当联系”为据积极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4〕参见“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7 号民事裁定书;“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与夏普株式会社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管终517 号民事裁定书;“诺基亚公司等与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167 号民事裁定书。
伴随以开放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确立,我国正在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并积极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此背景下,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第276 条对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进行了扩张规定,根据该条第2 款的规定,对于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涉外民事纠纷与我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这意味着我国在立法层面引入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反映了立法者完善本国涉外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最新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51 条规定的“裁量管辖”也允许人民法院在案件情况与我国有适当联系且行使管辖权为合理时,对有关的诉讼行使管辖权。〔5〕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3-14 页。由此可见,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以“适当联系”为据扩张人民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已形成基本共识。
“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开启了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要求下我国适度扩张人民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新时代,必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首先,国家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当下提升涉外法治水平的重要因素。〔6〕参见吕江:《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4-6 页。“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灵活性和扩张性,可能招致“司法沙文主义”的批评。作为一种涉外法治话语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至少需要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检视。其次,在涉外法治工作的战略布局中,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至关重要。〔7〕参见刘仁山:《我国涉外法治研究的主要进展、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载《国际法学刊》2022 年第1 期,第39 页。“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与国内地域管辖权、国内法域外效力条款、国际民事诉讼“管辖落空”等问题均存在密切关系,故需审视其在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的体系效应。最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不仅是当前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8〕参见涂卫:《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载《学习时报》2022 年2 月16 日,第A3 版。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角度考量,无疑应厘清“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适用的扩张与限缩问题。
基于此,本文先论证作为一种涉外法治话语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正当性,再揭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体系效应,最后阐释涉外执法司法效能要求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范适用。
二、涉外法治话语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正当性检视
(一)作为涉外法治话语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
国际法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也是一套话语体系。〔9〕参见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6 期,第35 页。我国提出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既不同于美国依据最低联系标准确立的对人管辖权,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保护诉诸司法权的必要管辖权。可以说,其是我国以司法实践为基础创建并表达中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但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为一种涉外法治话语,能否避免产生“过度管辖”的误解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话语即权力”。一般认为,当前我国并不缺乏在国际社会表达观点的“话语权利”及其实现的合法途径,而亟待加强的是“话语权力”。〔10〕参见张志洲:《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几大基础性理论问题》,载《学习时报》2017 年2 月27 日,第2 版。强化我国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话语权,不仅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有力武器,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从逻辑上说,没有较高水平的涉外法治话语,不仅难以充分呈现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也不可能赢得较大的话语权。涉外法治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在国际社会的被接受度和影响力。当然,涉外法治话语的中国主体性并非要求否定国际法话语的统一性,而是不能当然认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话语的绝对性。应该说,“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涉外法治话语,既不能过度强调国际法规范的国际化而忽视本国利益诉求,也不能单方面凸显本国利益诉求的主张而导致曲高和寡。
客观而言,“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在国际社会中的被接受度无法由我国单方面施加决定性影响,即“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被接受的普遍性程度无法脱离国际社会成员的理解与认同。从法律层面说,提升“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在国际社会的认同感,至少需要存在不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正当性予以加持。实际上,国际法除了其裁判功能外,还具有评判一国行为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的功能,〔11〕参见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6 期,第35 页。这就要求“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应兼顾国际法的基本要求,促进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同我国创建和适用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并形成关于国际民事管辖权实践的共识。鉴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及国际民事诉讼法的角度,审视作为一种涉外法治话语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正当性。
(二)基于国际法的检视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2 款规定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可以适用于该条第1 款涵盖范围之外的涉外民事纠纷。而且,以“适当联系”作为管辖依据赋予了人民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当程度上扩张了我国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尽管一国行使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具有天然的域外性,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张性仍可能引发其是否违反国际法的疑虑。
对于国际法与国际私法上管辖权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各国尚存分歧,但是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项具体权能,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必然受到国际法的约束。〔12〕参见杜涛:《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过度管辖权》,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1 期,第19 页。理论上,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对于国内管辖事项,一国有权以其愿意的任何方式、为任何目的制定自己的管辖权规则。〔13〕参见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国际法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8 页。一般而言,国际法对于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限制主要聚焦于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关系,并未充分考虑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主要源于传统国际法在管辖权问题上不考虑私人行为者及其利益,多关注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及其监管权力。〔14〕See Alex Mills, Private Interests and Private Law 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Jurisdiction, in Stephen Allen, Daniel Costelloe, Malgosia Fitzmaurice, Pau Grag and Edward Guntrip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31, 336.因此,国际法对一国管辖权行使的限制主要体现为不干涉他国主权。然而,一国管辖权的行使在何种程度上干涉他国主权并无明确的标准,无法为相关国际行为和交易提供充分的法律确定性。〔15〕See Cedric Ryngaert,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56.国际法院在“诺特波姆案”中提出的“真实联系”(genuine connection)的要求,被认为可能在限制一国管辖权行使方面发挥作用,〔16〕See Nottebohn Case (Liechtenstein v.Guatemala), I.C.J.1955, I.C.J., 4 (1955).“真实联系”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国际法对一国域外管辖施加的主要限制之一。〔17〕See Notably B.Grossfeld and C.P.Rogers, A Shared Values Approach to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2(4)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ly 931, 945 (1983).但是,实践中无法避免同一案件的事实、相关行为或当事人可能与多个国家同时存在“真实联系”的情形。尽管国际法上“真实联系”的要求可能会剔除某些过度管辖权的行使,但无法为一国管辖权的限制提供实质性指引,也无力杜绝各国间的司法管辖权冲突。〔18〕See Cedric Ryngaert,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56-157.
与传统国际法不同的是,现代国际法被认为不仅适用于主权国家,也可以用于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国家主权意味着国家应承担保护其公民的首要责任。例如,如果侵害行为发生地国家不行使管辖权,其他国家可以基于保护自身利益乃至国际社会利益进行域外管辖。然而,国家承担的保护责任或义务并不被视为一项国际法规则,而被认为是追求国际法地位的道德概念。〔19〕Ibid., p.161-162.而且,国际法上广为接受的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皆不禁止一国法院进行域外管辖。〔20〕参见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国际法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8-9 页。
此外,在国际人权法上,一国承担的保障当事人诉诸司法权(right to access to justice)之义务,不仅为诸多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所承认,〔21〕主要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7 条和第8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 条、《美洲人权公约》第8 条、《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公约》第9 条、《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第1 款。亦构成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22〕See Stephanie Redfield, Searching for Justice: The Use of Forum Necessitatis, 45(3)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93, 903 (2014).可以说,避免拒绝诉诸司法已成为当今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为了保障当事人享有的诉诸司法权,一些国家通过设立必要管辖权(forum necessitatis)或通过扩张解释国内法规则的方式适用必要管辖权。〔23〕See Chilenye Nwapi, A Necessary Look at Necessity Jurisdiction, 47(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 211, 271(2014).尽管各国均承认有效保护当事人诉诸司法权的重要性,但一国是否存在国际法上的义务,即是否必须通过扩张司法管辖权的方式达成此目的,并无定论。特别是,很难说主权国家在国际民事管辖权中确立的哪种管辖依据可被视为其履行国际法上保护诉诸司法权的义务。〔24〕See Alex Mills, Private Interests and Private Law 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Jurisdiction, in Stephen Allen, Daniel Costelloe, Malgosia Fitzmaurice, Pau Grag and Edward Guntrip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41.显然,在国际人权法上同样难以找到限制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明确依据。相反,其在特定情形下支持主权国家基于保护当事人诉诸司法权的需要而进行域外管辖。
正如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法官在国际法院审理的“比利时诉西班牙案”中撰写的独立意见所指出的,国际法确实未对主权国家划定其管辖范围施加硬性要求,但各国均有义务在涉及外国因素的案件中对本国法院的管辖范围保持适度的克制,并避免不当侵犯更合适的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25〕See ICJ,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 Ltd (Belgium v.Spain), ICJ Rep.3, 105 (1970).除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规则外,国际法并未对一国管辖权的设立及其行使设置禁止性要求。〔26〕See Louwrens R.Kiestra, The Impact of the ECHR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 Analysis of Strasbourg and Selected National Case Law, Springer, 2014, p.90-91.相反,习惯国际法允许一国依据“实际联系原则”(actual connection principle)对相关争议行使管辖权。〔27〕参见[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30 页。总体来看,各国较少直接批评他国在国际民事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依据,特别是相关外国法院可以在判决承认与执行环节审查原审法院管辖权的情形下。〔28〕See Alex Mills, Private Interests and Private Law 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Jurisdiction, in Stephen Allen, Daniel Costelloe, Malgosia Fitzmaurice, Pau Grag and Edward Guntrip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46.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主权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限制,除了前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规则外,国际法尚未确立明确的成文法规则,亦无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存在。受诉法院对某一国际民事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主要由各国国内法加以规整。〔29〕参见蔡华凯:《国际裁判管辖总论之研究——以财产关系诉讼为中心》,载《中正法学集刊》2004 年第17 期,第3-4 页。
上述分析表明,国际法并未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设定明确的禁止性规则。作为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涉外法治话语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会与当前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话语相悖。
(三)基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检视
20 世纪中叶以后,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的基础上,与“联系论”或“权力论”相比,有关管辖权的行使日益强调方便、公平与正义。〔30〕参见[美]阿瑟•冯迈伦:《国际私法的司法管辖权之比较研究》,李晶译,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6 页。典型例证是,美国法院在20 世纪40 年代抛弃了传统的“权力论”,转而采取了“联系论”作为对人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借助《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要求限缩对人管辖权的行使。晚近以来,作为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公平正义论”甚至被认为逐步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31〕参见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44 页。从逻辑上看,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上,强调案件事实及当事人与受案法院的联系,不仅是便于法院推进诉讼程序和开展诉讼活动的现实需要,也是协调与他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及保护被告正当预期的客观要求。毕竟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除了适当顾及不同国家之间管辖权的跨国分配关系,还不可避免地要考量当事人与法院以及两造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管辖权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国家愈加强调“公平正义论”,淡化“权力论”的影响,但只要国际社会仍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国际民事管辖权便不可能完全割断与国家主权的关联,〔32〕参见章晶:《海牙判决项目管辖协调之困境与前景》,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17 年第20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5 页。也无法阻断国家主权对其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仅与方便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直接相关,而且涉及本国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的权限划分,是充分实现国家司法主权的重要途径。也因如此,各国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上往往会适当扩张本国的管辖权,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33〕参见袁发强:《确立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考量因素》,载《法学》2006 年第12 期,第115-118 页。诚如学者所言,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大小决定着一国法院的管辖范围和能力,也直接影响着一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背景下利益的保护。经济外向型的国家会尽量扩张本国的管辖权,〔34〕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第124 页。这也正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为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采纳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在我国无住所的被告,“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可能会加剧与他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担忧,并无充分的依据。一是所谓“过度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不是以其是否会引起管辖权冲突为判断依据,而是以是否便利当事人诉讼,以及是否有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为衡量标准。〔35〕参见袁发强:《确立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考量因素》,载《法学》2006 年第12 期,第121 页。在无条约义务的情形下,一国通常不会将避免与他国产生管辖权冲突作为本国设定管辖依据的优先性政策加以考量。只要能有助于法院推进诉讼程序,并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么我国法院以“适当联系”为依据对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的被告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便有其正当性。二是相较于避免国家间司法管辖权冲突的利益,一国在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上更为重视对本国民商事利益的保护。国际民事管辖权与国家对外经济交往增强、国家法律和对外政策实现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扩张管辖权的动因在于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驱动,体现在国家欲通过对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实现国家参与管理国际民商事活动的目的。随着贸易、投资及人口跨境流动的激增,作为经济大国,我国需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也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自身利益。〔36〕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第146 页。“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是扩张国家主权、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体现,其在法律政策上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国与他国协调管辖权的国际民事合作利益。三是在民族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各国间民事管辖权冲突客观存在且难以彻底消除。在全球化时代及互联网技术广泛运用的背景下,跨国民商事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民商事争议与不特定多个国家的联系日益多元和复杂,导致了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越发频繁。在尚无协调管辖权冲突之全球性多边机制的客观现实下,除非主权国家单方自愿放弃其管辖权,否则仍无力根除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在比较法上,从争议与国内法院联系之角度看,无论是美国“国际鞋业公司案”确立的“最低联系”标准,〔37〕See International Shoe Co.v.Washington, 326 US 310 (1945).还是欧盟在《布鲁塞尔条例Ⅰ》序言中指出的法院和诉讼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据此建立其他可替代的管辖依据,〔38〕参见2012 年《布鲁塞尔条例I》(重订)序言第16 条。都可以构成一国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基础。这种做法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确定性目标的实现,避免了被告在一个其不能合理预见的国内法院被起诉。正如学者指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从来就不是确立涉外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而仅是法律选择的方法之一。各国在确立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时,往往要求案件与本国存在适当的联系。如果案件争议本身同法院地国存在一定的利益联系或政策导向因素,那么法院地国也可能行使司法管辖权。〔39〕参见袁发强:《确立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考量因素》,载《法学》2006 年第12 期,第116-117 页。而且,在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下,对于涉外民事争议与人民法院存在“适当联系”的理解,除了考虑事实因素外,还应包含案件与我国存在包括法律利益在内的利益联系。理由如下:一是仅依赖于事实因素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据宪法等国内法享有的程序利益,亦无法有效回应现代国际法提升基本权利保护的客观要求,故需扩张解释“适当联系”标准,以达成保护本国当事人诉诸司法利益的目的;二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国际反垄断、国际证券、反外国干涉和制裁等领域扩张解释“适当联系”标准,符合提升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竞争性、发展本国法律规范和实现本国法域外效力的制度利益;三是扩张解释“适当联系”标准是发展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的内在要求,蕴含了完善我国涉外法律规范体系的法律利益;四是在人民法院参与跨国司法治理的背景下扩张解释“适当联系”标准,有助于建立国内法与国际法联系与互动的途径,特别是借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司法实践,在输出中国法律价值观的同时,也为中国法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和适用奠定了基础。在上述意义上,“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足以作为主权国家自主选用的一种具有正当性的管辖依据。
前述分析证明,以涉外民事争议与受案法院联系为基础作为国际民事管辖权行使之依据,在国际民事诉讼法上被普遍接受。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2 款确立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并非迥异于各国实践,也不会产生无法克服的实践困境。作为一种涉外法治话语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同样具有充分正当性。
三、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体系效应
(一)替代国内民事管辖规则的类推适用
依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0 条的规定,只要该法涉外编对国际民事管辖权没有专门规定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援引该法第一编第二章规定的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确立国际民事争议的管辖权。这种做法也被学界认为,我国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上采取了“一元论”。〔40〕有学者认为,2021 年《民事诉讼法》涉外编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在本质上属于“一元论”体例框架下的补充性规定。参见向在胜:《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184 页。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除了涉外编专门规定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外,“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能否替代前述指引条款援引的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首先,以“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代替国内地域管辖规则,契合《民事诉讼法》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立法体例上采取 “二元论”的修法目的。从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上看,除了《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1 款规定的国际特别地域管辖规则外,该法还增加了国际协议管辖权(第277 条)、国际应诉管辖权(第278 条)、国际专属管辖权(第279 条)以及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制度(第280、281、282 条)。可以说,我国大体上构建了有别于国内民事管辖权的专门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体系,在立法体例上基本实现了由“一元论”向“二元论”的立场转变。对于2023 年《民事诉讼法》涉外编未涵盖的具体国际民事纠纷的管辖权,在逻辑上应优先援引第276 条第2 款规定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而无需再求助于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的类推适用功能。因此,支持“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替代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类推适用于国际民事争议的立场,符合《民事诉讼法》在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上确立的“二元论”立法体例之内涵。
其次,以“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代替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符合其作为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中“剩余管辖权”(residual jurisdiction)的性质。相较于2021 年《民事诉讼法》第272 条概括性地规定了我国法院针对“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境外被告设置的6 种管辖依据,〔41〕依照2021 年《民事诉讼法》第272 条的规定,管辖依据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代表机构住所地。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1 款将上述管辖依据适用于除身份关系以外的任何涉外民事纠纷。从体系解释上看,该条第2 款规定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为第1 款中6 种管辖依据的补充,也必然适用于第1 款适用范围之外的所有类型的国际民事争议。就此意义而言,“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可以作为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中的“剩余管辖权”,不仅完全可以替代国内地域管辖规则发挥的类推适用于相关国际民事争议的功能,也可以起到填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1 款可能存在的管辖空缺之作用。实际上,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问题上仍寻求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的帮助并非一劳永逸,毕竟在立法层面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的体系化程度亦十分有限,无法涵盖所有类型的具体民事争议。
最后,以“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代替国内地域管辖规则切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是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体系对于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此次修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合理增加管辖涉外案件的类型,适度扩大相关管辖依据。〔42〕参见《周强就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载《人民法院报》2022 年12 月28 日,第1 版;王俏:《我国民事诉讼法完成修改,将更好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解读新修改的民诉法》,载《人民法院报》2023 年9 月2 日,第4 版。相较于2021 年《民事诉讼法》第272 条的规定,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的规定意在适当扩张人民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特别是该条第2 款规定所蕴含的填补国际特别地域管辖空缺的体系功能,避免了人民法院类推适用国内地域管辖规则仍可能存在规范空缺的窘境。而且,相对于类推适用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的做法,人民法院援引“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更具灵活性和扩张性,符合立法者意图实现的更好地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诉权,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立法意旨。
上述分析证明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具有替代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类推适用于国际民事争议的体系效应,有助于强化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统一性。
(二)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管辖规则
作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建设成为立法者的紧迫任务。在此要求下,我国在晚近的诸多法律法规中均设置了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条款。〔43〕例如,2022 年修改的《反垄断法》第2 条、2016 年《网络安全法》第5 条、2017 年修正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 条、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2 条第4 款、2021 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 条第2 款、2021 年《数据安全法》第2 条第2 款,以及2021 年《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 条、2021 年《反外国制裁法》第12 条。从理论上说,国内法中规定的域外效力条款本质上是划定国内法地域效力范围的立法管辖权规范。实践中,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最终实现仍需借助相关涉外司法和执法活动,包括需要以国际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司法实务界也认为,理论上符合中国法域外适用条件的涉外案件集中在涉外民事诉讼领域,在此领域人民法院应积极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44〕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我国法院参与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机制构建》,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1 期,第166 页。
由上可知,国际民事诉讼是保障中国法域外效力得以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相对于行政机关,由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推进中国法的域外适用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45〕参见霍政欣:《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之构建——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视域》,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1期,第51 页。在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已初显成效的当下,无疑需要建立健全与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直接相关的人民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体系,毕竟中国法域外效力的最终实现归根结底需要仰赖相关国内法的涉外执法司法效能。〔46〕2021 年12 月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意义。参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人民日报》2021 年12 月8 日,第1 版。国际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实现中国法域外效力的“私法路径”,能够通过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私法争议的过程中达到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目的。〔47〕参见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36 页。由此,也就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管辖规则。
在涉外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反垄断法》第2 条,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可以基于被诉垄断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结果地作为管辖权依据。〔48〕参见“西斯威尔国际有限公司、西斯威尔香港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2 号民事裁定书;“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 号民事裁定书。实务者的研究也指出,有关反垄断和证券的涉外民事诉讼,可以注重结合《反垄断法》第2 条及《证券法》第2 条第4 款规定的域外效力条款认定地域管辖,如《反垄断法》第2 条规定的“效果原则”应成为垄断纠纷案件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考量因素。〔49〕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我国法院参与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机制构建》,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1 期,第166 页。但是,《反垄断法》和《证券法》的上述规定所确立的“效果原则”在性质上属于实体法规则,并非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50〕参见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23 页。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为实施国内法域外效力条款提供相衔接的司法管辖规则。在此方面,“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能够作为与此类国内法域外效力条款相衔接的司法管辖规则。而且,鉴于一国可通过放宽民事诉讼管辖权来扩张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法等公法的域外管辖,〔51〕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载《法学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187 页。故具有扩张性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对于强化我国涉外法治斗争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无疑能产生重要的实践价值。
与之类似,《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 条及《反外国制裁法》第12 条规定的阻断追偿机制,是基于保护我国当事人实体法上权利的客观需要,而为我国企业和个人提起追偿诉讼提供实体法依据。此类法律法规域外效力的实现,亦有赖于我国相关司法管辖权规范的配合。〔52〕参见黄志慧:《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必要管辖权制度的体系定位与规范阐释》,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4 期,第49-50 页。例如,对于前述阻断追偿条款的实施,当人民法院依据其他法定管辖依据无法为位于境外的被告提起的违约或侵权之诉确立管辖依据时,“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能够成为此类诉讼中有效填补管辖空白的法律工具。显然,此种防止管辖落空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对于丰富我国涉外法治斗争的“法律工具箱”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涉外专利许可使用费率纠纷中适用的“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即是出于维护我国专利使用人利益之现实需要,将专利授权地、专利实施地、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等作为争议与人民法院存在“适当联系”的依据,〔5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管终517 号民事裁定书。以免落入“管辖真空”的窘境。
在国际私法意义上,鉴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与相关案件准据法的确定(也包括非经冲突规范指引的实体法之适用)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建立并妥善实施“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可以说,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司法竞争和国际民商事利益博弈,“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有助于凸显法院在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这既是加快建设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当下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的必要举措。
总而言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具备供给与国内法域外适用条款相衔接的管辖规则之体系效应,有利于提升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协调性。
(三)填补必要管辖权功能的空缺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并未专门规定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必要管辖权,〔54〕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52 条规定了必要管辖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条文说明》,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4 页。此外,2021 年7 月4 日、2023 年8 月18—19 日分别在宜昌和深圳举行的《中国国际私法典》(学会建议稿)管辖权编草案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学者专门研讨了该草案规定的不同版本的必要管辖权。但是实践中根本无法避免外国法院针对特定争议无管辖权,以及外国法院虽享有管辖权但基于某种原因拒绝行使管辖权,或事实上不能行使管辖权等情形。对我国而言,必要管辖权主要用以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保护在外国的中国人的合法权益。〔55〕同上注,第112-115 页。因此,“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是否具备填补必要管辖权的立法缺位,有效保护我国当事人的诉诸司法权并为本国海外民商事利益提供司法救济的体系效应,值得思考。
应该说,“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与必要管辖权存在显著区别:一是必要管辖权是在明显没有其他国家的法院可以提供司法救济而出现国际裁判管辖权消极冲突的情形下,一国法院可以行使的管辖权。〔56〕参见张仲伯:《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91 页。而“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则并无此要求,甚至通常是在涉及与外国法院争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情形下适用。二是基于保护当事人诉诸司法权之需,必要管辖权的适用并不必然要求建立在争议与受案法院存在联系的基础上。例如,在必要管辖权的行使上,适用于加拿大一些普通法区域的《法院管辖权与诉讼移交法》第6 条并不要求争议与法院地国家存在任何联系。〔57〕当然,在当事人与法院地国家并无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法院可据此拒绝行使必要管辖权。See NaÏt-Liman v.Switzerland,Application No.51357/07, Judgment of 15 March 2018.而“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仍需考虑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三是必要管辖权本质上是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次要或辅助依据,〔58〕See Alex Mills, Rethinking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84(1)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25 (2014).其不以扩张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为目的。与之不同的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显然具有扩张本国司法管辖权的意图。
但是,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构建了基本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体系的前提下,与必要管辖权类似的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仅适用于发生在外国的与我国联系较低的案件。需指出的是,各国法院在援引必要管辖权时,通常不会对案件与法院地国家存在联系的标准予以严苛解释,这使得法院享有高度自由裁量权决定必要管辖权制度的适用与否。〔59〕See Chilenye Nwapi, A Necessary Look at Necessity Jurisdiction, 47(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 243-245(2014); Stephanie Redfield, Searching for Justice: The Use of Forum Necessitatis, 45(3)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3-914(2014).与必要管辖权在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中的地位相同的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亦可作为一种填补空白的“剩余管辖权”。〔60〕参见黄志慧:《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必要管辖权制度的体系定位与规范阐释》,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4 期,第55 页。在此情形下,基于保护当事人诉诸司法权之需,人民法院可借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灵活性进行扩张解释。实际上,“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剩余管辖权”理论的影响。对于此种管辖权的适用,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既然我国设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主要立法目的和政策是保障本国当事人享有的诉诸司法权以及海外的民商事利益,则可不必对争议与我国之间的联系作严苛解释。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国际秩序中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利益,不应超越诉诸司法权所保障的公正利益。〔61〕See Chilenye Nwapi, A Necessary Look at Necessity Jurisdiction, 47(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 240-241(2014).为了保障国际民事诉讼中公正利益的实现,一国法院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问题上,于例外情形下应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而非坚持直接的地域联系。特别是,当我国当事人在外国可能面临被拒绝诉诸司法的风险时,理应依据“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为其提供我国法院作为获取司法救济的最后途径。
因此,在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中,“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可以发挥替代国际民事诉讼中必要管辖权的体系效应,有益于促进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周延性。
四、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范适用
(一)扩张“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理据
传统的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都以主权视角审视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正当性,将管辖权视为主权者的司法特权,而对于私人的公平正义则持漠视态度。但是,国际民事争议中跨国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各国无法再以机械的属地或属人管辖充分回应一国对外交往和有效保护当事人利益的需要。正因如此,当今国际民事诉讼法更为关注当事人之间的公平正义,并以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己任。这种理念于“二战”以后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到遵循,特别是国际民事管辖权从威权型管辖权向权利型管辖权的明显转变引人瞩目。〔62〕参见向在胜:《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185-186 页。这就意味着“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关注的不再是被告与法院地的物理联系,而是被告与法院地之间的关系,如此便极大地扩大了受案法院对争议相关事实及当事人的考量。〔63〕参见郭玉军、向在胜:《网络案件中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载《中国法学》2002 年第5 期,第167 页。
尽管绝对的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观点趋向淡薄,但也要求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正当性。〔64〕参见何其生:《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民事诉讼》,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53 页。就此意义而言,寻求争议与受案法院某种程度的联系是国家行使司法权趋于理性的表现。“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为一种为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以及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的途径,客观上要求只有在争议与本国所需保护利益存在足够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该争议的解决能够促进该国社会公共福利(包括保护作为该社会之成员的个人利益)时,才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然而,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上,对于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并无普遍接受的标准。从比较法上看,亦无国家对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的“联系”进行界定的立法例。而且,目前我国对“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用,均涉及与相关外国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例如,在“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列举了专利授权地、专利实施地、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等具体联系因素。前述地点之一在我国境内的,应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即可依据争议与我国的“适当联系”确立本国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6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0)摘要》,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88131.html,2023 年9 月2 日访问。上述做法显然是出于保护我国当事人民商事利益和提升人民法院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之目的,适度放宽了对联系标准的认定。
客观而言,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有其特殊性:一是不同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意味着其将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和准据法,进而可能导致个案裁判结果的迥异,这也致使当事人挑选法院现象的频发;二是不同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致使相关当事人可能承受不同语言文化及时空距离带来的高额诉讼成本,对诉讼两造公正性的考量成为法院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的重要考量因素;三是从现代政治传统的视角看,一国亦只有在诉讼与其有足够关联而使其投入司法资源值得时才会为当事人提供私权保护。上述特性揭示了国际民事管辖权与国内民事管辖权的差异性,也使得国际民事管辖权对于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联系”的要求明显高于国内地域管辖权。〔66〕参见向在胜:《中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立法体例研究》,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186-187 页。这一来可证明为何美国法院在“国际鞋业公司案”中确立的“最低联系”标准受到不少国家的诟病,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法院在晚近实践中对“最低联系”标准的适用进行了限缩。〔67〕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当前的限缩并不表示未来不会根据情势需要再度扩张。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载《法学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183-184 页。
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上述特性虽能阐释一国在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联系”要求的应然立场,但无法回应人民法院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重大要求:一是本国海外民商事利益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需求客观上要求我国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上对“联系”标准不宜过于严苛。实际上,当今大国在国际民事管辖权领域均存在扩张现象。经济上的大国地位要求在管辖权的规制上超越纯粹的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以大国的思维和视角规范管辖权,尤其是突出经济联系和外国行为对我国的影响等作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依据。〔68〕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5 期,第136-137 页。二是作为我国对国际民事争议行使管辖权的分配性规则,适当降低“联系”标准并单边扩张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做法,不仅有助于保障中国法域外效力的实现,也有助于维护我国在某些法律领域形成法律规则的利益。〔69〕这些领域包括保险、航运或者商业等。参见甘勇:《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法理基础》,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5 年第2 期,第125 页。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和对外开放国策不断深入的情势下,推动人民法院在国际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也是彰显我国跨国司法治理权和积极参与民商事争议全球治理的表现。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会对国际法产生渐进式影响,从而左右全球治理的长远效果。〔70〕参见霍政欣:《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内法院》,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281-282 页。四是全球化时代人民法院不仅以解决纯粹国内案件为己任,也应分担解决国际案件的任务。在决定本国法院是否具有国际民事管辖权时,应摒除仅以内国法院自居的国家主义的狭隘审理观,而应以普遍主义的国际审理观,发挥本国法院保障国际私法关系安定性的目的。〔71〕参见吴光平:《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决定基准——总论上方法的考察》,载《政大法学评论》2006 年第94 期,第329 页。而且,这种理解也契合我国在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中创建全球和区域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目标。
上述分析表明,“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并非完全以“联系论”为理论基础并强调争议与我国法院存在紧密联系,而是侧重于为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乃至实现参与全球治理并在特定法律领域发展本国法律的目标。如前所述,对于联系标准的认定,可基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之目的,积极回应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基础的变迁,并以包括法律利益在内的利益联系为据适当放宽对联系标准的认定。
(二)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方法
在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体系化程度不完全充分的情势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为一种替代国内地域管辖规则类推适用的“剩余管辖权”无疑蕴含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而且,在对联系标准的理解包括法律利益在内的利益联系之情形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必将显著扩张人民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由此也会加剧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而需加以限缩。这本身也是人民法院致力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应有之义。在此方面,可借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法律制度,作为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适用的方法。
其一,援引排他性管辖协议达成避免与他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目的。尽管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0 条延续了2022 年第二次修正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31 条对于对抗式平行诉讼的放任立场(同时该法增加了重复式平行诉讼的规定),强调了人民法院法定管辖权的优先性,但也明确在当事人订立的选择外国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不违反我国专属管辖,且不涉及我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72〕参见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0 条。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以“适当联系”为据行使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让位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院的排他性管辖协议,从而达成适当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适用之目的。
其二,利用先受案优先原则适当协调与他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冲突。尽管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删除了《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第283 条规定的预期承认方法,但该法第281 条在我国国际民事诉讼中引入了先受案优先原则,并将其作为人民法院中止诉讼的依据,即外国法院先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经当事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基于自由裁量权可以中止诉讼。但是,当事人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或纠纷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以及案件由我国法院审理明显更为方便时,也不适用先受案优先原则。而且,外国法院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件,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审结时,依当事人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恢复诉讼。〔73〕参见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1 条。尽管存在上述适用的例外情形,但作为一种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方法,先受案优先原则的适用本身不牵涉复杂的利益分析,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民法院的诉累,并避免可能产生相互冲突的判决,从而合理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张性。
其三,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有效发挥其适当限制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行使的作用。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2 条对2022 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30 条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进行了重构。特别是将“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的条件修改为“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删除了“案件不适用中国法律”的限制,并且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当事人参加诉讼均明显不方便”。〔74〕参见202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2 条。立法者对不方便法院原则规定的改进,大大提升了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基于自由裁量权避免国际管辖权积极冲突产生的可能性。就此意义而言,改进后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仅降低了外国法院对人民法院扩张司法管辖权的担忧,〔75〕参见黄志慧:《人民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现状反思——从“六条件说”到“两阶段说”》,载《法商研究》2017 年第6 期,第157-158 页。也有助于适当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用。
总之,利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理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用,避免特定情形下国家间在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上的不必要对抗,同样有助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
(三)“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规范适用中的利益衡量
涉外法治的实施主要包括相关法律的国内实施和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两个方面。〔76〕参见涂卫:《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载《学习时报》2022 年2 月16 日,第A3 版。鉴于司法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密切关系,使得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提升,既有赖于人民法院确立并积极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也需要在特定情形下在此问题上持谦抑态度。换言之,一国对国际民事管辖依据的适用和解释既不能过于封闭,亦不能过度扩张。因此,人民法院援引“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时对联系标准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关于争议与受案法院之间“适当联系”的认定,主要是一个司法而非立法问题。在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要求下,作为一种需要充分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和贯彻司法能动理念的制度,无论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张还是限缩适用,均需要对个案中的相关利益进行权衡。
其一,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衡保障。国际民事诉讼需要遵循两造攻防平等的基本理念,〔77〕有学者称之为“诉讼法上的真正立足点之平等”。参见陈隆修:《中国思想下的全球化管辖规则》,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版,第338 页。这意味着受案法院在决定管辖权的问题上必须平衡两造的程序利益。在国际民事诉讼中,既然原告依据案件事实和相关国家法律的规定享有挑选管辖法院之自由,则基于保护被告公正审判权之目的,应兼顾其诉讼负担。尤其是,“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应考虑是否致使被告须至对其而言遥远或不方便的法院应诉,造成诉讼的延宕与法院地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对被告造成极大的负担而显失公平。对于原告来说,“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用主要应考量原告是否能借由法院地国家的诉讼而获得司法救济。人民法院需适度审视外国法院是否稳定且正常运作、原告取得的胜诉判决是否能获得有效执行等程序性问题,以避免原告在外国法院的诉讼遭遇不合理的拖延,或存在其他侵害原告程序性基本权利的现实风险。对于两造之间程序性利益的平衡,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82 条规定的“两阶段式”的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从诉讼程序有效推进上看,兼顾两造程序利益的平衡,本身也是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内在要求。
其二,当事人与受案法院地国家之间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当事人与受案法院地国的利益冲突通常表现为私人利益与法院地公共利益的龃龉。一方面,当事人基于程序法和实体法方面利益的考量,而将相关争议系属于特定国家法院的分歧,必然会形成私人对管辖权问题的博弈;另一方面,受案法院所在国往往基于对本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价值的考量,超越当事人对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的攻防,径直依据保护本国公共政策之需决定行使管辖权。特别是,当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裁判系争案件有助于维护本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和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倾向性保护涉外劳动争议、消费者争议、环境侵权等特定案件中身为弱势者之原告,以及必要管辖权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积极捍卫国际法上诉诸司法权等人权法价值是必要的。〔78〕参见吴光平:《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决定基准——总论上方法的考察》,载《政大法学评论》2006 年第94 期,第298-300 页。此外,国际私法争议也牵涉公法利益和国家利益,其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其公法为本国公民的福祉服务,通过私法实现公民之间的公平正义。〔79〕参见邹国勇:《克格尔和他的国际私法“利益论”》,载《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5 期,第152 页。显然,在管辖权行使与否的决定上,受案法院地国家的公共利益会超越对当事人私人利益的考量。实际上,对法院地国家公共政策的捍卫也常常与私人利益的保护保持一致。当存在维护法院地公共利益并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之需时,人民法院对于自身与争议的“适当联系”之阐释应持宽松立场,以便主张其享有管辖权。
其三,不同国家之间秩序利益的适度考量。尽管“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不为国际法禁止,但鉴于此种管辖权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及其本身的扩张性,为防范可能存在的“过度管辖”进而强化管辖权行使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对其合理限缩。尤其是,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 条第1 款已经囊括了诸多相对普遍采用的管辖依据之情况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必然面临与其他和案件存在联系(甚至更为紧密联系)的外国法院管辖权之冲突,并无法回避判决的国际协调问题。在无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尽管我国无须对相关外国法院的管辖权加以礼让,但至少应确保“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不涵盖各国普遍将其作为专属管辖的事项。〔80〕关于各国相对普遍接受的专属管辖权的讨论,See Geert van Calster,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the EU, 3rd ed., Hart Publishing, 2021, p.81-96.这不仅是确保判决实效性的需要,也是适当尊重外国司法主权的表现,同时有助于避免招致外国对我国“司法沙文主义”的批评。无论是从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还是从判决国际协调的利益出发,都有必要考虑对“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度限缩。这既有助于强化国家间民事司法合作并提升国家间的国际秩序利益,本质上也有利于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
总之,在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的要求下,人民法院适用“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张与限缩,应基于程序利益、公正利益和秩序利益的综合判断寻求管辖权行使的妥当性。
五、结语
国际民事管辖权是一国司法竞争力的基石,也是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在对外民商事交往的进程中,我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体系需要发挥跨国分配司法裁判管辖权的重要作用。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构成部分,“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与中国法域外适用存在密切关系,是中国法域外适用的配套制度。在各国司法管辖权争夺日益激烈、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完善以国际民事管辖权为核心的国际民事诉讼规则和制度。这不仅是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参与国际民商事争议治理规则制定的基础性工作。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只有适应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需要,并契合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和制度,才能有效回应我国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积极行使管辖权,是践行能动司法的生动体现,也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举措。作为对当今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国不仅建立了限缩“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相关国内法制度,也积极参与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推动的国际民事管辖权统一化工作,并秉持国际民事司法合作理念化解国家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81〕参见何其生:《海牙管辖权项目的困境与转变》,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2 年第6 期,第36 页。上述事实均展现了我国在合理扩张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同时,也基于维护国际秩序利益的需要兼顾与他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适当协调。
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我国参与国际民商事争议治理和构建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法治保障。〔82〕参见刘敬东:《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载《法学》2016 年第7 期,第3 页。当前国际民商事领域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尤其是一些国家基于单边主义立场扩张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并片面维护本国利益,而忽视便利和保障有序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实践,无助于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民商事新秩序。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出于构建国际民商事新秩序和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量,应在国际民事管辖权领域提升国家间的互信,并推动国际民商事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公平分配。遵循这种价值导向,不仅有助于达成国际民商事争议有效治理的目标,而且也对各国强化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