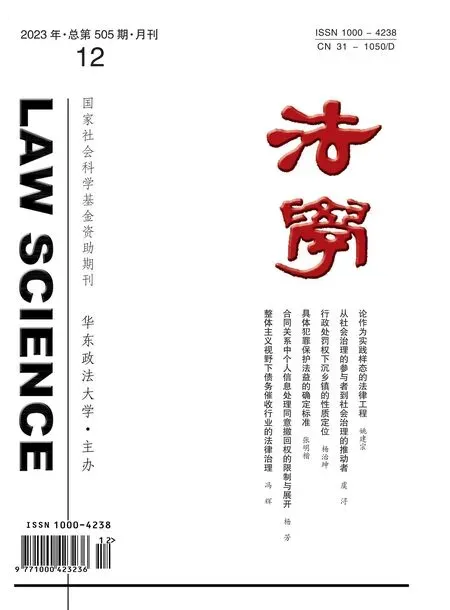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
——基于分配正义理念的跨法域研究
●高 旭
自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来,各地检察院在食药品安全领域纷纷提起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由于现行法并未对消费公益诉讼能否诉请惩罚性赔偿作出明文规定,既有研究已对检察院在消费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合法性、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如何计算等诸多问题予以关注,但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这一问题还缺乏专门研究。
惩罚性赔偿在性质上本就极为特殊,由私法机制执行了本应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是一种特殊的惩罚制度。〔1〕See David G.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anova Law Review 364, 365(1994).相关中文介绍,参见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3 期,第104 页。在功能上,惩罚性赔偿不同于赔偿权利人实际遭受损失的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2〕See Andrea A.Curcio, Painful Publicity —An Alternative Punitive Damage Sanction, 45 DePaul Law Review 341, 344 (1996).不过,在美国司法实践中,补偿性赔偿可作为衡量惩罚性赔偿是否过重的参考标准。〔3〕See David G.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anova Law Review 364, 402(1994).相关中文介绍,参见刘志阳:《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1 期,第216 页。我国现行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均以补偿性赔偿的成立为前提,以实际损失乘以特定倍数计算。然而,检察院主导的消费公益诉讼已经改变了惩罚性赔偿的私人执法属性,诉讼请求也并未实现对消费者群体的补偿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已经对传统的惩罚性赔偿救济机制和制度功能形成冲击,难以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协调。
惩罚性赔偿发轫于普通法系,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发达,〔4〕参见朱广新:《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究》,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152 页。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在美国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学术话题,虽然其颇具特色的数额分享制度难以直接移植,但在该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中,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聚焦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分配机制上衍生出精细的讨论,其背后的分配正义价值理念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化转向值得关注。在我国,这一命题处于诉讼法与社会法的交错地带,存在法域耦合和义和的探索空间。〔5〕法域关系中耦合与义和的界定,参见苏永钦:《多元法域的六个介面——现代法教义学的最后几片拼图》,载《师大法学》2019 年第2 期,第22-24 页。通过对数额分享制度在价值层面和功能意义上的比较法考察,社会法的基本范畴可作为我国相关制度完善和建构的理论工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也具有作为社会权利救济机制的发展前景。
一、比较法考察下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正当性检视
(一)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实践样态与理论困境
在我国,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机制,即收归国库、检察院或法院托管、专用于特定目的,〔6〕参见时磊:《检察公益诉讼办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路径》,载《中国检察官》2020 年第15 期,第64 页。但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收归国库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7〕参见黄忠顺、刘宏林:《论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基于990 份惩罚性赔偿检察消费公益诉讼一审判决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9 期,第81 页。托管是资金归属确定前的一种暂时性安排。专用于特定目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益目的,专门用于公益诉讼中的必要费用支出或者公益修复;另一种是混合目的,优先向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发放,超过诉讼时效或者无人申领的剩余资金则上缴国库或者用于其他公益目的。在资金管理方式上,专用于特定目的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财政专户集中收缴,专款专用;〔8〕参见《苏州市吴江区消费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吴江检会〔2018〕3 号)。另一种是汇入专项基金,实践中多数是由检察院、法院或财政局等政府机关单独或联合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加以管理。〔9〕如四川省犍为县正在探索建立由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设立并管理的食品安全公益基金。从财政法的角度看,如果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管理,那么在性质上属于财政收入,均按收归国库处理,只不过须区分是否专款专用:要么是作为非税财政收入,统一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即实践中最为普遍的处理机制;要么是作为限定用途的专项资金,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原则设置独立的管理核算机制。
就收归国库模式而言,现有案例在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属论证上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认为检察院诉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来源为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10〕参见黄忠顺、刘宏林:《论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基于990 份惩罚性赔偿检察消费公益诉讼一审判决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9 期,第83 页。由于消费者未起诉,且胜诉后也难以找到确切的权利人,实践中法院通常判决直接上缴国库,在法理上比照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处理。〔11〕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 民初384 号、385 号、386 号、387 号民事判决书。此种方案有两方面不足:一方面,法律规定此类请求权为消费者专属,检察院主张惩罚性赔偿并没有获得私人授权或让渡,本身就欠缺私法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金已经由公益诉讼判处并收归国库,若有消费者单独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在程序处理上将面临一系列难题。〔12〕如果经营者已经偿付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而丧失清偿能力,消费者嗣后提起的私益诉讼则会“赢了官司却输了钱”。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1 期,第271 页。第二种方案是将惩罚性赔偿认定为一种公法债权,其源于大陆法系认为惩罚性赔偿属于刑事制裁的通说,〔13〕参见[奥]赫尔穆特•考茨欧、瓦内萨•威尔科斯克:《惩罚性赔偿金: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视角》,窦海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88、130-131 页。故在资金归属上也应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作等同处理。法院在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允许扣除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便是这一观点的体现。第二种方案虽更为自洽,但招致的批评意见较多,主要观点为本属于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被变相国有化,欠缺正当性与合法性。〔14〕参见黄忠顺、刘宏林:《论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基于990 份惩罚性赔偿检察消费公益诉讼一审判决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9 期,第82 页。但若将资金专用于公益诉讼费用支出或其他公益事业,学界态度对此则较为宽和。〔15〕代表性观点,参见杨会新:《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126 页。
除收归国库模式之外,实践中的少数做法是将惩罚性赔偿金完全分配给消费者,其依据在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私权属性,〔16〕同上注,第117 页。但这一理路也有瑕疵。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私法构造与私人执法的优势息息相关,受害人通常能够直接获取加害人身份和侵权事实等信息,〔17〕See Steven Shavell,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Law Enforcement, 36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255, 271-274 (1993).惩罚性赔偿又通过额外的激励机制弥补私人起诉动力的不足,保障私人执法的便利性。〔18〕See Marc Galanter & David Luban, Poetic Justice: Punitive Damages and Legal Pluralism, 42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394, 1451 (1993).但公益诉讼以公共执法为手段,诉讼成本由公共部门承担,将惩罚性赔偿金全部分配给私人将消解惩罚性赔偿鼓励私人维权的政策性因素。此外,主流学说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并非补偿原告损失,而是单纯对被告不法行为的惩罚和威慑。〔19〕See David G.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anova Law Review 364, 378(1994); Bethany Rab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 Statutes: Good Policy But Bad Law, 1 Utah Law Review 333, 342 (2008).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同样是为了强化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遏制功能,填补消费者损失并非首要目标,在数额计算上也没有对此予以关切。〔20〕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1 期,第268-269 页。
从我国实践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被不加区分地收归国库,这一做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存疑。目前学界并未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公法债权属性提出质疑,而且在“专款”的权属性质与管理模式、“专用”的法理依据与具体路径等问题上还欠缺讨论,这使得专款专用仅成为一种符号式倡导,欠缺规范化和技术化的教义学路径。因此,收归国库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理论支撑,亟需补足正当性和合法性等层面的论证,否则就需要探寻更加合理的归属与分配机制。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舶来自美国法,〔21〕参见朱广新:《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究》,载《比较法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152 页。但既往研究却集中在私法领域,忽视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还兼具公法的一面,未能还原制度原貌,在法律移植上存在疏漏。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公法色彩体现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机制上,美国法发展出了独特的数额分享制度,赋予政府掴取胜诉判决中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力。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实践强调公权力对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这与数额分享制度下的“政府主导”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有必要考察数额分享制度,通过与域外制度经验和价值机理的比较,探索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
(二)数额分享制度下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理据
虽然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并非不无争议。在上世纪80 年代兴起的美国侵权法改革运动中,大量司法判例对巨额赔偿金的支持引发了学界声讨,〔22〕See David G.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anova Law Review 371-372 (1994).惩罚性赔偿被批评为是一项合法牟取暴利的制度,〔23〕See Paul F.Kirg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843, 843 (1993).这种“意外之财理论”(windfall theory)促使人们反思这一分配机制的正当性。〔24〕See James B.Sales & Kenneth B.Cole, Jr., Punitive Damage: A Relic That Has Outlived Its Origins, 37 Vanderbilt Law Review 1117, 1165 (1984).1987 年,美国律师协会发出倡议,惩罚性赔偿金在扣除补偿性赔偿金及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之后应归国家所有。〔25〕See E.Jeffrey Grube,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41, 841-842 (1993).也有法官对惩罚性赔偿归属原告提出异议(dissent),认为应当归国家所有。See Leah R.Mervine, Bridging the Philosophical Void in Punitive Damages: Empowering Plaintiffs and Society through Curative Damages, 54 Buffalo Law Review 1587, 1605 (2007).随后,美国数个州相继通过立法或判例创制了数额分享(split recovery)制度。
从美国各州规定来看,数额分享制度均要求原告不得享有惩罚性赔偿的全部金额,胜诉判决支持的惩罚性赔偿金应扣除一定份额上缴给州政府。各州对惩罚性赔偿的扣除比例、收缴程序、资金管理及分配方式等规定各不相同,其中资金管理和分配方式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不区分资金具体用途,统一收归至州政府设立的一般基金〔26〕See Alaska Statutes Title 9,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 09.17.020 (j).或州政府国库〔27〕See Georgia Code Title 51, Torts § 51-12-5.1 (2).;第二种是汇入补偿刑事犯罪被害人的专项基金;〔28〕See IND.CODE ANN.§ 34-51-3-6(c); Or.Rev.Stat.Ann.§ 31.735 (1).第三种是汇入补偿侵权行为被害人或援助贫困诉讼当事人的专项基金。〔29〕See IOWA CODE ANN.§ 668A.1; Mo.Rev.Stat.§ 537.675 (3).后两种模式虽然限制了资金用途,但是基金管理主体为联邦或各州的公权力部门,包括联邦司法部、州政府或州法院下设的行政管理机构。三种模式的功能侧重也各有不同。在第一种模式下,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旨在充实财政收入,以减轻纳税人的税负,〔30〕See E.Jeffrey Grube,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41, 854 (1993).例如乔治亚州政府明确表示数额分享制度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合理手段。〔31〕See 737 F.Supp.1563, 1568 (1990).在后两种模式中,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则用于实施特定的政策目标或者建设公益事业,其理据在于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功能是保障社会利益这一政策目标的体现,故社会应当从中获益,政府将这部分资金投入公益基金,作为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一种实现社会利益的方式。〔32〕See Bethany Rab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plit-Recovery Punitive Damage Statutes: Good Policy But Bad Law, 1 Utah Law Review 333, 333 (2008).也有观点认为,直接收归国库以平衡纳税人负担也是一种社会获益的体现。〔33〕See E.Jeffrey Grube,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54 (1993).
但是,数额分享制度毕竟让政府进入诉讼,直接成为胜诉利益的占用者(appropriator)或判决债权人(judgement creditor),使民事诉讼的品格发生了变化。〔34〕See Paul F.Kirg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843, 847 (1993).数额分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旋即遭遇违宪审查,争议为是否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征收条款(takings clause)、禁止双重危险条款(double jeopardy clause)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过度罚金条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35〕See Clay R.Stevens, Split-Recovery: 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Punitive Damage Dilemma, 21 Pepperdine Law Review 857, 857 (1994).
禁止双重危险条款和过度罚金条款的适用前提是对同一行为的指控以及惩罚都必须在本质上是刑事的。政府参与诉讼在本质上是否是刑事的并不由诉讼类型决定,而是要由法院评估诉讼的目的是救济还是惩罚,只有出于惩罚被告的目的才会触发上述条款。〔36〕同上注,第857、883、884、887 页。在“United States v.Halper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当政府对被告提出刑事指控且对被告判处了刑罚,任何后续的民事诉讼只要没有严格体现救济功能,都会违反禁止双重危险条款。〔37〕See 490 U.S.435, 450 (1989).但如果政府在同一诉讼中同时诉请惩罚性赔偿和刑事罚金则属例外,因为此时处罚是否过度将成为一个争点,故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此外,禁止双重危险条款也不适用于双方都是民事主体的民事诉讼。〔38〕See 490 U.S.451 (1989).该案确立了禁止双重危险条款的适用标准,即政府不得在对被告人提出刑事指控后再以惩罚性赔偿为由提出民事诉讼。但是在数额分享制度中,政府既不是惩罚性赔偿诉讼的具名原告,也没有在惩罚性赔偿诉讼中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仅以部分惩罚性赔偿金被分享给政府并不足以论证其改变了民事诉讼的性质。〔39〕See Clay R.Stevens, Split-Recovery: 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Punitive Damage Dilemma, 21 Pepperdine Law Review 886 (1994).
与禁止双重危险条款不同,数额分享制度违反过度罚金条款曾获得判例支持。在“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 Inc.v.Kelco Disposal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政府既没有起诉,也没有享有惩罚性赔偿金份额的任何权利,那么不受过度罚金条款约束。〔40〕See 492 U.S.257, 274 (1989).从这一意见可推断如果政府分享了胜诉的惩罚性赔偿金,那么会触发过度罚金条款。〔41〕See Paul F.Kirg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843, 857 (1993).在“McBride v.General Motors 案”中,美国乔治亚州地区法院引用了前述判例,认为政府攫取惩罚性赔偿金会使其转变为罚金。〔42〕See 737 F.Supp.1563, 1579 (1990).但美国爱荷华州地区法院在“Burke v.Deere & Co.案”中持不同意见:爱荷华州政府在惩罚性赔偿上没有被赋予任何权利,因为根据州法规定,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交给州法院行政官(state court administrator)管理的民事信托赔偿基金,这与乔治亚州法规定的直接上缴国库存在实质差别。〔43〕See 780 F.Supp.1225, 1243 (1991).学界有观点认为,禁止双重危险条款和过度罚金条款是为了保护惩罚性赔偿诉讼的被告,因为只有被告才会被提起刑事指控或被过度制裁,但数额分享制度仅改变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即便没有数额分享制度,所有的惩罚性赔偿金归原告所得也是被告的法律责任,难以认为被告被重复追诉或者不当加重了其责任。〔44〕See E.Jeffrey Grube, Punitive Damages: A Misplaced Remedy, 66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41, 871 (1993).
数额分享制度是否违反征收条款在判例中也同样存在争执,核心问题在于惩罚性赔偿的胜诉判决是否构成一项财产权。在“Kirk v.Denver Publishing Co.案”中,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认为,在被告履行判决义务之前,政府对惩罚性赔偿金不享有任何权力,也无权介入惩罚性赔偿诉讼,判决的全部利益只得由原告享有。〔45〕See 818 P.2d 262, 262 (1991).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在先判例已确认财产权包括损害赔偿,故原告在胜诉判决下享有的权益属于财产权;政府占用原告的财产必须与其公共服务之间具有合理关系,而州法规定的分享比例已经远高于部分税种的课征比率,故难以认为合理关系成立。综上,州法违反了征收条款。〔46〕See 818 P.2d 262, 270-272 (1991).但美国大部分州的判例认为,原告有权诉请惩罚性赔偿并不意味着其胜诉后就享有一项财产权。〔47〕See Clay R.Stevens, Split-Recovery: 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the Punitive Damage Dilemma, 21 Pepperdine Law Review 857, 874 (1994).由于美国不同州的数额分享制度存在差异,〔48〕See Shepherd Components, Inc.v.Brice Petrides-Donohue & Associates, Inc., 473 N.W.2d 612, 619 (1991).每个州的立法可以对惩罚性赔偿施加不同的条件,甚至有的州拒绝承认惩罚性赔偿的合法性,因此原告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胜诉判决下的财产权是由各州立法所决定的。对于分享给政府的部分,原告本来就不享有财产权。换言之,数额分享制度仅赋予原告有限的财产权,政府权力应处于更优先的地位。〔49〕See Paul F.Kirg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e Allo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 Awards, 50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843, 854-855 (1993).
尽管曾遭遇过合宪性危机,迄今为止依然实施数额分享制度的美国各州大体肯认并维持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学界对数额分享制度也形成了以下共识: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两大核心功能体现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将一定比例的惩罚性赔偿金分配给能够代表社会利益的机构,不论是收归国库还是汇入特定基金,不仅能够降低原告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的投机性,而且能在资金的使用上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府有权分享惩罚性赔偿金也是因为惩罚性赔偿兼具公法属性,故而在程序和实体方面都应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数额分享制度均能满足相应的要求:在程序上,数额分享制度并未赋予政府诉讼当事人的资格,政府没有直接参与惩罚性赔偿民事诉讼,因此没有发生重复的刑事或准刑事追诉;在实体上,被分享给政府的惩罚性赔偿金既不属于原告的财产权,也没有加重被告的法律责任。
二、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归属与分配的制度困境与价值指引
(一)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欠缺合法性基础
在数额分享制度下,惩罚性赔偿的受益者不应仅限于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还应惠及社会,从而证成了收归国库的正当性。但是,数额分享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宪法规范的严格约束之上,否则将导致政府以公益为名滥用公权。我国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做法能否获得同样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则需要考察其是否与公法体系相抵触。需要注意的是,数额分享制度以惩罚性赔偿的私人执法模式为基础,仅调整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并没有改变惩罚性赔偿的私权性质,而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创设了一种惩罚性赔偿的公共执法模式。虽然两者都将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但公共执法模式与私人执法模式相比存在以下不同:一是公权力主体直接作为原告参与诉讼;二是惩罚性赔偿请求在较大程度上依附于刑事指控;三是作为权利人的消费者不参与诉讼,也无法分享胜诉赔偿金。
以禁止双重危险条款为例,其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均源自罗马法,〔50〕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563 页。在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上均相通。〔51〕参见宋英辉、李哲:《一事不再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5 期,第131 页。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可以从两审终审中解释出来。〔5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 条第6 项体现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精神。我国的现有模式是检察院在法律未明确赋权的情况下主动诉请惩罚性赔偿,大多在刑事判罚后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赔偿金主要上缴国库,这使得在实体上惩罚性赔偿与罚金刑别无二致,但在程序上公益诉讼被告并没有获得刑事诉讼被告的各项权利。已有研究认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和罚金并处的模式已经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如果《刑法》在相关罪名下规定的罚金刑难以起到最优威慑效果,那么也应该由立法机关修改《刑法》而不是由检察院单独提起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已造成法定刑的实质升格。〔53〕参见王承堂:《论惩罚性赔偿与罚金的司法适用关系》,载《法学》2021 年第9 期,第163 页;黄忠顺、刘宏林:《论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基于990 份惩罚性赔偿检察消费公益诉讼一审判决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9期,第83-86 页。
我国现有模式也涉及征收合法性问题,《宪法》第13 条第3 款规定对公民合法财产的征收须提供合理补偿。在数额分享制度下,原告诉请惩罚性赔偿能获得一定比例的金额,尽管是作为激励机制的“额外奖励”,这部分金额却具有鲜明的财产权属性。此外,原告获取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补偿性赔偿已得到法院支持,补偿性赔偿是侵权法对被害人的普通法救济,其财产权属性自不待言。而在我国现有模式下,检察院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并没有主张被害人的损害赔偿,虽然理论上被害人还可以继续诉请损害赔偿,但很难认为被害人会在惩罚性赔偿被“收归国有”的情况下还有动力起诉。有观点认为,公益诉讼并不排斥私人再对同一被告提起惩罚性赔偿,〔54〕参见崔晓丽:《食品安全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20 年第10 期,第57 页。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大多是以瑕疵商品销售总额或者批发价总额为基数乘以法定倍数来计算,〔55〕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1 期,第268-269 页。被告实际上已经履行了对每一位潜在被害人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再允许私人提起“搭便车”式的民事诉讼将致使被告重复清偿。因此,现有模式造成了被害人维权的激励机制被剥夺,被害人的补偿性赔偿实际上也难以实现,无异于对公民合法财产的征收。如果将惩罚性赔偿金全部分配给消费者作为合理补偿,那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际运行将可能完全转化为国家导向,国家将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56〕参见熊丙万:《法律的形式与功能——以“知假买假”案为分析范例》,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2 期,第317 页。这又偏离了我国在食药品安全案件中强调社会共治的初衷。〔57〕参见应飞虎:《禁止抑或限制?——知假买假行为规制研究》,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4 期,第67 页。我国现有模式所面临的征收合法性困境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即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分配关系应如何平衡。
实际上,从我国惩罚性赔偿民事诉讼的既往实践和国家倡导探索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政策导向来看,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美国的司法实践存在一定差别。美国之所以发展数额分享制度,是为了平抑惩罚性赔偿金的畸高现象,尤其是要修复惩罚性赔偿的“意外之财”缺陷。但这种功能异化现象在我国鲜有出现,我国对惩罚性赔偿一直采取审慎态度:在立法上,自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来,各单行法在计算规则上均设置了倍数上限;在实践中,我国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呈现出一定的规制倾向,尽管在制度上有过摇摆,但是反映了对惩罚性赔偿社会效果的重视,在其负面效应暴露出来后能够及时调整司法政策,〔58〕参见应飞虎:《禁止抑或限制?——知假买假行为规制研究》,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4 期,第63-66 页。在我国几十年来的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从未出现过天价赔偿事件。相反,食药品安全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一直运行不畅,〔59〕参见葛江虬:《“知假买假”:基于功能主义的评价标准构建与实践应用》,载《法学家》2020 年第1 期,第165 页。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大力推动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的现实基础也是基于传统私人执法模式的失灵,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故须通过公共执法模式补强。但这种基于实践需求的自发尝试还面临大量合法性问题,亟需与我国现有的公法制度相协调。数额分享制度难以直接作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模板”,虽然表面上看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是两种模式的交集区域,但数额分享制度克服各项合宪性争议的过程与传统的私人执法模式息息相关,这一理路不仅无法适配于公共执法模式,反而更加凸显了规制公权力的现实需求。现有研究已注意到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修补方案,具体包括通过立法为检察院另行创设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建立独立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制度;〔60〕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1 期,第271-272 页。完善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诉权优先、明确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诉讼请求扣除私人起诉金额与公法处罚金额等配套机制;〔61〕参见杨会新:《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125-126 页。强化对抗式审判模式以平衡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公诉化倾向,保护弱势被告的诉讼权利。〔62〕参见张明哲:《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审判模式:以对抗制为中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1 期,第150-162 页。从我国现有的公法理论资源来看,上述建议的理论来源可追溯至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一事不二罚、当事人主义等各个部门公法的基本原则。
前述方案可用以填补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面临的诸多合法性罅漏,但主要是从实体请求和诉讼构造两个方面规制检察院的公益诉权行使,避免因权力滥用而侵害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不过,仅靠规制公益诉权无法解决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因为在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属于财政收入,此时对其的管理、使用由财政法调整,已经脱离了公益诉权的范畴。此外,规制公益诉权也无法证成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合法性,收归国库意味着惩罚性赔偿被界定为公法债权,而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并未严格与补偿性赔偿相区分,公法债权属性难以与惩罚性赔偿的私法构造相协调,在私人执法和公共执法竞争的状态下,一旦公共执法行使了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私人执法即告落空,依附于惩罚性赔偿的补偿性赔偿也难以实现,此时公共执法模式就存在征收合法性的问题;而如果认为公私两种模式并行不悖,公共执法不影响私人执法,那么就会导致被告处于“双重危险”之中。
(二)公共执法模式应以分配正义作为价值指引
在公共执法模式下,对赔偿金分配机制的探索不应完全仰赖于对公权力的规制,而是要关切如何取得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分配关系的平衡。数额分享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分配正义,美国新近学理也对收归国库模式进行了反思,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前文所引述的“Burke v.Deere & Co.案”即为适例,法院认为资金专用于特定公益用途比收归国库更具有正当性。美国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Dardinger v.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案”则更具开创性,法官提出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须用于慈善目的,判决将大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用于设立一项癌症研究基金。〔63〕See 781 N.E.2d 121, 190 (2002).“Dardinger 案”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惩罚性赔偿的社会效益保障功能得到进一步关注,围绕分配正义,社会性赔偿(societal damage)、治愈性赔偿(curative damage)等新兴理论相继提出,推动了数额分享制度的革新。数额分享制度的借鉴意义在于其背后的分配正义理念和社会效益追求,以及新近发展的多元化资金管理模式和司法权的能动介入,这能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提供价值指引和方向参照。在我国的部门法体系中,分配正义影响了社会法的体系形成,是社会法的价值基石,〔64〕参见谢荣堂:《社会法治国基础问题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33-35 页。本文论题可接驳社会法寻求对应的基本范畴,作为本土制度完善和建构的理论工具。
分配正义理论始于亚里士多德,〔65〕参见[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第24 页。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义务和责任分配的正义。〔66〕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3 页。在19 世纪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加剧分化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意义的分配正义开始形成,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学者达班将亚氏理论体系化,在其定义下分配正义用以调整社会团体及其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达班认为,社会收益由社会团体生产,在分配之前属于社会团体的财产,但基于社会团体是为成员的共同福祉而存在,成员有权依据团体规章分享该收益。在现代国家,弱势地位应纳入分配正义的考量标准,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是一种分配负担的正义,其决定性原则是贡献社会所需的能力大小,能力越大者应当承担越多的社会义务。〔67〕See Emil Lask, Gustav Radbruch & Jean Dabin, The Legal Philosophies of Lask, Radbruch and Dabin, translated by Kurt Wil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446-448.
现代分配正义强调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一命题,〔68〕参见[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第5 页。达班提出的社会团体概念以及成员有权分享社会收益已经隐约勾勒出社会法的思想范畴。正式将分配正义理念纳入社会法的是拉德布鲁赫。其提出在个人主义法律观下,人的概念是一种抹平一切差异的形式平等概念,但在社会现实中,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是社会强势者的支配自由,社会弱势者处于被支配的依附地位。社会法旨在打破这种形式平等,将具有社会联系的集体作为社会法基础,在每一种私法关系背后都会浮现第三方利益相关者——大众。〔69〕See Emil Lask, Gustav Radbruch & Jean Dabin, The Legal Philosophies of Lask, Radbruch and Dabin, translated by Kurt Wil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74.在社会法领域,公法得以介入私法关系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并限制社会强势群体。因此,要达到分配正义,必须以存在一个超越个人的机关为先决条件,有组织的社会救济(特别是国家救济)将取代自我救济。〔70〕同上注,第154 页。
不过,拉德布鲁赫仅将正义视作法律的一种形式理念,〔71〕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雷磊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30-31 页。一些学者则进一步尝试在建构意义上探讨分配正义。在保障社会弱者这一价值面向上,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要求国家对家庭与阶级出身、个人天赋、机运等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予以一定限制,在保证公民自由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甄别出最少受惠者,使之得到补偿。〔72〕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73 页。在界定社会结构的正当性标准时,罗尔斯引入了社会共同体概念: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表现出的天赋才能的总和。〔73〕同上注,第510 页。在社会共同体进入分配正义后又衍生出了多元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认为作为分配正义对象的社会善品应根据不同的实践场域确立不同的分配原则。普遍主义分配正义与多元主义分配正义都认同社会共同体划定了分配主体的范围,但在分配客体的理解上存在分歧:罗尔斯认为社会善品是每个理性之人想得到的东西,可简化为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74〕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7 页。但沃尔泽认为只有人们先有善及其社会意义的观念,才能摹制出分配观念,善品须置于特定的社会领域加以界定。〔75〕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版,第5-6 页。多元主义相比普遍主义的进步之处在于揭示了社会共同体之于分配客体的意义:善品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分配公平与否应由善品的社会意义所决定。〔76〕同上注,第6-9 页。社会意义的典型体现是共同体,“一群人致力于分割、交换和分享社会善品,首先是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因此分配正义的前提是成员资格。〔77〕同上注,第31 页。在社会福利与安全这一领域,分配正义要求善品应提供给需要的成员。〔78〕同上注,第98-104 页。
无论是法哲学还是政治哲学,分配正义始终围绕对社会弱者的关切和对社会结构的纠偏,并强调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当分配正义作为价值基础进入具体法律部门的体系形成和概念建构时便具有了法学品格。不同于公私法概念的“先验性”,社会法旨在解决既有法律框架难以容纳的社会问题,〔79〕参见沈建峰:《社会法、第三法域与现代社会法——从基尔克、辛茨海默、拉德布鲁赫到〈社会法典〉》,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4 期,第52 页。因此会天然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社会政策的因应,〔80〕广义社会法即所有为实现社会政策而制定的法律。参见郭明政:《社会法之概念、范畴与体系——以德国法制为例之观察比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7 年第12 期,第374 页。努力将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兴法律现象纳入社会法的基本范畴加以调整。在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可以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法论题,考察分配正义并非要将这一问题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而是要在分配正义的价值基础上寻求相应的社会法基本范畴,整合和建构能够作为理论工具的中观概念。现代分配正义强调特定社会领域的共同体概念,以弱势群体或特定成员身份作为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的对象。因此,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需要厘清以下问题:(1)消费公益诉讼是否具有一定社会领域的共同体特征;(2)成员资格和分配依据应当如何界定;(3)共同体具有何种产权形式;(4)国家(主要为司法机关)需要担负何种职能。
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其余三个问题的前提条件。在现代意义上,共同体概念除了存在情感、习惯的相互隶属关系或者存在共同的利益结合等基本要素,〔81〕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 年版,第77 页。更加凸显以联结某一特定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为导向。〔82〕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8 页。在诉讼发展史上,共同体主义构成了公益诉讼的政治哲学基础,共同体利益的优先性证成了代表型集体程序的正当性,〔83〕参见王福华:《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2 期,第71 页。故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可视为一种保障受害人群体利益的共同体。〔84〕现代型纠纷具有讼争利益的公益性、讼争主体的群体性、纠纷影响的社会性、权利实现的宪法性和纠纷双方的非对称性等特点。受侵害群体存在扩散性利益或集团性利益,呈现出团体的样态。参见王福华:《变迁社会中的群体诉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3 页。不过,过于强调共同体优先也容易导致对个体利益的忽略,例如将惩罚性赔偿金不加区分直接收归国库的做法是一种对共同体利益的绝对追求,有悖于分配正义理念。在本文论题下,以法院和检察院为代表的公权力组织和责任人、受损群体共同划定了消费公益诉讼共同体的范围,〔85〕但这一共同体关系并不是封闭的,其他主体也可能被纳入这一共同体关系之下,比如消协组织。分配正义要求共同体对成员需求负担保障义务也就明确了分配问题的社会法属性,其后三个问题可归入以下基本范畴:成员资格和分配依据问题要求界定权利主体及权利内容,产权形式问题要求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产权归属及组织管理形式,国家职能问题要求探索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在社会权利保障层面的功能转向。
三、社会法范畴下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一)权利界定:社会补偿
由前文可知,出于防免企业责任过重以及重复清偿等考虑,检察院统一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应承担相当程度和数量的谦抑性要求,但从受损群体的角度而言,对责任主体的保护和对行权主体的谦抑也贬损了惩罚性赔偿对私人维权的激励,如果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不向消费者分配而是直接收缴国库,那么瑕疵商品或服务造成的大规模侵权损害会因为私人维权激励的欠缺而难以得到有效填补。从加害行为这一端来看,因不法行为而被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企业大都同时构成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86〕参见黄忠顺、刘宏林:《论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基于990 份惩罚性赔偿检察消费公益诉讼一审判决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9 期,第81、87 页。其法益侵害程度更甚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加之食药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扩散特性,受害群体数量较大,已经不亚于公害事件。
犯罪行为与公害事件中的被害人通常由社会补偿制度加以保护。社会补偿是社会法的重要分支,〔87〕参见郭明政:《社会安全制度与社会法》,翰芦图书出版公司1997 年版,第130-131 页。是指在特定原因下向个人提供一定给付以弥补其损失的社会保障制度。〔88〕参见郝凤鸣主编:《社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E1 页。在共同体责任和社会连带等理念下,〔89〕参见蔡维音:《社会福利制度之基础理念及结构——以德国法制为中心》,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8 期(1997 年),第27 页;娄宇:《论社会补偿权》,载《法学》2021 年第5 期,第95 页。对于意外事件、犯罪行为等特定因素给个人造成的损害,依托民事诉讼的侵权法救济往往耗时耗力,社会补偿将其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负担,能够对被害人提供及时的保障。〔90〕参见郑尚元主编:《社会保障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314 页。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完成社会补偿的体系化和制度化建设,但从国家对一些标志性食药品安全事件的因应来看,已出现了社会补偿的理念和雏形。典型案例是“三鹿奶粉事件”。在政府的担保下,三鹿集团贷款9 亿余元人民币并支付给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由乳协对近三十万确诊患儿制定一次性现金赔偿方案并统筹偿付事宜,具体发放由各地政府负责,最终接受赔偿方案的受害人高达总数的90.7%。〔91〕参见刘哲玮:《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模型的反思与重构——从三鹿毒奶粉事件切入》,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3 卷第1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 页。尽管这一事件的处理在解纷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在彼时代表人诉讼束之高阁、公益诉讼尚付阙如的背景下,此种由政府力量积极介入、全面接管和统筹规划被害人补偿的做法并不逊于国际上对同类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并且相较于群体性诉讼制度更加凸显了补偿的快速、全面、相对合理和经济优势,因而被学者高度评价为妥善处理大规模群体性侵权事件的范例。〔92〕参见范愉:《群体性侵害事件的多元化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与日本C 型肝炎诉讼案的比较研究》,载《法学家》2009 年第2 期,第57 页。如果将其中通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机制善后处置的突发性和应急性等情形撇除,对群体性的消费侵权行为建立常态化的社会补偿机制,将惠及更多的消费者群体。
鉴于国家力量对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政策推动和积极行动,受害群体的补偿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演化为社会补偿权的正当性基础。一是依靠个人起诉的民事救济手段在剥离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后更加难以发挥作用,社会保障法的勃兴即为弥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通过对损害迅速、确定的救济填补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传统赔偿制度的效率缺失。〔93〕参见张俊岩:《风险社会与侵权损害救济途径多元化》,载《法学家》2011 年第2 期,第95 页。现有公益诉讼旨在强化对企业不法行为的惩罚和威慑,但忽视了对受害群体的权利救济,既然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演化出公共执法模式,那么就应当在其中添加社会保障的法律属性。二是在比较法上有相近制度可资借鉴。首先是刑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这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94〕参见娄宇:《论社会补偿权》,载《法学》2021 年第5 期,第106 页。以填补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不足。〔95〕参见郑尚元主编:《社会保障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323 页。在检察院就食药品安全事件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受害群体兼具刑事被害人身份,其社会补偿权的正当性更应获得刑事诉讼之保护人权理念的背书。其次是公害事件被害人补偿制度,学理上认为针对公害事件导致的群体性健康损害,在不构成国家责任以及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困难的前提下,政府应基于社会连带和分配正义理念对福利资源 “再分配”,通过社会补偿措施填补损失。例如,《日本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以迅速、确实地填补公害事件所致被害人健康损害并推行受害人福利事业为宗旨,向企业事先强制课征一笔费用作为补偿金来源,由政府建立基金并负责运营。〔96〕参见林秀雄:《日本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之简介》,载《辅仁法学》1990 年第9 期,第475-476 页。我国台湾地区设置食品安全保障基金,将针对食品安全事件没收的不法所得与罚款作为资金来源,用于健康风险评估、消费诉讼辅助、维护受害者健康权益等事业。由此,也可仿效上述做法,将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作为社会补偿的资金来源。
不过,有疑义的是社会补偿是否需要以国家对人民的生存照顾义务作为法理基础。〔97〕德国学理对生存照顾的界定如下:因个人的生活已无法自给自足,即便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生活空间,仍有取用于社会的必要性,凡是所有满足人们这种“取用必要性”的设备,便是生存照顾。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63 页。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生存照顾义务的典例,由于补偿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从平衡国家财源和补偿必要性的角度须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请求权施加诸多限制条件。一是限制犯罪行为及其后果,域外法普遍将补偿或救助的对象限于暴力犯罪造成的重伤以及死亡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法益。〔98〕参见兰跃军:《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主要问题及其评析》,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2 期,第19 页。域外代表性立法例参见《德国暴力行为被害人补偿法》《欧洲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公约》《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二是限定犯罪被害人的经济状况,若被害人的生活未因犯罪陷入生活困境,则无给予救助的必要。〔99〕参见刘学敏:《台湾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评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08 年第2 期,第82 页。域外代表性立法例参见《荷兰刑事伤害补偿基金法》《瑞典刑事伤害补偿法》《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按照上述标准,只有健康严重受损且处于经济困窘状态的被害人才应享有补偿权。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高检发刑申字〔2016〕1 号,以下简称《司法救助细则》)对救助申请条件的规定也体现了此种生存照顾的精神,〔100〕《司法救助细则》第7 条以正面清单的形式列举了救助申请条件,要求刑事犯罪被害人或者民事侵权被害人因犯罪或侵权行为陷入生活困难。但如果按照该标准限定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补偿权范围,那么大量受害人的损失将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如果认为凡是涉事企业的消费者均能就其损失获得补偿,与犯罪被害人补偿权相比又过于宽松,难以解释为何在消费公益诉讼情形下普通消费者能够获得如此特殊优待。
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应确立消费者补偿权,且不宜采生存照顾标准。首先,社会补偿是一项社会福利制度,约束福利水平的核心因素是资金。犯罪被害人补偿权以国家财政为主要财源,财政资金的稀缺性决定了公共预算要平衡各个部门的需求,〔101〕参见刘洲:《财政支出的法律控制——基于公共预算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8 页。但是在消费公益诉讼中,消费者补偿权的资金来源是企业负担的惩罚性赔偿,且数额能够覆盖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并不需要国家财政的额外投入。参照沃尔泽的多元主义分配正义标准,单个消费公益诉讼可以理解为一个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共同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应优先满足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即对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其次,采生存照顾标准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在法理上应属于社会救助而非社会补偿。社会救助以扶贫济困为宗旨,被害人若因犯罪行为而罹于困顿,则应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获得保障。〔102〕参见钟秉正:《社会福利之法制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版,第246 页。我国《司法救助细则》第7 条明确规定了陷入“生活困难”这一要件,是典型的社会救助。〔103〕关于补偿与救助的区别,参见陈彬:《由救助走向补偿——论刑事被害人救济路径的选择》,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2 期,第183 页。社会补偿以特定事件为给付原因,不对受害人的经济状况有特定要求,公害事件被害人补偿制度即为适例。食药品安全事件属于社会公害事件,广大消费者群体因此蒙受损失,具有请求社会补偿的正当性。美国新近的社会性赔偿理论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大规模侵害会对社会造成分散型损害(diffuse harm),〔104〕See Catherine M.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aw Journal 347, 392 (2003).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对民事诉讼原告以外的其他受害群体应予补偿,〔105〕同上注,第451 页。传统数额分享制度下的分配方案应予改进,对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应建立赔偿受害群体的专项代理基金(specialized proxy funds)。〔106〕同上注,第420 页。
此外,建立消费者补偿权还能够纾解征收合法性的困境,国家出于打击食药品企业不法经营行为的需要“征收”了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那么就有义务实现对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由于公益诉讼是由国家负担诉讼成本,惩罚性赔偿对私人维权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发挥作用,故消费者补偿权应仅包括补偿性赔偿(填补损失),不应涵盖惩罚性赔偿(额外奖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垄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鉴于私人获取侵权信息更加直接,维权方式更为灵活,应肯认惩罚性赔偿对私人维权的激励,只有在激励不足而导致不法行为难以被有效遏制时,国家才有干预的必要。换言之,私人执法模式下的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属于民法上的请求权,由民事主体自主行权,自行承担成本并获取收益;而公共执法模式下的社会补偿属于社会法上的请求权,由国家代表社会利益行权并承担成本,但仅填补广大未行权消费者的损失。因此,在公益诉讼发动前,应鼓励消费者主动维权,私人诉请的惩罚性赔偿完全归于私人所有;在公益诉讼发动后,应限制消费者“搭便车”,不再受理消费者因同一加害行为而另行提起的惩罚性赔偿民事诉讼,而且在数额计算上,公共执法模式下的惩罚性赔偿还应扣除私人执法模式下已被法院支持的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二)权属安排:社会产权
建立消费者补偿权并优先由惩罚性赔偿金作为补偿义务的资金来源,应有相应的配套管理模式。惩罚性赔偿是按照补偿性赔偿的倍数乘算,实践中可能会基于部分被害人放弃申请、部分申请因缺乏证据而难以核实等因素导致出现剩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的权属也需要妥善界定。由前文可知,在我国的公共执法模式下,对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主要依托公共财政制度,只不过按照是否限定资金用途区分为统收统支和专款专用两种模式。在专款专用模式下,有两种财政工具可加以调整:一种是财政专项资金,通过设立财政专户归集惩罚性赔偿金的收缴和支出;另一种是政府性基金,通过基金设立的特定目的管理和使用惩罚性赔偿金。
根据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公共预算是采专用模式还是公用模式取决于政府所提供公共物品的性质。一般公共物品因其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只能由政府提供,并以税收作为资金来源,采公用模式;〔107〕参见岳红举:《〈预算法〉视阙下政府性基金的法律规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7 期,第79 页。而准公共物品因其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具有收费的可能,可以通过向使用者或者受益者收取合理费用补偿特定公共服务的成本,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采专用模式。消费公益诉讼应作为一项准公共物品而非一般公共物品,这是因为尽管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有限,但仍有消费者愿意自行起诉获得补偿性赔偿之外的额外收益。因此,消费公益诉讼原告所投入的诉讼成本可以从胜诉后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扣除,在财政管理模式上应采专用模式。〔108〕如《江苏省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暂行办法》就规定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除向消费者支付外,还可用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所需的专家论证咨询费、检验费、鉴定费、律师费、证人出庭作证的合理费用,负责赔偿金申领、审核、发放等具体事项的独立第三方的运作费用以及其他合理支出,保护消费者公共利益产生的其他合理支出。从财政法上看,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性基金都是专用于特定公共事务、促进与保障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财政工具,但是财政专项资金是纯粹的财政性支出资金,资金直接来源于国家公共财政拨款,不与社会公众形成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关系,〔109〕参见田开友:《政府性基金课征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63 页。制度约束程度比较低。我国财政专项资金的法制化水平也不高,法源效力层级低且数量不足,仅有极少省份出台了省一级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10〕目前只有江苏省、河北省、福建省、四川省颁布了地方政府规章层级的财政专项资金/财政专户管理办法。从财政透明度来看,财政专户常年居于财政资金信息要素类别的末位,〔111〕参见郑春荣、蒋洪、彭军:《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2014)》,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6 期,第5-11 页;杨丹芳、吕凯波、曾军平:《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2015)》,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 年第5 期,第5-14 页;吕凯波、邓淑莲、杨丹芳:《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2016)》,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1 期,第14-22 页;邓淑莲、曾军平、郑春荣、朱颖:《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2017)》,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 年第3 期,第19-27 页。有研究者认为,当前财政专户不仅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有些地方甚至连基本的内控体系都没有,专户资金“监守自盗”的现象时有发生。〔112〕同上注,郑春荣、蒋洪、彭军文,第9 页。
与财政专项资金相比,政府性基金的制度化水平和法治化要求更高。政府性基金是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113〕参见《预算法》第9 条第1 款。政府性基金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课征依据法定:政府性基金的设立要受法律保留原则或授权明确性原则的限制。〔114〕参见田开友:《政府性基金课征的法治化及其制度路径》,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 期,第33 页。(2)课征目的为实施特别政策:政府性基金用以支应国家为履行特定公共职能或行政给付义务而产生的资金需求,有明确的特别政策目的。〔115〕同上注,第39 页。(3)课征对象特定:政府性基金秉承受益者付费原则,缴费义务人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之间具有潜在的受益对价或者利益关联。〔116〕参见岳红举:《〈预算法〉视阙下政府性基金的法律规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7 期,第80 页。(4)专款专用:此为政府性基金区别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最大特征,也是设立政府性基金的基本要求。〔117〕参见熊伟:《专款专用的政府性基金及其预算特质》,载《交大法学》2012 年第1 期,第70 页。目前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在规范层面还缺乏法律授权和一系列的细化规则,如果以政府性特别基金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机制,将有助于推动和完善公益诉讼的专项立法。此外,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能够通过政府性基金予以明确,比如涉事企业可作为缴费义务人,惩罚性赔偿金专用于实现消费者补偿权、填补公益诉讼支出及其他公益目的。这在域外法上也有例可循,在数额分享制度中,美国部分州便是将被分享的惩罚性赔偿金挹注给政府或法院设立的特定基金。
但是,我国的政府性基金制度也有较多的限制性因素。首先,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依据为法律和行政法规,实行中央一级审批制度,以体现严肃性和权威性,但制度刚性也使得其设立审批很难跟进全国各地公益诉讼飞速发展的需求。其次,出于严格财政监管的要求,政府性基金的支用应与预算编制相符,以防挪作他用,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尤其是剩余资金)的使用需要一定的裁量自由,根据消费维权事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灵活安排资金支用。实践中已经出现检察院设立的食品安全公益基金因为用途不明确而导致支出困难,产生了“冬眠基金”。此外,对政府性基金出于审慎监管的考量,没有保值增值的要求,容易造成资金沉淀。最后,我国政府性基金的法治化程度也不容乐观,收支分离未被严格遵守。征收主体和使用主体虽然形式上分立,但在利益归属上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118〕参见田开友:《政府性基金课征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37 页。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性基金出现了收支“一体化”,〔119〕参见冯俏彬:《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府性基金管理研究》,载《地方财政研究》2015 年第7 期,第18 页。充用于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在内的经常性支出”等情况屡见不鲜。〔120〕参见田开友:《政府性基金课征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40 页。
囿于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水平,不论是通过财政专项资金还是政府性基金管理惩罚性赔偿金,都需要以优化和健全现有财政制度为前提,而财政法治化对制度约束的刚性要求又会与惩罚性赔偿金的灵活分配产生矛盾,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作为财政收入的惩罚性赔偿金在权属性质上等同于国有资产,难以体现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社会属性。在社会法中,除了由政府负责、公共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模式之外,还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形,〔121〕参见金锦萍:《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形式选择——兼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分类的规范意义》,载《当代法学》2018 年第4 期,第15-16 页。在此种模式下,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公益或慈善信托等社会组织的财产也是专用于社会公共事业。负有特定社会法义务主体的财产权属既不同于私人产权,也不同于公共产权,而是一种专属于社会法领域的社会产权。社会产权是控制权与剩余利益索取权相分离的一种产权形式,控制权由负担社会法义务的主体享有,而剩余利益索取权由特定范围的社会公众群体享有。社会产权不适用国有资产规则,但适用社会法上的特殊财产规则,包括使用目的限制、禁止利益分配、保值增值、强制性年度公益支出等规则。〔122〕参见金锦萍:《寻求特权还是平等:非营利组织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兼论“公益产权”概念的意义和局限性》,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 年第1 期,第1-15 页。在社会产权的独立性意义上,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主张,例如“社会保险基金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权属性的财产,是属于特定社会成员共有的财产”。参见黎建飞、谢冰清:《公权视野下社会保险基金权属问题之审思》,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4 期,第65 页。同样观点,参见彭丽萍:《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58-59 页。
社会产权作为社会法的基本范畴,可以明晰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属安排。由社会产权所界定的惩罚性赔偿金不再具有公法债权属性,能够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相区别,从而解决一事不二罚的合法性难题。在公益诉讼的语境下,社会力量的参与本就薄弱,引入社会产权符合社会共治的政策倡导,由社会组织承担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职能,在专业性、亲民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独具优势,在社会产权治理结构中履行社会监督义务的主体也能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123〕参见王名、贾西津:《试论基金会的产权与治理结构》,载巫永平主编:《公共管理评论》(第1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2-123 页。消协组织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的对商品和服务负担社会监督义务的社会团体,也是消费公益诉讼的另一适格原告,适合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机构。但是消协组织又不同于民间意义上的社会团体,而是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消协组织的经费开支也要纳入国家财政统筹。〔124〕参见孙颖:《“消法”修改语境下中国消费者组织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4 期,第87-89 页;金锦萍:《消费者协会法律地位再探析》,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3 年第3 期,第25-29 页。如果比照财政拨款管理惩罚性赔偿金,则等同于适用国有资产规则,与社会产权的属性和优势相背离。因此,更合理的组织形式是消协组织设立基金会或公益信托。这一理论构想已获得实践支持。2022 年3 月上海市消保委牵头成立了首个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专用于支持开展消费维权事业。〔125〕参见陈友敏:《首家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成立》,载《上海法治报》2022 年3 月15 日,第3 版。惩罚性赔偿金可以作为基金会财产,不过因为负担社会补偿义务等特定目的要求,不宜与基金会的一般财产混同。以往的公益实践有一种做法是将公益信托嵌入基金会,以信托方式在基金会内部设置专项基金,由基金会担任受托人,组建由捐赠人、公益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管委会并制定管理规则,专用于特定公益项目。〔126〕参见金锦萍:《论公益信托之界定及其规范意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6 期,第84 页。专项基金能够发挥信托财产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对偿付被害人后的剩余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功能,对剩余资金的使用可根据基金规则或“近似原则”专用于特定公益事业。不过,设立基金会的要求比较苛刻,运行成本较高,〔127〕参见金锦萍:《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而信托则相对灵活,在不具备基金会设立条件的地区可以由消协组织作为受托人设立公益诉讼信托,依据社会产权的基本原理和公益信托的法律规定,专用于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
(三)国家职能:能动司法
与一般诉权不同,社会法上的诉权通常秉持相当的司法克制,〔128〕不过,司法在社会权的法律续造上也有突破克制主义的例外,德国社会法院就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由司法确认并执行、实现权利“可诉性”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具体介绍,参见娄宇:《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可诉化”的突破——德国社会法形成请求权制度述评与启示》,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122-130 页。这是因为特定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权利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状况,司法权无权干预国家给付关系,应由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决定公共资源的分配。〔129〕参见余少祥:《社会法的诉讼机制:特性及其限制》,载《江淮论坛》2015 年第5 期,第18-19 页。不过,前述观点在公益诉讼的语境下并不适用。首先,公益诉讼的胜诉效果即为实现社会权利,在机制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由特定机构履行社会保障义务的国家给付方式。其次,公益诉讼赋予法院主动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职能,在本文论题下即履行分配正义的共同体义务,出于对社会权利的保障,法院有权对资金分配作出裁判。最后,在公益诉讼被告被判处承担惩罚性赔偿时,社会权利的实现得益于对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和分配,无需耗费财政收入。从域外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公益诉讼的功能已经超越了纠纷解决,通过积极的司法能动主义参与社会治理。〔130〕参见王福华:《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2 期,第74 页。因此,在社会法视角下,消费公益诉讼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利保障机制,即通过司法机关的能动司法积极管理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保障和救济消费者的社会权利。
在惩罚性赔偿金分配的美国司法实践上,也曾产生过在欠缺立法的情况下法院能否基于慈善或公益目的主动分配赔偿金的讨论。传统观点对此持否认态度,但新近判例及其支持观点予以肯认:一方面,立法落后于实践需求,且法律也无法为个案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根据惩罚性赔偿应补偿社会性损害的理念,以及惩罚性赔偿的衡平法性质,法院有权主动为其他潜在受害人提供救济。〔131〕See Catherine M.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aw Journal 347, 425-427 (2003).源于前述“Dardinger 案”等代表性判例的治愈性赔偿理论就提出惩罚性赔偿金应用于治愈不法行为导致的社会损害,法院有权对惩罚性赔偿金如何治愈社会损害作出裁判。不同于传统的数额分享制度,治愈性赔偿更尊重原告的处分权,如果原告声明愿意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用于特定慈善事业,则原告须签署一份具有拘束力的协议并交由法庭登记,胜诉后该笔资金的使用将受法院监督。〔132〕See Leah R.Mervine, Bridging the Philosophical Void in Punitive Damages: Empowering Plaintiffs and Society through Curative Damages, 54 Buffalo Law Review 1587, 1637-1638 (2007).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演进表明,美国法关注惩罚性赔偿的社会效益功能如何更好地实现,并强调司法权的能动介入。从我国消费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大量裁判并未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出于分配正义理念和保障社会效益的追求,法院应积极对该事项作出裁判。参照社会补偿理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应作为消费者补偿权的资金来源,分配给食药品安全事件或类似大规模消费侵权事件的受害者。这一事项的审理应有别于确定被告责任的对抗制审查而贯彻协商性司法理念,〔133〕协商性司法是多方主体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纠纷的司法模式。参见唐力:《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6 期,第112-120 页。即由公益诉讼的多方主体开展对话共同协商,因地制宜地确立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模式和分配方案。在管理模式上,参照社会产权理论,应根据本地情况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鼓励通过基金会或公益诉讼信托管理赔偿金。在监督机制的设立上,检察院、消协组织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应积极行使监督职能,具体表现为参与资金管理方式、使用目的等规则的制定,在公益诉讼信托或专项基金中担任监察人,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定期开展监督并向社会公示。在偿付消费者的程序设计上,应尽可能地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已有检察院在获得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胜诉判决后,自主设计微信小程序,只需消费者上传电子消费记录、身份证号和银行账号即可完成债权申报,通过审核后便能获得赔偿,此种简易处理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结论
不同于美国的私人执法模式,我国的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采取的是公共执法模式。在公共执法模式下,司法实践中直接将惩罚性赔偿金收归国库的通行做法凸显了公法债权理论的窠臼,存在一系列合法性难题,不仅难以与我国现行的公法体系相衔接,也无法通过规制公益诉权得到纾解。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需要明晰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依托于私人执法模式的数额分享制度无法直接移植;其次,公法债权的性质界定无法证成政府主导模式的正当性;最后,作为受损方的消费者群体利益应予考量。
数额分享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及其新近理论演进表明,公共执法模式下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应关注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其背后的分配正义理念能够为我国的制度建构提供价值指引。社会法的基本范畴可作为理论资源,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依据、管理模式和职能主体予以界定。首先,对消费者损失的救济应确立社会补偿权,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应优先满足消费者社会补偿权的实现。其次,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属应明确为社会产权,为弥补政府主导模式的不足,可考虑设立基金会或者公益诉讼信托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组织管理形式。最后,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应明晰相关主体在管理和分配问题上的职能,法院应贯彻能动司法和协商性司法理念,检察院、消协组织应积极履行监督职能,共同建立高效的分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