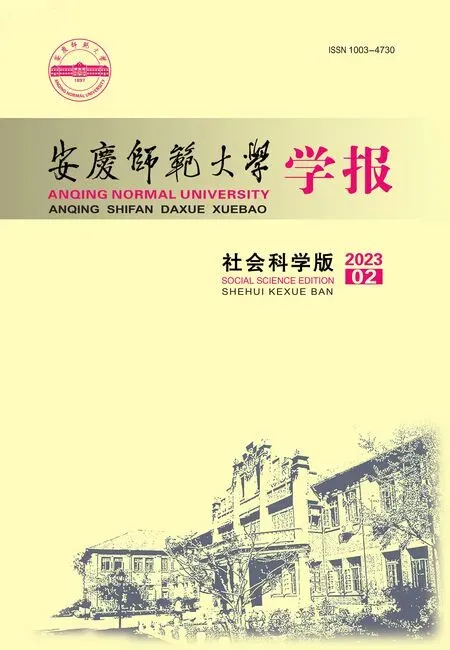“格致”新说:方以智对传统“格物致知”的贯通
聂 磊
(1.安徽大学 道家文化研究所;2.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格物致知”是《大学》修身八条目之始。自宋明理学后,“格物致知”便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尤其是经过朱熹、阳明新的诠解后,“格物致知”的内涵也有了新的不同理解。处于明清之际的方以智,面对晚明学术风气崇虚蹈空之流弊,发出“拘者外理于气,而执其名;荡者执一,而荒逞矣”[1]22的感叹。故而方以智试图突破传统宋明理学对“格物致知”解释,寻求新的“格致”说。方以智所言“格致”是对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升华与突破;以往的“格物致知”或是向外格物理、或是向内格本心,然多侧重于心性功夫论层面。而方以智“格致”说则是从“格物”之格的新内涵、“心物互格”的功夫新路向,以及“不落有无”的新指向等三个方面体现对传统心物关系的突破与超越。
一、格合内外:方以智“格致”说的新内涵
方以智所言“格致”,在于对所格之“物”内涵的延展上,在《一贯问答·问格致》中,方以智有言:“心一物也,天地一物也,天下国家一物也,物格直统治平参赞,而诵诗读书、穷理博学具在其中”[2]39。内在之心性也是一物,宇宙天地也是一物,天下国家之具体事物也是一物,格物能够统领治国平天下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可见“格物”之物不仅指具体之物,更延展至宇宙天地、天下国家。对此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亦有言:“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里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3]自序。从外在事物的层面而言,所格之物即是指具体事物,如所见所用之事、制器利用之物。进而言之,器具有“因其表里以治其心”的作用,那么从在内心性的层面而言,所格之物也包含“治其心”之心、内在性命,进一步推扩而言,天地也是一物。基于此,方以智所格之物包涵外在“所见所用之事”与“制器利用之物”,也包涵内在之心、性命,并包涵宇宙天地。方以智之所以将天地间一切事物含摄于所格之物的范围,在于其致力于扭转明末崇虚蹈无的空谈学风,以期树立崇实的学风。方以智这种“‘崇实’的格物观既是针对阳明后学蹈虚离器之弊,亦是受到西学冲击所带来的影响”[4]。
“格合内外”是方以智赋予传统“格物致知”说的新内涵。方以智提出的“格致”说主要从哲学理式、理气关系、格物对象、致知目的等四个层面对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内涵进行新的改造与突破。传统儒学中对“格物致知”说内涵的解释主要以朱熹和阳明两派为代表。朱熹主要以外求格物为主要诠释路径;阳明主要以内求格心为主要诠释路径。在方以智看来,这种理学和心学二分的传统诠释路径,并不是最佳的“格致”说,故而方以智基于其圆∴哲学理式,给出新的诠释。
首先,就哲学理式而言,方以智立足于圆∴理式,提出“格合内外”。内外即是圆∴下方左右两点,格即是上一点。以格统摄内外,内外即是内在心性与外在事物。诚如方以智在《一贯问答·问一贯》中所言:“一多相即,便是两端用中,举一明三,便是体统相用。若一多相离、体用两橛,则离一贯之多识”[2]34。“格致”所言格物即是内外相互贯通的,并非对立二分的;方以智从其构建的独特哲学理式为基点,试图折中朱熹与阳明对“格物致知”诠解的分歧。“格致”说在方以智那里呈现出一种贯通的新解,既是格内在心性的性命之学,又是格外在事物的物理之学。此二者亦非彼此对立的,而是统摄于格物之内,内在存有一个“一”将其贯通起来。如此“格合内外”的“格致”说即是对传统格物致知的突破。
其次,就理气关系而言,由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理先气后”的理本论逐渐式微,而“气先理后”的气本论渐渐成为主流认识。方以智“格致”说是建立在“气先理后”的基础之上,这与朱熹、阳明的“格物致知”说的立论基点不同,传统“格物致知”说是建基于理先而气后的认识之上,如朱熹所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5]1。阳明虽然以内求格心,但是阳明亦指出心即理。可见,朱熹与阳明在理气关系上有着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都承认理先而气后的理气关系。方以智则认为“生理在生气中”[1]22,理只是气之中的条理,而非将理作为本原意义上的存有。就方以智“格致”说所立足的理气关系而言,方以智赋予了“格致”说新的内涵,并将“格致”说建基于气先而理后的基础之上。
复次,就格物对象而言,方以智主张格物不仅是格外在物理之学,也格内在心性之学。如上文所言,方以智将所格之物的外延和内涵皆做了扩充,格物的对象既包涵外在“所见所用之事”与“制器利用之物”,也包涵内在之心、性命,并包涵宇宙天地。这与朱熹所言格物对象仅指具体可见事物不同,朱子所言格物是在于向事事物物上外求,穷尽一物之理,诚如朱熹所言“所谓格物,只是眼前处置事物,酌其轻重,究极其当处,便是,亦安用存神索至!只如吾胸中所见,一物有十分道理,若只见三二分,便是见不尽。须是推来推去,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5]294。“格物,是格尽此物。如有一物,凡十瓣,已知五瓣,尚有五瓣未知,是为不尽。如一镜焉,一半明,一半暗,是一半不尽。格尽物理,则知尽”[5]295。朱熹认为格物即是格尽物理,将一物之理推究到极致,完全穷尽其中道理,才是知尽。阳明认为格物岂能在外物上寻求,在于自己心念上格。如阳明所言:“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6]。可见,阳明所言格物是指格除内心不正之念,这是将格物之对象视为心念,在心性层面上直接格物,所格之物亦是指内在心性。这与朱熹格物的进路不同,朱熹则是将外在具体之物作为格物的对象,阳明即是将内在心性作为格物的对象。方以智认为格物之格是“至也,方也,正也,通也,感也,有‘格君心’之格义”[2]39,可见,方以智将朱熹之外向格物而穷其理与阳明之内向格心而致良知的路径,皆含摄于“格合内外”之中。方以智格物之格是“格合内外,则心物泯矣”的贯通之格,而非理学与心学不同路径的彼此对立的格物。
最后,就致知目的而言,方以智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依然是穷其理,不过这个“理”已然不同于传统儒学所言之单纯的天理,而是一分为三之理,以至理统摄物理和宰理。至理则如圆∴上一点,物理和宰理则如左右两点。方以智指出“儒者不得已而以‘理’呼之,所谓至理统一切事理者也”[7]448。“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例、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8]。可见,方以智所言之理不仅含摄传统儒学的心性之理,更延展至客观事物之理;既格致内在心性之学,又格致外在物理之学,最后统归于至理,至理是含摄宇宙万物与成德成己的一切理的公理。
基于此,方以智以“格合内外”重新诠释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内涵,从其独特的圆∴哲学理式、理气关系、格物对象、格致目的等四个层面重新诠解“格致”说新内涵。方以智提出的“格合内外”即是外格于物,内格于心。心物内外皆是格物所格之对象,物理、宰理皆是致知所致之理。
二、心物互格:方以智“格致”说的新路径
方以智“格致”说探寻的新路径在于“心物互格”这一独特的路径。方以智所言“心物互格”旨在打通心物的二元对立,正如所言“物物而不于物,格物物格,心物不二,即可谓之无物,无物即是无心。践形、复礼、博文,具是打通内外,不作两橛”[2]39。格物但不拘泥于物,不为具体之物所束缚,要以物为我所用,格物之目的在于贯通心物,打通内外,不做对立、两橛二分。方以智“格致”说指出无论是格具体物理之学,还是格内在心性之学,当以心物不二为原则。正是基于“心物不二”,方以智以“心物互格”破除朱熹和阳明格物各执一端的传统“格物致知”说。如上文所言方以智认为“格物”既包含朱熹外向格物理,也包含阳明的内向格本心。在论及“心物互格”时,方以智依据其“先天即在后天”的易学哲学思想指出:“举先天未分前,以格先天已分后,知此已分前知天地。一在二中,彼此互格,即无彼此”[7]356。这里先天即为心,后天即为物。在心与物彼此互格之下,心与物的分别对立也随之泯灭,可见,方以智所言“心物互格”并非是心物分别对立,而是心物不二的。
基于“心物不二”的心物关系,“心物互格”的新路径不仅是对朱熹与阳明的“格物”的融合与突破,也是对同时代“格物”说的纠偏。如与方以智同时代的王夫之则以为方氏“格物”是专言物理之学,如其所言:“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9]。王夫之只看到方以智父子倡导实学风气,便误以为方氏“格物”是专言格物理之学的质测之学。其实,如上文所言,方以智“格致”说是含摄外在物理之学与内在心性之学的“格物”,并非专言一偏,偏于物理之学。王夫之所言“格物”则是专指质测之学,就外在物理之学层面的格物,并以为邵雍与蔡元定以理格物不是“格物”。方以智对此直接指出:“此格物乎?曰:一端也。……或分物理之学、性命之学,曾知性命亦一物理耶。今所言者,一气之质测也”[7]355-356。质测之学只是“格物”的一个维度,并不能完全代表“格物”,方氏所言“格物”是对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的双重格物。同时,也指出回应王夫之所言“格物”仅是在气上言,是物理之学层面的格物。
“心物互格”在心物关系上即是心不离物,物不离心,亦可称之为心物不离。方以智基于心物不离的哲学论述,探寻其独特的“心物互格”之“格致”说新路径。心虽然是物的一部分,但心在天地万物之中却有着主宰意义,心不是单纯的心胞之物,而是思维意识的存在。如方以智所言:“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万物,知其原即尽其性矣”[3]2。心与物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心能感通天地万物,即是以心格物。方以智又指出:“舍心无物,舍物无心,其冒耳”[3]10。万物与心之间同样存在内在关联,离开心则无法感通物,离开物则心之主宰作用无法见诸于物。心物不离、心物互格,正是方以智“格致”说开创的新路径。在方以智看来,心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依存性和互摄性。
方以智所言“心物互格”旨在强调心物之间融通无二,并非彼此对立。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思潮中,西方物理知识逐渐为当时学者所了解,这种思潮虽然有助于推动崇实学风,但却容易造成心物彼此的二分,从而忽略致知的目的之所在,容易陷入心物两橛的对立境况。故而,方以智以薪火为喻指出:“天载于地,火丽于薪,以物观物,即以道观物也。火固烈于薪,欲绝物以存心,犹绝薪而举火也。乌可乎?”[10]172“心”固然是格物的关键所在,但是离开物而专言心,则犹如离开薪而言火。同样,“格物”若是离开心而专言物,则犹如离开火而言薪。心虽然不能独立存在于物,但物离开心则是单纯的物理意义存在,方以智主张“心物互格”正是对西学东渐思潮之下的心物二分的纠偏。关于心物不离,方以智还从心与意、知,意、知与物的关系中指出:“心以意知为体,意知以物为用,总是一心;离心无物,离物无心。但言心者,包举而不亲切;细推及意,又推及知,实之以物,乃所以完全知分量而明诸天下者也”[2]38。可见,在心物关系中心以“意知”为体,“意知”又以物为用。当心见诸于“意知”之上时,才是心之体的呈现。当“意知”见诸于物之上时,才是“意知”之用的呈现。无论见诸于“意知”还是见诸于物,都归属于心。方以智所言心物不离即在于此,如若只就心而言,则仅推及到“意知”的思维层面;无法将“意知”见诸于物,那么,所言心也只是虚妄的存在。心不离物,即是内格于心要见诸于物,物不离心即是外格于物要建基于心。如是,则如方以智所言“因触而通,格合内外”。
基于此,方以智“格致”说的新路径在于对传统“格物致知”进路的突破,在于融合了朱熹与阳明“格物”的进路。朱熹“格物”即是在事事物物上去格物,在外物上寻求一个天理,朱熹的格物更加侧重于知识论的维度;阳明“格物”即是内求吾心之良知,在本心上格物,阳明的格物则偏向于道德论的维度。方以智认为朱熹与阳明在格物的进路上,二者皆所有偏颇,易于造成心物二元的对立;故而提出“心物互格”,心与物互为主体,彼此融通无碍。心能格物,物能格心,心与物彼此都能处于主体的地位;并非只有心或物才是主体地位。可见,方以智对主体地位的互换,其互格亦是主体精神的象征;由心物主体的互通,达到内外贯通,消解心物彼此二元分别的观念。
三、不落有无:方以智“格致”说的新指向
方以智“格致”说的新指向旨在破除心物两橛,破除传统“格物致知”执著于实有一偏的指向。基于此,方以智提出“不落有无”为“格致”说的新指向,以期融合贯通传统“格物致知”说中的朱子与阳明之争。同时,并从内外一贯、绝待、破除分别、归于圆∴等层面来把握“格致”说的新指向。
“不落有无”是方以智“格致”说的新指向,其中内外一贯则是一个重要层面。内外一贯不仅源于孔子的“一以贯之”,还基于方以智“格致”说新路径的探索。在“心物互格”之下,方以智认为格物不仅是要心物相通,还须是内外一贯的。对此,方以智说道:“圣人之几本一,而本不执一,齐圆如珠。朱子曰:‘以一理贯万事。’未尝不是个‘理’字,而圣人不说定‘理’字;分明是‘心’而圣人亦不说出‘心’字。……不能变即是不能权;不能权,不可与几;不可与几,岂可谓之贯!”[2]33就传统“格物致知”而言,方以智认为朱熹的所言天理是能够含摄万事万物,就格物来说,也只是格一个“理”字。与朱熹所言“理”相对而言,即是阳明所言万事万物都含摄于“心”之中。方以智认为这都是对圣人“一以贯之”思想的分别说法,而不是究竟的说法。方以智以孔子“一以贯之”的一贯之道为“格物”的面向,认为“格物”须当贯通内外,切合圣人“本一”的思想。同时,方以智还指出“一贯”须是能变、能权、能几的,贯通内外是鲜活的思想,而非固定的、单一的范式。可见,贯通内外其中所具有的内在生生不息性与内在灵活性;心物互格、内外贯通,坚持一以贯之的内在机理方可达致方以智“格致”说“不落有无”的新指向。
此外,方以智还指出一贯与多并非是矛盾,说一贯时依然含有多,故而说道:“不必回护,不必玄妙,不妨矛盾;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此乃真一贯者也。一贯者无碍也,通昼夜而知;本无不一,本无不贯;一真法界,放去自在。若先立一意,唯恐其不一,则先碍矣!故有为碍所碍,有无碍所碍”[2]34。值得思考的是,方以智对一多关系的深刻认识。基于“一以贯之”的思考,一多关系所指向的则是“不落有无”的一多相贯。“真一贯”是立基于一多相贯、内外贯通、无碍无滞的存在情状中,如其所言,一是大原则,不能先确立一个一,也不能先确立一个多,一在多中,多在一中;“一外无多,多外无一:此乃真一贯者也”。
在“不落有无”的新指向之下,不仅“内外一贯”是其中一个面向。“绝待”以摒除对待也是方以智“格致”说新指向的另一个面向。关于“绝待”,方以智从对待处与一多相较而言。他指出:“一多相即,便是两端用中;举一明三,便是统体相用。若一多相离,体用两橛,则离一贯之多识,多故是病,离多识之一贯,一亦是病。最捷之法,只从绝待处便是。两间无非相待者,绝待亦在待中,但于两不得处,即得贯几。以先统后,即无先后;二即是一,则无二无一”[2]34-35。对待的世界则是落入有无的世界,若要臻至“不落有无”的世界,则须明析一多关系、体用关系、对待与绝待。方以智认为“不落有无”通过对一多、体用的贯通方可达到,一多犹如果核与根干花实,一多是不离的,不能强行分本末,也不能强行分内外;体用是一贯相通的,若是离开了一多相贯而言体用,则体用便是二分的。换言之,一贯与多识是无法分开的,若是单言一或多,则是落入病端。
为此,方以智提出“绝待”,如其所言“后天卦爻已布,是曰有极;先天卦爻未阐,是曰无极。二极相待,而绝待之太极,是曰中天。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而先天即在后天中,则三而一矣”[10]47。太极即为绝待,无极和有极便是有待。如果是太极是形上的绝待世界,那么有极和无极便是形下的有待世界;依据方以智“先天后天”说,“中天即在先、后天中,先天即在后天中”“先天不离后天”,“绝待”并非离开有待,并非取消对待,而是没有对待。方以智旨在强调“绝待”的形上层面,同时也兼顾有待的形下层面;如此“最捷之法,只从绝待处便是”,可见,“绝待”便是方以智“格致”说“不落有无”的新指向。有一点值得注意,“绝待”并不是离开对待,而是超越对待、贯通对待,如同“物物而不物于物”。
方以智以《大学》中“知”字,作为破除分别关捩处;同时“不落有无”的新指向还包涵破除分别。如方以智说道:“大学以一个‘知’字包天包地,原非两个。教家以无分别之真智为般若,以分别之妄识为烦恼,有何异天理人欲之分两边字面耶?化欲之理,即统理、欲之天理,层楼乃是一屋,分别即是无分别,可了然矣”[2]39-40。“知”则指“知止而后定”与“格物致知”中的“知”字。在方以智看来,“知”是包天包地的一贯原则,并引证佛家以无分别为真正的智慧,无分别才是般若大智慧,有分别即是烦恼障碍。般若智慧与烦恼妄想如同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格物致知”之“知”即是化欲之理,是统摄物理和人欲的天理;方以智所言天理是“不落有无”的绝待之理。可见“格致”说的新指向即是“不落有无”,不落分别,破除分别,达到贯通的境地。
“不落有无”的新指向还包含方以智指向圆∴的哲学理式,构建独特的哲学范式。方以智构建的圆∴哲学理式正是“不落有无”的内涵之一,如其所言:“合看圆∴之举一明三,即知两端用中之一以贯之,则三无非一而无非中,四不得中,无五无非五矣。透过大易之一多相即,与华严之阴阳互参,则可有六经、五灯作家常伎俩矣!然未大透彻得到‘由己’天地,则捉个不落有无,捉个无所得,依然是病。”[2]36“不落有无”所包涵的圆∴正是,其上一点,无与有则是左右两点。“不落有无”的内涵如上文所言,包涵内外一贯、绝待、破除分别、归于圆∴,从圆∴的哲学理式高度上来看,“不落有无”则是“举一明三”,方以智所举之一即是圆∴的上一点,这是超越有无的的存在;“不落有无”也是不作两橛、绝待、破除分别,内在指向“知两端用中之一以贯之”的内涵。同时,方以智又从易经中八卦之三爻本于阴阳与华严宗六相之三组本于阴阳①华严宗法界缘起的次第开展,“一真法界、理事二法界、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等与《周易·系辞上》所揭示的宇宙生成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有着相近的逻辑体系。其中华严宗“六相圆融”说的总相、别相为一组,同相、异相为一组,成相、坏相为一组;六相中的“三组”与八卦中的“三爻”相近,六相之三组本于阴阳,八卦之三爻也本于阴阳,六相导向圆融中道,八卦则导向圆通中道,二者在根本上可谓异曲同工。故方以智以易经与华严之阴阳互参引证“不落有无”。二者相互参校,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而执著于“不落有无”的这个文字意义,反而易于落入弊病之中。“不落有无”是达到“由己”的境界,内在于外在自然贯通,内外一以贯之,同时也是摒除对待、破除分别的境界。
因此,方以智“格致”说的新指向在于“不落有无”,然“不落有无”又内在包涵内外一贯、摒除对待、破除分别、归于圆∴等四个内涵。此外,值得思考的是,方以智在《一贯问答·问格致》中,特意提出《中庸》的内外一贯,如“中以内摄外,庸以外摄内;无内外而不坏内外,乃为中庸。”[2]40将也中庸含摄于“不落有无”之内,简而言之,“不落有无”即是不落如分别对立的偏执一端中,贯通内外、一多、对待的分别,超越于有无之境,归于圆∴上一点。
综上所述,方以智在传统“格物”之物的基础上,对“物”进行新的内涵赋予;将传统“格物”之“物”在外延上赋予西学物理知识,在内涵上融合外在物理之学与内在心性之学,在此基础上突破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内涵、路径与指向。进一步而言,方以智“格致”说的理论基础是其独特的哲学圆∴理式,在这一理式构架之下,方以智背后的深层问题意识实际是在面对王学末流“舍物言心”与西方物理知识及其天主神学对中国传统“格物致知”说的冲击之下,思考传统儒学如何应对明末“崇虚尚无”的学风与西学东渐的冲击。方以智基于其圆∴哲学理式,提出“格合内外”“心物互格”“不落有无”的三个层面,重新诠解传统“格物致知”说。另有一点值得思考,方以智“格致”说的新指向最终指向“不落有无”,这与方以智以往对圆∴理式的诠释不同,是落在上一点,而非落在右下点。可见,方以智思想的内在转变,其贯通与超越的思想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