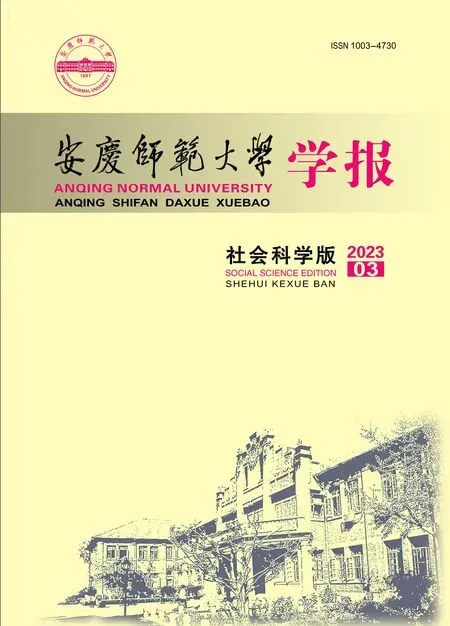戴钧衡与桐乡书院
李宜江,张 妮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桐城派中期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味经山馆文钞》《味经山馆诗钞》《蓉洲初集》《草庐一得》等作品。戴钧衡早年恃才傲物,后读方东树《昭昧詹言》恍然大悟,感慨道:“二十七,从游植之方先生,始知所作皆非。”[1]370于是拜师方东树,潜心学习。戴钧衡关心桑梓教育,振兴当地文教事业,与乡里友人共同创建了桐乡书院,并在书院内践行其教育主张。他还与友人共同整理乡贤书籍,发扬文派门楣,收集戴名世的遗作并整理成《谦虚先生文集》,收集桐城文人的著作并编撰重订《古桐乡诗选》《桐城文录》《望溪先生文集》,使得桐城派得以重新发展。后世评价“此数十年间,桐城之文得以不坠者,殆皆此辈之力也”[2]。咸丰初年,贼寇犯县,戴钧衡暂避舒城,妻妾留守故土。在临淮请兵期间,远在异乡却听闻妻妾遇害,愤懑之郁交织于心间,最后早亡。好友曾国藩听闻后感慨万千,“送戴存庄之侄银五十两,为存庄葬事之用”[3],并亲自题写“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
一、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创办
桐乡书院现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的孔城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明清时期,孔城镇与桐城境内的枞阳、汤沟、练潭并称“四大古镇”,桐城城中建有毓秀书院、桐阳书院等多个书院,供学子进行学习。据《桐乡书院志》记载,清道光六年(1826)桐城西乡天成书院建成,北乡的伍姓贡生提议在北乡兴建书院,并率先进行捐金却鲜有人响应,兴建书院的提议遂无疾而终。同时北乡学子众多,经常需要前往他乡的书院进行求学,面对“生邑地广,向分四乡,城中及西南两乡俱各建有书院,惟生等北乡独无”[4]1011的教育窘境,使得乡里的有志之士皆感痛心。“岁庚子夏,诸生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复兴斯议。”[5]715戴钧衡他们希望创建北乡的书院,造福本地学子,振兴本地文教。因北乡在汉代时被称为舒县桐乡,故书院取名桐乡书院。
兴建书院的提议一经提出,得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由于当时书院筹办面临资金短缺等问题,为此,戴均衡等人为筹建书院积极奔走,号召本乡周围地区的民众为书院的创建进行捐资。同时请求官府发布劝捐示,兴建书院的做法很快也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愿意帮助他们发布劝捐告示,“仰北乡各保绅士庶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书院为振兴文教之要务,所需工费浩繁,不能不做集腋成裘之举,务各踊跃捐输共襄善举”[5]717。当年秋,书院的募捐工作得到桐城乡人的热情支持,富家大族们纷纷慷慨解囊,为书院的筹建贡献钱财。即使是贫寒家庭没有捐钱捐物,也积极响应号召予以声援,戴钧衡的好友王祜臣出生富贵豪门,就曾重金出资来支持好友的义举,“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1]418。书院创建之初就募捐到大钱9 000 串零9 820 文,造建房屋5 幢,购买田产若干[6]。《桐乡书院志》将重视教育、乐于捐助人士的姓氏和金额都详细如实地记录了下来,据现代学者张晓婧统计,“道光二十一年(1841)共有244 位,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有370 位,道光二十三年(1843)共有283位,道光二十四年(1844)共134 位”[7]。可见当时民众对创办书院的热情。根据书院留存的图纸可以看出,书院建筑宏大,建有五重门,有朝阳楼、漱芳精舍、旷怀园、藏书阁等教学建筑。书院的建设名称蕴含着创建者的美好宏愿,因其书院内有梧桐树,戴钧衡便把生徒学习的地方命名为朝阳楼,认为“朝阳者,始生之日也,与今书院创始之义亦合”[5]764。他希望学子能够凤鸣于朝阳,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桐乡书院建成后,戴钧衡还积极邀请友人前来参观指导,为桐乡书院撰写文章,提高书院的声望。当时桐城派名人姚莹、方东树以及通政大夫罗惇衍等人均为书院写过记,姚莹就曾写道:“道光甲辰,余过孔城,戴生钧衡邀观之,……戴生乞一言以志其成,诺之,而未暇也。明年方使西域,而生以书来趋之,乃举气运赖人之说,以告此乡之有志者。”[6]罗惇衍也曾接到过训导马国宾为桐乡书院作记的请求,但因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迟迟未写,“庚戍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8]71。才使得《桐乡书院记》一文完成,该文镌刻于碑,以此激励学子,该碑仍现存于桐乡书院旧址之内。
咸丰三年(1853),桐城遭受兵灾,桐乡书院未能幸免。同治六年(1867),乡人共同购买程姓屋宇,将其房宅改建成书院。受洋务运动兴办新学的影响,清政府下诏进行书院制改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桐乡书院改建成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清末停办,后为孔镇中心学校旧址。
二、戴钧衡对桐乡书院的管理
中国古代书院的管理多由书院山长直接负责,戴钧衡作为桐乡书院的创办者,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其担任过桐乡书院山长,但作为书院创办者,书院内实施的管理措施为他所制定或认可,侧面反映出其书院管理思想。桐乡书院建成后不久时人就编撰《桐乡书院志》,其书共有六卷,为舆地、剏建、章程、乐输、产业、艺文。其中戴钧衡《桐乡书院四议》一文更是被收录在艺文卷中,戴钧衡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关于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的教育理念。现存于桐乡书院旧址内的碑文同样证明当时的通政大夫罗惇衍在看到《桐乡书院志》中戴钧衡《桐乡书院四议》一文后,担心其教育思想仅为戴钧衡或戴钧衡好友一二人认可,未必人人能信服,“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8]72。后来这篇《桐乡书院记》被镌刻于碑,放置于桐乡书院内,供学子观摩。由此可见戴钧衡的办学理念对桐乡书院的管理影响很大。桐乡书院的管理内容,主要涉及到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经费管理、设施设备管理以及书院运行的管理体制等方面。
(一)教学管理:灵活严谨,宽严得体
桐乡书院教学管理包括周密灵活的教学计划、严格详细的考试制度、教化师生的祭祀活动等。
1.周密灵活的教学计划。书院教学计划为书院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戴钧衡在管理桐乡书院时,与书院董事共同商议制定《桐乡书院章程》,章程对书院教学作出详细安排,提出“每岁大课春秋两次,小课俟当年酌定。春课定期每月十五日,秋课定期九月十五日”[5]724。可见,书院每年组织两次重大考试。除基本的教学安排外,还要求“先期半月,值年董事会同常董,禀请邑尊于课期前一日按临书院”[5]724。同时还要求书院的董事和值年董事须前五日齐集书院办理相关事务,书院的副董更是须提前半月到院办理前期准备工作。这种预备性和计划性的管理特点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书院规定其他考试根据书院当年的实际情况另行决定。
2.严格详细的考试制度。在考试类型上,书院考试可分大课和小课,大课按时间分,为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举办的春课和农历九月十五举办的秋课,其小课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再行决定。在考试内容上,为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在考试组织实施上:一是考试前期工作,书院董事须提前一个月将考试信息贴榜告知考生并提前前往书院内进行筹备工作。二是考试具体规定,书院要求士子衣冠佩戴整齐,不准有辱斯文,考场的座位人数也有规定,考试当天书院考生随到随进,进入者不准随意外出,考试交卷人数达到三十人,可开放书院门户,此后随时交卷随时走人,已交卷者不再入书院。考试公平体现在考试出题和阅卷的保密上,书院规定“文诗题董事预请邑尊拟定封固,临日于讲堂开拆。次日将各卷包封送县,以凭甄别甲乙。……其决科课卷,用弥封,坐号浮票各自揭去”[5]725。三是成绩公布,书院董事将其贴于书院的门首之处,方便生童知晓成绩,及时领取奖赏,查取试卷。
3.教化师生的祭祀活动。在书院祭祀的对象上,戴钧衡指出孔子等先贤大儒已在学宫内祭祀,书院祭祀当地乡贤即可。为此桐乡书院以朱熹、何唐、方学渐以及方苞、姚鼐等人为祭祀对象。戴钧衡希望达到“其将使来学者,景仰先型,钦慕夙徽,以砥砺观摩而成德。而亦使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于其间”[1]378的目的。在桐乡书院祭祀次数上,戴钧衡指出一年举办两次,“山长春秋择日,率诸生行祭,又于月吉月望”[1]378。观摩瞻仰先贤,从而实现激发士子见贤思齐的使命。
(二)教师管理:德才兼备,榜样示范
戴钧衡主持桐乡书院时,针对当时山长疲癃充数、品行不修、鱼龙混杂的社会风气,阐述自己在教师管理上的理念,并专门论述如何择山长,提出从知识、道德、行为三个方面来选聘与管理教师,即经明行修的知识要求、老成硕德的道德规范和与生同居的榜样示范。
1.经明行修的知识要求。戴钧衡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书院山长志向鄙陋的现状,“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1]378。很多书院山长在清朝统治者手中沦为谋求钱财、相互贪污的工具,不问其品行高低而聘请。戴钧衡在筹办桐乡书院时,指出聘请“山长由董事及诸生议,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不由官长推荐”[5]727。他认为只有老师具有经学和道德方面的知识涵养,才能给学生以指引。他痛批当时一部分学者没有真才实学,却虚假宣传自己通晓五经的行为。可以看出戴钧衡在对教师的选聘上是十分严格的,在当时山长多是庸陋之人的社会现状下,依然能够保持经明行修的知识要求,聘请有真才实学之师来担任书院山长。
2.老成硕德的道德规范。在主管桐乡书院时,戴钧衡强调山长的德行是非常重要的,他拿选聘童子师重视师德来类比,指出人们在选聘童子师时,尚且考察教师的学问德行是否优良,何况偌大一个书院选聘山长,因此选聘教师更需注重师德。他批判当时清末部分山长滥竽充数,与官府勾结一气,指出他们“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其所聘为山长者,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1]377,这使得有些书院的山长是通过与创建者关系紧密,或者托人请办等方式上任,并非凭借着其知识水平和品德。他批判书院管理者在选拔山长时不讲求学问深浅、品行高低,单纯听从官府指派的行为,致使书院聘请一些无德无才之人。为此他非常注重教师的道德水平,认为只有山长拥有高尚的道德,才会使得学生心悦诚服地向其学习,他认为“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众而慑世,则人岂乐从之游?”[1]378可见当时书院颓疲的状态,戴钧衡依然能够在选聘山长和教师时对其品行、德行保持重视,坚守他的教育初心。
3.与生同住的榜样示范。面对当时清末世风颓败,学风与日俱下,很多山长只是徒有虚名,并没有承担书院的教学工作,面对有些书院山长甚至常年不入书院,担山长一职,只为求取修金,甚至还有代取转付的方式,戴钧衡感到十分痛心,批判那些不到院而教的山长,指出孔子这样的圣贤尚且不能够做到隔空教学,一些山长却希望不到院而教导众生。为此戴钧衡提出“夫为子弟延师,必将使朝夕与居,亲承讲画,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资效法”[1]378。戴钧衡要求教师做到与学生朝夕相处,亲承讲画,发挥好师者的榜样示范作用。
(三)学生管理:品学兼优,逐步激励
历代书院都看重对学生的管理,戴钧衡同样重视学生管理,为此他提出经学为先的学习内容、品学为先的考核方式以及优秀学子的奖励政策。
1.经学为先的学习内容。清末受八股取士的科举影响,书院出现追求时文帖括来获取科名荣誉,而不注重学习经史故籍的学风现状,戴钧衡痛批科举考试存在的诸多弊端,他认为经学是万事学习的基础和根本,为此在桐乡书院时他提出经学的教学内容,然而想要扭转当时学风,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他提出“处今之时,而欲修明经学,非徐而引之,渐而入之,其势不能以骤转”[1]380。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引导、激励学子进行经学学习。他指出学生应该通其经,明其道,如果“不此之务,而徒从事于揣摩得失剽窃影响之为,则吾未见其出而实有裨于世也”[1]378。当时的通政大夫罗惇衍夸赞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实属难得,指出当时能“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见焉”[8]71。
2.品学为先的考核原则。受清末科举制度的影响,出现了“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9]的教育现状。他反对当时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观,认为学生应该潜心学习,培养高尚品德,他提出“则惟深之以学问,践之以躬行,然后发之皆德音,不必以文名也”[1]402。桐乡书院对学生的考核除了要求品学兼优之外,还考核学生的解经、律赋、四文书、试贴等,同时书院章程里还提出:“经解、诗赋最为士子要务,每月必请师于文题外更发此题,各士子务宜留心讲习,此于文卷外另行甄别甲乙,录取者,另给奖赏。”[5]728可以反映出桐乡书院对士子的经解和诗赋能力的重视性。
3.优秀学子的奖励措施。戴钧衡面对当时学风不振的文化氛围以及桐乡书院经费不足的现实状况,提出逐级奖励的激励政策。戴钧衡提议:“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金,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1]380同时书院详细记录了生童奖赏规定,考试“录取一名者,奖赏纹银一两,二三名各八钱,四五名各六钱,六七八九十名各四钱,以后无赏”[5]725。可以看出桐乡书院侧重于优秀学子的奖励,以及实行不同成绩水平不同奖励的差额奖励制度,有助于激发学子的学习热情。同时,桐乡书院也进行实物奖励和精神奖励,“考名列前茅者,奖赏纸笔若干”[5]728。书院对优异的文章进行汇编刊刻,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子的学习激情和动力。
(四)经费管理:独立自主,详实透明
书院的经费是书院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戴钧衡的经费管理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多种多样的经费来源。清末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采取通过拨款的方式来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面对当时这种局面,戴钧衡积极寻求多渠道来筹措经费,请求官府发布劝捐告示,受到了当地里人的热烈响应,“殷富有力之家,各皆踊跃”。一般家庭“虽不尽踊跃争先,亦可谓尚礼义轻财货”[5]721。面对筹集到的书院经费,戴钧衡及书院董事们并没有坐吃山空,书院规定:“逐年董事必须留其有余,以筹积增产。或有宜购之田,现存钱财不足,即借贷补凑,逐年以存余偿还。但必须量事而行,恐妨尾大不掉。”[5]728“将此课存余之赀,或添设小课,或留为蓄积,增置田产。”[5]728通过筹集置办书院产业或购买书院田产来收息和获取收益,倡导多渠道筹措书院经费,减少对乡人捐赠的依赖。
2.明确详实的经费开支。桐乡书院对各项开支进行明确详实的规定,上到邑尊开课的费用,下到柴房小斯的各种开支都有规定其规格大小、金额多少。按照人员来分大概有三类:一是县令主持一次春秋大课时所需要的一系列人力、物力费用。对县令以及其马夫、挑夫、家丁等人工资给予明确的规定。对其伙食也有详细规定,如“惟开课本日午席从丰,其余俱用便席。至家丁中席,开课日亦稍从丰,其余毋得过六簋。茶房、探听、听事、轿头诸役饮食毋过四簋”[5]724。可以看出县令一次讲课所需费用项目虽然繁杂,但是数额都有详细的规定。二是董事协助管理书院的补贴。书院规定:“董事因公聚议书院,饮食毋得过四簋。一人只许携带仆从一人,且必能为书院任事,方准在内食宿。其舆夫只给便饭一顿,即行外出。”[5]726可以看出董事们的伙食标准远不及邑尊的规格高,体现书院管理上的节俭。董事每年一次性支取八折银二两用于办事的路费,对那些自行贴费的董事,为其刻碑用以嘉奖其德行。三是奖励学生勤奋学习的费用。书院对学生勤奋学习的奖励主要是根据学生掌握经书的数量来奖励学生膏火,或者是奖励在课卷中名列前茅的学子。前文已提到一部分,相似部分不再赘述。
3.规范透明的经费公开。“书院的办学资金出于公众,公众势必关心这笔投资的‘效益’,对其实行舆论监督,并行使实际的管理,即择人任董事或监院、首事,督促书院的教学及其他活动的开展。”[10]桐乡书院实行的是经费公开制度,方便众人监督,桐乡书院将其各项开支进行详细规定,要求“每年交账之日,所有上年出入一切账目,务要逐项录明出榜,使众共知”[5]725,比如在学生学业奖励的费用上,还规定“闱后给散旋里,即将所散名数若干列榜张贴书院门首,以杜侵渔徇滥之弊”[5]727。同时书院还实施多台账本制保证经费的规范,防止贪污侵占。桐乡书院对各项事务开支进行明确规定并公开张榜,供众人知晓,保证了书院的经费透明化和规范化。
(五)设施管理:统合资源,规范使用
书院的各项设施设备对于书院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桐乡书院关于设施设备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书院藏书聚之以观。戴钧衡认为书院应该广泛藏书,他指出:“昔宋太宗、真宗之世,凡建书院,有司必表请赐书。江述之于白鹿洞,李允之于岳麓,皆是也。”[1]381面对当时繁多的书籍,戴钧衡忧虑道“故吾以谓人不患不能读书,患所读之非其书。”[1]381他赞赏乾隆年间朝廷给各郡县学官颁书,让贫苦子弟就近去学宫里读书的做法。书院本是藏书读书之所,却慢慢沦为科举的附庸品,面对这种局面,他批判当时书院“近世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1]381,认为藏书是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为此,他想要“今窃欲取此义,奉行之于书院之中”[1]381,让书院藏书可以实现聚之以观。
2.书院器物分类载明。由于桐乡书院是乡办书院,书院各项资产来之不易,为此,戴钧衡在管理桐乡书院时就十分注重书院各项资产的维护和管理。书院规定“书院器物,逐一分类载明器物总簿”[5]727。将书院设备登记造册,有利于对书院各项资产进行统一、明晰的管理,节省书院的经费开支。同时书院建立定时核查制度,要求“每年董事必要稽查,有损必修,有阙必补”[5]727。有效避免他人侵占书院财产。同时书院内还实施严格的交接审查等措施,书院规定“开课之际,董事尤须择一二精明谙练之人稽查收捡,防有失脱,每年董事交卸之际,亦必照簿查明,不可疏忽,外人不准借用”[5]727。这些措施有效地避免书院内部贪污腐败、侵占书院财产等现象的出现,保障书院的日常运行。
(六)管理体制:行董事制,民主规范
戴钧衡作为书院的创建者,全程参与到桐乡书院的管理建设中,桐乡书院的管理体制是在他的领导下实施的,是其书院管理思想的实践体现。
1.董事会的成员组成与任期。《桐乡书院志》对书院董事的组成成员与任期等有着明确规定。规定:“书院董事议定多人,内以数人为常董,十六人值年,每年四人,轮流更换。”[5]725书院章程还要求董事会中常董数量为二个人或者是四个人皆可,不需要逐年进行人员更换。这样的人员设置有助于保证不因人员流动频繁而导致书院内的制度朝令夕改,同时又不会因董事人员长期固定,导致管理思想僵化。人员设置具有灵活性还体现在书院事务繁忙时,可以增加副董一职。
2.董事的职权内容。书院董事工作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安排教育教学工作。每次教学活动开始时,董事们须提前筹办好各类事务,保证书院各项教学活动的开展。除了提前到院筹备外,董事们还组织学生开展考试,进行考场监督。二是对山长和老师的选聘。不能因外部因素来干预书院山长、教师的选聘。三是对书院经费进行管理。董事是书院经费管理的直接负责人,桐乡书院的账本实行三方制,防止了书院贪污腐化的出现,董事还对书院田产等资产收租收益等进行管理。
3.董事监管制度。为了防止书院董事出现尸位素餐等现象,书院实施董事监管制度。对于书院的经费账目实行年际交接式,在账目交接时,若有所差错,下一位接管者可不予接受,如若接受,后期发现也只能自行将差额补上,这种做法有利于董事之间形成相互监督。除此之外,桐乡书院还将涉及贪污的人员名单公之于众,将其贪污金额明细“在书院门首张贴,使众闻之,俾其自愧”[5]726。通过这种贪污公示的方法,让书院董事羞于侵占书院资产。书院还要求董事不攀强附势,不阿谀奉承,保持书院培养人才,振兴文教的初心。
4.董事公议制度。对于桐乡书院的各类事务,桐乡书院实行董事共议制度,不仅体现在山长教师的选聘上,还体现在书院的各项事务上。桐乡书院章程就曾对董事因公事聚议于书院时的饮食进行明确限制,侧面也反映出书院事务是需要共同商议决定的。同时对于保持书院章程的有效性上,防止书院章程积久弊生,后续无法实行,书院还规定董事们可以随时商改,但是“必宜斟酌尽善,公同会议,方允改行,不可以一己之私妄为更易。”[5]728可以看出书院各项事务的处理不是一人独断而是共同商议决策的结果。
三、结 语
桐乡书院的建成与管理离不开戴钧衡的积极努力,面对当时家乡学子求学不便,他便与友人共议创建书院,共同谋划书院的管理。针对当时的教育现状,戴钧衡对桐乡书院的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与举措。面对当时整个社会风气日渐衰颓,书院山长癖癃充数,士子志向鄙陋,读书只为追求科举功名的现状,戴钧衡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埋没和对思想的钳制。他指出“今天下习俗之坏,制度之隳,积重难返。非得贤俊布满天下,其势不能以骤回。而欲贤俊之多升于朝,非于取士之法有所变更,亦必不可得”[1]395。他认为不仅需要改革科举制度,还需要培养真正的贤俊,需要在教育的内容上进行改变,让士子谋有用之学,务求实用之举。因此在桐乡书院的管理中,他积极主张自己的教育理念,强调书院应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为此,戴均衡在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经费管理、设施管理和书院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管理主张与改进举措。正因如此,桐乡书院创办后的短短几年就声名鹊起,影响广泛,对当地的教育事业起到教化作用,解决北乡学子求学问题,造福了当地民众。著名的桐城派学者方东树就曾给予桐乡书院较高的赞誉,他认为当时很多书院都不能够真正地培养学子,而桐乡书院是独树一帜,能够培养出真正贤良之才,他称赞“吾于新建桐乡书院,而以为可即之以求明夫道焉”[4]1013。罗惇衍听闻书院的功绩后,称“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8]71。其好友方宗诚评价其一生:“严法令,明教化,励气节,改科举,破资格。”[1]678后世评价其“一生致力于整理桐城前贤诗文,创办桐乡书院并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书院教学得人,管理有方,成绩卓著。桐舒两地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11]。从他人对戴钧衡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戴钧衡在桐乡书院的创办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