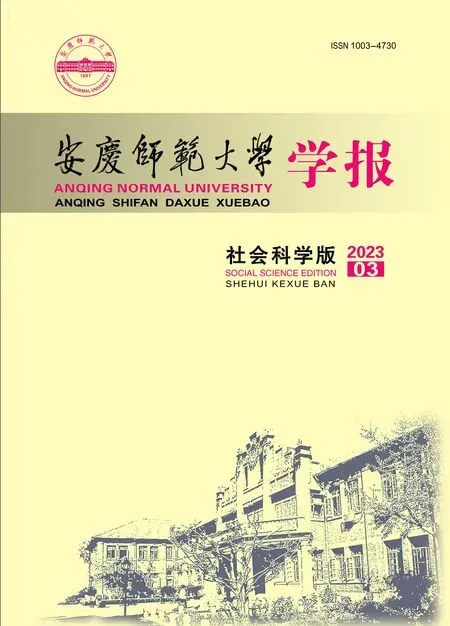近代早期法国鬻官制的形成与发展原因
杨慧英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
官职买卖在近代早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法国、西班牙、英国、瑞典、德意志、尼德兰等欧洲国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和英国的亚洲殖民地,以及奥斯曼帝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等地都存在。但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背景、政治体制、财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官职买卖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形式和特点。其中,法国的鬻官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欧洲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近代早期的法国君主和中央政府是鬻官制最强有力的执行者,在合法化的基础上,不仅成立了管理和运行官职买卖的专门机构——额外收入局(bureau des parties casuelle),开发了一套官职买卖的专有流程,设置了一系列官职税费;而且在官职买卖的过程中,把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发展到了极致,官职作为一种交易对象,被赋予了私人财产的特征,可占有、可出租、可转让、可继承、可抵押,亦可充当嫁妆。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官职买卖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其产生的行为习惯和作风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了法兰西社会和政府的每一个角落[1]。鬻官制何以发展至如此程度,在近代早期的法国以合法的形式存在了约3 个世纪之久,值得深究一番。
一、鬻官制是中世纪的遗产
法国的官职买卖溯源于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为近代早期法国的官职买卖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提供了实践先例,并经常以“有利辞职”(résignation in faveur)和出租的迂回方式呈现。
作为典型的基督教国家,法国的官职出售首先受到了教会法中有俸圣职辞职转让相关规定的启发。教会中有俸圣职的持有者最初通过选举产生,但当疾病突发或能力不济之时,他们选择卸任并无偿把重担过渡给具备资格的人,这就是辞职的来源。此后,这种转让官职的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惯例[2]。世俗官职的“有利辞职”模仿了有俸圣职的转让方式,官职的持有者通过辞职的方式把官职有偿转让给第三方以获利,故名。“有利辞职”的约束规则也借鉴教会法。有俸圣职的辞职需得到教皇的首肯,且在辞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构成圣职买卖罪,确保辞职的无偿性,教会法规的实施受到严格监督。若有俸圣职的持有者在临终之时自由选择继任者则冒犯了教会权威,故而,教会对有俸圣职的辞职转让施加了“20 天规则”,即职位持有者因疾病而在辞职之后的20 天之内死亡,则辞职无效。在世俗官职的辞职转让中,20 天期限被延长至40天,称为“40天规则”。但“40天规则”在认定规定时限内死亡的事实时,不区分辞职者的身体处于健康抑或疾病状态,只要求辞职时必须还活着[2]21‐22。世俗官员从教会法规中寻找官职转让的相关依据,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国王允许的情况下自由支配官职。
14 世纪起,法国国王允许官员进行“有利辞职”。当时,授予官员职位的国王去世后,官员经新国王颁发确认书,可继续持有官职,官员逐渐把官职当作自己的财产,并想自行处置。公共权力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官职的直接出售是不可能的,但国王允许官员辞去职位,好从中收取一笔转让费。本质上讲,“有利辞职”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官职出售。15 世纪始,为了牟利或实现官职在家族内部的继承,“有利辞职”愈益频繁。16 世纪30年代,受教会法影响的“40天规则”正式确立,法国官职的转让程序得以初步形成[3]。
1605年,亨利四世开征官职税,又称波莱特税(Paulette),因首位该税包税人的名字查理·波莱(Charles Paulet)而得名。波莱特税把“40天规则”豁免权的出售变成了一种收入来源[1]7。官职持有者只需每年交纳固定的税,即便在辞职之后的40 天之内死亡,官职也不会落回到国王手中,而是由继承人自动继承。波莱特税丰富了官职买卖的内容和形式,保障了官职在家族内部继承的安全性,同时也为统治者提供了稳定的财源,故而,波莱特税的设置标志着法国鬻官制的正式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波莱特税即代表了近代早期法国的鬻官制[4]。
中世纪时期的教会组织形式和教会法内容广为人知,所以,从实践的角度讲,法国世俗官职的转让借鉴教会法的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的人利用了他们最熟悉的东西,以至于后来的法国人认为“教会职位和有俸圣职的买卖对出售爵位和临时官职产生了坏的影响”[5]。
法国的官职出售还是世俗世界公权私有化的结果。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公共权力私有化与政治的独立性。因封建制以封土为基础,所有的权利与义务都与土地相关。某个人拥有一块领地,同时也就享有了这块土地上独立的政治权、司法权、经济权等管理臣民的各项权力。此时,领地拥有者对上级封主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这种政治独立性加之封地和所谓的公职都是世袭性的,公共的义务和私有的权利混在一起,一切就变成了个人私有的东西”[6]。中世纪时期并未形成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人们不认为个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所遵循的规则与个人在相互关系中所遵循的规则有所不同,也并没有明确界定两者的相关法律供人们遵守。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权力与私人财产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构成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一直存在于自12 世纪欧洲统治者建立的行政机构中[7]。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世纪的人们大都只把官职当作一种牟利的资源而非责任和义务。君主把国家看作私有领地,将之分割并分封出去,国家权力也随土地一起层层分散下去,被各大小领主当作私有财产。君主出租公共权力以增加财政收入,领主也经常把领地上的职权出租给依附民以收取租金。如此,法国在中世纪时期便形成了一个职位出租体系。
卡佩王朝时期,罗贝尔二世(996—1032 年在位)创设了传达国王命令的司法执行官(prévôt),统管行政、司法、军队和财政,掌有很大一部分公共权力,此类官职几乎从一出现就被纳入了职位出租体系。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派遣代表国王的领地大法官(baillis)以及驻南方省份的司法总管(sénéchaux),并授予他们职权,令他们负责管辖区内的司法、税收、档案和军事。领地大法官和司法执行官的职位经常被路易九世出租给出价最高者,租期一般为一年,有时也打包出租给包税人群体,甚至以出租的名义出售,所得构成国王的部分收入。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曾拒绝过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为其祖父路易九世封圣的要求,理由是路易九世允许公开出租王国内的官职[2]12。自路易九世起,法国君主一直在官职出租和直接任命两种官职授予方式之间来回摇摆。在腓力四世和腓力五世(1316—1322年在位)任期,官职出租方式略胜一筹。腓力六世时期(1328—1350 年在位),直接任命的官职授予方式曾短暂回归,但随着百年战争的开启,更能满足财政需求的官职出租方式被重新启用,并几乎贯穿了百年战争始终。
如果说官职出租体系是鬻官制的起源,这可能有所夸大,因为两者不仅不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在期限、行为和结果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官职出租是在固定的期限内,在承租人支付固定费用的基础上,把职权短期或长期转让出去;而在官职出售中,购买者一次性付清费用,成为官职的所有者,一般终身持有官职。其次,反复的官职出租带来的收益是可持续的,而官职出售一般只能带来一次收益。再次,一旦租约到期,出租的官职即可收回;而出售的官职非偿付不可撤除,而且因为政府经常没有偿付能力,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分割。但中世纪的人们一般把官职出租当作出售,因为承租人倾向于无限期地续租同一个职位,直至死亡。但无论存在何种差异,我们不能否认官职出租是官职买卖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并为鬻官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9。
二、财政危机是鬻官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法国的近代早期几与绝对君主制兴衰昌敝的历程相始终,通过战争的方式向外扩张既是绝对王权增强的需要,也是重要体现之一,这种向外力量的释放往往需要丰盈的财政收入加以保障。然而,当战费高扬之时,法国税收体制和信贷体系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缺陷难以消弭,财政收支难臻平衡,财政危机频发。故而,法国君主把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大额款项的官职买卖合法化和制度化,并将之纳入了法国的公共财政体系。
近代早期法国的税收体制绕不开特权、习俗和惯例的交织,特权的让渡和惯例的因循导致了财政税收的严重流失。
自中世纪以来,教士和贵族作为最初的特权阶层,以拥有军役税(taille)等税收的豁免权彰显其优越性和特权身份。阿克顿曾言:“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对于政府来说,取消这些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是至关重要的。”[8]然而,免税群体自中世纪晚期不断扩大,尤其自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官职买卖在法国取得合法地位。统治者通过出售司法、财政、军事和市政等各类官职筹集临时额外收入。本就视纳税为耻辱标志的平民有望通过买官的途径入贵,获得税收豁免权和社会地位的晋升。又恰逢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之际,法国资产阶级纷纷购买可入贵官职,跻身穿袍贵族之列,获得免税特权。在鬻官制发展的中后期,法国统治者甚至直接出售与免税权挂钩的部分贵族证书,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路易十四出售了500份贵族证书[9]。显然,免税特权和鬻官制是交互作用发展的,前者极大地增强了官职的吸引力,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导致了免税人群体的扩大。不仅个人,鲁昂、迪耶普和勒阿弗尔以及一些较晚并入国家版图的行省也拥有免税特权。广泛的免税人群体和地区限制了中央的财税收入,让法国本就有限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强了对鬻官制的依赖。
再者,自中世纪以来,法国的税收一直是“本地收、本地支”,财政收支体制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主义”的特征。因循地方惯例,税收依据各省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区别征收,但相当部分的税收留作地方所用,并未上缴中央国库。分散的财政收支体制无法为统治者提供即时且大笔的资金,尤其难以应对不断攀升的军费支出。有鉴于此,查理七世(1422—1461 年在位)和弗朗索瓦一世先后进行了财税体制中央集权化的改革,同时规范地方财政支出,要求地方必须先获得授权才能拥有支出部分财政的权力,剩余收入全部上缴储蓄国库,并依照固定的程序进行有计划的划拨。到弗朗索瓦晚年时,法国的税收实现了相当的集权化。然而,“即便是君主权力机制中最为集权化的财税管理,在具体实践中,也要面对广泛存在的地区多样性和特殊主义,根据地方习俗、惯例,或不同群体、省区的特权做出妥协或调适”[10]。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于技术困难性及地方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考量,直到18世纪末,相当部分的税收仍然“地方收、地方支”,并没有进入国库,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仍任重而道远。弗朗索瓦一世通过公开合法地出售官职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意大利战争,而他制度化和集权化中央财税体制的努力又使法国的财政官僚膨胀,反为鬻官制的发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
除了广泛的免税特权和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外,近代早期法国的税收还存在征税成本高、重直接税轻间接税、征税人盘剥和纳税人拖欠税款等诸多弊端,导致税收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加重了本就不富裕的中央财政的流失,法国君主和政府愈加仰赖各种财政权宜之计,从根本上促进了鬻官制的发展。
当弊端重重的税收体制无法为法国政府提供即时、足额的财政收入时,公共信贷即成为维持财政良性运转的另一有效手段,这自中世纪以来就成为法国的一种惯例。1522 年,弗朗索瓦一世设立了额外收入局,旨在创造和筹集临时性和非经常性的收入,但其主要收入几乎从一开始就源于官职出售以及这些官职所承担的各种课税[1]4。熊芳芳认为出售官职作为新的信贷方式,自弗朗索瓦一世时期成为法国国王获取收入的惯用手段,推动了法国公共信贷体系的发展。鬻官制构成了近代早期法国公共信贷体系的重要内容[11]。它类似于国王以官职为抵押品的借贷行为,支付的价格即官职购买者给国王的借款,薪俸即国王给官职购买者的借贷年息[12]。官员成了国王借贷的对象,除了直接抵押官职外,君主还通过经常更新波莱特税,或提高薪俸,或确认官职委任书的方式,向官职持有者个人或团体强制借款。
传统信贷体系的有限性有力推动了官职出售这种新型借贷方式的发展。法国的信贷体系弊端明显,尤其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更显如此。其一,税收与信贷紧密相关,因为信贷往往以税收为抵押,但法国的税收效率远不如由议会动员征税的英国。1788 年,英国的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4%,而法国的税收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13],意味着英国从经济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更高,可为公共信贷提供更好的支撑。其二,当法国的信贷仍严重依赖官职持有者、商人、银行家、包税人等中间群体,松散且低效之时,英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良性公共信贷体系,致使法国消化债务的能力远不如英国。1788 年,英国有效消化了占国民生产总值181.8%的债务,而法国尚且不能解决比率不足英国1/3的债务[13]98。其三,法国的财政模糊不清,不似英国通常将财政以报告的形式出版,因此法国在国际上的借贷成本远超公开信用的英国。1788 年,当英国的年度借贷利率仅为3.8%时,法国高达7.5%[13]98。既然传统信贷的弊端暂时无法克服,法国君主只能在既有体系内尽量节约借贷成本、扩大借贷规模,鬻官制可助他们有效达成目的。首先,作为官职投资利息的大部分薪俸的正常利率远低于国际借贷率,整个18 世纪基本维持在3%[1]199。其次,作为主要的借贷对象之一,扩大官职持有者群体的规模可行度高且可为君主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官职出售成为一种极佳的借贷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形式而言,鬻官是一种变相借贷,政府支付的薪俸是一种独特的长期债务[14],与其他债务无异,最终都需要纳税人的税收加以偿还。本质上,鬻官是法国君主以出让部分公共权力和未来税收为代价暂时解决财政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随着君主不断扩大附着于买卖性官职的特权,官职逐渐从抵押品变成了官职持有者的私有财产,反过来限制了君主选择和委任官员的权力。
三、战争是鬻官制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动力
战争因素对法国鬻官制的形成和发展也至关重要,鬻官制的几乎每一次大发展都离不开战争的刺激。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庞大战争机器的开支造成了绝对主义国家严重的收入危机,对大众的税收压力普遍强化,同时,卖官鬻爵成为所有君主政体重要的财政应急措施并且被系统化了”[15]。
法国官职买卖的大发展始于意大利战争时期。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为了解决财政困境,他私下纵容官职出售。路易十二承袭了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的野心,但没有强大的军队和财政做后盾,他在战争中使用了瑞士雇佣军却无力支付酬金,只能拍卖部分王室财务官职筹集钱款。路易十二终未能在意大利立足,被迫从意大利退却。弗朗索瓦一世即位后重启战端,先后公开出售财政和司法官职以解决战费吃紧的问题。1522年,他同意时任高等法院院长的掌玺大臣迪普拉(Duprat)设置20个参事职位进行拍卖。这是第一批以出售为目的而专门设置的官职,虽然所得远不足以支付远征意大利的费用,但是开了专门设置官职以公开出售的先河。黎塞留认为,正是弗朗索瓦一世把法国的官职出售变成了一项公开合法的交易[16]。当他的统治结束时,大部分司法官职都买卖化了。自此,设置官职进行出售成了法国大革命前政府筹集资金的惯常手段。
亨利四世于16世纪末结束了困扰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后,急需臣民的财政支持,用以恢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加强王权。1605年起,他向官职持有者开征波莱特税,年征税额为官职估价的1/60,税期9 年一更。波莱特税的征收为近代早期的法国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新来源,但也开启了法国官职收费乱象丛生的局面。逐渐地,除了反复征收的波莱特税外,官员还需负担与波莱特税配套的强制借贷、强制加薪费、官职确认费、世袭权购买费、官员团体接纳费等纷繁复杂的税费。波莱特税及其他税费征收程序的建立及执行意味着法国的鬻官制逐渐向系统化发展。
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法国的战争时期多于和平时期,战费支出扩大,作为最可靠的战争财政手段之一,政府对官职的出售和操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三十年战争期间,官职出售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潜力发挥到了极限[1]10。当战事接近尾声之际,法国国内爆发了要求司法独立、反对国王专权的福隆德运动,司法界的官职购买者积极参与并推动了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的发展。路易十四从福隆德运动中看到了鬻官制的危害性和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支持科尔贝尔(Col‐bert)改革,改革取得了短期成功。但随着荷兰战争的爆发,鬻官制迅速回归。科尔贝尔对荷兰战争的抵制险些使他失去了职位,他终于意识到法国国王不可能发动一场大战而不求助于一系列包括鬻官制在内的已成习惯的财政权宜之计。路易十四时代的最后几十年里,法国是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度过的,其间,法国的鬻官制在广度上发展到了极点,不仅市政官职首次被纳入到官职买卖体系并被推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且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需购买从业资格,官职出售的对象从最初的资产阶级扩大到了平民大众。
随着官职买卖市场的日益饱和,18世纪20年代至法国大革命期间,鬻官制对战争的贡献率愈益变小,但战争依然是它发展的最大动力。直到1763 年,法军在七年战争中的不良表现被归咎于军队中的军衔买卖后,军界的官职交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军衔每转手一次即削价四分之一,四次之后,不再具有任何投资价值,鬻官制才在确定的某一领域获得了相对成功的改革。而且,年金、范围扩大的间接税和日益倚重的直接税的征收,辅以国际市场上公债的出售,推动了运作起来早已不很灵活的鬻官制在法国余生中的边缘化[1]53。当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政府已经主要靠借贷来维持开支了。
无疑,鬻官制是法国近代早期历次战争的财政需求带来的最严重的弊端之一。自官职公开且合法出售的那一天起,鬻官制的形态、规模与运作的主要决定因素都一直是战争,新战争的周期性威胁对于官职买卖的扩大与收缩起了直接的决定作用[1]51。
四、资产阶级的狂迷是鬻官制发展的必要条件
近代早期法国鬻官制的发展还与资产阶级①近代早期法国资产阶级的范围广泛,通常指代“城市居民”或者更狭义地指代“城市公民”(citizen),这里的“公民”具有法律属性,仅指每家每户的户主组成的特定群体,而非所有住在城墙内的人。另外,“资产阶级”还用于指代那些以土地和借贷为生,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一小撮城市居民。最后一类“资产阶级”属于我们所谓的“独立财富”阶层,包括最富有的商人和声名显赫的银行家等城市上层。参见:William Beik,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07.本文中的资产阶级主要指后两类。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在官职出售的过程中,若缺失了潜在的官职购买者,官职买卖难以进行,君主和政府的财政目的也难以达成。所以,官职买卖的实现需要社会中存在具备相当购买力的群体,经济上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充当了最狂热的官职购买者。彼时,贵族等级因频繁的战争、政府中央集权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式微;而资产阶级通过积累财富和接受教育,重要性逐渐增加。资产阶级手握财富,积极寻求社会地位的改变,热衷于购买官职,逐渐形成了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官吏阶层。到17、18 世纪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官职买卖的情况日益严重是“近代初期经济日益商品化,商业、制造业在其中地位相对上升这一事实最令人震惊的副产品之一”[15]14。
资产阶级对官职的偏好被卢瓦索(Loyseau)称之为“官职狂迷(archom‐anie)”[17],德雷马(Des‐marets)甚至有言“当国王创造一个官职时,上帝就会创造一个傻瓜来买它”[2]130‐131。此种现象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当时法国政治运作模式下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投资选择。
官职买卖首先是等级制的产物。大革命前,法国人被划分为贵族、教士和平民三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享有封建特权和免税权,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负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备受压榨。在贵族——平民二元对立的世俗社会里,贵族高贵的出身、优越的地位以及非凡的特权都深深吸引着第三等级。但第三等级的成员既不可能世袭贵族称号,也很难凭借军功进爵,捐官入贵便成了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官职购买者首先获得的是荣誉性特权。只要购得了官职,哪怕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能或已离职,官员仍然可以享有头衔,享受尊称和荣耀,甚至可以延及家人。而军役税和盐税的豁免权、为军人提供住宿和夜间巡逻等公共事务的豁免权等则可为购买者节省一大笔钱,官职的荣誉性特权得以具象化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得以凸显。官职购买者的最终目标是获得贵族身份,这就使得当时的法国出现了极特殊的现象,即“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18]而且,“在别的地方,平民融入贵族圈子的过程都发生在平民获得贵族身份之前,而法国平民融入贵族圈子的过程却是在平民获得贵族身份之后才开始的”[1]166。
资产阶级购买官职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君主为了增强王权和缓解经济困境,急于拉拢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则为了提高政治地位、镇压反抗资本掠夺的城乡居民、统一并开拓国内市场,与国王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国王,在政治上助其牵制旧贵族。其经济动机也不亚于政治动机,资产阶级把官职投资看作除土地投资外的另一种选择,在相应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具备时,不遗余力地购买官职,主要是因为官职特有的稳定性,资本流动和商业活动都有风险,资产阶级成员的不稳定性远高于贵族等级。资产阶级在积累财富后,总是希望把财富转移到稳定的领域,例如土地和官职。可以说,官职是资产阶级能在等级制社会中获得的除土地外最牢固的东西了。但是,官职却具有土地不可比拟的世袭性、不可分割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购买官职成了一种牢靠的不动产投资选择。资产阶级购置官职,实际上也是他们出于对自身持久稳定性的渴求。吊诡的是,财富创造了资产阶级,但是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时期,他们的成就却总是通过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职位和贵族身份加以衡量,而非财富。
五、结 语
可以说,近代早期法国的鬻官制是国家经济发展不理想、政府官僚体系不完善、财政制度不合理的粗糙简单的政体组织形式的副产品,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国家机器不健全时期等级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鬻官制的形成与发展是法国的内部因素和对外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主要表现为:其一,官职出售是中世纪的一种遗迹,在公共权力与私人财产不明晰的时代,公共权力是牟利手段的认知深入法国民众的内心,在财政困难之际通过出售官职筹款是法国君主的潜在意识,这是中世纪时期埋下的“地雷”,待到合适的时机它自然会被引爆。其二,地方分权和特权充斥的财税制度以及不发达的公共信贷体系无法为法国筹集急需的巨额钱款,政府只能另辟蹊径,从根本上促成了鬻官制的形成和发展。其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国资产阶级崛起,原本在森严的等级制中入仕无门的他们既有强烈的意愿也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通过购买官职跻身社会的上层,全国性的官职买卖市场藉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鬻官制的形成与发展。此外,频繁、持久的战争给法国造成了空前的财政压力,为鬻官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这也是该制度一直受王权庇护的原因。中世纪的遗迹、法国的内部缺陷和对外扩张共同导致了近代早期法国鬻官制的出现,并共同为其发展保驾护航。法国鬻官制的发展如此强劲,以至于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和国家都难以企及,也是因为它几乎集齐了鬻官制发展的所有因素[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