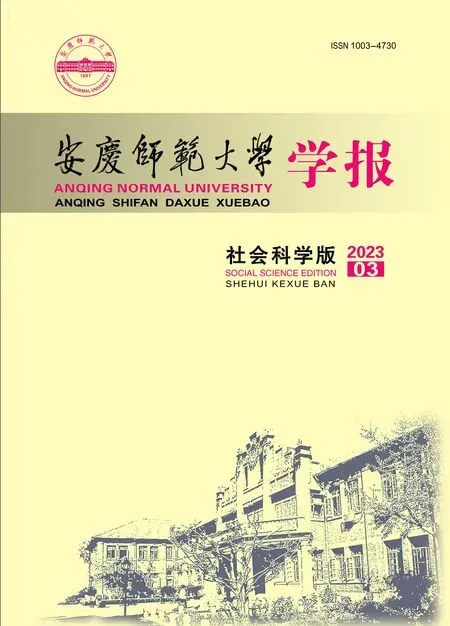反预期标记“这一V不要紧”的语篇功能及表意机制
薛高领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现代汉语书面语或叙事口语中存在一种标记,它常常暗示读者或听话人接下来表述的信息超出了他的预期,例如:
(1)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姑娘本来是杨柳细腰,这时候劲也来了,就使足了力气,把缸一下掀起来了,这一掀起来不要紧,就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道闪光一道电光屋里头全部是香味,香气扑鼻,她静静一看,下边卧着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的头,后边身子是什么呢?还是一只黄狗。(倪宝臣《钤记中华》)
(2)解文华弄不清要他到哪儿去,要把他怎么样啊!心里暗想:敌人要是也这样对付我……啊!他这一想可不要紧,立时就觉得心里哆嗦,浑身发冷,喘不上起来,两条腿一软,粘粘糊糊地就瘫在地下了。(刘流《烈火金刚》)
例(1)“这一掀起来不要紧”前项表述的是施事执行的动作“把缸一下掀起来了”,根据读者的常识或逻辑推断,这个动作不会造成特殊的后果,但是实际上出现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等超出他预期的情况。作者或说话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读者或听话人理解语篇内容的障碍,采用了特殊的话语标记“这一掀起来不要紧”来提示听话人或读者接下来的信息表述的内容超出了他的预期。我们将这一类具有相同格式和相似功能的语块码化为“这一V 不要紧”,它具有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元语言功能。
关于“这一V不要紧”格式的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不多,仅有的几篇研究也都是从构式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张艳(2016)的硕士论文运用构式理论对“这一X不要紧,Y”的构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描写,将其构式义概括为“X 造成的致使结果出乎说话人预期,表层形式与深层语义的反差造成凸显致使遭受结果义”[1],她认为反预期的语义来源于表示转折或意外的词汇和短语,此外,“要紧”表“不要紧”间接否定也能表示反预期。我们认可表示转折或意外类的词汇及短语形成的语境对“这一X 不要紧”结构反预期语义的规约有部分的作用,但是将“要紧”等同于“妨碍”,并采用礼貌原则来推理这种规约性语义并不合适。
孟德腾(2018)同样采用构式的理论认为该结构是一种“假性否定构式”,主要功能是用以凸显引发反预期结果的原因的重要性[2]。这和张艳总结的构式义正好相反,张文认为结构凸显的是“致使遭受结果义”,而孟文则认为凸显的是“引发反预期结果的原因”。孟文认为该构式利用惯常的具有规约性质的常理或者言语行为者的心理期待,以“Y”的反预期性来招请人们由果溯因,通过修正理解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从而得出原因的重要性。胡承佼(2019)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构式重新进行了整合,将其认定为“意外因果句”,即说话人主观上认定前项和后项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意外性和突发性[3]。
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推进了“这一V 不要紧”格式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此格式的认识,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一些学者错误地将“这一V 不要紧”结构中的反预期判定为超出说话人的预期,实际上在语篇组织过程中,“这一V 不要紧”并不标记作者或者说话人的反预期心理,而是作者或说话人认为接下来出现的信息有违常理或违背听话人或读者的预期,之所以使用该结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听话人或者读者理解话语内容的障碍而做出的话语索引。
第二,这些文章研究的角度单一,多从内部构件的描写和解释入手,推导出格式的构式语义,没有从更大语境的角度来考虑其篇章定位以及交际语用功能。综上所述,“这一V 不要紧”仍然存在继续探讨的价值。本文从话语组织的角度出发将“这一V 不要紧”识解为一个话语标记,研究其语篇组织过程中的功能价值,并试图归纳反预期语义的来源及表意机制。
二、形式特征的判定及语义表现
(一)语篇位置及定位性
作为一个提示性的话语标记,“这一V 不要紧”在篇章组织过程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它只能处于反预期信息的前面,用来提示读者或者听话人接下来表述的信息和他的预期不一致。
(3)“现在,我要求你,让我看看她。”这一说不要紧,沈国英脸上顿时收住笑容,一下子站了起来,望着秀姑,沉吟着道:“你是为了她?”(张恨水《啼笑因缘》)
(4)新王来到,出来瞧,出来看!这一喊不要紧哪,喝!山上东西南北全呕呕地叫起来,一群跟着一群,一群跟着一群,男女老少,老太太小妞儿,全来了!(老舍《小坡的生日》)
例(3)中,秀姑的乞求从常识和逻辑来看不会导致沈国英态度的骤然立变,但是实际上却是“沈国英脸上顿时收住笑容”,这一反常的信息前可以用“这一说不要紧”进行标记。同理,例(4)中说新王来了应当不会引起“山上东西南北全呕呕地叫起来”这一极端情况的出现,可是实际上却出现了,此时,“这一喊不要紧”这一标记必须要放置在反预期信息之前。
(二)语块化及凝固性
“这一V不要紧”原本是一个话题-述题结构,但是随着位置的边缘化以及高频使用之后,内部的句法结构已经模糊,现在已经被识别为一个语用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篇章组织和信息传递中。此时结构的内部通常不能断开,也不能添加其它成分。
(5)a.“胖胖,我是坏女人,我打疼你了吗?我给你揉揉。”这一揉不要紧,胖胖就哼起来,好像大象打呼噜一般。(王小波《黑铁时代》)
*b.“胖胖,我是坏女人,我打疼你了吗?我给你揉揉。”不要紧,这一揉,胖胖就哼起来,好像大象打呼噜一般。
*c.“胖胖,我是坏女人,我打疼你了吗?我给你揉揉。”这一揉啊/吧,不要紧,胖胖就哼起来,好像大象打呼噜一般。
上面的例子中,“这一揉不要紧”已经凝固化为一个语块,中间不能拆开,也不能添加语气词,只能作为整体被识解为一个语用单位。虽然因为存在着变项“V”,但是不论“V”实现为何种动词或短语,都不影响语块的凝固性。
从“V”的构成来看,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复现前面所出现的动词,“这一V”回指前时动作:
(6)小马意识到了来自于嫂子的威胁。他抿了一下嘴。这一抿不要紧,小马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笑,这个隐蔽的表情是那样地没有缘由。(毕飞宇《推拿》)
(7)同时,心中也很佩服这个小孩儿;别看他人小,志气可是大呢。于是就去拉住小木人,往门里让。这一拉不要紧,老人可吓了一跳:“我说,小朋友,你的手怎这么硬啊。”(老舍《贫血集》)
上面两个例子中“抿”“拉”在前文中已经出现,这里只是重复了一遍,回指之前出现的动作。
一类是采用词义相似的动词来代指前文出现的动作,例如:
(8)谁知那个人直着脖子就吼起来了:这姓孙的想溜呀!你们是怎么看着的!他这一喊不要紧,从旁边钻出好几个人,架住孙老板的胳臂说:孙老板,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没喝多少哇,干吗要逃酒?(王小波《怀疑三部曲》)
(9)她把额头伸向我,我把她轻轻搂在胸前;她抬起眼睛,我亲了她的眼睑。这一吻不要紧,我猛地感到一种新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充塞我的心胸,不由得热泪盈眶。(纪德《背德者》)
上面两个例子中分别用了形式不同词义相近的“喊”和“吻”来代替前文中出现的动作“吼”及“亲”。
还有一类是概述性动词或短语,概括前文发生的一系列动作,例如:
(10)这壶奔小伙子胳膊,“吱啦”一下,当时把油皮都烫破了。嗬!“老头啊!我说你不长人眼吗?你瞧给我烫的!”老头呢,倚老卖老,“干吗呀?怎么啦?碰上了,那算什么呀,胳膊坏了能好,这壶摔了没地儿买去!它比你爷爷岁数都大。”三青子话!俩人越说越呛,打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不要紧,人们都往外头看。(郭德纲相声精选)
(11)像啃骨头似的,咯崩、咯崩,全咬成了两半儿,咬完了一看说:“有你的,马五,我担保你设赌局没玩鬼,你们大伙兄全看着了,他是货真价实。马五瞎子原已叫石二矮子作弄得冒火的,一听这番奉承,又变成哭笑不得了,摊开两手说:“矮爷,您这一查看不要紧,把我一付大骰子硬糟蹋掉了,我又没准备另一付骰子,眼看赌不成了。(司马中原《狂风沙》)
例(10)“矫情起来”概括的是老头的一番说辞特别矫情,例(11)“查看”概括的是前面“像啃骨头似的,咯崩、咯崩,全咬成了两半儿”这一系列动作。
综上来看,不论动词是何种形式,“这一V 不要紧”都已经语块化,具有凝固性的特征。
(三)程序性语义及部分可删略性
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中,语言的交际功能通常被认为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语言指向物质世界以及心理世界,包括概念的整合与意义的表达,是交际过程中的本体;另一方面,说话人除了表达自己的意义之外,还要关注着交际对象,关注交际对象的参与状态和反映,关注彼此关系和心理距离,并相互配合或进行某种调整。在这一方面,说话人可以采用非语言形式进行调节,也可以采用话语标记这一语言手段。因此,话语标记的使用虽然不涉及命题表述,但是对于整个交际行为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虽然不改变概念内容的表达,但却影响听话人对于话语意义理解的效率和进度。所以对于命题内容来说,话语标记可以删略,这种特征反映形式上,体现为部分可删略性:删略话语标记后,命题内容并未有改变,但是会显得连接不自然、不顺畅或者语气、态度等发生变化。例如:
(12)a.不一会儿,就听见厨房间有碗筷响动的声音。他悄悄地爬起来,在门缝里偷看。这一看不要紧,乔大夯顿时难过万分,热泪滚滚,抱着头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言语。(魏巍《东方》)
b.不一会儿,就听见厨房间有碗筷响动的声音。他悄悄地爬起来,在门缝里偷看。乔大夯顿时难过万分,热泪滚滚,抱着头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言语。
(13)a.这时郭祥忍不住问:“妈,我爹哪儿去了?”这一问不要紧,母亲的泪,扑簌簌地迎着灶门口,像一串水珠似地滚落下来。(魏巍《东方》)
b.这时郭祥忍不住问:“妈,我爹哪儿去了?”母亲的泪,扑簌簌地迎着灶门口,像一串水珠似地滚落下来。
例(12)中“这一看不要紧”并没有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增添具体的语义,删略“这一看不要紧”并不影响语篇语义的理解,但是却显得情节之间的连接和过度不自然,影响篇章理解的效率和进度。例(13)同理可证。
三、“这一V不要紧”的语篇功能
(一)语篇衔接功能
Schiffrin(1987)认为所谓的语篇衔接功能指的是在语篇组织过程中,说话人或者作者为了更好地编排内容而采用的一系列元语言标记[4]。这些标记的使用使语篇内容衔接更为自然,语篇的表述更为连贯。“这一V 不要紧”前项为施事执行的某个动作,后项为此动作所引发的某个结果,逻辑上此动作和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是一种非常规的,弱因果关系,这就导致两者的联系不够紧密。这时可以采用添加“这一V 不要紧”这个反预期标记来衔接、连贯动作及其所引发的后果,使语篇表述更加自然、流畅。例如:
(14)俺感到眼睛里杀得紧,想了想才明白了俺是出了汗。俺用衣袖擦脸,把衣袖都擦红了。这一擦不要紧,眼前又发生了变化。(莫言《檀香刑》)
(15)嘎保森格回头咬不着它,只好跟上次一样奋力朝前跳去,这一跳不要紧,它把自己的尾巴跳掉了。(杨志军《藏獒1》)
例(14)“用衣袖擦脸”和“眼前又发生了变化”存在一种弱因果关系,即“用衣袖擦脸”不是导致“眼前又发生了变化”的直接原因,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关联,这和常规的因果关系有一些区别,两者的联系也不够自然、紧密。添加“这一擦不要紧”后,可以使两者的衔接更为流畅。例(15)同理可证。
(二)信息凸显功能
Blakemore(1992)指出,人的交际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认知活动,人类认知的总目标是力图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5]。根据该理论,为了让对方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说话人或作者会尽可能清楚地表述话语,并使用各种语言手段来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地寻找,采用话语标记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语言手段。作者或说话人在组织语篇的时候,大脑中已经有了一种具体阐释自己话语的选择,在交际的过程中,他期待听话人或读者能够理解并得出他这个选择[6]。具体到“这一V不要紧”这一标记,标记的前项为施事实施的一个动作,后项为这个动作触发的某种结果,逻辑上前项的发生并不会导致这个结果的出现,两者虽然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也只是一种弱因果。作者或听话人知道这种弱因果关系很难被对方所识别,为了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所付出的代价,作者采用“这一V不要紧”这一标记使前项与后项之间的非常规因果关系凸显出来,提示听话人接下来的信息和他预期的信息不一致。例如:
(16)任保用手扒着边沿,脚踩着墙边,费好大事才爬上了窗台。任保不看也就罢了,这一看不要紧,立时把他吓呆了。他清楚地看见,屋里除去王镯子和孙承祖,加上孙承祖的舅父汪化堂,还有另外四个人。除了王镯子,他们每人都带着短枪短刀,杀气逼人。(冯德英《迎春花》)
(17)玉宝跑到院子中间喊:“保长呀,快起来,有贼啦,我们抓着一个贼!”这一喊不要紧,鬼子军官正在屋里睡,听见了,他带了两个护兵拿着手枪就跑出来。(人民日报1952‐05‐29)
例(16)“这一看不要紧”前项是任保爬上了窗台“看”后项是“把他吓呆了”,我们通读上下文知道,实际上“把他吓呆了”的原因是下文“屋里除去王镯子和孙承祖……”,“看”与“把他吓呆了”不具有事理上的因果关系,“看”只有触发结果的效果。当然,也可以将前项与后项之间关系理解为一种非常规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读者或听话人来说,它们理解这种关系需要付出极大的认知努力,为了让对方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作者采用“这一看不要紧”来凸显其间的关系,暗示读者后文出现的信息有违预期。例(17)同理可证。
(三)主观评述功能
作者或说话人在语篇组织过程中,常常插入自己对于事态的观点、认识和态度,是一种“言者现身”的特殊句法表现。“这一V不要紧”就是一种“言者现身”的特殊载体,它不是施事情态指向,而是言者情态指向,即不是施事认为“这一V 不要紧”,而是说话人或作者评述这一动作行为,认为“这一V不要紧”。例如:
(18)当车辆行驶至离颐和园新建宫门约100 米处时,不知周围群众中谁大喊了一声:“是姚明。”这一喊不要紧,原本站在道路两边等候观看火炬到来的观众全都涌了上来,一下子便把奥迪车团团围住。(文汇报2004‐06‐10)
(19)有一次他刮胡子的时候就把它给碰破了,于是他就开始发烧,一病不起,最后这一烧不要紧,把他的命烧没了,他死去了。(李晓东《法老的诅咒》)
例(18)“这一喊不要紧”不是施事“周围群众中的某个人”认为“这一喊不要紧”,而是作者在叙述故事的时候,自己添加的评论,是作者认为“这一喊不要紧”,“这一喊不要紧”这一话语标记蕴含着主观性。同理,例(19)“这一烧不要紧”不是施事“他”所作的评论,而是作者在叙述整个事件过程中所作的评论。
四、“这一V不要紧”的表意机制及语法化
(一)语用推理
格莱斯提出的适量原则指出,在交际过程中,传递的信息要遵循适量原则,即所提供的信息是交际需要的,不多也不少。其中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所提供的话语包含交际目的所需的信息。二是所提供的话语不应超过所需要的信息[7]。“这一V不要紧”是作者或说话人在叙述事件过程中插入的关于自己对事件的评价。“不要紧”从字面意思看来是“不重要”的意思,“这一V不要紧”即“这一V不重要”。既然作者认为“这一V不重要”,那为什么作者还要采用特定的话语将其表述出来,而不采用直接省略不写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策略,采用特定的形式来标记“这一V 很重要”,与此同时,在语义上采用否定贬抑的方式来降低概念语义在情节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即:
形式:采用特定话语凸显
语义:采用否定方式贬抑
按照适量原则,所提供的话语要包括交际目的所需要的信息,同时所提供的话语不应超过所需要的信息,说话人表述一段话语必然有其特殊的意义或功能。在常规的认知中,语义的凸显驱使作者或说话人采用特定的形式来进行区分和强调,但是在“这一V 不要紧”中作者采用形式上的凸显和语义上的否定是为了传递某种特殊的目的——强调“这一V 不要紧”的结构功能或语用功能,即上文所说的篇章衔接功能和信息凸显功能。
(二)语义感染
上文概括的“这一V不要紧”的篇章衔接功能和信息凸显功能是语用推理产生的结果。那么反预期的语义标记特征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认为,作者或说话人之所以采用否定“这一V”的语义,是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故意将前项内容进行贬抑否定,从而凸显后项情状之出人意料。“这一V 不要紧”与后项意外信息往往暗含着逆接的语义联系,即,“虽然这一V 不要紧,但是……”后项意外信息常常被“居然、竟然、没想到”等反预期的词语标记,这些标记长期与“这一V 不要紧”共现,使得“这一V 不要紧”慢慢“感染”上了反预期的语义特征。随着高频使用,“这一V 不要紧”感染的反预期语义或功能逐渐稳固下来,慢慢地,当后项反预期信息没有被反预期词语标记时,读者或听话人也可以凭借“这一V不要紧”将后项信息识别为反预期信息。至此,“这一V 不要紧”的标记反预期信息功能彻底固化下来。例如:
(20)但这位妇人如此热情地冲着我喊,我几乎不能装着看不见。于是我过去用英语同她道了个寒暄,并用眼角稍稍瞄了一下她手中的那几页纸。这一看不要紧,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那老妇手中的几页纸居然全是用中文写成的。(人民日报2000‐04‐07)
(21)11月19日,宣武防疫站的小李到牛街检查,一眼瞅见一辆送货的三轮上装了一箱他日思夜想的“魔鬼糖”,立刻目光灼灼地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扑过去,“你这魔鬼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一问不要紧,竟吓得老头直哆嗦:“是……是华奥的”。(人民日报1994‐08‐10)
上面两个例子中“这一V不要紧”后项的信息都被表反预期义的词语所标记,例如例(20)中的“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例(21)中的“竟”。这些反预期标记词与“这一V 不要紧”组合共现,使得“这一V不要紧”感染上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功能,伴随着高频使用,“这一V不要紧”这一功能逐渐固化,当后项信息没有反预期义的词语时,“这一V 不要紧”也可以承担单独标记反预期信息这一功能。例如:
(22)她学着战士们的称呼,这一问不要紧,战士们都消失了脸上的喜色渐渐垂下了头。(冯德英《苦菜花》)
“这一V 不要紧”作为一个新兴的反预期标记,仍然处于语法化进程之中,依旧残留一部分概念意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标记反预期信息的语用功能。在语篇组织过程中,使用这一标记可以使听话人或读者降低语篇内容理解的难度,还能够丰富叙事策略,使情节叙述更为生动有趣,提高读者或听话人对于篇章内容的接受度。总而言之,“这一V 不要紧”是认知和受用双层机制下诞生的标记,随着语法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它的生命力也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