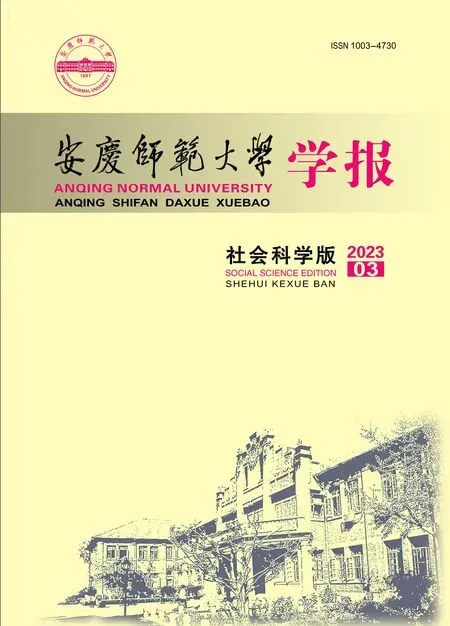叶嘉莹的词学思想和创作
何 群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在一首赠诗中这样评价叶嘉莹先生。的确,叶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古典文学权威学者。她在诗词学方面的造诣尤为精深,举凡古典诗词的创作、鉴赏、研究、传播等均创下了非凡的实绩。“知”与“情”兼胜是叶先生最大的禀赋,笔者多年来阅读其著作最深切的体会就是,它们不仅有深邃的学理,也有浓挚的情感;不仅能充实人们的头脑,也能餍足人们的心灵。这是它们独具的魅力,也是它们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的根本原因。在词学方面,她不局限于撰著,还着眼于推广普及,在世界各地开设词学讲座,由词学研究入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她的词学思想别开境界,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词作“清真秀逸,饶有情韵”[1]265。二者如水晶般折射出多面光影,美轮美奂,常读常新。
叶嘉莹先生,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并受聘为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08 年荣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13年荣获“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20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代表作品有《迦陵文集》10 卷、《叶嘉莹作品集》24卷、《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中国词学的现代观》《迦陵诗词稿》,等等。叶嘉莹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舌耕不止、笔镂不辍,其诗教精神和传承中华精神文化的使命感,令我们无限景仰。诚如学者吴晓枫所说:
她对古典诗词中所洋溢的生命力进行阐释与发掘,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论中蕴含的生命美学的思想[2]。
无论是叶嘉莹先生的著作,还是她的课堂,都充满了她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兴发感动”的生命力,都是源自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由衷热爱,而且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叶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待于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本文仅就其词学思想和创作加以管窥,且将前人未曾述及或论述尚不充分之处作为探究的重点,或可有抛砖引玉的功效。
一、擅以“词心”治词学
叶嘉莹先生是词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词,从唐五代、宋、明清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她都进行了精微深刻的研究。关于治词与治学,她曾说:
我个人在性格方面一向就具有两点特色:其一是主诚,其二是认真……我在说词时乃不敢人云亦云地作欺人自欺之言,而一定要诚实地写出自己真正的感受[3]369。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4]405。
叶先生的词学创获与这种踏实勤恳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
凭着敏锐直悟的能力,叶先生发现了古典诗词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义理,即诗歌中兴发感动的作用。这是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在其本质方面永恒不变的质素。她将兴发感动的作用视为诗歌的基本生命力:
我论诗一向主张中国诗歌之传统,实在以其中所蕴含的兴发感动之生命力为主要质素[5]92。
兴发感动对于更为纯粹的抒情体的词而言,更为关键。因此,在解读词作(诗歌之一种)时,不能仅停留于解释典故或照搬理论,而“应该透过自己的感受把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的生命传达出来。”[3]356叶先生对诗词中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的重视及提出,是经过创作及批评的实践后,与古人之说相印证所得出的结果。中国诗论有着悠久的重视心与物之间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传统。《礼记·乐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6]。
钟嵘在其《诗品·序》开端即强调: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
人在天地间活动,景物、世事触动人的感情,于是兴发为歌唱吟咏,可见,诗是源自作者对万事万物满怀关切的活泼泼的心灵。不仅诗人创作时重视兴发感动,读者读诗时也同样应重视兴发感动。《论语·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8]
“诗可以兴”,即诗歌具有非常大的令人联想感发的力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来说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9]16,是读词时注重联想与感发的极佳的表现。因此,叶先生说:
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诗歌之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正在于它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5]120。
诵读诗词可以让人有一颗不死的心灵。
词作具备了兴发感动之力,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就一律等同。感发之生命在质和量两方面还有许多精微的差别。
这种质与量上精微之差别的主要因素,则与酝酿和孕育出这种感发之生命的作者有着极密切的关系[3]360。
深探词人的感情世界,参透古今词心,是叶先生词学思想中最为宝贵的方面,却常常被忽略,因为人们往往关注她的“兴发感动”说而未及其余。事实上,兴发感动的本质在于词心之“真”。缪钺先生在他与叶嘉莹先生合著的《灵谿词说·后记》中评价叶先生有言:“其所谈意见,往往能深探词人之用心。”[10]450“灵谿”出自郭璞《游仙诗》:“灵谿可潜盘,安事登云梯。”书名以之为本,指的是一种幽远美好的词境。“灵谿词说”也可以理解为“灵犀词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意味着该著以探究词人之用心为旨归。缪钺先生在书中明确说:
《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引《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擥论作赋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论赋而提到“赋家之心”,实为抉微之论。我们论词,也应探“词家之心”[10]139。
叶先生擅长以“词心”治词学,这在《灵谿词说》的论词绝句中即有充分的体现,如她论李煜词:
悲欢一例付歌吟,乐既沉酣痛亦深。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10]86。
又如论秦观词:
花外斜晖柳外楼,宝帘闲挂小银钩。正缘平淡人难及,一点词心属少游[10]194。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赋家之心”“文心雕龙”“诗心”等皆是经典之论,“词家之心”也抓住了词学命脉。晚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11]23。
词心承载着抒情个体的禀赋、性情、人格等,也承载着深刻的自然和人生内蕴,它是灵敏的感应器,在风雨江山及世事变幻的刺激之下,自由发抒,词作由此产生。
“吾词之真也”,况周颐大力倡导词之真,他在《蕙风词话》中还提出:“‘真’字是词骨。”[11]14强调词心之真,也是叶嘉莹先生词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当我们注意到这种感发之生命在传达之际所形成的艺术价值以外,当然便也当注意到这种感发之作用在社会中的伦理价值。……这种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3]362。
唐五代、北宋的一些艳词,读了后让人觉得亲切动人,就是因为其词心之真,词人在这些作品中
无意地留下了他自己心灵中一些感发生命的最窈眇幽微地活动的痕迹,这种痕迹常是一位作者最深隐也最真诚的心灵品质的流露,因此也就往往更具有一种感发的潜力[3]364。
真诚的心灵品质,是我们欣赏和品评词时最应注重的方面。《庄子·渔父》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2]。
不真不足以动人,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历来将“真”视为好的艺术作品的核心本质。具体到词学领域,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曰:
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柳、秦之妍婉,苏、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13]。
将“真”视作词之精髓。王国维《人间词话》曰: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9]5。
叶先生对这则词话中“真”字的解读极为精准:
它所指的并非仅是外在景物或情事实际存在的‘真’,而是指作者由此外在景物或情事所得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之感受,而这种感受作用也就正是诗歌的主要生命之所在[3]305‐306。
透过叶先生对“真”的深刻体会,我们可以明白,对一位作者、诗人而言,必须有发自真心的兴发感动,才能写出富有感发之生命力的真正的好作品,否则便只能写出浮嚣跟风的伪作。这一点对当代作家创作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昔赵朴初先生唱和叶嘉莹先生《瑶华》一词曰:
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灵台偶托灵谿,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1]237。
性情至真的叶先生以她的一颗赤子之心参透古今词心,特别是词心之“真”,为词学界贡献出卓越的学术成果。
二、辛勤积沙成词厦
叶嘉莹先生的词学研究注重将词作品评、词的发展流变及词学批评等方面综合起来探讨,点、线、面纵横交织是其词学思想非常鲜明的特色,其词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具体而言,关于词体的美感特质,从深远曲折的内蕴美到弱德之美;关于词的发展史,从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到哲化之词;关于词学理论,从对比兴寄托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纯熟运用到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文学理论的参照……我们由此看到了她在漫漫词学道路上求索的身影。一沙一砾就这样在她多年不懈的努力之下构筑成一座词学之厦。
对词体美感特质的真切把握,贯穿叶嘉莹先生整个词学研究过程,构成她词学思想的显著特点。她在对历代词人词作精妙阐析的基础之上,一再强调:
词之佳者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10]728。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4]323。
对于词体的不同于诗的特殊美感,各朝词评家早就有所体认,如宋代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曰: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14]。
但他们的体认只是抽象而模糊的概念,未能如叶先生这样在比较作品异同之后作出理论性的通说。缪钺先生对词之特美的阐发是:
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15]。
此一说法与叶先生提出的“曲折含蕴之美”异曲同工。
词作何以具有这种特殊美感?好词何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感发和联想?叶先生认为:
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的情意——如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4]323。
她后来又将这一词学思想发展为“弱德之美”:
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16]。
通览我国千年词史,《花间集》所体现的是一种“弱德之美”,苏轼、辛弃疾等词人的悲凉沉郁之慨和怨断幽咽之音,在本质上也同是属于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将难言之隐曲折含蓄表达的“弱德之美”。词体的“弱德之美”如果上升到哲学、文化层面来解读,就是:
“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4]325。
比起诗来,贤人君子在词中展现的处在强大压力之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美好品德,引起叶先生深深的共鸣。“弱德之美”是她特别喜爱、特别欣赏的词之美感特质,是她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后的精彩发现。
充分运用历史的观念考察历代词人、词作、词论,重视对词的发展规律的探求,是叶先生词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体演进的历程、内容及风格特色、重要词论等,她都能以一种史观加以纵览,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以词体演进的历程为例,叶先生常常论及“演进之三个阶段”,即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歌辞之词、苏轼辛弃疾的诗化之词和周邦彦的赋化之词。后来,她在论王国维词时又补充了哲化之词。只是学界往往更为熟悉她的词之演进三阶段,而忽略了她提出的作为词体演进第四个阶段的哲化之词。叶先生在评论王国维词时说:
以思力来安排喻象以表现抽象之哲思的写作方式,确实是为小词开拓出了一种极新之意境。……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哲化之词。这种超越于现实情事以外,经由深思默想而将一种人生哲理转为意象化的写作方式,对于旧传统而言,无疑是一种跃进和突破[10]807。
这一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对词学史上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对词的发展流变总结出了客观的规律。叶先生采取的这种将文学演进之史观与文学个体之赏析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可以避免分析问题时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
无论是任何作品,都要能将之置于历史演进之长流中,然后方能更正确地认识此一长流之趋势,以及个体的作品在整体中之关系、比例,与其真正之价值[17]。
再以重要的词论为例,叶先生对比兴寄托说、知人论世、常州派词论、王国维境界说等,均能以历史眼光考量,并且不断充实、更新自己对它们的认识。“通古今之变”,成就了叶先生的“成一家之言”,其纵观古今的治词思想为词学研究界提供了示范。
在纵观古今之外,叶嘉莹先生又能融合中西,中外文学理论的相通互证使得她的词学思想带有浓厚的比较文学的色彩。借助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是对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方法的有益补充。西方文论长于思辨,逻辑明畅,运用其思辨方法和精密的批评术语来辨析常常神妙难解的中国词话,令人豁然开朗,是叶嘉莹先生的一项专长。让中国传统词论焕发出新的生命,叶先生的这一理论建树有着重大的意义,即
将以片言只语见精义却缺乏理论系统的传统词学,提到理论高度加以论析,探索并显现其理论内涵,也为其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寻得一适当而正确的位置[18]。
叶先生对传统词学与西方文论皆有透彻的领悟,中外兼长,所以才能有如此建树。例如其新近出版的著作《性别与文化: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而以“性别与文化”作为立论的依据,则是受了西方近年来有关性别研究的影响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角度[19]5。叶先生的深切体会是:
我虽然也引用西方现代之诗论,来赏析中国古典之诗歌,然而却并未曾使之成为夺主之喧宾,而是欲使之为我所用,成为我在表达自己之情思意念时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方式[5]59。
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时,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自己批判性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用新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加以博大中正的拓展,这是叶先生给予我们的宝贵经验。
关于词的源流演变、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如何正确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等问题,叶先生皆是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才有了清晰的认识,也才形成了她自成一家的词学思想。《词学新诠》开篇提及她曾在哈佛大学看到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中西本自同。”[20]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是她一直都在实践的课题。以现代观念、理论为工具对传统词学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这令叶先生构筑的词学之厦尽显恢弘端丽之美。
三、词方漱玉多英气
“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这是缪钺先生对叶嘉莹先生其人其词的概括,点出了叶先生志向高远、超凡脱俗,其迦陵词可与李清照的漱玉词相媲美。实践出真知,叶先生擅长创作诗词,深悉其间甘苦,所以在品评古典诗词时能够惬心贵当,发人所未发。叶先生“兼工诗词,而词尤胜,盖要眇宜修之体,幽微绵邈之思,固其才性之所近也”[1]3,她的才情更适宜用含思婉转的词来发抒。她曾在《学词自述》中回顾自己的填词经历:
少年时虽往往触物兴感,时有尝试,然未尝专力为之。其后又饱经忧患,绝笔不事吟咏者有多年之久。近岁以来,因故国乡情之感,重拾吟笔[1]9
由此可见,叶嘉莹先生平生为词的大略经过是:青少年时代,常常因为触景生情而填词;中年时代历经患难,吟咏的雅兴几乎消失殆尽;晚年则喜爱创作关怀家国的诗篇。
叶嘉莹先生填词,自1940 年16 岁时作《如梦令》(山似眉峰愁聚)到今天,前后计有80 余年之久,在由青年而中年而老年的人生各个不同阶段,她历经风风雨雨,尝尽酸甜苦辣,这些都在其词作中得以展现。据新版《迦陵诗词稿》,叶先生的词作共有150首左右。填词以诚为本,用词来记录真情实感,记录心灵,叶先生的词作极具兴发感动之力。这些词自然真淳,情深韵远,兼具闺秀词风与高远意境。
叶先生曾这样总结女性词:
作品中写的感情生动、深挚、真切,可以给人一种直接的感动、感发,女子就以这样的词为美[19]203。
她本人的词正具备这种美感特质。“感情生动、深挚、真切”,根源于她在词作中发抒的都是真挚朴素的人生感怀,这也构成了其词作所呈现的思想性的一个方面。1941年秋天作《忆萝月·送母殡归来》: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将惨遭母殁的17 岁女孩的心理与情感真实呈现,催人泪下。1967年哈佛作《鹧鸪天》: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把多年漂泊异国的苦闷和回归故里的渴望真切地表达出来,感人至深。《破阵子》(理鬓薰衣活计)之写青春女子的快乐生活,《满庭芳》(樱蕊初红)之写自己与中国台湾好友的深情厚谊,都是感悟生命、深挚动人的好词。大约作于1980年的《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21]171。
这首词写出了叶嘉莹先生饱经沧桑后的人生感慨。上阕写,生活艰辛,有过彷徨的时候,也有过困顿的时候,但再多的苦难也改变不了藐姑射山之仙子般的赤子之心。下阕写,这颗心是坚强无畏的,犹如不畏严寒的苍松,亦如终将展翅高飞的鲲鹏。“藐姑仙子”“谷内青松”“鲲化鹏飞”三个意象选取得十分神妙,它们具有相同的特征,那就是苦难中的坚韧。在它们的兴发感动之下,作者创作了该词;该词又能给读者以无尽的兴发感动。词作中闪耀着作者坚韧品格的光芒。在美感特质方面,词作呈现的是“弱德之美”,让人可以从中获致一种属于心灵上的激励。
叶嘉莹先生还常常在词作中表现哲理思致,形成一种深邃幽远的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极为推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人间词》,深受王国维喜好以哲理入词的影响。叶先生“知”与“情”兼胜,在创作这类词时以其“知”的一面为主,即以思力之安排借用一些具体的物象或事象来喻写心中的哲学思考。写于1943 年春天的《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上片写欢娱本非难事的感悟,下片借严寒终会过去喻坚定信念和保持乐观,词作哲思深沉。创作于晚年的《鹧鸪天》:
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
感慨自己在并不平坦的一生中执著求索,期待自己的精神火种能后继有人。以《鹧鸪天·一九四三年秋广济寺听法后作》为例:
一瓣心香万卷经。茫茫尘梦几时醒。前因未了非求福,风絮飘残总化萍。时序晚,露华凝。秋莲摇落果何成?人间是事堪惆怅,帘外风摇塔上铃[21]42。
此词写叶嘉莹先生听法心得。她的体会无疑是非常深刻的,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位早慧的女子。上片写对尘世间因果关系的彻悟,下片借“秋莲摇落果何成”喻托对人生的迷惘。作者巧妙化用佛经用语,同时融合佛教人生如梦等哲理入词,令词作特别具有一种慈悲的意味,其传达出的感发生命力极为深厚。作者在“能感之”和“能写之”两方面都禀赋独具,正如缪钺先生所言:
叶君具有真挚之情思与敏锐之观察力,透视世变,深省人生,感物造端,抒怀寄慨,寓理想之追求,标高寒之远境,称心而言,不假雕饰,自与流俗之作异趣[1]3。
迦陵词在艺术手法方面非常讲究,其艺术性非常高妙。在用字方面,亦雅亦俗,研炼至极归于平淡,例如《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
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
在章法方面,注重层转深入和反衬对比,如《采桑子》:
少年惯做空花梦,篆字香薰。心字香温。坐对轻烟写梦痕。而今梦也无从做,世界微尘。事业浮云。飞尽杨花又一春。
在意象、意境方面,注重意象与情意、情境的巧妙融合和相互感发,例如《破阵子·咏榴花》:
时序惊心流转,榴花触眼鲜明。芳意千重常似束,坠地依然未有声。有谁知此生?不厌花姿秾艳,可怜人世凄清。但愿枝头红不改,伴取筵前樽酒盈。年年岁岁情。
除此之外,叶先生非常注重用朴素而平凡的语言写出深刻而真挚的情感,让人一读即懂而又百读不厌。当我们读到“西风何处添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菩萨蛮》)这样的词作,会“惊异地感到这些寻常语言而何以会成为这样不寻常的艺术。”[22]
在叶嘉莹先生的词作中最常见的两个意象,一是“知音”,二是“荷花”。“知音”意象,如《浣溪沙·新获莲叶形大花缸,喜赋》下片:
翠色洁思屈子服,水光清想伯牙琴。寂寥天地有知音。
又如《金缕曲·有怀梅子台湾》:“高山流水钟期谊。”选取“知音”“高山流水”等意象,表达作者对珍贵友谊的渴望和珍惜。叶先生出生于荷月(即农历六月),幼年时双亲以“小荷”作为她的乳名,所以荷花一直是她珍爱的花卉。她在写诗时就常用到“荷花”意象,例如《梦中得句杂用义山诗足成绝句》(其三):
一春梦雨常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
在词中写荷花,如《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又如创作于1983年的《木兰花慢·咏荷》:
花前思乳字,更谁与、话平生。怅卅载天涯,梦中常忆,青盖亭亭。飘零自怀羁恨,总芳根、不向异乡生。却喜归来重见,嫣然旧识娉婷。月明一片露华凝。珠泪暗中倾。算净植无尘,化身有愿,枉负深情。星星鬓丝欲老,向西风、愁听佩环声。独倚池阑小立,几多心影难凭[21]202。
在这首长调前面,叶嘉莹先生写了一段长序,说荷的根、茎、叶、花……每一部分都有单独的名字,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她非常喜爱荷花。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她定居加拿大的温哥华,此地气候宜人,花木繁茂,可是却没有荷花,这让她感到非常遗憾。后来有机会回国讲学,每次看到荷花,她就会有无限感慨,既怀念久已离世的父母,又感叹年华的一去不返,于是创作了这首词。此《木兰花慢·咏荷》抚今追昔,感念人生,取境幽微婉约,是女性词的上品,非常具有“清丽、清新、天然”[23]之美。词中抒情女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与荷花的形象相互交融,以花的“净植无尘,化身有愿”喻人的情志高洁、甘于奉献。从“星星鬓丝欲老”到“几多心影难凭”,表达的是叶嘉莹先生在《我与莲花及佛法的因缘》一文中所说的:
我就一个人站在荷花池的旁边,心影——我内心之中的影像,我内心之中的追求、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我究竟完成了多少[24]?
在艺术性方面,这首词触景生情,随物写意,达到了浑化的艺术境界。词中“别饶一种浑灏流转的气象、韵致,使人能发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拘限的无穷想象,与王鹏运所谓‘烟水迷离之致’相仿佛”[25],其感发之力极其强烈。
顾随先生在讲授中国古典诗词感发时,开场白中有:
与花鸟共忧乐,即有同心,即仁。感觉敏锐,想象发达,然后能有同心,然后能有诗心[26]。
叶先生得此真传,拥有一颗善于感发的词心。她以女性的作者身份写女性的情志和情怀,“写得婉约,写得细致,写得真切,写得生动。”[27]迦陵词具含深远曲折耐人寻绎的美感特质。叶先生既能体悟词的这种特美,又能在创作中加以实践,知行合一,非常可贵。
四、结 语
叶嘉莹先生将中华古典诗词研究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她曾经这样说过:
我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到现在已经教了70多年古典诗词,虽然已经90多岁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书。我自己就像一条吐丝的蚕,我希望我的学生和所有像我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我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28]。
在词学研究领域,叶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被陶文鹏先生赞为“当世词家君第一”[29]。在她的系列词学著作中,有深邃的学理,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崭新的研究方法,有典雅的语言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予人无限启迪。她擅长以“词心”研治词学,把握词人词作的命脉之所在,即兴发感动之“真”,而兴发感动之“真”根源于词心之“真”,这一词学思想非常有价值。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她在词体的美感特质、词的发展流变、用西方文学理论诠释中国传统词学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创获,形成了成熟的理论。融贯古今中外,她的词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创作方面,迦陵词于朴素真淳之中,往往“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30],极具兴发感动的生命力,也极具她最为推崇的“弱德之美”,是女性词的典范。总体而言,叶先生的词学思想和创作能够为新时代的词学发展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研读她的著作,学习她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是我们所能够给予叶先生的最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