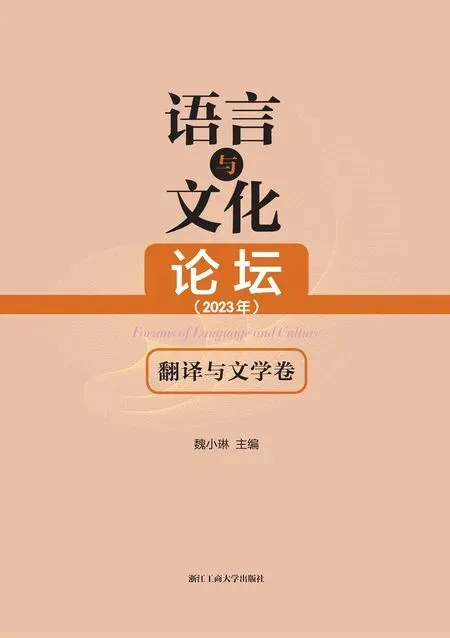《奥瑟罗》中英格兰王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文本再现
张建萍
“反转”(turn)一词在《奥瑟罗》中多次出现,且多由奥瑟罗本人说出,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又再转来转去”(莎士比亚,2015a)99。事实上,本剧处处皆反转,如他对妻子由爱至恨,苔丝梦娜由女神沦为“婊子”(莎士比亚,2015a)101,他眼里的老实人伊阿戈成了“万恶不赦的奴才”(莎士比亚,2015a)131,等等。相比之下,宗教反转较为隐蔽却不容忽视,故《奥瑟罗》又有“转宗剧”之称(Vitkus,1997)。
“转宗”意为改变宗教信仰的行为,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王国极其普遍。狭义上看,这种行为主要发生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广义上的转宗还包括新教与天主教间的转宗,这的确更为常见,因为宗教改革后,英格兰王国的新教不仅遭到天主教讨伐,还有本国玛丽一世的血腥镇压,虽然后来伊丽莎白一世奉行“中间道路”,但两者的冲突有增无减。据记载,为免受迫害,无数新教徒曾转宗求生。英格兰王国的民众对伊斯兰教并不陌生。16—17世纪逐渐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一度掌控地中海周边地区,往来其间从事贸易活动的基督徒商人为方便出行,转宗伊斯兰教。许多进入欧洲的伊斯兰教徒为适应环境又会转宗为基督教徒,欧洲人用“摩里斯科”特指转宗的伊斯兰教徒。“奥瑟罗是个‘摩里斯科’。”(Hall, 2015)他时刻以基督徒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以此为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哪怕他为保卫威尼斯立下战功赫赫,却依旧被剧中各色人等称作“摩尔人”。经笔者梳理,“摩尔人”是本剧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从第一次伊阿戈说“摩尔人亲眼得见我在罗德岛”(莎士比亚,2015)11,到最后一次洛多维科说“摩尔人的遗产也全部收缴”(莎士比亚a,2015)135,共计出现约40次。莎士比亚对其转宗态度则可从副标题“威尼斯的摩尔人”中窥得一斑。这都暗示着奥瑟罗转宗的失败。
基于文本描述,以下2个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作为一个“摩里斯科”,奥瑟罗转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莎士比亚借此在表达什么?探求答案并非易事,转宗这一行为向来不简单。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摩尔人承载更多的是“宗教而非种族身份……意味着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的”(Bate, 2009)275,同时“表面上它是两种宗教的二元对立,实则极其复杂、多面”(Vaughan, 1994)。奥瑟罗转宗失败,原因同样复杂,它涉及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崛起,出于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原因,英格兰王国逐渐向它靠近融合,一度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转宗者。随着逐渐感觉到威胁,英格兰王国开始怀疑、否认转宗基督教者的信仰是否虔诚,并希望借此在与奥斯曼帝国的较量中占据上风。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转宗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徒数量直线下降,《奥瑟罗》正是完成于此时,主人公作为转宗者的命运变迁正是英格兰王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以下简称“英奥关系”)的文本再现。
1. 靠近与融合:双重身份的转宗者
威尼斯主流社会曾积极接纳转宗者。以奥瑟罗为例,他亲述“蒙她父亲看得起,我常常应邀到她家去。他们问我一生经过什么事……这些故事,苔丝梦娜都听得非常认真”(莎士比亚,2015a)27—28。
奥瑟罗皮肤黝黑,这让学界常从种族角度解读本剧。实际上,早期现代的种族概念早已多元化,多与宗教等问题相伴共生,因此需要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才能准确定义。对应的,《奥瑟罗》的广阔性可从第一幕看出,它与《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theGreat)一样,虽故事发生在威尼斯,但所涉及的广阔地域赋予本剧全球化的视野。奥瑟罗的身份正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中。
虽然“摩尔人典型特征是黑皮肤”(Tokson, 1982),学界还有个词是“黑摩尔人”,黑皮肤的摩尔人常被认为来自非洲,且摩尔人进入学术领域也是作为非洲人,但非洲黑人并非都是摩尔人。莎评家A.C.布拉德雷(A. C. Bradly)在《莎士比亚的悲剧》(ShakespeareanTragedy)中认为摩尔人主要指与那些与奥斯曼帝国往来频繁且信奉伊斯兰教的非洲人。
具体来看,“摩尔人通常信奉伊斯兰教”(Vitkus,1997)。可推测的是,奥瑟罗极可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人。可举出的例证颇多:他送给妻子的手帕是埃及女人给其母的礼物;威尼斯派来特使委任卡西奥接替奥瑟罗的职位时,伊阿戈说他会带着苔丝梦娜回到马里塔尼亚(“马里塔尼亚”指古代北非地中海沿岸一带,还包括现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伊阿戈向布拉班修揭发奥瑟罗勾引其女时说,“难道你愿意你的女儿给一匹野马糟蹋吗?你愿意你的外孙只会像马一样撕叫?你愿意和野马攀亲戚吗?”(莎士比亚,2015a)14文中的“野马”指的是奥瑟罗,英文原文是“Barbary house”,即“柏柏里的马”,“柏柏里”指代的就是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区。因此,奥瑟罗的出生地可以进一步缩小为北非。相比非洲其他地方,北非与欧洲国家及奥斯曼帝国等联系更紧密,人们常用“摩尔人” 指代北非人,用“埃塞俄比亚人”指代非洲内陆人,用“黑摩尔人”指代西非人(Picard, 2004)。
奥斯曼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以下简称“土耳其人”)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因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得名,存在于1299年至1922年间,权力顶点在16—17世纪,当时领土覆盖从中东到东南欧洲的广阔地区,还有北非地区。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
奥斯曼帝国对英格兰人也颇具吸引力,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奥斯曼帝国版图横跨3个大洲,是英格兰王国一直试图拉拢的国家。英格兰王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两国不仅可以联合对抗欧洲天主教,且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地中海,英国商船频繁往来其间,双方交好对开展贸易活动有利。两国交好为当时的教徒提供了转宗的土壤。故在当时,许多基督教徒转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徒转宗基督教的情形也很常见,奥瑟罗便是其中一位转宗者。他以基督徒自居,并视“土耳其人”为“野蛮人”:“难道你们都变成了土耳其人,动手打起自己人来了?这样像野蛮人一样大闹,难道不怕丢了基督徒的脸!”(莎士比亚,2015a)52相比诡计多端的伊阿戈等基督徒,他表现得更虔诚。所以学界对其的评价是,他“虽外表黝黑,本质却是白色的”(Washington,1984)。
目前,多数评论将奥瑟罗看作“局外人”。但从英格兰王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互动中审视其身份变迁,他真的是个“局外人”吗?“局外人”是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宗教新政策推出后转宗者生存状态的写照。在更早时,他们是被两个世界定义的具有双重身份者。
这从《奥瑟罗》一剧选取的背景地中可见一斑。同时作为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入口的威尼斯公国既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紧密的商贸往来,又是基督教国家的忠诚盟友,外交政策中立、圆滑。威尼斯各国人士云集,因此这里的转宗者甚多,且转宗行为在这里更易被接受。莎士比亚选择威尼斯作为背景地,与这里对多元混杂身份的包容不无关系,“它建构了一种独特、封闭的空间,但又在更大范围的地理环境中……如同一个试验田,各种身份在这里相戏剧性地碰撞、摩擦、融合”(Bate, 2009)42。威尼斯又可以与伦敦类比,当时伦敦曾一度为来往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提供临时的避难所,如1536年受葡萄牙迫害的转宗者在这里继续保持精英商人的体面。英格兰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交好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转宗行为一度成为时髦之举,也因此,当时书写摩尔人的热潮此起彼伏,随处可见伊斯兰文化的身影,如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国国家的主要航行、航行和发现》(ThePrincipaliNavigations,Voiages,andDiscoveriesoftheEnglishNation)和理查德·克诺尔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史》(GeneraliHistorieoftheTurkes)等。据统计,这一时期,至少有61部剧作以奥斯曼帝国为主题:知名的有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帖木耳大帝》和《马耳他的犹太人》(TheJewofMalta)、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的《西班牙悲剧》(SpanishTragedy)、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亚历山德拉的盲人乞丐》(TheBlindBeggarofAlexandra)、乔治·阿伯特(George Abbot)的《对整体的简单描述》(BriefeDescriptionoftheWhole)、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的《阿尔卡扎之战》(TheBattleofAlcazar)等。16世纪90年代,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戏剧创作达到高潮,莎士比亚足有13部戏剧提及奥斯曼帝国、摩尔人或土耳其人。
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相遇,或通过战争,或通过贸易。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强大,欧洲国家逐渐感到威胁,这直接让英格兰人对转宗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 威胁与丑化:边缘化的转宗者
纳比尔·马塔尔(Nabil Matar)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土耳其,摩尔人和英国人》(Turks,Moors,andEnglishmenintheAgeofDiscovery)和《英国和柏柏里,1589—1689》(BritainandBarbary, 1589—1689)均展示了英国与奥斯曼帝国间的融合史实,但他在其《伊斯兰教在英国,1558—1685》(IslaminBritain,1558—1685)里笔锋一转,谈及后者崛起使前者产生的危机感。
马修·迪莫克(Matthew Dimmock)认为“奥斯曼(帝国)是欧洲潜在的威胁者,几个世纪以来,都没变过”(2005),且这种威胁无处不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1446年,奥斯曼帝国入侵希腊,攻占了科林斯,并于1478—1481年间,征服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都加剧了欧洲人面对奥斯曼帝国产生的危机感。随着版图的扩张,奥斯曼帝国逐渐掌控了地中海贸易,财富激增,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力上,欧洲国家都无法与之抗衡。虽然当时欧洲国家已在世界各地积极开辟新航线,以期发现更多“新世界”构建庞大的殖民版图,但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东方被西方所决定并不适用当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相反,欧洲国家时刻都有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恐惧。本剧中,奥瑟罗未经其父同意,就与苔丝梦娜私订终身,两人半夜同眠,奥瑟罗非法侵占苔丝梦娜的身体影射了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国家,并对当地资源进行掠夺的史实。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权势逐步达到顶点,欧洲国家的恐惧感越来越明显。宗教方面的体现则更明显。早在中世纪,基督教就意识到伊斯兰教的“威胁”,如在9世纪的《阿卡迪的道歉》(ApologyofAl-Kindi)中,基督教徒设法保护自己的信仰不受伊斯兰教的“污染”;十字军东征时期,土耳其人被视为异教徒。
英格兰王国是面积狭小又被欧洲各国天主教势力包围的岛国,领土和财富等各个方面均被奥斯曼帝国碾压,且多次遭受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据记载,奥斯曼帝国的海盗常常扣押往来地中海的英国商人和船员,或索要赎金,或将英格兰商人和船员出售,1592—1609年间,每年被奥斯曼帝国掠走的船只中有多艘来自英格兰,船员都是基督徒。这些被俘者为了活命、改善生活等不得不转宗伊斯兰教。虽然英国神职人员曾采取各种方式抵制这种转宗行为,如公开抨击转宗者的忠诚,甚至用爱德华·凯利特(Edward Kellett)和亨利·柏姆(Henry Byam)等例子树立基督教殉道者典型,但效果寥寥。除了被俘者,追随父母的孩童、为获自由的奴隶和文化的往来者等转宗者也同样众多。
英格兰人恐惧转宗伊斯兰教者,更恐惧转宗基督教者,对两者,尤其后者极尽丑化,宣称转宗基督教者是异教徒,攻击他们淫荡、叛逆、易怒暴躁又不忠诚,认为他们混迹于英格兰,威胁了基督教的纯洁性,甚至宣称基督徒与之交谈都是乱伦或堕落。因此多数英格兰人拒绝与其共享基督徒身份,并坚信无法与之和平相处。
在《奥瑟罗》中,布拉班修得知奥瑟罗要跟女儿结婚时说:“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把我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她害怕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喜欢!”(莎士比亚,2015a)20“假如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可以不闻不问,那不是让奴才和异教徒来当家做主,横行霸道!”(莎士比亚,2015a)21布拉班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担心与摩尔人通婚会威胁白人种族的纯洁性,同时这种担心中也有对转宗者无处不在的丑化。奥瑟罗的姓名“Othello”与奥斯曼“Ottoman”两个单词类似,而后者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者奥斯曼一世(Osman I 或Othman I)。奥瑟罗因嫉妒杀死苔丝梦娜,奥斯曼一世也声名狼藉,据传曾杀死众多妻妾等。
剧中最明显的丑化是丑化奥瑟罗的转宗之因。据剧中描述,奥瑟罗并非因经济、政治原因皈依基督教,促使他转宗的是对苔丝梦娜的爱。伊阿戈曾说:“摩尔人一定唯命是听——甚至可以使他放弃宗教信仰,放弃灵魂得救的希望——她的爱情已经锁住了他的心灵,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要他做或不做什么事;她的意愿成了他的上帝,他已经无力反抗了。”(莎士比亚,2015a)58最后他因为怀疑苔丝梦娜不忠贞而杀死爱人后自杀,自始至终,他处理爱情的方式不合规矩且极端、鲁莽。如奥瑟罗与苔丝梦娜“先斩后奏”,完全不符合基督教婚配的流程,对此,布拉班修说道:“我把我全心全意不愿意给你的人交给你,因为她已经是你的人了。”(莎士比亚,2015a)29奥瑟罗也算不上合格的爱人,他自陈:“我有一颗不太容易妒忌的心,可一旦有人煽风点火,我又会走极端,妒火一发不可收拾。”(莎士比亚,2015a)134他受伊阿戈欺骗,杀死无辜的苔丝梦娜,后虽醒悟但为时已晚,奥瑟罗因爱情而起的转宗最终因爱情覆灭而失败。
因爱转宗是诋毁转宗基督教者常见的主题。当时作品如《欲望统治》(Lust’sDominion)、《转宗基督教的土耳其人》(AChristianTurnedTurk)、《暴食者》(TheRenegado)等均是如此。此时,转宗被蒙上色情目的,意在暗示信徒的性堕落,奥瑟罗堪称其中代表。伊阿戈说他“好色”(莎士比亚,2015a)45,罗德里戈说他“不要脸”(莎士比亚,2015a)15,布拉班修则指责他“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用什么迷魂汤灌进了她的心里,才让她做出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情!”(莎士比亚,2015a)20这里“迷魂汤”可能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民众十分喜爱的土耳其咖啡,当时有流言说它不仅让英格兰人的肤色变深化,还会“污染”他们的道德。这在1672年的《反对咖啡,或土耳其的婚姻》(ABroad-sideagainstCoffee;Or,theMarriageoftheTurk)、1663年的《少女们控诉咖啡》(TheMaidensComplainAgainstCoffee)和1700年的《家庭主妇抵制咖啡》(TheCity-WifesPetitionagainstCoffee)等中均有详细描述。
可以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英格兰王国包容转宗者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英格兰人从对转宗基督教者的丑化逐渐变为怀疑、否认、打压、迫害,以期让无数转宗者在试探中暴露其基督教信仰的虚伪。也因此,在莎士比亚看来,奥瑟罗正如本剧副标题所述,始终都是“威尼斯的摩尔人”。
3. 试探与暴露:失败的转宗者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步步威胁和大量转宗基督教者进入英格兰,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也是英格兰王室重臣的埃德温·桑迪斯(Edwin Sandys)在1605年的《欧洲反射镜》(EuropeanSpeculum)中,哀叹基督教世界的教派分裂与无能,并呼吁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要以基督教为核心紧紧团结,战胜奥特曼帝国。他得到了民众和政府的积极响应,如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被重提。勒班陀海战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海战之一。在这次海战中,奥斯曼帝国大败。战后英格兰大肆庆祝胜利。虽然这种胜利并未持续太长,很快奥斯曼帝国就重获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但这次海战的意义在于它是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能力的例证。
17世纪起,英格兰基督教进入排斥异己的时代,基督徒到处散布言论说转宗者绝非基督徒,他们只是表面信仰基督教,内在依然忠于伊斯兰教,甚至一定程度上,表面越虔诚的转宗者,越表里不一,因为他们需要伪装欺骗基督徒。“他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但这么做或出于恐惧,或只是单纯想活命而已……私下里他们还是老样子,内心依然是抗拒基督教的,直至去世都不会变”(Prynne,1656)。随之到来的是一个揭露虚假转宗者的时代。
《奥瑟罗》中,得知女儿深夜外出幽会,布拉班修喊道:“我要抓你去进行审判,惩罚你这个欺世盗名、违法犯禁、伤风败俗的罪人。——抓住他:他要是敢反抗,就制服他,让他自食苦果。”(莎士比亚,2015a)21在当时的英格兰,一旦发现转宗基督教者并不虔诚,那他们立刻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严重者甚至会被驱逐出境,此举是要将他们中间真正的基督徒挑选出来。英格兰的政策效仿自西班牙。1568年,转宗基督教者联合起来发动暴乱,占领了西班牙的格拉纳达,这就是著名的“阿尔普哈拉斯叛乱”,此后,无数转宗者被西班牙驱逐出境,尤其西班牙宗教法庭更以擅长处理此类异端著称。在《奥瑟罗》中,布拉班修所言“进监狱去,等到法庭正式开庭,传唤你的时候再说”(莎士比亚,2015a)21,说明这段历史可能给了莎士比亚灵感。这场暴乱之后,西班牙不断敦促英格兰吸取教训,抓捕那些虚假转宗者,扣押其财产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忧惧已久的伊丽莎白一世于1599年到1601年间颁布法令,规定驱逐的对象中包括了转宗基督教者。
作为转宗基督教者,奥瑟罗一直备受怀疑,虽然他宣称自己为虔诚的基督徒,但在别人眼里,他始终都是摩尔人。
莎士比亚处处埋伏笔,暗示奥瑟罗并未放弃伊斯兰教,如奥瑟罗被指控使用魔法。基督教世界认为转宗者不仅没有放弃伊斯兰教,还经常秘密进行伊斯兰教的仪式,以示忠诚。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些仪式常被看作巫术、魔法,都是主流社会指控转宗者为异教徒的借口。布拉班修指控奥瑟罗对女儿施了魔法:“假如你不是用歪门邪道……让全世界来评评看,看这是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假如你不是用了什么左道旁门的秘方邪术,迷惑了她娇嫩的心灵,削弱了她行动的能力,你可能做得到吗?”(莎士比亚,2015a)20“她被人用歪门邪道的魔法妖术偷走,受到糟蹋蹂躏。……如果不用妖术魔法,怎么可能犯下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呢!” (莎士比亚,2015a)24,奥瑟罗则坚决否认:“我绝没有用过什么迷魂汤药、魔法妖术,还有什么歪门邪道。” (莎士比亚,2015a)24“我知道她爱上了一个经历过千难万险的男人,而我爱她却是因为她对一个历经磨难者的深刻同情。这就是我所用过的魔法邪术。” (莎士比亚,2015a)29再如在西班牙驱逐转宗者期间,保留《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相关的物品的人都会被严惩。剧末,奥瑟罗却提及自己留有一把剑:“我在房里还有一件武器,是把西班牙宝剑,在冰川雪水中淬炼过。”(莎士比亚,2015a)130“从来没有哪个战士用过比这更好的剑。我用这条胳膊和这把利剑杀出过重围,比你们多20倍的人也阻挡不了我突围。” (莎士比亚,2015a)130据记载,在公元624年的巴德尔战役中,穆罕默德被敌军包围。大天使加百利突然从天空现身,赐予穆罕默德一把神剑,帮助其军队反败为胜。战后,穆罕默德将此剑赐给他最信任的追随者和女婿阿里·本·艾比·塔利卜,让他代替自己用剑传道。此后,剑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著名历史学家汤姆·霍兰(Tom Holland)的《剑的阴影下: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和古代世界的终结》(IntheShadowoftheSword:TheBattleforGlobalEmpireandtheEndoftheAncientWorld)一书就讲述了伊斯兰教发源、阿拉伯帝国兴起的故事。莎士比亚是熟悉这个典故的,在《威尼斯商人》(TheMerchantofVenice)中,他还写了摩洛哥王子对着月牙宝剑起誓这样的情节。奥瑟罗暗自保留这样一把宝剑,其意图不言自明,这是其伊斯兰教徒身份的象征。此剑出现在他自杀之前,暗示他最终认回并在基督徒面前展示自己的伊斯兰教徒身份。
转宗基督教者在英格兰处境艰难:“他们不仅被英国剧作家、牧师、神学家等丑化虚构……且一旦有冲突,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基督教。”(Matar, 1998)奥瑟罗曾感叹道自己无法掌控命运,其命运为基督教徒一手操控。这需要从其转宗意图说起,他并非为真正信奉基督教而转宗,而是出于对苔丝梦娜的爱转宗,随着他杀死妻子,其转宗也随之结束。可以说,苔丝梦娜一手操控了其行为,而苔丝梦娜是基督教徒,面对夫君“你难道不是个婊子吗?”的指控,她反驳:“当然不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要为天主也要为我的夫君保持我身体的冰清玉洁,不受非法的玷污,怎么可能犯下亵渎天主的罪名呢?所以当然我不是。”(莎士比亚,2015a)104。两人的婚姻象征的是两种宗教的融合,苔丝梦娜的温柔美丽吸引奥瑟罗为其转宗基督教。可是布拉班修曾提醒奥瑟罗:“要把她看紧了,摩尔人,她欺骗过她的父亲,小心也会骗你呀!”(莎士比亚,2015a)33,伊阿戈也曾添油加醋:“你想想看,她这么年轻,就能这样巧妙地蒙蔽她的父亲,就像用橡树叶子蒙住他的眼睛一样,使她父亲误以为你用了什么妖术魔法。”苔丝梦娜说自己犯的罪就是爱上了奥瑟罗,暗示英格兰社会对接受、纵容改宗者的悔意。第五幕第二场,面对洛多维科的审问,奥瑟罗招供:“我行凶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做人。”(莎士比亚,2015a)132如果说奥瑟罗与苔丝梦娜的较量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的较量,此言说明在他心里,意欲杀死的不是苔丝梦娜而是基督教,以期摆脱基督教的束缚,回归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另外能够体现基督教之于伊斯兰教胜利的还有伊阿戈对奥瑟罗的操控,正是由于奥瑟罗听信了伊阿戈的谗言,他才杀死妻子,酿成悲剧。
奥斯曼帝国在勒班陀海战中是被基督教国家打败的一方,在《奥瑟罗》中同样有所体现。莎士比亚虽没有详细描述交战的过程,而以寥寥数笔交代了威尼斯获胜的消息:“有好消息,大家请听!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狂风暴雨给了土耳其人怦然一击,挫败了他们的图谋。威尼斯来了一艘大船,看见土耳其舰队给风暴打击得七零八落的惨状。”(莎士比亚,2015a)37这样的处理一箭双雕,一方面弱化了摩尔人英勇善战的形象,表明奥瑟罗在这场战争中展示才能的空间缺失。另一方面,暴风雨的出现使得威尼斯获胜:“从来没有这样的狂风暴雨震撼过我们的城墙。如果风暴在海上也这样咆哮,那再牢固的橡木船也吃不消这大山压顶的海浪呀!”(莎士比亚,2015a)36。这让人想起1588年,海上突现风暴,使得英格兰的舰队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英格兰的崛起被看作“神意”。在《奥瑟罗》里,决定战争胜负的并非参战者是否勇猛善战,而是“神意”,这间接肯定了“神意”对英格兰基督教的支持。
可见,此时的英格兰不仅对转宗基督教者态度大变,对转宗伊斯兰教者也是如此。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1604—1610年的《西方世界的美丽少女》(TheFairMaideoftheWest)、约翰·梅森(John Mason)1607年的《土耳其人》(TheTurke)和菲利普·马斯金尔(Philip Massigner)1624年的《叛变者》(TheRenegade)等中均有此类描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4. 结语
学界对英格兰王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研究不多,对莎士比亚笔下的摩尔人形象的研究也不多。莎士比亚共有13部剧作提及奥斯曼帝国、摩尔人或土耳其人。如在《理查二世》(RichardⅡ)中,卡莱尔主教说:“荣耀的日子永远看不到了。好多次,流亡国外的诺福克在光荣的圣战中为耶稣基督而战,在猎猎飞扬的基督教十字旗下,抗击着邪恶的异教徒、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莎士比亚,2015b)在莎士比亚笔下,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摩尔人,多为负面形象,如《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Andronicus)中的阿戎是哥特女王的邪恶情人,“已做了坏事一千桩,我乐在其中,就如拍死只苍蝇一样”(莎士比亚,2015c);《威尼斯商人》中的摩洛哥王子因皮肤黝黑被鲍西亚嫌弃,“谢天谢地……但愿所有和他同肤色者都选错匣箱”(莎士比亚,2016);《奥瑟罗》中的奥瑟罗虽勇敢忠诚,最后却沦为穷凶极恶的“杀人魔”;等等。
莎士比亚借奥瑟罗这位由伊斯兰教转宗基督教者从与威尼斯主流社会融合靠近,因威胁被丑化,最后暴露伊斯兰教徒身份的过程,表达了对他们的态度。
当然,这种态度与莎士比亚自身的经历有关。英格兰庆祝勒班陀海战的盛大场面给还是孩子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驱逐转宗者的法令他一定熟悉。1603年,詹姆斯一世1603年继承英格兰王位,相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更加厌恶奥斯曼帝国。早在他1591年的长诗《勒班陀》(Lepanto)里,就盛赞大胜土耳其的威尼斯。继承王位后,詹姆斯一世积极推行“和平政策”,修补与欧洲诸国的关系,尤其将长诗《勒班陀》的写作看作促进英格兰王国与欧洲其他基督教国家结盟的和平之举动,再次大力宣传这首长诗。《勒班陀》随之大热,人人争相传阅。《奥瑟罗》不但是莎士比亚参阅和增补了吉拉尔·迪辛西奥(Giraldi Cinthio)1563年的小说集《百则故事》(GliHecatommithi)中的第七个故事《一位摩尔上尉》(UnCapitanoMoro)、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Knollys)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HistoryoftheTurks)、路易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的《奥兰多·福瑞奥索》(OrlandoFurioso)和约翰·雷奥·阿弗里卡纳斯(John Leo Africanus)的《非洲地理史录》(AGeographicalHistorieofAfrica)等后完成的作品,而且是受作者自身经历及詹姆斯一世的《勒班陀》等影响完成的作品,反映了摩尔人,尤其转宗者在英奥关系变迁中的多舛命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迎合詹姆斯一世政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