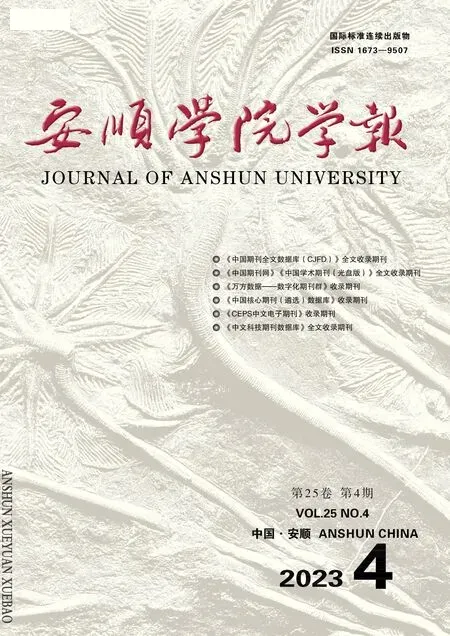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
龙 潜 李益茜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性别意识与乡土叙事
地理位置的僻远与自然条件的恶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贵州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位置的闭塞让其地域文化得以保存。贵州各民族文化争奇斗艳,呈现出一片繁华的盛况。21世纪以来,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取得可喜成绩。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中,郑欣、王华、肖勤、杨打铁和崔晓琳、聂洁、幺京等一批女性作家前后出现,她们以女性独到的眼光聚焦于时代生活,用女性细腻的笔调窥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厘清世俗生活与文学世界相纠缠的脉络,使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呈现一片光亮。
20世纪90年代,一批年轻女作家以身体叙事进行写作,创作出一些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但这种私人写作最终走入封闭的圈子,消失于文学视野。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谋求新的写作道路,关注现实生活。她们把笔触伸向乡土,从女性的视角去描摹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乡村风俗和世态人情。女性视角的介入使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对乡村历史与现实的叙述呈现新的美学特质。乡土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中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从狭义讲,指以故乡生活、乡村面貌等为题材创作出的具有泥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从广义说,指一切书写乡村生活世界的文学形态。乡土文学作为主流文学延续了近百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质。从20世纪30年代的蹇先艾到20世纪80年代的何士光,贵州的乡土文学以男性话语为主,经验主体和表达主体的性别身份单一,文本中呈现出的人物形象以男性为主,作家主要从男性的视角建构小说话语体系。由于性别和社会环境的差异,男女作家建构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女性性别意识与乡土叙事的融合,打破了贵州乡土小说以男作家为主导的创作局面,使乡土小说在性别上具有双重视角。女性乡土叙事成为新的创作潮流,丰富乡土文学创作内涵与形式。性别意识不独属女性群体,男性同样具有性别意识。但更多时候它是与“女性”同时出现的。这既体现出将女性视作“第二性”的传统思维逻辑,又反映出女性自身反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强烈诉求。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中展现出来的性别意识有:一是女性成为“主角”。虽然以往乡土小说中不乏乡土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只是男性构建小说故事内容的一个“配角”。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作家开始关注乡土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重塑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女性真正意义上成为小说“主角”。二是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时带有自我审视的眼光,她们更加关注女性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三是不回避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艰难。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叙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深刻剖析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的弊端,直指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困难,表达出作家对女性前途命运的探索与思考。“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的崛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将性别意识带入了有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1]女性文学与乡土叙事两个因素在21世纪贵州小说创作潮流中同时显现,二者并非是简单相加,从更深层次来讲,二者之间的内部联系密切,在相互融合中构建了女性乡土叙事的独特话语体系。
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用性别书写却又超越性别意识,着眼于人性之本质的探寻与追问。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加入让贵州乡土叙事文学进入更广阔的视野。性别意识与乡土叙事交织形成的关系展现出作家的书写立场、写作姿态和审美追求。
二、多重文学主题的呈现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把握主流文学的同时又融入自身地域体验,从时代主旋律、城乡关系、民族民俗角度书写文学主题。从文字中感知时代面貌,传递时代精神。
一是主旋律下的家国史。郑欣的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获“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贵州省首届文学奖”、贵州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艺报》发表系列评论展开讨论。《百川东到海》[2]是一个史诗性的作品,讲述北洋军阀覆灭之际,第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对革命道路的摸索和人生的爱恨纠葛。作者以唐氏家族的兴衰折射一个时代的沧桑变化,诠释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正确选择的伟大主题。大浪淘沙后,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抉择后的人生,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百川归海,滚滚向前。这是时代摧枯拉朽的过程。小说中三条线索齐头并进,塑造众多具有生命温度的人物,还原历史真相。在虚构与真实中剪裁故事,凸显小说的张力。第一条线索由大儿子唐淳衷完成,他贪图享乐,不谙世事,没有理想信念与伟大抱负,最后被社会吞噬。第二条线索以二儿子唐淳祐为主,因家族被卷入政治风波致使父亲遇害,决心为父报仇,放弃留学,进入黄埔军校,随后加入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重新审视个人与革命,明辨历史发展趋势,最终走向中国共产党,为天津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第三条线索以三儿子唐淳袏的成长经历铺展开,作为首批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年轻人,他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坚定革命信念,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小说将诸多历史事件与唐氏三兄弟的人生相交织,呈现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廊。作品叙述了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众多历史事件,把历史的深沉厚重写进小说,荡气回肠、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
《百川东到海》不仅有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社会价值,还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古典传统的融入让小说厚重且绵实,小说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小说前部分写唐氏家族的生活,这与贾府由繁荣走向衰落极其相似。作者在小说中也直接引入《红楼梦》中的一些手法技巧。曹雪芹在塑造王熙凤这一人物时,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成就了王熙凤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郑欣巧妙的借鉴这种手法,精心设计了方大总统公子方可为的出场。如果说王熙凤的出场代表的是封建制度下女性间的一场较量,那么方可为的出场就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暗潮涌动。小说文字细腻、富有古典韵味,以书香门第孟家两个女儿的出场开篇,环境、玩物、语言都带有一种书香气息。小说并非只是书写宏大的革命历史主题,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让小说更加具有生命力。孟敏之温柔、睿智,挑起家庭的重担,成为唐淳祐的坚强后盾;顾蕙茗却在历史中迷失自我,最终结局悲惨;翠仙有着传统文学中青楼女子不羁的个性,也有现代莎菲女性的自觉。文学是人的艺术,《百川东到海》呈现出的女性形象系列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这些人物的生死悲欢牵绊着读者的情思。小说的空间转换与故事情节的推进相得益彰,早期人物主要活动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者们遭到逮捕,被迫转移阵地。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空间也由城市转到农村,这也预示着农民阶层走向革命的可能,跟随小说中个体的行动轨迹与革命形势的走向,小说的空间涉及北京、天津、聊城、遵义、重庆、延安等各地区,辐射出各阶层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作品奏响时代和个体相交织的生命旋律,凸显丰富意蕴,传达家国情怀。
二是城乡关系的冲突与和解。“乡土世界不再作为自然村舍和自然群落独立于世外,古老的、静态的、凝滞的‘传统社群’在现代化的逼迫下,处于不断的变动和重组中”[3]。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农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涌入城里,不幸的是,城市不是伊甸园,处于城市底层的打工人慢慢失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20世纪60年代,美籍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4],这部小说用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写生态环境被污染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向人类提出严重警告,这部作品也是生态文学诞生的标志。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她始终关注乡村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关注生态环境变化。作品不断见诸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山花》等,曾两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王华在《回家》中叙述了一群由城市返乡的打工人故事[5]337。管社会无论如何也要买一张卧铺,前两次回家他都向母亲谎称自己是坐卧铺回家,他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让他们心安。第三年回家他买上了卧铺,但由于手中没有钱,只能买到娄底的卧票,辗转回到村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是生存的艰难。王华借这篇小说谈论了经济危机下,打工人难以在城市立足,被生活蹂躏后无奈回到农村的现实问题。随后,她发表长篇小说《雪豆》,这是一部与生态危机紧密相关的作品,揭示经济迅速发展后留下的弊病,启发人们对未来命运的思考。《雪豆》讲述几十户村民为谋生搬到桥溪庄,但这个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巨大烟囱喷出的灰笼罩整个村庄,由于长期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村民患上各种怪病;桥溪庄自从最后一个健全的孩子雪豆出生后就没有新的生命到来;在无数次的挣扎后,一批桥溪庄村民无奈离开,寻找生命的住所。[6]作品描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带给人类的灭绝性灾难,表现人们渴望救赎,渴望重生。王华的《在天上种玉米》讲述一个村庄向城市整体迁移的故事,这群农民有着向往城市的梦想,房东看到自家房顶一片片玉米林时的妥协则体现了城市人的田园梦。[5]127王华在女性的人文关怀下展现出一幅和谐的图景,那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玉米林是“城乡融合”的象征。
三是对陨落的民俗文化的复活。钟敬文提出:“民俗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传承的生活文化。”[7]民俗随着民族的历史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以一种流动的姿态而存在。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将民俗文化带到文学创作中,彰显民俗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肖勤先后在《当代》《十月》《小说选刊》《民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棉絮堆里的心事》《霜晨月》《丹砂的味道》《云上》《暖》等几十部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其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蕴。
肖勤作为仡佬族,对本民族文化无比崇敬,她渴望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到民族历史的记忆,挖掘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她穿梭于历史的幽径,解读民族代码,追忆一代代仡佬族人的生活。《丹砂》中的“我”出生时,奶奶刚好离开人世,这让“我”的身份更加神秘;而“我”的行为也是非常怪异,晚上清醒,白天睡觉,总是重复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梦里有一片红色海洋,堂祖公给“我”冲傩时,“我”一进门就要屋里藏着的“红色东西”;对“我”而言,丹砂是身体不可或缺的元素“锌”,我在丹砂的滋养下走出大山,奔向外面的世界;对于堂祖公老一辈的人,丹砂是他们的“命”,是一种身份象征,堂祖公在死时都因没有借丹砂给奶奶而愧疚自责,寻找丹砂也是在寻找远去的仡佬族文化。[8]235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奇特而神秘,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不断流失,语言、建筑、服饰、节日等元素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以肖勤为代表的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怀着对民族的信仰与崇拜进行文学创作,期望重拾民族文化的碎片。肖勤在《你的名字》,通过塑造冯愉快、滚月光、袁百里三个性格身份迥异的人物,连接起底层社会、村寨、基层权力机关三个不同场域,写出社会的不公、生活的沉重、欲望的膨胀和权力间的较量[9]。肖勤用真挚的情感和执着的姿态,用质朴坚实的语言叙述乡土中的人们迈向现代文明时遇到的种种困惑和抗争,书写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传承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
三、多种艺术手法的探索
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植根现实土壤,用文字记录时代变化,同时,她们借鉴吸收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小说内容,增强小说艺术感染力量。
一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注重小说真实性、典型性,关注现实人生。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一直贯穿其中,她们关注地域文化、苦难叙事、底层书写。王华的《傩赐》、肖勤的《暖》、崔晓琳的《东一街》、幺京的《彩蝶飞舞》和聂洁的《我在老鸹林》都是取材于黔地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展现贵州独特的地域特点,一方面关注环境中人的生存状况。这些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亲眼见证贵州乡村近几十年的沧桑变化。贵州的乡土杂糅了新与旧、苦难与温情,在走向现代化时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作家们用女性温柔情怀细数乡土点滴,她们的创作有意识地对本民族文化、风俗、语言进行展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一部好的作品往往隐含着作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达出对人的关怀。王华的《傩赐》表达作者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对陋俗的鞭挞[10];崔晓琳的《东一街》讲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揭示现代化浪潮带来的时代变化和精神困惑,是对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11];幺京的《彩蝶飞舞》讲述黔东地区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当地独特的风俗文化[12];聂洁的《我在老鸹林》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记录老鸹林的发展变化[13]。女作家们展现出在新的审美观念下对乡村书写的新探索,挖掘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探寻贵州乡土精神中生生不息的文化要素。
二是借鉴吸收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5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掀起了魔幻现实主义浪潮,该创作方法在拉美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并传入国内。一些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受其影响,少数民族身份更为她们的创作添上一种神秘文化色彩。王华的《雪豆》、肖勤的《丹砂》创作手法都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雪豆》的“魔幻”主要体现在故事背景的神秘与故事情节的荒诞上。《雪豆》中的桥溪庄充满“魔幻”色彩,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笔墨写村庄的怪异。桥溪庄多年不下雪,村庄周围都在飘雪,但桥溪庄的上空依旧不见雪的影子。作者笔下的桥溪庄永远死气沉沉,整个村庄充满异样。在情节上,“雪豆”是桥溪庄最后一个健康出生的婴儿,这个人物带有一种神秘性,刚出生时她就会喊“完了”,在母亲咳嗽严重时开口会说“妈,不死。妈,不死”。“雪豆”身上被赋予某种象征意味。桥溪庄“雪”字辈的人命运不同,但都蒙上了一种神秘而悲惨的色彩。雪山为雪豆偷猫不幸被砸傻,雪果因雪朵的离去、田妮的逃跑而变得非常怪异,最后对母亲和雪豆犯下乱伦之罪,被李作民砍掉一只脚板,后来雪果悄悄地离开了桥溪庄,而桥溪庄的人都疯疯癫癫,得了各种怪病,“魔幻”的色彩始终笼罩桥溪庄。肖勤的《丹砂》中同样有一种“魔幻”的气息。“我”在奶奶刚死之时毫无预兆地来到世上,只在白天睡觉,经常做相同的梦,而梦中的红色海洋让我如痴如醉,“我”的堂祖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说“我”身上附有“我”奶奶的魂,他对着我喊“崽他奶”。作者在真假变幻中显示出现实、希望与幻想之间的紧张冲突,使文本呈现荒诞性。作者直面荒诞、用节制陌生化的语言将魔幻现实主义渗透于文本中。
三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的运用。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传统的小说观念和形式被弃如敝履,他们用游戏化的姿态对待小说语言的使用和文本呈现,在叙事上以元叙述和碎片化的策略打破传统小说的封闭性和完整性,用各种体裁、话语的杂糅和拼凑打破小说的体裁界限。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小说本身是虚构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局限情节的逻辑顺序,虚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融为一体,力图从内部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解构,建立新的叙事模式。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并非是一个整体,而是由零散的碎片拼凑而成,这种认识下后现代主义小说故事的完整性也被破坏,这些小说家呈现的作品是由混乱的故事碎片构成,这与传统小说叙事主张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逻辑性截然不同。布依族女作家杨打铁的小说突出特点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运用,获“骏马奖”的作品《碎麦草》[14]就是最好的体现。“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零度写作是一种直陈式写作,叙述者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讲述笔下的故事,给读者一种没有温度的情感体验,让人难以把握写作者的立场。”[15]杨打铁用后现代主义构建了另类的文学磁场,她的小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情节破碎。《碎麦草》中情节跳跃,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存在,作品像无数个故事拼凑在一起。从杨打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对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也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四、体悟日常生活中的文学价值
崔晓琳、聂洁、幺京三位女性作家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在平淡悠长的日子中讲述时代变迁,展现人与命运的漫长对决。她们的作品呈现一种绵密、细致、内敛的叙述气质,善于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像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雷蒙德·卡佛等艺术家都擅长将日常生活的书写作为创作的重要内容,对生活进行文学性关照,构建一个日常生活间隙中的诗意世界。日常生活,是与众生最贴近的生存之地,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与忘却的现实。作为生存空间,日常生活展现出一种琐碎、真实、新奇的状态,最能反映时代生活的变化和人的精神困境,是当下现实的真实写照。在众多文学经典作品中,作家们更倾向于把日常生活作为叙事背景呈现。崔晓琳、聂洁、幺京充分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把生活细节纳入话语体系,找回生活本体的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乡村在衰败、在改造、在重生,乡村日常生活的变化演示着中国时代文化形态的变化。书写乡村日常生活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描写,彰显乡村在变与不变中始终保持着的蓬勃生命力。文学不应该只写那些宏大主题,更应该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的细节,抓住日常生活也就抓住了叙事的重要内容。
崔晓琳的短篇小说集《东一街》把故事定格在一条充满人间烟火的小街巷,小说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有平淡日子里普通人的生生死死。崔晓琳把普通人请上舞台,上演了一个个琐碎而又真实的故事。《金镯子》讲述婆婆与新媳妇的暗自较量,如何才能让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代人消除对彼此的顾虑,让两颗陌生的心真正靠近。《如果就此老去》写一个家庭破碎后,彼此之间的牵挂。“我”的父亲是神一样的存在,是有知识、有气质的男人,母亲其貌不扬,整天唠唠叨叨,但任劳任怨。“我”的父亲选择离婚,母亲从此独自生活,但是母亲一直默默守护着他,任何节日都要“我”去陪父亲说话、吃饭,关心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有着庸常、平凡、孤独的生活处境,也有着自尊、固执、善良的性格。母亲身上的温暖让整篇小说散发人性的光辉。他们终将在爱与被爱中释怀。
聂洁《我在老鸹林》讲述一个真实存在的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也是她用心建构的文学世界。她用“村落志”的文字记录乡村的地理空间与日常生活,在前进的历史潮流中留下自己的生命体验。聂洁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去看待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借助大量真实存在的人物讲述“老鸹林”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化,为读者呈现一个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勾连的乡村。聂洁用一个中立者的姿态记录,尽可能还原现实真相,揭示现实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聂洁用文字记录老鸹林人们生活的种种景象,关注这群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如何寻找生活的出路。
幺京的《彩蝶飞舞》取材于黔东少数民族生活,读她的文字如沐春风,她笔下的生活明亮,作品中传达出生活的温度。她用锐利的眼睛挖掘时代变迁下的日常生活,作品中跳跃的是她炽热的青春以及体察生活后的感悟。《猫眼》中,李卫国和妻子在偏远的地方当驻村干部,帮扶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而把年幼的贝贝交给行动不便的母亲照看,贝贝意外受伤,夫妻俩无比自责,为时刻关注家里的情况,特地安装摄像头,父母和孩子之间通过那小小的猫眼传递着对彼此的挂念。近些年,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有关乡村扶贫题材的作品,一方面,这是时代现实的写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这些作家的时代自觉。
五、“土地”意象及其内涵
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小说中意象繁多,烘托出浓厚的地域色彩与多姿的风俗民情,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审美范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16],这里“意象”即表意之象,指用来表达某种观念或具有哲理的艺术形象。庞德认为意象是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意象承载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意蕴。在众多的乡土小说中,土地始终作为核心意象被阐释。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乡村植根于土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人们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斗争,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土地文化史。作为一种物质生产资料,土地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真实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土地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原点。在人类长期发展形成的话语系统中,土地的含义又远远超过其自然属性,承载着内蕴丰厚的文化原型。在现代化语境中,土地衍生出诸多的联想物,代表生命、故土、母亲、原乡等文化命题。“土地”意象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含义,是人类精神的符码,在社会现实意义、审美特质、价值立场上有重要作用。从文学表现看,“土地”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存在于中外文学视野中,由于国别、地域、种族的差异,作家们赋予土地的内涵也有所不同。艾略特笔下生成的是辽阔的荒原,而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的是“麦地”“商州”“东北高密”等精神原乡。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土地的文学书写更具表现性、意义更加丰富。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受到城市化、商业化的冲击,城市的价值观念体系日渐侵蚀乡村的伦理价值,现代生产方式改变传统的农耕方式和土地的自然属性,土地的重要性遭到质疑。新一代农民放弃土地,奔向城市寻求新的生存方式。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把土地作为文本内容的核心意象,进一步探讨人和土地的关系。王华《傩赐》《在天上种玉米》《回家》和肖勤的《暖》《霜晨月》等作品中反复出现“土地”这个意象。她们以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乡村巨变的现实,反映21世纪的农民关于土地观念的变化,描写在历史变迁中农民对土地情感变化的轨迹。
21世纪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中土地意象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人与土地的疏离两种状态。第一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在传统观念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土地是衣食住行的重要载体,是漂泊者的精神原乡,对土地的眷恋与依赖是人的天性,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对土地的热爱早已烙印于心。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文本中就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崇拜与依赖。《傩赐》中的村庄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但是傩赐庄的村民辛苦耕耘于那片土地,从未埋怨、从未想过逃离。《在天上种玉米》中,年轻一代带领整个村庄搬离农村,实现了从土地谋生到打工谋生的过渡,但以王红旗为首的老一辈却放不下“土地”,于是他们在异地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第二是人与土地的疏离。随着社会转型,世代在土地上挣扎的农民选择逃离家园,寻找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在乡村和城市相互流动的过程中,作家们关注到土地意识弱化、农民身份缺失等问题。王华《回家》中,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经济危机的到来让他们难以在城市立脚,无奈之下又回到乡村,由于土地转租与撂荒,他们很难回到土地,于是这批人就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艰难寻找出路。究竟何去何从是小说中这批人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作者的发问。肖勤的《暖》以商业化冲击农村,一批农民流向城市为写作背景。他们对土地价值持怀疑态度,于是失去了耕种的热情。事实上,人们对土地的疏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于经济发展,人们不再需要将土地视作唯一出路,人与土地的感情也随之破裂。贵州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没有一味地去营造乡村诗意化的田园生活,也没有去揭露乡村愚昧与落后的精神状态,她们只是把故事的背景建构在自己熟悉的地域,将土地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去阐发自己对土地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